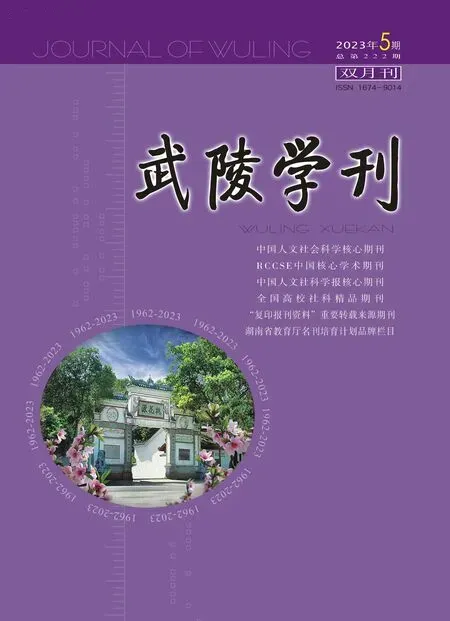新物质主义视域下的生命伦理与审美嬗变
——基于21 世纪以来身体物质性话语的考察
赵炎秋,刘 帅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21 世纪以来,新物质主义①(New Materialism)因其跨学科的批评理路和极具现实性的理论关怀,成为塑造哲学、社会学以及文学等多学科理论前沿的思想热潮。当下这一热潮正在穿透文化读本的边界,与我们新型身体动态产生着惊人的共鸣,进而在心脏移植、基因改造以及人脑接机等身体事件中,召唤出全新的理论议题和批评话语。
新物质主义与全新身体动态的耦合,生成了“身体物质性”(the materiality of body)这一论域宽广的议题及其系列相关话语。回溯21 世纪以来西语学界中关于身体物质性的讨论,以让- 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斯塔西·阿莱默(Stacy Alaimo)以及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为代表的众多理论家,都致力于在不同的身体事件中揭示新型身体伦理,在跨躯体现象的哲学反思中建构新型审美观念,进而提出了“复数生命”“跨身体”“赛博格”等理论概念。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表征着西语学界内新物质主义与身体动态正发生良性的理论互动。而自2010 年以来,汉语学界也陆续出现了一系列关于身体物质性话语的研究成果②,不同学者从媒介、影像以及文学等源点对身体物质性话语展开了理论阐释。但总的来看,大部分研究都着眼于个别身体物质性概念,而未能兼顾到作为含括性话语的“身体物质性”的整体内涵与理论意义。基于此,本文将以整体性视野聚焦当代身体物质性话语的建构与衍进历程,试图耙梳其理论流变过程,厘清其核心假设,并由此展开新物质主义视域下的生命伦理和审美嬗变分析,以进一步推进身体物质性话语在当代的传播与接受。
一、身体物质性话语的缘起与衍进
身体物质性话语的兴起,与20 世纪末期生物医学、生物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学界多将20 世纪末确认为身体物质性话语发展的重要节点。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信息学的迅速发展,生命科学获得了以前只为理论物理学保留的特权地位,而这也推进了人文社科领域中的思想家开启生命物质性质、地位等问题的思考议程。
1993 年,美国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出版《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其间她游走于性别研究与身体研究的交叉领域,开启了“身体物质性”话语的建设和探讨任务,这也标志着“身体物质性”这一概念在当代人文领域的正式出场。巴特勒延续了前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中对身体建构论的批判思路,认为透过性别这一载体,我们可以发现身体仍陷于建构主义的泥沼。由此她提出了一种重返物质的主张,她强调“对于建构的这些概念,我主张重返物质(matter)概念本身,不将其看作一个场域或表层,而视其为一个物质化过程,其最终的稳定产生了我们称为物质的边界、固定性与表层”[1]。巴特勒的研究立足于20 世纪末期现代生物学与医学的发展,两性的生理差异被各种新型生物技术发现、佐证,因此她也拒绝将性别或身体视为一个静态事实,而主张将其视为一个正在生成的物质实体。巴特勒这一观点,至少从两个方面影响到了21 世纪的身体物质性话语建设:其一,基本确立了身体物质性话语的学理核心,即强调身体向物质世界的回归;其二,基本形成了身体物质性话语的学理倾向,即在对激进建构主义的批判中,重新描绘物质实体生成的动态过程。
进入21 世纪,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超速发展,不断改写着我们理解物质世界和人类身体的现实语境:一方面,随着生物细胞学和量子力学的迅速发展,“在生命科学和物理学中,物质现象越来越多地被概念化,不再是离散实体或封闭系统,而是开放的、复杂的、有着广阔边界的系统”[2]15;另一方面,在身体领域,一些已经存在的生物技术——比如外科移植、假肢、神经药理学或无处不在的互联网链接设备已经把人类变成后人类。而现实语境中物质实体和身体现象的不断复杂化,也为21 世纪的身体物质性话语建设提供了热土,它使当代理论家着眼于思考如何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物质世界和身体模型中,实现物质与身体的互渗。这一思考既延续了巴特勒对身体物质性的关注,同时又增补了对新型物性(thingness)文化的反思,进而在物质与身体的缠绕中,将身体物质性话语建设推向新的高峰。2000 年以来,西语学界出现了一系列与身体物质性相关的理论术语和学术研究,这一方面表征着学界对新型身体动态和物质概念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也彰显着“身体物质性”这一议题的强大话语生成能力。
2000 年,法国当代哲学家让- 吕克·南希发表《闯入者》(L'Intrus)一文,其间他着眼于心脏移植后所经历的伦理危机,主张在真实的躯体事件中召唤出一种以“复数”为核心的身体物质性观念。在《闯入者》中南希重点讨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接受心脏移植意味着什么?其二是心脏移植后幸存的后果又是什么?南希认为对于医学界而言,心脏移植可视为是一项技术成就,而对于病人而言,移植事件则会衍生出各种形而上学的问题。在接受移植后,主体将陷入一种既开放又封闭的身体体验,一方面为了延长生命,主体需要努力地接受异体心脏的植入,不断将外部的陌生侵入内化为自我身体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受制于犹太-基督教的身体传统,主体也不断地对这个外物产生强烈抵触,因此,心脏移植后幸存的后果就是“我成为一个多种解体着的形式的不可解体之物”[3]339。立足于这种独特身体体验,南希进一步思考了身体与外物的关系。他认为在身体中外物入侵是时刻发生着的,“不同的闯入者在任何时候都能出现在我的位置上,让我处于对他者的再现或与他者的关系之中”[3]340,因此身体或生命从来就不是以单数形式出现,而是以复数形式出现。“复数生命”这一概念的提出,表征着21 世纪以来身体物质性话语建设的新思路,即不再单纯依靠文化研究的学理力量来推进身体向物质世界回归,而强调在真实的身体事件中挖掘身体与物质的原生性缠绕关系。
在这一建设思路的影响下,2000 年后比尔·布朗(Bill Brown)、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等一系列新物质主义理论家将身体物质性话语的研究边界进一步拓宽,他们试图从身体与物质的原生性缠绕关系入手,来为新物质主义提供一种本体论上的确证,由此身体物质性话语也被塑造为批判社会权利关系和不平等现象的重要基础。出版于2010 年的《肉身自然》(Bodily Natures)可视为这一时期身体物质性话语建设的重要成果。其间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阿莱默基于20 世纪末和21 世纪初的全新物质动态和身体现象,正式提出“跨身体”的概念。“跨身体”强调各种身体性质之间的流动和交换,一方面阿莱默利用“跨身体”概念,反思了女性主义、后人类主义以及环境主义等新兴人文话语,她认为这些话语在批判传统人文主义的同时,自身也陷入了二元主义的桎梏,比如她谈到“许多重要的女权主义论点和概念都主要是在二元论系统中运作,而不是反对这种二元论”[4]5,因此,阿莱默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想象当下话语分析模式,需要关注更为强大和复杂的学理概念;另一方面阿莱默利用“跨身体”概念,观察了“环境正义”和“环境健康”运动中人体和环境之间出现的重大变化,并提出了一种“人体与环境无法分离”的生命伦理,以回应当下政治批判和性别问题中的新现实。阿莱默的“跨身体”概念,具有文化批判和伦理塑造的双重功效,其内部既含括了20 世纪身体物质性话语的批判性思路,同时它又在21 世纪以来的物质- 身体变迁动态中,重构了当下的生命伦理,因此,这一概念也可视为对过往身体物质性话语的一次系统性总结,它的出场也表征着21 世纪的身体物质性话语建设正式迈入了成熟期。
但近年来,受技术论转向和后人类美学的影响,身体物质性话语总是在后人类知识场域中被不断提及,并由此产生了新的裂变。从1977 年埃及裔美国学者伊哈卜·哈桑(Ihab Hassan)以剧本的形式发表学术性文章《作为表演者的普罗米修斯:走向一种后人类主义文化》起,“后人类”已经从一个虚拟性文化概念一步一步转变为我们实际的身体遭遇。而当下后人类的身体遭遇也正在褪去世纪初外科移植等身体事件中的危机属性,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进一步接轨,在各种有机可穿戴设备(cyborganic wearables)的嵌入中,“后人类”已经从一种激进的身体事件转变为一种日常性的身体现象。这一变迁,也形塑了后人类场域中的身体物质性话语,它使得当下的身体物质性话语不再简单地聚焦于“身体”与“物质”的互渗关系,而更为强调如何将这种互渗关系建构为一种全新本体论概念,以应对当下我们正在遭遇的后人类身体现象。2019 年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生物政治研究专家约瑟夫·巴尔拉(Josef Barla)在其新作《身体生产技术装置:技术与物质的新唯物主义理论》(The Techno -Apparatus of Bodily Production :A New Materialist Theory of Technology and the Body)中,借用了女性主义理论家凯蒂·金和哈拉维对身体生产装置的思考,提出“身体生产技术装置”(The Techno-Apparatus of Bodily Production)的概念。透过这一概念,巴尔拉试图去观察物质与身体的内部关系,进而营构出一种以“不确定性”为核心的本体论思考。首先巴尔拉拒绝了以“物质”改写身体的学理进路,“而是将身体的生殖潜力和难以驾驭的潜力作为了一个问题”[5]11。在这一进路下,巴尔拉反思了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他认为“哈拉维的赛博格仍然陷于‘一加一’的演算逻辑”[5]107。在哈拉维“赛博格”的身体模型中,技术仍然是身体外部的东西,与其说赛博格表征着身体与技术的实际性混合,不如说是特定种类身体突破和混淆了传统身体的边界。进而,巴尔拉强调了一种更为开放的身体物质性观念,他认为身体和物质无论是从认识论还是从本体论,都不是预先存在的实体,也不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身体和物质都是世界形成的一部分,身体和物质的边界通过特定的实践而具体化,只有通过特定的实践,身体和物质的边界和属性才会显现并变得有意义,这一实践过程被巴尔拉称为“身体生产技术装置”。最后,立足于“身体生产技术装置”这一概念,巴尔拉在身体与物质之间建构了一种“不确定性”的关系。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指代知识的缺乏,或时空的含混,而是强调身体和物质之间的界限,我们无法一劳永逸地确定,而这也意味着身体和物质总是以多种方式纠缠在一起,身体的存在总是物质性的存在,物质总是具身化的现象。巴尔拉通过对身体与物质内部关系的重新解读,反思了过往身体物质性话语建设中的缺漏,而主张将身体与物质都视为正在生成的实体。这一理论回应了后人类场域中的新型身体现象,在各种可穿戴设备对肉体的嵌入下,身体物质性话语也不应再以一种“溯源”的姿态去探访身体与物质的交叉,而需要立足于新型的身体动态,为现下的身体现象提供物质性解读。
回溯20 世纪末期以来的身体物质性话语的衍进过程,“身体物质性”这一议题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理论活力和理论效力,它能在不断变化的身体模式和物质世界中,召唤出不同的理论话语和分析方法,凭此它也成为当下开启后人文主义致思的关键。不断涌现的身体物质性话语,一方面说明当下身体、物质和环境的界限正在被不断模糊,在各种身体事件和身体现象的内爆中,我们将迎来真正的后人类未来;另一方面它也挑战了自笛卡尔以来的传统身体观念、物质观念,在全新的思考方式和理论范式中,我们将迎来当代伦理和审美的嬗变契机。
二、身体物质性话语的理论基石与生命伦理
纵观21 世纪以来身体物质性话语的衍进浪潮,其中带有两个明显趋势:其一是反建构主义,其二是反二元对立主义。前者着眼于描绘身体物质性话语的建构策略,后者聚焦于定义身体物质性话语的建构目的。但在实际理论运用过程中,这二者往往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矛盾,在反建构主义的策略下,身体物质性话语往往陷入二元对立的误区,比如阿莱默曾谈到“因为跨身体性使人体成为焦点,所以有可能指责它重新树立了人类中心主义”[4]15。由此,在众多相关术语表述下,探寻身体物质性话语的核心假设和理论基石,并在现实场域中阐释其生命伦理,应成为“身体物质性”这一议题获得长足理论效力的必经之途。
作为一个论域宽广的议题,“身体物质性”能在多变的身体模式和物质世界中,召唤出不同的理论话语,进而构成一个充满异质性的理论空间,但这一理论空间也保有相当大的同质性,身体与物质、人类与非人类以各种形式缠绕在一起,身体与物质、人类与非人类的交换、过渡构成这一空间的话语中心。首先,不同学科视角、时代因素以及文化背景的渗入,使得这一理论空间呈现为一个开放、多元的系统,“身体物质性”这一议题能生成多元的话语表述,它不但含括了南希“复数生命”、阿莱默“跨身体”以及“后人类”等公认术语概念,而且与身体物质性相关的思维方法与衍生概念都能被其兼容,如布朗“物论”、贝内特“生命唯物主义”等。其次,既然众多话语表述都能被“身体物质性”这一理论空间所统摄,那么也表明其内部具有相当大的同质性,对此,阿莱默在《肉身自然》中就将身体物质性话语的同质性定义为“探索人体和非人类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交换和过渡,通过关注人类和超人类世界之间的物质联系,有可能在‘物质’的惯用定义中召唤出一种伦理”[4]2;而戴安娜·库尔(Diana Coole)和萨曼莎·弗罗斯特(Samantha Frost)则认为身体物质性话语的同质性正表现于“它们补充了内在生产性物质的本体论,描述了生命物质在被理性行为者遇到之前是如何建构自然和社会世界的”[2]20。基于身体物质性话语的异质性和同质性,我们可以发现,身体物质性话语之所以能够建构起一个完整的理论空间,关键在于它为学界提供了一系列关于“物质”“身体”的新观点、新方法和新思维,为分析当下的的身体现象和物质动态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模型。
而众多关于“物质”“身体”的新观点、新方法和新思维集合在一起,大致可以提炼为三个核心要义,即“动能”(agency)、“内在互动”(intra-action)与“跨体性”(transcorporeality)。首先,“动能”即运动之能,在融合布朗“物的力量”、贝内特“活力物质”等学理资源的基础上,“动能”强调了身体和物质的运动机能和生成属性,身体和物质都不应被视为被动的铭刻载体,而应被视为具有生命活力的建设性实体。其次,“内在互动”即物质间的交互与运动,在融合巴拉德“纠缠”“相遇”等学理概念的基础上,“内在互动”强调了身体和物质的敞开状态和复杂系统,身体和物质都不应被视为静态的惰性存在,而应被视为一个复杂、多元且开放的生产过程。在“内在互动”的视域下,身体和物质都拥有自我转化、自我生成的能力,凭此身体和外物的交互也不是一个定型的结果,而是一个正在生成的过程。最后,在融合阿莱默“跨身体”、南希“入侵者”等理论资源等基础上,“跨体性”强调了身体和物质的互渗性关系,身体和物质都不应被视为单独存在的实体,而应被视为相互渗透的整体性系统。总之,基于“动能”、“内在互动”及“跨体性”的描绘,身体物质性话语获得了独特的理论内涵:它在积极描绘物质与身体的耦合进程中,重新赋予物质与身体以内在活力,并以物质与身体的原始互动轨迹来质疑传统身物关系,进而在松懈二元对立哲学思维的基础上,将我们带入到万物皆有动能的一元本体论哲学体系。
身体物质性话语表征着物质场域和身体场域中的活力回归,而这也为重新配置当下的生命伦理提供了强大动力。身体物质性话语的生成,一方面突破了笛卡尔实体论和牛顿机械论对物质的惰性描述,取而代之的是以量子物理学和混沌物理学为基础的物质活性描述;另一方面它也突破了弗洛伊德以及早期福柯对身体的规训式解读,取而代之的是充满能量的积极身体。在万物皆有动能的理论前提下,身体物质性话语中的生命伦理大致包括两个向度:
第一,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重塑。“鉴于我们在21 世纪面临的几乎每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都需要与非人类接触——从气候变化、干旱到饥荒;生物技术、知识产权和隐私;种族灭绝、恐怖主义和战争——似乎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将我们未来的注意力、资源和精力转向被广泛理解的非人类”[6]。而身体物质性话语则通过质疑身体的连续性和恒在性,来消解身体永远在场的假象,进而还原出身体与外物的原生性混杂状态,由此开启了重新配置人类与非人类伦理关系的契机。
在身体物质性话语的积极介入下,我们取缔了由主动主体和被动客体所构成的二元暴力关系,积极揭示非人类在人类世界中的参与与存在,赋予非人类存在以文化意义和伦理价值。具体而言,身体物质性话语对非人类伦理塑造包括两个维度。其一是批判人类物种中心主义立场,在更为广阔的物质背景下重审人类与非人类的伦理关系。随着有机和无机生命身体界限的模糊,人类与非人类的纠缠关系得以揭示,这使得我们重新反思人类的物种价值,如库尔所言“人类及其所谓的高阶主体性能力(自我认知、自我反思以及理性品质),现在看来只不过是广泛进化或宇宙生产中的偶然性或临时性的结果”[2]20。其二是挑战非人类物质的被动性特征,赋予非人类以完整生命活力。在身体物质性话语的作用下,非人类物质不再被视为静态惰性存在,而正式成为人类文化和伦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等非人类物质实体的意义建构作用,恢复非人类在人类世界中的重要价值,这也与当下人文社科领域中兴起的非人类转向(The Nonhuman Turn)运动相呼应,二者将共同筑力以建构起全新的非人类生命伦理。
第二,人类世界中的亚群体关怀。随着物质和身体的概念改写与实体变形,库尔在《新物质主义》中强调当下“最狂热的现实主义者也必须承认,我们在其中蹒跚而行的经验领域并没有在任何终极意义上抓住物质的真相或本质”[2]11,因此当下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颠倒标准的“现实主义”概念。在新物质主义的视域下,以物质为基底的现实主义概念面临着被重新建构的风险,以库尔、齐泽克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物质主义理论家都不约而同聚集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他们认为随着“物质”概念的改写,“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也需要全新升级。齐泽克在《少于无:黑格尔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Less than nothing : 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中提出,“我们应该放弃‘客观现实’的标准概念,即拥有完全确定的属性集的事物”[7],而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现实概念也由此成为新物质主义的本体论核心。
而当下的伦理体系中也存在着一种泛现实主义倾向,“好像在伦理概念和它所指向的世界对象之间存在某种线性和透明的关系”[8]190,比如性别伦理往往是基于两性生理差异而设置道德规范。而随着现实主义概念的改写,这种“线性透明”关系在全新身体物质观念中也将失效。身体物质性话语批判了基于自然身体和物质而设计出来的道德规范,将我们的视线转移到基于“健康”身体而生成的性别、种群以及阶级的暴力排斥史中。如凯里·沃尔夫就曾指出,当下大部分文化研究都“几乎总是被锁定在未经检验的物种主义框架内,这个框架,就像它的同源物一样,包含了仅仅基于一个一般特征而对另一个人的系统性歧视”[8]1,由此全球文化霸权也只赋予了少数人以理想人类的标签,而那些偏离了这一男性、白人以及异性恋等标准的人,则被打上了劣等人的标签。在身体物质性话语的积极介入下,我们更为关注残疾人、同性恋以及有色人种等亚群体,致力于在与这些亚群体的实际接触中解放被困在“客观现实”樊笼之中的亚群体生命活力,由此当下人文场域中也出现了一系列更为开放、平等的伦理观念,如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快乐伦理”③、齐格蒙特·鲍曼的“后现代伦理”等。
三、身体物质性话语下的文学转向与审美嬗变
“人的身体是被自然、社会与文化所构建出来的,它总是呈现出自然的身体与文化的身体之间的张力,呈现为人们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来不断重构自己的身体”[9],而在由多种身体物质性话语建构起的知识场域中,“身体物质性”这一议题的理论效用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溢出哲学、社会学等单一的学科区域,渗入和影响当下的文艺研究,为文学的本体重塑与审美范式转型,提供了学理启示与方法机制。身体物质性话语在文学研究中的积极汇入,不但回应了后人文主义时代中的新型文学生态,而且也塑造了物质生态批评、物质女权主义批评以及后人类身体批评等一系列前沿批评趋势,为当下的文学批评活动注入了全新活力与动能。
不同身体物质性话语从多个源点向文学场域渗透,由此也使得文学场域中的身体物质性话语研究呈现出丰富面貌。纵向来看身体物质性话语与文学研究的汇合,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一是21 世纪头十年以来的文学本体重塑运动(以媒介文艺学为代表);其二是2010 年以来的审美现代性反思与重构(以物质生态批评、后人类美学为代表)。前者着眼于文学本体的反思;后者则聚集于文学审美品格的再造。而这一脉络也基本符合新物质主义这一宏观学理热潮与文学研究的互动进程,即“21 世纪头十年强调‘动能’‘内在互动’的本体论转向、再到2010 年爆发期之后对于主要文学批评疆域的影响和塑造……”[10]。立足于此,我们将展开身体物质性话语下的文学转向与审美嬗变的分析,在新型文学生态的窥探中,反思身体物质性话语对文学活动的多方位渗透情况,进而推进当代文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总体性转型。这可从两个方面探讨。
第一,文学本体的媒介物质化转向。进入21世纪,各种身体物质性话语的出场,表征着欧洲大陆哲学的学术兴趣发生了明显变化。西语学界再一次开启了对物质与身体的本体阐释,以比尔·布朗、简·贝内特以及格雷·厄姆哈曼为代表的一大批新物质主义理论家都纷纷聚焦于物质、身体的本体论改写与重构。而随着新物质主义的溢出,这一学理热潮也激活了文学场域中的本体论研究,在各种身体物质性话语的积极渗入下,被束缚于语言论之中的文学本体产生了新的裂变。
自1967 年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中提出“语言学转向”的概念后,当代思想范式就正式从本体论、认识论转向语言论,而这一思想范式的转型也形塑了文学研究。自20 世纪语言学转向发生后,文论话语基本被束缚在语言论的学理框架中。有学者提出“‘语言学转向’(现实发生而非理论提出)后,当代西方文论主流基本没有溢出语言学文论的疆域”[11]1,只是其研究视点存在分野:部分集中于语言内部结构研究(以结构主义为代表),部分集中于语言外部形态研究(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由此在文学场域中也基本形成了以语言为核心的本体论体系。在语言本体论内部,其最为核心的价值在于确立了语言符号这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的基本地位,无论是静态的文本形态,还是动态的文学实践,文学都不能脱离语言媒介而存在,但同时也正是由于语言这一单一媒介的存在,语言本体论出场后,就面临着多方位的质疑。美国学者里德万·阿斯金(Ridvan Askin)指出,“几十年来,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要么因为本质主义与解构主义的斗争,而被视为不可回答;要么被故意转向社会历史层面,从而只能得到暂时和临时的回答”[12],因此,以单一的语言媒介作为文本本体是不够彻底的。
而由身体物质性话语所带来的物质性回归,则为语言论之后的本体探讨提供了新思路,它将助推文学本体从单一语言媒介转向复合性物质媒介。在新物质主义的视域下,身体物质性话语积极为媒介赋能,推动文学本体论的媒介物质化转向,具体而言包括两个维度:其一是身体物质性话语中开放的物质身体观念催生出具有多种复合形态的媒介类型。“在功能意义上,媒介指任何处于两者之间,发挥居间、谋和、容纳、赋形、建构功能的存在物”[11]8,而随着身体与物质两大实体的交互与开放,媒介也逐渐摆脱了单边性特征,而呈现复合性的特征,由此出现了虚拟现实媒介(Virtual Reality Media)、数字电子媒介等一大批新型媒介类型,而这也为突破以单一语言为媒介的文学本体提供了新的资源类型;其二是身体物质性话语中整体性的物质身体观念改写了文学本体中的媒介关系。在身体物质性话语跨体性的学理启示下,我们也可以发现文学意义的产生并不是依靠单一的语言媒介,而是源于整体性的多媒介协同作用。在当下文图融合、文技融合等多种形式的跨媒介叙事形态中,文本意义的建构与还原不仅需要作者、读者等多层主体的参与,它也需要语言、图像、技术等多媒介的参与。
总的来看,由身体物质性话语所引发的文学本体媒介物质化转向既是对数媒时代下新型文学生态的能动反应,又是当代文艺理论接续性发展的内在表现。一方面,当下的文学场域已经涌现了AI 创作、跨媒介叙事、泛文本生产等新型文学现象,文学本体需要对这种全新的文学生态做出解释;另一方面,文学本体的媒介物质化转向也可视为对语言学文论的推进,是立足于当下新物质和新媒介现实,对文学本体的重新思考。
第二,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反思与话语生成。2010 年,以阿莱默“跨体性”概念提出为标志,身体物质性话语建设正式迈入了成熟期,基于此,西语学界也同时展开了对身体物质性话语的学理致思,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则是由身体物质性话语所引起的审美现代性反思。以阿莱默、巴拉德以及海瑟琳·凯勒为代表的一系列理论家都纷纷在物质、身体的改写中反思现代性精神,进而以一种非人类主义的视角构建出全新的审美范式。而这一审美现代性反思,也同步推进了身体物质性话语与文学批评的相遇,生成了物质生态批评、物质女权主义批评以及后人类身体批评等一系列批评前沿趋势。
在身体物质性话语的理论空间中,最基本的运作动力是质疑现代性思想和实践的二元论特征。阿莱默、卡拉·巴拉德等人都认为现代性是建立在物质与精神这一组核心概念的对立基础之上,在这组对立中物质往往被视为惰性、被动的存在,而精神则被视为活力、超越性的存在,由此物质也成为了精神所规训的对象。长期以来,随着精神对物质的压迫,物质实体甚至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调节机制,正如阿莱所默指出,“长期以来,大自然一直是一个哲学概念,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节点,以及一个针对妇女、有色人种、土著人民、同性恋者和下层阶级的规范和道德主义的文化宝库”[4]4,而现代性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带有明显先验主义特征的人文思想基础上,它往往借助“自然”来为它所建立的二元关系提供辩解和论证,进而在生态、种群以及性别等维度建构出一系列的人为差异,以区别于前现代性社会中的原始状态。
而身体物质性话语则提出了一种一元论的内在哲学,专注于物质、身体的活力恢复,避免将身体与物质视为注定要由精神塑造的实体,强调在二者的内在互动中重塑现代性的审美品格。在身体物质性话语的积极渗入下,当下文学批评场域内形成了一种非人类的审美立场。这一立场并不把世界视为已经在物质与精神、经验和先验的二元对立中组织起来,而是积极探索宇宙间各种非人类元素的重叠与过渡,从而批判潜藏于现代性概念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立足于非人类审美立场,当下的文学批评场域也开辟出两条具有非人类视野的研究进路:其一是以物质为视点,在物质活力的回归进程中重审惰性自然遮蔽下的人类暴力叙事,由此孕育了物质生态主义、物质女权主义等一大批新型批评话语以及动物转向、植物转向等一系列新型前沿趋势。其二是以身体为视点,在跨身体的境况下重思文本中的人类主体性、身体物质性等问题,由此派生了后人类主义、非人类主义等一大批后人类身体批评话语。
综上所述,身体物质性话语在文学场域中的渗入,不但催生了文学本体的媒介物质化转向,而且也孕育出一系列具有非人类主义视野的批评话语和前沿趋势,而这也进一步推动了文学在后人类主义时代下的整体性转型。“在后人类时代,随着当今数字化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和艺术在赛博空间中进行交合,形成了文、艺、技渗透交融的新形态”[13],而文学形态的迭变也催生着文学理论的转型,西方语言论文论已经难以解释当下复杂的文学生态,后人类主义时代中文学和越来越多的跨学科文本和叙事研究可以走什么样的道路成为当下文学理论建设的新问题。而随着身体物质性话语在文学场域的渗入,它为探索后人类主义时代下的文学发展道路至少提供了两方面的启示:其一是伴随物质性回归而带来的文学媒介拓展,后人类主义时代下的文学将突破以语言为中心的单一媒介,而迎来以物质为中心的多媒介形态;其二是伴随现代性反思而带来的文学审美品格塑造,后人类主义时代下的文学将以更少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通过不同故事、图像和文本来体验和阐释各种人类和非人类的思想和世界。
结 语
作为新物质主义思潮下的衍生理论,身体物质性话语在共享新型物质观念的同时,还增补了身体维度的反思,由此在对物质和身体的重塑中派生出全新的生命伦理和审美范式。21 世纪以来,身体物质性话语的建构与流变,不但为学界重思以物人关系为核心的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伦理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而且也为当下跨学科、跨媒介甚至是跨种群的文学研究搭建了学术平台。
而在中西学理互渗的基础上,将身体物质性话语考察纳入到中国语境中,我们仍能发现这一理论空间具有穿越地域、穿越文明的学理价值。一方面,在身体物质性话语内部不乏与中国传统哲学相通的论述,身体物质性话语重开放、重整体的观念与老庄哲学所提出的“心物一元论”产生了理论上的共鸣,二者都共同强调了心物一元、万物一体的生命伦理;另一方面,身体物质性话语也为中国问题的思考注入了新活力。近年来随着新冠疫情、人工智能超速发展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叠加,如何重思人类主体性成为全球性的重要议题,而这一议题又在以人为中心的中国语境中被不断放大,身体物质性话语的渗入为调整当下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社会人文伦理提供了重要启示。基于此,如何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透视身体物质性话语的学理内涵,挖掘传统中国思想中隐含的身体物质性观念,并将其导入到当下中国问题思考与中国话语建构进程,将是当代中国学者面临的重要学术任务。
注 释:
①作为一股宏观性的学理热潮,新物质主义旨在关注被压抑、被边缘的物质实体,积极描述物体的“物化”过程,“强调物化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相对开放的过程”,进而增补进“动能”“内在互动”等哲学观念,以重新配置人类与物质的关系;而作为一种方法集合,新物质主义则致力于对现实生活状况及其内在不平等现象展开批判性分析,在其充满积极性和建设性的主流精神中生成全新的概念和形象,重新恢复起被二元论话语所诋毁和压制的人类边缘群体以及非人类的生命活力。
②2010 年以来汉语学界中的身体物质性研究可参见下列文章:范譞著《物质性与物质化〈身体之重〉一书中的身体理论》,载《社会》2012 年第3 期,第224—240 页;程鹏飞、陈嘉美著《媒介变革语境下影像身体的物质性转向》,载《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22 年第4 期,第67—74 页;张进、王垚著《现象学视域下的物质文化研究》,载《湖北大学学报》2017 年第5 期,第45—51 页。
③有关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快乐伦理”的阐释,可参见周伟薇、王峰著《朝向共同体的后人类快乐伦理——布拉伊多蒂后人类伦理研究》,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3 期,第31—4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