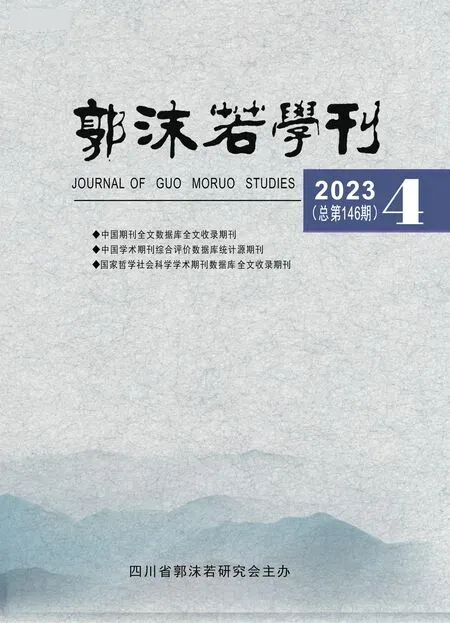试论郭沫若对商周青铜器分代问题的思考*
刘婧妍
(故宫博物院,北京 100009)
明确铜器年代是彝铭作为史料应用的前提,也是借由金文实现商周社会分期的基础与重要内容。郭沫若曾指出:“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①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九五四年新版引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2 页。明确史料年代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郭沫若以文字为社会文化之要征,以殷周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为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必由之路,铜器断代始终是其史学研究及古文字学研究的核心内容。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系统创立了标准器断代法,铜器年代学研究由此进入科学发展阶段。郭沫若以此法研究殷周铜器,主要针对两周特别是西周有铭铜器②王世民:《郭沫若同志与殷周铜器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82 年第6 期。,因此学者对其青铜器研究的关注也多以西周铜器断代为主③参见王世民:《郭沫若同志与殷周铜器的考古学研究》;张政烺:《郭沫若同志对金文研究的贡献》,《考古》1983 年第1 期;王世民:《科学的方法,完整的体系——略谈郭沫若的金文研究成就》,《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专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第238-243 页;刘正:《重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南方文物》2009 年第4 期;陈荣军:《金文“标准器断代法”考论》,《殷都学刊》2013 年第1 期。,对郭沫若关于离析商周铜器的探索则少有论及。而相关内容的厘清不仅是古文字与青铜器研究史的重要工作,也对深入认识郭沫若商周社会分期与古代社会研究的相关工作极为关键。本文即以郭沫若对商周铜器分代因素的探索为主要内容,兼及殷周二代铜器与西周铜器分代标准之差异,以此试论郭沫若对青铜器断代问题的相关思考。
一、殷周铜器分代
断代是金文及青铜器研究的重要基础,只有在铜器年代明确后才能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工作,铭文才具有作为史料运用的价值。断代的首要就是分别出不同王朝的铜器,金石学形成伊始,分别殷周铜器便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宋代学者断代首重铭文,兼及铜器纹饰、形制与出土地点等因素。但由于缺乏明确标准,以及对如日名等因素的认识存在局限,以致铜器断代极具主观随意性。清代学者虽对宋人学说有所匡正,但仍未形成明确且有效的分代标准。直至1927 年,马衡在《中国之铜器时代》一文中首次建立了分别商器的原则,使商器的鉴别从以往的臆度中摆脱出来,真正步入科学时代①冯时:《中国古文字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446 页。。马衡确立的分别商器之原则含纪时、祖先称谓、周祭制度以及征人方事迹诸因素,还包括出土地为殷墟者②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118-119 页。,陈梦家、容庚、张维持等学者或有所补充,但皆不出马衡所立之标准。郭沫若虽未系统建立分别商周铜器的原则,但出于研究商周社会的目的,铜器分代实为其不得不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对商周铜器分代标准的探索多散见于郭沫若史学研究诸作中。相关内容的整理与厘清,有助于对郭沫若铜器分代及商周社会分期理论的深入认识,也是对其运用古文字资料研究古代社会具体方法的揭示。
相较于两周有铭铜器,郭沫若对殷器的研究相对有限。所作《戊辰彝考释》一文,将戊辰彝年代断在帝辛二十年,为研究殷末铜器提供了一件标准器③张政烺:《郭沫若同志对金文研究的贡献》,《考古》1983 年第1 期。。而对殷周铜器分代问题的思考早在郭沫若以文字治史的初期就已十分成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用“彝铭中殷周的时代性”一节专门探讨殷周铜器之差异:
殷彝与周彝,其器物的品类(如殷之爵,周之鬲),形式(如鼎足殷为倒立圆锥形,周多兽蹄形),花纹(如殷彝花繁,周彝花省)等,均判然有别。(如有人细作化学分析的比较研究,两时代的金属的成分恐亦有所不同。)
从文字的表现来说,稍有经验的人差不多一见即可知其差异。殷彝文简,每仅一二字之图形文字,周彝文已脱离原始畛域,文字之多者如西周末年之毛公鼎四百九十七字,春秋时代之齐侯钟四百九十二字,同镈四百九十八字。
但这些都还是皮相的见解,最重要的是殷、周的时代性或者社会情形的差异。④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286 页。郭沫若认为区别殷周铜器,器物品类、形式、花纹、文字多寡的差异仅为表象,铜器铭文所反映的时代性才是断代的关键,与马衡所确立的判别商器的标准内涵实一。商周铜器的离析涉及不同王朝、不同文化、不同族属、不同制度的分别,类型学研究尚不足以明确地区分商代晚期与西周早期以及西周晚期与东周早期的铜器⑤冯时:《中国古文字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444 页。,相较于纹饰形制这类外在尺度,铭文内容实为区别殷周铜器的决定性因素。
1929 年至1935 年期间,郭沫若与容庚频繁通信,时值《两周金文辞大系》诸作撰写之际,二人就古文字学研究与铜器研究的科学体系等问题多有探讨。信札内容不仅对标准器断代法孕育之过程多有揭示,亦可见郭沫若对辨别殷周铜器的相关探索,是研究郭沫若铜器分代理论的珍贵资料。在1929 年9 月的信札中,郭沫若以铭文之纪时与称谓特征为据判断绅敦年代:
此器上用周制之初吉,下沿殷习之父丁,制作当在殷周之间。⑥郭沫若:《郭沫若致容庚书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第164 页。
1929.9.19
初吉指一月中的第一个吉日⑦冯时:《晋侯穌钟与西周历法》,《考古学报》1997 年第4 期。,属周制,为周器铭文重要的纪时特征①此为郭沫若从王国维说,王氏以周人月行四分制虽与史实不符,但以初吉属周制则为不易之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87-288 页。。宋清金石著说多以日名为判断殷器的标准,直到罗振玉《殷文存·序》仍以日名属殷习:“惟商人以日为名,通乎上下,……日名之制,亦下施于周初,要之不离殷器者近是。”②罗振玉:《殷文存》,《艺术丛编》第八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年,第359 页。郭沫若彼时亦以日名属殷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篇章对日名问题也有所论及:
此器疑为殷器者仅“父丁”二字。然按文词体例及字迹,确是周器。周初亦沿殷习以日为名,旂鼎已可见,他如遹簋文云:“隹六月既生霸,穆王在(丰?)京,乎(呼)渔于大池。王卿酉(飨酒),遹御亡遣。穆王(亲)锡遹雀(爵)。遹拜首稽首敢对扬穆王休。用作文考父乙尊彝,其子子孙孙永宝。”这明明是周穆王时器,而亦称“文考父乙”,即其明证。③此篇落款日期为1929 年11 月7 日夜,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88 页。
遹簋铭文已称穆王,知其为恭王世标准器,记穆王事,实难用周初沿殷习而以日为名作解。可见郭沫若彼时虽仍以日名属殷习,但已有所动摇。1930年4 月的信札中,郭沫若改变了此前对日名的看法,在与容庚探讨《武英殿彝器图录》一书的体例时提到:
又器物时代颇不易定,历来大抵依据款识以为唯一之标准,然此标准亦往往不可靠。例如以日为名者古即归于商器,然遹乃穆王时器犹称“文考父乙”,即其一例也。
1930.4.6
指出以日名作为断代依据并不可靠。《十批判书》中“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节则彻底推翻了以日名为判定殷器标准的断代原则:
近年发现穆王时的遹簋有“文考父乙”,懿王时的匡卣有“文考日丁”,足见“以日为名”之习至西周中叶也还有残余,而且已被证明,不是生日而是死日了。这一条例一被打破,于是举凡以前的著录中所标为殷器的都成了问题。④郭沫若:《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9 页。
郭沫若对日名的看法经历了以其为殷习,到认识到以日为名为商周通例的转变过程。这一认识对厘清一系列铜器年代而言极为关键,为郭沫若商周社会分期及古代社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
除了纪时语词与以日为名,郭沫若对商周铜器分代因素的探索还包括铭文所见锡物之区别。以殷周彝铭中习见的锡朋为例,郭沫若据锡朋数量的差异指出,贝在殷周二代经历了社会职能的重要转变:
殷彝中锡朋之数,至多者不过十朋,此与周彝中动辄有二十朋、三十朋、五十朋的判然有别。……殷彝中的锡朋,在我看来,是在赏赐颈环,不是在赏赐货币。⑤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87 页。
郭沫若认为贝在殷代尚未真正成为货币,于《甲骨文字研究》释朋一篇详论道:
贝玉在为货币以前,有一长时期专以用于服御,此乃人文进化上所必有之步骤。
案此实中国货币史上极重要之一段文字,考古者固不可不知,即谈经济学、社会学者胥不可不知也。惟贝朋在为颈饰时,其来多得自实物交换,则虽有货币之形,尚无货币之实。其实际用为货币,即用为物与物之介媒者,余以为亦当在殷周之际。
彝铭中锡贝之事多见,其著朋数者入周以后多在十朋以上,如效卣之廿朋五十朋,匽侯鼎之廿朋,吕鼎、剌鼎之卅朋,如此多数于殷彝中绝未有见。……当为殷末之器,至迟亦当在周初,而锡朋之数多不过十。……赏贝者率为当时王侯,而所赏者仅此数目,此与其视为货币,无宁视以为颈饰之较近情理。……故余谓贝朋之由颈饰化为货币当在殷周之际。①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107-114 页。
郭沫若以见于商周彝铭及卜辞锡朋数量的差异为据,探讨了贝朋在殷周之际社会职能的变化,可见辨别殷周铜器既是郭沫若商周社会分期及古代社会研究的基础,同样也是相关研究的产物,两者实为相辅相成之关系。
此外,郭沫若以铭见锡土田臣仆为周器的重要标志,并以此探讨商代社会的土地制度与奴隶制度。在1929 年10 月的去信中郭沫若曾询问容庚:
又古金中锡臣仆田土之事,除已见于诸家著录者外,如周公敦之“锡臣三品”之类,不识足下尚有新见否?
1929.1 0.3
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详论此事道:
殷金存世者甚少,其中虽然偶尔有锡贝朋器物的记录,而决无锡土田臣仆的例证。
……殷彝中无土田之赐予,这是表明殷代的土地尚未开始分割,即是说殷代还是在原始公社制度之下。
殷彝中无锡臣仆之事,这是说奴隶的使用尚未推广,奴隶尚未成为个人的私有。②郭沫若于此补注云:“殷代已有私人奴隶,由安阳小型墓葬亦有殉葬者可以证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86-287页。
尽管相关推测未必与史实完全相符,但仍对殷周铜器分代以及探析商周社会时代性极具重要意义。如郭沫若所言,金文资料中“锡土田”相关内容极具时代性,且其不仅是离析商周铜器的标志,也为辨别西周铜器的具体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综观金文,西周早期国势强盛,土地转移之事几不见记载,但至西周中期穆恭二王以后,相关的交易与诉讼则频繁出现,究其根本,穆王之奢靡是造成西周国势由盛而衰的重要转折③冯时:《裘卫鼎盉铭文与西周土田转移》,《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273 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在王庭财用难以周转之际,土田在某种意义上实属“取之不尽”的财富资源,故周天子或以土田作为交换财物的代价,这也促使了西周中期土田转移的频繁发生。锡土田相关事宜的时代性可以见得。
图形文字也是早期学者判别殷器的重要标志,如高本汉便认为金文中的、与、三类图形皆为殷器标识④B.Karlgren,Yin and Chou in Chinses Bronzes,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o.8,1936.。在1929 年12 月写给容庚的书信中郭沫若首次提到了彝铭中图形文字的性质:
甲寅父癸角作回环读亦可,然 终是疑问,前人释子孙固臆说,尊著《宝蕴楼》谓象陈牲体于尸下而祭,恐亦未然。非牲象,殷人用尸与否尚无明征。余疑姓氏者不仅此,凡殷彝中图形文字,余疑均系当时之国族,犹西方学者所称之图腾。尚有他证,暇将为文以明之也。
1929.1 2.24
郭沫若彼时已摒弃前人旧说,以图形文字为当时国族之图腾。1930 年7 月郭沫若著《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专门详述这一问题:
且如所谓“析子孙”及“子孙”二例,据余所见,于周彝中亦犹见使用。例如旂鼎,……此器用“初吉”,乃周制,故器必作于周代无疑。
……要之,准诸一般社会进展之公例及我国自来器物款识之性质,凡图形文字之作鸟兽虫鱼之形者必系古代民族之图腾或其孑遗,其非鸟兽虫鱼之形者乃图腾之转变,盖已有相当进展之文化,而脱去原始畛域者之族徽也。⑤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四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15、22 页。
郭沫若以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大背景,考图形文字的性质为图腾,并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审视图形文字的原始与进化,而不以其为判别殷周铜器的绝对标准。以郭沫若对作册令方彝及令簋铭末鸟形族徽的考释为例:
鸟形当是作册夨令之家徽,乃图腾之孑遗。《小雅·六月》所谓“织文鸟章”之类也。令簋铭末亦有此形,可以为证。①郭沫若:《令彝令簋与其它诸器物之综合研究》,《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四卷),第55 页。
综合以上内容可知,郭沫若虽未建立系统的商周铜器分代标准,但分代实为其古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与重要内容。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完成的第一部史学研究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专辟“彝铭中殷周的时代性”一节探讨金文所见商周社会之特征;《十批判书》中设有“关于殷周青铜器的处理”“古器物中所见的殷周关系”“关于殷代的生产状况”“关于西周的生产状况”诸章节,皆以彝铭内容为探讨商周社会基本情况的重要论据。其中所体现的殷周社会的时代性差异,即为离析二代铜器的关键。但断代从不是郭沫若研习商周金文的初衷,在断代的基础上探析彝铭史料所反映的殷周二代各自的时代性以及继承与发展关系,进而研究古代社会才是其最终目的。
二、西周铜器断代
对于研究古代社会而言,辨别出属殷属周仍远远不够,将铜器年代落实到具体王世才是彝铭作为史料应用的关键。尽管早期学者已对西周铜器年代问题多有研究,但直到郭沫若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搭建起西周铜器的年代学框架,才首次将一团混沌的传世铜器整理成为可供古史研究利用的科学资料,所创立的标准器断代法确定了大批有铭而年代不详的铜器的时代,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年代明确的直接史料。
1931 年9 月郭沫若于初版《大系》自序中阐释标准器断代法之核心内涵:
余专就彝铭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怀若何之成见,亦不据外在之尺度。盖器物年代每有于铭文透露者,如上举之献侯鼎、宗周钟、遹簋、趞曹鼎、匡卣等皆是。此外如大丰簋云“王衣祀于王不显考文王”,自为武王时器;小盂鼎云“用牲啻(禘)周王□王成王”,当为康王时器,均不待辩而自明。而由新旧史料之合证,足以确实考订者,为数亦不鲜。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它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络可寻。得此更就文字之体例、文辞之格调,及器物之花纹形式以参验之,一时代之器大抵可以踪迹,即其近是者,于先后之相去,要亦不甚远。③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文求堂书店,1932 年,第7 页。
又在1934 年所作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序文中对此法予以简要说明:
盖余之法乃先让铭辞史实自述其年代,年代既明,形制与纹缋遂自呈其条贯也。形制与纹缋如是,即铭辞之文章与字体亦莫不如是。④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图录),《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七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68 页。
可见除了年代自明的标准器外,系统的器物形制、纹饰参照系也是标准器断代法的关键所在。据《致容庚书简》之内容可知,《两周金文辞大系》编纂于1931 年年初至当年九月期间,但标准器断代法的核心思想早在1930 年4 月与容庚讨论《武英殿彝器图录》一书的体例时就已十分成熟。信札记:
余意花纹形式之研究最为切要,近世考古学即注意于此,如在铜器时代以前之新旧石器时代之古物,即由形式或花纹以定其时期。足下与古物接触之机会较多,能有意于此乎?如将时代已定之器作为标准,就其器之花纹形式比汇而统系之,以按其余之时代不明者,余意必大有创获也。信中所言以时代明确之铜器为标准,就其纹饰、形制之脉络串联时代不明之器,即标准器断代法之核心。由书简内容可知,标准器断代法的产生实为现代考古学传入的结果。1929 年上半年,郭沫若在转译德国学者米海里司的著作《美术考古一世纪》时,了解到现代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①王世民:《郭沫若同志与殷周铜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的方法,完整的体系——略谈郭沫若的金文研究成就》,第239 页。。郭沫若在1946 年为此书改版重印所作的译者前言中写道:
1930.4.6
我的关于殷墟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主要是这部书把方法告诉了我,因而我的关于古代社会的研究,如果多少有些成绩的话,也多是本书赐给我的。
我自己要坦白地承认,假如我没有译读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得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砂上楼台的。②[德]米海里司:《美术考古一世纪》,郭沫若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 年,第2、3 页。
据此可知在郭沫若以殷周古文字治史之初便深受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足见现代考古学对郭沫若青铜器研究及古代社会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郭沫若对铜器纹饰极为重视,与容庚多次就花纹研究相关问题深入探讨。兹举例如下:
臣辰盉拓片及图能见示否?既有图可作参考,则弟稿殊未备,盖花纹形式于器之制作时代上大有攸关也。
1930.1 2.4
花纹定名弟尚未尝试,惟于花纹研究之方针早有腹案,惜无资料耳。定时分类为要,定名次之,分类已成,即名之为甲乙丙丁,或ABCD 均无不可。定时乃花纹研究之吃紧事。此与陶瓷研究及古新旧石器之研究同。此事最难,须就铭文之时代性已明者作为标准,逐次以推求之也。花纹之时代性已定,则将来无铭之器物或有铭而不详者,其时代之辨别将有如探囊取物矣。
1931.7.17
至花纹研究一事,当综合群书另作一有系统之研究方可。
1931.8.24
尊著《宝蕴楼》于花纹形式确有暗默之系统存在,……窃意此花纹形制系统学之建设,兄为其最适任者,望能通筹全局而为之。
1931.9.27
针对铜器纹饰研究之方案,郭沫若反复强调“定时”的重要性,以花纹形制发展脉络的厘清为无铭或有铭而不详类铜器断代的基础,可见其着眼于铜器纹饰研究旨在建立纹饰年代学系统,以此作为判别铜器时代的参照系。而对纹饰内涵的研究则居次要地位。这种区分器类和花纹形式再作断代的方法,就是考古学研究所运用的类型学方法③王世民:《郭沫若同志与殷周铜器的考古学研究》。。在《毛公鼎之年代》一文中郭沫若更直言道:
大凡一时代之器必有一时代之花纹与形式,今时如是,古亦如是。故花纹形式在决定器物之时代上占有极重要之位置,其可依据,有时过于铭文。
余谓凡今后研究殷周彝器者,当以求出花纹形式之历史系统为其最主要之事业。④郭沫若:《金文丛考·毛公鼎之年代》,《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五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613、615 页。
以纹饰形制为决定铜器年代的关键,甚至有时还要过于铭文,郭沫若对铜器纹饰形制的重视可见一斑。《武英殿彝器图录》作为始专门摹录铜器花纹的著作,其中郭沫若所起到的作用应十分关键。容庚初版于1941 年的《商周彝器通考》,首开系统整理铜器纹饰之先河,专立章节讨论花纹,将商周铜器纹饰分为77 类,对于每一纹样通行的年代皆予以说明,并对各纹饰内涵略作诠释,与郭沫若信札中所言花纹研究方针之腹案“定时分类为要”颇相一致。可见尽管郭沫若并未建立铜器纹饰形制的年代学系统,但对花纹形式的重视与整理著录是在他的影响与推动下展开的。
郭沫若念兹在兹要建立的铜器形制、纹饰历史系统,旨在为断代提供相对可靠的参照系,而在离析殷周铜器时他曾提及,以器物品类、形式、花纹、文字多寡为据皆为皮相之见解,对铜器纹饰、形制的态度可谓两极。但我们并不认为这种差异是受现代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从而导致郭沫若对铜器纹饰前后态度变化的反映,而应只是在辨别殷周二代铜器与同一王朝不同王世铜器时所作出的具体调整。对于商末周初与两周之际的铜器而言,类型学方法并不足以作为判断铜器年代的决定性因素,铜器器类、形制、纹饰这类外在尺度并不会因政治事件的发生而随即作出相应改变,郭沫若所强调的不同社会的时代性及社会情形的差异才是离析这类铜器的关键。就青铜器这一载体而言,铭文无疑是体现不同王朝时代性的最佳表现形式,不同朝代不同的纪时制度、称谓制度、语言习惯、祭祀制度以及史迹等时代特征,皆会伴随着王朝的更替以最为直观的形式呈现在铜器铭文之中。所谓的时代性,既是离析不同王朝铜器的关键,也是金文研究的重要归宿。而以时代差异区分同一王朝不同王世的铜器则殊为不易,除了铭文自身所反映的年代信息外,形制、纹饰及铭文书体特征等因素实为落实铜器所属王世更足资依凭的参照系。西周铜器被大致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便由此类因素所决定。由此可见,郭沫若对纹饰、形制在铜器分代问题中的不同态度,是为区别不同王朝及不同王世铜器而据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具体调整,郭沫若对殷周铜器断代相关问题思虑之精深可见一斑。
结论
综观郭沫若对商周铜器分代问题的相关探索,可得出如下认识:郭沫若系统梳理了传世及出土的西周有铭铜器的年代序列,所创立的标准器断代法将铜器的年代学研究引入科学发展阶段。通过梳理郭沫若史学研究相关著作可知,除了落实西周铜器所属的具体王世,离析殷周铜器也是郭沫若青铜器研究的重要内容。郭沫若以彝铭所反映的时代性及社会差异为分代的关键,深入探索了称谓制度、锡物内容以及族徽铭文等因素对断代的影响。具体而言,郭沫若对日名的认识经历了以日名属殷制,到以其为殷周通例的不同阶段;以锡朋数量的差异为殷商西周时期贝社会职能转化的反映;而锡土田相关内容,作为离析商周铜器的标识,也为探讨殷周二代不同的社会情形提供了重要线索。郭沫若对族徽铭文发展规律及其性质的揭示对商周铜器分代标准的校正极为关键,在深入认识商周社会的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重要见证。郭沫若对铜器分代的探索皆渗透在其商周社会研究之过程中,分别殷周铜器既是其古代社会研究的基础,同样也是相关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郭沫若的史学研究工作而言,二者实为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区分出不同王朝的基础之上,将铜器厘次至各王世是铭文作为史学研究资料应用的关键。郭沫若创建的标准器断代法,系统建立了西周铜器的年代学框架,现代考古学研究方法是促使其产生的重要因素。以铭辞史实可自述年代的标准器为核心,以诸标准器为节点,将一时代之铜器的纹饰形制条贯厘次,以作为无铭或有铭而不详铜器断代的坐标系,建立了一时代铜器相对完善的类型学研究体系,铜器年代学研究由此步入科学发展阶段。为建立此坐标系,郭沫若极为重视对铜器纹饰形制的梳理,对铜器纹饰系统研究的相关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针对铜器分代所涉及的不同王朝与不同王世的区别,郭沫若对纹饰、形制这类反映铜器年代的外在尺度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而这是综合了对现代考古学研究方法与殷周社会时代性差异深刻认识的结果。铜器断代作为商周社会分期的基础与重要内容,是郭沫若古文字学及史学研究的结穴所在,时至今日仍是相关研究工作的基础与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