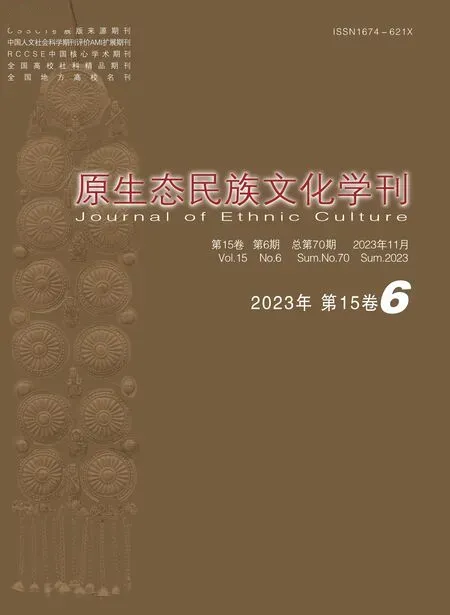仪式治疗的历史形塑与意义延展:一个布朗族村寨的个案研究
王 舫,保 虎
一、问题的提出
既有的一些研究已经提出现代医疗、仪式治疗以及民间草药疗法等多种医疗体系不是简单的并存,也非简单的替代,而是更复杂地交织在一起①徐君,李沛容:《医学人类学视野下的民族地区医疗体系——四川省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的案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4期,第51-55页。②余成普:《多元医疗:一个侗族村寨的个案研究》,《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第68-79页。③张实,郑艳姬:《治疗的整体性:多元医疗的再思考——基于一个彝族村落的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96-103页。。可以看出,现有有关多元医疗的研究,多集中在多元医疗体系现象的原因分析以及围绕多元医疗体系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研究者更多是聚焦某一族群,进行具体细致的调查研究。这些无疑为医学多元主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个案与素材。总的来看,很多的研究多将医学多元主义视为理论框架,填充来自不同地方的田野调查资料。当然已经有部分学者注意到此问题,一些研究者不满足于简单的理论套用,而是进一步将医学多元主义观点之下不同医疗体系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等具体问题①余成普:《多元医疗:一个侗族村寨的个案研究》,《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第68-79页。。
诚然,调查与了解一地的多元医疗体系至关重要,其可以帮助我们获取一地有关多元医疗的整体性面貌与认识,但过度纠结或者停滞于这个现象本身的介绍,可能会忽视一些我们真正需要研究的问题。正如张有春所讲,人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医学体系,医学多元是一个普遍事实,因此“医学人类学家所做的不是去展示‘体系’,而应该关注当患病或遭遇不幸时,人们如何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相关信息去应对疾病”②张有春:《一个乡村治病过程的人类学解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57-61页。。也就是说,我们更应该关注医学体系中人的疾病应对实践以及人们是依赖哪些因素做出医疗体系中的选择,或是一元或是多元选择。无论是“一元选择”还是“多元选择”,就西南民族地区而言,仪式治疗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疾病应对实践。“仪式治疗”虽然在医学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但从世界各国的研究来看,它并没有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而销声匿迹,它仍然稳固地存在于诸多社会之中。
有关仪式治疗原因的研究主要涉及三类。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由于前文中提及多元医疗作为一种无法忽视的社会事实,这里提及的“仪式治疗的原因”设定了现代医疗已然进入的社会背景。第一类有关仪式治疗原因的探析。有关研究认为,人们之所以选择与长期使用仪式治疗,是因为现代医学发展至今,它虽然具有疗效,但其不能保证对所有病人都有疗效,也不能实现对所有疑难病症的治愈,这在现代医学发展初期尤是如此。某种层面上而言,现代医学疗效的不确定性致使病患或家属陷入慌乱,构成“问题”,而仪式治疗构成人们缓解或破解这一不确定性的“信仰”实践。这类的研究主要有梁其姿有关种痘术及借助仪式化解种痘术疗效不确定性的研究③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3页。,许烺光有关西城人应对霍乱时既注射疫苗又使用“魔法”的研究④许烺光:《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王芃,徐隆德,余伯泉合译,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7年。,以及余成普有关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中,面对现代医学辅助生殖技术的不确定性、不完整性,不孕女性患者借助信仰途径,寻求精神层面的支持等⑤余成普,李宛霖,邓明芬:《希望与焦虑:辅助生殖技术中女性患者的具身体验研究》,《社会》2019 年第4 期,第84-115页。。涉及此类仪式治疗原因的研究,有的还提及病患关怀等,一定程度上这是人们择取仪式治疗的第二类原因。比如程瑜有关侗族妇科病应对实践中的仪式治疗研究⑥程瑜,黄韵诗:《被遮蔽的妇科病:广西柳州侗寨妇女的就医选择》,《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第69-75页。。此外,有关研究者还提及构成人们仪式治疗的客观性因素,比如徐君与余成普⑦徐君,李沛容:《医学人类学视野下的民族地区医疗体系——四川省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的案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4期,第51-55页;余成普:《多元医疗:一个侗族村寨的个案研究》,《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第68-79页。的研究中都提到仪式治疗相比于现代医疗,仪式治疗的费用较低,从医疗费用层面实现了对病患的一种关怀。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涉及交通因素等,距离现代医院路程较远可以构成人们择取物理距离较近的,且触手可及的仪式治疗。
第三类有关仪式治疗原因的分析路径是围绕宗教人类学、象征人类学进行的。刘志杨有关白马藏族的研究,其认为白马藏族的疾病应对实践受到其信仰影响较大①刘志扬:《“神药两解”:白马藏族的民俗医疗观念与实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 年第10 期,第14-21页。。高登荣等对傣族叫魂仪式的研究,他们认为在云南金平傣族的认知世界中,灵魂离开身体意味着失序与肮脏随之而来。举行叫魂仪式方能使得失序的社会、不适的身体正常运转与恢复健康②高登荣,黄昕莹:《灵魂与空间:金平傣族的叫魂仪式》,《民族学刊》2020年第1期,第76-82页。。此类的研究较为丰富,较多研究谈及仪式治疗的信仰因素。总体而言,上述人们择取仪式治疗的三大类原因可以归纳为外因(客观因素)、内因(心理、精神因素),当然这个分类不是绝对的,比如上文中提及的第一类因素,人们为了应对现代医疗的不确定性而进行的仪式实践与人们需要找到化解焦虑的一种应对办法,这里可能既涉及外因,又涉及内因。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因素常常内外交织,或许可以说,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人们选择仪式治疗的作用力。
以上,我们相对比较清晰地了解到,有关仪式治疗、多元医疗的研究确实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与拓展了医学人类学相关研究主题。与此同时,我们需注意,以上有关研究更多是一种共时性层面的研究,本文将借助另外一种视角——历时性视角,以下寨布朗族1949 年以来仪式治疗作为切入口,洞察作为“传统权威”的仪式治疗是如何“应对”具有“科学权威”性质的现代医学,换句话说,在现代医疗尚未进入下寨之际,仪式治疗构成下寨人疾病应对实践的主体选择,而作为“新来者”或者“后来者”,现代医疗是如何进入到当地社会以及如何被当地人接受与采纳的,这一过程是否出现一些“节点性事件”,或者转折性事件。研究仪式治疗与现代医疗等的“碰撞”与“交织”或可加深我们对仪式治疗意义以及多元医疗之间并非简单替代、亦非简单并存以及交织的复杂性等的理解与认知。洞察以上问题,或将进一步拓宽有关仪式治疗等的研究视野。
二、下寨布朗族仪式治疗的历史形塑
下寨是位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以布朗族为主体民族的村寨,且距离乡镇卫生院仅1公里左右。20 世纪80 年代,其逐渐从老寨所在位置搬迁至下寨所在的山脚坝区,距离老寨12公里左右。这是笔者自2014年8月参与观察至今的一个田野点。
2020 年8 月的一天下午笔者来到呀甩的家中。1931 年出生的呀甩,精神状态较好,当谈到需要访谈她时,她专门去沐浴,并换上一身绣着布朗族特有花纹的筒裙。她的记忆力很好,这表现在笔者访谈其口功内容时,由于内容比较多,原本第一天访谈过的内容,第二天再次请其口述有关口功内容时,老人家清晰记得她前一天为我们讲过有关内容。与同龄人相比,呀甩听力、视力都较好,只有腰部几乎弯成了近80度。这般高龄与反弓腰背带来的不适,却没有影响她为周边病患治病,其擅长的疗法是口功,所需草药则主要由其儿子与孙女协助采集。关于仪式治疗的“自由生长”阶段,老人家回忆:
以前我们在老家(老寨)生病,(身体)不舒服了,不像现在有医院,我们(在老寨)就吹吹口功、做做迷信、吃吃草药,我爸爸会吹口功(口功治疗师往往也是草药治疗师),我从小跟他学。有的哪里不舒服还会找巫师占卜原因,再请“布占”或者大佛爷叫叫魂,严重的还要驱鬼,配合草药,一般会好①访谈对象:呀甩(1931-,女),访谈地点:呀甩家,访谈时间:2020-08-09。。
仪式治疗的繁盛状态一方面体现在下寨村民在疾病应对时普遍选择仪式治疗,另外一方面则体现在佛爷、巫师与口功治疗师的数量较多,他们共同构成“仪式治疗师”群体。岩赛站(新)的父亲哒三坎是下寨以及周边村寨远近闻名的口功治疗师,在很多上了年纪的村民眼中,他通识草药、治病救人,治疗费用收取甚少,有时一顿饭、一瓶酒或者一包烟就足以。根据岩赛站回忆。
那个时候,村寨里很多口功治疗师、巫师等,有的懂得多,还可以招收徒弟。他们要学这个,有的是口头传承,有的是有书的。那个时候(1966~1976 年间),不管你是什么书,全部烧丢(烧掉)。
我老爹留了很多关于中医药的书,后来有个村里的骨干就给(把)这些书烧丢(烧掉)了。以前经书都不能离开我们自己家的,但是那时,他们就不准留这些书,只要被发现,(就)会被批斗。后来我爹的书被发现,就被村里的骨干给烧丢(掉),我爹说:我留的书是中药之类的,那个骨干就呵斥我爹说,你不用留,留那个没用,现在国家都有医院!
有的不仅要烧毁书,人还要得挨批斗。我们老寨的大佛爷,他学习佛法很多年,懂很多,我们都很尊重他。后面(他)遭批斗,受不了了,就逃克(逃去)缅甸,在缅甸成了功德很大的佛爷。后面那个时期结束后,他回来寨子过一次,一回来就哭,估计是想起来以前的伤心事了②访谈对象:岩赛站(1973-,男),访谈地点:岩赛站家,访谈时间:2020-07-27。。
一时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成为当时的主流话语,当地村民对于“口功”“巫师”“占卜”“叫魂”等仪式治疗的术语噤若寒蝉。在这一背景之下,由于下寨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与邻近缅甸的便利性,很多遭受不了身体与精神批判与折磨的佛教从事者、巫师等治疗师纷纷逃往一江之隔的缅甸。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结束后,一些人回归家乡,一些人则永远留在了他乡。
或许由于信仰本身的文化根基性较强,即使遭遇如此冲击,有关的信仰疗法并没有瞬间销声匿迹。正如黄彩文所说,或许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远与边缘,当地的民间信仰并没有完全被政治运动的推行与冲击而完全没有了生存空间,反而一些信仰活动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悄然生长③黄彩文:《仪式、信仰与村落生活——邦协布朗族的民间信仰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80页。。
一方面,下寨人另辟更加隐蔽与安全的藏书之地。下寨原本所在的位置老寨坐落于海拔1700 米的深山之中,距现在下寨所在山脚位置12 公里处④“老寨”旧址依然存在,且有17户村民一直生活在老寨。。为了免于佛教经书被毁等,下寨的一些老人悄悄将经书背入与藏存至仅有一些老人们知晓的一个山洞。2021 年1 月,笔者进入老寨参加老寨佛寺“上新仪式”⑤所谓“上新仪式”是指村民集体修复年久失修(布朗族有“一村一寺”的传统,老寨佛寺在1966~1976年间遭到了严重破坏)的老寨佛寺,并为佛寺举行赕佛仪式。此次“上新仪式”由老寨村民与下寨村民合力完成,各户村民自由分组与承担佛寺上新需要完成的任务。有的负责墙壁粉刷,有的负责佛寺吊顶的维护等。有一点需要说明,这里任务在村民看来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而是主动承担的责任与获得功德的机遇。,发现两大纸箱的经书保存完好,笔者追问这些经书的时间时,老寨佛寺布章①布章,主要是指从僧还俗的人,主要主持村寨的仪式活动等。回复说,这些经书就是历经那个特殊的年代被藏存在老寨山洞的经书②笔者田野笔记(2021-01-24)。。
另一方面,虽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强大的信仰文化根基早已扎根于当地村民的心理与精神世界。长久以来形成的疾病观与信仰观促使下寨人在身体不适与应对疾病时,即便面临可能遭遇批斗的风险,人们依然悄悄地进行仪式治疗,悄悄地帮助那些被扣上“四旧帽子”的佛爷、巫师等。
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我爹也会一点,人家来找,都是亲戚,要帮忙。晚上人都睡了,就悄悄地搞迷信,不要请人参加,悄悄地不被发现就好了。③访谈对象:岩赛站(1973-,男),访谈地点:岩赛站家,访谈时间:2020-07-27。
我舅舅当时在我们寨子是功德很高的佛爷,当时他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我妈妈就让我悄悄给他送饭。他后面逃到了泰国,后面回来过一次。④访谈对象:玉坎拉(1964-,女),访谈地点:岩赛站家,访谈时间:2020-07-27。
在那个时期,“破四旧”等的强大浪潮不可规避,一方面我们目睹了佛寺被砸、仪式治疗师的被迫出逃等。在众多村民的认识世界中,实施这些极端的行为与做法势必会招致报应与惩罚。一位村民回忆,当时有个人冲着佛像小便,那个人后面遭遇眼睛失明,人们将其眼睛失明归因于其当年的不当行为。随着类似事情的出现,一些村干部甚至白天从事“破四旧工作”,晚上回家忏悔,请求神灵的宽恕。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仪式治疗历经苦难与磨难并没有直接地中断或被村民从生活中“铲除”与丢弃。相反,历经此劫难,作为信仰疗法的仪式治疗的根基则被巩固。
1956 年,打洛镇建立了卫生所。下寨村民虽然客观上拥有了接触现代医疗的机会,但是卫生所的建立并非意味着村民对现代医疗的快速认同与接纳。1961 年出生的下寨乡村医生岩苏三说:
我们老寨最开始有部队“卫生院”,主要是有部队在我们寨子旁边。但很少有人打针吃药,主要是(未知与)害怕。(开始阶段)很多村民不相信西医,直到后来寨子里一个老人患了一种很严重的病,部队的人就来给他打针。(这个老人)好了之后,以后整个寨子就开始慢慢相信西医(有疗效)了。(以前西医刚进来的时候),(老寨)整个寨子可能对西医半信半疑,经历过这个老人被治愈的事情之后,寨子(的人)才开始慢慢相信(西医)。一些人就算打针吃药了,回克(去)寨子还是会做迷信。虽然后面有了医院,但是我们老寨距离医院(打洛镇卫生所)太远了,不像现在,以前路不好,从上面(老寨)下来就只有一条小路,也没有摩托,我们下来赶一趟街子要两三个小时。⑤访谈对象:岩苏三(1961-,男),访谈地点:岩苏三家,访谈时间:2021-02-26。
虽然下寨人逐渐地开始相信西医的疗效,但由于医疗条件与医疗水平受限等客观因素,村民能够接触与使用现代医疗的机会少之又少。因此,对于下寨村民而言,择取何种医疗实践或者说此阶段两种医疗体系之间的关系并不构成“问题”或者“难题”。换句话说,即便当时已经建立了打洛卫生院,且不说当时缺医少药的现实困境,距离卫生院12 公里且道路不便的客观因素足以构成人们选择现代医疗的阻碍,抑或成为一些村民痛失家人的惋惜与遗憾。
下寨玉阿姨的第一个孩子发烧了几天,不见好,平常用的薄荷降温这次却不见效了,由于其年轻时担任过乡镇干部,于是和其老公背着发烧的孩子历经三个小时的山间小路至镇卫生院,“不像现在有摩托,当时路不好,我们只能背着,我们步行,背上又热,到了卫生院,医生给她扎针,她就哇地哭了一声就不在了,如果是现在,可能就救过来了……”玉阿姨回忆起这件事情时,眼睛里对因发烧而去世的孩子的怜爱与痛惜流露出来。①访谈对象:玉坎拉(1964-,女),访谈地点:岩赛站家,访谈时间:2020-07-27。
现代医疗针对急症等的疗效逐渐被村民认识,村民也想借助现代医疗为病患家属等治疗与化解疾痛。也可以说,村民为了维护健康,已经逐渐开始尝试现代医疗,并将现代医疗视为对仪式治疗与药草治疗等的一种替换与补充。当然,迫于当时道路交通等因素,这一替换与补充多是在仪式治疗与药草治疗等疗效受限的前提下。于大多数村民而言,只要借助药草治疗与仪式治疗“治愈”疾痛,人们则不必再路途奔波、选择现代医疗。
20 世纪80 年代后,全国各地民间信仰逐渐获得更加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当年为了躲避时局的人陆续从缅甸返回境内、返回家乡;佛寺活动逐渐恢复;佛爷、巫师、草药师等部分人员归位,仪式治疗活动开始逐渐频繁与活跃。而此时也恰是村民从老寨位置搬迁至下寨的关键时期,下寨所在的山脚坝区距离乡镇卫生院1公里左右。此时,村民才真正开始能够接触与享受到现代医疗。而实际的情况是搬迁至山脚实现了村民与乡镇卫生院空间距离的极大拉近,村民在就医决策时却陷入了两难之选。那么这种“两难之境”为何发生,现代医疗的介入对仪式治疗等意味着什么。这或将对进一步挖掘多元医疗并非简单的共存等提供有力的支撑。
(一)死亡观念的对抗与就医决策的冲突
即便进入医学科学昌明的今天,人们对于死亡的理解与认知绝不仅仅是一件日常生活事件、一件纯粹的医疗事件,而更是一件与信仰世界紧密相关的精神实践。于长期践行万物有灵、南传佛教信仰的下寨人而言,他们对死亡的认知与实践更是如此。当现代医院更多地将“死亡”视为一种医疗事件时②张容南:《好的死亡为何重要——西方生命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对话的可能》,《道德与文明》2022 年第1 期,第148-158页。,尤其是在下寨人接触现代医疗初期,甚至是现在,人们对“死亡空间”——“死在村内”与“死在村外”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的判定。而这样的死亡认知则直接决定着他们在面临危及性命等疾病时的就医决策。
1998 年的时候,我在广州打工,突然接到我家里的电话,说我爸喝酒胃出血,快死了,让我赶紧回家。当时,卫生院医疗条件比较落后,什么都没有,我爹胃出血比较严重,需要输血,当时这里卫生院没有血液,我就打电话给县医院,县医院说他们也没有(血液),我们这都认为死在医院不好,当时我妈着急了,不知道怎么办,我外公就决定,把我爸从卫生院接回家,叫魂、拴线,其实当时只是一种心理安慰,根本救不了他,他们不给我爸在医院,一方面,医生也说救不了了,另一方面,他们担心,他死在外面,死在医院里不吉利,当时寨子里很少有人在医院里死,他们担心,我爸死了以后,他的魂会来找家人的麻烦……
当时,我爸已经昏迷不醒了,也不可能征求他的意见(是在医院还是回去寨子)。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赶紧把我爸送往卫生院,如果在医院里死了,让他的灵魂来找我好了,都和他们无关!我决定,我来负责!
接着,我就打电话,找熟人帮忙问哪里有血液。当时我爸在家里躺着,我就问卫生院可以派救护车吗,我让他问勐海县,他说他打了电话,上面不派。我说怎么可能,我自己打过去,勐海县的卫生院院长直接让卫生院的院长接电话,电话里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后面他们帮忙找血液,景洪问到了,最后紧急送过来。我爸才算逃过一劫,如果当时不输血液,只是叫魂的话,那早就没命了。①访谈对象:岩地(1983-,男),访谈地点:岩地家中,访谈时间:2021-01-17。
实际上,人们在搬迁至下寨所在位置前即已经接触到现代医疗且已经开始相信现代医疗的疗效,那么为何一直到了20 世纪90 年代,当地社会还会发生如此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呢?通过以上个案,我们可以看到,当地虽然建立了以现代医疗为主的卫生院,但由于当时医疗资源不足、医疗服务水平不高以及一些可能的人为因素等,村民们遭遇急病重症则只能“认命”——返回村寨进行仪式治疗。
有一点需要提及,涉及可能致死等的重大疾病时,村民会将死亡空间视为一个重要因素。“空间”成为当地人择取医疗体系的一个主导性因素,或许可以说,这一“空间”因素及其与死亡有关的认知构成人们就医决策的“拉扯”。而仪式治疗与现代医疗不同,仪式治疗师可以上门为病患驱鬼、叫魂等,同时还能运用药草辅助减轻病患的不适与疼痛。最为关键的是,这一治疗可以发生在家中火塘前、可以发生在村寨之中。万一病患去世,家属可以为病患举办丧葬仪式。在家中死亡被视为“正常死亡”,正常死亡的人在死后是可以进入寺庙享用后代所赕吃食等,这意味着可以进入轮回;而“非正常死亡”之人则只能沦为孤魂野鬼,无法进入轮回,更不能进入寺庙享用后代所赕的物品等。死亡空间的内外之分于下寨人而言意义重大。
以上个案的结局比较幸运,岩地的父亲在经过输血与治疗后得到了痊愈。这件事情几乎改变了岩地母亲对“叫魂”的认知。夏季的版纳湿热多雨,蚊子较多,尽管村民每周都要进行药物灭蚊,依然有逃过重重药杀的蚊子。2020 年暑假期间,笔者在小卖部门口遇到岩地的母亲,上去打招呼,却看到她身后有一缕青烟升起,她好像看出了“我”的疑惑,她转身示意,哈哈大笑起来。岩地的母亲为了防止蚊虫叮咬,身上挂了一盒蚊香。当“我”问起有关叫魂、“做迷信”的事情,她赶忙摆手示意:“身体不舒服就去医院,做迷信没有用!”尽管她如此表达,丈夫从医院回到村寨,依然举行了叫魂等仪式。尽管岩地坚持了现代医疗,但其并没有放弃属于他们的“传统”治疗实践——仪式治疗。在岩地看来,虽然现代医疗急救了其父亲,但是借助仪式治疗,可以将父亲由于生病住院,可能丢失在外的灵魂叫回家中且回到其身体,这样的做法有助于其父亲身体的康复。
如今,现代医疗的疗效逐渐被当地人认可,人们若遇急病重症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现代医疗。仪式治疗等传统疗法则作为补充。换言之,在下寨,人们针对不同的疾痛,可以选择一种医疗体系,同时又可以几种医疗体系“自由组合”用于疾痛的应对与治疗。而此阶段的仪式治疗并没有由于现代医疗的介入而销声匿迹,反而其与其他医疗体系一道构筑成多元医疗体系,共同致力于缓解与化解人们的疾痛。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发展至今的现代医学并没有实现对所有疾痛的治疗与治愈。“科学和知识虽然能够极大地帮助人们获得向往的东西,但是知识并不能完全控制变化,不能消灭偶然事故,也不能预料自然界的突发事件,或是使人为之事可靠并且完全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①马凌诺夫斯基:《巫术与宗教的作用》,史宗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金泽,宋立道,徐大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84页。。以上是马氏称之为“特殊的仪式活动类型”,人类学家称之为“巫术”的诞生背景。“知识不能完全控制的变化”具体化至下寨人有关疾病事件中,或许是“不能消灭偶然事故”的交通事故“致病”,或许是“不能预料自然界突发事件”的一场火灾“致病”,亦可能是“使人为之事可靠并且完全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之现代治疗的并非万能等。
(二)现代医疗的失灵与仪式治疗的出场
不得不说,现代医疗的救治无效与失灵给仪式治疗留下了空档与空间。在下寨,关于现代医疗的失灵与无效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一为“病患”到医院查不出病因却身体感知不适或疼痛;二为病患经过现代医院的治疗却被宣布救治无效。
对于借助高精尖的现代医疗设备都不能查找到“致身体不适”“致病”的原因时,人们对病因的想象较容易蒙上不可言说、表达不清的神秘色彩。不可言说的未知与表达不清的神秘感或将很快繁殖出人类的疑惑与恐惧。这对下寨人亦如此。若要破解迷惑、化解恐惧,下寨人首要的是找到致病原因,并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找到真正的病因至关重要。病因不成立又何以做到“对症下药以及药到病除”?
针对第一种情况,下寨人普遍的做法是反思与回顾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是否触犯了“什么不干净之物”。“不干净之物”主要是指可能引发灵魂与躯体分离的“鬼怪或神灵”。他们的应对之策便是仪式治疗。
面对第二种情况,针对经过现代医疗救治无效的一些疾病,如恶性肿瘤、脑卒中等一些大病重症,病患家属深知这类疾病短时间内无法治愈,仍坚持一边使用药物的同时,一边进行仪式治疗。在仪式治疗师看来,这类疾病多为恶鬼缠身,同时意味着若他们为病患驱鬼与叫魂,他们将面临恶鬼的攻击,严重者将可能丢掉性命。实际的情况是,大凡遇到人上门求助,仪式治疗师往往不能拒绝。常用的做法是几位仪式治疗师一起为病患驱鬼、叫魂等“治疗”。于病患而言,这是家属对其的“不抛弃不放弃”,于家属而言是尽可能尝试所有的治疗后的“不留遗憾”。
在这里,仪式治疗的重点非“治愈”,而是尽可能减轻病患及其家属的心理负担。正如杨善华所言,仪式治疗重在过程,这是乡土社会重伦理道德表达孝心或关怀的表征②杨善华,梁晨:《农民眼中疾病的分类及其“仪式性治疗”——以河北Y 县NH 村为例》,《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82-89页。。于病患而言,一方面借助“驱鬼”实现了与命运的抗争,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而言,仪式治疗师的“最后一搏”虽无力回天,但却可能实现了病患历经与命运抗争后的和解。
看着肝硬化腹水、极度痛苦的妻子隆起的腹部,岩赛总是想做些什么,哪怕缓解妻子一丝一毫的疾痛。张建世在《高原、山地与大海》中说,虽然我们能明显感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但当我们要真正认识与理解它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甚至有些被武断地被称为“落后”的东西,实际上它往往有自己的逻辑①张建世:《高原、山地与大海》,郑少雄,李荣荣主编:《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73-274页。。在玉儿肝癌晚期的个案中,玉儿所在的医院医生通知其家属可以准备回家与准备后事等。于玉儿及其所在的家庭而言,选择仪式治疗是“最后的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其丈夫岩赛想要尽可能缓解妻子疾痛的唯一可能做法,实际上,不论仪式治疗的效果好与不好,他都会选择,因为这是他“没有选择的选择”。一方面,他支付不起高昂的换肝脏手术费用,另一方面他不能看着自己的妻子死在医院,死在村寨之外的空间是其无法接受的,同时,他也无法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忍受病痛的折磨。仪式治疗是最后的尝试也是最后的应对之法。
前述可以看出,仪式治疗的出场看似是人们面对疾痛的被动走向与无奈选择,不如说是人们面对生命终将逝去的一种主动作为、积极面对与寻求生命意义的实践。病患、病患家属、仪式治疗师以及可能参与到仪式之中的病患的邻居、亲戚等共同促成了仪式治疗,并实现了乡村社会伦理道德观的表达及其对病患家属的一种情感照护。
在仪式治疗发展初期,由于现代医疗的缺位以及人们疾病治疗的现实需要与精神需要,人们将药草与神圣疗法“合二为一”应对疾病,一方面下寨人借助草药治疗躯体的病症与不适,另一方面则从仪式治疗的层面寻找致病的信仰层面解释。后遭遇政治运动的压制,一度“见不得光”,它却未真正脱离当地人的生产生活。即便被扣上“迷信”的帽子,村民对于仪式治疗的认知仍然是“这是我们的老传统,这是我们的文化。”现代医疗出现与介入下寨人生活后,表征科学的现代医疗虽然在治疗大多数疾病时能做到快速与高效,但针对疑难杂症的难以治愈,人们转身借助地方文化或传统文化寻求解释与心理安慰②余成普,李宛霖,邓明芬:《希望与焦虑:辅助生殖技术中女性患者的具身体验研究》,《社会》2019 年第4 期,第84-115页。。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段中的仪式治疗,无论其是否以“主角”的身份出现,人们对仪式治疗的需求与实践都是一以贯之的。这提示我们人们借助仪式治疗寻求文化范畴内合理化的解释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
三、仪式治疗意义的延续与发展
从“传统”至现在,仪式治疗过程的变化当然不是没有发生。总体而言,仪式本身的过程以及仪式用品变化不大。相对而言,仪式治疗是一个相对程式不变的符号,而人们对其的意义赋予与解读却有了新的拓展。
(一)仪式治疗与孝道履行
现代医疗尚未进入下寨社会前,仪式治疗与药草治疗等是下寨人主要应对疾痛的方法;现代医疗进入下寨后,仪式治疗(包括草药治疗)则不再仅仅是人们应对疾痛的办法,它的隐喻之义逐渐拓展与丰富,具体体现在那些经历现代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与无法在现代医疗系统中找到病因的病患中。仪式治疗的举行,意味着病患家属对于病患的不放弃、不抛弃,这是家庭伦理道德的遵循与坚守。否则,这在下寨看来,可能意味着照护的不足、与情感的冷漠、孝道履行的缺失,甚至是有损功德之事。
83岁的呀新已经住院输液近两周,不见好转,且已经无法进食,老人用微弱的力气嚷嚷着要回家、回寨子。家属咨询医生后,呀新回家的愿望终于如愿以偿。呀新的儿子见老人状态,恐难过此关。棺材已经购置好放在了家里,后事所需的物品也已经备好。呀新健在的亲戚朋友开始逐渐来到家里与老人道别。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老人已经返回家中一周了,作为儿子的岩L 却没有给老人“做迷信”,即仪式治疗。在下寨人看来,即便已经对老人采取了现代医疗。待老人返回家中,其家人仍必须对老人进行仪式治疗。不进行仪式治疗则可能意味着家属对老人的不孝。一些村民开始悄悄与笔者说:“这个你不要和他们说,老人家从医院回来,要搞搞迷信,试试草药,你看他们早早把棺材准备好,好像是等着老人死,哎!”①访谈对象:岩Y(1973-,男),访谈地点:岩Y家,访谈时间:2020-08-05。
老人儿媳的说法是:“看着老人快不行了,医生说可以回家了,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回来后,就喊了寨子的岩医生给她输液、打小针(针水),没想到后面回家后,她开始逐渐能吃饭,喏喏,你看看,一大碗饭,她都能吃完了……”②访谈对象:玉L(1964-,女),访谈地点:玉L家,访谈时间:2020-08-06。
在下寨社会,他们常挂在嘴边的“做迷信”“搞迷信”绝非与科学对立的“迷信”,而是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看着亲人遭遇疾痛而不加任何干预,即使这种干预可能不会产生疗效。在下寨,“做迷信”不仅仅包括请巫师占卜寻找超自然因素的病因,也包含草药师的口功治疗与草药治疗等。如下寨肝癌晚期病患在遭遇现代医疗“无效”的情况下,医生建议返回家中,以备病患的后事。而后病患丈夫不忍看到妻子的疾痛而不采取任何措施,借助当地人的“做迷信”,如下寨妇女主任所说,草药的使用可能没有办法治愈癌症,但确实可以极大地缓解病患的疾痛,这一提高病患生活质量的做法——使得病患尽可能行动自如与生活自理。
“做迷信”这一概念的形成与被下寨人挂在嘴边使用并没有很久的时间。“文化大革命”时期倡导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摧毁一切祭拜场所、器物,甚至批斗进行祭拜活动的村民,凡是涉及祭拜的都被视为“迷信”,都要被打倒,人们将巫师、和尚以及传统社会中从事祭祀相关的人与传统文化事项统统视为“与科学对立的迷信实践”,这种极端的实践深刻地镌刻在下寨人的话语表达与记忆中,以致后期党和国家扶正了民间信仰为民俗活动的合法性地位后,村民们依然沿用“做迷信”的说法。只是这一时期的“做迷信”更接近于民俗实践活动。也正是由于经历过特殊的历史时期,“迷信”这一词语在下寨人的思想认识中具有了双重意涵。于更多的下寨普通村民而言,它是指承传传统文化的民间信仰实践。
于一些绝对理性与科学的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而言,“做迷信”是指与科学对立的迷信实践,“是没有用的”。
下寨村民岩ML,男,今年38 岁的他至今单身,是寨子里十几个大龄男青年之一。常年在外打工的他非常反对寨子里的“做迷信”,提起身体不适时是否需要“做迷信”他情绪有些激动,对笔者说:“妹子,你不要相信那个迷信,不有(没有)用,要相信科学!”可是,他的父亲突发脑出血,在勐海县医院住院了三个月,老人脱离了生命危险后,岩ML 带着父亲回到了寨子。他接着补充道:“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了,以前我还能打工,现在医药费都花光了,没有办法啊,我也想给他住在医院里。那些都是迷信,不科学!”
我追问:“那回寨子后,有给他做过‘迷信’吗?”
坐在一旁,离异一年的岩S借着微醺的酒劲儿却一脸严肃地说:“我们布朗族,(生病了)都要做迷信,你不做就是不孝,送到医院治疗后他大哥前面带着老人的衣服去找过巫师了,巫师说,他去世的父母来找他,赕了衣服、吃的那些,不然可能要救不回来了。”
“不进行巫师占卜”是要被村民们“骂不孝的”。尽管岩ML 认为那是不科学的与“无效的”,深知不进行巫师占卜“可能的后果”的岩ML 的大哥早已经采取了行动,进行了巫师占卜与仪式治疗。
在下寨,大病重疾是必须进行巫师占卜致病因素的,尤其是长者、老人遭遇疾病时。一方面主要是从老人的主体性出发,绝大多数老人坚信生病不单单是因为细菌、病毒等因素。他们更加相信是“丢魂致病”。巫师占卜到病因后必须进行驱鬼或叫魂、拴线,重病老人的身心才能获得“踏实与舒服感”,正如一位村民们所说:“不管效果怎样,他(她)的心里会舒服点,你不做,他(她)心里会一直想着这个事情。”①笔者田野笔记(2020-08-11)。
另一方面,下寨人无法看着病患的家人遭受疾痛,而无动于衷或者不采取任何可能的干预,如果那么做则是有违伦理道德的。
当地人借助仪式治疗实践构筑起的地方道义世界,这一道义落在鲜活的生活中,则表现为借助仪式治疗形成的互助互惠组织。一方面表现在叫魂、拴线等仪式治疗环节中,病患的亲戚、邻居等会给予病患一定的费用支持。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病患及其家属与亲朋好友的道德与情感互惠之中。如上文中提及的“不管效果怎样,他(她)的心里舒服点”,于那些大病重疾病患而言,运用信仰文化的力量是其化解疾痛的最后应对之法。
(二)瘾君子及其仪式治疗
由于长久居住于深山之中,靠山吃山的村民很少有机会接触毒品。20 世纪80 年代,村民陆续从老寨搬迁至下寨,下寨距离缅甸仅一江之隔,便利的交通加上橡胶种植以及带来的“高收入”,以及打洛口岸的开放等综合因素,下寨逐渐出现了一些吸毒或贩毒人员。有意思的是,这些吸毒贩毒人员返回村寨时,其家属竟为他们举行叫魂、拴线等的“仪式治疗”。这与笔者所在的社会生活世界对待这些人群的方式大为不同,在笔者所在的社会,哪家若出现了吸毒或者贩毒人员,尤其是那些服刑回来的人,周围的人都会远远地躲开,甚至其家人都会与其断绝关系、中断往来。下寨人则不同,他们不仅不疏远这样的群体,反而邀请亲戚朋友共同为其举行叫魂与拴线仪式等,以上操作着实震惊了笔者,这是一个多么富有温情的村寨,而显得“我”所在的那个社会是多么的无情与冷漠。两种社会对这群人的做法让“我”陷入了沉思。
田野调查期间,笔者参与观察了一位“瘾君子”从昆明戒毒所返回村寨,其家人为其举行叫魂与拴线仪式的个案。仪式过程与笔者参与观察的其他仪式治疗及其过程、参加人员组成以及所用物品等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有一点需要注意,这次仪式已经是这位吸毒人员的第三次仪式治疗了,意味着其已经历经两次吸毒、戒毒,此次是其家人为其举行的第三次“仪式治疗”。
仪式结束后,准备饭菜的村民开始张罗参加仪式的亲朋好友的吃食,由于村民们对笔者已经非常熟悉,平时加之他们也不怎么避讳讲吸毒、偷渡等话题。在男人们看来,聊起这些话题,好像更能打开他们话匣子与激发起他们吃饭喝酒聊天的兴趣。当笔者以“吸毒是不是病的”问题开场后,刚开始相对安静的饭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坐在笔者斜对面的中年男子A认为需要看吸毒的种类以及是否上瘾,如果吸了不容易上瘾的毒品且很快不再吸,那么就不会上瘾,就不是病;如果吸毒上瘾了,且戒不掉的话,可以算是“病”了。关于吸毒是不是疾病,有一个重要的界限与界定,即“是否上瘾”。而罗伯特·汉对疾病的界定是“疾病乃是一种自我不想要的状况,或某种会导致出现这种状况的实质性威胁”①罗伯特·汉:《疾病与治疗:人类学怎么看》,禾木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6页。。A 对毒品是否属于疾病范畴的解释是“上瘾是‘瘾君子’吸毒不想要的一种状态”与罗伯特·汉对疾病本质的界定“不想要的状况”有一些共通之处。
在新冠病毒暴发之前,村民A在打洛车站长期从事摩托车载客的营生,主要是把来游玩的客人输送至打洛口岸或者缅甸掸邦第四特区的小勐拉。很多来打洛口岸游玩的游客多是冲着边境沿线的风景与民俗。新冠疫情暴发前,当地的旅游线路设计中有一项是掸邦第四特区一日游。2019年的1月,笔者乘坐的中巴车刚一驶入打洛汽车站的时候,他就百米冲刺般地冲向还未停稳的中巴车,问乘客要不要去口岸,要不要去小勐拉,还未等笔者从中巴车上下来,他第一眼就认出我②为了实现相对舒服的一种表述,文中使用了“我”与“笔者”,这两者都是指本文作者。来,非常真诚地笑着说:“你又来了,来,我送你回寨子!”笔者还没来得及答应,他就去后备箱帮忙提行李直接到他的摩托车那里了。一阵风的工夫,就到了寨子。
村民A经常将“游客”送往缅甸掸邦第四特区的小勐拉,或许由于其所从事的工作,接触到毒品不是一件难事儿。笔者看到他眉头紧锁了一下,又很快舒展开说:“要看是哪种毒品了,种类很多,如果是麻黄素,吃几天没有事,它(带给人)的瘾不大。如果是冰毒或者白粉就麻烦了,那个一沾上就不行了,以前都是提炼的,现在都是化学合成的,那个劲很大。上瘾了就是病,必须去戒毒所吃药、喝盐水(生理盐水)才能戒掉!又不能说是病,主要是他(她)的欲望大,管不住他(她)自己,他(她)不去碰那个,也不会上瘾!”③笔者田野笔记(2020-07-27)。
另外一位面生的布朗族中年男坐在笔者的旁边,普通话极其地流利,同时其与饭桌上其他男性用布朗话交流。根据笔者长期的调查,这不是笔者能够经常遇到的情况,这引发了笔者的好奇与进一步访谈。
当笔者主动去问他的名字时,他才微微一笑说:“我刚从监狱里出来,原本是无期徒刑,表现好,服了十七年出来了!我听我朋友说,戒毒所戒毒,刚进去,他们还会给你一点(毒品)吃,不然会很难受,后面就是喝生理盐水,不停地喝,一大罐一大罐地喝,时间长了,慢慢就好了(戒了)。”④笔者田野笔记(2020-07-27)。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当地村民的眼里,他们视“吸毒”亦病亦非病。视“吸毒”为疾病的人,认为上瘾的话必须借助戒毒的药物来治疗,应属于疾病的范畴。视“吸毒”非疾病的人认为,吸毒不是患病,患病是患者不想要的一个行为,而吸毒是人有意去获取毒品并吸食的行为。
而实际上,不管一些人认为吸毒是不是疾病,当吸毒的人戒毒归来,回到家庭,回到村寨就像生病住院回到寨子的“病人”一样,都需要村寨老人、亲朋好友参与到其回归寨子正常生活秩序的仪式之中。因此在这一仪式中,老人们祈福“病人”的健康不仅仅是希望“病人”获取身体的健康,更是希望他们能获得被村民视为“正常人”,拥有寨民身份的村寨一分子,经过仪式的过渡阶段①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重新获得健康的身体与灵魂。
在下寨,服刑人员出狱后的仪式实践与“仪式治疗”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解读。第一是服刑人员出狱回归村寨于其及家属而言,这与他(她)的出生、青春期、结婚与死亡虽不同,但也存在共通之处,也就是这都是他(她)的人生转折点,仪式的举行象征着他(她)与过去状况(因触犯法律而被监禁)的分离与告别。同时,也就是第二,其家属考虑到其与村寨日常生活“长期脱节”的问题,为了能够使其顺利地回归村寨的日常生活,仪式治疗发生了。这里的“治疗”便有了“希望其回归村寨正常生活”与赋予他(她)新身份的内涵了。第一点与第二点是紧紧衔接在一起的,“与过去状况的分离、向新阶段的过渡与新身份的结合”②刘易斯·M·霍普费,马克·R·伍德沃德:《世界宗教》(第11版),辛岩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19页。。第三是于服刑人员本人而言的,下寨原本被判无期徒刑的岩X出狱后令其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姐姐一家、哥哥一家以及曾经的友人一起到景洪机场接他,且为其举行仪式。这让其十分动容。
于其家人而言,这些事情虽然看似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于“曾经犯罪的人”而言,其意义非比寻常,这意味着他(她)重新被接纳、欢迎与爱,这是其获得“新生”的动力。回归村寨后,一场“叫魂”的仪式治疗紧接着举行,不仅至亲,邻居与友人们也会来参加他(她)的仪式,神职人员如佛爷、“布占”为其念经、年长者为其拴线、祝福。虽然说乡村熟人社会中有一套严格的道德规范,但是它也有另外一面,或可以称之为这个社会的“吐纳”机制。这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固然严格,却不是不分场合与情境的。相比于现代社会对于那些有过“案底”经历的人的远离与排斥,下寨社会借助仪式接纳这些有过“案底”经历的人而言,是极具人文关怀与值得现代社会反思的。
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是当具有“案底”的这群人进入社会,想要获得一份谋生的工作机会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他们虽经历了监狱的“劳动改造”与“重新做人”,但是社会是有“记忆”的,且它也有规避可能风险的考虑,这群人想要获得工作绝非易事。难以融入社会是这群人面临的最大的也是最难的问题。同时也是每一位从服刑人员出狱后首先担忧的问题。正如岩X 所说:“刚开始知道我可以出狱了很开心,但转念一想,我在里面十几年了,外面的社会(我)不适应该怎么办,当时我就想好了,如果家人不管我,我就还回克(监狱)!”③访谈对象:岩X(1976-,男),访谈地点:岩X家,访谈时间:2020-07-27。
岩X道出他们这个群体可能都会思考的问题,服刑出狱后的人,会有一部分不被亲人接纳,甚至排斥,同时又担心自身生存的基本问题,日新月异、发展迅速的社会是否能够给予他们一些解决温饱的机会?
下寨是中国万千乡村社会中的一个,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它有着熟人社会严格的、近乎苛刻的道德约束。但同时,我们看到,这一近乎严苛的道德约束的社会有着另外一个面向,它足够包容、有一套自己的“吐纳”实践与机制。借助仪式实践,下寨人真正“疗愈”了一个个刑满人员或者曾经的“瘾君子”等。此外,“疗愈”不仅仅体现在仪式本身的举行,也表现在下寨社会切切实实有考虑到这群人今后的生存问题。岩X 回归村寨后,村长在争取了岩X以及几位村干部的意见后,决定委以其护林员的职务。如此一来,岩X不但可以获取每个月的固定补贴与收入,而且还能让这些人与其他村民有所接触。这样其方能逐渐地融入下寨社会。
四、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本文运用个案的形式梳理了当地不同阶段人们实践仪式治疗的过程,尤其是当现代医疗进入,短时间内我们看到两种医疗实践的“碰撞”与“纠缠”,实际上则是现代医疗发生的空间与他们的死亡观之间的“摩擦”。一方面,人们对于现代医疗有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认知,另一方面,人们仍需要借助仪式治疗寻找面对未知、化解不可控因素与继续下去的信心、勇气与意义。同时,人们正在将新出现的事物纳入仪式治疗之中,为的是希望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舒缓、化解,甚至治愈一些特殊人群的“心病”与“瘾病”。总之,当地长期存在的仪式治疗,其治疗的对象或者作用的事件并非一成不变。
现代医疗进入到当地社会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被当地人逐渐接纳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关键的事件或者节点是有村民体验了现代医疗以及现代医疗可见的疗效。这些节点性事件出现之初,或许存在所谓“现代医疗”与“仪式治疗”的碰撞与冲突,实际上这一冲突并非治疗本身带来的“对抗”,而是治疗的空间与当地的死亡空间发生了碰撞与纠缠。在医学科学的强势权威之下,人们并不是不知道或者对现代医疗的“疗效精准与快速”视而不见。现代医疗结束后,人们返回村寨时,仪式治疗自然而然地“出场”,且至今不曾中断。尤其是针对那些现代医疗无法舒缓或者化解的疾痛,人们需要通过仪式治疗寻找某种意义层面的“疗效”。总之,我们看到仪式治疗及其意义在当地的延续,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仪式治疗意义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的“生产”与“延展”。村民不断地将新发的事情纳入仪式治疗之中,仪式治疗的内涵也在这些新生的事件中得到了丰富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