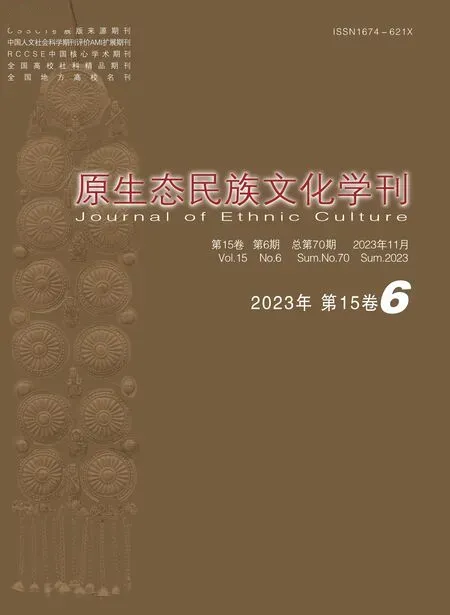多元医疗与文化整合:一个苗族移民群体的医疗实践
温士贤
一、现代社会中的多元医疗
疾病,在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都不可避免,疾病治疗因此成为人类社会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在疾病治疗实践中,不同民族群体形成了自己的疾病观念和治疗手段。诸多研究表明,疾病不仅仅是生命机体本身问题,同时也受到生态环境与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①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方筱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3页。。处于不同生态区位与文化体系中的群体,会根据自身的文化体系对疾病做出解释,并试图采取各种医疗方法加以防范和应对②聂选华:《民俗医疗与本土医药传承研究——以傈僳族的疾病认知及治理实践为例》,《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2年第4期。。医学人类学家赫尔曼·塞西尔(Helman Cecil)指出:“在所有的人类社会中,与疾病有关的信仰和实践是文化的一个中心特征。”③Helman,Cecil.Culture,Healty,and Illness.London:Wright,1990:7.可以说,一个民族的医疗体系既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他们生命观和世界观的重要表征。
在传统部落社会,由于对疾病缺少科学认知,人们多是将疾病与神灵世界联系在一起。早在1924 年,英国人类学家里弗斯(W.H.R.Rivers)发表《医学、巫术和宗教》一书,书中将人类的世界观划分为巫术的、宗教的和自然的3 种类型①W.H.R.Rivers.Medicine,Magic and Religion.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Co,1924.。在里弗斯看来,每种世界观都会衍生出一套与之相对应的病理学观念,进而导致疾病治疗方法上的差异。里弗斯的研究对后继学者产生深远影响,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大都关注到土著居民的疾病与医疗问题。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20 世纪初对特罗布里恩德岛的研究发现,巫术力量对土著居民的健康有着重要影响。在当地土著居民的观念中,“人只不过是巫术力量、妖魔鬼怪和黑巫术的玩偶而已。任何形式的死亡都是这种力量造成的后果”②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40页。。拉德克里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对安达曼岛人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当地土著居民认为“所有的疾病以及病死都是精灵所致”③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梁粤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在非洲阿赞德人部落,人们将疾病归咎于他人施加巫术所致,并相信通过巫医、神谕、魔法等仪式手段可以治疗疾病④E.E.埃文思-普里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覃俐俐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与阿赞德人一样,恩登布人也将身体疾病归因于神灵世界,他们对疾病的治疗大多按照顺势巫术原则进行,即认为对代表疾病的某种东西采取仪式措施即会对疾病本身产生相应的效果⑤维克特·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09-311页。。总体来看,在人类学研究的部落社会中,人们多是在地方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寻求疾病治疗方案。
实际上,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疯癫治疗史的研究发现,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同样经历过类似顺势巫术的治疗尝试⑥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20 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生物医学(中国社会习惯称之为“西医”)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主流医疗模式。各具特色的民间医疗手段,日益受到来自科学主义和生物医学的质疑与批评,主流观点往往将各种民间医疗手段视为“落后”与“不科学”的表现。实际上,各种民间医疗手段的采用并非人们观念的落后,其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在特定文化体系中形成的文化习性。在遭遇疾病困扰时,人们不自觉地从自身的文化习性出发寻求对疾病的解决之道。
诚然,建立在现代科技之上的生物医学是当前较为有效的疾病治疗手段。与此同时,现代生物医学与国家权力的紧密结合,赋予了生物医学的合法性与权威性。现代生物医学力图将人类身体视作标准化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身体间的生物性差异与社会性差异⑦余成普:《地方生物学:概念缘起与理论意涵——国外医学人类学新近发展述评》,《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然而,在面对一些民族群体特有的文化束缚综合症时,现代生物医学往往难以进行有效治疗,进而为各种形式的民间医疗手段留下生存空间。有学者指出,生物医学用群体概率来预测个体情况,探讨人类物种的普遍生物机制和过程,将个体与其所处生态和社会历史过程分开。因此,生物医学在处理大群体的瘟疫和灾难时具有显著成效。但对个体的很多疾病,尤其与个体生活和社会文紧密相连的慢性病和精神疾病却收效甚微⑧张文义:《社会与生物的连接点:医学人类学国际研究动态》,《医学与哲学(A)》2017年第10期。。时至今日,在诸多民族群体的医疗实践中,现代生物医学未能完全替代各种民间医疗手段,而是被嵌入到地方性的多元医疗体系之中。即便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欧美国家,在主流的生物医学之外仍存在形形色色的民间医疗手段。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移民群体要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中进行切换。移民群体的迁徙流动并非简单的身体位移,同时也意味着自身所依存的环境系统发生变化,进而需要移民群体在身心上做出积极调适。特别是对生存型移民而言,他们的迁徙流动是一个充满压力的过程,生存环境的改变、经济条件的限制、语言文化障碍等因素往往容易引发移民群体的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由于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多元医疗现象在移民群体中非常普遍①参见Porqueddu T,“Herbal medicines for diabetes control among Indian and Pakistani migrants with diabetes.”Anthropology& Medicine,24.1(2017):17–31;Main I,“Biomedical practices from a patient perspective.Experiences of Polish female migrants in Barcelona,Berlin and London.”Anthropology & Medicine,23.2(2016):188–204;Kujawska M,“Forms of medical pluralism among the Polish Community in Misiones,Argentina.”Anthropology & Medicine,23.2(2016):205–219; Rao D,“Choice of Medicine and Hierarchy of Resort to Different Health Alternatives among Asian Indian Migrants in a Metropolitan City in the USA.”Ethnicity&Health,11.2(2006):153–167.。实际上,在诸多民族群体的医疗实践中,并非生物医学与非生物医学的简单二元划分,而是将多元医疗手段进行对接并整合到自身既有的认知体系和文化习性之中。
各种民间医疗手段的广泛存在和普遍应用,与移民群体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习性有着密切关联。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习性定义为一套行为倾向系统:“条件制约与特定的一类生存条件相结合,生成习性(habitus)。习性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②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80页。在布迪厄看来,人的实践行为既不是由独立存在于个人之外的客观因素(结构、规则等)所决定的,也不是完全由人的主观意识所引导的,而是由一种既非属于客观因素又不完全属于纯粹主观意识的东西,即“习性”所引导的。尽管习性具有结构性、客观性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习惯是固定不变的。相反,习性是一个历史积累的过程,是一套具有创造性和开放性的行为倾向系统,社会个体也在有意识地选择和控制自身的文化习性。布迪厄的习性理论实现了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的双向互动,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情境下的实践活动。
对于现实世界里的普通行动者而言,习性才是他们感受和辨认某项“外部刺激”的意义并做出选择性反应的前提③谢立中:《布迪厄实践理论再审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特别是在医疗实践中,社会个体的就医选择无意识中受到文化习性的影响。与此同时,社会个体也会通过各种医疗实践经验,不断丰富与重构自身的医疗选择习性。本文借助文化习性这一理论视角,对一个苗族移民群体的医疗实践进行研究,旨在发现多元医疗背后的文化整合机制。20世纪90年代初,云南文山州的一些苗族群众迁徙到广东阳江农村地区代耕定居④参见温士贤:《落地生根:阳江苗族代耕农的土地交易与家园重建》,《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温士贤:《阳江苗族代耕农的生存策略与制度困局》,《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目前,在阳江定居的苗族移民群体有400余户2500余人。尽管从原本的社会文化生态中脱嵌出来,进入到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空间,但这些苗族移民仍保留着自身的文化习性和文化传统。在定居异乡的过程中,苗族移民群体遭遇诸多疾病困扰,他们采取仪式治疗、草医治疗、民间西医或是医院就医等多种手段进行疾病治疗。透过苗族移民的文化习性,可以洞见诸多民族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多元医疗与文化整合问题。
二、万物有灵信仰与神药两解传统
在长期的山地生活中,苗族人形成了自己的生命观与世界观,并衍生出一套与之相对应的疾病观念和医疗体系。在苗族人的传统观念中,人是灵魂与肉体的统一体,与人类休戚相关的自然界也充斥着各种神灵。人的灵魂一旦被自然界的神灵干扰纠缠,便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疾病甚至是死亡。即便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苗族人仍保留着这一信仰底色,他们往往将疾病与神灵世界联系在一起。
(一)万物有灵的世界观
万物有灵信仰被认为是原始宗教的一种典型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有限,往往认为世间万物皆是灵性的存在。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曾指出:“万物有灵观构成了处在人类最低阶段的部族的特点,它从此不断地上升,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深刻的变化,但自始至终保持一种完整的连续性,进入高度发展的现代文化之中。”①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9页。时至今日,万物有灵信仰依然影响着一些民族群体的认知逻辑和文化习性。现代人将往往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看作是两个分立的领域,但诸多部落民族倾向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视作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而万物有灵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鸿沟。
文山州位于云南东南部,境内以山地高原地貌为主,经济社会发展较为滞后。文山州的苗族人长期生活在闭塞的山地环境中,因此其传统的宗教信仰和民间医疗手段得以延续。文山州地方志记载:“苗族相信万物有灵,认为天地万物都由看不见的鬼神主宰着,生活的每个角落也都有无形的鬼神存在。”②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99页。在频繁迁徙流动中,苗族人仍保持这一传统信仰。即便是迁徙海外的苗族群体,也仍然保留着万物有灵信仰,并普遍采用传统仪式手段进行疾病治疗③黄秀蓉:《灵魂的世界——美国苗族传统萨满信仰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可以说,各种民间医疗手段对保障苗族人的身心健康和维系族群认同发挥着重要作用。
苗族人的万物有灵信仰,本质上说是对自然世界的遵从和敬畏,并力图在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找到联结点。在与苗族人生活较密切的自然世界中均可以找到对应神灵,诸如天神、雷神、山神、树神、土地神、药王神、家族祖先以及自然界中的各种鬼等等。在苗族人的传统观念中,对自然界的各种神灵要敬而远之,否则会招致自身的疾病和灾难。
在苗族人的观念中,人的灵魂由三魂七魄构成,只有三魂七魄牢牢附着于肉体时生命体才是完整健康的。疾病的发生,通常被苗族人解释为部分魂魄离开肉体所导致。因此,一旦发生疾病,人们便会从肉体和灵魂两方面寻找病因并进行相应的治疗。对于感冒发烧、身体外伤等常见生理病症,人们会求助于民间西医或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治疗。对现代医疗机构难以确诊和治愈的“怪异”病症,人们往往会将疾病归因于自然界的某些神灵所致。所谓“怪异”病症,是指在苗族人的医疗实践中难以理解或难以治愈的病症。尽管现代医疗机构可能会对这些“怪异”病症做出科学解释,但苗族人的认知结构中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现代生物医疗的科学解释。在这种情况下,苗族人会从自身的文化习性出发,求助于传统的仪式治疗,从心理和精神层面为患者进行疾病治疗。
(二)神药两解的医疗观
长期以来,生活在文山州的苗族人较难接触到现代生物医疗,只能依靠自身的民间医疗手段进行疾病治疗。相关文献记载:“在今文山州苗族地区,中医的传入是在改土归流以后,西医的传入则是民国时期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西医对山区苗民的影响并不大。”①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志》,第96页。近年来,文山州的医疗卫生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医院和卫生所等现代医疗机构在城乡社会普及,这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苗族群众接受现代西医治疗。然而,现代生物医学的普及并没有将各种民间医疗手段取而代之,而是形成了传统的仪式治疗、草医治疗和西医治疗共生并存的多元医疗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苗族群众的西医治疗并非单纯依靠正规医疗机构的专业医务人员,同时也包括民间西医治疗即苗族群众自发学习西医技术进行疾病治疗。
迁徙至广东阳江的苗族移民群体中,有魔公、草医和民间西医三类行医者,这为解决自身的疾病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医疗保障。魔公被认为具有沟通超凡世界的能力,一旦身患现代西医难以治愈的“怪异”病症,人们便会求助魔公进行仪式治疗。草医则利用草药进行疾病治疗,每位草医都有自己熟悉的药方和擅长治疗的疾病。民间西医则是部分苗族群众自学西医治疗技术,并根据自身掌握的经验技术用各类西药为患者进行治疗。
仪式治疗在苗族社会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历史文献及各类地方志中存在诸多记载。时至今日,定居阳江的苗族移民群体中仍存在较频繁的仪式治疗活动。苗族移民的仪式治疗可大致分为“叫魂”和“走阴”两种形式。叫魂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仪式治疗,从普通苗族群众到苗族魔公均可为患者进行叫魂。叫魂仪式一般借助烧香、画符、竖鸡蛋等仪式,使脱离肉身的魂魄归附于肉身进而使患者身体恢复健康。“走阴”指魔公在仪式中进入一种类似于萨满仪式的超凡状态,探寻是何种神灵使患者致病并对患者进行仪式治疗。一般而言,较轻微的病症会采用简单的叫魂仪式,对于久病不愈的“怪异”病症或重大疾病,苗族人会请魔公进行走阴仪式治疗。
近年来,随着西医的日益普及和苗族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现代西医治疗成为人们疾病治疗的主要手段。然而,当面对现代西医难以治愈的病症时,人们还是会求助于传统的仪式治疗。定居阳江乐安东门屋的苗族移民李正运②为保护研究对象隐私,文中所涉及人物均已做化名处理。抱病多年,对此他如是讲道:“我这几年经常性的肚子胀痛,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原因,没办法只能找我们信任的魔公做迷信。做过迷信之后会稍微好几天,但过一段时间又会反复。”诸如此类难以确诊和治愈的病症,苗族移民最终只能依赖仪式治疗以暂时缓解病痛和焦虑。
三、神灵庇佑下的行医实践
有学者指出,所谓的“多元医疗”是精英群体客位视角下的分类体系,并不能准确反映出普通民众的医疗认知图式①王瑞静:《整合药礼:阿卡医疗体系的运作机制》,《社会》2020年第1期。。实际上,普通民众对身边的医疗资源有自己的认知和分类图式。在苗族人的传统观念中,并非只有专业医务人员才有资格进行疾病治疗,普通民众也可以通过各种仪式或自学医药知识进行疾病治疗。在苗族人的多元医疗体系中,各种医疗手段并非独立运转的体系,在其信仰层面有着内在一致性。无论是魔公、草医还是民间西医,其行医实践背后均有自己的神灵信仰。
(一)神授能力与仪式治疗
仪式治疗在人类社会曾普遍存在,在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医巫合一的医疗传统。在今天的苗族社会中,仪式治疗活动仍较为普遍。魔公具有仪式治疗的能力,其具有巫医合一的特殊身份。在日常生活中魔公与普通人无异,仍要通过农业生产或进厂务工以维持家庭生计。对阳江苗族移民中的多位魔公访谈发现,他们大都有着类似的人生经历:即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经历过一场重病,在康复之后即获得仪式治疗的能力。在苗族人的解释中,这种即生即死的生命阈限状态即凡人与神灵世界交流的过程。海外苗族社会的相关研究表明,魔公(萨满)由神灵选中之后,还需跟有经验的魔公师傅学习才能获得强大的法力②黄秀蓉:《从神选萨满到法力萨满:美国苗人萨满当代传承机制探微》,《民族研究》2016年第5期。。就阳江苗族移民群体案例来看,魔公的仪式治疗能力主要来自神灵授予,而不需要同行内部的学习交流。
年近六旬的熊开和是阳江苗族移民群体中一位较有影响力的魔公。据其自己讲述,在12 岁那年生过一场大病,大病初愈后便获得了仪式治疗的能力。在他看来,仪式治疗能否起作用取决于魔公与病人之间是否有“缘分”。这种“缘分”说为仪式治疗的效果提供了很大的回旋余地,一旦仪式治疗失效,他们会将其归因于患者与魔公之间缺少“缘分”。从治疗成本上看,除必要的献祭用品外,魔公不会主动提出治疗费用,患者家属一般会支付一两百元作为酬劳。仪式治疗为苗族人的疾病治疗提供了一根救命稻草,即便苗族人自己也认为仪式治疗具有“迷信”色彩,但其治疗效果的或然性却给人们带来一丝希望。正是缘于这一点,仪式治疗才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
面对疾痛与死亡的威胁,仪式治疗可以从精神层面为患者解脱,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患者承受的病痛、压力与焦虑。相关研究表明,有些心因性、神经失调性的疾病吃药不一定能见效,对此类疾病只能通过对患者的心理和生理进行调节的方式来治疗,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体内在的自我康复能力③色音:《萨满医术:北方民族精神医学》,《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有学者认为,仪式治疗的本质是一种信息疗法,仪式治疗的学理基础在于,仪式实践过程所产生的强大信息流对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所产生的秩序修复过程。不同主体对同一信息的感知(应)不同,决定了相同的仪式实践模式,对不同患者可能产生不同的信息治疗效果①麻勇恒,张严艳:《创伤与信息创伤:医学人类学视域下的仪式治疗新解》,《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2年第4期。。从这一意义上说,仪式治疗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二)家族传承与草医治疗
在长期的山地生活中,苗族群众积累了丰富的草药知识并形成了自身的草医治疗体系。特别是针对跌打骨折、腰腿疼痛、风湿疾病、虫蛇叮咬等疾病,苗族草医治疗具有较好疗效。民国《马关县志》记载:“苗俗信鬼,有病不服药,惟请巫公禳改退送,或于野旷之地悬竿为记,击鼓吹笙,焚香奠酒,然后执斧椎牛,以祭祖先。……至于外科,又每有良药接骨生筋,其效如神,又复秘而不宣,流传不广,识者惜之”②何廷明,娄自昌:《民国<马关县志>校注》,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9页。。时至今日,苗族群众对传统的草医治疗仍具有较高依赖性。与仪式治疗相比,草医治疗具有较强经验性,草医医生需要对草药药性及适用病症有较为丰富的经验认知。
苗族草医治疗具有家族传承特点,每位草医医生都有自己家族擅长治疗的病症。陶文位家族是草医世家,其家族行医治病传统已延续四代人。陶文进自18岁开始跟随父母上山采药,逐渐熟悉各种草药药效及其适用病症,到28 岁时开始独立行医治病。在长期的行医实践中,陶文进形成了自己的治疗方法,尤为擅长治疗跌打损伤、毒蛇咬伤、胃肠疼痛等病症,苗族同乡遭遇病痛时多请他来治疗。陶文进家中供奉着家族传承下来的“药王神”,在每月农历的初九、十九、二十九焚香祭拜。在他的观念中,自己能够行医治病并治愈患者有赖于家族“药王神”的庇佑。
陶文进对西医治疗和仪式治疗并不排斥,在他看来各种医疗手段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如对治疗骨折、跌打损伤等病症,他会建议患者先到医院检查,根据医院X 光拍片检查结果对患者进行草医治疗效果会更好。对于自己无法治愈的疑难杂症,他会建议患者采取一定的仪式治疗。草医治疗成本较低且具有一定疗效,对于跌打损伤等外科病症,苗族群众更喜欢求助草医进行治疗。在适应现代社会过程中,苗族传统草医治疗面临着传承危机。在传统山地环境中,苗族群众与大自然密切接触,从中能够认识各类草药并能够将其用于疾病治疗。迁徙阳江定居之后,年轻人多进城务工,从而缺少认识各类药材的机会。陶文进的三个儿子现在均在外务工,没人愿意跟他学习草医治疗,其家族传承几代人的草医治疗技术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境地。
(三)自学成医与民间西医
随着现代医疗机构日益普及,少数民族群众对西医不再陌生,甚至一些少数民族群众自学西医进行疾病治疗。相关研究表明,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许多家庭都备有注射器并能使用注射器进行肌肉注射③刘小幸:《彝族医疗保健:一个观察巫术与科学的窗口》,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6-57页。。在阳江的苗族移民群体中,也存在自学西医进行疾病治疗的情况。实际上,在迁徙阳江定居之前,部分苗族群众已掌握一定的西医治疗技术。之所以自学西医,一方面由于苗族村寨交通不便,发生疾病难以及时去城镇医院就医治疗;另一方面,与到医院治疗相比,自己购买西药和医疗器具进行治疗成本更低。
定居阳江乐安的苗族移民李元光从25岁时开始自学西医,在谈及自学西医的经历时如是讲:“我为什么要自学西医呢?以前我们住在云南大山里,村里一个医生都没有。我的几个小孩经常生病,从村里到医院路途太远,有时候跑到医院医生又不在。后来,我就买书学习西医知识,慢慢地就掌握了静脉注射、肌肉注射这些基本治疗方法。”至今,李元光家中仍保留着《农村医生手册》《医院卫生员教材》等几本陈旧的医学教材,他的西医知识和医疗技术即是从这些书本上学到的。李元光自学西医技术知识,但在其信仰层面仍是传统的神灵信仰。在其家中祖先牌位旁,供奉着药王神龛位。自一次医疗事故之后,李元光便不再行医看病,但其家中仍供奉着药王神龛位。在苗族行医者的观念中,行医治病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因此,不管采用何种医疗手段都需要药王神的庇佑,唯有如此才能在行医实践中顺利治愈患者。
由云南文山迁徙广东阳江定居之初,这些苗族移民遭遇诸多疾病困扰,其患病率和死亡率较之以往大幅提高,诸如水土不服、精神疾病、交通事故、意外工伤等状况时有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各种病症与意外的发生是文化震撼在他们身体上的反映。在定居之初,这些苗族移民面临较大的经济困难,即便是治疗感冒、头疼等小病都要大家一起凑钱。为节省医疗开支,头脑灵活的年轻人开始摸索学习西医。实际上,自学西医的苗族行医者并非科学主义的信奉者,他们对疾病治疗的认知往往是将科学主义与神灵信仰杂糅在一起。由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在苗族人的医疗实践中,他们将西医治疗有机地嵌入到自身既有的医疗体系之中,并试图将多种医疗模式整合到自身的文化体系之中。
四、文化习性下的就医选择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苗族移民的就医选择也发生了变化。当前,苗族移民发生疾病会做出如下就医选择:对于较轻微的疾病,他们首先会求助于群体内部的草医和民间西医进行治疗;对于较严重的疾病,他们会到城镇正规医疗机构就医治疗;当遇到医院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时,他们则会求助于苗族魔公进行仪式治疗。在具体的疾病治疗实践中,他们会根据病症特点采取不同的治疗手段抑或采用多种治疗手段同时进行。可以说,苗族人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习性在无形中引导着人们的医疗选择。与此同时,这种开放性的医疗实践也在不断模塑和重构苗族人的文化习性。
在阳江苗族移民的医疗实践中,他们一方面相信现代西医所做的科学解释,同时也相信各种民间医疗的实证经验和文化解释。在科学主义的冲击下,苗族社会的各种民间医疗手段得以保留下来,很大程度上缘于苗族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习性。由于人类机体的复杂性和医疗认知的有限性,现代西医尚不能解决人类所有疾病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社会距离”较近的民间医疗手段①周爱华,周大鸣:《多元医疗及其整合机制——以青海互助县一个土族村落为例》,《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基于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习性,苗族人在自身的社会文化结构中赋予仪式医疗和草医治理以正当性和合法性。
在苗族人的观念中,仪式治疗更多是从心理层面发生作用,患者的身体康复还需要西医治疗进行配合。各种医疗手段可以相互补充,共同维护人们的身心健康。实际上,现代生物医学并不会天然地被各民族群体接受,它需要从文化上植入到各民族群体的文化认知体系之中。可以说,苗族社会特有的信仰体系,将仪式治疗、草药治疗与西医治疗有机联结起来,进而使苗族人医疗体系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在民间医疗实践中,各种医疗手段在功能上相互补充,为患者疾病治疗提供了多种选择方案。现代西医治疗手段更多地是借助医疗设备对疾病进行检查确诊,进而从病理学层面对疾病做出科学的解释并进行相应的治疗。然而,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患者致病的社会文化因素。相关研究表明,一些民族地区医院的医生认识到这一点,并鼓励采用民间医疗手段(包括仪式治疗)进行疾病治疗①张文义:《现象与现象的链接:中国西南边境多元知识体系的交融与衍异》,《开放时代》2021年第2期。。对苗族群众而言,正规医疗机构不仅是一个寻医治病的场所,同时也是他们接触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与此同时,正规医疗机构中的挂号、就诊、检查、缴费、复诊等一系列复杂流程也令他们感到陌生与茫然。苗族人在就医过程中,深刻感受到人与机器、人与科技、人与制度之间的张力。在现代西医治疗体系中,患者在医生和各种设备面前沦为一个被动的客体,其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主体性未能得到充分尊重。
与此同时,即便是对于正规医疗机构能够确诊的某些病症,患者也难以从自身知识结构中对其加以理解。由于语言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苗族人在就医过程中难以和医务人员就自身病情进行有效沟通。在患者的就医过程中,由于医患双方医疗知识的不对等,会导致医患之间的结构性不信任②彭杰:《知识不对等与结构性不信任:医疗纠纷中患者抗争的生成逻辑》,《学术研究》2017年第2期。。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正规医疗机构不能有效治愈疾病时,患者便会对其产生怀疑并回归到民间医疗中寻求解决。心理治疗的相关研究表明,对治疗本身的期待、对治疗者的信任、可信赖的安全感、获得病情的解释等因素构成疾病治愈的内在机制③曾文星,徐静:《心理治疗:理论与分析》,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4年,第8-13页。。从这一点来看,苗族社会的仪式治疗起到了类似心理治疗的作用与功效。
有学者指出,民间医疗所具有的生理性、心理性与社会性多层次疗效,是一些民族群体信任并采用民间医疗的重要因素④汪丹:《分担与参与:白马藏族民俗医疗实践的文化逻辑》,《民族研究》2013年第6期。。田野调查期间,笔者居住在杨发民家中,每天前来找他打针输液的患者络绎不绝。前来治疗的患者多是其亲友,他们可以用本民族语言就病症进行沟通交流。一般情况下,杨发民仅是收取十几元到数十元的医药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患者的就医成本。为方便治疗,一些患者甚至是在其家中吃住。民间西医治疗拉近了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为患者的疾病治疗提供了社会文化支持。
不可否认,西医治疗已成为苗族人应对疾病的主要手段,但各种民间医疗手段对解决苗族群众的疾病问题仍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各种民间医疗手段并非完全有效并且存在一定风险。在阳江苗族移民群体中曾发生过多起民间医疗事故,诸如注射器消毒不慎导致患者发炎、抗生素滥用引发副作用、仪式治疗使患者病情恶化,甚至有盲目使用草药使患者致死等等。尽管如此,苗族群众并未放弃传统的民间医疗,在他们看来西医治疗也同样会存在类似的医疗事故。特别是对于癌症等重大疾病而言,西医治疗也难以从根本上治愈,而且高昂的医药费用会使家庭经济陷于困境。多元医疗体系的存在,不仅为苗族群众的疾病治疗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其社会文化的连贯性与整体性。
五、余论
透过阳江苗族移民的医疗实践可以看出,多元医疗体系并非苗族群众愚昧落后的表现,而是他们积极利用各种可能的医疗资源进行尝试性选择。多元医疗体系中的不同医疗手段之间也并非矛盾对立的存在,它们相互补充并被有机地整合到苗族社会的信仰体系之中。从苗族社会多元医疗体系中的各类行医者来看,不论何种类型的行医者其信仰层面都保留着传统的万物有灵信仰,这也是不同医疗手段实现文化整合的内在机制。正是借助于传统的神灵信仰体系,苗族群众将现代西医治疗纳入自身的认知结构之中,并由此发展出一种新的多元医疗体系。可以说,多元医疗体系为苗族群众应对疾病提供了多种选择,同时也为他们面对疾病与生死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解释框架。
多元医疗体系之所以能够在诸多社会中保留下来,一方面缘于医疗行为具有较强的地方文化色彩,另一方面也在于今天的我们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万物有灵的信仰底色。正如泰勒所指出,“事实上,万物有灵观既构成了蒙昧人的哲学基础,同时也构成了文明民族的哲学基础”①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第349页。。对个体生命而言,疾病与生死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现代西医治疗尚不能解决所有疾病问题,进而为各种形式的民间医疗手段留下生存空间。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曾对现代医学刻薄地批评道:“多亏有了更灵敏的医疗技术设备,这些疾病才能被诊断出来,但目前尚无有效的方法治疗这些疾病,就连相应的希望也看不到。”②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文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260页。现代西医治疗在解决人类疾病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更多的恐惧、焦虑与不确定性。从这一点上看,各种民间医疗手段能够给病人一定的信心和慰藉。
疾病的发生都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们需要在没有充分疾病认知的情况下进行医疗选择。对苗族人而言,现代医疗机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场所,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代价和风险。在这种情境下,他们的医疗选择更多地依赖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习性。尽管各种民间治疗手段在现代社会显得不合时宜,但人们长久以来熟悉的文化体系无法被轻易抛弃。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苗族群众既不能抛弃固有的民间医疗传统,同时也无法拒绝作为主流的西医治疗手段,从而使得他们面对疾病问题时在多种医疗手段之间做出文化整合。苗族社会的多元医疗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是苗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链接与整合,同时也是苗族社会本土现代性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