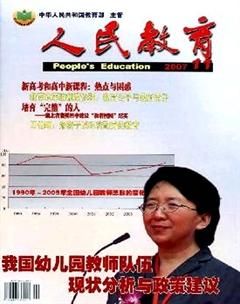培育“完整”的人
李帆
在湖北省襄樊四中,无论是管理还是教育教学,都充斥着一种“柔软”的特质。
正是这种特质,造就了襄樊四中的“和谐校园”。
做让教师有安全感的校长
有威不一定有信,我追求一个“信”字
2002年,苏超时被任命为襄樊四中校长。
上任伊始,一位曾在四中教过他的退休教师,特地找到他,讲了一个“牙齿与舌头”的故事:
“牙齿坚硬,舌头柔软。但是,当牙齿全部掉光的时候,舌头却依然完好无损……”
苏超时握着昔日恩师的手:“我明白了,请您放心!”
尽管如此,担任襄樊四中校长、党委书记,苏超时不是没有顾虑。
当时,襄樊四中刚刚由原襄樊市第四中学、市体育运动学校、市二十二中、襄城东街小学四所学校合并而成。学校1万多人的规模,背负着沉重的外债,内部人心不稳,各种矛盾凸现,各种关系亟待理顺。
全校上上下下都盯着苏超时。
苏超时一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自己做起,把行政管理人员和非教学人员的岗位津贴下调了三分之一,同时把教师的课时津贴翻了一番———合并不久的襄樊四中,在职教师不过400多人,却有80多个中层干部。他们都想留在管理岗位上,不愿意到一线上课。
这样一来,准备做中层干部思想工作的话没有必要说了。校长的行动,就是最好的引导。
“学校必须以教育教学工作为核心。”如今,苏超时的岗位(课时)津贴在学校排在100位以后,排在前面的,总是那些教育教学水平高、工作量大的一线教师。
五年过去了,四中的教师仍然感激苏超时的这一举措:没有激烈的冲突,全校的人心却得以安定。
苏超时上任后,第一次在教职工大会上的讲话,至今还像楔子一样钉在教职工心里。他说,“校长办公室的门永远向所有的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敞开”。于是,遇到工作、生活上的烦难事,老师们总爱往校长办公室跑。而苏超时不管多忙,都会乐呵呵地倾听、出主意、想办法。
在襄樊四中,苏超时的包容是出了名的。在他看来,当一名校长,就不能以自己的个人好恶为标准,要善待每一位教师,要容忍教师的非原则性错误。
每个新学年,襄樊四中都要进行全员聘任,让教师填写择岗意向表,选择自己想去的岗位。如果学校不同意,苏超时就会在择岗意向表上亲笔写上学校的意见,并返还给教师。
一次,一位刚来两年的新教师提出,要去教高三。考虑到他经验比较欠缺,苏超时没有同意。在择岗意向表上,他建议:“作为一名年轻教师,我们希望你能在高一、高二年级得到更多的锻炼,打好基础。”
没想到,意见反馈到老师那儿,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一把将校长的意见撕得粉碎。
苏超时虽然生气,但还是主动找到小伙子进行沟通。
事情圆满解决了,可别的教师看不下去:“苏校长,你啥都好,就是太过‘柔软,少了一点威信。”
苏超时笑了笑:“有‘威不一定有‘信啊。我追求一个‘信字。”
其实,襄樊四中的老师心里明白,苏校长这种管理方式既源于他的个性,更源于他的管理理念———在苏超时看来,好的校长是一个能够给教师带来安全感的校长。要达到这个目标,除了校长个人的修养外,关键还得有制度的保障。
“只有制度公平、公正,才会让每位教师都有安全感。”苏超时理解的“安全感”,不仅是情感上的关怀,更是对教师的尊重和信任。
2005年,襄樊四中在高中部推行中层干部任用机制改革,对所有的中层干部实行公开竞聘。竞聘方案出来后,每一道程序都向全体教职工公示,民主测评的结果也现场公布。
在竞聘答辩的环节,需要由专家组成员出题,对竞聘者进行考核。出题的是四中一位特级教师。这位老师把题拟好后,想把题目拿给苏超时看一看。出乎她的意料,苏超时拒绝了:“题目明天直接拿给专家组成员,一切按照已经定好的程序来做。”
在制度面前没有例外,校长也是一样———苏超时的坚持,换来的是中层干部任用机制改革的顺利进行。高中部39个中层干部,一下子减少到23人。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找校长“走后门”、“扯皮”。
公开透明的制度,让平等、公平地对待每一位教师成为可能,也让教师真正拥有了安全感。
“校长只有把教师放在第一位,教师才会把学生放在第一位。更重要的是,我做的任何事,学生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会对他们的将来产生影响。”对苏超时来说,做校长不是一辈子的事,做人才是一生的功课。
“六减一等于零”
协作是利己的最佳前提
在襄樊四中,常会听到教师说,“六减一等于零”、“二十减一等于零”———对于高考来说,一个班六个科任老师,一个老师的工作没做好,这个班就会受影响;一个年级二十个班,一个班掉了队,这个年级的工作就上不去。
这样的协作意识,不知不觉中化到了襄樊四中教师的骨子里。
王政良,学校教务处主任,特级教师。2005年与他同在一个年级的,有一位青年教师小赵(化名)。小赵虽然年轻,但人聪明、刻苦,几年的时间,就当上了毕业班的班主任。
進入高三,细心的王政良发现,小赵老师的工作不细致:别的老师在教室接受学生咨询的时候,小赵却在办公室里上网、玩游戏;同一个内容,别的老师讲两节课,小赵却一节课就讲完了……
王政良主动找到小赵:“这节课内容很重要,恐怕一节课的时间不够。”
小赵回答得很干脆:“我知道了!”
一回头,小赵仍然我行我素。
眼看高考临近,王政良老师着了急,找到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杨继禹:“杨校长,你能提醒一下小赵吗?”
可是,年轻的小赵听不进去:我班学生的基础不错,犯得着费那么大的劲吗?学生自己会处理好的。
高考结束,小赵所在的班拖了年级的后腿。
看见王政良老师,小赵很惭愧:“没有听您的意见。”
其实,像王政良老师这样全心全意帮助其他教师的,在襄樊四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教育得靠合力起作用。”副校长杨继禹说,自己在四中工作了近三十年,四中教师间的协作精神,就一直没断过:在坚持了三十多年的集体备课会上,没有老师会藏着掖着,好的做法总是第一时间与大家共享;在长达几十年的“老带新”制度中,一批批教师无私地把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传授给年轻人;多年来,四中老师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教案放在办公桌上,以方便其他老师作参考……
对协作精神,四中老师这样阐释:“一个人的智慧是火花,大家的集体智慧是火炬。”
而校长苏超时说:“协作永远是利己的最佳前提。”因为,在协作中,每个人都会得到进步。这个时代,一个人不可能“包打天下”,要想利己,必须利人,所以,襄樊四中的全体教师都要把协作放在首位。
如今,“协作利己”已成为襄樊四中教师的习惯,也成了默契:大家在协作中共享资源,在共享资源中提高自己———这样的共识,在襄樊四中营造了一个“磁场”。这个“磁场”看不见,摸不着,但确确实实地存在着。
进入襄樊四中的教师,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被这个“磁场”所同化,也情不自禁地被这个“磁场”所吸引。
2001年,襄樊四中有6名教师考取了教育硕士;本省的另一所中学也有7名教师考上了。
毕业时,另一所中学的7名教师全部辞职而去,校长勃然大怒,宣称:不准老师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实在想读的,必须先辞职!
但在襄樊四中,不仅这一年参加学习的6名教师回到了学校,而且到现在为止,所有参加过教育硕士学习的22名教师,全都按时回校———他们舍不得离开襄樊四中这个和谐的精神家园。
“你是我们的精神妈妈”
如果学生不爱你,说明你的心离他们不够近
从1981年进入襄樊四中,苏超时先后担任物理教师、学校团委副书记、校办主任、校党委副书记、校党委书记、校长兼党委书记。整整21年的时间,他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校长。
多年的教育教学经验,让他深知,再好的教师,如果不能赢得学生的爱,就无法走进学生的内心,也就无法谱写出师生间的和谐之歌。
为这,襄樊四中要求,每位老师都要把师生关系的构建,当作一个教改课题去探索。
2003年,高一的英语老师刘红云,临时给别班代课。
上课铃一响,正走进教室的刘红云迎头撞上了一个从教室往外冲的男生。
刘红云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上课了,你到哪里去?”
“我要出去,你不用管我!”
奇了,还有这样的学生?
“我才不信留不住你!”刘红云使尽力气抓住他的衣服。
无法走掉的男生急得面红耳赤,猛地,右手握拳往墙上砸去。“梆梆……”男生手背上的皮被蹭破了,血开始渗出来。
刘红云心中一痛,抓住他的右手,用右手小指钩住他的右手小指,直视着他:“咱们拉钩,上课必须坐在教室里!”
下課后,刘红云向其他老师了解到,这个男生叫张影(化名)。进校时成绩不错,但不知怎的,厌学了,成绩一落千丈。
从此,刘红云对他多了一份关注:以后刘红云上课,张影果真不往外跑了。但他也不学习,只是睡觉、说话,有时还在课堂上做起广播体操———这个学生的举动让刘红云哭笑不得。
高二文理分班,巧合的是,张影被分到了刘红云的班上。
“当时,我头皮都发麻了。”开朗的刘红云双手比划着,“我真的怕他,我不敢要他”。但电脑分班是不能调换的,就这样,刘红云“不情愿”地当上了张影的班主任。
张影的问题还是一大堆。他拒绝上早自习,下午自习课常去踢足球,上课不时地接老师的话茬儿,有时,回答问题还故意模仿老师的地方话口音,把“2”说成“饿”,搞得课堂笑声一片。
刘红云急得不行:这班主任该怎么做?来硬的,只会让张影更加叛逆;来软的,他可能会更加张狂。
事情在不经意中,有了转机。
刘红云有个口头禅,就是把学生喊“儿子”。一次,无意中,刘红云对张影喊:“儿子,过来。”然后,顺手拉起了张影的手。让她吃惊的是,不像第一次,张影的手是硬的,努力想挣脱她。这一次,他的手是软的。
后来,张影的父亲告诉刘红云,那天,张影回去对他说:“今天,老师喊我儿子了。”爸爸赶紧趁热打铁:“老师都喊你儿子了,你还不好好学习?”
师生的心,随着一声“儿子”而慢慢靠近。张影常常找刘红云聊天,他看刘红云的眼神也开始改变,对刘红云的意见也能听进去一些了。
刘红云也开始努力去发现张影身上的优点:聪明,乐于助人。老师冬天刚进教室,热气凝结在眼镜上,他会马上把眼镜布递过去;他的理科成绩不错,常常会主动给大家讲解题目;他模仿能力强,能表演电影中的长段对话……
“这是一个多可爱的孩子啊!”刘红云的赞叹没有直接说出来,可她的一举一动都在不断地向张影传达着这个信息。
张影违纪的情况越来越少,成绩也渐渐回升。2005年,本来对升入大学失去信心的他,考入了一所大学学习建筑。
在离开襄樊四中的时候,张影对刘红云说:“我的妈妈管了我的物质生活,在精神世界里,你就是我的妈妈!”
像刘红云一样,襄樊四中的老师都努力成为学生精神世界里的“妈妈”、“父亲”或“兄长”。毕竟,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只有老师找到了通往学生心灵的大道,只有师生间的融洽,才能唤醒学生的生命感与价值感,从而让学生在和谐的师生关系中成长为一个“和谐”的人。
面对如何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这个难题,襄樊四中人的答案,既简单,却又发人深省:如果你的学生不爱你,那么,说明你的心离他们不够近。
让学生做最好的自己
不要只看到一片花瓣,却没有看到整个花朵
襄樊四中是省级示范性高中,有很高的社会声誉,也因此更多地面临社会对学校升学率的高要求。
可是,苏超时却常常提醒教师:对学生,我们不能有“别人能考好分数,为什么你不能”的想法。学生各有特长,作为教育者,我们应该让每一个学生都和自己比,成为最好的自己,而不是最好的“他人”。
这样的“提醒”,符合教育规律,但在现实中,却要受到极大的考验。
何冬丽,在进入襄樊四中的时候,成绩在班里靠后。面对从全市各个学校走出来的尖子生,她很痛苦,一时间找不到方向。
教语文的杨老师看在了眼里。通过观察,她发现何冬丽普通话挺标准,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
如何帮助何冬丽在这方面成为“最好的自己”呢?
高二时,机会来了。襄樊四中组织了一次演讲比赛,优秀选手可以代表学校参加襄樊市的演讲比赛。
杨老师找到何冬丽,鼓励她去参加比赛。
何冬丽既高兴,又担心:马上要期末考试了,自己成绩本来就不好,如果再花时间去准备演讲,影响了学习可怎么办?
“你这方面有特长,为什么不给自己一次机会?”见何冬丽有些犹豫,杨老师为她鼓着劲。
可是,何冬丽的父母有些担心:难道有比考试更重要的事情吗?
他们找到杨老师,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我们不能只关注孩子在高中的三年时间,而要关注她是否能成长为一个阳光的孩子、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杨老师建议家长,不要让何冬丽生活在只有分数的精神世界里。
毕竟,如果一个学生只是在分数上表现了自己,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等于根本没有表现自己。如果教育者也只关注于学生的这种片面性表现,也就根本算不得是教育者———他们只看到了一片花瓣,却没有看到整个花朵。
襄樊四中教师的做法,在社会看重升学率的大背景下,难能可贵。
那次考试,何冬丽的成绩稍有退步,但老师一句责怪的话也没有说。
那次比赛,何冬丽脱颖而出,顺利地参加了市里的比赛,并最终取得了全市第一名的好成绩。曾经自卑的女孩,绽放出了笑脸。
更重要的是,何冬丽发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她以演讲作为突破口,带动语文成绩提高,最终带动各科成绩整体上升。高三毕业时,她考进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学习播音与主持专业。
“要让学生达到自己发展的上限。”在各个场合,苏超时总是不失时机地向教师们灌输这个观念:“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每个教师要时刻自问:‘我是否为学生成为独特的这一个而尽了全力、而提供了最大的帮助和服务?”
为了强化这个教育理念,苏超时曾向教师讲过这样一则寓言:一个水罐子完好无缺,而另一个有道裂缝。每次打水回到家,好罐子都装着满满一罐水,而有裂缝的罐子只能打回半罐水。
有裂缝的罐子感到很惭愧,对挑水人说:“因为我的缺陷,你没有从辛劳中得到足够的回报。”
可挑水人对它说:“你注意到了吗?挑水的小路上,你那边长满鲜花,而另一个罐子那边却没有。那是因为我知道你的特点,就在小路的这边种下了花种。每天打水回来,你就给它们浇了水。”
“我们要做‘挑水人,把那些在别人眼里是‘有裂缝的水罐的学生,看作能够浇灌花朵的源泉。”苏超时说,襄樊四中要做的,就是为这些孩子撒下美丽的“花种”:为这,学校每年都会举行“小发明、小制作、小论文”比赛;鼓励学生在校园网开设自己的网页、网站;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军营、乡村、法庭和社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举办体育周、艺术周、科技周、演讲比赛、诗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学校搭建的各种舞台,让学生在充实了学习生活的同时,也完善和发展了自我。
讓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绝不能让学生学得只剩下分数
考入襄樊四中的,大都是一些成绩优秀的孩子。比起别的学生来,在学习上,他们让老师操心少一些。
但是,襄樊四中并没有因此减少自己教育的责任。
“我们要培养的是‘完整的人。”苏超时这样解释“人”字:一撇是智力因素,一捺是非智力因素。只有前者没有后者,趴下;只有后者没有前者,卧着。只有两方面都兼顾,“人”才能站立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大写的”人。
一次,语文特级教师韩锐阅读学生的周记,看到学生写了这样一件事:同班的刘坤(化名)在父亲来看望他时,表现得很不耐烦。
这个细节立即引起了韩锐的注意:一个不知道感恩与爱的学生,怎么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呢?
从那以后,韩锐悄悄地观察刘坤。这是一个大家眼里的“优秀”学生:出身贫困的农村家庭,学习刻苦,成绩也不错。不过,与城里的同学在一起时,他总是显得很自卑,难道他对父亲的不耐烦与这有关?
韩锐找到刘坤:“你是不是有点烦你的父亲?”
刘坤点点头。
“能告诉老师为什么吗?”
长时间的沉默。终于,刘坤告诉韩锐老师,到了四中读书,和别的同学一比,自己很沮丧,因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不能帮助和呵护家庭的人。
韩锐没有批评他,而是对刘坤说:“你能给老师讲一讲你的父亲是怎样的人吗?”
在刘坤的回顾中,父亲是一个不得志的人,但为了支撑起家庭,一直勤奋地劳作着。
他告诉韩锐,有一件事曾让他非常感动:一次,他和父亲从田地里劳动完后,走在田垄上。父亲的脚被一块玻璃划破了。他一脚就把玻璃片踢到排水渠里。可是,父亲马上跳进排水渠,把玻璃捡了起来,并告诉他:“来年别人挖渠,扎到脚怎么办?”
说到这里,刘坤的眼睛湿润了。
在下一次作文课上,刘坤写了一篇作文《我自豪,我是农民的儿子》。
“抓学生人格的完善,应该从细节抓起。”韩锐老师说,我们绝不能让学生学得只剩下分数,学校应该是健全人格的熔炉。对学生来说,除了成绩,更要重视培养他们的感恩、激情、正直、宽容、互助协作的精神和耐挫的能力。
只有这样,学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人”;也只有这样,学校才算是真正完成了教育的使命。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育者必须牢记:一个学生,对襄樊四中来说,只是万分之一;但对他的家庭来说,却是百分之百。
为了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除了言传,襄樊四中的教育者更注重身教:校长和老师经常无偿地资助贫困学生;学校建立起了“蓝天工程”基金会,号召学生把勤工俭学的收益捐给基金会,以帮助困难同学……
良好的品质是可以传递的。
来自农村的耿志伦,父亲去世,留给他的是年迈的奶奶、体弱多病的母亲和几万元债务。作为困难学生,他每月可以领到学校100元的补助金。可是,每次领到钱,他都会分一半给班上另一位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毕业时,耿志伦以高分考取了西安交大,而得到他帮助的同学考上了清华大学。
“我们希望,学生在离开襄樊四中的时候,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只是一个考试的能手。”苏超时说,只有和谐的教育工作,才能培育出和谐发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