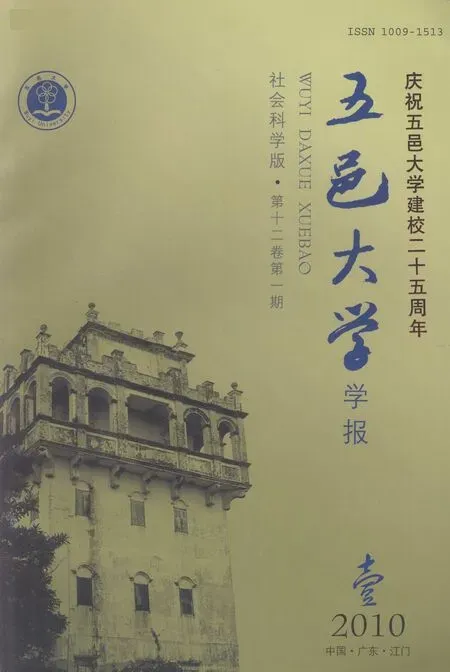当代法治背景下的传统礼法关系新释
屈振辉
(湖南女子职业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当代法治背景下的传统礼法关系新释
屈振辉
(湖南女子职业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中国传统法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以“礼”为其本土资源。在进行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时,仍然不能忽视“礼”的传统。在新的法制背景下,传统礼法关系对当代法治的借鉴意义主要表现在划分道德与法律的边界、推进道德的不断法律化、引导法律的不断道德化和建构德法同治模式四个方面。
当代法治;礼法关系;本土资源;借鉴意义
礼法关系是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的重要视角,“礼”与“法”的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的本质特征和文化渊源。“礼”从原始社会中的宗教祈福仪式蜕变为阶级社会中的强制性法律规范,意味着它既是中国法的滥觞,又从根本上左右着传统中国法的发展。“从总体来说,整个中国古代法制历史始终受礼制的支配和影响,一部中国古代法制史实是礼法合治的历史。这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1]“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精髓,中国自古就是崇尚德治却偏废法治的国度,道德始终在法治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2]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法治进程显著加快,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从法治的本土资源中寻找积极因素。由于礼的实质是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基本规范,在探究传统礼法关系对当代法治的借鉴意义时,法律伦理学就成为最重要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法律伦理学研究对于正确评价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3]13-14本文正是以此为研究理论起点,探讨传统礼法关系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借鉴意义。
一、“出礼入法”:划分道德与法律的边界
在有关中国法的起源问题上,“刑起于兵”、“法源于礼”,已经得到人们的公认。如果礼是社会道德关系的反映,那么,“法源于礼”揭示的就是法源于道德的事实。“法的发展可以逻辑地划分为三大阶段:首先是法律与宗教、道德浑然一体,此为‘混沌法’;其次是法律走出宗教、但仍与道德不分,故乃‘道德法’;最后是法律进一步与道德分离而独立化,便是‘独立法’。”[4]前者占据着中国法的主流,后者的出现则是近代之事。而中国传统法律的特征之一,就是“法”与“德”的关系模糊不清。“在中国古代,也有模糊道德与法律的界线,或者说以德代法的倾向。”[5]这种“法”、“德”不分的传统,至今仍对中国社会有着重要影响。不过,这种状况在中国古代也并非绝对,“出礼入法”的论断就是最好的例证。所谓“出礼入法”,就是对严重违反“礼”的行为必须加以刑罚制裁。礼刑结合、以礼为体、以刑为用,出礼入法或出礼入刑,正是中国封建法律体系的特征。如上所述,若礼是社会道德关系的反映,就可这样理解“出礼入法”:当人们逾越道德达到某种程度时,必然会受到法律的调控和规制,“法”与“德”之间必然要有明晰的边界。这对当代中国法治是重要的借鉴。
法治现代化在当代中国虽已具雏形,但因历史上“道德法”的长期存在,“法”、“德”不分的现象还很普遍。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缓慢,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古人对此的认识并不是模糊不清的。“法”、“德”的分离在中国东周以后就已出现。儒家传统虽在整体上力主德法融合,但其中仍有不少德法分离的星火。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者荀子就提出:“礼者,治之始也”,“法者,治之端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他认为“法”是由“礼”所派生的,这实际是表明了“德”与“法”究其根本是“源”与“流”的关系,当然,其中也蕴含着“德”、“法”有别之义。法家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德”、“法”分离的思想。“‘不法先王,不是礼义’、‘法为天下之至道’、‘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等偏激法治观念的蔓延,则标志着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越来越远。”[3]32德法融合的思想虽从汉代起开始成为主流,但人们对“德”与“法”的区别却愈来愈明晰,“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以及“出礼则入刑”,这些论断都出于东汉时期。大唐王朝虽主张“一准乎礼”、“德主刑辅”,但对于“德”与“法”关系的认识仍是明晰的。唐太宗更提出了“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以及“失礼之禁,著在刑书”等众多精辟论断。[6]353其中后者将刑的作用归于禁止失礼行为,用现代话语表达就是法律是底线道德,逾越道德底线的行为必然要受法律的制裁。中国社会自宋后进入了“以德代法”的时代,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取得了统治地位,它对社会的调控功能甚至超越了封建法律,德礼与刑法的界线从此在中国开始变得模糊,而此前道德与法律依然处于分离状态。这表明中国传统社会虽在总体上“德”、“法”不分,但期间并不乏“德”、“法”分离的主张。这些主张值得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借鉴。
二、“引礼入法”:推进道德的不断法律化
将道德视为立法的重要素材,这是道德法律化的理论基础。“所谓道德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是指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7]道德的法律化是法律生成的主要途径,“引礼入法”是对其最为集中的概括。“道德在中国古代被誉为‘法上之法’,法律史上所谓的‘引礼入法’,就是法律的道德化。”[8]“引礼入法”其实就是把道德原则引入法律,把道德作为立法的精神,并直接成为法律规范本身。
“引礼入法”思想最早发端于先秦时期,“荀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将礼与法结合起来,以‘法治’充实‘礼治’的思想家。他引礼入法,将体现贵族利益的旧礼改造成了维护封建官僚等级制的新礼”。[6]84“引礼入法”思想的正式确立是在汉代,董仲舒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董氏以儒家典籍,六经之一的《春秋》作为判案的依据,便是他为调合儒法两种思想实际上做出的一种努力……它以一种特殊方式开启了中国古代法律史上一个伦理重建的主要时期。在此期间,儒家以其价值重塑法律,系统地完成了儒家伦理的制度化与法律化,结果是在继承先秦乃至青铜时代法律遗产的基础上,将礼崩乐坏之后破碎了的法律经验补缀成一幅完整的图景,最终成就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完备体系。这一过程亦即是后人所谓的‘以礼入法’,我们名之为道德的法律化。”[9]传统儒家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引礼入法’的过程,不但是使法典的制定贯彻儒家的基本精神和原则,还把具体的礼制规范引入法律,以确保法律的强制实施过程本身就是道德的推行过程,它不但是使法律成为所谓‘最低限度的道德’,还要使法律成为教化成俗的实现德化天下的至善目标的手段。它使法律与道德一体化的过程,不但在形式上消除了法律所独具的形式和技术上的独立意义,还从本体上消除了法与道德的争论。”[10]此后中国才开始真正的“礼法融合”。
道德的法律化在当代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社会的制度文明建设,也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极大提高。“引礼入法”、促进道德的法律化是中国法的传统,从中可以得出诸多有益启示。一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礼仪、廉耻的国度里,要实现法治,必然需要借助于道德的力量……法律规范应以道德准则为标准,‘引礼入法’,将符合人们道德准则的行为规范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使道德法律化”[11]。二是在公德即全社会公认道德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律,不但会大大减少法律运行的社会成本,最重要的是还能稳定基层社会的秩序。中国封建统治者们正是以“礼”的道德教化形式,以最少的法制成本换得了社会的稳定。三是道德应当在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发挥导向作用。有些伦理思想虽与现实生活相去较远,但却能对法律产生导向性影响。
三、“以礼统法”:引导法律的不断道德化
以礼统法,是指礼也就是道德应该贯穿法律的全部,法律应当显现出道德的内在要求及精神实质。在法律伦理学研究领域中,法律道德化也是重要命题。所谓法律道德化,就是使法律更加符合道德的要求,更加彰显出道德价值的要求。公平、正义等许多道德理念要体现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价值追求当中,“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12]。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道德化的作用形式是与“礼”相联系的。“在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化现象历来十分严重,甚至形成长时期的‘礼法文化’,合礼即合法,合法即合礼,道德是制定、判断法的根本标准;法是好是坏……一个人是否遵法守法都以‘礼’为准绳。”[13]这实际上就是“以礼统法”。中华法系在“以礼统法”方面可谓登峰造极,甚至达到了“礼法不分”、“以礼代法”的境地。礼为中华法系打上了深深的伦理道德烙印,每当读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类语句时,就会强烈感受到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脉脉温情。鲜明的道德色彩是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也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
自清末修律以来中国大规模引进西方法制,以至被划入大陆法系范畴,许多中华法系的优良传统早已荡然无存。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在西方源远流长,近代又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故而西方法律表现出鲜明的“重理性、轻德性”倾向。带有这种倾向的西方法制传入中国,导致后者对崇尚德性、以礼统法传统的摒弃。“以礼统法”、促进法律道德化,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颇有借鉴意义。根据这个传统,立法应符合道德要求,即所立之法应当是具有道德合法性的“良法”。“法律存在本身就是人类创造出来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的,最终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是它的终极道德依据。”“既然法律对于道德如此重要,它本身就应当是合乎道德的,应该拥有道德的合法性。”[14]另外,立法时也应注意对其进行道德方面的考量,尤其是对中华道德文化中有益因素的积极汲取,从而摒弃西法的冷冰冰而融入中国式道德的温情。“在传统的中国人心目中,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不仅相通,甚至可以理解为是‘三位一体’的。”[15]注重理性固然重要,但更应兼顾德性的要求,这样的法律才更适合国人并让其乐于自觉遵守。
四、“隆礼重法”:建构当代德法同治模式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社会治理模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德治和法治是其中的两个基本方式。德治,主要是对社会的道德控制,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构的重视和运用。而法治则指以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基本手段,通过其规范性、强制性、可操作性来完善对社会的治理和控制。”[16]当代中国选择了德法同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这是历史上德治、法治几经离合后的必然选择。然而,对德法同治模式国人似乎有些不适,一些学者也认为中国缺乏德法同治的传统。实际上,德法同治的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先秦至辛亥革命数千年,从总体上呈现出德法合治——法治——德法合治的基本线索。”夏商“神权法与伦理紧密结合,在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共同目的下展现了德法初分而不分离,德法合治的最初形态。”西周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提出明德慎罚的主张,“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和推崇德治,所谓慎罚,就是慎重的使用刑罚,从而开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德法合治之先河。”当然,当时德治与法治都不甚发达,这种“同治”的水平也很低。在经过从东周至秦代短暂的德法分离到法治后,中国的德法同治历经复归、成熟、僵化等阶段,在清末修律中逐步走向解体。然而,随着“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等理念的相继提出,中国从20世纪末又开始构建新的德法同治模式。江泽民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当代中国社会所努力构建的德法同治模式,其实是有着悠长的历史渊源的,对其的研究仍可以“礼”为基点。荀子认为在治国过程中,“礼”和“法”都不可偏废,他提出“至道大行,隆礼重法则国有常”的主张,他甚至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德法同治理论的人。“隆礼重法”既强调“隆礼”又强调“重法”,认为德治和法治同样重要、不可偏废,用今天的话语表达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西汉贾谊认为礼、法结合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17]到了唐代,“唐律一准乎礼,使礼的基本规范取得了法律的形式,从而把礼义道德原则和法律规范有机结合起来,这标志着封建纲常的法律化和法律的伦理化,是封建社会德法合治思想成熟的表现”[3]34。也有学者将现代德法同治称之为礼法结合:“现代的礼法结合,是指在以法治国环境下对法律伦理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一个功能性概念,从过程上看,它是作为法治精神内涵和保障实现的手段与法律在现实中运行的有机结合,从结果上看,礼法结合的目的是为了要达到和实现理性的法律秩序和社会正义。礼已经不仅仅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的中华民族传统法律精神,它被充分赋予了时代精神,即社会主义道德。”[18]
当然,当代中国在构建新的德法同治模式时,在强调德治与法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时,应将德治即道德建设置于更重要的位置。“选择法治作为我国的基本社会控制模式,只是起到了治标的作用,而加强良好道德对社会的引导和调节作用,进一步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增强人们的守法意识,提高人们维护社会秩序的自觉性,才是社会治理的根本。”[19]“隆礼重法”,“隆礼”在前“重法”在后,“德治”在德法同治的过程中更为重要。古人之所以如此措辞是深有道理的。
以礼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启示也远不只上述。法治文明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制度文明,它应该而且必须在中华传统礼制典范中汲取养分,寻求借鉴。
[1]史凤仪.中国法制历史中礼与法的关系[J].中国法学,1988(3):105.
[2]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6.
[3]李建华,曹刚.法律伦理学[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
[4]胡旭晟.法的道德历程:法律史的伦理解释(论纲)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7.
[5]戴茂堂.西方伦理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344.
[6]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7]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J].法学评论, 1998(2):34.
[8]陈林林.对古代鬼神信仰的一种法文化观察[J].法律科学,1998(5):26.
[9]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33.
[10]唐凯麟,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86.
[11]金国坤.依法行政的现实基础:影响和制约政府依法行政的因素分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352.
[12]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J].哲学研究,1997(1):11.
[13]周文华.说法的正义价值[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9-10.
[14]曹刚.法律的道德批判[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4-16.
[15]范忠信.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6.
[16]李建华.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7-28.
[17]杨寄荣.“引礼入法”的现代启示[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80.
[18]关倩.礼法结合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J].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2):59.
[19]张洪涛.德法并举的社会控制新论[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7.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of Rites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the Rule of Law
Qu Zhen-hui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Hunan Women’s Vocational College,Changsha 410004,China)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was based on rites.In building the ruleof law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traditionsof“rites”canno t be neglected.In the new legal context,the main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of the traditional rites fo r the rule of law lies in demarcating the division between morality and law,p romoting the legalization of mo rality,guiding themoralization of law,and constructing a governance model of the rule of both mo rality and law.
contempo rary rule of law;rites;local resources;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D909.2
A
1009-1513(2010)01-0030-04
[责任编辑朱 涛]
2009-09-30
湖南省公民礼仪素质研究基地基金资助课题“中国传统礼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编号:jdyb0903)。
屈振辉(1977-)男,河南信阳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法律伦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