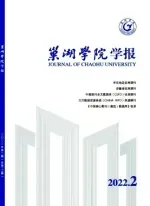《新序》与《说苑》的用“材”方式初探
王启敏
(淮南联合大学政文系,安徽 淮南 232000)
《新序》与《说苑》的用“材”方式初探
王启敏
(淮南联合大学政文系,安徽 淮南 232000)
刘向编撰《新序》、《说苑》的主要目的在于说理。二书各卷中对于材料的组织安排并非是无序的。经过仔细研究可以发现,编撰者是先收集材料,然后再在材料的整理编排中明确主题。因此,各材料(“章”)之间,往往是在某一主题下的分配,也可以说是被某一思想贯串起来的。反过来,这些材料在编排上又起到强化主题的作用,其表现形式主要有对照、连贯等。此外,二书各卷中往往出现一系列事件情节大体相同的材料,有时一个结束,另一个接着出现,中间很少有停顿或过渡。像这样连贯出现的故事,也是作者为了强化主题而特意编排的。
新序;说苑;编撰;说理
刘向《新序》《说苑》的材料是“采百家传记”而来,但大多数材料在入选时编撰者都做了有目的(为了说理)的加工和编排。刘向在《说苑?叙录》里自称的对材料“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只要对二书作些更仔细的研究,便可以体会出编撰者在材料展开方式上用心之精细。
1 主题先行还是材料先行
刘向编撰《新序》《说苑》,究竟是先让思想去适应材料,即先有材料,然后在材料的整理中明确主题;还是头脑里先形成主题,然后再有目标地收集材料,并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这一点前人尚没有作过研究。故二书的主题和材料孰先孰后需首先做一番探究。
刘向本人于《说苑叙录》中说: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混,或上下谬乱,难分次序。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号曰《新苑》。[1]
作者清楚的说明自己在整理材料时,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 “事类众多,章句相混或上下谬乱”,因而“难分次序”;《新序》中名为“杂事”的诸卷,题目已经表明这些材料需要加以条理。据此,我们大体可以描述出刘向“编”二书的过程:
第一步,编撰者以校中秘书之便利,获得中秘藏书 (“所校中书”),加上自己和民间的藏书(“臣向书,民间书”),有了大量的材料。但这些材料还只是以原始的状态存在(“事类众多,章句相混,或上下谬乱,难分次序”)。
第二步,刘向用一把“义理”(不可把“义理”理解为专对《说苑》而言的)的标尺,对已得到的原始材料进行筛选,即被选用材料都是围绕“义理”这一主题的:这一步事关材料用与不用的问题。
第三步是对可用材料进行归类 (“以类相从”):这涉及的是材料怎么用的问题。“后令以类相从”之“后”字,正表明“编”的顺序。卢文弨疑“后”字下有脱文(见《群书拾补》),孙诒让则认为“后”当为“复”字(见《札迻》),我认为均属多虑。
第四步是给每一类材料归纳主题性篇名(“一一条别篇目”)。
这一过程的简单表示就是:
原始材料……大主题 (“义理”)——录用材料——小主题(篇名)
“原始材料”与 “大主题”(“义理”)之间,我用“……”连接,是因为二者之间不一定存在关系,即大主题未必是从原始材料中得来。“大主题”与“录用材料”之间有一个编选的过程。“录用材料”与“小主题”之间则是加工的过程。“小主题”之后还有一个重新编排、加工的过程——这一问题将在另一篇论文中讨论。至于在“小主题”之下是否还有新材料填充进去,值得另作研究。
《新序》《说苑》的有关内容也反映出上述“编”的过程的存在。
《新序》的前五卷不同于其它卷之处,即没有标识主题名(即“小主题”),都是笼统的以“杂事”呼之。《杂事》五卷的材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合于“义理”(“大主题”)。 这正反映出“义理”在先,材料在后。至于《新序》材料所合的“义理”具体所指,据《新序》其它卷内容看,应该是能解决现实社会方方面面问题的思想理念。如《刺奢》之所以成立,在于成帝统治集团 “制度太奢”;《节士》警示是现实中那些在权力和利益面前丧失做官、做人原则者;《义勇》是对《节士》内容的补充。而《杂事》反映的问题不是那么迫切和有具体的现实针性。如《杂事》之一主要论孝、仁道;之二言用贤为主;之三言兵事和礼贤等;之四言用贤、臣道等;之五言学习、仁道、下贤等。大体以儒家传统的“悟主安国,因事内诲”思想为主,而且“人非一时,事非一类”,[2]故刘向未对这些材料做进一步归类,也未题篇名。与《说苑》相比,这也是《新序》材料编排上显得粗疏之处。
至于《杂事》分为五卷,我推断可能只是与《新序》其它卷做的量上平衡。
就《新序》遗存的各卷看,它与《说苑》在每卷的题名上有相关之处,它们大体上可以对应起来。如:《杂事》——《杂言》;《立节》——《节士》;《善谋》——《权谋》。《新序》中《刺奢》的思想也散见于《说苑》的《建本》、《贵德》等卷。二书题名上的不完全相同,如“立节”和“节士”,可能是刘向想显示二书有所区别,故稍作了些变化。可以推测,完整的《新序》与《说苑》相关之处一定更多。篇名上的大致对应,说明二书的材料必是在同一指导思想(“义理”)下选定,并在近似的“主题”下再归类。《新序》《说苑》各卷题名的情况,我上面说过,是刘向把合于“义理”的材料归类之后确定的称谓。其实这也是笼统的说法。具体到二书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新序》各卷的题名必然是从同类材料中归纳出来的,而非事先设定好的。《杂事》的材料没有具体篇名,本身就证明《新序》是材料归类后再以类题名;否则,若先拟好“杂事”这样漫无目标的题目,题下恐无法组织和确定材料。徐复观认为《说苑》是把《新序》中已经用过,及浅薄不合义理的除掉,“剩下的材料(余者),则以类相从的分配到拟订的篇题中去”。[3]这一说法不完全准确。我们从《新序》与《说苑》题名大体可以对应起来,能够断定,《说苑》的《权谋》、《立节》等卷,名字有沿用《新序》的痕迹。这些卷可以认为是按题分配材料,即小主题先于材料;其它卷情况则相反,题名也是从材料中归纳来的,即材料先于小主题。《说苑》的《谈丛》、《杂言》两卷的篇名也可为证。这两卷所录的明显是一些无法归类的剩余材料,但因为它们又合“义理”,所以也被分别组合起来,然后以“杂言”“谈丛”作为笼统的称呼,类似于《新序》之“杂事”。而不可能出现作者先拟好“谈丛”、“杂言”这样含糊的名字,再去收集材料的情况。
2 构想解决现实问题有效途径的反映
从《说苑》各卷看,在“义理”大主题之下,材料的分配也清楚地反映了刘向的政治观念。他把《君道》、《臣术》放在全书之首正符合他编撰此书的初衷——为人君、人臣提供行为上和道德上的规范。编撰者想表明,社会现实问题的根本解决,首要的是统治集团自我反省、自我改变。这一点可以从《君道》之四十五章清楚地看出: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亏也,犹水火之相灭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门盛而公家毁也。人君不察焉,则国家危殆矣。管子曰:“权不两错,政不二门。”故曰:胫大于股者难以步,指大于臂者难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4]
“私门盛而公家毁”,是刘向经历了元帝朝的政治迫害后的痛切之悟!他把朝代的更迭、国家危亡,归之于人君不能明察臣下所导致的“私门盛”,固然是其认识上的局限,但也确实反映出了元、成间政治上权移外家这个最大的现实问题。这也是刘向或奏疏、或献书,反复强调此点的原因。接下来的三——九卷,内容也主要是解决政治问题的种种构想。其中的卷三《建本》在全书的位置较前,与刘向坚持“君子务本”(孔子曰),希望能够建立起某种解决政治根本问题的普遍法则有关——“慎始”、“务本”也是刘向对作为一国之主的基本要求。从材料来看,《建本》实际上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内容:孝道;学习;富民。这是儒家一贯关注的问题,乃立身立国的根本。《立节》接于《建本》之后。刘向所讲的“节”与“仁”、“义”是相联系的,为了成就仁义可以抛却生命,这是刘向论节士的基础。在汉代,“士”的政治命运起落升跌是常有的事,跌落者难免有生存的危机,不甘心者就有可能做出失节丧志的事情。况且失节现象在元、成时期的确已经构成了一种社会危害。《说苑》突出这一问题,完全是有现实意义的。《立节》之后的《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等卷,偏重于阐释儒家传统的政治思想,理论性较强。卷十《敬慎》虽言处世态度,但也是把“不诫不思”与无以“存身全国”并提,并未远离政治。《权谋》,可以与《新序·善谋(下)》全录汉事结合起来理解,是刘向对汉政权建立的历史经验和他亲身参与现实斗争经历的反思:刘邦“收诸侯、讨项王、定帝业”以及御臣僚等,靠的就是成功的谋略;元、成二帝则困在宦官、外戚构筑的阴谋陷阱之中,不能区分权谋中的诚与诈。所以刘向在《权谋》开篇即郑重的要求“圣王之举事,必先谛之于谋虑”,并特别强调:“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夫正者,其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百姓也诈。”他认为行使权谋之术的首要问题就是“必察诚诈之原而以处身焉”,也是希望皇帝能切切实实地体察清楚那些居处在政治要害位置的人,他们对于国家、对于君王的用心到底有多少诚意。《至公》中“大公”的提出,我认为是出于元、成时期私门富、私权盛的现实提出,其目的同样在于立公道、废私权。《指武》、《谈丛》、《杂言》、《修文》、《反质》诸卷与迫切的政治问题似显疏远,故位置靠后。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只是作大致上的划分,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
材料的分配上与政治结合的亲疏,在《新序》里反映得不明显,这也说明《说苑》在编撰上比早于它的《新序》要精细一些。
3 顺向观照:材料在同一主题下的分配与归结
上文描述二书“编”的过程时,说过“小主题”确定之后作者对已归类的材料,继续进行排序、加工等。这一过程最能体现刘向“编撰”的用心。《新序》《说苑》以“章”为单位的各“语录”之间,往往是在某一主题下的分配,是被某一思想贯串起来的。这比起《论语》的语录样式是一个进步。但这种分配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次完成的,有的要经过几次分配,数次归结。这和《论语》中各语录之间呈游离状态的分散分布是不同的。《新序》《说苑》各条材料之间的独立是相对的,是游而不离、分而不散,是被某一主题组织、支配;同时材料之间的分配和归结又使主题得到加强。
《说苑》每卷之首都有一个总论,是题旨性质的议论,即主题阐释。但在《君道》中却省去了这样的议论,改之以几段人物对话(1—6章),通过人物的对白(师旷对晋平公、尹文对齐宣王、成王对伯禽、泄冶对陈灵公、孔子对鲁哀公、河间献王曰)阐明了本卷主题“君道”的含义。因为这几章话题直接围绕“人君之道,何如”这样的问题展开,阐述得已经很具体,道理说得也极明白,刘向觉得没有必要再于卷首填加自己的议论,所以就空缺了。因此,这几段对话实际上起到卷首主题议论的作用。以下材料即在已确立的“君道”主题下渐次展开。到第二十三“明主者有三惧”章,进行第一次归结。以下二十四至四十一章是材料的第二次展开。再到第四十二“夫天之生人也”章又第二次归结,认为天生人,天立君,因此为人君不顾其民而行私欲,就是违背天意。剩下各章又围绕此主题第三次展开。这样,由阐明“君道”内容所指(1—6 章);到以古代圣君(尧、舜、禹、周公、成王等)具体事例来正面说明何谓“君道”(7—13章);再集中古代贤臣的谈论(伊尹对汤、太公对武王、宁戚对齐桓公、晏子对齐景公、郭隗对燕昭王、楚庄王思贤等),强调君王要重视用贤以及怎样用好贤(14—21章);接着以反例来告诫君王要行“君道”(22—42章);最后或以正例或用反例进一步说明只有行君道才能合天意、保社稷(42—47章)。材料经过这样两次归结,三次展开,“君道”的主题得到不断的演进、深化,其警醒的意味也越来越浓烈。
同一情况也出现在《说苑·臣术》当中。本卷共二十五条材料,材料的展开形式是:提出主题——分配——归结——再分配。开篇“人臣之术顺从而复命”章提出主题:“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这样就可以做到“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刑见思”。以下从“汤问伊尹曰三公”章到“陈成子谓鸱夷子皮”章,是在主题下的第一次分配。这一部分材料大旨是突出进贤用贤、君臣和谐共事。“从命利君谓之顺”章则是作了一次归结,对人臣事君列出四种态度:顺(“从命利君”)、谀(“从命病君”)、忠(“逆命利君”)、乱(“逆命病君”)。进一步提出要做到谏、诤、辅、弼。谏是“尽言于君,用则留,不用则去”;诤是“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辅是“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弼是“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窃君之重……”。“简子有臣尹铎、赦厥”章以下是材料上的第二次分配。材料主旨则是强调做诤臣、直臣等。材料进行前后两次分配,主题也发生了调整,由强调进贤用贤到要求做谏、诤、辅、弼之臣,完成了针对君臣双方提出的构建君明臣贤的诉求。
4 逆向观照:强化主题的主要方式——对照、连贯
上一节是顺着主题来观照材料,研究材料在确定主题下如何分配;本节则是逆向由材料来看主题,研究材料分配中如何深化主题。
第一、对照。《新序》《说苑》在编辑材料方式上与强化主题有关的,首先是对照。根据对照是在一组材料之间展开还是在一条材料内部展开,分为外部对照和内部对照两种。
4.1 外部对照。《说苑·复恩》之三到之六,是一组关于晋文公的材料。“晋文公亡时”章,说明晋文公在逃难中行赏能作到公平公正,是正面阐释“复恩”的主题。但接下来的“晋文公入国”、“晋文公出亡”两章,则通过咎犯的哭诉和晋文公行赏不及介子推、舟之侨,又从反面说明晋文公没有做到“复恩”。这样正反安排材料表现刘向本人对晋文公失意时知行赏、得意时却忘恩的褒贬态度。尤其反面材料的使用,说明刘向更看重一个人处于顺境时尤其不能忘“复恩”。这一组材料之间是典型的外部对照关系。
4.2 内部对照。《说苑·君道》“齐景公游于蒌”章和“宴子没十有七年”章,前者以齐景公闻晏子卒后的悲痛失态反衬晏子于齐国之重要;后者以齐景公多年后依然不能忘怀晏子,反衬晏子作为人臣对于国家的重要。同样是关于晏子的材料,《说苑·正谏》“景公饮酒,移于晏子家”章,其中四个人物,四种形态。景公是一个贪图享受“酒醴之味,金石之声”到处找乐的庸君;梁丘据是一心讨好媚上、逢迎献谄的佞臣;此二人恰好衬托出晏子和司马穰苴,一个是心念国事的忠臣,一个是安危系于心头的将军。
内部对照往往是原材料已有的,其强化主题的意义不像外部对照那么显著。但值得注意的是,内部对照往往是伴随着外部对照而存在的。
第二、连贯。指的是并列的情节协调的几个故事,一个结束,另一个接着出现,中间没有停顿或过渡。《说苑·复恩》之十“秦缪公尝出而亡其骏马”章,至十三“孝景时吴、楚反”章,此四章内容本身不相关的故事之间的协调,不仅在于它们围绕的是同一主题——“复恩”,也由它们的情节结构相似所决定:故事都是开始于“罪犯”对主人犯下了不可恕之罪过,但主人却意外地宽恕了他们,伏下了以后罪者复恩的契机;故事都结束于主人落难,而当年的“罪犯”挺身相救,完成复恩使命。这一组故事在《复恩》中保持自己情节结构上的一致性和独立的特点,有别于它们的前后篇章。像这样“连贯”呈现的故事,显然是作者为强化主题所作的特意编排。
还有一种特殊的“连贯”,即几个并列的故事不是主题相同、情节结构近似的问题,而是记的实为同一件事,只是背景、人物稍有区别而已。如《说苑·杂言》“梁相死”以下三章: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堕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无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间而困,无我则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艘楫之间,则吾不如子,至于安国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视之狗耳。”(九章)
西闾过东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问曰:“今者子欲安之?” 西闾过曰:“欲东说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说诸侯乎?”西闾过曰:“无以子之所能相伤为也……今子持楫乘扁舟,处广水之中,当阳侯之波而临渊流,适子所能耳,若诚与子东说诸侯王,见一国之主,子之蒙蒙无异夫未视之狗耳。 ”(十章)
甘戊使于齐,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间耳,君不能自渡,能为王者之说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所长……今持楫而上下随流,吾不如子,说千乘之君,万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十一章)[4]
这一组“连贯”的故事是事同而人物异。编撰者从“事类众多”、“难分别次序”的大量材料中将它们搜索出来,并编排在一起,其用心之精审也可以想见。此三则材料反映的是“物各有短长”的常理,故被置于《杂言》中。接下来的十二章“今夫世异则事变,事变则时移”云云之论,既是对前几章内容的“归结”,也是为了显示这几个故事的相对独立性而进行的过渡。
[1](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石光英.新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汉)刘向.说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PRELIMINARY DISCUSSING ABOUT THE WAY OF USING MATERIALS OF XIN-XU AND SHUO-YUAN
WANG Qi-min
(Huainan Union University,Huainan Anhui 232001)
The new sequence of liuxiang compiled Xin-xu and Shuo-yuan said deco aims to argue. Two books for material mane is not disorderly arranged.After careful study,which is the first can be found in collecting material,then the layout of clear theme.Therefore,the materials("chapters"),is often in a theme of distribution,also can be used by a thought.In turn,these materials in the format and have strengthened,the main form contrast,coherent,etc.In addition,the second book in a series of incidents mane is approximately the same plots of materials, sometimes an end, then another, rarely pause or transition.As such,is the story of coherent designedly for strengthening the theme.
Xin-xu; Shuo-yuan; compilation; reasoning
I206.2
A
1672-2868(2010)02-0040-05
2009-10-15
王启敏(1971-),男,安徽怀远人。文学博士,安徽淮南联合大学讲师,研究方向:先秦汉魏六朝。
责任编辑:澍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