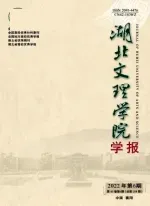宗白华的艺术批评思想、方法及实践
张泽鸿
(湖北文理学院 美术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宗白华(1897—1986)建构了完整的现代生命本体论美学和生机论艺术学体系,这是学界近年来的一致看法,但是宗先生在艺术批评上的基本观念和方法及其批评实践却很少有人探究。这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宗白华没有留下完整的艺术批评著作和论文,只有零散的札记和编辑后语等批评文字;二是宗白华一般被误解为只研究古典艺术理论而不关注现当代艺术发展,因此其艺术批评思想是不完整的,没有研究的价值。基于这两点,学界对宗白华的艺术批评学关注较少。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在生命哲学美学的相关背景下来揭橥宗氏在艺术批评领域的独到贡献和价值。
在现代艺术学理论构成中,艺术批评(学)是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要显现艺术理论应用于艺术评判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在运动中建构理论、创造思想的功能。阿诺德·豪泽尔曾说:“在艺术家和他的消费公众之间建立桥梁的中介者中最重要的就是以中介为职业的批评家”[1],艺术批评要在“美学与艺术之间,艺术的观点和艺术的直觉之间”[2]建立一种联系,由此可见艺术批评之于人类艺术活动的重要性。宗白华的艺术批评学是独具特色的,他在中国古典艺术批评理论的启发下,他将基于生命本体论的艺术观念运用于现代艺术语境中,建立了“生机主义”的现代批评模式,开辟了生命意象批评与境界体验批评的方法,并具体展现在对中国现代诗画及西方现代艺术的批评实践中。宗白华以其批评思想、批评实践以及批评史研究这三个维度建构了现代“艺术批评学”。宗白华的艺术批评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规避了中国现代艺术批评“唯西方是从”的方法论缺陷①陈池瑜认为,中国现代艺术批评呈现出四大特征:一是以西方近代美学批评为参照,打破了本土批评的封闭系统;二是以西方艺术为尺度来批评中国艺术;三是西方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批评观以及苏联文艺批评原则被应用到中国;四是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进行批评。这四大特征都是“唯西是举”,缺乏本土化的艺术批评方式。请参阅陈池瑜《中国艺术批评的四大特征》(《装饰》2004年第11期,第6-8页)一文。,并对当代中国艺术批评学和批评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宗白华生机主义艺术批评观的确立
宗白华融合中西智慧的生机主义美学思想构成了他的艺术批评学的理论基础。他曾说:“叔本华发现盲目的生存意志,而无视生命本身具条理与意义及价值(生生而条理)。……至今怀德特之哲学乃显以一‘全体性的生机哲学’,调和‘价值界’与‘数理界’。”[3]近代哲学从康德、黑格尔到叔本华,他们的哲学(真)虽然触及道德(善)与艺术(美),但是没能完全贯通一体,将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旁观统贯”,实现生命整体的观照。在宗白华看来,近代哲学家中唯有怀特海(Whitehead)真正打通了真善美的三界割裂,实现了理论与价值的融通。宗白华扬弃叔本华的盲目的“生命意志”,转而寻求怀特海的有机哲学(过程哲学)与中国生命哲学的会通。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认为“自然是活的”[4],他要求用“自然界和生命的融合”[5]来弥补我们关于物质自然界概念的缺陷,并强调以“审美直觉来补充逻辑”[6]对于当代生活的重要性,建构起真正的机体主义宇宙观。这种泛生命化的宇宙观对于宗白华无疑具有理论诱惑。
同时,宗白华的艺术批评思想是在融合中国古代艺术批评与近代西方艺术批评两种传统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以“生命”(活力)为核心范畴,并形成了境界体验批评与生命意象批评两种方法。苏珊·朗格曾说:“在艺术评论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暗喻便是将艺术品比作‘生命的形式’。每一个艺术家都能在一个优秀的艺术品中看到‘生命’、‘活力’或‘生机’。”[7]朗格将艺术视为一种生命的感性形式与宗白华的艺术观具有本质的相似性,二者都受到20世纪初西方生命哲学思潮的影响。可以说,在现代中国艺术批评史上,宗白华建构了一种全新的“生机主义”艺术批评原则,它具体表现为生命意象批评与境界式批评两种方法。
1.生命意象批评
中国传统的艺术批评强调以“意象”为中心进行艺术品鉴。譬如韩愈说:“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宗白华非常欣赏这种批评思想,他认为张旭书法体现了变动的自然形象,这些自然形象是通过他的情感体验形成的“可喜可愕”的生命意象;书法家在表达自己情感的同时也反映和暗示出自然界的各种形象特征,或借助这些概括性的生命形象来象征对于自然的“情感”。因此,自然生命形象在书法里已不是“事物的刻画”,而是情景交融的“意境”[8]。蔡邕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象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赵孟頫在写“为”字时,为了使“为”字更具生气和意味,他通过观察鼠的形象并习画鼠形数种而获得启发,达到深层的“生命形象的构思”。宗白华说:“这字已不仅是一个表达概念的符号,而是一个表现生命的单位,书家用字的结构来表达物象的结构和生气勃勃的动作了。”[8]402在宗白华看来,这些生气勃勃的自然形象原本就是一个有生命的躯体,它们都是由“骨、肉、筋、血”构成的。其中“骨”是生物体最基本的间架,生物体在“骨”的支撑下才能站立和行动。附在骨上的“筋”是一切动作的主持者和运动感的源泉。包裹着骨、筋的“肉”构成了生命体的外在形象。流贯在筋肉中的血液滋润着全部形体,因此有了“骨、筋、肉、血”的生命体才完整。在宗白华看来:“中国古代的书家要想使‘字’也表现生命,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就须用他所具有的方法和工具在字里表现出一个生命体的骨、筋、肉、血的感觉来。”与绘画的模仿性不同的是,书法主要是“通过较抽象的点、线、笔画,使我们从情感和想象里体会到客体形象里的骨、筋、肉、血”,以及启示着人类的生活内容和意义。[8]402宗白华在对待同时代的艺术家譬如徐悲鸿、齐白石、胡小石等人书画作品时,也是从艺术意象所体现的生命活力角度给予鉴赏和评判的。
宗白华为何如此看重传统艺术的意象分析?这与中国文化哲学的尚象、重象的思维传统有关。在宗白华看来,中国人尽管重视“象”,并不排斥对“数”的科学应用,如《周易》在六爻、八卦、六十四卦及其卦象的玄妙推演中都有着对“数”的推崇,但是“中国之‘数’为‘生成的’、‘变化的’,象征意味的”,中国文化哲学中的数往往是“流动性的、意义性、价值性的”,它是“以构成中正中和之境为鹄的”。《周易》中对六爻、八卦、六十四卦之间变化不仅体现了“数”本身的奥秘,它还与“位”(空间)与“时”(时间、生命)相关,“数”的变化彰显了宇宙人生的“演变”之机,即所谓“明数之妙,通于鬼神”[3]597。由此看来,“数”与“象”相联系,共同体现宇宙人生的无穷意蕴。因此,宗白华说,“此‘数’非与空间形体平行之符号,乃生命进退流动之意义之象征,与其‘位’‘时’不能分出观之!”[3]597中国文化中“数的哲学”也被运用到文学艺术批评中,如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即是明证,特别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诞生以后,艺术品评的跟风之作代不乏人,历代画评、乐评、书评、曲评中,都有“二十四品”现象。诚如宗白华说,“中国之数,遂成为生命变化妙理之‘象’矣!”[3]598这句话对中国艺术批评学研究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照宗白华的看法,中国艺术批评中的“数”(如二十四品),不仅是艺术批评的模式化倾向,更重要的是这个数体现着“生命”变化之妙理,它本身就是一个“象”(意象与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艺术批评实践是一种“拟物批评”(即以自然物象来比拟艺术特征),准确的说是“生命意象批评”①中国传统艺术强调的“意象式”批评模式可参看朱良志先生《象:中国艺术论的基元》一文的论述,亦可见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172页的阐述。的体现。
中国传统的“拟物批评”是一种生命意象批评,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的艺术批评是以艺术意象为中介的,这个意象又被视为“生命意象”。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的思路强调“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创造一种亦情亦景、亦心亦物的艺术形象,这种艺术形象并非单纯的物象本身,其中蕴涵着人的情趣,因此被称为“意象”。它是“生命与生命交往的结果,是自然生命对自觉生命的感发和自觉生命向自然生命的投入,是心物双方在这样的交往中凝聚而成的生命共同体。总之,是有生命的。因而在‘意象’之前还应加上‘生命’二字,称作‘生命意象’。”[9]由此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艺术创作和批评主要是围绕着心物一体的“生命意象”而展开的,因此被现代学者称之为“意象式批评”[10]。进而言之,对传统艺术观念和批评思想深具同情之体验的宗白华,他的现代艺术批评思想是继承中国传统的,因此他是在古典艺术拟物批评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生命意象为核心的艺术批评原则。
2.境界体验式批评
宗白华的艺术批评思想和方法与其生命本体论美学是密不可分的。从意象批评方法出发,宗白华进而提出“境界体验”的批评方法。有学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存在三种不同的传达媒介:言、象、境。这三种媒介反映世界的方式不同:“言”是对世界进行描述;“象”是以象征的方式表现世界;“境”则是“一种以世界本身来显现世界的独特方式,它是以心灵所创造的活的世界来显现意义。它不是描述,也不是象征。它是以体验的世界来呈露,境的方式就是‘呈露’。”[11]在中国艺术批评史上,境界往往作为评判艺术审美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其中,以晚唐诗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为代表的诗学境界批评范式及其妙悟致思路径对后世艺术批评影响最大,也对宗白华有着重要启发。
《二十四诗品》开创了中国艺术妙悟论与境界批评论的先河,其以象显境、以境喻境的批评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诗品》以四言句式描述一个完整的诗歌意象,营造独特的境界,让读者在诗的意境呈现中去体验所要评价的“诗品”,达到纯粹理论概括所不能完全表达的境地。司空图强调了主体胸襟、人格精神对境界创造的意义,司空图的批评方法绝不是西方的“印象式”批评,而是“境界式”批评。宗白华深得其中三昧,并将司空图的诗化体验批评进一步弘扬和现代转化,使其适用于现代艺术语境。宗氏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形与影——罗丹作品学习札记》等批评名篇中都创造了诗化的批评语言,他没有概念化的阐述中国艺术、罗丹雕刻的美,而是以诗化的语言来营造意境,让读者在艺术体验中感受到批判对象的魅力所在。因此,宗白华在美学表述、艺境探索与艺术批评中创造的这种“以象示境”方法,重视“象外之象”的体验性,在艺术批评中强调对艺术意境的“还原”,追求一种“气象混沌,难以句摘”的境界,这是一般的理论批评很难达到的。宗白华艺术批评和致思路径往往是跳过逻辑论证而进行“单刀直入”的意象直观,通过“以象显境”的方法来评判艺术,这种境界式批评方法与现象学强调“直观”与“还原”的方法有相近之处。
尽管宗白华的艺术批评的思想基础主要来自中国古典,但他并未停留在传统意象式批评方法上,而是进行了由“直观体悟”式意象批评向直观与理论分析结合的“意象分析法”的转变[10]255,注意传统批评模式与现代分析方法的融合,将其具体应用于现代艺术。尽管如此,由于“描述”、“解释”、“规范”被视为现代艺术批评的三大特征[12],而宗白华极具民族化的重视体悟的艺术批评模式在一定意义上说与此是不太契合的。这就涉及到艺术批评领域的本土化与世界化相冲突的难题,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是当代艺术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任务。总的来说,宗白华通过生命意象批评与境界体验批评这两种方法确立了基于生命美学的批评原则,建构了生机主义的艺术批评观。从宗白华生机主义美学来看,艺术意象体现“生意”(生命的外在形态),艺术境界体现“生理”(内在的生命精神)。因此,意象批评与境界批评正好构成了其生机主义批评观的内外两个维度。
二、宗白华生机主义艺术批评的现代实践
在西方现代艺术学者看来,艺术批评家的基本任务就是“在那些观念已过时的公众和具有新的批评性要求的新艺术之间建立起文化桥梁。”[13]宗白华也是非常重视批评家充当艺术家与公众鉴赏力之间的桥梁作用的,他曾说:艺术批评是建立在“常人”(普通民众)平均的艺术鉴赏力基础上,但同时又要对“常人”鉴赏力进行超越和提升。在宗白华看来,第一流的艺术作品往往以“通俗性”来构成它们的“普遍性和人间性”,同时还须“含藏着一层最深的意义与境界”以等待真正的读者知己[14],因而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艺术都难免有“孤寂”之感。艺术批评家的任务不是跟在大众、流行与时尚后面人云亦云,而是要对公众和常人尚无法解读的那些艺术杰作做出真正的评判,从而在艺术家与公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一般来说,艺术批评是“运动中的美学”,它的对象是正在发生、发展、变化的“正在进行时”状态下的艺术现象。[12]293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批评主要是批评家对当代的正在“运动”和发展中的艺术(包括艺术现象、艺术家、艺术作品)的评论,因此它与艺术史有别;另一方面,在艺术批评活动中对于艺术作品的“感性描述”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因素,因而它与艺术理论也不同。[12]298意大利艺术理论家文杜里曾认为,在艺术批评中,对于艺术的判断一方面是根据批评家的美学观念,另一方面又是根据艺术作品,二者之间形成一种批评的“二律背反”效应。而在实际的运用中,美学观念与艺术作品往往又“融合在一种批判的冲动、一种意愿的倾向、一种感情的形态里”[2]12。因此,批评家要根据艺术现象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批评方法和视角。宗白华那一代学者所受的艺术熏陶大多是古典式的,但是他又有幸接触到了西方20世纪以来的现代艺术思潮。面对现代艺术运动,他看到的不再是和谐静穆的古典美,而是对古典美的否定与背离。无论是后期印象派对光、色的追求,打破了对世界完整清晰图像的再现,还是表现派致力于抽象表现,立体派、达达派侧重展现一个抽象、怪诞的符号世界。面对这个迷茫、复杂的艺术世界,宗白华并没有固守古典的艺术理想,他力图从这些新的艺术实践中去发现新的艺术理论问题。这种当代视界使得他的艺术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现代性”。
宗白华对中西方现代艺术的关注处处渗透着其生机主义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尽管宗白华主要研究古典艺术,但是他的艺术批评趣味并不拘泥于古典,而具有开放包容的现代感。在西方现代绘画艺术家中,宗白华很喜爱塞尚的作品,尽管西方学者都对塞尚有误解,但宗白华却认为“塞尚只是通过某种超视觉的印象,表达更深一层的自然和人生的意义。”[15]并高度肯定了塞尚一生倾心于自由创造的艺术精神。宗白华弟子林同华回忆说:“宗先生热爱古典艺术,但他并不为古典艺术所束缚,他也热爱现代派艺术。他很早就研究现代派艺术,从20年代至80年代,在课堂上,在著述里,在谈话中,他对于马蒂斯、毕加索、马尔克、康定斯基、蒙德里安、布拉克……等等的艺术和思想进行过精心研究。1970年代末他还为中国艺术家翻译出版了一部宝贵的《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15]792这部画论选里包括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未来派、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派、野兽派、构成主义等流派。宗白华在对待各种艺术流派的观念上采取宽容的态度,他甚至在20世纪30-40年代就说过,马蒂斯等现代派画家厌倦了对自然表象的刻画,而“企求自由天真原始的心灵去把握自然生命的核心层”,因此这些作品是有价值的。由此可见,宗白华在拨开现代派艺术的表象背后看到的是一种现代艺术对人生的关怀和尊崇生命的意识,其评价标准仍是“生机主义”的。
宗白华一直强调在艺术批评中应持有“自由、宽容”的态度,这种批评的自由和宽容实质上隐含着宗白华对艺术和人生的总体看法,即强调艺术在表现自我与表现世界之间的平衡,现代艺术也要表现宇宙人生的新境界。他曾说:“搞艺术批评的人要尽量宽容些,搞美学研究,也需要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要让作品在社会上多经一些人看看。这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8]596宗氏认为美学研究与艺术批评的宗旨在于要从材料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他还主张在艺术上采取宽容的政策,艺术批评者要打开眼界,对各种艺术流派不要轻易下结论。从西方现代艺术流派的演变可以得知,艺术的发展需要多元化的宽松环境。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派艺术被国内艺术批评界所熟。关于当时热烈讨论的现代派艺术与“表现自我”说的关系,宗白华认为“表现自我”的理论不可一概而论,关键要看表现“什么样的自我”;“艺术不仅要‘表现自我’,还要‘表现’客观规律。”[8]601表现自我与表现世界相结合,心灵与世界的统一,才是现代艺术的真正方向。他认为“现代派艺术不能一概否定,如毕加索。但毕加索原来写实的基础很好,后来搞的立体派都是在原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才有新意,新境界。”[8]601宗白华对现代艺术采取宽容的态度也是出于生机主义的艺术批评观和境界批评方法。
宗白华对同时代中国艺术家的研究和批评,也是基于其生机主义美学和文化创新理念,并以“意象”和“境界”为范畴进行了评论。1944年,宗白华应中央大学艺术系同事兼画家吕斯百(1905—1973)之邀去他的画室看画,并在《凤凰山读画记》一文中对其进行评论,宗白华说:他(吕斯百)的画境,正像他的为人和性格,“静”和“柔”两字可以代表,静故能深,柔故能和。画中静境最不易到。静不是死亡,反而倒是甚深微妙的潜隐的无数的动,在艺术家超脱广大的心襟里显呈了动中有和谐有韵律,因此虽动却显得极静。这静里,不但潜隐着飞动,更是表示着意境的幽深。唯有深心人才能刊落纷毕、直造深境幽静。陶渊明、王摩诘、孟浩然、韦苏州这些第一流大诗人的诗都是能写出这最深的静境的。不能体味这个静境,可以说就不能深入中国古代艺术的堂奥![14]377
吕氏几幅初春野景,色调柔韵欲流,氛围和雅明艳,令人有“如饮春风,如吸春胶”[14]378之感。这种描述和批评话语都是“生命意象”式的。宗白华指出:吕氏的静物、画面、山水,都仿佛笼罩着一层恬静幽远而又和悦近人的意味,能令人同它们发生灵魂深处的“接触”和“安慰”。其油画“静而有热”,堪称“嫩春”境界。这是从“生命体验境界”来评述吕氏作品的精神价值。宗氏还在《读画感记——览周方白、陈之佛两先生近作》(1942)一文中从传统艺境的标准来审视对周方白、陈之佛两位画家的作品,宗白华说:“山水画因为中国最高艺术心灵之所寄,而花鸟竹石则尤为世界艺术之独绝。”宋元花鸟画完美体现了一种精美华艳、高贵深永的艺境,陈之佛、周圭两人的画作“皆欲努力承继此伟大传统而出之以新意”,他们都能在承继传统中力求创新,“使古人精神开新局面,而现代意境得以寄托”[14]299。这些都是基于生机主义的“意象审视”和“境界评说”。
另外,宗白华还以艺术意象和艺术境界的“生命彰显”为原则,参照唐代敦煌艺术重“色彩”和西洋古典艺术重“写实”的标准,从文化学与色彩学的双重视角对中国现代绘画进行了“生机主义”的批评。他说:“中国画趋向抽象的笔墨,轻烟淡彩,虚灵如梦,洗净铅华,超脱暄丽耀彩的色相,却违背了‘画是眼睛的艺术’之原始意义。‘色彩的音乐’在中国画久已衰落。幸宋、元大画家皆时时不忘以‘自然’为师,于造化絪缊的气韵中求笔墨的真实基础。近代画家如石涛,亦游遍山川奇境,运奇姿纵横的笔墨,写神会目睹的妙景,真气远出,妙造自然。”[14]112他认为只有“敷色浓丽、线条劲秀”的唐代壁画,堪与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薄蒂采丽的油画比肩。近代以来只有画家任伯年能在花鸟画上表现“精深华妙的色彩新境”,他的“色彩画”令人反省绘画本来的“使命”。而此外其他画家则一味模仿传统,外失自然真感,内乏性灵生气,目无真景,手无笔法;既缺乏西画绚丽灿烂的光色,又遗失了国画雄浑流丽的笔墨,宗白华由此强调:“艺术本当与文化生命同向前进;中国画此后的道路,不但须恢复我国传统运笔线纹之美及其伟大的表现力,尤当倾心注目于彩色流韵的真景,创造浓丽清新的色相世界。更须在现实生活的体验中表达出时代的精神节奏。”[14]112色彩的失落,体现的是民族创造心灵与文化生命精神的整体衰落。宗白华的现代绘画批评彰显了其“艺术形式-生命创造-文化精神”三位一体的批评思路。
美国艺术理论家曾指出,现代主义艺术具有四大特征:偏爱抽象,画面的平面化,关注自己的“历史功绩”,艺术的“知觉本性”。[16]不可否认的是,宗白华的生命意象氏批评与空间美学理论在一味追求“抽象化”与“平面化”的现代主义艺术面前丧失了部分功能,宗氏所运用的中国“意境”概念来阐释和批评西方现代派艺术时其批评效果毕竟是有限的。这是宗氏固守生机主义艺术批评观在批评实践上所遭遇的困境,这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
三、宗白华的艺术批评史个案研究
宗白华还将生机主义的艺术批评话语延伸到古代艺术批评史的层面,试图从批评史重估和分析中来拓展现代艺术批评学的历史维度。《张彦远及其<历代名画记>》(1946—1948)是其进行中国艺术(绘画)批评史研究的个案。该文从生平、著述、理论体系、方法、价值等多方面、多层次地展开对一个古代艺术批评家及其著述的研究,这是一种艺术“批评的批评”。
在宗白华看来,张彦远是以研究艺术为终身事业,他的“不朽”的《历代名画记》就颇相当于温克尔曼(Winckelmann)的《古代艺术史》[14]451。张彦远在世界艺术批评史上之地位堪与佩特(Pater)、罗斯金(Ruskin)、温克尔曼等一流批评家比肩。正如温克尔曼由雕刻艺术而确立了“希腊文化的轮廓”,张彦远是由绘画艺术而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美的范畴”[14]466-467。宗白华从批评家的修养、结构、理论、方法与影响价值等五个层面展开对张彦远艺术批评的研究。
从批评家的修养看,宗白华认为张彦远在艺术批评上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和标准,这来自于其家族的丰厚收藏给予的绝对自信,而“对于创作方面的歆羡和感到有心无力之中更加强了对于艺术的热情和忠实。”[14]449这就是作为艺术批评家的修养。张彦远对于艺术的深爱和眷恋,使得他能“以艺术为安身立命之所”,也使得他亲近审美而远离欲望,在张彦远那里始终“充溢着审美的教养和陶冶”[14]450。视艺术为生命,这是张彦远作为一个严肃的艺术鉴赏家所确立的基本态度。从结构看,《历代名画记》与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类似,两者都是先有理论“体系的论述”,后有“史”的梳理,做到了史论结合。在《古代艺术史》里,温克尔曼在希腊的雕刻上发现了“希腊精神”,这种希腊精神成为后来古典主义者的“理想目标”。而在《历代名画记》中,张彦远也发现了中国人的绘画中所包涵的“中国所独有的文化教养与文化姿态”,从而使得中国的文人学者“获得了一种明显的文化传统”,并将这个文化传统“川流不息地发挥光大下去”[14]453。由此可见,张彦远和温克尔曼可谓是中西艺术史上两种“伟大的传统”的“发现者”和阐释者。
宗白华指出《历代名画记》呈现的艺术批评原则和方法有五个层面:其一,艺术的性质是“形上的,道德的,政治的”。张彦远继承了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所树立的中国学者对于“艺术之道德性”的肯定态度。张彦远不仅认同绘画可以“成教化、助人伦”,而且更看出了“艺术之形上的意义”[14]454。其二,张彦远认为艺术是“天生”的,艺术创造“贵乎天才”,“贵乎气韵”,而反对“谨细”(雕琢做作)。因为艺术家是“禀承大自然而从事的;一点人工的、机械的意味也不能有”[14]454,这便是天才;又因为“天才是能够符合大自然的,所以艺术不当以模仿他人为事,却应当创造,应当以自然为师”[14]455。张彦远说:“画性所贵天然,何必师范!”师范是模仿,他反对模仿前人,即当以自然为师。其三,张彦远发现中国绘画技巧的根本问题在用笔。从用笔之重要他又发现“书画同源”之说,书画同源既是指书画历史起源的一致性(“书画同体而未分”),也是指这二者运用了共同的技巧(笔法),因此中国绘画与书法同具“舞蹈性”、“音乐性”和“壮美性”[14]459-460。其四,张彦远首次提出“士大夫”绘画的概念,后来“士夫画”、“文人画”的心态肇始于张彦远。所谓士夫画、文人画,“即把绘画限制到是有教养的,有学问的读书人的活动,而对于倘若没有这些附带的资格的人的绘画则加以排斥”[14]460。张彦远说:“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这种观点影响了千年中国文人画的发展,到明代董其昌,更是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视为文人画家的理想生活,“匠气”和“书卷气”成为画坛衡量画品优劣的重要标准。其五,对艺术史进行美学风格的划分。宗白华认为,一种艺术史的时代风格划分显示的是我们对每一时代艺术的“一种美学的、批评的意味”[14]460。由此可见,宗白华将张彦远当做儒家美学思想的传承人,通过对张氏的儒家人生观、艺术观和历史观的梳理,建立了以儒家人格美学为基础的文人画史观。同时,宗白华强调了张彦远以自然为师的天才观,进一步彰显了生机主义的艺术理想。
宗白华对艺术史演进的解读,对艺术史的四个时期的划分,也是充满了生机主义的艺术批评观。宗白华说:温克尔曼曾认为艺术史的目的就在于叙述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艺术家的艺术风格变迁史;古希腊造型艺术的四个时期因时代不同而体现为四种不同风格,即“远古风格”、“崇高风格”、“典雅风格”和“模仿风格”这一由发展、繁荣、逐渐转向完全衰落的过程。《历代名画记》这部“中国画史”几乎以同样的思路概述了上古至唐代绘画风格的变迁:“上古之画,迹简意澹而雅正,顾陆之流是也。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展、郑之流是也。近代之画,焕烂而求备。今人之画,错乱而无旨,众工之迹是也。”[14]461四个时期四种风格,由简澹而精致,由新创而摹仿,由鼎盛而衰落,与古希腊艺术风格的变迁极为相似。宗白华说:“大概凡是一种艺术的生长,总是由自然而趋于造作的,到了造作的时期,就非有新内容,或者新刺激不能发展了”,而中国绘画却幸而由人物画而过渡到山水画,所以才有了“第二期的光荣”。艺术史“由简澹而精致,由新创而摹仿,由鼎盛而衰落”,恰恰体现了自然界“生长繁衰”的生命过程,这体现了生机主义模式的艺术史学观。
宗白华还借用一些西方美学范畴来对译中国古代艺术批评的概念,试图对中国传统艺术批评术语进行通俗化的解读。譬如张彦远将“谨细”视为匠人之画,他推崇的是天工之画,以“自然”为最高境界。在张彦远看来,绘画的品第是自然最高,其次是神,再次是妙,最后是精,精之为病成为谨细。宗白华认为“谨细”等于西方美学的“优美”(grace),他认为中国绘画所要求的是“壮美”(sublime),而不是“优美”。壮美就是要求单纯和简净,优美的就是琐屑和雕琢。张彦远的“谨细”固然是琐屑和雕琢,但并不等于西方美学中所谓的“优美”。照张彦远的本意看,谨细的对立面应该是“自然”(天工),而不是壮美。即人工之极致与天工之极致的对立。谨细与自然,代表了中国画的两个极端。宗白华将“壮美”与“优美”概念引入中国绘画批评中,来解释“天工”(神妙)与“人工”(谨细),尽管有误读的成分,但毕竟拓展了中国艺术批评的科学化路径,促进了传统批评话语的现代转化。总而言之,宗白华的生机主义艺术批评思想和方法继承了中西思想艺术批评的精髓,必将对当代中国艺术批评学建构和批评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1]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M].居延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157.
[2]文杜里.西方艺术批评史[M].迟 轲,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
[3]宗白华全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586.
[4]M·怀特.分析的时代[M].杜任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80.
[5]怀特海.思维方式[M].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32.
[6]吉尔伯特,库 恩.美学史:下卷[M].夏乾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759.
[7]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滕守尧,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41.
[8]宗白华全集:第三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01.
[9]成复旺.走向自然生命——中国文化精神的再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35.
[10]汪裕雄.审美意象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251.
[11]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82.
[12]李心峰.元艺术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97.
[13]H·G·布洛克.美学新解——现代艺术哲学[M].滕守尧,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389.
[14]宗白华全集:第二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313.
[15]宗白华全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789.
[16]阿恩海姆.艺术的心理世界[M].周 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14-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