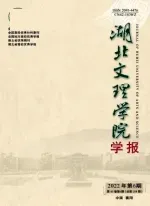文化因子·人性内涵·审美表达——论长篇历史小说《楚武王》的战争叙事
何冬梅
(江汉大学 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56)
战争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最高、最暴力的手段,通常也是最快捷、最有效果的解决办法。战争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沙比诺夫说:“战争是人类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必须要经历,这样促使了人类的发展,所以说战争是双向刃。”在中国历史的春秋时代,战争常常是诸侯国尤其是小国生存、发展、确立霸主地位的手段。刘保昌的长篇历史小说《楚武王》将叙述视点放在了春秋中叶的楚国,这是春秋时代最主要的历史时期之一,也是楚国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作品为我们讲述了楚武王背负先辈期望,承继楚国先辈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凭借坚韧、智慧及勇气,带领楚国人民,南征北讨,杀出一条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及强的艰难血路的故事。从楚庸争战开始,到伐随病逝,楚武王一生戎马,折冲沙场,经历了大大小小若干个战争。应该说楚武王的故事离不开战争,战争叙事成为小说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塑造楚武王形象,凸显楚人精神、楚文化精神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作者不仅凭借其非凡的想象力,生动形象地还原了近3000年前的战争场景,还凭借其深厚的学养为我们勾勒出楚文化茁长期战争的人文内涵,以悲悯的情怀对战争进行了深刻的人性化思索,同时又以诗意化的战争描摹为我们带来了审美享受。
一、战争的文化因子
历史,不仅是社会史,也是文化史。文化是历史的积淀,也是影响和左右人们行为的深层意识和根本价值观念。楚国号为“百战之国”,历来对楚人的评价,褒贬不一,褒之者曰‘尚武’,贬之者曰‘好战’或‘喜斗。楚人的“尚武”和“好战”是有其历史文化原因的。《史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说:“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楚文化的起点,就在这狭小的天地之中。“自周天子始封芈姓熊绎以子男之田,创立楚国,五传至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再十传至熊通,楚国立国已经270余年。东周时代,礼崩乐坏,周天子天命神授的权威,不时遭到诸侯的挑战;而列国之间,中原逐鹿,生灵涂炭。楚国因为僻在南国,又是子男之爵,一向被中原诸国视为草莽未化之区,地小民贫之国,是以无意侵伐,才得以在风雨飘摇的大时代中保存下来。”[1]165对从部落联盟体制中蜕化而来的楚国来说,如何在群强环伺中生存下去尤为重要。因此在楚国的发展史中,文治为武功奠定了基础,武功为文治开拓了天地。“战争”是楚文化生成及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楚武王》这部小说中,战争叙事包含诸多的文化因子。
1.兵制
在《楚武王》这部作品的战争叙事中,多次提到了楚国的兵制,无论是步兵时代的战争还是车兵时代的战争。在“楚庸争战”一章中就有这方面的介绍:楚师五人一组,号为“一伍”,五伍为一俩,作为一个战斗单元,二俩组成一偏,二偏组成一卒,十卒为千,由千夫长率领,直接听命于将军。
楚师的主帅称莫敖,后来也设大司马,左司马,右司马之类。组建了车兵之后,中军以“广”作为作战分队。在车战中,“开阔的战场上,楚师展开鱼鳞阵法,步军五人攻防组迅即跟进,甫一接战,即显声威。”楚国兵制方面的这些特点,是因夷夏结合而形成的。充分展现了楚人的智慧及其创新精神。
2.兵器
春秋时期兵器的精良与否往往决定着战争胜败,同时也与这个国家的铸造术及铜锡产量相关。《楚武王》中有大量关于武器的描写:“在春秋时期,戈分两种:步军所用戈,一般柄长一丈二尺;车兵所用戈,一般柄长两丈四尺。戈是其时作战的主流兵器,可以勾、啄、割等方式杀敌;”[1]88“五百乘战车甲士,改用矛戈合体的长戟。戟在楚国又被称为“孑”,兼具戈与矛的优长,杀伤力则更强更猛。”[1]296文本中还有对“弓箭”的大量描摹,因为春秋时代及远的兵器只有弓箭,而且楚人善射。作品中“琴青山”这个人物就是一个善于制造、发明弓箭的神射手,而且著名的楚将“斗仲比”、“斗丹”也都是善射的猛将。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中出现较多的兵器是戈与矛,因为春秋早期楚国兵器以戈和矛为主。
小说不仅为我们介绍了春秋时代武器的相关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在文本中兵器使用者的个性与兵器的特点是和谐的。刚勇的斗沮使用长矛;斗缗城府极深,心机莫辨,他善使剑;勇敢机智的斗仲比善用弓箭;忠勇的蒍章也善使用长矛;细腻深沉的斗廉善用长戈。公子瑕,威猛无匹,一柄阔身厚背长刀重十斤八两,所向披靡。特别是武王熊通所使用的武器——楚戈(楚公家秉戈),它锋利、纹饰华丽、怪异,不仅充分彰显了武王善战、刚猛的个性,而且具有楚文化神秘的色彩。
3.精神
楚国将士身上拥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因子,在战争中表现为勇往直前,不畏生死。有蚡冒、熊通这样的君王,身先士卒,冲杀在前;有公子瑕、斗沮、蒍章、斗廉这样的将领冲锋陷阵,攻城斩将;更有千千万万普通士兵,他们战死沙场时嘴角泛起的微笑,告诉世人“生何其欢,死又何惧”的宁静与满足。于是才会有“宝剑锋从磨砺出,干将发硎,谁与试锋?”的豪情,才会有“人生一世,有多少美好的东西值得留恋?又有多少美好的东西值得以生命去换取,以玉碎为代价去誓死捍卫?”的慨然。关于楚人的爱国精神,张正明先生有过这样的论述:“楚人的先民在强邻的夹缝中顽强地图生存,时间之长以数千年计。楚人在穷乡僻壤中顽强地求发展,时间之长以数百年计。由此,养成了楚人以民族利益为至重至上的心理。”[2]108楚国的将领,如果有覆军之败,往往自尽以谢国人和君王。武王命其子屈瑕伐罗,结果惨败,公子瑕自裁。作者满怀激情地评价这段历史:“楚国就是这样一个敢于承担的血性民族!楚人就是这样一群宁可站着死也不愿苟且活的热血儿女!”
积极的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是楚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从兵器的改良,到“走险棋,出其不意”的战略部署,到完备兵制的建设,无不体现了这一点。楚国原没有战车,若想与中原列国争胜,必建战车营,于是楚人举全国之力建战车营。“对楚国来说,谨守诸夏的发展模式抑或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是生死攸关之事。假使楚国甘心步诸夏的后尘,那么,在强侵弱、众暴寡的时事里,恐怕它等不到战国,而早就从春秋的舆图上消失了。幸而楚人独行其是,变弱小为强大,而且在许多方面由落后到领先,创造了先秦历史上的奇迹之一。楚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所显示的独创性,是楚文化的原动力。”[2]88
二、战争的人性内涵
战争意味着屠杀和毁灭,胜利是除了失败以外最大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从来就没有胜利者,这才是人类最大的悲剧。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最能彰显人性的内涵。作者刘保昌在《楚武王》后记中谈到其写作冲动在于为楚人和楚王“正名”。在“喜战”的楚人征战光辉历程中的不光有流不尽的英雄血,嗜血的冲动,杀人的欲望,更有身处乱世以求自保和发展的无奈与悲凉。
1.悲悯情怀
楚人迁居江汉地区历时既久,栉蛮风,沐越雨,潜移默化,加以他们对自己的先祖作为天与地、神与人的媒介的传统未能忘怀,由此,他们的精神文化就比中原的精神文化带有较多的原始成分、自然气息、神秘意味和浪漫色彩。[2]88楚人是浪漫而多情的,因此在《楚武王》的战争叙事中我们看到了“爱的依恋”。斗伯比在大战前夕轻轻捏住腰间玉佩,缓缓抚摸,就像抚摸情人的脸庞。此时此刻,他想到了表妹姬荷;面对卢、邓联军视死如归的斗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了容兰的小手和她明亮的双眸。在文本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悲悯。“西河关塞,将会成为多少将士的坟场?”这是斗沮感受到一种玉石俱焚的悲凉;大战后飘来一片箫声,如泣如诉,悱恻凄怜,这让蒍章、季梁不禁悲从中来;每临战阵,楚王熊通总是难以抑住天地不仁的感叹。他在格杀庸将时也会充满悲悯的同情。“此种同情,绝非骄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既然生在乱世,人或为刀俎,我或为鱼肉,杀与被杀,都同样是被命运欺玩。”战争总是会让人变为非人,但战争并不能使人性泯灭。
2.激情倾诉
在《楚武王》文本中,我们会看到一种直接介入的叙述方式,这是一种激情倾诉,是作者真情的流露,尤其是关于战争,作者有若干直接评述。“只有醇酒美妇的快乐,才能忘却死亡的恐怖和无常;正是因为见证了死亡的迅捷和莫测,醇酒美妇才会更加让人沉醉和迷恋。”这是对战争与死亡的理性思考;“楚国民众,众志成城,誓死抗争,硬是在弱肉强食之际,堪堪地生存下来。多少血泪,流成了江水,莫不是为了楚国的强大。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就会被列强所灭。”这是借熊通之口对楚国历史的深切的反思;“历史的理性更需要有一位精明强干、能征善战的英雄作为自己的国君,而熊通,正是这样一位青年英雄。这才是历史的选择。”这是对历史的中肯的判断。这种直接叙述的方式使叙事服从感情的需要,叙事与情感互为表里,从而升华了作品的内涵。
三、战争的审美表达
1.凄美的意境
意象世界的营造对于渲染情境,烘托气氛,衬托人物的心境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战争的残酷性会使山河失色,大地呜咽。《楚武王》中为我们精心营造了一个个意象世界。让我们感受战争、体味战争、反思战争。“山风习习,刁斗声声”;“月光如霜,夜雾如梦”;“星河黯淡,西河呜咽”;“金风玉露,冷月寒蝉”;“此夜无月,繁星满天”;“火光映天,星斗失色。杀声动地,水流不前”。“一切景语皆为情语”,这里山河、日月、星辰都承载了情感,那是一种“万物为刍狗”的悲情。一幅幅凄美的画面与惨烈的厮杀、血腥的搏斗后的残躯断臂、血流成河相映衬,产生了触目惊心的视觉效果,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冲击力,具有较强的审美表达效果。
2.壮观的战争场面
战争的英雄化和战争的灾难性是文学反思战争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基本向度。刘宝昌把战争的残酷写到了极致,这种极致表现为战争逼真的描摹。阴冷、凄美、壮观的战场叙事让人在目睹毁灭和死亡的时候不忘记对战争本身的思考。
在《楚武王》中战争场面描写比比皆是,无论是大规模的全局性战争还是局部小范围的战争作者都在用心地描摹。无论是“蚁附蚋聚,前后相踵”的攻城战,还是“血溅如雨,摧枯拉朽”的步军之战,“战马嘶鸣,杀机凌厉”的车军之战,作者都写得酣畅淋漓。鲜血,断肢,杀戮,死亡,嗜血的冲动,战斗的激情,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特色完全凸显出来。
小范围局部战斗的描写,作者也写得既有美感又有个性特征,颇有中国武侠小说之风。这种个性化与艺术化相结合的武技描写,写出了中国武术的“神韵”,同时也颇具文化意味。如作品中对楚武王熊通武技的描写就突出了这个特色。熊通好武,对天下兵器和武技痴迷。他的成名武技是“祝融九式”,从“九式”名字就可以看出楚文化的气韵,从第一式“开榛辟莽”到第九式“江晏汉清”,春秋时代的楚国不正是这样一路走来,开拓进取,愤发图强,才得以在风雨飘摇的大时代中保存下来吗?“祝融九式”看似朴拙混沌,却极具实战性。楚人自古就有“楚狂”的称谓,熊通是楚人的代表,也是典型的楚人,“狂”亦是他的人格特征。因此战场上熊通将他的“狂”发回得淋漓尽致。他的长戈浑如出水蛟龙,短剑势如苍鹰行空,破敌杀人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心手相应的舞蹈。
3.典雅的叙事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传统的民族语言则是文学的民族形式的第一要素。作为历史小说既要还原历史情境,营造小说的历史感和古典氛围,又要方便今天的读者阅读,这需要作者高深的语言功力。《楚武王》在战争描写中,非常注重语言古典美的追求。如:
凄美的月色下,薄雾如帐,将天地间一场惨烈的厮杀后留下的枕藉尸体,涂抹成浓浓淡淡的阴影;群山环列,如梦似幻,宛若朦胧飘渺的梦境。三千楚国壮士血染沙场,七千余庸国将士大地长眠,都已成为慈母或爱妻的深宵梦中人。
这是一段大战后的场景描写,句式整齐,音韵优雅,节奏舒缓、低沉,渲染了悲凉的氛围;对偶、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增强了文本的美感。再如:
战场如同默片,但见人影幢幢,火光四起,中箭,斧砍,射杀,剑劈,戈击,矛刺,流血,倒地,活人似已变身为无欲无知的木偶,杀人与被杀俱已成为机械动作,杀人者不喜,被杀者无悲,超越生死之际,一切已无法撼动衷怀。
繁复的意象,不断闪烁的画面,短促的句式,强烈的节奏感,犹如频频鼓点,撞击人的心灵,营造了紧张的气氛。《楚武王》的语言运用充分彰显了汉语言的魅力,言简义丰,空灵蕴藉。作者成功地汲取了古汉语含蓄典雅的精髓,用具有古典美特色的语言引领我们走进历史,感悟历史。
历史知识对于人类,不仅仅是一种智力上的需求,而且是精神上的慰藉和一种审美的渴望。审美化的战争叙事是《楚武王》的显著特征,小说文本以文学方式恢复了民族历史记忆。战争叙事中文化因子的注入,使读者了解了独具一格的楚文化传统精神;文本中传递出来的对生命的人文关怀及悲悯情怀,让我们看到了战争背后的人性内涵;其凄美的景物渲染,壮观的场面描写,典雅的语言风格,更把我们带入到瑰丽的审美世界。
[1]刘保昌.楚武王[M].武汉:崇文书局,2012.
[2]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