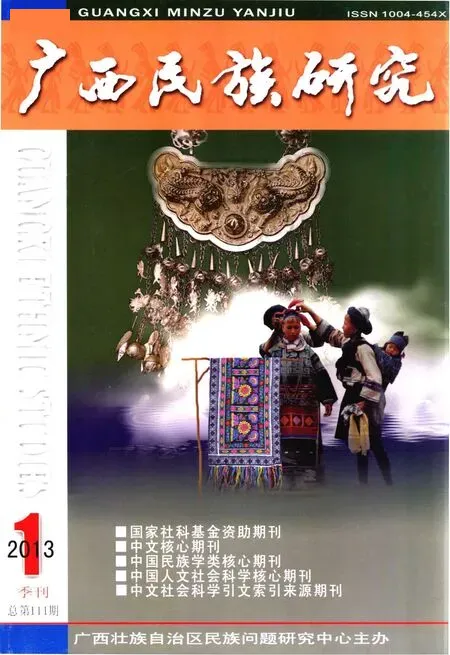人类学中国宗族研究的嬗变与创新*
刘 芳 刘树奎
一、中国宗族研究的弗里德曼范式
20世纪四十年代,福忒思等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通过对努尔、泰兰西等非洲部落社会“裂变宗族制”结构的深入研究,构建起颇具影响的非洲宗族范式。[1]弗里德曼的研究旨趣和理论雄心,正是通过对中国宗族的深入研究,修正和突破非洲宗族范式。他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2]、《中国宗族与社会》[3]等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国宗族有关的理论观点,标志着人类学宗族研究的弗里德曼范式的形成。弗里德曼在其理论范式中提出的若干研究假设,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探讨得最集中、争论最激烈的核心论题。可以说,围绕着弗里德曼范式的分析和论辩,构成了中国宗族研究的一条主线。在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范式中,通过族产、祠堂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祀产要素发挥了核心作用。[4]从这类经济性要素出发,弗里德曼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宗族的裂变模式、类型结构和形成机制。
非洲宗族范式关注地缘政治结构和血缘宗族间的高度契合,宗族裂变在这一理想情境下会达至某种平衡状态。相比之下,弗里德曼将影响宗族结构的关注点转向了经济性因素,并指出在中国是“宗族内部的贫富不均产生了不平等的裂变分支”,而这些“直接依赖于经济资源”的裂变群体,如果没有祠堂、土地等祀产要素的支持,就不可能产生并作为独立的实体长期存在。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宗族的“非平衡裂变”模式,突破了非洲范式的理论框架。[2]48-49[3]37-39
弗里德曼进一步指出,社会声望、政治权力,尤其是经济地位上的巨大优势,使中国宗族中的强宗大族往往比弱小宗族更具凝聚力,也体现出更为复杂的非平衡裂变结构。基于中国宗族的这种特性,弗里德曼构造出一个以A模式、Z模式两个“理性类型”为两端的宗族类型连续系统。由于“共同财产的不平等获益模式一直是大规模宗族组织的重要特征”,因此具有“非平衡裂变”典型结构的,是较为富裕、成员众多且高度分化的Z型宗族。[2]74[3]169-170相对的,小型的A模式宗族并不稳定,当他们富裕起来并形成祖田、族产后,就会开始向大型宗族发展。换言之,A型宗族始终具有Z型化趋势,而拥有较多祖田族产的Z模式才是中国宗族的发展趋向和主要形态。在这里,共同财产规模、分化程度等经济性要素始终是弗里德曼运用“A-Z模型”类型化中国宗族的关键变量。
最后,弗里德曼对中国宗族存续和形成机制的解读,也是建立在共同财产等经济性要素之上的。在他看来,中国东南区的大型宗族组织,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移民早期开垦高产土地形成的共同财产。共同财产与宗族存续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如果祖田、族产等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蚕食殆尽,则宗族组织也会随之消亡。在探讨宗族形成机制时,弗里德曼指出,“高产稻米经济形成的财富盈余和累积促成了共同财产体系的运作,共同财产又推动了大型继嗣性社区共同体的发展”。继而,弗里德曼在“边陲社会”情境下,又综合稻作、水利、处女地开发等经济性要素,建起一套分析宗族形成的独特解释机制。[2]129-130[3]160-163
总体来看,弗里德曼对共同财产的强调,使他倾向于把中国宗族理解为一种以继嗣关系为载体、以合作性为基本特征、具有非平衡裂变典型结构、拥有共同财产的实体性组织。在人类学界的后续研究中,中国宗族以继嗣关系为载体的合作性特征获得了广泛认同,[5]但其他围绕祀产等经济性要素形成的论断和假设则遭到了普遍质疑。这些不间断的学术争论和反思,推动了中国宗族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二、对弗里德曼范式的反思与突破
弗里德曼范式的核心假设,是作为关键变量的共同财产等经济性要素与中国宗族的构成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相关和因果联系,而大量针对弗里德曼宗族研究的学术反思和创新,也围绕着这一假设及其核心变量展开。
华若璧 (R.Watson)在她的新界宗族研究中注意到,大型支配宗族完全可以通过祠堂等共同财产,由无法上溯继嗣关系的独立宗族联合形成。共同财产等政治经济要素不仅可以形成非平衡的宗族裂变,还可以产生相反的聚合效应,构成裂变模式无法涵括的聚合型宗族。[6]研究台湾宗族的学者也发现了相似情况,并对裂变型和聚合型两类宗族组织进行了区分。[7]实际上,弗里德曼本人在他学术生涯的晚期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聚合型宗族的存在表示了认同。[8]
学者们对台湾的田野研究也推翻了弗里德曼从经济生态角度对宗族形成所做的因果解读。巴博德 (B.Pasternak)借助两个台湾村落的实证资料指出,边陲状态下基于稻作和灌溉需要而形成的生产合作,可能首先是一种基于地域性网络的跨宗族合作;而一定规模的稳定的宗族组织,则已经是边陲社会的晚期形态。[9]此外,也有研究质疑了弗里德曼意义上的大规模Z型宗族与富裕度高、分化明显等要素间的密切关系。韩敏的皖北研究,就提供了一个并不富裕且贫富差距不大,但却系谱清晰、规模庞大的宗族个案。[10]
同时,宗族作为共同财产的控产单位的思路也受到较多批判。有学者研究发现,占有相当多土地的大宗族也可能把田产继承限定在家庭内部,并由此成为不具备共同财产的非控产性宗族组织。[11]73-245尹沛霞 (P.Ebrey)也指出,拥有共同财产的控产型宗族,有可能是华南地区的特有类型,共同财产应该更普遍地存在于家庭层面,而不是宗族之中。[12]16-61
上述针对共同财产等经济性要素展开的反思和批判,动摇了弗里德曼从经济性视角解读中国宗族的范式逻辑。大量研究表明,经济性因素与宗族的结构类型、生成机制之间并无明确的相关或因果联系,非平衡裂变并非中国宗族的典型构成形式,大型控产宗族也仅是中国形态各异的宗族组织中的特殊一种。由此,要理解更为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宗族,就必须突破弗里德曼的解读模式,寻找新的更具普遍解释力的变量和要素。
基于上述原因,在尝试突破弗里德曼范式,实现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弗氏相对忽视的地缘性因素对宗族的影响。弗里德曼受到非洲学派地域、宗族重合模式的影响,更多关注单宗族村落,并认为形成这类村落是宗族发展的内在动因和总体趋势。而针对此论断的研究反思,则更为重视村落内的宗族聚居和地方化要素。
福瑞德 (M.Fried)等人认为,中国宗族是个相当严格的封闭系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村落社区多由数个宗族构成,这与非洲范式血缘、地缘高度重合的社区模式完全不同。[13]杜赞奇(P.Duara)也注意到,那些没有共同财产且宗族意识强烈的华北宗族,往往高度聚居于村落内某一区域,这类宗族“不仅力求同族聚居,甚至希望同族土地连在一块”。[14]105艾亨 (E.Ahern)反思了弗氏的单宗族村模式,并对单宗族村落和两类不同的多宗族村落进行了区分。她发现,很多宗族族谱不仅标示出血缘系谱的脉络,更详细记载了该宗族迁徙、定居的过程。她由此推断,是聚居和地方化等地缘性因素而不是财产性因素,在主导着宗族的构成和运作机制。[15]
不过,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即使已经达到地方化聚居理想状态的单宗族村落亦可能宗族意识淡薄,鲜有合作性的宗族活动。郝瑞 (S.Harrell)曾就此指出,共同财产和地方化聚居都有强化宗族组织的作用,只不过地方化似乎更容易凝聚宗族组织,而前者除非有相当规模,否则很难达到同样的凝聚作用。[16]由此,聚居和地方化变量虽然重要,但仍需与其他要素综合起来解读中国宗族的形态和构成。
除了地域性因素,另一类尝试突破弗里德曼范式的研究把关注点转向了族谱、文化等历史性因素。弗里德曼的宗族范式虽建立在深入文本研究的基础之上,但仍明显具有结构功能主义的实证方法论倾向。在弗氏看来,族谱虽是人类学研究的绝好素材,但却可以主观臆造,因此与具备合作性特征、凝聚力较强的宗族组织没有必然的联系。
就此问题,科大卫 (D.Faure)区分了口传族谱和文本族谱,并从“入住权”理论出发,指出宗族存续的意义更多体现在族人的历史认同上,而文本族谱不仅编制出共享入住权的宗族群体,更凝聚了宗族成员,因此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科氏提出了宗族的“文化创造”理论,之后更进一步扩展到“国家认同”等宏观的文化历史维度。[17-18]受其影响,不少研究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宗族,认为它“是在国家行政划分的框架下,由一群无论有无血缘关系的人建构的一个父系继嗣群体”,应该从文化认同角度对其展开研究。[19]
不过,也有研究对族谱和文化视角持怀疑态度,认为族谱和宗族的生成发展没有必然联系。有的宗族虽然有族谱和祠堂,却没有集体性的宗族活动。实际上,如果注意到弗里德曼等人对宗族合作性基础的强调就不难发现,重视共时性实证材料的人类学学者,更多将族谱等历史资料作为田野资料的辅助和补充。若从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出发,则单纯的族谱记载还不足以理解具有合作性特征的中国宗族组织,笼统的文化因素也很难直接运用于相关的人类学宗族研究之中。
三、仪式与宗族
在弗里德曼的宗族范式中,仪式与共同财产等经济性要素相比始终处于次要位置。在弗氏看来,各类仪式中只有以祠堂、祖牌或祖先坟茔为载体的祭祖活动,能部分体现宗族的合作性特征,其他则多不具备凝聚宗族组织的作用。受其影响,人类学研究者在探讨中国宗族时,很少把仪式活动从政治经济系统中剥离出来,独立加以研究。
随着理论对话和相关探讨的深入,仪式性活动开始受到重视,更有研究将其作为理解中国宗族形成和发展的核心要素加以强调,认为族谱和祠堂作为发达继嗣组织的重要元素,都具有仪式上的目的;选墓址,看祭日,重长幼,也都具有仪式上的意义。也有学者关注葬礼仪式,认为明清以来宗族组织的发展与宗族性葬仪的流行关系密切,葬礼活动也是形成宗族纽带的重要因素之一。[20]
不过,华琛 (J.Watson)等学者注意到,研究者在运用仪式要素解读中国宗族时多关注祭祖或葬礼,似乎中国的继嗣群体仅仅在面对逝者时才存在。[21]但实际上,这两种仪式体现的宗族合作特征也会因地因时而有所不同。在华北,即使合作性特征明显的宗族组织,在清明时也可能按门支分开进行祭祀。而华北的宗族祖坟祭祀与祠堂、祖牌祭祀虽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相似功能,但更容易和家庭、门支祭祀混淆,近年来这里的族祭也更多转变为针对近世祖先的家庭性祭祀。[22]韩书瑞(S.Naquin)的研究就显示,与宗族特征明显的华南葬礼相比,华北的葬仪多在家庭的凝聚力上发挥作用。[23]58-59
同时,不少研究也注意到,与宗族密切相关的仪式并不限于祭祖和葬礼。华若璧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宗族性婚仪中的姻亲和宗亲原则多处于相互竞争的张力状态。明确的宗族意识和父系继嗣观念,可以表现在对姻亲和未嫁女儿的消极态度上,更可以体现在对婚姻仪式的操持和运作之中,弗里德曼实际上忽视了婚姻仪式在表达、彰显宗族凝聚力方面的巨大作用。[24]另外,不少学者也关注节庆仪式在形成宗族凝聚力方面的关键作用,认为这类仪式普遍存在于那些宗族意识较强的宗族组织中,比如华北宗族的拜年活动就多被广泛的宗亲互动主导,因此是与清明节类似的体现宗族凝聚力的重要年度性仪式。
另外,很多围绕宗教尤其是民间信仰及其仪式活动展开的探讨,也将中国宗族研究与乡村信仰仪式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方面,民间信仰在传统乡村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乡村社区的凝聚和整合提供一个超越经济利益、阶级地位和社会背景的集体象征。[25]86通过庙会等民间信仰和仪式活动,村落内部形成了一种密切互动的关系,村民的共同体意识也得到了增强和巩固。另一方面,民间信仰仪式并不局限于村落社区层面,那些围绕神明展开的仪式活动,同样可以发挥凝聚宗族组织的作用。[26]在福建和广东,祭拜妈祖的仪式活动也可以成为强化宗族共同体的手段;[27]在台湾,保圣大帝崇拜也体现出民间信仰在巩固宗族凝聚力方面的重要作用。[28]82而且,除了民间信仰,天主教等制度性宗教中的仪式也可以提升宗族的凝聚力,这在华北和东南地区的宗族组织中都有所体现。[29-30]
总体来看,虽然仪式性要素还未引起中国宗族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但这些从丧礼、婚姻、节庆、信仰仪式出发,探讨中国宗族组织的研究反思,已经凸显出仪式要素在解释中国宗族结构、特征和凝聚力上的重要作用,拓展了学术界分析、探讨中国宗族组织的研究路径。从这个视角来看,祖先祭奠、丧葬活动、婚礼仪式、庙会节庆、宗教活动等等,都可以发挥维系和凝聚宗族组织的作用。宗族性仪式互动的研究思路,为我们理解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宗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
四、中国宗族研究的范式创新
综观中国宗族研究的发展历程,虽然从弗里德曼对经济性变量的强调,到反思弗里德曼范式的学者对地域性、文化性要素的关注,中国宗族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从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的实证研究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宗族研究仍面临着很多困境和挑战。
首先,目前用于分析中国宗族特征的诸要素还不够完善。弗里德曼之所以将经济性要素作为宗族研究范式的核心,不仅在于其对中国宗族结构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更在于其作为宗族组织重要的外显特征具有方便观察、易于测量等特点,因此从某种角度讲,弗里德曼关注的经济性要素与实证研究中“变量”的基本特质相当吻合。波特 (J.Potter)就曾强调指出,弗里德曼的研究之所以具有范式性的指导意义,就在于经济性要素是一个具有社会学价值的研究变量,透过它可以清晰、具体地探讨中国宗族组织的结构和特点。[31]相比之下,地域性、文化性要素的变量特征则非常模糊,地方化聚居的程度、文化和族谱认同的程度都很难清晰的界定和测量。
其次,中国宗族研究的实证性取向还不够突出。受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的影响,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范式具有鲜明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特征。但囿于时局的限制,弗里德曼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不得不偏重文献和史料分析方法,在资料采借上也更多倚重史料记载、前人著述等文本性的非实证材料。弗里德曼范式的这一结构性特征,使得后续的学术对话多在文本材料和实证材料两个层面上展开。而随着研究者更为广泛地借鉴和引述文献史料,近年来文本研究的方法论取向已日渐成为中国宗族研究的主流。只不过历时性的研究方法不能替代共时性的实证考察,单纯地关注文本和史料并不符合弗里德曼构建中国宗族范式的初衷,也无益于在当代中国宗族研究中延续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凸显人类学传统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的特色。
最后,研究中国宗族的理论范式的推广性还存在问题。在构建中国宗族范式的过程中,弗里德曼希望其强调的经济性要素可以用来分析、探讨所有类型的宗族组织。基于此,弗里德曼将不具备共同财产的血缘继嗣群体排除在“宗族”之外,从而实现了其理论范式的自圆其说。但实际上,这种基于华南宗族经验的论断,并不符合华北等地宗族组织的现实情况。从这个角度看,弗里德曼最初的范式雄心至今也没有达成。与经济性要素的范式困境相类似,文化性要素和地域性要素也同样面临着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推广性问题。
近年来,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社会变迁对中国传统宗族家族模式的巨大挑战,并认为当代宗族研究应该从族谱、族产、祠堂等外显特征,更多转向对日常事件等实际宗族作为的关注上。[32]本文所关注的仪式性要素,正反映了人类学研究视角的这种转换。与以往的中国宗族研究相比,着重探讨仪式性互动的研究路径将宗族的日常仪式活动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关注祭祖、葬仪、婚礼、节庆、信仰等具体仪式活动中宗族组织的互动形态、互动范围和互动频率,以及这些不同的仪式互动对宗族共同体产生的凝聚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也从人类学实证研究的角度,提出若干探讨中国宗族的研究预设,以期对未来人类学中国宗族研究的实证考察和田野调研有所助益:
首选,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宗族是具有共同体特征的血缘继嗣群体,普遍存在的宗族性仪式是维系其群体特征的主要形式,宗族凝聚力的强弱是衡量宗族共同体特征是否明显的主要标准。
其次,祭祖、葬仪、婚礼、节庆、信仰等不同形式的仪式性互动,在维系、巩固宗族凝聚力方面发挥着相似的作用。这些仪式在互动频率、互动范围、互动类型等方面的变化,是分析和探讨中国宗族特征的关键指标。
最后,宗族性的仪式互动越多样、越深入、越频繁,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就越强,其宗族共同体的特征就越明显;反之,缺乏各类宗族性仪式互动的血缘群体则凝聚力较低,也不具备人类学意义上的宗族组织的特征。
总体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宗族的人类学研究经历了数次发展、创新,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无论是弗里德曼的经典宗族范式,还是相关研究反思中形成的理论突破,都丰富并充实了学术界对中国宗族的认识和理解。只不过,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这些经典研究可能已无法完整概括中国宗族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复杂情况。在当代人类学研究的语境下,围绕仪式性要素展开的中国宗族研究或可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学术尝试。
[1]Fortes,Meyer& E.E.Evans-Pritchard.African Political system[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0.
[2]Freedman,Maurice.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M].London:Athlone Press,1958.
[3]Freedman,Maurice.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M].London:Athlone Press,1966.
[4]乔素玲,黄国信.中国宗族研究:从社会人类学到社会历史学的转向[J].社会学研究,2009(4):196-213.
[5]Watson,James.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J].China Quarterly,1982,92:589-627.
[6]Watson,Rubie.The Creation of a Chinese Lineage[J].Modern Asian Studies,1982(1):69-100.
[7]Cohen,Myron L.Agnatic Kinship in South Taiwan[J].Ethnology,1969,8(2):167-182.
[8]Freedman,Maurice.The Politics of an Old State:A View from the Chinese Lineage[G]//The Study of Chinese Study: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9]Pasternak,Burton.The Role of the Frontier in Chinese Lineage Development[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9,28(3):551-61.
[10]Han,Min.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 village in northern Anhui.China:a response to revolution and reform[M].Osaka: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2001.
[11]Rawski.The Ma Landlords of Yang-chia-kou in Late Ch'ing and Republican China[G]//P.B.Ebrey & J.Watson.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000-194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12]Patricia B.Ebrey.The early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scent group organization[G]//P.B.Ebrey& J.Watson.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000-194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13]Fried,Morton.The classification of Corporate Unilineal Decent Group[J].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57,87(1):1-29.
[14]Duara,Prasenjit.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15]Ahern,Emily.M.Segmentation in Chinese Lineages:A View through Written Genealogies[J].American Ethnologist,1976,3(1):1-16.
[16]Harrell,Stevan.Social Organization in Hai-shan[J].In Ahern,Emily and Hill Gates eds.,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1981:140.
[17]Faure,David.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J].Modern China,1989,15:4-36.
[18]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J].历史研究,2000(3):3-14.
[19]张宏明.宗族的再思考:一种人类学的比较视野[J].社会学研究,2004(6):23-31.
[20]Brook,Timothy.Funerary Ritual and the Building of Lineag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J].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89,49(2):99-146.
[21]Watson,James L.Anthropological Overview: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escent Groups[G]//P.B.Ebrey & J.Watson.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000-194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274-292.
[22]Cohen,Myron L.Lineage Organization in North China[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0,49(3):519-521.
[23]Naquin,Susan.Funerals in North China:Uniformity and Variation[G]//J.Watson,E.Rawski.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24]Watson,Rubie.S.Class Difference and Affinal Relations in South China[J].Man:New Series,1981,16(4):593-615.
[25]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范丽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6]Sangren,P.S.Traditional Chinese Corporations:Beyond Kinship[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4,43(3):391-415.
[27]Watson,J.Standardizing the Gods: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G]//D.Johnson et al.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28]Wang,Shih-Ch’ing.Religious Organ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 Chinese Town[G]//Arthur Wolf.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29]Madsen,Richard.China’s Catholics:Tragedy and Hope in 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M].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30]张先清.官府、宗族、天主教[D].厦门: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3.
[31]Potter,Jack.Land and Lineage in Traditional China[G]//Maurice Freedman.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32]杨善华,刘小京.近期中国农村家族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0(5):8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