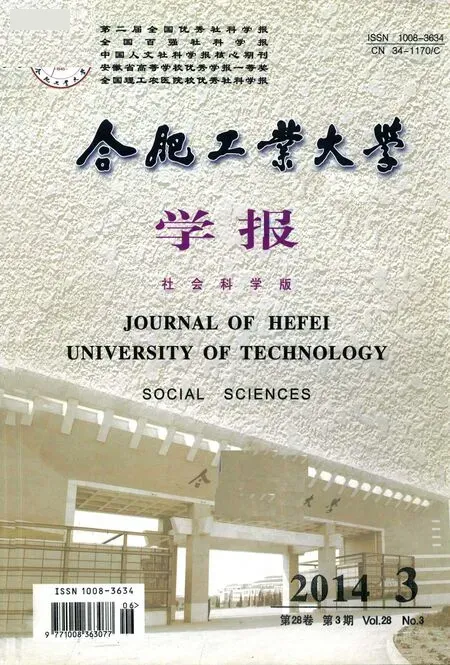苦难历练中追寻自我的民族家园——小说《伙计》的犹太文化母题解读
沈 萍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15)
一、文化母题与家园意识
伯纳德·马拉默德(1914-1986)因其鲜明的犹太道德观和犹太性被公认为美国当代重要的犹太裔作家之一。纵观马拉默德的作品,可以发现他深受犹太历史和《旧约》的影响,犹太文化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也是理解其作品深层次内涵的关键所在。文化研究(包括对犹太性的解读、对原型母题的阐释和对犹太文化的解读等)是目前国内学者对马拉默德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来看,马拉默德的代表作《伙计》和作者其他的著作一样,对犹太民族坚守的“寻找自我的民族家园”这个文化母题进行了移位运用,展现了犹太民族的受难意识、追寻主题和对当代美国社会文化的反思。
母题是一种具体和个别的话语形象,它通过在作品中不断重复地出现而表达出来,它表述的是一种集体的文化意识,源自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集体记忆和民族传统意识[1]。母题所表述的民族历史传承是对文学作品进行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它不仅体现了作者本人的创作意图,而且还融合了本民族的集体文化意识。
犹太文化母题是犹太文化历史进程中具有恒定意义的品质结构,体现了犹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业已形成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及其范式。它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寻找自我的民族家园”是犹太民族的一种恒定的文化母题。从犹太历史角度看,犹太人几千年的民族演进历史是一部典型的流浪史。在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之前,犹太民族自诞生以来从未有过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家园。他们总是以客民的身份,寄寓在他种文明之中,甚至遭受他种文明的迫害。历史上的数次大灾难——十字军的杀戮、中世纪的西班牙的犹太隔离区,奥斯维辛集中营……,都深深震撼了整个犹太民族。苦难的流散生活状况使犹太民族的留存无法再依靠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来维系。他们共同的文化传统、经历和非犹太人社会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迫害便成为犹太民族流散史的主要内容。尽管远离故乡,但生活在散居地的犹太人以自己的方式,从一日三餐到所有的节日庆典,都在精神上与故土联系在一起。重回迦南可以说是每个流散犹太人的梦。在颠沛流离中,犹太人既要坚守自我的文化故土又要寻找自我的文化身份,这就形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民族集体意识。
马拉默德的小说多以追寻精神家园为主线,描绘了20世纪中期的美国社会中一大批犹太人的精神风貌。从《天生运动员》(1951)中的罗伊、《新生活》(1961)中的列文、《犹太鸟》(1963)中的施瓦茨到《基辅怨》(1966)中的雅柯夫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主人公寻找自我价值、追寻精神家园的文化母题,他们历经磨难,虽看似失败,却在坎坷中实现自身道德的完善与人格的提升。
二、小店——精神隔都与迦南圣地
从文化批评的母题传承角度看,小说《伙计》对犹太民族坚守的“追寻”母题进行了艺术阐释,体现了对当代美国社会和文化富有哲理的反思。小说生动地描述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犹太移民莫里斯·鲍伯的苦难隐忍和孤儿出身的意大利流浪汉弗兰克·阿尔帕恩的救赎历程。
整部小说的框架结构——十个章节简直就是一部犹太历史的隐喻体:先知的慈悲(莫里斯的善心)、人的原罪(弗兰克的罪恶)、惩罚(弗兰克的受难)、流放(被驱逐出小店)和回归(接替莫里斯)。这样的构思与马拉默德的成长、所受的文化熏陶不无关系。他出生于俄国犹太移民家庭,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希伯来文化和犹太教圣经《旧约》,所以他对自己民族传统有着深刻的认同感。他在小说创作中继承发扬了犹太一神教的思想传统,“他擅长让意第绪语文学和民间传说中的常见人物穿上现代人外衣,重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借此来探讨精神危机的主题”[2]123。他在描写人的精神困境和危机同时,更强调人应该去追求真善、道德、伦理,过上《托拉》要求的那种生活,去履行活下去的道义和职责。
《伙计》是一部关于现代受难者与现代追寻者的小说。马拉默德原本打算将这部小说命名为《学徒》(The Apprentice),在他创作手稿的笔记中,他将四个人物做了如下定位——“莫里斯:逃脱经济困境;弗兰克:追寻道德的自己;伊达:逃脱不安的生活状态;海伦:追寻有价值的生活”[3]56。莫里斯是一位现代的约伯、亚伯拉罕式的受难者。他是俄国犹太人,从沙皇军队开小差逃到美国,定居于犹太族裔群居地,孤独经营一爿小店20余载,终日劳作不息,却依旧贫困潦倒,最后他带着无尽的悲哀离开了人世。弗兰克是一位追寻者,小说沿袭了“父与子”的犹太文化母题,并以独特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意大利移民在美国经济萧条时期所经历的‘寻父-尊父-为父’的心路历程”[4]。弗兰克在圣·方济和莫里斯两位精神之父的感召下承受良知的考验、实现道德再生,其寻父-尊父-为父的历程体现了小说寻找民族家园的隐喻性主题。现代受难者与现代追寻者在这爿小店相遇——于莫里斯,小店是他栖身20余年的“隔都”;于弗兰克,小店是他的涅槃之地,造就他重生的“迦南圣地”。
隔都是犹太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隔都的出现“既取决于犹太人飘零所至的各居住地主民文化,也取决于犹太文化作为客民文化自身的某些内在原因”[5]43。作为一个离散民族,犹太人若想延续其民族生命,隔都作为犹太文化在异质文化里的重要载体,无疑成了犹太人保持其文化传统的有效工具。在小说中,莫里斯的杂货店,不断地被称之为监狱、坟墓、墓地、棺材、没有去向的长黑隧道……,它十足是一个现代的隔都。莫里斯放弃了成为药剂师的儿时梦想,“长大成人来到美国以后,他难得看到天空。早先他赶大车的时候,还是看得到天的。一开店,就看不到了。在店铺里,你就等于进了坟墓”①文中所引小说文本均出自《伙计》,叶封译,译林出版社,2008。。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当有机会卖掉这家小店时,他却断然拒绝,因为“他一想到上无片瓦的情景,就心神不安”。
其实,莫里斯坚守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栖息之所,同时也是试图在维系自己本民族的传统和精神核心。对犹太人而言,犹太性是保持其民族身份的重要特性,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讲,小店是犹太性的载体,是莫里斯的精神隔都。在近代社会随着有形的隔都之墙削弱,一道无形且更坚韧的墙,即精神隔都,在继续规范犹太人的现世生活、维护犹太人的历史传统。何为精神隔都?“精神格托喻指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在可能改变了传统的格托生活的情景下仍然具有一种深刻的精神和文化联系[5]46。因此,作为一名犹太后裔,莫里斯一直在坚守这爿小店,小店即是他的精神家园。然而,一名意大利裔的流浪汉为什么也要留守这爿看似了无生机、令人窒息的杂货店?
弗兰克是一名孤儿。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身边带着的枪被刑警的儿子沃德看到,在沃德的诱逼下他们合伙抢劫了莫里斯,后来因为一时萌发的赎罪之念,他来到了莫里斯的店里帮忙。初来小店,他感受到了生活的稳定与家庭的温暖。然而当他渐渐意识到小店里乏味而压抑的生活时,他不禁感慨:“生下来注定要把自己关在这样一口大棺材里,这得是怎么样的人才行?”因此,小店不仅是莫里斯坚守犹太道德的场所,也同时成为弗兰克实现道德重生的受难场所。当莫里斯向他表达肺腑之言:“铺子等于坐牢”时,弗兰克却毅然选择留在监狱般的铺子里。于是一个充满欲望的年轻人,一个负罪深重的灵魂,一个穷困潦倒的流浪汉,开始跟随精神之父的指引,带着职责与勇气,经过炼狱的洗礼,实现了自我救赎,恶的灵魂最终变成了善的象征——圣·方济。这个历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旧约》中摩西带领数万以色列子民历经40年磨难最终抵达“应许之地”——迦南的场景,小说中莫里斯扮演着摩西的角色,指引着弗兰克在小店这片流奶与蜜之地涅槃重生。在马拉默德笔下,一个非犹太人在犹太性的感召下找到了心中的迦南圣地,可是自耶路撒冷的毁灭后那些一直渴望回归的犹太人该如何重回迦南?在原罪之后人类又将如何重返伊甸园?马拉默德试图以其鲜明的犹太性用一种文化母题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在一次Paris Review的访谈中,当被问及禁锢的母题时,他解释道:“我将它隐喻为全人类面临的困境。我们将自己囚禁于过往的经历、愧疚、妄想中。人类必须构建和创造自己的自由”(Stern 54)。马拉默德坚信以犹太人为代表的全人类通过不断地磨练终能克服自身的局限,实现自由与重生。
三、踯躅在两种文化之间的身份认同
Sidney Richman曾这样评价马拉默德,“马拉默德被认为是我们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声誉不仅是巨大的,而且还是国际性的”[6],他认为马拉默德的声誉主要是他在作品中完美地表现了自己的犹太性。一般认为,马拉默德的犹太性主要表现在他对犹太宗教和文化的理解上,例如,他对“苦难”以及犹太伦理道德观等问题的认识,都深刻地表现了他的犹太性。
同时,马拉默德笔下的道德导师几乎都是犹太民族智慧与集体记忆的化身。“他们穿着现代的外衣,给那些精神上受挫、误入歧途的追寻者以道德与审美上指引”[2]125。在小说中,莫里斯既能以坚忍的毅力去承受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又能以坚定的犹太信念对待生活。用忍受苦难和施以善行的方式救赎自己和他人。可见,马拉默德通过这一人物的塑造,意在说明“美国犹太人应该如何在非犹太社会中生活;如何用犹太人所持有的坚定的宗教信念在救赎自己的同时,完成对非犹太人的救赎——让非犹太人自愿地皈依犹太教”[7]387。因为这样的书写,马拉默德常被冠以“犹太味最浓”的美国犹太作家。他始终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并将自己的犹太身份与整个犹太民族的生死存亡相联系。
然而,在非犹太人弗兰克追寻精神家园的历程中,反复出现了一个基督教的人物——圣·方济。小说出版后,一些犹太人开始不断指责马拉默德的写作太受基督教的影响,一位以色列的读者在来信中,直接称《伙计》为一本“基督教的书籍”[3]138。或许,马拉默德的作品对一些美国人而言,太过犹太化;或者对一些犹太人而言,太过基督化。但这绝对不是他小说创作的窘境。作为移居美国的犹太人,他必然存在着身份认同问题、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融合问题以及缅怀犹太传统和重新认识犹太传统精神等问题。一方面,他站在历史的高度,清楚地认识到:犹太人以客民的身份寄居在他种文明之中已是非常不易,他们要生存并发展下去,只凭忍受“苦难”来救赎自己、实现犹太人的身份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以忍受个人痛苦的方式去救赎非犹太人,并藉此救赎来巩固、扩大或保全自己民族生存的机遇”[7]390,因此小说中意大利裔的流浪汉皈依犹太教的情节并非偶然;另一方面,马拉默德一直受着犹太文化和美国社会主流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双重影响,尽管他并未像索尔·贝娄一样对认同自我民族的文化之根产生困扰,但他在小说创作中综合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道德思想,并提出了基于人性的、实现道德重生的可能性。在《伙计》的挪威版本序言中,马拉默德借机表达他对这两种宗教的看法:“以爱、善、忍等特质去定义一种宗教优于另一种宗教是毫无意义的”[3]139。
因此,弗兰克在圣·方济的指引下实现犹太身份的新生,并非是基督教与犹太教两种宗教文化的冲突,恰恰相反,这是两者在人性的光辉下实现的道德共生,这也是犹太裔作家在美国社会现实中进行文学创作的一种策略。
离散文学的批评家认为:对于离散群体,家代表归属。身份认同的过程,也是寻找家园的过程。作为世代流浪的民族,犹太人渴望建立自己的祖国(即使不是真正地理意义上的家园),他们渴望获得一个精神上的民族家园。追寻精神家园也许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但对于犹太人来说,这种探索似乎特别沉重。正如美国学者比尔·汉迪所言,马拉默德小说在简单的故事情节中始终包容了一种固执、甚至不无沉重的精神探索历程,他的主人公无一不肩负着对生命终极目的探索,而且,在探索中成熟起来。这是他的小说的基本格调。
马拉默德本人曾说,“我很看重我的犹太血统,但我并不把自己仅仅当作是一个犹太作家,我有更广泛的兴趣,我认为我在为所有的人写作”。他在文学创作时将犹太人作为人类生存的悲剧经历的象征,移位运用犹太文化母题,展示对当代美国社会和文化富有哲理的思考,体现了其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在他看来,所谓的“犹太人”已超越了种族概念,已成为全人类的一种象征,正如他的名言“人人都是犹太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马拉默德的文学创作主旨衔接了美国犹太文学中的犹太性与普世性。
[1] M H Abram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M].Orlando:Harcourt Brace Publishers,1999:169.
[2] Kremer,S Lillian.Reflections on Transmogrified Yiddish Archetypes in Fiction by Bernard Malamud[M]//The Magic Worlds of Bernard Malamud,Albany:State Unvi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
[3] Davis Philip.Bernard Malamud:A Writer's Lif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4] 傅 勇.在父辈的世界里——对马拉默德小说中“父与子”母题的文化解读[J].当代外国文学,2008,(2):62-73.
[5] 刘洪一.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2.
[6] Scholes Robert.Portrait of Artists as“Escape-Goat”[M].Critical Essays on Bernard Malamud,Boston:G.K.Hall &Co,1987:47.
[7] 乔国强.美国犹太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