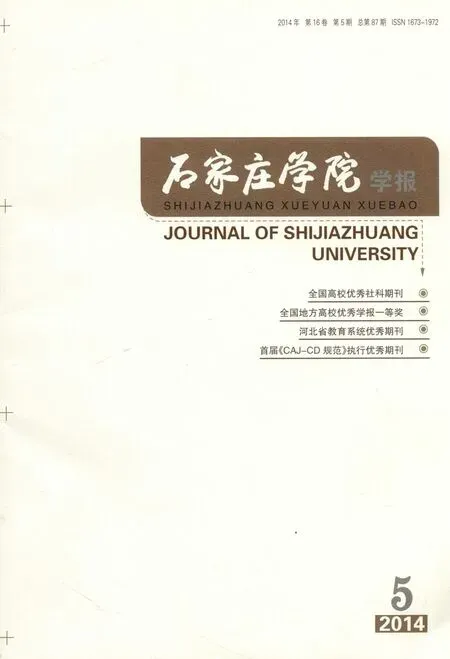北朝赵郡李氏的家学传统与慈善
许秀文,王文涛
(河北师范大学 a.历史文化学院;b.公共管理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北朝赵郡李氏的家学传统与慈善
许秀文a,b,王文涛a
(河北师范大学 a.历史文化学院;b.公共管理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赵郡李氏是北朝时期著名的世家大族,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佛教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赵郡李氏固有的经学传家的仁爱思想与佛教信仰的悲悯情怀既彼此独立又互相融合。李氏族人在这些思想指导下进行了很多慈善活动,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关系和救助百姓,也扩大了赵郡李氏家族的影响。
北朝;赵郡李氏;经学传家;佛教慈善
赵郡李氏家族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世家大族,鼎盛于北朝时期,与当时的博陵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南阳郑氏、太原王氏等高门著姓并称于世。政治上官位显赫,经济上田连阡陌,文化上引领繁盛,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浓厚的文化氛围、经学传统和宗教信仰、悲悯情怀也将这个高门望族与慈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北朝赵郡李氏概况
赵郡李氏的先祖可以溯源到很古老的年代,这里只上溯到与本文所论问题关系密切的西晋时期。李楷任西晋“司农丞、治书侍御史”,后因“避赵王伦之难,徙居常山”[1]卷七十二上,“家于平棘南”①平棘在今河北赵县城南1.5公里的固城村,汉时属常山,晋时属赵郡。[2]卷三十三。唐高宗时所修《姓氏录》②《新唐书》卷九十五《高俭传》:“又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昏(婚)。”参见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 842页。,亦以李楷为赵郡李氏的代表人物。历史上,赵郡作为一级行政区划的置废和辖区时有变更,基本区域包括今赵县、高邑、赞皇、临城、柏乡、宁晋、隆尧、栾城、元氏等县,李氏家族活动的遗迹在这些地点均有所发现。
李楷在平棘开创了赵郡李氏的家业,有子五人:辑、晃、芬、劲、睿。北魏初期,随着人口繁衍增加,李氏家族逐渐析居,兄弟五人分为三支,李辑、李晃兄弟居平棘城南,为南祖房;李劲、李芬兄弟居巷西,为西祖房;李睿居巷东,为东祖房。③关于赵郡李氏房支问题,本文采张葳《赵郡李氏“三祖”小考》的观点,未将辽东房、江夏房、汉中房纳入赵郡李氏。参见张葳《赵郡李氏“三祖”小考》,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5年第22辑。北魏统治者为了巩固在北方的统治,极力拉拢汉族豪门士族。凭借旧时的门第、威望和经济实力,赵郡李氏各祖房很快发展为颇具影响的大族,进入家族的鼎盛期。
在中国古代社会,能否入仕为官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登科入仕者的数量是判断一个家族是否显赫的重要因素。赵郡李氏人才辈出,众多子弟步入仕途,荣任北朝政坛重要的职位和官爵。梁武帝曾说:“伯阳之后,久而弥盛,赵李人物,今实居多。”[3]卷二十九仅以东祖房支为例,北魏太武帝时期,李顺晋爵高平公,为四部尚书,“宠待弥厚,政之巨细,无所不参”[2]卷三十三。李顺从父弟李孝伯晋爵宣城公,为平西将军、秦州刺史,太武帝“委以军国机密,甚见亲宠”,并称“朕有一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为?”[2]卷三十三李孝伯之子李安世,曾为主客给事中,后为相州刺史,假赵郡公,上疏孝文帝提出均量土地建议,对北朝和隋唐实行均田制产生了深刻影响。北朝官员选任采用九品中正制,赵郡李氏东祖房族人有李宪、李元忠等数人曾兼任本州的大中正,品评人物,择优推荐。结合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及效果可知,多人多次被择任本州大中正,足证赵郡李氏世家大族的地位和这些官员的品级高贵、地位尊隆。
二、北朝赵郡李氏的经学传家与慈善
(一)北朝赵郡李氏的经学传家
诚如钱穆先生所言:“门第与儒学传统有不解之缘。 ”[4]169-170世家大族多以经学传家闻名于世,即使是军功起家,也会逐渐从军功转向经学,教育子弟以经学为务,由武力强宗转为文化高门,以经学传家的文化传统薪火相传,维持家族地位累世不坠。赵郡李氏亦是经学传家,世代学习儒家经典,各房支都有一些造诣颇深、卓有才名的代表人物。
南祖房。李义深“学涉经史,有当世才用”;其弟李同轨“学综诸经,多所治诵”;其族弟李神威“幼有风裁,传其家业,礼学粗通义训。又好音乐,撰集《乐书》,近于百卷”;其子李騊駼“有才辩”,出使南朝陈,“为陈人所称”;其孙李正藻,“明敏有才干”。[3]卷二二
东祖房。李勰“恬静好学,有声赵、魏间”;李勰之子李灵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征天下才俊,灵至,拜中书博士。再迁淮阳太守。以学优,选授文成皇帝经,加中散、内博士,赐爵高邑子”;李灵曾孙李瑾“淳谨好学,老而不倦”;李灵曾孙李浑参禅代仪注及删定《麟趾格》,熟悉国典朝章在魏收之上;李浑之弟李绘幼年早慧,“历中书侍郎、丞相司马。每霸朝文武总集,对扬王庭,常令绘先发言端,为群僚之首。音词辩正,风仪都雅,听者悚然,文襄益加敬异”;李绘弟李纬“少聪慧,有才学”;李浑之子李湛,“涉猎文史,有家风”;李灵侄孙李宣茂,为中书博士;宣茂孙李公绪“性聪敏,博通经传”,“雅好着书”;宣茂曾孙李德饶,“少聪敏好学”。[2]卷三十三
李灵从父弟李顺一支,李顺 “博涉经史,有计策”;李顺子李敷“以聪敏内参机密。敷性谦恭,加有文学,文成宠遇之”;李敷弟李式,“学业知名”;李式子李宪“清粹善风仪,好学有器度”;李宪子李希宗,“性宽和,仪貌雅丽,有才学”;李希宗弟李希仁,“有学识”;李希仁弟李骞,“博涉经史,文藻富赡”;李骞弟李希礼,“性敦厚,容止枢机,动遵礼度”;李希礼子李孝贞,“好学善属文”。[2]卷三十三
李顺从父弟李孝伯,“少传父业,博综群言,美风仪,动有法度”,“风容闲雅,应答如流”,“体度恢雅,明达政事”;李孝伯父李曾,“少以郑氏《礼》《左氏春秋》教授为业”;李孝伯兄李祥,“学传家业,乡党宗之,位中书博士”;李祥子李安世上书魏孝文帝均量之制;李安世子李玚,“涉历史传,颇有文才,气尚豪爽,公强当世”;李玚弟李谧,“少好学,周览百氏。初师事小学博士孔璠,数年后,璠还就谧请业”;李谧弟李郁,“好学沈靖,博通经史”,“自国学之建,诸博士卒不讲说,其朝夕教授,唯郁而已。谦虚宽雅,甚有儒者之风”;李谧子李士谦,“诣学请业,研精不倦,遂博览群籍,善天文术数”。[2]卷三十三
西祖房。李诜,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年间,和东祖房李灵同为被征召的天下才俊;李普济,“学涉有名,性和韵”;李皦,“有学识”。[2]卷三十三
(二)北朝赵郡李氏的家风与慈善
经学儒术作为世家大族的文化身份特征,其意义绝不仅仅是能培养学识渊博的饱学之士,更重要的表现是世家大族的经学传承,随着时代的进程已经把儒学的精神实质烙印到族人的为人处事里,体现在他们的社会活动中。儒学的仁孝礼让、恻隐之心等追求,蕴涵着悠久的慈善思想,或许远不能与现代定义下的慈善相提并论,但在赵郡李氏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家风与善行生动丰富的体现。
1.从孝行到推己及人
西祖房李密之母缠绵病榻多年,遍寻名医诊治,仍不见好转。李密于是“精习经方,洞闲针药”[2]卷三十三,终于治好了母亲的疾病,也因此成为了闻名遐迩的良医。
东祖房李德饶“德行为当时所重”[2]卷三十三,非常孝顺,父母卧病,他衣不解带、废寝忘食地守候在病榻之侧。父母去世,他悲痛至极,口吐鲜血,在寒冬积雪中哀凄送葬,几欲气绝,哭嚎之声令旁观者动容落泪。德饶的孝行感天动地,国家特别下旨吊慰,将其居住的村改名为孝敬村,里改称和顺里,号召百姓向他学习。
东祖房李元忠也是著名的孝子,因母亲年老多病而潜心钻研医药,多年之后于药石之术有了深厚的造诣。他天性仁恕,见到病人,不管病人有没有钱,医药费需要多少,都立刻尽心尽力为他们治疗。
李士谦,北朝著名隐逸贤士。幼年丧父,“事母以孝闻,母曾欧吐,疑中毒,因跪尝之”[2]卷三十三,可见其孝心之重。后来一心向佛,多行善事。
孝老爱亲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要求,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友爱是人伦,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则是道德的延伸,是慈善。
2.从修齐到仁民爱物
东祖房李绘做高阳内史时,遇上高阳干旱,陂淀干涸。李绘设置专门的农官劝课农桑生产,使得垦田数量倍增,百姓家给人足,得到实惠。
李元忠的父亲李显甫,“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2]卷三十三。 这件事发生在北魏后期,李显甫在父亲李恢去世之后,带领数千家李氏族人迁至殷州西山,开“李鱼川”,以李姓命名,聚众垦荒,从事农业生产,希望建成一个鱼米之乡。在战乱年代,这是招徕流民重返故土的极好举措,救济安抚了流民,为国家减少了不安定因素,有利于恢复社会生产。
李元忠时,家境殷实,多余的钱物在乡里间放贷求利。李元忠经常将债券焚毁,免除贫穷乡邻的借贷,乡邻敬之。
北朝后期,“时人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2]卷三十三。李安世虑及百姓利益,向孝文帝上疏建议实行均田制,限制士族多占田产、民户,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
修身齐家是儒家理想的基础目标,仁是儒家思想的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二者有着层次上的差别,修齐之后才能治国平天下,才能逐渐达到仁的境界。仁者,爱人,仁爱的本质决定了仁爱必然要得到无限的扩大,最终达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仅仅做到修身齐家,还停留在血缘或地缘亲情的层面;仁民爱物才将仁心推广到最远,造福更广大的人群。
三、北朝赵郡李氏的佛教传承与慈善
(一)北朝赵郡李氏的佛教传承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被君主和世家大族所接纳,传播得相当顺利。北朝赵郡李氏族人中有相当多的人接受或信仰佛教,甚至形成了家族信仰佛教的传统。
南祖房李同轨是北朝著名经学家,兼通佛学和医术。“学综诸经,多所治诵,兼读释氏,又好医术”。永熙二年(532年),魏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讲法,敕同轨论难,音韵闲朗,往复可观,出帝善之”。兴和年间(539-542年),李同轨以兼通直散骑常侍的身份出使梁朝。梁武帝萧衍“深耽释学,遂集名僧于其爱敬、同泰二寺,讲《涅盘大品经》,引同轨预席。衍兼遣其朝臣并共观听。同轨论难久之,道俗咸以为善”[5]卷八十四。
东祖房李祖娥,李希宗女,嫁于高洋,后为皇后,社会动荡,命运多舛,屡遭凌辱,最后被迫出家为尼。[3]卷九李元忠之女出家为尼,号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为尼。所居去邺三百里,往来恒步,在路或不得食,饮水而已”[2]卷三十三。
李士谦,事母至孝。十二岁时,被东魏广平王元赞聘为开府参军事,后因母丧辞官归家。守丧期满,他舍去家宅为伽蓝,延请僧人入住;自己则脱身游学,博览内外经籍,善天文术数。终身不饮酒食肉,口无杀害之言。
西祖房李裔,字徽伯,因参与高欢谋建东魏,封固安县伯。北魏宣武帝元恪笃信佛教,当时整个北方崇佛之风大盛。李裔深受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子孙多受其影响,信奉佛教。
(二)北朝赵郡李氏的佛教慈善活动
北魏宣武帝延昌末年(512-515年),李裔感叹“假使门兼万石,不能遣生灭之源;家累千金,不能去吉凶之域”,认为“同生者物,异物者超生;滞教者方,离方者会教”[6]卷五十九,产生了舍弃部分田宅财产、种下福田功德,以求得到今生平安和来世快乐的念头。不久,李裔将自己位于今天河北省元氏县的山第别业捐给僧人建立寺院,名偃角寺;孝明帝孝昌之际(525-528年),改为隐觉寺。隐觉寺经魏末到北齐,僧徒众多,香火旺盛。至北周武帝灭佛,佛像被毁,僧徒遭遣,寺产没官。后因李裔之子李子雄为北周高官,寺产赐还给了李裔嫡长孙李祖元。隋初,李祖元继承李裔遗志,仍然在旧址建佛寺,更其名为开业寺,由李氏族人世代整修维护。唐太宗年间为其颁赐名额,由于政府的认可和保护,开业寺成为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上述事迹记载在唐朝开耀二年(682年)李氏子孙所立的“开业寺碑”中。碑文记述了开业寺从李裔舍宅建寺到唐初的历史变迁,颂扬了李裔的功德,并记载了李裔的子孙后代及其仕宦情况。李裔子孙受其影响,世代奉佛,悉心护持开业寺,在北朝至隋时期士族崇佛中很有典型性。
李元忠之女法行出家后,一片慈悲心肠。“逢屠牵牛,脱衣求赎,泣而随之。雉兔驯狎,入其山居房室。”[2]卷三十三齐灭亡后,遭遇荒歉之年,法行便在路上施舍糜粥。她的俗家异母弟李宗侃与族人李孝衡争夺一块地,不可开交。法行说:“我有地,二家欲得者,任来取之,何为轻致忿讼?”[2]卷三十三宗侃等人闻言非常惭愧,于是互相谦让,原本相互争夺的土地变成了闲田。法行虽已出家,但仍有一定财产,并与家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佛教信徒的身份增加了她话语的分量,在维护家族和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士谦是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终身从事慈善活动的慈善家。他“家富于财,躬处节俭,每以振施为务”,邻里中有人无力办理丧事不能殓葬的,他施以棺木。有兄弟分财不均而争讼的,他就出钱补助不足的一方,以致兄弟惭愧而互相推让,也都成为善人。有一年灾荒,李士谦拿出家中的存粟数千石,借给同乡。次年,仍然歉收,借粟的人都无法偿还,到李士谦家中道歉。李士谦说:“吾家余粟,本图振赡,岂求利哉!”他把欠债的人全部请来吃饭,当众把乡邻们借粟的债券烧为灰烬。对他们说:“债了矣,幸勿为念也。”第三年大丰收,欠债的人争相来还债,全部被李士谦拒绝,一无所受。乡人称其大德,感激不尽。“他年又大饥,多有死者,士谦罄竭家资,为之糜粥,赖以全活者将万计。”[2]卷三十三他还帮助收埋骸骨,所见无遗。第二年春天,李士谦又捐出粮种,送给贫困乡民,让他们及时播种,生产自救。
开皇八年(588年),士谦死于家中,时年66岁。赵郡百姓听说后,无不痛哭流涕,说:“我们不死,反倒让李参军死了啊!”参加葬礼的有一万多人。他的妻子范阳人卢氏,也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李士谦去世后,所得赙赠,她一概不受,对乡里父老说:“参军平生好施,今殒殁,安可夺其志哉!”[7]卷七七于是散粟五百石以赈济穷乏。《北史》还记载,李士谦“凶年散谷至万余石,合诸药以救疾疠,如此积三十年”[2]卷三十三。李士谦的慈善活动前后长达30年,慈善行为涉及济贫、赈灾、助葬等方面,凶年散谷达到一万多石,救济的灾民数以万计,其慈善活动规模之大,成效之显着,在中国古代极为罕见。李士谦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他的慈善行为无疑受到佛教慈善观念的巨大影响。李士谦这样的民间慈善家的出现,既表明北朝慈善活动的活跃,也说明慈善事业比前代有了显著的发展。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等认为,六朝时期形成了以豪族之家为主导核心的共同体,在战乱动荡的社会里,地方名门望族在聚居区中履行“孝义”的家庭伦理,也履行“友义”的公共道德,为同居住区的宗族、乡党提供赈恤、御敌、调解纠纷和教化等帮扶活动。①参见谷川道雄《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续)》,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6辑,第22-24页;川胜义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史研究における立场と方法》,载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日本东海大学出版会,1980年,第3-16页。随着佛教的顺利传播,在北朝的华北地区出现了许多佛教“邑义团体”。“邑义团体”以一个村落或更大的乡里地域为范围,大多数由当地豪族与僧侣发起,小区居民共同参与造佛像、建寺院、读诵佛经、举行斋会仪式和互助等活动。
出土于河北正定的东魏兴和四年 (542年)《李氏合邑造像碑》,记载了以李次、李显族为首的李氏宗族198人以及村邑中其他姓氏的佛教信徒及比丘僧共计231人以李氏宗族为主体开展的一系列佛教活动。颜尚文以东魏李氏豪族发起的村邑居民共同信奉《妙法莲华经》而从事建寺、造像、种树、造井等集体公益行为,阐述了北朝佛教小区共同体的组织与活动。他认为,李氏合邑小区的集体佛教活动,以建造“佛像”“菩萨像”为主。此外,还进行村邑外面的社会公益事业。[8]233-247《李氏合邑造金像碑颂文》中有这样的文字:
今季末李次、李显族百余人,藉胄轩皇,兰枝玉叶,望芙海标寸仁英,建□□祖。乃宗出自赵垄,因官爰处,即居□境。乘此敷分,胤隆千室。虽居异方,抱馨转馥,子孙孤挺,跗萼相承,联光槐□。[9]
从中可以看出,这里的李氏族人有可能出自北朝赵郡李氏,因做官而整族迁徙。碑文中还写道:
于村中造寺一区,僧房四周,讲堂已就,宝塔凌云……复于村南二里,大河北岸,万路交过,水陆俱要,沧海之宾攸攸,伊洛之客亦届,经春温之苦渴,涉夏暑之炎燠。愍兹行流,故于路旁造石井一口,种树两十根,以息渴乏。由斯建立,遐迩称颂。自前生后,信心弥着,重福轻珍。……斯等邑人,置立方处。方处临河,据村南东。平原显敞,行路过逢。人瞻来仰,府设虔恭。含咏发心,报福是钟。[9]
《李氏合邑造像碑》彰显了“法华思想”主导的佛教小区共同体中的组织和与活动情况。李次率领族人和村中居民,共同信奉《法华经》并组成法华邑义团体,会归众生入一佛乘的愿力,落实随缘实践慈悲救渡的菩萨行,共同建立寺院讲堂;[8]239-243在修建寺庙、僧房、宝塔、造像的同时,在水陆交会的要道旁掘井、植树,供来往行人饮水、纳凉、休憩,蒙受法华菩萨行的恩泽,还吸引行人到村庙中瞻仰佛像,启发他们虔诚的菩提心,得享更大的福报。这个以李氏家族成员为主的邑义,将佛教的慈悲善念推而广之,泽被他人,突破个人、家庭、宗族、小区的救助局限,到居住区之外从事更加广泛的社会公益事业。“邑义之活动,不但是组织乡村城市佛教信徒进行广泛的佛事活动,尤其在乡村更发挥了其进行公益建设的组织者的作用。”[10]257邑义作为一种佛教信仰者的团体,就是以普世的慈悲情怀关注每一个加入其中的成员,这个组织超越了身份地位、种族和贫富的限制。[11]11但是,并没有完全摆脱等级制因素的束缚,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10]266
赵郡李氏以家世学养鼎盛于北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也在社会思想大潮中接受了佛教的影响,与经学的精髓相融合,做出了许多慈善之举,既仁爱百姓、造福一方,也助推了家族的繁荣。
[1]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M]//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
[5]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王昶.金石萃编[M]//历代碑志丛书:第五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7]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新乡市博物馆.新乡北朝、隋唐石造像及造像碑[M]//文物资料丛刊: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9]颜尚文.法华思想与佛教小区共同体──以东魏 《李氏合邑造像碑》为例[J].中华佛学学报,1997,(10):233-247.
[10]尚永琪.3-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11]杜继文.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程铁标)
Li Family Tradition and Charity of Zhao Country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XU Xiu-wena,b,WANG Wen-taoa
(a.School of history&Culture;b.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 050024,China)
Li family of Zhao Country was a famous aristocratic family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at time.Buddhism developed rapidly.Li’s kindheartedness from Confucian culture and the compassion of Buddhist belief wer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mutually penetrative as well.Li family conducted many charitable activ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se ideas.These activities eased social conflicts,adjusted social relations and rescued the poor,and expanded the influence of Li family of Zhao Country.
the Northern Dynasties;Li Family of Zhao Country;Confucian classics education;Buddhist charity
K239.2
:A
:1673-1972(2014)05-0015-04
2014-05-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经验研究”(10BZS013);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慈善通史”(11&ZD091)
许秀文(1972-),女,河北玉田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