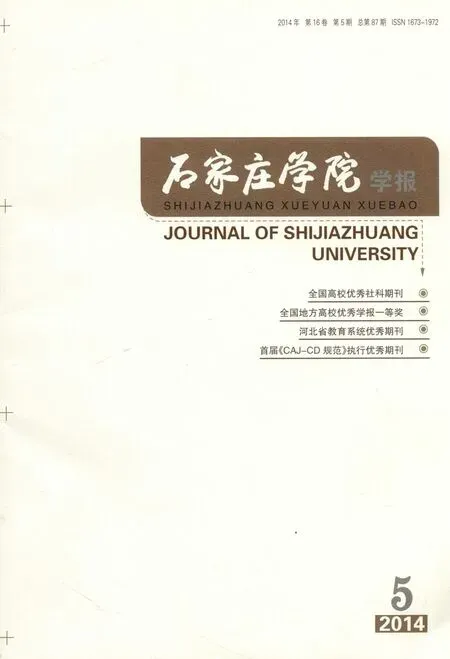生态环境伦理保护的冷思考:根治“心灵雾霾”
赵一强
(河北经贸大学 法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环境危机蔓延世界,其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同时也是主观意识作用于现实的结果。应对环境危机不仅需要技术改造,更需要意识形态的转向,无论是环境治理的形上基础还是现实操作机制,其中总贯穿有基本的价值取向或价值诉求。价值属于伦理学研究范畴,它将自身悬挂于行为主体的意识世界,通过区分善恶边界引领主体行为,激励实然向应然辩证发展。环境本来就具有生态性,主要是由于工业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强大征服力和改造力影响了自然环境自身的新陈代谢规律,给人类的生存、发展和繁荣带来了环境瓶颈,所以才有生态理论的出现,才有保护复归环境生态性的迫切需要。而从生态环境向社会领域的类比挪移,就出现了建立生态社会或在人类社会中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追求。生态环境的伦理保护,就在于从道德维度反思人类的精神世界,拨开笼罩在心灵上空的迷雾和灰尘,将精神世界中关涉环境保护部分的原则理念显现出来,实现从道德混沌到道德明澈、再从道德明澈到道德顶点的辩证演练,为生态文明确立坚实的伦理根基。
一、环境是否真的需要保护
环境是否需要保护是环境哲学思维的逻辑起点。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环境范畴,是在自然环境的意义上使用的。自然环境在古希腊神话中就是宙斯所统领的世界,在中国古代则称为宇宙,现在亦称为自然界。
自然环境作为实体和主体,主要由三种元素组成,即浩淼的宇宙虚空、众多的美丽星球、散布于具体星球上多种多样的事物。经过科学探索,人类现在能够使用宇宙虚空传递信号,能够探索其他星球的奥秘,同时利用地球上的相关资源谋求发展和进步。在人类能力无法企及的距离、时间或领域,环境保护就是一个虚命题,因为这里根本没有人类的主体性、意志性、利益性在内。人类具有高度的自信,认为自己是万物之灵、万物之主,能够管辖、统领和使用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殊不知,这仅仅是人类自信心的表现,从真实性上看,人类无非就是地球上的一种高级生命形式,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潜力是不断拓展的,但是就具体时代而言,人类的活动区域又不能超越其能力所允许的范围之外。如果我们希望人类去保护太阳系之外的世界空间,那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以目前人类所拥有的技术力量来看,只能是“变形金刚”式的憧憬和对自我安全感的宽慰。在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上,只能把关系区域定位在人类活动所能达到的环境部分,而不能将人与环境的关系区域置放于无限巨大的宇宙空间,也只有在“关系域”内讨论环境保护才有现实意义。
人类是自然之子,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不处于平等地位。环境是人类的载体,是人类的生存基础、活动舞台,是消亡后的归宿;环境是容器,将包括人类在内的很多物品囊括其中,人类作为“裸虫”,本身也是宇宙的构成元素,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或者消极作用本身也是自然环境运动环节的组成部分。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立体场域,人类是自然环境中的具体因子;如果把自然环境当作一个系统,那么,人类就是生态子系统中的某个元素。基于这种认识,就不可能推论人类与自然环境具有对等性。没有对等性的关系就不再是商榷关系或者契约关系,而只能是管理关系或治理关系。由于自然的演变而出现了人类,也会由于自然演变而使人类蒙受苦难甚至消失,而这一切都是作为实体的宇宙或自然所固有的规律性变化。人类并不能决定宇宙的命运,恰恰相反,人类的命运是为宇宙所决定的。所以,在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关系上,就出现了人类早期的思维方式,即敬畏自然。
敬畏自然的思维方式并不仅仅体现于东方哲学,在世界各地的初民时期都有对自然或者某种自然力量的敬畏崇拜。因为人类无法把握全部的自然规律,不理解所有的自然现象,对于某些自然灾害更是无力躲避或抗争,所以在早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总是处于弱势地位,从保障生存的基本条件的获取到决定生死存亡的疾病,都受制于自然环境的自发规律。为了摆脱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关系困境,人类想方设法增加自身的力量,主要的方式有三种:一是依靠信仰的力量,把自身所在群落赋予图腾含义,增加心理自信;二是依靠技术力量,观察和利用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三是依靠团结的力量,结成更大规模的群体,用来抵抗自然灾害和保障人类的绵延生存。这三种办法一直贯穿于人类发展的过程之中,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具体的现象表征。信仰演变为宗教,团结演变为国度,技术演变为科学,这就是其在现代社会的具体表征。
三者之中,真正的宗教是导人向善,在环境保护方面,则能使人保持对自然的尊敬,通过修正自身的不良习惯而顺应环境,同时在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为人类提供精神寄托。国度源于团结,国度可以形成整体意识并推进整体意识的落实,属于行动力量,所以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国度所形成的关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的整体意识不足或者说所形成的建设性的整体意志不足,均会对其所在环境产生巨大影响。从科学方面来看,科学的进步在很多领域解放了人类,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但是机器的滥用会导致资源枯竭,放射物的泄漏会迫使居民远离家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信仰的目标,具体国度则承担着发展的权利和义务,机器设备被科学家研制出来开始全方位地渗透、使用,造福于人类的生活,同时也将人类牢牢地控制在技术统治之下,人变成单向度的部件或信息网络上的节点。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人类的天性,也是历史变化的必然规律。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必须有“软约束”,必须坚持正确的边界规则和准备必要的环保措施,“先污染后治理”的办法适用于工业革命初期,因为那些先发国家可以转嫁环境危机,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不可能向外转嫁环境负荷,所以就必须坚持“边生产边治理”的环保举措,防患于未然。世界上还有很多欠发达国家或者说原生态国家,他们还对发展现代工业抱有美好的憧憬,如果他们对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预防措施不到位,将来必然会自吞环境污染的苦果。
当下的问题是,人类在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处理上逐渐占据了上风,但是对自己利用技术力量改造自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或者放任自流,于是就形成了资源枯竭、气候变暖、土地沙化、饮水污染、雾霾笼罩等严峻的现实危机。为了避免这些危机,人类开始反省自身对于环境的所作所为,希望在人类发展与环境正常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有了生态意识,距离人类与环境关系改善和良性互动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就能在自然环境中追求人类健康美好的生存目标,又能不破坏甚至促进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就此而言,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模式具有类似的意蕴图景,但自然经济中人的主体性地位不高,生活质量还需要提升。如果使用中国古代的和合思想,再加上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同时以环境伦理为行为边界,我们相信很多国家或地区的污染问题都能逐步化解,而这也应当是环境保护的根本大道。
环境与人类的关系分为三种情形:一是环境占据主动地位,二是人类占据主动地位,三是环境和人类处于势均力敌的地位。在环境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环境保护与否意义不大,因为人类在这种境遇中没有任何自主性,只能采取顺应自然的方式来生存;在人类占据主动地位的情况下,也是人类最容易骄傲和犯错的时候,如果不对人类自身的行为进行调控,必然会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反过来殃及人类自身;环境通过自身的规律昭示出人类在环境行为上的错误和应承担的后果,同时人类开始反省自身,主动改善与环境的关系,这个时候,环境与人类的生态关系就确定了。这实际上是从自然状态到自为状态再到自觉状态的逻辑演变和历史递嬗。自然状态需要保护自然环境,但那是顺应型保护;自为状态需要保护环境,那属于改造型保护;而在自觉阶段,环境保护则属于协调型保护或者说和合型保护。顺应型保护、改造型保护、协调型保护既是历时性存在,又是共时性存在。虽然环境保护不能改变人类的最终命运,但是它可以使人类在其存续期间过一种健康美好的生活。
二、环境保护的伦理支点在哪儿
伦理作为关于人应当如何行为的基本理论,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伦理重要的关注对象。但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方面,总不能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或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1]31去行动,因为目前与人类能够发生关联的环境区域及存在于该环境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并不真正地拥有拟人化的主体资格。如果非要将它们也当成类似于人一样的生命体去认识,那就是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在闪现。但是,如果没有一种适宜的环境保护的伦理理论或者说伦理意见,那么就无法设计环保领域的合理的诸种制度、规则和做法,从而失去环境保护的价值皈依。现在流行的环境伦理理论,为环境保护伦理原则或伦理支点的探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人类中心论被认为是导致环境与人类关系紧张的原因。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类是自然万物的中心,人类之外的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只是作为人类活动的客体而存在,人类对于自然界总是尽力控制利用。这种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具有两面性,从发挥人类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视野考虑,它也许是人类在为自己的前进呐喊助威,同时刺激自身改造自然的勇气;从消极方面考虑,就是当人类将这种认识推向极致,以为自己可以任意掠夺自然界,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就会陷于紊乱。其实,无论是“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弱人类中心主义”,它们还是存在自身合理性的。因为人类作为存在于地球表面的一个物种,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自身及其种族的生存延续,然后才是逐步发展。人类在拥有利他性的同时也具备着利己性基因,而且,人类的利己性是先于利他性而存在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利他性与利己性是在习性层面谈的,而问题恰恰在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场合都是以习性面貌示人的。“客观的利己主义”伦理理论对这一点有深刻的把握,功利主义伦理学把“趋利避害”当成人的现实属性,而亚当·斯密(Adam Smith)则说人是“利他与利己的统一”。德性伦理学很多时候是一种开示引导,并不直接点出习性中的毛病,而只是从善的门径直接接引,所以孟子会说人有“四端”,而又认为人性本善。实际上,人类的自利性非常突出,在这一点上,人类与别的动物并无本质区别,向生恶死,趋利避害,追求幸福。这一习性来源于天然,自然应当服膺天然,关键的问题是,人类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不能无限地损害环境或其他相关物种的利益。地球上任何一种物种的生存都是以其他物种为能量或原料补给单位,这属于自然法则,但既然是自然法则,那就同时有一个基本限制,即对自然资源和其他物种的索取需要遵循适度原则,否则这种索取就是违背自然法。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均为许可,但是基于奢侈型消费对环境索取则不恰当。任何理论都是人类提出的理论,任何表述的变化或国家符号的出台最终还是为了解决人类自身的意识问题,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过火的价值观,但我们也并不能否认其为人类生存和发展谋求福祉的合理成分。
自然生命论被认为是改善自然与人类环境的重要伦理学说。动物解放论希望伦理学能把关爱的对象扩展到动物;动物权利论谴责食用动物和利用动物进行商业、娱乐、科学研究等行为,认为这侵犯了动物的权利;生命平等论认为植物、动物和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只有人帮助处于危机的生命,才可能是伦理的,人应对一切生命负有责任;敬重自然论希望把人看成是地球生命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与其他生命同根同源、共荣共辱;同时强调人应该对其他生命采取不干涉态度。[2]6这些学说实际上是掀开了那些遮蔽对动物或其他物种的爱心的面纱。在人类的早期或人的童年时期,与大自然及某些动物是有着直接接触和深层的情感沟通的,成长过程中的这种对环境和其他物种的天然喜爱的情愫并不会随着岁月的变化而消逝,只不过逐渐为其他繁杂的事物和情感所掩盖。自然生命关爱主义学说替大多数人说出了他们所忽视的话题和心声。动物解放以动物束缚为前提,但是能为人类所束缚的动物实在不是太多,倒是被驱逐至于困顿的动物居多,动物解放所想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不要对其他动物任意驱逐或猎捕,大象的偷猎者应当从中受到教益。动物本身就是一种物种,分有其天赋而生存延续,有的能在天空翱翔,有的则在深水嬉戏,更有许多在陆地上自由奔跑,他们没有人类语言中所说的权利。他们如果拥有权利,那也是来源于天赋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论实际上是用人类的权利概念去唤醒人们心目中的 “同情”,从而尽可能地不去伤害或虐待动物,至于说动植物和人的生命一样都是神圣的、平等的生命从而都需要伦理关怀,则是从更深层次启发人类对其他物种的爱心。这些学说的合理性在于用人类的语言唤醒人类对动植物或其他生命形式的良知,它们的局限性在于忽略了自然法则对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共同约束。实际上,在环环相扣的食物链中,高级物种离开低级物种的食物支持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人类对于自己驯养的动植物,因为有自身的汗水和所提供的生长原料在内,所以可以食用,但是对于纯天然的,对于没有给过一把米、没有浇过一碗水的动物、植物而言,如果去对它们主张自己的要求就不符合“物种相与之道”了,这应该就是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自然法则,因为人能劳动。而其他物种之间,只有依照自然规律自发地去运行了,虽然在这些动物身上也分有了道德,也具有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道体,但也只能说应当服从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自然生命论可以成为环境伦理启蒙,如果要把他们当成环境伦理原则,似乎还需要具体化和现实化。
深层生态论被认为是环境与人类和谐相处的哲学思想。土地伦理把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视为最高的善,指出农业生产使用杀虫剂会导致人体健康受损,导致“寂静的春天”。深层生态学理论主张生物圈平等原则,反对物种歧视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把生物平等原则建立在所有存在物都拥有生存、免遭过度的人类干扰的自由及追求其幸福的与生俱来的、内在的、天赋的权利基础之上,把权利主体的范围不仅扩展到所有生物,甚至扩展到河流、大地和生态系统。生态论把世界,包括人、自然、社会都看作有机的生命体,它们相互关联、共生互动和自我生长。生态论比较全面地看待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与中国古代对宇宙结构的理解有点类似。五行相生相克、相比相合构成这个世界的基本结构和根本运动。“组成这个世界的所有存在物,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3]21,生态论在环境学中具有基石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深层生态论理解起来相对简单,但实行起来未必容易。理论学说从意识世界走向意志世界,需要制定简单易行的原则,需要具体方法,更需要制度的保障。生态理论找准了人类思维的关键,但是还需要把它转化为最基本、最简单的原则,以便于治理环境,恢复蓝天白云。学界所提出的“环境正义”是纯粹的法律思维,正义是用于社会共同体的,并不能直接套用在环境上;“可持续发展原则”[4]456主要是一种认识维度和经济原则,环境的保护还只是一种笼统倡导和模糊思维。“环境危机属于实践哲学的问题”[5]60,我们的愿望是,从方便实践的角度,找寻一个环境伦理的简单原则。我们认为,这个简单实用的原则就是“环境安全”。
环境安全指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及自然处于良好的状态。环境安全的实践观念是顺应自然规律开发和使用环境,使环境保持自身的新陈代谢能力。人类是生态体系中的动物性元素之一,作为生命样态,既然不能超越自然界,那就必须在自然系统内生存和发展。自然与人类的关系类型具有自然图式、人为图式、生态图式三种,其中生态图式最值得推崇,因为它是天然与人为有机统一的图式,能够实现合法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人类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和科技能力,遵循所能意识到的自然规律,主动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既实现了人类利益,又维持了环境发展。环境安全中所说的环境是一个“梯度概念”,即存在着多重的环境保护区间。自然环境、区域环境、个体环境依次构成环境范畴的不同层次。自然环境是基于人类认知而达到的能够参与自然运转的能力所决定的人类的活动空间,区域环境是指既定的人类某一群落所占有的自然空间,个体环境意指个体在成长发展过程中所需要占用的空间范围。自然环境关涉全人类,其中所涉及的要素有空间范围、时间跨度和这一时空界域内所有生命形式与物种类别;区域环境是以群体、部落、民族或国家为单位,实际占有或控制的自然空间;个体环境是因个体生命活动的不同活动规律所提出的具体空间要求。“环境安全”可以作为环境保护的伦理支点或伦理原则。
三、环境保护的道德要求是什么
德性伦理学给人们列举了许多具体德目,古希腊的“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中国古代的“孝、悌、忠、信”都属于德目谱系。那么究竟最能够与环境安全的伦理原则保持一致的德目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就是“适度”。所有德目都源于作为本性的美德,但是并非所有行为主体都能以“中”为用,能够以正确的“直觉意识”去行为,所以首先需要理智的层面设置人人都能理解并能在现实操作的道德规范,即鼓励行为主体首先在“分析意识”的指引下行为。环境保护的效果直接取决于行为主体的道德意识、道德水平和道德行为,若只有伦理没有道德,环境保护只能是一句空话。“适度”意指恰到好处,即在与环境打交道时应当掌握合理的度,发现在行为主体与环境发生作用时的关节点,由适当的行为主体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对适当的环境对象以适当的方式进行适当的作用,并取得适当的行为结果,从而保持行为主体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双赢。实现这个“适当”美德的关键,就是要依据环境安全的伦理原则。
在行动之前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这样行动会对环境造成怎样严重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否能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得到恢复?在环境恢复过程中人类或者说具体行为主体有没有帮助环境修复的现实能力?如果有现实修复能力,那么行为主体在考虑成本因素后是否愿意进行这种修复?即使是进行这种修复,是不是环境就能恢复到原来状态或者是取得更大发展?行为主体所认为的环境的恢复状态或发展状态究竟在多大时空范围内具有真理性?行为主体的行为所产生的负外部性是否会超越既定的具体环境而扩散到其他更为广阔的地区或者潜藏下来等待爆发的时机和条件?促使行为主体动用环境的动机无疑是人类利益需要,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利益需要?是生存性利益、发展性利益,还是繁荣性利益?这些利益的代理主体后面的终极主体究竟是谁?仅仅是个体、家庭,还是某个企业、单位,或者集团、民族、国家,还是人类的全部?是否存在着全局利益名目掩盖下的局部利益甚至个体利益追求?如果是局部利益甚至个体利益追求,在这些行为主体内心深处是否深藏着只是保护好自身所在环境,而对其他环境漠不关心或放任自流的情况?是否想冲破种种限制而转嫁环境危机,在转嫁环境危机之后是否心中窃喜?等发现环境危机的回流又影响到自身的生存发展时,是否会对当初转嫁危机的行为感到懊悔?在懊悔烦恼之余,是继续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顽劣行为,还是能够反省自己,并与其他行为主体达成协议,寻找避免环境污染或修复环境问题的办法?即使是该行为主体具有为环境保护而合作的诚意,那么其他行为主体是否能具有同样的态度?这种保护环境的诚意是否为制度、法律或风俗所承认、鼓励或赞赏?如果制度、法律或风俗没有对保护环境的良好行为进行肯定、奖励和赞美,那么行为主体是否会丧失坚守环境安全伦理原则的勇气?如果坚持下来,所得到的是眼前利益,所损失的是环境利益,如果仅仅是部分行为主体坚持,而其他行为主体不坚持,根据环境整体性理论,坚持环境保护的那部分行为主体就能真正拥有清洁的环境吗?或者说他们的环境权能够得到最终保障吗?如果那些坚持环境保护的行为主体最后也放弃了自己的环保热情和环保理想,将自身降低到与那些不愿进行环境保护的行为主体同样的水平,环境保护水平岂不大大降低,或者说会倒行逆施?如果所有行为主体都遵循这样的思路,那么要追问的就是,为什么所有这些行为主体明明知道这样做会危及环境,但是为什么还这样做,造成这种追求利益意识的社会环境氛围是什么?是不是在生存、发展、繁荣的利益追求之外,还有其他不合理的想法?是否在攀比的心理之下追求畸形的发展和进步?国家与国家攀比、群体与群体攀比、家庭与家庭攀比、个体与个体攀比,这种风气促进了人的上进心,但同时也应该有个攀比的游戏规则,它们应当存在于世界各国和各个角落,那么,这个游戏规则或者行为规则是什么呢?再需要思考的就是,是谁在影响或者建构人类整体的行为秩序或生活秩序?具体说就是谁设计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样态?我们的原始样态、我们的工业样态、我们的生态追求,究竟哪一种才是对人类发展最具终极意义的模式?生存于地球上的人类是否存在霸权控制?这种人类霸权是否能够自觉地坚持全局性的环保理念而不是仅仅关心于局部?战争残留、核试验不构成环境污染吗?这些行为的根源是否在于人的习性?以习性建构的世界必然会出现很多的困境和苦难,与其以苦为乐地生活,为什么就不能进行人类自身的反省,将内心深处的雾霾涤荡干净,依照真正的生态理念、天人合一思想,依照道德本性或者道德本体去生存、去完善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悲苦,如果有悲苦的元素,这种悲苦产生的原因就目前看来已经主要不是自然灾害而主要在于人类自身了,习性中的偏执与张扬、现实生活的多元与混乱,和谐中的混乱、混乱中的和谐,如果能在地球这个人类家园中提升我们的生存质量和生存期限,让作为自然之子的人能够享受自然的恩赐,能够使人类过一种明智的德性生活,那就是人类之于自身的最大贡献和巨大福祉。因为,唯有德,才是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
环境伦理与环境道德在现实世界相互促进、“德得相通”[6]45,这是环境伦理的主要任务。环境问题主要是人类问题,人类问题主要在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问题主要在意识思维,意识思维主要在于心理活动,心理活动主要在于习性使然,习性使然则主要在于人仅仅还是人。但是,人所同时具有的本性元素给我们指出了另外一种出路和生活方向,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应当多让本性参与。本性是平台,是依据,是共同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原始根据。只有从本性出发才能实现环境领域的真诚沟通和有效的现实合作;只有从本性出发,才能使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走向更高程度;只有从本性出发,才能自觉把握处理环境关系时“度”的位置和分寸,使和谐状态趋于完美;只有从本性出发,才能使行为主体最终达到理性或中庸境界,具有真正的道德智慧。
环境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存在,只是呈现出不同的样貌;环境保护看似是一个整体性行为问题,实际上它与每个人每天的行为息息相关;环境问题貌似主要是工业化历史阶段的产物,但是在原始社会也有毁林现象,在未来社会也照样会出现自然灾害或者流行疾病;环境问题须依赖现代化的技术来防治,但是环境问题更与人类内心的思想内容相关。归根到底,环境污染和废弃物乱置等环境问题的解决,生态保护或生态文明的建设,最终还是需要“心灵的正确引导”。使生态理论成为心理基础、安全原则成为环境保护的伦理原则、适度美德成为行为主体的自我规范,在此基础上进行沟通,达成共识,制定具体方案,筹措资金和设备,及时治理已经存在的环境问题,预防尚未出现的环境问题,敬畏自然、研究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如此,就能使人类无愧于自赋的“万物之灵”美称,就能经由“心灵的蓝天”造就“环境的蓝天”,就能使人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自由惬意地生存、繁衍和发展,过一种健康、富足而美好的生活。参考文献:
[1][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周青.西方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流派价值理念解读——以我国环境法价值理念提升视角[J].环境教育,2010,(4):5-8.
[3][美]R·F·纳什.大自然的权利[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4]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5]杨通进.探寻重新理解自然的哲学框架——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研究概况[J].世界哲学,2010,(4):5-19.
[6]樊浩.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张 转)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解释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