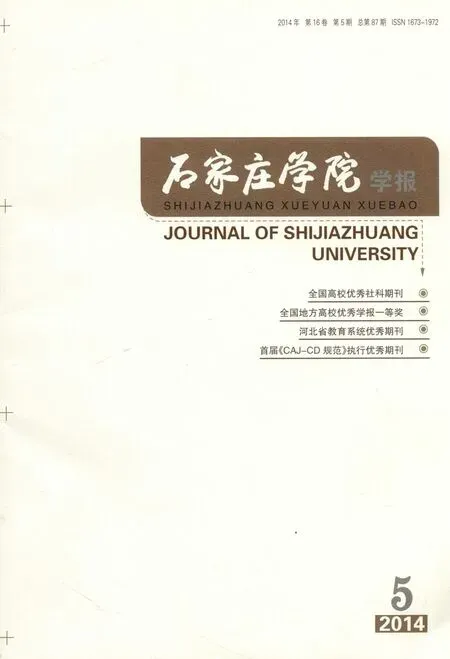论休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的诠释
彭子细,刘光斌
(1.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基础课部,湖南 长沙 410000;
2.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为当今社会的环境问题提供一个评价框架?针对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英国学者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作了诠释和辩护。从一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出发,休斯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为当代环境问题提供一个价值评价框架。依据生态依赖原则和生态影响原则,休斯指出,人类对自然的依赖的认知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生态问题的观点符合马克思生态价值观的评价框架。
一、马克思主义的“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
休斯认为讨论生态问题是与我们视为生态问题所依据的价值观或伦理观有关。也就是说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或伦理观将影响我们对什么是生态问题的评价,为我们提供评价框架。目前环境伦理学的大部分争论涉及两种被广泛接受的评价框架:“一方面,‘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因其自身才具有道德价值,我们应该保护环境只是因为这是人类的栖息地;另一方面,拥有‘生物中心’‘生态中心’甚至‘宇宙中心’等多种不同名称的立场,把道德价值归因于部分或全部非人类的自然。”[1]20即生态问题的分析主要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大立场,这两种立场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或争论,并影响我们的评价视角,而评价视角的选择将影响到我们应把哪些问题视为环境问题以及将采取何种解决该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可以为当代生态问题提供一个评价框架?休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坚持一种 “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评价框架,批判了上述两种评价框架。
首先,休斯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不赞成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但不意味着不关注生态问题。他指出:“为了评估马克思主义是否能迎接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解决主张以非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伦理问题。”[1]24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将道德价值延伸到人类之外的观点,将道德关怀扩展至感知生物(比如人之外的动物)和非感知动物。在休斯看来,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看,同样可以把道德关怀延伸至感知动物和非感知动物,“我将由此假设,在道德关怀的对象方面,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说可以延伸至不只限于人类的感知生物,并将焦点集中在道德关怀是否应该延伸至自然中的非感知生物部分这样的问题上”[1]25。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人类中心主义的这种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承认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人类受非人类的自然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影响非人类的自然。如何看待这种关系中的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及其相互作用,是我们理解生态问题的依据,“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以及人造环境之间实际关系的理论阐释之上”[1]15。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来分析,生态系统应得到保护或者我们应该重视环境问题,不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利益,而且是为了它们自身的缘故。虽然大部分环境伦理学家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危机负有责任,因此转向非人类中心的伦理准则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但休斯认为非人类中心主义不能很好地解释生态问题。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来分析生态问题,我们可能作出相互矛盾的评价:一方面,非人类的自然可以造福于人类,因此保护环境符合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人类又影响非人类的自然,自然因为自身的缘故需要我们保护包括动物在内的感知生物和那些非感知的生物符合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如果马克思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者,那么他将只考虑人类的利益而不会尊重自然的权利;如果马克思是一个非人类中心主义者,那显然与他自己所持的观点相悖。因此,休斯认为马克思不是一个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因为他考虑到自然对于人类利益的重要性;他也不是一个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因为他尊重了自然的价值。
其次,休斯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者,他区别于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自然尤其是非感知生物的价值是为了造福于人类,但需尊重自然的价值。休斯主要借助莱内尔·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的理论为马克思辩护。按照格伦德曼的观点,生态正常性的标准解释只有和人类利益相联系才会有意义。我们确定自然生态系统的繁荣,必须依据该系统服务的人类利益。非人类中心伦理学遭到广泛批评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道德结论:“为了非感知实体的利益而牺牲人类的重大利益。”[1]29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只要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就可以控制自然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评估马克思生态价值观的重要论据,也是休斯区分广义人类中心主义与狭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依据。休斯认为格伦德曼捍卫了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人类统治自然的观念。对自然的统治是我们解决生态问题的合理路径,“人在自然中生存和人控制自然是可以协调一致的;人生活在自然中又控制着自然”[2]23。格伦德曼力图说明生态问题不是人类统治自然的结果,而是对自然缺乏控制的证据。休斯指出为了人类利益控制自然并不是不尊重非人类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内在价值”一词包括了非工具性意义,“正是非工具性价值这一属性,决定了一个伦理是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一种环境伦理,就是主张非人类存在物首先具有内在价值:就是主张非人类存在物不是单纯地作为人类目的的手段的价值。’”[1]36休斯这个观点可以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辩护,因为“尽管我们保护非人类实体的原因是基于它们对我们福祉的贡献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价值是纯粹工具性的”[1]36。休斯认为我们要非工具性地对待自然,关注生态问题以及生态系统的繁荣是使我们过上富足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非人类中心主义看到人类中心主义狭隘的工具主义的一方面,没有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还存在着非工具性的一面,一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就是将非感知自然的价值建立在对人类生命价值所作贡献基础之上的,但它不同于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即不单单从工具性方面看待这种贡献”[1]44。按照休斯的观点,“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大区别就在于是否工具性地看待非感知自然的价值,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区别在于自然是否造福于人类。就是说,“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反对工具性地统治自然,我们控制自然促进人类利益,并不是要对自然采取耗尽其对我们所具有的价值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坚持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
休斯认为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之间存在双向的互动关系。人类受非人类的自然影响,人类又影响非人类的自然,自然限制了我们的社会行为,同时必须承认社会行为对自然产生破坏的非道德事实,生态问题只有在这个框架下才能得到理解。休斯还概括出两个生态原则:(1)生态依赖原则。“生态依赖的原则说明,人类为了生存而依赖自然,因此无论他们想要做什么都离不开自然,而且他们所面对的自然的特征会对他们的生活进程造成重要的因果影响。”[1]126(2)生态影响原则。“生态影响的原则说明,人类行为会对自然造成重要的影响(无论是否有计划)。”[1]126这两个原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就因果影响而言,每一方都影响另一方,但人类对自然的生存依赖是一件单方面的事情,因此生态依赖原则可以再细分为因果依赖原则和生存依赖原则。根据休斯对两个生态原则的理解,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的诠释,集中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与两个生态原则的一致性方面。
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
休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定调就是在自然中定位社会,人类依赖自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论点。他指出马克思由于重视经济或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被看作是经济或技术决定论者,由于忽视自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受到谴责。针对这种指责,休斯辩护道:“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念中的人类依赖于自然的观点的核心论点,使马克思主义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生态问题的适当框架。”[1]128马克思虽然把他的历史的理论解释为唯物主义的,但“马克思似乎更钟爱一个较弱意义上的‘唯物主义’”[1]128,“甚至当人类生存的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它对自然现象对人类产生的因果影响也只字不提”[1]129。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依赖原则无关,休斯通过对“唯物主义”的解释性断言评述和马克思的文本性证据的考证,发现了马克思对生态依赖原则的贡献:在自然中定位社会。
休斯主要评述了三位思想家①休斯借用廷帕内罗、本顿和狄更斯著作和论文中的一些观点,作为论据用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包含了生态依赖原则。TIMPANARO S.On Materialism[M].london:New Left Books,1975;BENTON T.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J].New left review 1985;DICKENS P.Society and Nature:Towards a Green Social Theory[M].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1992.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的解释:其一,塞巴斯蒂亚诺·廷帕内罗(Sebastiano Timpanaro)认为唯物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自然优于思维的认可,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是对物理层面优先于生物层面、生物层面优先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的认可;在时间优先的意义上 (这个很久远的时间发生在生命在地球上出现之前与生命起源和人类的起源之间)和自然仍然对人类施加作用并将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施加这种作用的意义上是这样的。”[1]129廷帕内罗指出了自然对社会的优先性,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持续影响,认为马克思认可生态依赖原则。休斯指出廷帕内罗为我们指出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 “生态学”的解释方向。 其二,泰德·本顿(Ted Benton)主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天然地被认为可作为一个理解人类自然和历史的生态学方法建议。”[1]131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重要命题,即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的人类社会生活独立于自然—给予的物质条件’”[1]131以及 “理解人类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形成中地理变异和历史变迁的关键,通过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不同方式而被发现了”[1]131-132,这两个论题符合人类对自然的生存性依赖和自然作用于人类的因果影响的观点。其三,彼得·狄更斯(Peter Dickens)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一发展了一门目前所需的对环境问题进行适当理解的科学的作者。”[1]133狄更斯提到社会现象对自然现象的依赖,但需要克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脑力劳动的分别,因为这种分离一定程度上造成生态学与影响生态学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关联关注不够,或社会科学也没有足够关注自然环境。狄更斯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和自然相互制约关系的评论:“在改变自然的进程中,人类也改变了自己。”[1]133这说明了人类依赖自然以及社会制度和社会进程调节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根据上述评述,休斯指出廷帕内罗、本顿和狄更斯不仅意识到人类对自然的依赖,而且把这种依赖关系看成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三位思想家都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看作马克思著作的一个中心原则”[1]134,对自然的依赖符合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解释,成为他的研究的一个“指导线索”[1]134。
除了一些思想家支持生态依赖原则之外,休斯还进一步挖掘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文本性证据。其一,《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被看作是马克思最具有生态意义的著作。其中广泛引用的一句话:“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56-57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对生存依赖原则的认同。其二,休斯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许提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理论中对人类依赖于自然的观点的最为清晰的描述,涉及几个重要论题:(1)人类是自然的一个部分;(2)承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对于合理理解历史进程是至关重要的;(3)生产是历史的一个基本的和不断发展的条件。这些论题无不是生态依赖原则的表现。其三,在《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把共同的生产过程的一般物质特征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物质形式作了区别,依然坚持生存依赖原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过程 “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4]215,这暗示着马克思支持人类的生存依赖于非人类的自然。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5]25马克思在此再次肯定了人类劳动过程对自然的永恒依赖。从《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肯定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从自然中定位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人类生存的物质先决条件的知识对理解社会是必要的事实,再次显示出对自然施加于人类社会的因果影响的认可,即使在人类生存的条件一旦得到满足的情况下 (因果影响的原则)。 ”[1]140
一些马克思的批评者指出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存在一个生态学上的断裂:“环境评论家经常感觉到,无论马克思关于人和外部自然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观点,他都会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以这些观点为中心,而在晚期的著作中放弃或忘记了这些观点。”[1]140他们认为后期著作中反生态的特征基于生产力发展的观点,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长会导致生态问题。休斯认为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不存在一个生态学上的对立,在自然中定位社会的生态依赖原则,并不与生产力发展相关的生态影响原则相矛盾,或者说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并没有说明生态影响原则因此就不需要依赖自然了,必然会对环境产生破坏。人类改造自然的不同方式中,只有一些可能与生态问题相关,因此不能抽象地谈论自然的改造,需要对自然改造的特定论述进行考察,休斯认为这需要考察生产力的发展的观点。
三、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生态维度
马克思主义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影响原则的论述集中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方面,不同于一些马克思的批评者,休斯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影响自然但不一定导致生态问题。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生态维度。
一方面,对马克思的批评者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技术发展导致生态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马克思的批评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技术决定论,马克思把生产力的发展等同于技术的发展,从而导致生态问题。在休斯看来,技术只是生产力的一部分,技术发展和生态问题之间有联系,但认为技术发展必定产生生态问题的结论是不充分的。因为技术只是生产力的一部分,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技术的发展。正如休斯所说:“没有生产力的一个总体扩张,生产技术的发展也是可能的;或者当生产力的非技术元素例如原料的贮备有所下降时,尽管技术发展保持不动甚至还有所发展,但是生产力的下降也是可能的。”[1]182他还指出并不是所有形式的技术都伴随着生态问题,因为生态问题的产生与技术发展形式和服务的目标有关。休斯概括出三种技术发展形式:(1)生态破坏的可能范围随着技术空间的增长而得以大大扩张。休斯认为这只是看到了一个方面,实际上技术空间的增长也可能提供更多有效的控制来减少潜在的生态破坏及其发生的可能性。“造成环境破坏及治疗环境问题的原因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6]158-159(2)现代技术的复杂性和紧密结合减低了他们运作的透明性并允许其产生较大影响的小失败,环境破坏变得更加可能。休斯指出即使 “生态问题不可避免地产生于复杂的和紧密结合的技术,也不意味着这样的后果必然是由技术的发展引起的”[1]185。人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控制技术发展的方向,并引入那些对环境破坏可能更少的技术。(3)生产自动化会带来资源的大量消耗。休斯指出自动化技术并不包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通过技术的创新方式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来提高产品的数量。技术的发展产生环境问题就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减少劳动力的限制来提高产品的数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带来资源消耗数量的增加和废气产品的增加。在休斯看来,实际上技术的发展不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即使环保主义者要求停止生产增长的建议被法案通过,并被要求进一步减少劳动时间,那么引进技术创新设计以增加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废气产品的处理,从而减少当前生产活动水平的生态影响也是合理的。这样的创新似乎比在旨在使劳动生产率最大化的创新更值得拥有‘技术发展’的称号。”[1]188不是所有的技术发展形式都带来生态问题,对生态问题的评估必须依据技术发展服务的目标。因为技术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增进人们满足他们需求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追求的目标不一样,就有可能产生潜在的或实际的生态问题。
另一方面,休斯考察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作用以及对生态问题研究的意义。休斯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解释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作用是为社会的革命性转变创造条件。我把这一点称之为生产发展的革命性效应”[1]195。必须区分革命性效应的两个元素:一是破坏效应,一是促进效应。破坏效应指的是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可以破坏一个旧的社会形式存在的思想,即生产力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并破坏生产关系,表现为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当出现一个更好的生产关系来取代桎梏的生产关系时,生产力发展的破坏效应才具有革命性,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新的生产关系切实可行,便发挥了生产力的促进效应。根据休斯对促进效应的解释,不难看出,破坏效应和促进效应是部分重叠的。“如果我们依据相对桎梏阐述破坏效应,那么破坏效应和促进效应意味着同一个情况,即新的生产关系对旧的生产关系的优越性。”[1]209
休斯认为生产力发展的破坏效应和促进效应都不能说明马克思支持对环境的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表明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具有重要生态意义。从生产力发展的破坏效应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被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或生产力应用的桎梏破坏时,有理由去推翻桎梏的生产关系,但不一定支持生态破坏性的发展形式。“由于马克思归之于人们的利益驱动是人们自己的福利利益,由于人们自己的规范立场是由其对更普遍的人类福利的关心而体现出来的,所以没有理由把这样一个观点归之于他:共产主义将要从事或者应该从事不加选择的或者具有生态破坏性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或使用。”[1]205-206为了达到生产力被资本主义所桎梏的水平,马克思主义坚定地支持发展,使生产力的发展为推翻资本主义创造条件,但并不意味着不顾它的生态和社会影响,也并不认为具有生态破坏性的生产力的发展就意味着产生了桎梏。休斯认为:“对桎梏的充分阐述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去支持具有生态破坏性的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实现桎梏的步骤。”[1]208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只是意味着生产力的水平足以发挥它的破坏效应,而不能发挥它的促进效应,不需要通过生态的破坏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力发展的促进效应看,旨在增加商品产量的技术发展可能具有生态破坏性,但并没有内容表明马克思支持产出的无限增长,他提供了一个一旦产出足以满足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需要就应稳定产出的理由。“这不仅限制发展的生态后果,而且允许存在这样一个可能性,即这些后果被在生产技术中的生态效能的提高抵消。”[1]211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928-929共产主义的可行性取决于提供实现人类需求的合理满足的技术潜力,同时还要避免可能破坏这个目标的生态问题,生产技术的生态效能方面的增加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生态效能方面可能性的增强包括在实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技术先决条件中。
四、评休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诠释的意义
休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为当代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考框架,人类依赖自然环境是马克思主义环保思想的基石,生产力发展对生态产生影响,但不一定带来生态问题。休斯的论证回应了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为马克思主义进行生态辩护的理论资源。
第一,针对马克思主义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人类价值高于人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无视维护生态价值的质疑,休斯认为,从一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看,为了人类利益控制自然,马克思不会赞同牺牲自然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承认自然对于人类利益的意义,主张非工具性地对待自然,尊重非人类自然的内在价值,这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狭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区别开来。
第二,针对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包含了生态思想,而后期作品中放弃了早期生态思想的质疑,休斯认为马克思早期作品中人类依赖自然的观点并不与后期侧重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力的发展的观点相矛盾。休斯挖掘了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以来的一些有关生态依赖的文本证据,认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前后期是连贯的,虽然成熟时期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受到更多重视,生态影响原则表明生产力会对自然产生影响,但不能证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有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目标已经考虑到了生态问题。
第三,针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技术决定论,人类控制自然会产生生态问题的质疑,休斯指出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一种技术决定论,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狭隘的理解。生产力的发展观点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作用分析表明历史唯物主义不但不支持破坏环境的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强调“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这一理想可作为现存社会生态批判和变革动力的基础”[1]7。
休斯看到资本主义对利益的追逐造成的环境危害,这与马克思 “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界是对自然界的真正蔑视和实际贬低”[8]195的论断是一致的。在现代社会,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威胁,人与自然关系变得紧张。休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考察人类对非人类的自然的生存依赖和因果影响,把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结合起来,强调在自然中定位社会,正确看待生产力对自然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生态时代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英]乔纳森·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2]Reiner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1991.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郭剑仁.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张 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