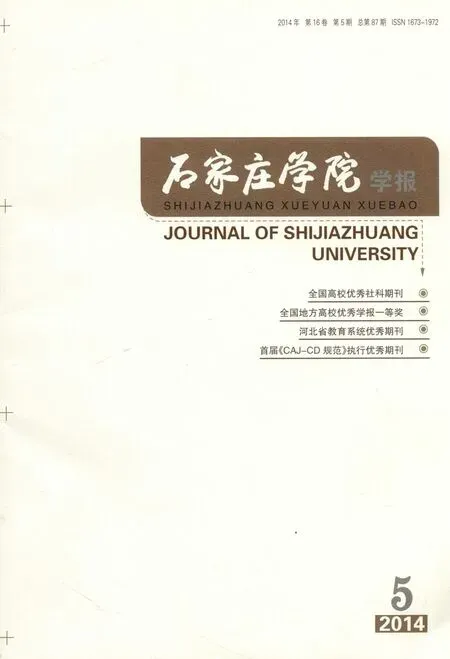论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与道德
邹平林,杜早华
(井冈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空前复杂且快速变动的社会关系,客观上需要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加以有效的引导和协调。道德领域日益凸显的问题与危机,也同样促使人们将制度创新作为走出当前道德困境的重要路径选择。制度创新不是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修修补补,而是系统性的整体革新,其首要前提是对制度的伦理基础进行自觉的反思与建构,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制度与道德的相互促进关系,同时厘清其各自不同的功能边界与作用机制。
一、制度与道德的现代伦理基础
“制度”的一般含义是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或准则。但制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制度是指正式制度,即由国家或政府制定出来的用以约束和调整人们的各种行为并带有强制性的准则或规则。而广义的制度则不仅包含正式制度,同时也还包括那些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并不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因而其对人们的约束不是强制性的,其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们的道德意识。本文所讨论的是指狭义的制度,亦即正式制度。
道德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方面,道德是指人们关于人际关系应当如何的一种内化了的观念,从这个层面上讲,道德就是个体的“良心”。另一方面,道德亦可指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用以协调人际关系的一系列的规范,从这个层面上讲,道德是一种客观化了的伦理规范。道德与制度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作用机制是人们对社会规范的自觉的认同与遵循,因而其对人们的约束是非强制性的;而后者的作用机制则是以权力为后盾的强制性规范。本文在以上两个层面上使用“道德”概念。
制度与道德本质上都是协调社会人际关系的伦理规范。但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中,由于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水平低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在传统形而上学世界观视野中,制度与道德的合法性最终来源于人之外的某种目的论预设。尽管制度与道德事实上发挥着协调社会人际关系的伦理功能,但社会人际关系的协调似乎并不是制度与道德的最终目的,而只是实现某种终极的形而上学目的的有限手段。因此,传统社会中制度与道德的伦理本质并未得到清晰的彰显和自觉的把握。或者说,作为合法性基础对传统制度与道德起到支撑作用的,不是社会人际关系的合理化这样一种伦理诉求,而是形而上学的目的论预设。以形而上学目的论为合法性基础的传统制度与道德是以群体为价值本位的,这是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传统社会必须牺牲个体以求得群体的生存与发展这一客观要求相适应的。
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提升,从而导致了世界观的世俗化或合理化,传统形而上学世界观整体上丧失了其对于现代人的合法性效力。根据世俗化、合理化了的现代科学世界观:世界无非自然的世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与现象,能且只能以自然的方式予以解释,而无须也不能借助于神秘的形而上学目的论预设;作为自然历史进程,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整体并不朝向某种神秘的终极目的,人与世界的意义或价值并不是预先规定了的客观存在,而是人的主观设定。在世俗化或合理化了的现代世界中,制度和道德不再与形而上学目的论预设相关联,而是被还原为人自身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为协调社会人际关系而进行的主观创制,从而其作为社会人际关系规范的伦理本质才得到了清晰的彰显和自觉的把握。
以自然的方式解释世界的现代科学世界观,一方面解除了制度和道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目的论的合法性依赖,另一方面又为其提供了新的世俗化了的伦理价值基础。既然世界没有整体的和终极的目的指向,那么,一个个的个体人本身就成为了价值的主体与本位。既然个体人成为了价值的主体与本位,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个体为自身之外的他人、群体或其他目的而牺牲自己。从终极的意义上讲,现代人是一个个相互平等的原子式个体,他享有根据自己的判断、意愿去行动、去生活的绝对自由权,这种自由权利仅以不损及他人同等的自由权利为限。也就是说,对个体自由权利的平等尊重,是现代精神的核心特质,因而也就构成了一切制度安排和道德诉求最为基本的伦理原则。任何以强制的方式剥夺人的自由权利的做法,都不可能获得现代人的理性认同和道义认同。
当然,保障个体的自由权利并非现代制度和道德唯一的和绝对的伦理价值原则,有效发展社会福利,引导人们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相互关心、相互合作,以及促进人的发展与完善,等等,同样也是制度和道德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但是,对个体自由的尊重与保障却是现代制度和道德的最为基本的一般性原则,它在价值排序中享有首要的优先权。也就是说,其他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对个体权利的平等尊重为前提,当其他价值与自由价值发生冲突时,制度安排和道德诉求必须优先考虑个体平等的自由权利。或者说,一项制度安排如果要牺牲个体的自由和权益,就必须征得利益相关者的同意,并给予相应的补偿。
诚然,优先保障个体的自由权利还只是现代制度与道德的一般性伦理原则,并非现代制度与道德的实然状态。现实社会生活中事实上存在着对个体自由权利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忽视与践踏,而且复杂性和差异性是人类社会不可消除的永恒特征,任何社会制度安排都不可能绝对保障个体的平等自由权利。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个体自由权利作为现代制度与道德首要的伦理价值原则,相反,只能肯定这一伦理价值原则,才能为批判现在不合理的制度提供价值依据,才能为制度和道德更新提供价值引导。
二、制度与道德的现代关系形态
社会生活的现代转型以及世界观的世俗化与合理化,从根本上革新了制度与道德的伦理基础,从而也就改变了制度与道德的关系形态,而制度伦理也正因此而成为了一个紧要的时代课题。
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制度还是道德,都是通过形而上学的目的论预设获得其合法性基础。这种形而上学目的论要求人类服从世俗生活之外的某种终极目的,并要求个体服从通过形而上学目的论获得其合法性的群体利益或整体利益。因此,尽管制度与道德已经有了一定的区分,但就其都具有强制性这一本质特征而言,两者又处于一种混沌未分的泛伦理化状态。这种泛伦理化状态表现为:一方面,以权力为后盾的制度是以伦理道德的形态出场;而另一方面,伦理道德本身又表现为一种以权力为后盾的制度安排。这种混沌未分的泛伦理状态集中体现为儒家的礼制体系。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似乎只是一种道德诉求,但本质上却是一套以道德形态表现出来的正式制度安排。这种“礼”固然诉诸人们的内心认同,但如果人们没有认同这种“礼”从而做出无“礼”行为时,他不仅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且事实上还要受到制度性的强制惩罚。这种泛伦理化状态,诚如樊浩所言,实际上是“道德话语掩盖下的伦理强势”[1]。
而在世俗化或合理化了并以个体为价值本位的现代社会,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个体为了他人、群体或任何其他目的作出牺牲,更没有理由和权利对平等而自由的个体进行强制性的惩罚,除非某一个体损及了他人的利益或同等的自由权利。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可以大致区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类型:一种是为他人或群体而自愿地节制、贡献和牺牲自己的行为,另一种是为了不损及他人利益和平等的自由权利而必须予以禁止或节制的行为。前一类行为以自愿为前提,它主要是道德规范的对象,制度无权加以强制性规范。而后一类行为尽管也可以是道德的规范对象,但不能完全依赖行为主体自愿的道德选择,而主要地必须通过制度加以强制性规范。这样一来,在现代社会中,制度与道德就因其规范对象以及规范方式的不同而清楚地区别开来了:制度主要是对那些可能损及他人权益而必须加以禁止或节制的行为进行强制性规范;而道德则对涉及社会人际关系的一切行为都具有规范作用,但道德规范是一种以自愿为前提的软性约束,而不是以社会权力为后盾的强制性约束。
制度与道德的现代分化,凸显了制度伦理建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同时也意味着伦理学科理论视野和致思路径的根本性转向,即由个体美德向社会伦理、由个体善向制度善的转向。
在传统社会中,制度和道德已经通过形而上学目的论预设而获得了其伦理的合法性基础,因而无须对自身的伦理基础加以反思,只是按照预先给定了的伦理目的和伦理秩序要求个体予以遵守。因此,传统的制度与道德只是单方面地要求个体 “善”,即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预先给定了的伦理目的与伦理秩序。而当个体偏离这预先给定的伦理目的或伦理秩序时,个体就被判定为“恶”,并以强制性的手段予以惩罚和矫正,尽管这种强制性手段表面上往往采取道德诉求的形态。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原则上既不允许制度和道德的制定者和颁布者对制度和道德本身进行反思,也不允许个体进行自由的道德反思和道德选择,伦理秩序的维持是以整体性的强制力量为前提的。就其无需对自身进行伦理反思这一点而言,传统的制度与道德是非伦理的,尽管它是以伦理道德的形态存在。而就其以形而上学的目的论压制人类和个体从而与彰显人类及个体价值的现代伦理背道而驰这一点而言,传统制度与道德是反伦理的。
而在现代社会中,制度与道德的本质功能被还原为世俗人际关系的合理化协调,判断制度安排与道德诉求是否合理的标准在于,它是否能够促进人际关系的合理化,即既促进人类整体或群体的和谐与发展,又促进个体的自由与发展。因此,某一特定的制度安排和道德诉求就不是天然合理的,它本身必须符合促进人际关系合理化这样一种伦理诉求。与此同时,一方面,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被还原为世俗生活本身,而世俗社会生活无非是一个个真实而具体的个体生活的总和,因而个体就成为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本位,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个体牺牲自己的权益以利于他人或群体,除非个体出于自愿。因此,那些为他人或群体而牺牲或贡献自己的行为,就从以往的强制性的伦理要求中解放出来,成为个体的纯粹自愿的道德行为,而不是强制性的制度规范的对象。另一方面,摆脱了传统形而上学束缚的现代自由个体,其追求自身权益的行为可能损及其他个体的平等权益以及人类整体或群体的长远利益,这一类行为不能仅仅依赖个体的道德自觉予以调整,而必须以强制性制度安排加以约束。但用以协调这一类行为的制度安排,本身又包含着基本的伦理要求,即不得以强制的方式损害个体的正当权益。
三、制度与道德的现代作用机制
制度与道德之伦理基础的现代更新,以及制度和道德的现代分化,同时也表现为现代社会伦理作用机制的根本性变化。现代社会的伦理分化为制度与道德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的作用边界和作用机制都各不相同。
制度所要规范的主要是那些由于可能损及他人和群体利益而必须予以禁止的行为,例如:不得杀人、不得偷盗等;或者是关涉到他人和群体利益而要求人们必须去做的行为,如必须抚养孩子成人、赡养父母等。“必须做”或“禁止做”这样一种被强制性,是这类行为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强制是制度规范主要的作用方式。但正因为制度的作用方式主要是强制,所以它就必须是普遍的,即它的规范对象必须是所有人或所有某一类人,而不能特殊地针对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否则它就违背了个体平等这一基本的现代伦理原则。因为如果制度规范对象是特殊的,就意味着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被强制要求为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作出额外的贡献或牺牲。
“所有某一类人”之所以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是因为尽管“某一类人”事实上不是所有人,但在形式上却可以指称所有人,或者说所有人在形式上都有权利和有可能成为这“某一类人”。例如,“所有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都必须为其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这一制度规范,尽管事实上针对的是企业经营管理者这一特殊人群,但实际上仍然可以理解为是普遍地针对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没有被禁止成为企业经营管理者,即是说,所有人都有权和有可能成为企业经营管理者。由此可见,在法律制度的规范性陈述中,实质上所有人都是潜在的规范对象。
当然,形式的普遍性还不足以保证制度的合理性,制度的合理性还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目的本身是否合理,即是否有利于保障和促进个体的自由与发展,以及是否有利于保障和促进群体的和谐与发展。例如,“所有人都必须自杀”或“所有人都不得吃饭”等这样的规范,尽管满足普遍性要求,但却不是合理的,因为它违背了“促进个体或群体的自由与发展”这一具有根本性的伦理目标。而当群体的和谐与发展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个体的自由与发展时,要求个体作出牺牲的制度安排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征得相关者的同意,并予以相应的补偿。这种“同意”当然并不意味着每一当事人都直接地表示同意,只要我们能够合乎理性地假定,这些当事人如果站在非当事人的普遍性立场就必然会同意这么做,那么,就可以视为征得了当事人的“同意”。例如,“严禁严重的传染病患者自由进出公共场所”这一规范,为了他人的健康而牺牲传染病患者的自由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我们可以假定,包括传染病患者在内的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同意这样做。因此“禁止传染病患者进出公共场所”这一法律制度的制定,就无须去征求每一个传染病患者的直接同意。
如果说那些可能损及他人和群体利益而必须予以禁止的行为,以及关涉到他人和群体利益而要求人们必须去做的行为,是强制性的制度规范的对象,那么,那些并不直接损及他人和群体利益的行为,则是道德规范的对象,无论这类行为是否有益于他人和群体,也无论这类行为是否给行为者带来损失。而道德的根基是人们的道德良心,即人们的自由意志基于理性反思而对某些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的认同。从根本来讲,道德行为是自由的而非强制的,道德规范对人们的约束是软性的,而非硬性的。对人们的道德选择加以外部的强制,由于违背了人们的自由意志,因而不符合现代伦理的合法性要求。外部强制或许能够促成一时的道德行为,但这一行为并非出于人们对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的自觉自愿的主观认同,因而并非真正的道德行为。并且,当外在的强制解除时,这种行为就不再发生,因而不是持久的。更为重要的是,外部的强制阻碍了人们对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的理性反思和自由认同,从而从根本上毁坏了人们的作为道德行为之根基的道德良知,最终不利于道德的整体的和长远的良性发展。
如果说制度规范的基本目标是保障人们的平等因而要求普遍性,那么,基于人们的理性反思和主观认同而发生作用的道德规范,则应当必然允许一定程度的特殊性和个别性。因为每个人对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的主观认同不可能绝对相同,而一个人通过对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的认同所形成的道德良心,因其包含着自身的真理性,因而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自我确信。黑格尔认为:“良心于是就这样行动并且这样保持自己于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的统一之中,保持自己于纯粹思维和个体性之中;良心于是就是自身确信的精神,而自身确信的精神本身就包含着它自己的真理性,它的真理性就在它自身之中。”[2]158“良心作为主观认识跟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东西的统一,是一种神物,谁侵犯它就是亵渎。”[3]140前苏联学者季塔连科也曾指出:“良心使人的内心世界服从于它的自我道德法庭。”[4]219可见,良心作为对伦理真理的主观反思,尽管必然具有主观的特殊性,但作为自我确信着的主观真理,却是他人无权过问更无权加以强制的神圣之物。因此,通过良心起作用的道德规范,只能对人们加以引导,而不能进行强制。
既然道德不能被强制,那么道德建设的根本途径,就不是强制推行某一特定的道德价值标准,束缚人们的道德视野并要求人们遵从,而应当在一种开放的道德氛围中允许各种道德资源自由竞争,从而使人们在对不同的道德资源的自觉反思和认同中形成稳固的道德良心。唯其如此,才能期待人们真正的和持久的德性和德行。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能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而是说,对人们的道德教育不能是一种纯粹外在的说教,更不能是一种违背意志自由的外部强制,而应当诉诸人们自身的理性反思和自由认同,进而形成稳固的道德确信。而人们的道德意识或道德确信,从根本上形成于他们对现实社会生活状况的反思性认知。因此,要使人们形成正确的道德意识或道德确信,就必须培育有利于正确道德意识或道德确信形成的现实社会生活土壤。如果现实社会生活本身与我们所宣导的道德背道而驰,那么,无论我们如何进行道德说教,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例如,如果现实社会生活本身是不诚信的,而且诚信总是受损,不诚信总是得益,那么,无论我们如何进行关于诚信的道德说教,诚信都难以真正成为人们的道德确信,从而也就难以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而当前中国的道德教育之所以举步维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现实社会生活实际所遵循的行为原则与我们的道德教育所宣导的道德原则之间存在着太大的落差。而要使现实社会生活土壤有利于形成正确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确信,有赖于具有强制性的制度规范加以有效的型塑与引导。
由此可见,尽管现代伦理生活出现了制度与道德的分化,但这二者又非绝不相关,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一方面,需要有制度规范对社会生活的强力型塑,以营造一种有利于德性生长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氛围,否则社会成员美德的形成和社会整体的道德进步就只是一句空话。另一方面,制度要得到真正有效的贯彻落实,同样也需要社会成员德性水平的提升,因为制度最终是由人来执行和运用的,而 “只有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有可能知道如何运用法律”[5]192。
总之,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制度与道德的伦理基础已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二者的关系形态、作用边界和作用机制也因此而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只有清晰地把握并主动地顺应这种变革,才能在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的互动中创造合乎人性的良好社会生活和伦理秩序。
[1]樊浩.“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J].学习与探索,2011,(1):7-13.
[2][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4][前苏]季塔连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5][美]麦金太尔.追寻美德[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张 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