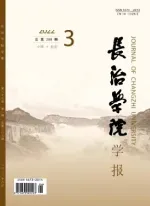元人笔下的汉唐悲歌——《汉宫秋》《梧桐雨》抒情性共同点浅析
温淳秀,郑海涛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元代是杂剧兴盛的时代,诞生了“元曲四大家”。其中马致远之《汉宫秋》和白朴之《梧桐雨》同属历史故事剧,均以曲辞华美,意境深邃,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著称,在元代剧坛璀璨夺目。孟称舜在《酹江集》中评价《梧桐雨》云:“此剧与《孤雁汉宫秋》格套既同,而词华亦足相敌。一悲而豪,一悲而艳;一如秋空唳鹤,一如春月啼鹃。使读者一愤一痛,淫淫乎不知泪之何从,固是填词家巨手也。”[1]可见,将两剧相提并论古已有之。本文专力于两剧最突出的共性——抒情性的分析,从而为两剧的比较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
一、借古人抒胸臆——个体感情的寄托
《汉宫秋》和《梧桐雨》同借历史题材敷衍了一段凄美深婉的帝妃恋情,它们同属于历史故事剧,创作目的均在于借古人之事寄托个体感情,彰显个体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感受。在这样的历史题材剧中,作者有时不很注意对于史料的尊重,相反却常按自己的需要去改变、创造人物,使它们成为一种情绪、一种精神内容的化身。如《汉宫秋》中,马致远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并设置了帝妃关系,目的就是抒发他的亡国之痛和对朝中无能大臣的不满,体现了作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作者首先把自己的民族情绪寄托在对王昭君形象的精心刻画上。她是一位具有勇于承担国家灾难的刚毅品质和坚贞节操的巾帼女杰,在她身上有着深刻的民族思想内涵。毛延寿献图,呼韩邪单于以大兵压境为威胁索要昭君和亲,面对这种羞辱,满朝大臣昏庸无策,却想牺牲娘娘保全国家。昭君深明大义,将国家安危、民族安危置于个人感情之上,为国家大计,为救一国生灵挺身而出,全剧至此已突破了元杂剧中惯用的儿女情长之藩篱,而具有深刻的民族思想内涵。昭君不愿“忍着主衣裳,为人作春色”,行至番汉边界,又毅然投江殉国,如此,自身的不甘受辱和民族气节的坚守使得其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紧密结合,进一步深化民族思想内涵。作者塑造王昭君的光辉形象还另有用意。王昭君不仅容颜娇美,而且品格高洁,堪称可爱,只有这样,汉元帝对她的留恋,对她的感情才有价值,才让人同情,才能超乎儿女之情的层面而渗透入更深刻的民族内涵。在我们看来,导致王昭君悲剧的重要因素是朝廷大臣的自私无能。马致远是由金入元的汉人,经历了金、宋被灭的两次国难,他正是借戏剧抒发了对不能抵御外辱,不能坚持民族气节的朝中大臣的不满。此外,马致远对汉元帝的态度体现了元蒙时代汉人对旧主怜悯与怨愤交加的矛盾心态。汉元帝有昏庸一面,但更有柔弱,善良,对爱情忠贞如一的一面。灞桥送别,不怕耻笑,昭君和番后,百日不设朝,未减半点恩爱。他贵为天子,权倾天下,却不能保护自己心爱的妃子,此时此刻他已经不是帝王,而是不幸人兼受害者,情同庶人,其情感特性与普通人无二。他在【得胜令】中唱到的“枉养着边庭铁衣郎”“今日央急煞娘娘,怎做的男儿当自强”[2]9这种悲痛感情的抒发,蕴含着元代一族人民的亡国之痛。马致远作为一个戏剧家,正是借亡国之君的情感悲剧抛洒其对时代兴衰的感受以及自身命运的感伤。
白朴的《梧桐雨》取材于一段具有极强感染力的历史故事——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风流韵事,剧作家除悲叹兴亡、追思故国之外,更注重表现的是一种较之《汉宫秋》更为深刻更为沉痛的情感体验——人生的幻灭感。这种幻灭感来自于白朴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感伤,在作品中主要从唐明皇不幸的政治、爱情遭遇中体现出来。就作品的创作立意而论,白朴的《梧桐雨》并不像洪昇的《长生殿》那样对李、杨之情加以净化和理想化,倾力讴歌他们之间生死不逾、感人至深的爱情,而是不为尊者讳,对李、杨爱情的阴暗面多有彰显,于第一折便交代了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奠定了全剧着力单方面表现唐明皇欢乐时沉溺于情和孤独时深切思念的基调。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喜爱迷恋之情愈是深厚,其失去杨贵妃后的凄凉悲苦就愈显强烈。昔日长生殿说誓约,沉香亭舞“霓裳”,何其美好,何其欢乐!如今乐极生悲,盛极衰来,爱妃长逝,西宫退居,唐明皇陷入爱情与权力双重失意的无边痛苦和万般无奈中。尤其第四折中,唐明皇一副形影相吊、满怀凄然的情状,倾泻着他对杨贵妃深切的怀念和追忆,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杨贵妃的情之所钟和失去爱妃后的悲痛落寞。“常记得碧梧桐阴下立,红牙箸手中敲。他笑整缕金衣,舞按霓裳乐”[3]361,“到如今翠盘中荒草满,芳树下暗香消。空对井梧阴,不见倾城貌”[4]361,作者将往日的欢悦、繁华与今朝的落寞、凄凉构成强烈对比,又让亘古不变的梧桐作为他们爱情凋零的见证,如此巨大的人生落差,充满沧桑之感,含蓄而深沉地传达出人生落寞、迷惘莫名的情绪。唐明皇早年励精图治,任人唯贤,创造了唐代历史上的“开元盛世”,到了晚年却专宠杨贵妃,荒废朝政,导致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盛世的一去不复返使处于乱世的白朴感同身受,《梧桐雨》中一首首哀婉的悲歌,正寄予着白朴对历史兴亡的感叹和对故国的怀恋追思。而唐明皇自身不幸、悲痛的爱情、政治遭遇更引发白朴的沧桑之感和沦落之悲,整部作品都笼罩在一种迷惘、悲凉的情调中。
二、压抑后的迸发——倾泻式抒情的运用
剧作家对戏剧自身特征的认知程度迥乎有别,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戏剧风格。《汉宫秋》与《梧桐雨》不以情节紧凑集中,展现激烈的戏剧冲突取胜,而以浓郁的抒情性、醇厚的诗味和华美的曲辞著称。作品中的抒情又呈现一种深积厚蓄之后的喷薄迸发、一泻千里之态,属于倾泻式的抒情方式。首先,作者通过对戏剧冲突的集中处理为倾泻式抒情蓄势。《汉宫秋》把戏剧冲突的重点放在汉元帝和王昭君的感情纠葛上,而其他的情节、矛盾则吝于展开,甚至也未让王昭君和她的对手毛延寿当场“撞击”,也未展开汉元帝和奸臣毛延寿的直接较量。而第三折灞桥送别,情节、时间原本非常简单,作者却用了整整一折进行详细叙写,为的就是让汉元帝借助此折抒情,从而把汉元帝压抑着的内心悲痛尽情倾泻出来。在此,作者正是有意腾出时间与戏剧篇幅来为主人公的倾情诉说创造条件。《梧桐雨》同样将戏剧冲突的重点设置在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情爱纠缠上,其余情节、矛盾按一般元杂剧的惯例处理,重在表现唐明皇怀抱美人时的欢乐多情与失去爱妃后的苦痛孤寂,并于第四折掀起情绪的高潮,以强烈的抒情笔调倾泻了失去爱妃后的悲苦心境。其次,戏剧主体曲辞极富有感染力,无论是痛斥群臣时的激愤、豪壮,还是与爱妃分别时的缠绵悱恻,亦或独居深宫思念妃子时的凄婉哀怨,曲词均写得淋漓酣畅,既有感情喷发带来的冲击力,又具细腻传情的流动性。如《汉宫秋》第三折灞桥送别,汉元帝在【七弟兄】中唱到:“说甚么大王、不当、恋王嫱,兀良,怎禁他临去也回头望!那堪这散风雪旌旗影悠扬,动关山鼓角声悲壮。”[5]10短短一首曲辞言深味永,本已无限怨恨群臣让他割恩断爱,现今尚书又薄情寡义、三番五次催促,就在这黯然神伤之际,昭君要上路了,一句“怎禁他临去也回头望”,写出了汉元帝被撕裂的心灵。此时此刻,汉元帝想必已经泪眼模糊。然而作者并未让抒情停顿在一个层面,而是更进一步以虚幻之笔写他想到昭君在塞外旅途的艰辛,他仿佛看到了旌旗的影子在漫天风雪中摇动,仿佛听到了那凄厉而悲壮的号角声在荒漠的天空中回荡。作者这种感情层层推进的写法也体现在《梧桐雨》中。第三折行至马嵬坡,军心哗变,要求赐死贵妃,白朴使用了【落梅风】【殿前欢】【沽美酒】等几支曲子尽情表现了唐明皇不能施救于贵妃的痛苦,对杨贵妃惨遭横祸的怜惜以及赐死杨贵妃后离去时的万般不舍。此外,两剧抒情媒介的巧妙使用迤逗地主人公感情一发而不可收拾,情感的潮水不可遏制、宣泄无余。汉元帝梦到一半便被雁声惊醒,由此引来汉元帝对雁的恼恨、埋怨,其悲情也随着大雁一声声凄厉、悲怆的叫声层层翻滚,感情的潮水倾泻无余。《梧桐雨》以秋叶雨打梧桐作为抒情媒介,唐明皇在寝殿被“一声声洒残叶,一点点滴寒梢”的梧桐雨惊梦,由此引发了唐明皇对梧桐雨的怨愤之情,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巧妙的排比铺陈模拟雨声,摹写雨态,伴随着梧桐雨的绵绵不绝,唐明皇的哀伤幽怨像雨水一样一泻而下。
三、为情造景,以景衬情——景物设置对抒情的促进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曾评价元剧之美:“然元杂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事也。”[6]99《汉宫秋》和《梧桐雨》以浓郁的抒情性打动人心,但是其情如果没有景物、画面作为依托,便缺少感人至深的力量,其美感亦无从展现。马致远、白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利用景物对抒情的促进作用,为情造景,以景衬情,将情感抒发与景物描写完美结合,创造出无比深沉的意境,最终成为元剧之美的典型。如《汉宫秋》第三折【驻马听】“尚兀自渭城衰柳助凄凉,共那灞桥流水添惆怅”[7]8,作者特意将离别的场景设置在黯淡的秋光中,以衰败的柳树,寂寞远逝的流水烘托出主人公内心的凄凉、惆怅,于幽凄的美景中含哀无限。再有最为动人的【梅花酒】“呀!俺向着这迥野悲凉,草已添黄,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8]10,设置汉元帝面对广漠的大地产生悲凉情绪,从而想象昭君塞外旅途与自己返回咸阳宫时的情景,融情于景,景里含情,情与景水乳交融,把汉元帝对王昭君走后的那种思念、悲凉的心境,通过景物的描写抒发出来,让人鲜明可见。往复循环的句式,铿锵有力的声韵,更使抒情缠绵悱恻,荡气回肠!再如《梧桐雨》第四折,作者设置“秋夜梧桐雨”的凄景,衬托唐明皇愁苦、烦乱、孤凄的心境,景物描写与人物感情的抒发水乳交融,充满浓郁的抒情色彩。【滚绣球】写因被秋雨惊了好梦,惹得唐明皇对梧桐雨充满怨恨。【叨叨令】用一组排比句模拟雨声,衬托出玄宗烦乱的心情。【倘秀才】写对梧桐雨恼恨到极致,想把梧桐“锯倒”当作“柴烧”,反映了唐明皇失意、痛苦的心态。【三煞】排比多种雨态,更显出梧桐雨的无情无意,添愁助恨,渲染了唐明皇的孤独与无奈。【二煞】写雨下个不停,玄宗的烦闷情绪也有增无减。【黄钟煞】把主人公的思想感情作为景物描写的归宿,“雨湿寒梢,泪染龙袍,不肯相饶,共隔着一树梧桐直滴到晓”[9]364,将“雨”和“泪”、情与景巧妙挽合,收结的含哀无限。这几支曲子用以情衬情、景交融的手法,造成一种凄怆冷落的意境,将唐明皇的幽怨哀伤,孤寂苦闷刻画的淋漓尽致。
四、结语
元代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激烈,处于这个时代的马致远、白朴经历了科举中断,儒士没有仕进之阶,文人生存空间变得十分狭窄的不幸处境。他们像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文人一样,将笔墨投向戏剧创作,借杂剧创作来抛洒他们对时代兴衰的感受,抒写自身命运的感伤。上述两篇经典作品中悲剧主人公酣畅淋漓的抒情,为情造景、情与景水乳交融形成的凄怆冷落的意境,让人千载之下为之动容。立足于此,元代剧作家虽然丧失了传统儒生的地位,失去了建功立业、名标青史的机会,但他们的戏剧创作本身就是一座丰碑,值得后人不断地对此进行探讨和解释。
[1]包小玲.《汉宫秋》与《梧桐雨》的异曲同工之“趣”[J].平顶山师专学报,2004(2):42.
[2][3][4][5][7][8][9](明)臧晋叔编.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