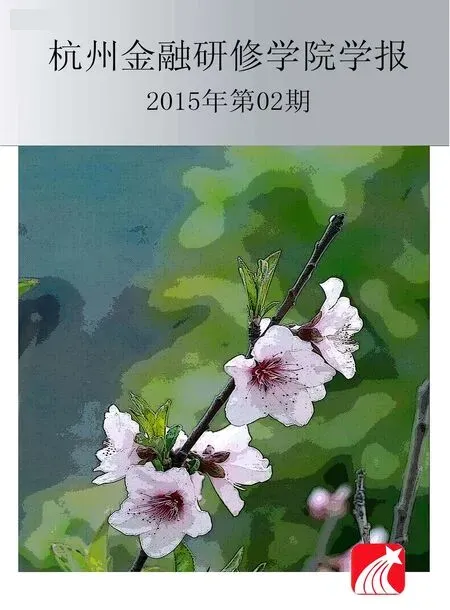反思城镇化与互联网突围
包刚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经历了形态不同的三个阶段,即1979-1984年城镇化恢复、1985-1991年的城镇化稳步推进、1992年至今的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不容置疑,过去三十多年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宝贵的经验。然而,由于过去一直强调推进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人和土地的城镇化,过于关注的是城镇化率,以至于留下了城镇化进程中“摊大饼”和“农民工”问题的深刻教训,以及土地和人口带来的其他问题。其中涉及如何有效解决资金的问题,可以说是至今无解。
土地城镇化 积累了经验
先说无奈的城市扩张“摊大饼”问题。过去城镇化的征地运动,成为我国城镇化的最直接动力。这一模式固然爆发出了城镇建设的强大推动力,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农村的集体土地很难自行增值,农村难以自主推进城镇化。农村集体土地的城镇化,只能寄希望于城市边缘的对外扩张。另一方面也给城市带来了不断扩张的巨大负担,城市不得不承担起土地城镇化的“使命”,只能以不断“摊大饼”的方式扩张外沿,从而推动城市规模无节制增长扩大。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被不断强化,城市规划布局一改再改难以定论。
伴随而来的是“农民工”的社会问题。农转非的户籍变更方式,被作为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否的关键标志,造成了限制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成为迄今为止遭受诟病最重的城镇化措施。一方面它创造了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名词“农民工”,他们虽然保持农村户籍,却长期在远离故土的城市打工,“农民工”的存在催生了大量社会性问题,诸如土地抛荒及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和春运高峰等;另一方面那些被征地而获得城市户籍的农民,匆匆忙忙从平房搬入楼房,农村社会结构被破坏了,却没有融入新的社区组织,农民户籍身份的改变,并没有带来农村社会习惯和社会心理的城镇化。加上一部分农民没有在城市再就业、再生存的能力,赌博、犯罪、心理抑郁等成为这一群体的高发问题。征地和户籍的城镇化方式,使过去三十多年来走了一条“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城镇化道路。即占有资源的大城市可以吸引更多资源,而资源外流的小城镇则面临更多资源的流失。其后果是小城市的基础建设、公共服务能力、就业能力与大城市形成天壤之别。大城市则普遍出现城市空间资源紧张、自然承载能力超负荷等严重社会问题。
缺少资金一直是制约城镇化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与我国财税体制密切联系。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实行的是分税制,财政与税收体制呈现出地方分割和层级递减的形态,地方政府的层级越低预算开支就越有限。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尽管县域的户籍人口明显增加了,但却无助于预算来源的根本改善。按省、市(地)、县三级行政区划,作为神经末梢的县域经济,一般都缺乏可以支撑地方预算开支的产业基础,多数县域只能依靠省与中央的转移支付,维持治理系统的基本运作。加之一般而言县域的户籍和土地指标,都受制于上级政府规划。因此可以说我国以往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方式,走的是政府主导城镇化的路径。美国的分税体制则与我国就不同了,美国的税收主要来源于个人所得税,人在哪里就向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纳税。我国地方政府可以存留的财政收入,主体是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由于多数县级经济的积累并不充分,尤其是中西部县域经济缺乏产业维系,企业实力薄弱,基本不足以维持行政的运作。
然而,回顾我国城镇化模式可以发现,尽管资本匮乏我们还是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如苏南模式,以地方政府与集体农户合资,筹建乡镇企业,实现了产业驱动城镇化;温州模式,任凭民间资本野蛮生长,从手工作坊逐步成长为规模企业,实现了市场驱动城镇化;深圳模式,通过对外开放市场,以外资外贸促进贸易增长,实现了贸易驱动城镇化。总结以上三种模式,说明我国经历的城镇化,离不开市场管制松动推动市场创新。上述三种模式无一例外都是依靠经济管制松动、调动民间活力,从而带来了产业推进城镇化的发展。三种模式的资本来源各不相同,苏南模式带有相对更强的政府色彩,其资本来源于地方政府和集体农户。温州模式的资本主要来源于民间积累。深圳模式的资本则来源于境外。但无论资本的来源在哪里,资本都扮演了为市场创新提供激励、推动创新扩张的关键角色。
新型城镇化 两类金融各得其所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其中蕴含了更多破旧立新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城市群空间形态的变化和城镇化核心内容的变化。城市群空间形态的变化,由过去的单中心层次结构,向多中心都市绵延区发展,在绵延区中有1-2个核心大城市,有多个城市副中心、县域经济作为支撑辅助,城市副中心和县域经济,将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关注点。而城镇化核心内容的变化,则由过去单纯关注城镇化率(户籍人口的由农业转为非农业),转向提高县域经济和新农村(城镇)就业容量,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从而实现人口的就地就近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目标的转变,对县域经济提供就业和满足城市公共服务的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最佳途径,就是由本地人来参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不是单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进行推进。前者不仅在于能够调动社会参与创新的活力,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人们对于所居住生活城市的依赖感和归属感。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互联网金融显示出来的优势,正是在于调动无法参与城镇化的人们,融入新一轮城镇化的重大变革,带来的不光是资金融通的可能性,更重要的带来了改变县域经济与农村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模式的巨大变化的可能性,进而改变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实践路径。
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新城镇化方式,并不是实现新城镇化的有效手段,也不是解决新型县域经济资本问题的最有效方式。而自下而上地激发民间创新和集聚资本的活力,恐怕才是真正有效的途径。然而,面对如今发展如火如荼的互联网金融,仍然应当保持冷静清醒的认识,因为在所有的金融环节中,互联网金融并非具有挑战传统金融的优势。具体来说互联网金融(如众筹模式、P2P等),主要的作用体现在解决融资的效率和降低成本,但却意味着需要依靠铺线铺面才能实现。而传统银行机构已经设立了20多万家银行网点和50万台ATM机,已经充足覆盖了存款与其他金融业务的来源。互联网金融机构一般是20人以下的小团队,通过用户的智能手机或电脑,触及到的目标借款和贷款需求,需要提供个性化服务如资产评估、风险评估、征信等专业服务。而对于解决个性化、多元化、复杂化的金融需求,互联网金融还远远不能达到安全性和准确性的标准。
理论上讲任何城市的城镇化对资金的需求都来自于两个层面,其一是政府财税主导的公共投资,其二是私人投资和融资需求。而互联网金融在政府财政参与的公共投资领域,可以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其原因在于在政府公共投资领域中,投资主体和借贷主体都相对明确且数量有限,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分析,是传统金融擅长的领域。只有在私人投资和借贷需求层面,互联网金融才有相应的空间可以挖掘。对于人口密度较低、物理网点覆盖成本更高、金融资源相对匮乏的县域经济而言需求会更大些。互联网金融事实上在县域经济中爆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2014年春节的一周内,余额宝在三、四线城市就猛增了700万用户,原因在于那些曾经在大城市打工的人返回老家后,又带动老家的亲戚朋友加入到余额宝的行列。可以相信未来私人投资的渗透会更快,更具有扩张的能动性。
期待“宜农贷”枪响过后
目前,互联网金融正在农村信贷领域进行积极尝试。如宜信公司将互联网金融思维与小额信贷连接在一起,以众筹和P2P的混合方式创立了“宜农贷”项目,为农民、低收入者提供无抵押的信用借款和咨询服务。宜信公司的操作模式是与小额信贷联盟,与妇女经济发展组织合作,获取农户资料和融资需求。一方面经过宜农贷和合作伙伴严格筛选,包括将借款农户的还款记录、信用状况、社区声誉、借款用途等因素都纳入考察范围之内,通过小组联保的形式再次控制风险,并予以技术指导和培训;另一方面以大数法则分解风险,宜农贷的贷款农户多数集中在万元以下,出借人的最低出资可以降低至100元。与一般P2P方式无法了解背后贷款人有所不同的是,所有的农户基本介绍(包括住址、照片、家庭成员、资产积累、贷款用途都在网页中展示出来。通过上述在两个层面上风险把控,运行了一年多的“宜农贷”还款率达到了100%。截至2013年末其总计贷款规模将近5900万元,其中当年就新增贷款2900万元。
然而,“宜农贷”存在的非商业化运作问题,决定了其正面临着运作的极限。比照贷款的盈利比例,“宜农贷”与其说是贷款,更像是农村的一种公益,其利率极低只有2%。“宜农贷”称其为“感恩收益率”,如此的收益很难吸引出借者资金的持续投入。因此当贷款金额出现过大的情况(比如某项目需要筹款5万元,理论上就需要售出最低出资额为500份的出借合同才可能完成)。而不得不面临的漫长的筹款过程,就难免会出现融资中途流产。
笔者认为“宜农贷”带给我们的思考在于,即使是带有公益扶贫性质的小额融资,也必须考虑可持续运作,确定必须的盈利模式,利用互联网技术,才能打破发展瓶颈,达到有效扩张的目的。产业经济基础薄弱的县域融资需求,往往以个体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小额贷款仅仅带动个体经济的复苏,对部分收益者具有改善生活的效果,但对整个农村或城镇以至于县域范围的福利改进、生产方式改善,以及城镇化发展,并不能发挥积极有效的实际作用。然而“宜农贷”只是一发信号弹,枪响过后更多的创新产品将会涌现出来。
“资金融通+商业驱动……”能重写历史
互联网金融虽然在大中城市扮演资金融通的角色。然而在县级城市相对单一的表现,可能会堵死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道路。互联网金融机构作为现代服务经济的代表,与个体和小农经济存在隔膜。意味着互联网金融机构并不具备改变个体和小农经济的能力,甚至可能因为这些源于生产方式的隔膜而一筹莫展。要挖掘县域经济城镇化的金融市场利润,就必须拓展互联网金融“资金融通+商业驱动”的县域经济模式。互联网金融机构与其他多元市场组织,包括了农户合作社、农信合作社、地方企业、民间微贷组织、担保机构、财务公司、电商、农业信息平台。多元市场组织联合的价值,不仅在于控制风险,更重要的在于打破个体经济和小农经济模式,改变县域经济相对封闭的状态,为从封闭的个体和小农经济,走向现代产业分工提供动力。
基于其占据了互联网思维和资本两方面优势,互联网金融机构可以在联合多元市场主体的过程中发挥带头作用。由于多元市场组织在县域经济的不同环节拥有丰富的资源,如农户合作社是农村社会个体的重要组织机构,农信合作社与农业信息平台是县域经济信息的重要占有者,地方企业、电商等是流通各环节中不可缺少的润滑剂。无论是建立乡镇合作经济、村民入股,还是私人之间的联合出资、联合经营等形式,都是新城镇化县域经济走向以分工合作的重要标志。由此带来的转变不仅具有商业层面的意义,即提高个体经济融资需求的规模,改进市场的整体利润;还具有社会层面的意义,即推动县域经济城镇化模式转型。毕竟社会生产方式转变所带动的社会变迁,才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意义。
我国的县域经济,尤其对地处内陆、城镇化基础较弱的地区而言,那里缺少必要的商业嗅觉,市场化进度相对缓慢有限。因此,只要个体经济和小农经济继续在县域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那里的互联网金融就会必然遭遇增长的“天花板”。如果没有外部商业资源的激活和驱动,互联网金融只能在养殖、餐饮、零售等个体经济融资需求里打转。诚然这些个体经济融资需求也是县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但互联网金融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应该停留在满足个体经济需要的层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互联网金融在融通资金的功能之外,必须结合商业驱动的功能,与多元市场机构和非市场机构的广泛结盟。如果这条道路可以行得通,互联网金融才可能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