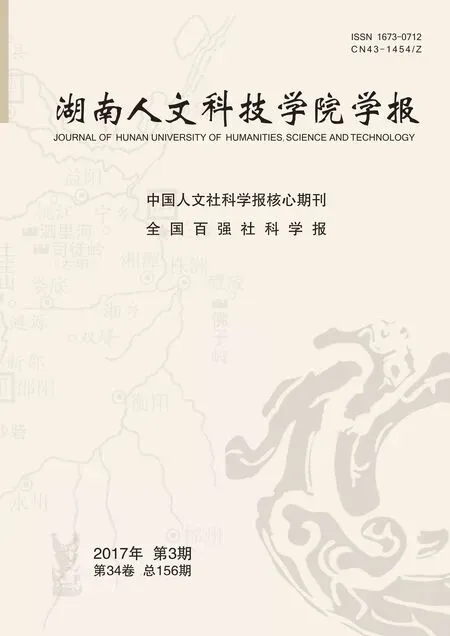不可言说的单一者的“生存”
——现代哲学的先驱者克尔郭凯尔
程 强
(贵州师范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18)
不可言说的单一者的“生存”
——现代哲学的先驱者克尔郭凯尔
程 强
(贵州师范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18)
克尔郭凯尔用怀疑与否定的方式否定一个外我的存在,从普遍的客观性转向个体、单一者的存在。“单一者的存在”是克氏思想的中心,他的思想使近代哲学追求的确定性被消解了:存在就是“单一者的存在”“单一者的存在”又仅向单一者自身显现,对于外界是非透明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生存”的秘密潜藏在语言之下。现代西方哲学中语言与存在关系的探讨就从这里系统地拉开了序幕。
不可言说;单一者;上帝;生存
克尔郭凯尔,丹麦人,一个非近代传统意义的哲学家、自由的精神表达者、忠实的基督教信徒。他身材矮小、驼背、跛脚,终生未娶,他“规避人与人之间任何亲密接触”[1]8,经常端着一大堆高得让人惊愕的尖脆物件在大街上颤巍巍地行走,或者欢喜雀跃、沿街漫舞,无视周围人的诧异,自称是这个世界的陌生客,被哥本哈根市民视为“街头怪人”。从克尔郭凯尔的怪癖行为可见,他是一个践行自己哲学的人。克尔郭凯尔的父亲是个成功的商人、虔诚的信徒,阴郁自闭,却具有惊人的观察力、想象力与辩证思维,对克尔郭凯尔的爱好、信仰及学术取向影响极大。克尔郭凯尔一直生活在他父亲的精神笼罩之中,“他的整个人生观就隐蔽在他父亲那儿”[1]15。他的哲学思想浸透着颓废、悲观、强烈而孤僻的个人感情,这与传统的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形成极为鲜明的异趣。也是从克尔郭凯尔等少数人开始,西方哲学至少在欧洲大陆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由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
然而,他的哲学并不是一开始就受人瞩目,在他生前及死后的数十年,一直是默默无闻的,作品只在少数人之间流传,直到20世纪初他才声名鹊起,卡夫卡、雅斯贝斯、海德格尔、萨特、加缪成了他的思想的某种回应者、追随者,他俨然成了存在主义的先驱者之一。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思潮兴起,解构主义者对他的作品进行“间接沟通”式的诠释,他的思想又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整个20世纪,欧洲大陆除了追求严格科学认识起点的胡塞尔之外,不同的哲学流派,都从他这里获得了某种启发或滋养,这些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汇聚起来,形成一股巨大的时代潮流,一起埋葬了西方大陆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踏入了现代哲学的门槛。对于克尔郭凯尔来说,这个转向的历程即是从对思辨哲学的兴趣而转成对“生存”“主体”“个体与单一者”的关怀。
一、“生存”就是偶然的存在
“生存”是克尔郭凯尔整个哲学的中心概念,“生存”赋予了克氏哲学的基本面貌,也是他的思想不同于近代哲学的一个最基础的逻辑起点,他的一切哲学思想都是在这个概念上展开、推演的。
近现代的哲学家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都喜欢把自己的思想上溯到古希腊时期,以便绕开或有别于当下的哲学流派。克尔郭凯尔也是如此,他很厌烦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十分乐意把他的“生存”智慧与苏格拉底的“助生法”紧系一起。在他看来,与其说,苏格拉底通过对话、逐渐否定来逼近真理;不如说,苏格拉底通过对话让自己与对话者都“体验真理”。真理不是苏格拉底辩证法最终要追寻的东西,对话本身就是真理的当下呈现。在整个对话中,苏格拉底扮演了一个真理的助生婆,把对话者从一个状态带入另一个状态。对谈话者来说,他仿佛获得了又一次的重生,重新认识了自己。苏格拉底的哲学就是一种现场呈现,当下展现对真理追求的“生存”现状。
这种现场发生的哲学展现了“生存”的个体性,个体单独面对真理,即面对“生存”本身,不需要人仰而追求之。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从追求中个体重新“被生下来”,获得“新生”,这种“新生”就是把真理落实在当下的“生存”中,体验当下的“生存”。然而,克尔郭凯尔的“生存”又不是简单的“日常生存”,而是幡然悔过之后获得真理的重新体验,是对“生存”的本真的当下体悟,是整个个体完全地投入到“生存”中,没有片刻从中抽出来反观对象。他说:“要是某个正开始其一生某一特定时期的人,头一次想要意识到作为他一生组成部分,具有永恒有效性的这一种生活,这么做恰恰就阻碍了它获得意义,因为他这是想让现在在场的东西在那个业已成为过去的瞬间里向他显示出来,这就取消了其意义。”[1]24真正的“生存”不能从“瞬间”中抽离出来,否则就失去了“生存”。他反对从过去整体的连续性中寻找个体的意义,认为从整体考察部分就是取消个体真实在场的价值所在,个体的真实存在绝不是简单的一个整体的必然延续的结果,因果关系在真实存在那里没有意义,单一者只是单一者,单一者的在场说明了一切,我们无需在这之外给单一者增加任何东西。因此,克尔郭凯尔来认为,真理虽然是需要学习的,但需要的是那种重新获得新生的学习,即从当下的在场来认识自己,而不是从整体的因果关系中认知自己是一个大系统的部分,因为个体与整体并不能相融,现在也不能看成过去或将来的一个因或果的部分,而“日常生存”总伴随着因果关系,总是伴随着“计划”“打算”等等涉及到总体对局部的筹划,这就失去了“生存”的当下体验。因此“日常生存者”可以说从没有真正体验“生存”,他们只是按部就班地活着,按照一定的生活经验或前人的经验而活着,因此他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中,让自己的生活服从“必然”。“哲学想做的是比这更困难的事:它想使一切都充满永恒和必然性的念头,它想要在此刻当下就这么做,而这意味着用永恒这一念头杀死此刻当下,又想留住它鲜活的生命。这将意味着想要将正在发生的事看成已经发生过的事,又同时看作正在发生的事,这还将意味着想把未来理解成现在,又同时理解为未来。”[1]81真正的“生存”反对把自己置于一个连续的链条当中,个体要重新面对一个新的个体当下存在,同时认识到真理从来不是一个最终的目标,只要有一个目标或对象存在,真理立即远离我们,把我们拒之门外。真理是单一者“在场”的具体展现,它并不暗示与一个先前的存在有何种联系,也不必然地是前一个存在者的继续,它只是如此这般自己存在而已。我们第一次真正面对一个不需依傍别的什么的自己,我只存在于当下之中,我所学乃是摒弃从前的我,还原一个重生的新我,我不用记忆来限制现在的我,我也不把自己置于记忆的连续性中。真理的本真是我们在“当下”学习或者说体会真理,而不是一个延续过来的结果或可以确定的预先目的。然而,“当下恰恰是一种不确定性。在当下之中不会发生关系,因为一旦有了关系,当下就会被取消。因此,一切当下都是真的,但这一真理在下一瞬里就变成谬误,因为在当下之中,一切都不是真的。假如意识可以存在于当下之中,那么也就取消了真理问题。”[1]36真理即在“当下”,也不在“当下”,我们只能在“当下”中寻找真理,然而“当下”又无法在意识中固定下来,因为意识只能存在于时间可延续的因果链中,故真理是不可确定地确定在“当下”之中,随之“当下”成为下一个瞬间,真理也便消失在时间链中而去迎接下一个“当下”的瞬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克尔郭凯尔认为,存在的真理其实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真理其实时时刻刻都以真理的形式存在。
排除因果的整体性、确定性、连续性,“生存”本身一下子就变成非确定性的了,它隔断了时间的线索,也隔断了空间的延续,它呈现了一种偶然性、随机性、突发性、片段性,无法延续,无法继承,个体之间在真理的状态中是隔离的,你一旦感到个体的关系,当下的“生存”真理就从你眼前溜走,而让位于“日常生存”。因此,真理不是一个共同认可的大背景下的产物,不能被定性,不能被确定,因为它不能“外在”地展示自己,也不能被真正的理性思考所捕获,它随时消失,又随时产生,时时刻刻都是分离的,非常类似于佛家的刹那生灭,只是佛家说的时间与色世界都不真实,而克尔郭凯尔说的“生存”真理只存在于刹那之中,前一刹与后一刹是不相关的,一有相关的想法,“生存”就倏忽间消失,因为“生存”不能当做一个对象物去关照、考察,而只能在此之中体会。“生存”与主体、个体、单一有关,与他人无关,每个人都拥有真理,个体的真理都是分离的,不能互通,这就是克尔郭凯尔独特的“现实性”。对于克尔郭凯尔来说,“现实性”就意味着主体的“生存”“个体”的感受、“单一”者的“存在”,由此他与理性主义客观对象性的“现实性”形成对峙,这个思路被后来的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者继承。
克尔郭凯尔认为,理性主义或学院派哲学家把“现实性”理解为概念构造与对象描述,他们所建构的体系与个体存在毫无关系,他们忘却或漠视了自身的生存,远离生活真相,甚至可以说这些理性主义哲学家并不曾真正生活过。因为,学院派把“现实性”纳入逻辑范畴,必然使“现实性”的“偶发性”特性丧失,这就抽空了“现实性”的“生存”基质。因此,要使“现实性”恢复其“生存”的本来特性,必须把“现实性”从理性主义的逻辑世界中剥离出来,把“偶发性”重新返回到“现实性”基质上,使“个体”或“单一”对存在的感受鲜活起来。因此,克尔郭凯尔所说的“生存”是一种鲜活的、开放的、偶发性的存在过程,是一种非逻辑、非体系、非必然的自由生活状态,而不是黑格尔作为逻辑起点的“实存”。
由于克尔郭凯尔注重的是个体的生存状态,他的“生存”实际是指个体在刹那的时间碎片中向无限而去的无休止的斗争:“什么是生存?生存就是无限与有限、永恒与瞬间所孕育的孩子,因此它是持续不断地斗争着的。”[2]449因为“生存”是有限的个体向无限的斗争,是有限摆脱无限获得自己的过程,也是个体摆脱被塑造的历程。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克尔郭凯尔对“重生”的描述,以往的哲学都指向整体、永恒,而克氏重建的生存哲学则反方向而走,因此何时能摆脱整体与无限,即与无限与整体的斗争获得胜利,何时我们就真正把握了真理。这个由来已久的生活惯性或思维如此之强大,所以我们永远只是在路上,这条路又不是从过去延生下来的,只是我当下的一个随机展现,当下的生存蔓延,摆脱永恒而获得当下的瞬间,真正的永恒就是当下的瞬间。我们注定要死亡,然而死亡与我们又没有关系,因为生存没有未来,没有预设,没有目标。既然没有什么永恒与整体,那么生命也没有所谓的尽头,只有永恒的瞬间。我们又与谁在斗争?不知道对象,不知道为何而斗,因为一旦知道对象,一旦知道为何而斗,我们就把生存对象化,我们就失去了生存的本真。然而我们又在斗争,因此,这样一种不知对象不知为何的斗争只能落空,只能陷于一个巨大的黑洞、真空当中,生存注定布满一脚踏空的陷阱,这就注定克尔郭凯尔的哲学带有悲剧式的颓废特质。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与萨特关于存在、死亡与虚空的探讨。
克尔郭凯尔为了挽救这种徒劳的争斗,把“信仰”的因素注入他的哲学里,使他的“生存”斗争有一股强心剂,丢弃斗争的对象与结果的种种考虑,守卫着信仰走完虚空的人生旅程。“如果一个人没有永恒的意识,如果潜藏在一切之下的仅仅是狂野不羁的强力,在阴暗的激情中产生一切有意义的或无意义的事物的强力,如果无边无际、不可遏制的空虚藏匿于一切事物之后,那么,除了绝望之外生活还有什么呢?如果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没有神圣的纽带将人类联系在一起……”[3]
“现实性”从逻辑的必然性中剥离之后,单一的“主体”与“偶发性”就会显露出来,“主体”就会在“偶发性”的“生活境界”中有“选择”性地“生存”。“生存”与“选择”是存在主义的两大主题,而这种“生存”“选择”在克氏那里实际是“无选择”地追逐信仰,而忘却“生存”本身的偶然与虚幻。
二、摒弃体系与客观性
理性主义的“现实性”是必然的逻辑下的概念,理性主义是对“现实性”的对象性关照而组建一套逻辑严密的体系。理性主义哲学家都非常自信地认为,在他们的体系中可以对一切对象作最终的、完满的评价,因此,他们的体系也是一种变相的知识终止。克尔郭凯尔的哲学恰好相反,因为他在“现实性”概念上剥离了理性主义的逻辑,而把“偶发性”注入“现实性”中。由于“偶发性”的时时存在,逻辑的必然性很难建立起来。由此,克尔郭凯尔也扬弃了传统的体系建构。他说“一个逻辑的体系是可能的”而“一个关于生存的体系则是不可能的”[2]451。这个说法的前提是,逻辑的体系对生存本身无法真实关照,逻辑体系基本是虚幻的思想游戏,因为任何一种体系本身都预先设定了一个不可能的假设性“终结点”,而现实性的“生存”则是“无限”的。因此,逻辑体系只在虚幻的思想游戏中具有可能性。
体系的解构实际上是伴随着客观性的解构一道而来,既然我们不能建立一套对“生存”行之有效的客观性解释,那么“生存”本身就不具有普遍有效的客观性,“生存”是片断的、零碎的、没有逻辑的、自由的、流动的,既无法预知,更无法操控,它溢出了客观性的因果关系,不能用一个完整的体系描述它,更不能用一个体系终极它。因此,“生存”在本质上不属于近代哲学的客观性范畴,它应该成为审美的、伦理的、宗教的对象。对普遍客观性的拒斥实际上存在于现代哲学的大多数流派之中,甚至存在于抱有严格客观性的胡塞尔现象学中,胡塞尔坚持认为只在意向中显现的对象才是显而易见的,而纯粹主体之外的客观本身深不可测,不是哲学探讨的对象,他的学生海德格尔也抱此观念。
不仅如此,在克尔郭凯尔看来,体系建立的本身也对个体自由形成威胁:体系建立者所追求的一种普遍客观性就是在个体之外建立一套森严的必然性真理体系,个体追求真理,则必须放弃个体所有的内在要求,消除自我来迎合普遍性客体,个体的存在就成了必然体系中的偶然性。因此,游离于这个必然体系之外的个体就不具有任何真理,也不能作出任何选择,在克尔郭凯尔看来就是无异于放弃个人的自由。在这里,我们多少也看到了康德的影响,他只是排斥康德理性批判的那部分,而发挥康德哲学里面道德自由的个人选择。在康德本人那里,实际也存在着建构体系与解构体系的犹豫与困惑。
摒弃体系的观点影响20世纪后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根本观点:他们只对具体问题感兴趣,无意于建立任何一种完备的体系,哲学最终成了一种诠释学,而诠释都带有个体的参与,偶发性随时存在,没有谁的判断具有绝对权威。这样,传统的文化中心主义就解体了,文化具有了鲜活的个体性,分散在每一个解释者那里。
三、单一的庇护者——虚无而玄深的上帝
摒弃了体系的逻辑建构,“生存”就只能是鲜活的、个体的“单一者”的生存,那么“单一者”的存在如何可以获得有价值的意义?如果单一者只是单一者,由于他的片断性,他的存在必然因为零碎、没有指向而失去价值。严格地说,单一者的零碎只是对它认识的零碎,它本身无所谓完整与零碎,因为完整与零碎都是意识后的描述,只要有对单一者有任何形式内容的判断,这些都不属于单一者的“生存”本身。不过,从不可避免的“反思”角度看,单一者的“生存”在每一刹那之间都是隔断的、零碎的,每一个片段都封锁在单一者那里,彼此互不相通,同一个单一者又被分割成千差万别的不同的单一者,更无法通向某个有意义的世界。
克尔郭凯尔为了让零碎的单一者具有意义,他把永恒与单一者联系起来,所有的单一者都指向一个永恒。由于单一者都是封闭的,它回归到自己,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这个永恒者也不能从单一者外部去寻找:“每个人本身就是中心,而整个世界都只集中在他身上,因为他的认识自己就是认识上帝。”[1]113世界的真实只在单一者身上体现出来,单一者与上帝建立了联系,这种建立起来的“联系”其实就是重生过后的单一者对自己的回归。上帝不在任何地方,只能在单一者身上体现出来,只有单一者重生之后,上帝才显现于自身,显现于单一者。
有趣的是,由于单一者都具有各自的独特性,甚至被自己的每一刹那分裂成片段的单一者,没有一个统一的单一者。因此,单一者所指向的同一个上帝又非常之不同,这样,上帝作为永恒的载体就呈现千差万别的存在,它们反过来由单一者自己决定的。从积极的方面说,上帝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因而可以适应于亿万个单一者,与传统的神学并不矛盾。然而,从消极的方面看,单一者由于决定上帝以何种方式存在而自动消解上帝主宰的本性,上帝由“因”变成“果”,则上帝作为创世的存在者也自动取消。如果说,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是个体迎合超越的本体,向本体靠拢,那么,克氏的哲学是反过来的,超越的本体迎合个体,向个体靠拢,与传统的路径正好相反。上帝之本体在克氏生存论中只有在单一者那里才能显现出来,独立性的本体实际上被消解了。
这个结论非常类似我国魏晋玄学的本体“无”:“无”根植于每一个存在者当中,不能独立于存在者而存在,是每一个存在者的根源,但“无”又不是存在者。由于“无”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者,因而“无”具有无限差异性,但“无”又是万物总体的自身根源,各个存在者的“无”又必须是同一个“无”,故此,“无”又不能有任何特别的内容,而只能是无任何内容的“无”。玄学家把这个无任何内容的“无”称为“玄冥”,深黑无法命名、无法认知。我们不相信克尔郭凯尔受到了中国玄学的影响,但单一者的存在等于把上帝虚无化:每个单一者分享一个不同的上帝,不同的上帝又是同一个上帝,这个上帝只能被虚无化。佛家以“月印万川”来比喻真如本体,而这个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没有独立的内容。我们不能用各个不同的主体面对同一个客体得出结论:克氏还保留一个独立存在的上帝。这个逻辑不适合克尔郭凯尔,因为他的存在是指单一者的存在,他不认可一个独立的客体上帝的存在。真实的上帝只能存在于独立的单一者那里。单一者与上帝秘密对话,由他来塑造自己独特的上帝,同时上帝的存在也只能在这个单一者那里展现,这样,上帝会深深地隐藏在个体的一片黑暗中。这与克尔郭凯尔拒斥普遍客观性的思维是一致的。
四、排斥公共社会、超语言的非意义存在及其影响
存在是一种“生存”,“生存”的状态只关及个体的单一者,单一者及单一者的指向——上帝,都深陷于单一者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除了单一者自己,任何其他单一者都无法真正地进入。而且,即是单一者自己,也只是在时间的碎片中体会“生存”,无法关照“生存”,只能进入“生存”,而无法从“生存”中走出来,走出来就意味着背弃“生存”。“生存”被片片切断,上下没有连续的因果链条,不能作整体关照。“生存”其中,任何片段又都是完整的,不可言说的。片段是如何整合起来的,只有当下的“生存”可以把握,但又无法去表达。单一者的零碎只是对它认识的零碎,它本身无所谓完整与零碎,因为完整与零碎都是意识后的描述,只要对单一者有任何形式内容的判断,这些都不属于单一者的“生存”本身。单一者试图走出“生存”而去描述或表达“生存”,那都是徒劳的。因此,克尔郭凯尔的哲学是不需要任何文字,文字只起了一个指向作用:有一个本真的“生存”存在那里,但到底是什么,无法清楚。真正的存在无法言说,外人无法言说,自己也无法言说,可以言说的都不是真实的,或者是无关于“生存”的。言说、表达都是以共通的存在与一般的抽象为前提的,并且都是一种“当下”之后的关照,与反思、对象物有关,这些恰好背离了“生存”的本性。超越语言之外的“存在”很类似道家的不可言说的、在知识之外的“道”,但二者是否有借鉴关系不可断定。我们不可以根据深受克氏影响的海德格尔的学术经历来逆推克尔郭凯尔的哲学思想,因为基督教神学里还有一种通过强烈的个体体验来接近上帝的思潮,个体体验也是无法真正言说的,作为信徒的克氏是否受到这种神学影响也未可知。
但不可确定性、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生存体验即使用确定性的哲学语言做指向性的表达也是有困难的。既然世界的真实存在仅仅与某一个体联系在一起,那么个体之间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就无法在存在主义理论上得到任何说明,因为本质上个体的自明性都在各自封闭的范围内自明着,不能向外界展现,共通性只是一个语言的假设。“生存”即是对外部世界的彻底粉粹,至少可以说外部世界只是一种不真实的存在,或者说公共存在只是方便权宜而已,是一种没有反思之前的日常存在。这可能就是克氏哲学里面的宗教性因素,也是一种西方近代哲学变相的二元分立思维。
公共世界的坍塌,个体世界也同时消失在一片局外人无法渗透的神秘的帷幕中。后现代倡导的粉粹中心主义可以从克氏的存在主义的逻辑中推演出来,这里是它的源头。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后现代意义下的极端个性化世界与存在主义中的神秘倾向关系极为密切。高高在上的、为大家共识的上帝一旦被推倒,个性化世界就呈现出一片无穷无尽、千姿百态的样式,没有一种样式对他人是合理的,也没有一种样式对自己是合理的。个人主义呈现出一种极端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奇形怪状、层出不穷是存在哲学神秘倾向一个必然后果,或者说这种对个人神秘化的向往滋生了后现代思潮。
极端个性化的神秘性的生存哲学影响到艺术上面,就是对各种奇特的个体感受抱有浓厚的兴趣。意识流的小说可以直接从这种哲学思想中得到滋养。这批小说家会描写一些莫名其妙的墙上的灰尘,对变幻的桌子上的污迹津津乐道,凡是意识指向的任何偶然存在都成了他们笔下的对象,它们连成一片,在个体的意识中形成了模糊不清、真实存在又没有意义的偶然世界,它展示了平常无法传达、没有意义、而对个体来说又是一个真实的、封闭的偶然世界。这一切在理性主义看来都是不屑一顾并毫无意义的,然而在克尔郭凯尔等存在主义哲学家看来,真实的存在本来就没有意义,意义世界是在当下生存中走出来的人为臆造的结果。克尔郭凯尔通过自己的生存哲学成功地粉粹了世界的意义,把世界还原成自己的当下生存,个体无法从中走出来,却与他的世界连成一片。这种世界经不得任何反思,因为反思不属于它,然而哲学家也意识到恰好是反思帮助他寻找到这样的生存状态。英国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最后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可以说,她既结束了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她的日常生活世界,也结束了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她的小说世界。
生存论哲学家也是如此矛盾,他总是往返生活在两边的世界,没有一个世界是有意义的:生存中的世界本没有意义可言,从生存外构建的日常意义世界因为是人为构造也没有意义。
[1]克尔郭凯尔.论怀疑者 哲学片断[M].翁绍军,陆兴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96.
[2]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第7卷:上[M].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3]克尔郭凯尔.恐惧与颤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
Abstract: Kierkegaard doubted and denied the existence of the external self, an objective concept, converting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single individual. Much of Kierkegaard’s work deals with “the existence of the single individual” and refutes the certainty pursued by modern philosophy. Existence refers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single individual”, which is visible to the single individual himself, and invisible to the external world. Existence is ineffable and can not be explained clearly in language, which triggers a discussion between existence and language in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Keywords: ineffability; single individual; God; existence
(责任编校:舒阳晔)
IneffableExistenceoftheSingleIndividual——Kierkegaard, the Pioneer of Modern Philosophy
CHENGQiang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Guizhou Education University, Guiyang 550018, China)
B151
A
1673-0712(2017)03-0021-06
2017-03-24.
程强(1971—),男,安徽马鞍山人,贵州师范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儒家哲学、中西比较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