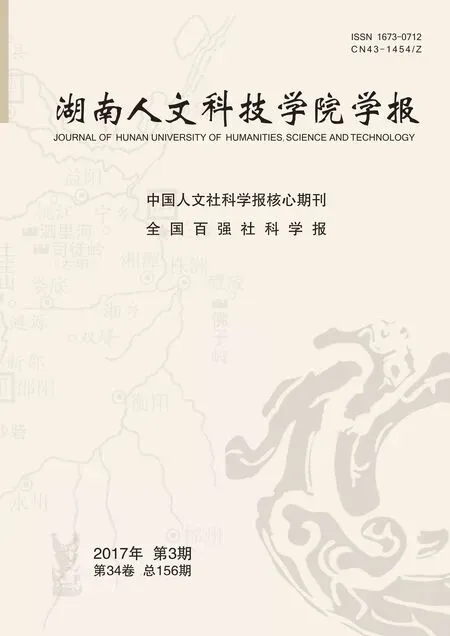课程改革的文化冲突及其超越
罗 燕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410205)
课程改革的文化冲突及其超越
罗 燕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410205)
当前,课程改革处于一种多样态的文化冲突中,既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历时性文化冲突,也有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并存的共时性文化冲突,更有教育文化与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结构性文化冲突。文化冲突是一种文化选择、适应和创造的过程,即在历时性文化冲突中进行必要的文化寻根,挖掘中国传统课程文化的当代意义;在共时性文化冲突中进行即时性的文化调适,探寻课程文化的国际理解;在结构性文化冲突中进行文化追问,强化师生文化主体的自我存在。
课程改革;课程文化;文化寻根;文化调适;文化追问
任何一次课程改革其实都是一种课程文化的重建。在课程发展的现代性构建过程中,文化始终无法缺位。泰勒(Edward B.Tylor)把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文化”定义为: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的复合体。由此推之,课程文化可被视为在课程形态和实践活动中体现的规范、价值、审美、信仰和表意象征符号的复合体[1]。从课程文化的视野审视当前的课程改革,其理论旨趣在于考量不同课程知识体系背后的历史文化处境及其蕴涵的教育价值取向,从而在与其他课程文化进行博弈和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建构突显本土文化价值,赢得其他文化理解和尊重,并彰显个体生命价值的课程体系。
一、课程改革处于多样态的文化冲突中
如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价值多元化、各种理论流派不断涌现、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课程改革正处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多维交汇点上,课程文化建设也面临着诸多矛盾与冲突。
(一)历时性文化冲突
历时性文化冲突是指课程变革所遭遇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根基的缺乏上。每一次课程改革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因此,课程改革需要追溯到当时的历史时间境遇,考虑这一特定历史时间前后的文化背景及其价值取向。
现代化是当今社会的显著特征,与之伴随而来的是具有课程理念人本化、课程内容现代化、课程手段技术化和学科综合化等特征的现代性主流文化。关注课程改革的文化处境,一方面要关注现代社会及其现代性文化对当今课程变革的规约;另一方面,要关注传统文化对课程改革的影响。“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世代沿袭下来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特质或文化模式。”[2]24课程文化有其内在的文化蕴意和自律品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课程改革不能忽视传统,数典忘祖。
从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课程发展史看,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儒家文化是一种以礼、乐为主的伦理型文化,它强调以政治、伦理为本位,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至上是它的最高准则[3]。在儒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一种传统、控制、追求实用的课程文化。传统课程文化长期积累的一些优良传统,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由博返约、长善救失、教学相长等等,至今依然是我们课程文化建设的有益资源和活水源头。
反思当下课程改革,我们需要理性关注改革的文化处境,从文化继承与发扬的视角思考传统课程文化与课程改革的关系,充分挖掘中国传统课程文化的当代意义,尽可能避免课程改革对传统课程文化的遮蔽与剥离。
(二)共时性文化冲突
共时性文化冲突是指课程改革所面临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主要体现在文化融合的缺失上。近代以来,我国课程与教学领域引进许多国外流行的理论,主要有人本主义、多元智能、建构主义、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些外来课程与教学理论的引进,对我国课程与教学理论的建构和实践变革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因社会背景、教育基础、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这些理论在课程变革的实践中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我们在引进国外的课程与教学理论时,必须避免曾经出现过的偏差,并对其进行语境和文脉的分析与追溯,找准中国文化根脉与教育实践的契合点,进行话语和范式的改造与转换,使其真正成为中国化、本土化的课程与教学论[4]。
从当下的新课程改革来看,我国的课程改革对本土的文化土壤和教育传统不够重视,课程改革缺乏足够的文化自觉和本土化意识[5],没有形成自己系统的理论体系。课程改革实践存在着将国外杜威、布鲁纳、加德纳、布鲁姆等人的课程教学理论简单地运用到我国课程与教学中的问题,而对统御我国几十年的“凯洛夫教育”以及由此形成的课程体系则“一棒打死”[6],这导致许多传统优秀课程与教学思想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降低了其应有的地位。可见,课程改革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价值取舍与抗衡中,缺失必要的融合。
(三)结构性文化冲突
结构性文化冲突是指课程改革所承载的教育文化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文化使命的缺位。课程改革是学校教育活动的组成部分,它承载的教育文化价值取向是通过课程改革来更好地促进人的自我实现与全面发展。但是,社会经济文化所追求的是通过课程改革使学校教育更好地为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服务,结构性文化冲突由此产生。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教育正面临着知识经济的挑战。那么,课程改革是一味迎合当下的经济发展,为市场服务,还是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和文化使命?抑或二者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而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新课程虽然提及了“文化使命”“文化再造”等主张,但当前的学校课程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文化工具,课程改革的文化使命和功能被消解。课程受制于执行社会经济文化的功能和任务,它的功能、目标、性质、运作方式、社会角色等都服务于某种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现实需要往往在课程的文化选择、内容的确定与组织、评价与管理方面起着主导性作用,如果学校教育课程文化的自身使命,被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的霸权式话语所遮蔽,那么它也势必会造成课程本应具有的自在的文化品性,及其所引发的内在的、独立的价值标准的消解和自身文化使命的缺位。课程被现代社会赋予教化、控制、征服的社会功能,成为现代社会强势文化的“代言人”和一种经世致用的工具,其完全受制于现存的社会文化旨意与规约,机械地服务于这种具有强烈功利色彩的社会文化。可以说,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文化的超验纽带,从根本上消解课程促进人的自我实现与全面发展的教育文化功能与价值,使得课程文化丢却了其原有的感召力。因此,课程改革既要保持必要的文化张力,也迫切需要一场文化“祛魅”。
二、课程改革中的文化自觉与超越
承上所述,课程改革中出现的这一系列文化冲突或矛盾,其原因相当复杂,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因此,解决矛盾不能一蹴而就。从文化发展视角而言,课程改革必须以优秀的民族文化为背景而不简单地提倡文化复古;必须以坚守本土化成果为原则而不排斥外来先进文化;必须以个体生命存在对文化的主体确认与创新为使命而不丧失课程文化的普遍性意义。
(一)文化寻根:挖掘中国传统课程文化的当代意义
教育与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定社会特有的传统文化弥漫于整个社会中,强烈地制约着人们对子女的养育方式和教育内容;这种稳定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又使传统文化在下一代身上得以再生……从而保证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2]27在我国传统课程文化中,虽然存在着与当今课程与教学实践要求不相适应的内容,但中国社会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是课程改革独特的文化境遇,对当下课程改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每一次课程变革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都是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酝酿和生发的。中国传统课程的特色,从理论体系来说,主要是以儒家课程思想为主线,以孔子、孟子、荀子为源,以董仲舒、韩愈、朱熹、陆九渊、王夫之等为流,以王国维、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等为变[4],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崇尚“中庸”、追求“和谐”的课程文化;从课程改革层面上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在面对课程变革时,既要虑及当下现实条件的规约与局限,又要避免消极保守的倾向。总之,在传统“中庸”文化视域下的课程改革,应该是传统与现代两种课程文化相斥力量的碰撞、妥协与融合,以此促进课程改革的发展,而不是在现代社会课程改革中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与改造。
从中国古代文化“以儒为主,伦理特色”到近代以来文化的转型,它的特征是“中体西用,多元并存”,关于现代及未来的课程改革,笔者认为,应在“以中为主,综合创新”的文化大背景下进行。当然,“以中为主”并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以中国优秀的传统课程文化为主,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前提下,兼容各家学说,真正彰显课程文化活力。如此,课程改革才不会被西方历史文化语境构建起来的课程知识体系所遮蔽。因此,现代社会和现代性文化的发展应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更应该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课程改革的影响,使课程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相互传承的载体,成为富有生命力的积极力量。
(二)文化调适:寻求课程文化的国际理解
文化调适就是面对错综复杂和不断变迁的文化现象时,当文化的一部分发生改变,其他部分为了适应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文化调适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既要保持文化的连续性又要保持文化的时代活力,不断创新。在课程改革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保持必要的文化张力,既不简单秉持“拿来主义”的文化态度、服从体现现代性文化的课程改革要求,也不盲目固守本土文化;既不能放弃自身内在的知识创生和课程文化的国际理解,也不能摒弃自身原有知识所特有的文化特征及其蕴涵的教育价值,而应在二者之间进行理性的文化审视,使课程改革的推进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实践行动,成为寻求国际理解的最佳途径。
简而言之,课程文化的调适,既是课程改革的基本需要,也是课程改革深化的必然趋势[7]。当今的课程改革在借鉴国外先进理论的同时,更要深刻把握本土文化对课程改革的影响,立足实际,科学借鉴,自主调适,融汇创新,寻求当下课程文化在国际中的理解。
(三)文化追问:强化师生文化主体的自我存在
课程改革发生在课堂这个基本场域中,教师和学生成为课程实践的关键主体,也就是说,课程文化理念转为文化行为进而形成文化习惯,都必须依靠师生双方来完成。教师和学生作为独特的文化个体,通过课堂教学这个场域进行文化生活实践,教师和学生自身所确立的文化价值观念、价值判断、价值取向也会严重影响课程文化的形成和根植。教育是一项“培养人的活动”,促进“人之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和重要使命。这就要求师生要勇于突破社会经济文化主导的传递性教学文化、同质化应试文化、学科本位课程文化的藩篱,获得对自身多元文化身份及其文化境遇的体认。
因此,作为文化变革实践的课程改革,必须彰显教师和学生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多元的文化身份,理解师生的文化冲突与困惑,相信师生能作为文化主体进行课堂创造,构建新的课程教学文化[8]。同时,尊重师生双方的文化主体地位,提升师生对课程文化的创生与创造能力,启发师生以理性的文化主体身份,在文化的继承与扬弃中进行课程文化的革新和创造,而非迁就、固守以往的文化主体地位。
总之,课程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一次文化创新,是一场价值革命。它需要我们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和多元的文化视野,认真考量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外、教育与经济等问题,夯实并拓宽其文化根基,引进、借鉴、融合国外课程文化,建构一种开放、民主、底蕴深厚的本土课程文化。
[1]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34.
[2]傅维利,刘民.文化变迁与教育发展[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
[3]靳玉乐,杨红.试论传统文化与课程价值取向[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6):65-66.
[4]张传燧,石雷.论课程与教学论的本土化[J].教育研究,2012(3):82-86.
[5]杨启亮.守护家园:课程与教学变革的本土化[J].教育研究,2007(9):23-28.
[6]钟启泉.课程的逻辑基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3.
[7]李本友.十年之思:课程改革的文化阻抗与调适[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1(3):45.
[8]程良宏.从教材改革到文化变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视域演进[J].教育发展研究,2015(2):51-52.
Abstract: The current curriculum reform is undergoing diverse cultural conflicts — diachronic ones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es, synchronic ones caus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local and foreign cultures, and structural ones between social economy and education. The process of settling cultural conflicts involves cultural selection, adaptation and creation, which means root-seeking in the diachronic cultural conflicts to gain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urriculum culture, cultural adaptation in synchronic culture conflicts to explore the interna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curriculum culture, and cultural contemplation of the effec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on the structural culture conflicts.
Keywords: curriculum reform; curriculum culture; cultural roots; culture adaptation; cultural contemplation
(责任编校:彭巍颐)
声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国内外文献索引、文摘和全文数据库收录,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本刊视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本刊编辑部
CulturalConflictsandTranscendenceinCurriculumReform
LUOYan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Hunan)
G423.07
1673-0712(2017)03-0105-05
2017-02-26
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隐形的翅膀:基于语文学习的小学生梦想教育研究”(XJK013BJC002)。
罗燕(1984—),女,湖南冷水江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