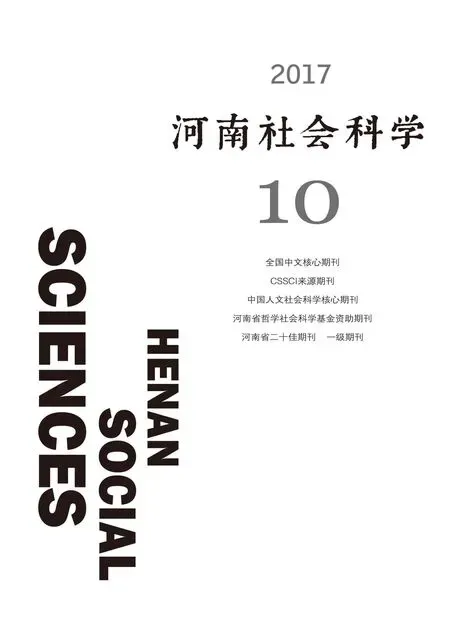贪污贿赂案件中“公务支出”解读
薛长义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2249)
贪污贿赂案件中“公务支出”解读
薛长义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2249)
贪污贿赂案件中赃款“用于公务支出”是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一个疑点和难点,也曾是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脱罪的一个辩点。其在实践中的认定,直接影响对贪污贿赂行为的定罪量刑,也直接关系到对腐败的打击力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4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为公支出”问题予以明确规定,为我们正确认定贪污贿赂犯罪提供了遵循。但因实践中为公支出、社会捐赠的情况较为复杂,如何理解与适用这一解释,需要进一步探究界定,以便更好地实现刑法的打击和保障功能。
贪污;贿赂;为公支出
“为公支出”曾是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脱罪的一个辩点,也是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一个疑点和难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后,将赃款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罪、受贿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这一规定对为公开支、社会捐赠抗辩理由采用了“有限认可”的模式,对于平息司法实践中的争论、降低控方指控风险具有积极的作用,但这种态度也将会导致以后的司法实践中出现更多的“为公支出”“社会捐赠”的辩解,而且实践中为公支出、社会捐赠的情况比较复杂,因此,如何理解与适用这一解释,需要进一步探究。
一、对“出于贪污、受贿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的理解
(一)对贪污、受贿故意的把握
《解释》既强调贪污、受贿行为的故意,又强调行为人对财物的非法占有,坚持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并重,严格入罪条件,符合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同时也符合此处特定的语境。因为贪利型犯罪在犯罪既遂后又将违法所得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用于社会捐赠,看起来更似一个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辩解,而对该种辩解的认可也更似一个悖论。贪污贿赂犯罪行为人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目的通常都是据为己有,据为己有反映了行为人犯罪的主观恶性。如果行为人一开始就没有将公共财物据为己有的目的,那么其主观恶性就不能说达到犯罪的程度,其行为就不应当以犯罪论处。个人受贿罪的本质特点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据为己有,而用于单位公务开支,说明行为人并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不可能构成受贿罪①。因此,对存在为单位公务支出或社会捐赠情节而又认定为犯罪的贪污、贿赂行为,需要对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素作出明确的解释和审慎的认定。
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态度。但故意属于行为中的主观要素,主观要素属于行为主体的内心世界的内容,是行为人的内心活动与状态,与之相联系的要素有行为人的认识、想法、目的等,难以被直接感受和查明。主观事实之属性决定了主观事实一般难以通过直接证据查明,而只能基于间接证据,依靠推论的方法加以认知。而这些间接证据,主要包括行为人在一定目的指导下的行为②。因此,贪污、受贿的故意,不能依靠行为人供述,只能根据行为人在行为中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他人财物的手段,占有时间的长短,对财物的处理方式等情节来进行判断。贪污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非法占有不仅是一种客观行为状态,其行为本身就包含和体现了行为人非法占有的故意。在部分贪污、受贿案件中,涉案人往往以为单位公务支出或社会捐赠情节来否认自己在整个行为中的贪污、受贿故意,导致行为人主观故意认定困难。《解释》描述“出于贪污、贿赂的故意”,意在强调要加强对行为人贪污、受贿主观故意的考察,避免对单纯的收入不上账、利用虚假发票套取公款、私设小金库等违规占有行为进行客观归罪,从而做到主客观要素全面证明。实际上《解释》是对存在为公支出、社会捐赠情节的贪污受贿行为入罪提出了更加严格、审慎的证明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贪污、贿赂案件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在行为初期并不明了。如在贪污案件中,行为人将公共财物截留或转出账外后,初期往往存在一种混合的故意:既有规避财务制度、方便单位违规开支的故意,又有趁机浑水摸鱼个人贪占的故意;或者初期仅为规避财务制度,在转为小金库后脱离监管,又萌生个人非法占有的故意。在贿赂案件中,行为人在收受他人财物的初期,也可能有退还的意思和表示,但在持有时间长后又产生非法据为己有并支配的故意。上述两种情形中,行为人在行为初期主观意图不明,只是把公共财物由明转暗,由他人占有转为行为人占有,在后期才产生个人非法据为己有的故意。因此,考察行为人的故意应从行为人非法占有的手段、时间长短、财产处理方式、知情面大小、有无退还条件等行为要素来证明。强调和考察贪污、贿赂的故意,目的在于把贪污、贿赂犯罪行为同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私设小金库及短时收受他人财物尚未退还的行为区分开来,严格入罪标准,准确认定涉罪数额,保证定罪量刑公正合理。
(二)对非法占有的理解
《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后”,强调的是行为人在特定故意(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支配下实施贪污、受贿行为终了的既遂状态。既对存在公务开支、社会捐赠情节的贪污、受贿行为的主观故意提出严格的要求,又对行为的客观要件提出明确的要求。
贪污罪是一种在直接故意支配下,以一定的贪污结果发生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能构成犯罪的既遂:一是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直接故意;二是行为人已经实施贪污行为,已经将特定的公共财物非法占有,即行为人已经将财物侵吞、窃取、骗取到自己手中,财物的合法所有权人已经完全丧失对财物的管理和控制。只有达到上述主、客观条件,才能视为贪污行为实施终了③。对于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虚假平账等贪污行为,但公共财物尚未实际转移或者尚未被行为人控制就被查获的,应视为贪污罪未遂。在索取型受贿中,“索取”应该是行为进程的终极点,表明行为人经由索要或者勒索继而取得对财物的占有或实际控制状态。索要是前提,落脚点在收受,以国家工作人员索取到贿赂作为犯罪既遂标准。在收受型受贿中,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了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并允诺或默认为他人谋利,就出卖了国家赋予他的权力,侵害了受贿罪的法益,继而构成受贿罪的既遂④。
总之,仅有贪污、受贿的故意,没有完成对财物的实际控制,只能按犯罪未遂处理,不存在为公支出或者社会捐赠影响量刑的问题。没有贪污、受贿的故意,而仅仅是违反财务管理规定控制了公共财物或临时占有他人的财物,从一开始行为就不能被认定为犯罪,故不存在公务开支、社会捐赠影响量刑的问题。只有行为人具备贪污、受贿的故意,并实际非法占有了公共财物或他人财物,行为才能被评价为犯罪,才能在此前提下考量为公支出、社会捐赠行为对量刑的影响。
二、对为单位公务支出、社会捐赠的理解
同自首、立功、积极退赃等情节一样,贪污、受贿犯罪既遂之后将赃款用于单位公务开支、社会捐赠的行为属于“罪后情节”。所谓“罪后情节”是行为人实施犯罪后对自己行为的认识及具体表现,反映了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大小,因而在量刑时应予以考虑⑤。“罪后情节”不属于犯罪构成的要素,但由于这些情节反映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并对原犯罪造成的社会危害有一定的弥补作用,所以在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刑法》已将自首、立功两种“罪后情节”确定为量刑的法定情节,司法解释也明确将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等罪后行为列为酌定量刑情节。
贪污、受贿行为实施完毕之后,将违法所得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社会捐赠的行为,是行为人犯罪后对所得赃款的处分,系典型的罪后行为,之所以在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系出于两方面考量:一是贪污、受贿之后,将违法所得用于公务支出或社会捐赠,反映了行为人人身危险性降低,再次危害社会的危险较小;二是为公支出、社会捐赠的行为对原贪污、受贿犯罪行为损害的法益有一定程度的弥补,其前罪行为损害的社会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刑罚的功能有两种,即惩罚功能和预防功能。惩罚功能是对已然之罪的“回顾”,即基于已然的犯罪而对犯罪人的权益予以剥夺与施加痛苦。预防功能,是刑罚对于未然犯罪的“前瞻”,即基于未然的犯罪而借助刑罚发挥其预防影响。对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是基于惩罚功能的需要,对人身危险性的评价是基于特殊预防的需要⑥。贪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和国家职务的廉洁性。在贪污的财物用于为公支出后,国家的财产损失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同时为公支出的行为也说明涉案行为人对财产的贪婪程度有所降低,再次贪污的可能性减小,对其给予刑罚处罚的严重程度可以适当降低。受贿犯罪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受贿后将赃款用于为单位支出或社会捐赠的,说明其对财产贪婪的程度有所降低,行为人再次受贿可能性较小,从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功能出发,可以在量刑时酌情考虑。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刑罚的功能和目的。
为公支出或社会捐赠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司法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实践中其情形和辩解多种多样,应否纳入酌定量刑的情节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量刑,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从支出的去向上分析,公务开支在实践中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支出项目符合单位的财务管理规定,完全可以由单位财务报销而行为人主动未报销的支出;二是可以由单位财务报销且行为人已启动财务报销审批程序,但尚未报销到手,行为人只是用贪污、受贿所得现金临时周转;三是不符合单位财务报销规定但系为单位利益开支,应当由单位支付的费用,如超标的烟酒等;四是违法的开支,如为单位利益花费但单位财务无法报销的礼金、贿款等。
行为人在贪污、受贿犯罪行为得逞后,将违法所得用于单位公务开支或社会捐赠,从动机上分析,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行为人在贪污、受贿之后,因廉政教育醒悟,或担心受到惩处,主动将赃款全部或部分用于为公支出或社会捐赠,反映在主观目的上是一种主动悔罪改过行为。二是行为人出于侥幸心理,将多笔贪污、受贿中的一部分用于公务开支、社会捐赠,在案发后辩称已将犯罪行为的违法所得用于为公支出或社会捐赠。而从证据上看,犯罪行为和违法所得之间并不能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三是行为人在贪污、受贿后,临时为单位垫支、周转,将赃款作为自己的周转金使用,并无将赃款用于公务开支的目的,但案发时未实际占有赃款。四是因单位、个人财务管理混乱,公私财物无法分清,行为人在案发后辩称将犯罪所得用于为公支出,此种情况实际上属于事实不清。
在为公支出、社会捐赠的知情面、公开程度方面,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单位领导或财务人员知情,经办人在开支时,将款项的来源、去向告知了相关人员,明确单位不再报销;二是单位领导、财务人员均不知情,行为人贪污、受贿及为公支出、社会捐赠的行为均为暗来暗往。在为公支出、社会捐赠行为中,支出、捐赠的动机、目的、去向、公开程度,所占违法所得的比例,都可以反映行为人对自己原犯罪行为的不同态度,从而表现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因此,在认定为公支出、社会捐赠事实时,均应查明上述详细情节。
三、为公支出、社会捐赠对量刑的影响
按照《解释》的规定,实施贪污罪、受贿罪行为后存在的为单位公务支出或社会捐赠的行为,属于刑罚裁量中可以考虑的“酌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是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的,司法机关在裁量刑罚时需要考虑的各种罪前罪后情节,包括犯罪的动机、犯罪人犯罪前的一贯表现、犯罪人犯罪后的态度。因法律没有明文规定,酌定量刑情节的强制性较弱,其在量刑中的作用弱于法定情节⑦。
存在为公支出、社会捐赠等罪后情节的贪污贿赂案件中,贪污、受贿的金额,贪污对象的性质,以及犯罪造成的损失是法定的量刑情节,是决定基准刑的关键情节。同时,在贪污、受贿两种罪行中,为公支出、社会捐赠对量刑的影响不应当相同。贪污罪侵犯的是国家财产所有权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两者是递进关系,第一层次是公共财物所有权,第二层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而作为第一层次的公共财产所有权,在受到损害后易于得到修复,行为人将违法所得用于公务支出后,原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因此其罪后为公支出的行为应当对量刑有较大影响。受贿罪侵害的是单一客体,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受贿人单位的公务支出与行贿人的财物所有权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即便受贿人将赃款用于公务支出,受到损害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也得不到修复。因此受贿罪中为公支出、社会捐赠行为对量刑的影响应小于贪污罪中类似的行为。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为公支出、社会捐赠是否影响量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量刑,则主要考虑为公支出、社会捐赠行为中的以下主客观要素:
一是为公支出、社会捐赠的目的、动机。如果行为人是真诚悔过,或者是害怕被查处而主动将违法所得用于为公支出、社会捐赠,说明行为人对自己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恶性有一定认识,有悔改的主观愿望,此种情况下罪后行为可以在较大幅度内影响量刑。如果仅仅是将违法所得临时用于单位支出的垫支、周转,在量刑时则不予考虑其罪后行为对量刑的影响。
二是非法占有赃款时间的长短。占有时间的长短影响贪污、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反映行为人再犯可能性的大小。占有违法所得的时间长,特别是为公支出、社会捐赠前曾个人使用违法所得的,其事后为公支出、社会捐赠行为对量刑的影响应当小于占有财物时间较短、个人没有实际使用财物的情形。
三是为公支出、社会捐赠所占全部违法所得的比例。为公支出、社会捐赠所占比例越大,其贪污、受贿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就会得到较大程度的弥补,其罪后行为对量刑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则可以不予考虑。
四是为公支出、社会捐赠的项目、对象。为单位正当项目的支出、出于公益目的的社会捐赠,对量刑的影响应当高于非正当项目、非公益目的的支出。在公务活动中超范围的支出、用于个人目的的送礼、出于封建迷信目的的捐赠,则不能认定为为公支出或社会捐赠,不能对量刑产生影响。
五是为公支出、社会捐赠的公开程度。行为人在为公支出、社会捐赠时对款项来源、支出项目的公开程度,单位人员知情面的大小,能够反映行为人对自己犯罪行为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再犯危险性的大小,因此对量刑可以产生影响。
上述因素反映了行为人对自己犯罪行为的态度,再犯的可能性大小及对损害结果的弥补程度,是酌定刑罚时需要考虑的罪后行为的主客观要素。总之,裁量者应当根据原贪污罪、受贿罪行为的性质、罪行的轻重,在确定基准刑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行为人罪后为公支出、社会捐赠行为的主客观要素,既可以在法定刑幅度内从轻处罚,也可以在法定刑幅度外减轻甚至免除刑罚。
注释:
①③刘方:《贪污贿赂犯罪的司法认定》,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6、53页。
②康怀宇:《主观事实证明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④郭作梅:《受贿罪新型暨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⑤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38页。
⑥邱兴隆:《罪与罚演讲录》,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⑦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309页。
编辑 潭 影 王小利
The Interpretation of“Expenditures Related to Official Business”in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ases
Xue Changyi
Expenditure related to official business is a doubtful and difficult point in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ases.It is also a point that the suspects of such crimes used to make in their defense.Its dissert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such crimes and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legal sanction against corruption.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Law Application for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ases jointly issu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Supreme Procuratorate in April 2016 explicitly stipulates the expenditures related to official business,which provides a rule for convicting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However due to the complex nature of such issues,it takes further investigation to understand and apply this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guaranteeing function of criminal law.
Embezzlement;Bribery;Expenditures Related to Official Business
D9
A
1007-905X(2017)10-0099-04
2017-05-28
薛长义,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法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公务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