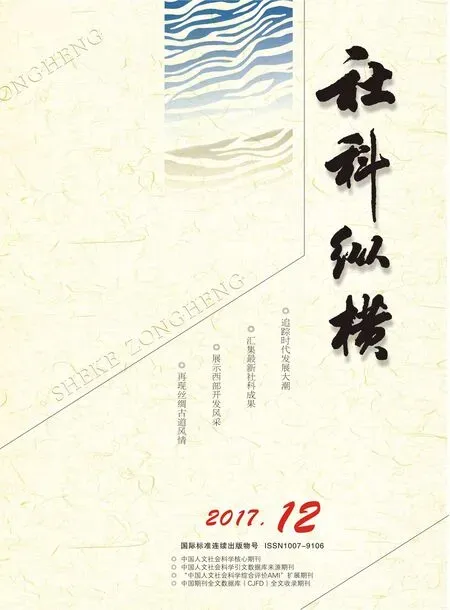李白凤诗论
司真真
(郑州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李白凤诗论
司真真
(郑州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李白凤重“灵感”、情感的炼制,轻“天才”与“模仿”,他主张诗歌创作应“真”与“美”并重,诗中必须有“我”,但后受左翼思想影响,“单纯的性感”的“我”变为“大我”。在诗与散文的异同方面,李白凤认为两者相同之处在于都有思想和境界,相异之处有五个方面,分别是韵、形式、暗示、抒情结构和用字与造句。李白凤的诗论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左翼思想和现代主义影响的复杂交织,展示出李白凤诗论独特的时代意义。
李白凤 诗论 灵感 真 美
李白凤在20世纪30、40年代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初入诗坛,他与路易士、吴奔星、常任侠、汪铭竹等交好,后与施蛰存等取得联系,至1940年代,结识穆旦,与臧克家关系颇为密切。因复杂的人生经历、社会历史背景和多变的诗风,他既被称为现代派诗人、左翼诗人,九叶诗人中亦能见到他的名字。那么,他究竟归属何派?他与现代派、九叶诗人对诗的看法是否相同?为何九叶诗人视他“面目可疑”?想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需先来看看李白凤的诗歌主张。
李白凤撰有多篇诗论,曾出版有诗论专著①,在《天才的有无问题》、《七十二峰斋随笔》、《诗坛闲步》、《〈烟〉的时代——读屠格涅夫〈烟〉杂感》、《诗与真》、《诗与散文》等文章中,他反复详尽地指出了对天才说的质疑、对灵感的重视和对感情的抑制,他认为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应当并重,诗歌应从现实出发,书写真实,针对自新诗伊始就争论不休的诗歌散文化问题,李白凤详尽地区分了诗歌与散文。
一、轻“天才”、“模仿”,重“灵感”、情感的炼制
李白凤在诗歌创作上重灵感而轻天才,他相信“并没有什么天才”,人类的智识是均等的,天才只是变形存在,被狡猾的人把持着,对于泰纳的三段论法和谢纳的“遗传,教养,经验”表示怀疑。[1]他认为“遗传”并非“天才”三要素之一,诗人的形成,更多是后天努力的结果。“一个诗人之培植,先天之资质与夫后天的培养,也是三与七之比的,有天资的人未必是诗人,天资较薄的人经过后天的良好培养,也可以成为诗人。”[2]因此,在他的文章中,我们常可看到他自勉尤其是勉励他人的话语,如“我鼓励有志于诗的去做‘诗坛无名英雄’”,“既立定志向以诗为终身事业,就要自谦自卑,眼光无妨远大,手法要尽量训练确实,文字要无虚词浪语。”[2]。他强调想要做诗人,就要经过后天的努力和训练。“你果真想做诗人——那被人认为无用的人的一种——你必须在环境中训练自己,克服自己。”[3]针对文坛上普遍存在的倚天才而作的现象,他多次进行批判,“中国的诗人们都在那里凭天才而创作,这种现象至少不是太好的。”[4]甚至对好朋友也丝毫不口下留情,讽刺那些自认“天才”的朋友们是“‘天然金刚石’的朋友,只会乱弹几只华尔兹或什么歌,立刻你可以看到他两手插在裤袋里,唇边挂着轻蔑的讥笑说‘我是天才’。在绘画方面也正一样,一切都是如此。”[5]而对于少数用脑子写作非凭借天才创作的诗人,李白凤自然也给予了正面评价。臧克家是李白凤在青岛求学时期认识的诗人,在李白凤看来,臧克家是一位“平稳扎实”的诗人,“在写作态度上是值得令人敬佩的”。在评价臧克家的讽刺诗时,李白凤就指出“你别担心写讽刺诗要凭什么天才,也许,臧克家自己就并不是天才,因为我觉得,至少他不单用手而且用了脑子去写;天才是什么呢?朝不好的方面说,应该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臧克家的自然不是‘偶得’的”。[6]李白凤在肯定臧克家手脑并用写诗的同时,含蓄地否定了天才论。
李白凤对模仿说也进行了否定。他认为诗人应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法,不能一味学习模仿他人,否则就是抄袭,就失去了作为一个诗人独特的价值。“学人者恒无我”。[2]“你爱那些诗人:英雄主义的拜伦,自由及浪漫主义的普希金,热情而羞涩的海涅,失望而自杀的玛牙可夫斯基,唯美的王尔德,神秘的爱伦坡,死于欧战的勃莱克,为人讽诵的杜工部,不得志而行吟湖畔的屈原,饿死于繁华都市的林德赛……啊!你爱的太多,结果便没有你自己了。”“旁人所能给予你的只是材料,你必须有自己剪裁的方法,否则怎能有合身的衣衫呢?”[3]对于那些毫无新意重弹老调的诗人,他批判他们是在抄袭,“你们拾起了别人的小小机智?坐在后方自己的书斋里,写前线一贯乏味的老调,你不也觉得抄袭别人的可耻么?”[3]
那么,李白凤认为应该如何进行诗歌创作呢?一是灵感,二是情感的炼制。
李白凤认为写诗第一个要素是灵感,“诗人必须有他或为诗人的因素,第一就是‘灵感’;那前人所发现而被你们卑视的,你们认为只凭热情就可以写诗么?”[3]在李白凤看来,缺乏灵感,就失去了成为一个诗人的根本条件。而这也是诗与散文境界相异的一大特点。在阐述诗与散文区别时,他指出:“诗与散文不同之处,就是诗是简练的,散文是铺陈的;诗之境界是近乎Fairies的,在字面上不妨平淡,然而在心理——即诗的灵儿必须超脱;……超者,有超越人的机智;脱者,脱却前人固持的描绘方法;用你的心来申诉你真X的灵感,在你的字汇中,创造出异于人的呼声,同于人的感情。”[3]
李白凤认为诗歌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情感的炼制。他认为诗人常常是感情最丰富也最真挚的人,但却不是凭冲动而写诗,光凭热情是写不出好诗的,他简捷了当地否定了热情不加炼制的诗歌根本算不得诗,“不加炼制的热情可以算诗么?我简捷了当的答应你一个字——否。”[3]且纯粹用“感情装饰的诗”,所走的不过是“一条危险的路,不,死亡的路”。[6]因此具体炼制的时候,要把握住度,他认为太泛、太乏都会于新诗的前途有害,“写诗是不要紧的,诗是灵感上至情的心的流露,不是应时文章的缀锦添华,我们无论写忧国愤世的诗也好,伤感的诗也好,甚至于写爱情离别也好,总是情绪不可太泛,也不可太乏,过于泛有伤于文章的修潔,过乏是会使人觉得味同嚼蜡的;那会遗害于新诗歌的前途的。”[3]他建议写诗的人在得到一个灵感的时候,必须马上把他记下来,然后用“最适于你应用的方法去构思,造句,缀字,推敲……”,且写成后要传给懂诗的朋友看,然后再修正,要做到“一字一句甚至连一个小符号都不要放松,必得达到自己称心而后可,你不要为自己的热情使自己流汗,至少这章诗必须在你的诗囊中存放至相当期限,半月至一月,以你自己的习惯而定。”[3]李白凤所说的诗写成后放置相当期限及反复修改就是情感的炼制。
二、“真”、“美”并重和“我”的演变
20世纪40年代,李白凤开始注重“真”与“美”。他认为“诗之传诸永古全靠‘真’与‘美’”,“美”就是对于事实的渲染,“真”乃是对于事实的传神。[2]换句话说,即李白凤认为真是真实,是诗之心,而美是铺陈之饰,是诗之衣,两者缺一不可。但李白凤认为“真”占据较主要的位置,“诗之传神,全在真实,因为铺陈之饰,其衣也;真实之骨骼,其心也;有饰无心,行尸走肉也。”[2]倘若诗歌对于事实忽略而一味渲染,失去真实,“虽然能够以它摇层鼓簧之舌去蠹惑群众,获得暂时的信仰”,但最终结果必将“如时代之一叶”,被历史摈弃,群众遗忘。[2]而且,李白凤认为新体八股圈套的制成与真实的丧失也密切相关。
要想做到真实,李白凤认为“诗人第一应该深入最下层生活,否则必须寂寞”,“艺术不但不应该脱离现实,而且应该与现实配合。”[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白凤“真实”的第一个涵义是现实生活的真实。这与当时左翼诗人的观念一致。但李白凤的“真实”的内涵并不仅止于此,他还指出现实生活的真实并非是千篇一律的,同样是面对战争,“有激昂就有悲观,有坚定就有动摇”,因此,诗人“要以自己思想概念去清理同样思想的群众思想体系,做一种‘真’的纪述,而凭藉文字的美的装饰,完成永恒的诗篇”。[2]李白凤没有一味以自己的思想去统一所有人的思想,他强调的是“真”的纪述,是“诗中必须有我”,“不能为了迎和读者的心理而烂造诗篇”,“即使为自己单纯的性感而写也没有什么,因为一个诗人的思想,必定能代表某一种人的思想”。[2]这一点与九叶诗人的现实观有相似之处。但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李白凤的思想逐渐粘附于现实,不再以多种方式表现多面的现实了,“我不否认自己的思想越更狭溢,老实说,我实在不能在这粘贴于现实的思想上安装一幅翅膀,让它们在快乐的天空任意飞翔;正像一棵果树,无论它开出多么鲜艳的花,也不能脱离泥土一样。”[7]映照在他眼中的只剩余“人民”的现实,诗中的“单纯的性感”的“我”也演变为“从个人主义的私爱,推广到群众的,人类的爱”[8]的具有广泛意义博爱精神的“大我”了。
李白凤认为“美”是诗歌的修饰,是诗歌的外在形式,也是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分散文的重要条件,不可或缺。他多次强调对于“美”的重视,“对于造句与修辞你不能草率,一章诗,不论是中国的五绝,日本的俳句,波斯的四行,荷马魏琪尔的史诗……在立意下笔之先,必须有精密的结构”[3]。用“最适于你应用的方法去构思,造句,缀字,推敲……”在诗歌音乐性上,李白凤并不主张将诗归之于音乐,他认为那不是在作诗,而是在做“改良的宋词”,他认为“当代的诗必须离着歌很远很远”。[4]在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差异方面,他主张两者相结合,要“承受中国诗丰盛的遗产”,“要有东方文字语言的组合形式”,同时要好好的接受西洋诗的影响,“应该走过民歌这座桥与我们所接受的西洋诗的好处结合起来”。但他也在权衡双方利弊之后劝告诗人们“不要再写外国的改组派诗,断句,倒置句,不合于中国譬喻的例证,不是中国诗具有的风格”。[2]
概之,李白凤认为“真”是真实,是诗歌的内容,“美”是铺饰,是诗歌的形式,两者并重。我们从他对“七七事变后的中国诗坛,思想的纯滤清,座谈会之于创作,重空洞的内容而不重形式,重幻想而忽略真实,重宣传而忽略记载,忘却自我而追逐别人……”[2]的批评就可看出。
三、诗与散文的区分
自新诗伊始,关于诗与散文的争论就喋喋不休,许多人认为新诗缺少韵味,过于散文化了,而写诗的人也不乏持散文分行即是诗、散文省略便是诗的谬见,使得诗与散文的界限难以被分清。针对这个问题,李白凤也进行了思考,在诗论《诗与散文》②中,他列数了古今中外的人们如雪莱、马拉美、刘勰、艾青等对于诗与散文或混而不分或狭隘的态度,并详细谈论了二者的异同。
李白凤认为诗与散文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诗与散文是同一情感之父体与文字之母体的孪生姊妹”。它们第一个共通点是思想(内容),即都有着哲学理论的依据。第二点是都有境界,“诗有诗的境界,散文有散文的境界。”第三点是广义意义上的都不借重于音乐,他认为戴望舒提出的“诗不借重于音乐”是部分的或狭义的说法,诗不借重的是反自然的“白话韵”或“旧韵律”,节奏的协均和音律的抑扬则是可以借重的。
诗与散文的区别既有狭义的,也有广义的。狭义的分别是“铺陈其辞的是散文,而不可宣传只能心会者的便是诗。”广义的区别有以下几点:一是韵。李白凤认为无韵也可是诗,韵文则“实在应称之诗的散文Prose in poem(请恕我的杜撰)或为散文诗Poem in prose”。二是形式。他认为散文分行,仍是散文。三是思想中的要素暗示。他认同雷德说“诗的(三种元素)分为声音、意义和暗示。”“暗示”就是一种思想中的要素,必须通过读者的思考力和思路要找到的东西。四是抒情结构不同。散文层层递进、丝丝相扣,诗则更简练(却不是省略),用字更节省,更慎密,诗可以用比、兴、象征、直述、托辞……等等方式来使读者从简单的词句间去推测作者感情寄托之所在。诗歌还可以运用夸张的手法合乎事实的丰富地联想,这才是上乘的诗,这是诗的境界,散文既没有也不必一定有。甚至诗歌可以夸张中带些傻气,而散文中不可有此傻气,在表现方式上,散文“最多是一种委婉曲折地叙述”。“诗与散文不同之处,就是诗是简练的,散文是铺陈的;诗之境界是近乎Fairies的,在字面上不妨平淡,然而在心理——即诗的灵魂必须超脱;此地所说的超脱你不要误会成了佛家的“超凡入圣”,超者,有超越人的机智;脱者,脱却前人固持的描绘方法;用你的心来申诉你真实的灵感,在你的字汇中,创造出异于人的呼声,同于人的感情。”“散文所要告诉读者的,是切身经历的申诉,从头到尾,层次分明,说花就是花,说鸟就是鸟……诗呢?似明白而晦涩,似难说而易解,如雾中看花,烟雨中看山色,隔沙看美人……似清醒,似朦胧,若真若幻,若有若无”。五是诗的用字和散文的造句不同。李白凤认为诗歌应锤炼句子,像古诗人陶潜、孟郊一样,推敲字词。他的诗歌创作也表达了对古人炼字炼句的感喟,“试追怀远古诗人造句之艰辛∕草率成章者能不自惭形秽吗∕缘何不力挽诗坛一往的颓风呢”[9]。
四、结语
李白凤与现代派诗人一样,受到过浪漫主义的影响,推崇灵感。但他又和现代主义诗人接触过,在诗论方面呈现出和他们相似的特征,如注重情感的炼制,强调多种方式多方面反映不同的真实。后来又受到左翼思想的影响,从个人主义的小我迈入到了大我的行列之中。尤其是1940年代后期,由于思想的改变,他开始对九叶诗人展开批判,在《关于新诗底方向问题》中,李白凤指出“现在大家写不出东西来,有人便在写新才子佳人类的东西了,甚而身上还贴着‘民主’、‘革命’的膏药,这是最可怕也最能够麻醉青年们的。”[10]这些话显然是针对九叶诗人的。在《茧里的诗论家——读袁可嘉先生〈诗与主题〉》中,他严厉斥责了袁可嘉的诗论,附带还批评了卞之琳、冯至等。其中,李白凤批评了袁可嘉们脱离现实、人民,把自己了关进象牙之塔,也批评了艾略特的《荒原》“像司马相如那种东拼西凑干燥无味的赋一样”。[11]而其实在对现实的理解上,他曾经是和九叶诗人相类似的,在诗歌创作中,他也多次运用现代主义手法表现都市中人的异化感受。但不管怎样,他对九叶诗人袁可嘉、陈敬容等的批评引起了陈敬容的反感与猜疑,不仅在1957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刊出批判文章《斥李白凤》,1983年在《图像与花朵》题记中愤愤不平地讲到当年翻译波德莱尔所遭受的挞伐,重点指责李白凤的《从波德莱尔谈起》对她的恶毒批评。后来在《答圣思》中针对九叶诗人作品选的问题时,陈敬容建议将李白凤排除在外,“当年与我们诗风相近的除来信中所列几位之外,还有方宇晨等。因《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两刊,我手边连一本也没有了,一时难想起还有哪些人。这,也是辛之兄最清楚。来信中提到的李白凤,其诗风与我们很少相近,而其人当年又面目可疑,故我们创办《中国新诗》时便再没有用过他的稿子。此人似以不提为好。”[12]这里指责李白凤“面目可疑”,无疑再次显示了李白凤对她的批评所造成的长久的心理创伤。但李白凤对左翼思想并非完全赞同,左翼作家认为诗歌应具有教育鼓动的意义和力量,而李白凤则认为诗并不只是“专供宣传使用之工具”,诗用作宣传只能作为当务之急,而不可误认为诗之必然。诗人只是间接培植民众的思想,提供给民众“思想的粮食,智慧的启示,忠实的记载就够了”。他还批评了新诗的大众化,称抗战之后的中国诗坛仿佛万花筒,“似牛非牛,似马非马,不但受着旧诗人攻击之愈深,而更陷新诗于泥涂,说是新诗大众化,结果大众化了没有?试问中国的老妪懂不懂这种诗?就是仰仗于解释懂了之后,真的需要这种诗吗?以天下愚昧之人未必聪明,打擂台式的阵容也必不能支持久远。”[2]对诗的“似明白而晦涩”的理解也和左翼作家不同,左翼作家认为诗应明白易懂,对晦涩进行了长久的批评,且把晦涩的原因归之于诗人自身政治思想、世界观等原因,而李白凤确认为诗歌可以具有多重内涵,读者根据自己的理解阅读,体会诗人的启示就好,诗人完全没有必要迎合读者,滥造诗篇。
概言之,李白凤的诗论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因此我们才会困惑于他诗人身份的辨认。理清了他的诗论思想,我们也就明白了现代派诗人、左翼诗人、九叶诗人这三种身份于他的意义和他的诗论的时代价值。
注释:
①李白凤曾出版过诗论专著《诗释》。他在《诗与散文》中说:“关于‘韵’,参见拙著诗释上卷”(文学创作,1943-2(1).)。但笔者未找到这本书。
②本部分引文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诗与散文》,不再一一注明。
[1]李白凤.天才的有无问题[J].星火,1935-2(3).
[2]李白凤.诗与真[J].现代读物,1940-5(8、9 期合刊).
[3]李白凤.诗坛闲步[J].中国诗艺,1941 复刊(2).
[4][26]李白凤.诗与散文[J].文学创作,1943-2(1).
[5]李白凤.《烟》的时代——读屠格涅夫《烟》杂感[J].罗迦主编.风雨篇[C].太阳出版社.
[6]李白凤.臧克家的《宝贝儿》[J].文萃,1947-2(15、16).
[7]李白凤.思想的散步[J].新新新闻半月刊,1947(2-3).
[8]李白凤.冥想[J].文潮,1947-3(6).
[9]李白凤.夜阑读唐人诗有感[J].现代读物,1939-4(11).
[10]李白凤,刘岚山等.关于新诗底方向问题[J].新诗潮,1948(3).
[11]李白凤.茧里的诗论家——读袁可嘉先生《诗与主题》[J].评论报,1947(13).
[12]陈敬容.辛苦又欢乐的旅程——九叶诗人陈敬容散文选[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195.
(责任编辑:丁芳琴)
I207.25
A
1007-9106(2017)12-0132-04
* 本文为2016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资助项目“李白凤、于赓虞作品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6—qn—082)。
司真真(1983—),女,南京大学文学博士,郑州师范学院初教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