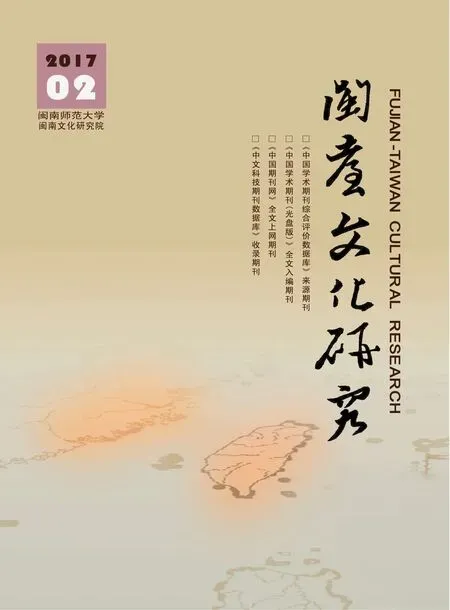闽南仪式戏剧探微
——从“猴戏”和“雷有声”说起
骆 婧
(华侨大学 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闽南仪式戏剧探微——从“猴戏”和“雷有声”说起
骆 婧
(华侨大学 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猴戏”在闽南民间中十分活跃,诸多史料可证,闽南超度仪式中出现了由孙行者护送目连下地狱救母的情节,说明“猴戏”与目连故事粘连,同样具备超度功能。以泉州提线傀儡戏、打城戏为例,在推动仪式向戏剧演进过程中,“猴戏”具备两大功能,一是调笑娱乐,二是技艺欣赏。目前唯独保留在闽南傀儡戏和打城戏《目连救母》中的“雷有声”一角,从身份到行为、性格皆与仪式戏剧中的“孙行者”相类,有可能就是“猴戏”演变的遗迹。
猴戏;雷有声;打城戏
一、引 言
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目连戏、傩戏研究热潮,至本世纪以来日益活跃的宗教“法事戏”研究,中国仪式戏剧研究已逐渐由戏曲学的一条“潜流”发展为显学。然而,目前的仪式戏剧研究似乎遇到了瓶颈。一方面,在经历过上世纪末的“井喷式”研究后,目连戏、傩戏研究从历史源流到思想内容再到艺术特征已十分详尽,代表作如康保成的《傩戏艺术源流》、刘祯的《中国传统目连文化》、朱恒夫的《目连戏研究》等。然而,这种本体研究也存在较大局限性,比如傩戏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容易给人造成傩戏‘断裂’于戏曲主航道之外、独立前进的错觉”。
另一方面,许多戏曲、宗教学者在对民间宗教仪式进行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披露了现存于全国各地的“法事戏”,代表作如胡天明等的《民间祭礼与仪式戏剧》、倪彩霞的《道教仪式与戏剧表演形态研究》、毛礼镁的《江西傩及目连戏:宗教民俗文化研究》等。然而,这部分研究又似乎较多停留在现象陈述的层面。另外,有时仪式与戏剧是如此紧密相融,以致于研究往往不自觉地模糊了两者的界限,“这些表演通过多种方式相互穿插与融合,使祭祀活动成为一个整体,因而使之构成为以请神、酬神、祈神和送神为基本构架的、祭祀仪轨与戏剧表演相结合的特殊文化形态。”
以上两大困境说明,仪式戏剧研究急需转变思路,既需避免过多倚重宗教学、人类学而偏离戏剧学正轨,又要避免陷入本体论而造成与戏曲整体的断裂。换而言之,我们急需一个从宗教仪式演进为戏曲艺术的“标本”,努力搭建起仪式戏剧与传统戏曲艺术之间的桥梁。一直以来,戏曲学界秉持着戏曲多源进化的观点,认为宗教仪式无法成为戏曲的直接母体。然而历史却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例。在闽南著名的“戏窝”泉州,恰恰出现过一种直接由宗教脱胎仪式的戏曲剧种——打城戏。在超度亡魂的仪式中,闽南僧道通常都会运用“打城”仪式来直观表现亡灵脱离地狱苦海飞升天堂的过程。由于“打城”呈现为一个个独立的情节表演,又融合了幽默戏谑与精彩的技艺表演,最终从超度仪式中分离,形成了独特的剧种——打城戏。打城戏的存在,揭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宗教仪式中已蕴藏的戏剧性扮演,有可能通过进一步艺术化,打破宗教与戏曲之间的鸿沟,最终形成独立的剧种。由此看来,若能探明打城戏从宗教仪式向戏曲艺术演进的推动力,或许将是突破上述研究瓶颈的一次有益尝试。
二、闽南“打城”仪式中的“猴戏”
与闽南宗教仪式相关的记载中,有几条史料值得格外关注:
清乾隆《鹭江志》卷十五《风俗》:丧礼之失,尤不可言。……每逢作七,礼佛拜忏,甚至打血盆地狱,以游手之人为猴与和尚,搭台唱戏,取笑男女。其尤甚者,用数十人妆鬼作神,同和尚猪猴搬(扮)演彻夜,名曰杂出。男妇老幼拥挤观看,不成体统。而居丧者自为体面,灭绝天理至此极矣。
清道光《厦门志》卷十五《风俗·俗尚》:初丧置酒召客,演剧喧哗,以为送死之礼。……至于延僧道礼忏,有所谓开冥路、荐血盆、打地狱、掷(献)铙钹、普度诸名目,云为死者减罪资福。……居丧作浮屠已属非礼,厦俗竟致演戏,俗呼杂出,以目连救母为题,杂以猪猴神鬼诸出;甚至削发之僧亦有逐队扮演,丑态秽语,百端呈露,男女聚观,毫无顾忌。丧家以为体面,亲友反加称羡,悖礼乱常,伤风败俗,莫此为甚。
林纾《畏庐琐记·泉郡人丧礼》:泉州处福建之下游,民多出洋,如小吕宋、仰光、槟榔屿各岛。富者或数千万,亦有置产于外洋,而家居于内地者,其丧礼甚奇,人至而吊丧,勿论识与弗识,咸授以鸦片一小合。延僧为《梁王忏》七日。……礼忏之末日,僧为《目连救母》之剧,合梨园演唱,至天明为止,名之曰“和尚戏”。
比照上述史料,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共同点:其一,在僧人主持的丧礼中都出现“打地狱”这个重要的仪式环节;其二,“打地狱”都蕴含戏剧扮演成分,“妆神作鬼”“扮演彻夜”,故称之为“杂出”;其三,参与表演的人员中,僧侣是主体;其四,表演的内容已相当成熟,角色上都有“神鬼”“猪猴”,甚至到了道光年间已发展出以《目连救母》为主的故事内容。其五,表演形态已呈现戏曲化:一是表演中有插科打诨的滑稽成分,以 “丑态秽语”来“取笑男女”;二是以丝竹配乐,“合梨园演唱”。由以上史料可以推断,迟至清乾隆后期至道光年间,亦即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打城戏的雏形就已形成。
由以上史料可知,在闽南佛教超度仪式“打地狱”(俗称“打城”)戏曲化的过程中,《目连救母》这一剧目曾经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前两条史料又都不约而同提及“猪猴”二字,亦即是说,闽南“打城”仪式中还存在猪、猴这样的戏剧角色。关于“猴”这一角色的由来,似乎不难推断。早在打城戏形成之前,明人郑之珍编撰的《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简称《劝善戏文》)就有《白猿抢经》一折。唐宋时代就已传入闽南的提线傀儡戏,亦保存有《目连救母》完整戏文。可见,僧人在“打城”中借用现成的一折《白猿抢经》是十分便利的。若是如此,那么“猴”这一角色即是“白猿”无疑了。然而若“猴”即是白猿,那么“猪”这一角色又从何而来?无论是郑之珍的《劝善戏文》还是泉州提线傀儡戏《目连救母》,都没有“猪”的出现。即使是《劝善戏文》中刘青提被救出地狱后变成的也是“狗”而不是“猪”。那么,两段史料无一例外将“猪”“猴”这两个角色并举,是否意味着除了《目连救母》之外,还有其他故事内容?
在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猴”“猪”搭档,就是《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和猪八戒。他们共同护送唐三藏西天取经,相互作弄打闹,确能达到“调笑男女”之效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打城”仪式直接借用了《西游记》的故事片段,与《目连救母》掺杂表演?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英国汉学家龙彼得先生曾在《关于漳泉目连戏》一文中,转述了荷兰人类学家J.J.M.de Groot于清代光绪二年(1877)在厦门调查佛教超度法事的记录,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高延(J.J.M.de Groot)说,这种戏的表演叫扑戏盆、搬戏盆或扑地狱。为了逗引观众的乐趣,目连的故事常被改变为鄙俗的笑剧。两个人一个扮猪,一个扮猴或狗,一路跟随这位寻母的圣僧,用他们的滑稽表演博得观众捧腹大笑。据说当时目连入地狱的路上曾遇一猪一猴,它们受目连的清德善行所感动,就一直跟随他,自愿充当他的使者。这种滑稽表演叫做搬猴戏或扑猴戏,通常只为那些付不起搭台演大棚的贫家大众所观赏。
以上文字已足以解释闽南方志中一再出现的“猪猴”二字。看来“打城”仪式中的表演内容,并非只是《西游记》与《目连救母》的简单拼接,而是将孙行者、猪八戒融合到目连救母的故事情节中。1996年,叶明生先生披露了福建漳平民间道教的“师公戏”,其中的“破砂墩”仪式即呈现为目连在孙行者、猪八戒的护送下西天求法、打破地狱的故事情节。这一发现有力地应证了孙行者、猪八戒二角在民间超度仪式中亦可具备宗教超度功能。
关于《西游记》与《目连救母》的情节融合,必然提及二者复杂的渊源关系。对此学界主要有两类观点。以朱恒夫为代表的一类学者认为目连变文出现的时间早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简称《取经诗话》),明代郑之珍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简称《劝善戏文》)基本保存了北宋目连杂剧的遗迹,通过它与《取经诗话》的比较可知,《目连救母》曾对《西游记》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目连戏中的“白猿精”,很可能就是取经故事中的“猴行者”的原型之一。以刘祯为代表的另一类学者则认为,将明代的《劝善戏文》和北宋目连杂剧划上等号过于武断。目连救母和西游故事同样源自唐代佛教题材,在宋元时期进一步俗化为文学、艺术样式,二者的影响应当是相互的,即《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塑造本依于《目连救母》,但后者情节之所以不断丰富则主要受前者的影响。另外,刘祯先生认为孙悟空的原型并非“白猿精”,而是目连。无论何种说法更为准确,闽南“打城”仪式中出现的“猴戏”,正是唐宋以来中原文化在闽南民间传播、遗存的明证。
基于此,我们可以就“猴戏”在闽南超度仪式中的出现,做出两种可能的推断:第一种可能是在宋元时期先有目连杂剧片段融入闽南超度仪式,后受盛行的西游故事之影响,遂将目连杂剧中的“白猿”改造为更为形象的“猴行者”,猪八戒亦随之加入;第二种可能是在明代两种故事都已形成成熟戏文,如郑之珍的《劝善戏文》和杨景贤的《西游记》,而后分别成为闽南超度仪式的表演片段,又在长期的合演中逐渐形成角色上的重合。
最关键的恐怕还是“猴戏”如何在超度仪式中发挥作用。为此,我们必须明确两大问题:第一,闽南民间超度仪式——“打城”的基本仪轨为何;第二,“猴戏”是如何与“打城”仪轨相融。
荷兰人J.J.M.De Groot于清末在厦门调查到的佛教超度仪式,曾对“打城”有较详细的叙述:
一座代表地狱的纸城已实现由孝眷准备好,被放置在灵堂中一个方便的地方,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城墙。……和尚们念诵着适合的经文,缓慢而庄重地绕着那些纸城行走。他们的声音在一些乐器声、木鱼声和鼓声的合奏下,显得十分悦耳。他们中的主持者走在前头,手中握着一种锡杖,不时地挥舞摇动着。这种操演,在中国人看来,代表着崇高的权威和尊严。过了一会儿,他用他的锡杖把纸城敲击成碎片,为亡魂创造逃脱地狱的机会。……
福建《连江县志》亦载:
悦尸有破地狱之举……遂置磁器一十八假为地狱,缁流扮目连菩萨,执禅杖以次击破之,以为破狱,救出犯罪者。
广东省梅州市的民间超度仪式亦有类似的做法:
仪式举行时,扮“目连”的主法师身披袈裟,手执锡杖,围绕莲池诵经,象征“一路寻母”。其他几位法师作配合表演,分别围绕莲池的四周诵经、巡游。统称“打莲池花”或“打四门”。其表演可分为五段:寻娘、请佛、入狱、施食、破狱。“破狱”时,“目连”用锡杖“向倒扣的瓦盆正中戳开”。
由以上几段记载,我们可大致推断福建、广东一带民间超度仪式中所必有的两大特征。一是由佛教禅师扮演目连一角,表演目连破狱救母的过程。二是仪式必有两大象征符号,一为象征地狱的“纸城”或“瓦盆”,二为象征佛教法力的锡杖。
那么,“猴戏”又如何融入到这样的超度仪式当中?笔者曾于2009年前往闽南漳州东山县铜陵镇进行田野调查,东山岛“香花僧”所操作的超度法事蕴藏着大量戏剧因素,故被百姓称为“和尚戏”。其中有一个特殊的仪式环节——“打火城”尤为关键。通过笔者对其科仪本《火城全章》的阅读,“打火城”仪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一)引魂
1、开经
2、引香魂
3、舞杖花:行走四门,使各路拳杖,任由经师督驶武场。
4、唱诵“打火城偈”一首:“目连尊者显神通,掷钹腾空瞬息中。金锡振开无间狱,宝珠照破徹虚空。欲令亡魂升天界,屡启精诚问佛光。崇建法筵燃慧炬,流传万古至今存。”
5、一经师扮目连上,唱[一更挑]南曲一首,说明亡魂姓名及此行目的。行走挑经势,缓步于四门。唱罢拜四城门。
(二)走出灵山寺
1、过隔阳亭
2、入黄泉大路
(三)过鬼门关
鬼门关内面有鬼将把关,鬼将都是由鼓师扮演。目连坚持要过鬼门关,鬼将多加阻拦,双方答对多次后方才过关。大唱入关韵[鬼门关]:“举手拨开生死路,翻身跳入鬼门关。”并合大锣鼓节奏。
(四)过阎君殿
经师扮目连,与鼓师扮的鬼将对话。两人就阎王殿的对联和地狱设置进行讨论。最后走过阎君殿。
(五)过望乡台
目连经望乡台,遇见由鼓师扮演的女鬼魂“愁娘”。后者因生前待人苛刻,失手打死丈夫,被鬼将索命,囚禁于望乡台。两人一问一答,插科打诨。女鬼作丑角表演,引众人发笑。
(六)奈何桥
目连与鬼将对话,叙述善人和恶人过奈何桥时受到的截然不同的待遇。经师牵帛布魂身,引亡灵过桥,师持刀念咒,净桥仪式,完毕后念[七洲桥]四句联调,或唱落山辞调。
(七)三途大路
仍按四城门步履,奏演毕。经师扮目连与鬼将对话,道出三途大路的来历。东畔一条通往阴府东嶽司,西畔一条通往西天路,中央一条路与董永孝行相关。
(八)过东牢关:
目连来到三途东牢,与看守鬼官进行对话,要求释放香魂一位。鬼官请其说明名姓缘由,经过讨价还价,目连最终打开地狱。
(九)破狱:
众人持仗花,劾敕四城门。一门一杖,一门各唱[背北调]西方偈一条。四城门演本完,取
锡杖,琢破血湖盆。大喊喧言:“稽首地藏尊,菩萨妙难论。手执金锡杖,打破血湖盆。”[16]
由以上步骤可知,佛教“打地狱城”的“戏剧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打城的过程表现为目连这名主角经历地狱重重关卡的戏剧情节,他在每一个关卡与鬼将、阎王和鬼魂等诸多地狱中的人物对话,明确采用了戏剧的代言体形式。它省略了目连救母的前因和全家升天的结局,只大致展现目连入地狱之后的过程。另一方面,打城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大量音乐演唱,其中不仅有庄严肃穆的佛曲,更吸收了闽南流行的南曲曲牌,甚至借鉴道教、民间戏曲的诸多乐器,使仪式表演向综合的戏曲艺术更进了一步。
遗憾的是,在漳州东山“打火城”中并看不到“猴”这一角色的出现,但同处福建的漳平道教法事戏则可成为一大旁证。叶明生先生曾整理出福建漳平道教“破砂墩”仪式的十五个科仪序列,其中几个步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3、目连做:即目连挑经挑母。
4、给件:目连到雷音寺朝拜释迦佛祖,佛赐目连“尊者”称号,并赠袈裟、经书、芒鞋、水盂、锡杖等法宝,并教其赴观音处取金圈收伏孙行者同行地狱寻母。
5、存变封狱:此为科仪,罗卜存变为目连尊者,砂墩存变为酆都,并封狱门。6、目连起身:目连离开灵山寻访孙行者。
7、出土地:桃花店徒弟化为目连指引孙行者之水濂洞去处。
8、行者起身:即孙行者出场自白身世。
9、行者出洞:孙行者作“逃苔”(即“跳台”)之种种武功、道功、杂耍之表演,以显示其神通无比。
10、行者过溪:目连寻到孙行者,请他引路,孙不服,目连以金圈收之。孙无奈辞妻与目连挑行李上路,途中以拜目连为师之名,又与目连斗法,终被目连降伏。
11、出八戒:路中孙行者又叫来猪八戒挑行李,三人同行。
12、游狱:在孙行者引路下,目连遍游地狱之鬼门关、破钱山、金桥、奈何桥、望乡台等重重险关。
13、四门白:到了追阳县禹州城十八层地狱,孙行者、猪八戒辞别而去。目连向地狱门官及狱主司官打听到母亲的下落,狱主不许其见母,退堂封了地狱门。
14、破狱:目连凭佛赐神通广大,唱着《地狱经》,挥舞锡杖破了砂墩(即打破酆都)救出亡魂,(此处为丧家之母或亡者之魂)。
若将漳平“破砂墩”与东山“打火城”加以比较,则不难发现其共通点:超度仪式都表现为目连入狱、破狱的情节。然而“破砂墩”多了一条情节线索,就是由孙行者、猪八戒共同护送目连入狱释放亡魂。这样看来,在清代厦门史料中出现的“猴戏”与“目连戏”相融的特殊形态已基本清楚。首先,仪式有几个重要角色:由禅师扮演的目连,助手扮演的孙行者、猪八戒,以及由乐师或助手扮演的鬼将、鬼魂。其次,仪式中融入曲折生动的戏剧情节,主要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目连与孙行者、猪八戒这一组合的形成过程,二是三人共同入地狱释放亡魂的过程。
三、从“猴戏”到“雷有声”——闽南仪式戏剧的成熟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闽南超度仪式向戏剧演进的过程中,“猴戏”不仅没有就此止步,反而从“配角”摇身一变,超越了目连这个主角。在上世纪初,闽南漳州石码至厦门同安一带,形成了“戏盆”这样擅演猴戏的特殊形态:
闽南土戏,皆演文剧,唯有戏盆兼擅武行,因扮齐天大圣者为全班主角,故又称猴戏。惯演目连救母,专供丧家或七月普渡之用。总之,此戏只可娱鬼,不可娱神。全班人数二三十人,戏资每台三四十元,因用途甚狭,班极少。只有红笼、青笼二班,在同安之灌口乡。
漳码颓俗莫甚于居丧演猴戏,此种猴戏皆一般无赖匪徒为之,其戏出均足以社会迷信鬼怪,而其所说科白尤足以诱男女坠于淫奔,伤风败俗,法纪难容,故列宪禁之,有犯必惩。无如日久弊生,欲演此戏者,略贿兵役地保则可演唱无惧。兵保纵容罪故难宥,然居丧之公然演此败俗之戏,律以不法不孝之条,殊无枉纵。本二十九日石码田厝街警察局之对门,有某甲者,竟以亲丧而演猴戏两班,对台以较优劣,远近男女来观者途为之塞。
由以上史料可知,闽南近代“戏盆”有几大特征:(一)专供超度场合表演。(二)以齐天大圣——孙悟空为主要角色和演出噱头,同时以目连救母为拿手剧目。(三)表演形式俚俗火爆,观众趋之若鹜。若与上述闽南“打城”相关史料相比照,则不难看出其间的渊源关系。地方学者在对“戏盆”的调查中亦证实,它与打城戏有着内在的关联。
而在打城戏的发源地——泉州,充分成熟后的打城戏,依然突显着“猴”的重要性。当代打城戏著名武生曾火成,因擅演孙悟空而被人们誉为“闽南猴王”。从清末“打城”仪式的“猪猴搬演”,到民国的“猴戏”,再到当代打城戏的“猴王”,一条发展线索已呼之欲出。或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大致的推断:清代闽南的“打城”仪式已有“猴戏”成分,清末至民国初年进形成两条不同的分支。一条进而发展为成熟的剧种——打城戏,“猴戏”达到高度艺术化;另一条则发展为“戏盆”这样的分支,仍处于“法事戏”阶段,娱乐性虽强,但表演场合极其有限。
若上述推断成立,则足以说明“猴戏”在超度仪式向戏剧演进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那么,“猴戏”到底为仪式戏剧之形成带来怎样的推动力?
众所周知,观演关系的建立是戏剧产生的先决条件。观演关系一旦形成,就意味着仪式的戏剧化进程加快,因为“演员和观众关系的疏远,直接影响到表演技巧,因为表演者不能再依赖宗教仪典或迷信传说中共同崇拜和信仰的联系,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只要极力模仿一个想象的角色就足以警动视听、打动人心了,而必须揣摩观众的心理、倾注自己的情感,以赢得观众,结果从本质上加强了戏剧模仿。”这样看来,“猴戏”对仪式戏剧之形成的推动,必然表现在促成“观众”这一审美群体之形成上。依笔者浅见,这起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猴戏”具备“取笑男女”之功能,增加了仪式的娱乐感。
上文所引闽南超度史料,皆提及“取笑男女”“丑态垢语”等词,对民初“戏盆”的评价亦有“所说科白尤足以诱男女坠于淫奔”,可见俚俗的语言、幽默乃至淫秽的对白是闽南超度仪式戏剧性表演不可或缺的特征。对照上述闽南“打城”仪式中出现的几个角色,目连、阎王都不可能以丑角形态出现,我们难以想象由禅师扮演的目连会是满口秽语的形象。那么,有可能承担“取笑男女”功能的角色就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由助手或乐师扮演的鬼将、鬼魂,另一类就是助手扮演的孙悟空、猪八戒。前者的滑稽性主要表现在超脱了人世之外的狂放、讽刺,而后者的幽默特征则可以表现为二者性格之迥异,这一点在小说《西游记》中曾得到充分的体现。可惜的是我们目前在闽南超度仪式中已无法见到猴、猪二角,但通过叶明生先生对漳平道教“破砂墩”仪式的调查可知,孙行者的许多台词确实都带有滑稽世俗色彩:
杏(行)者:南无咭咭(急急)修,急急修,修来修去到杭州。杭州有一介和尚两介(个)头,上头光光献三宝,下头光光寿延生.南无佛、弥陀佛、龙眼佛、荔枝佛、琵琶(批把)佛、佛佛……
杏(行)白:……师父,我归顺尔作手下才好,我的家事无人看顾,怎么去的?要尔一日已多银子与我攒。
僧应:一日一分银子与尔。
杏(行)白:师父,我不晓得己多,尔等我回家问老婆就晓的。
僧白:尔快去快来。
杏(行)向内:老婆,老婆……(与老婆算工钱)师父,我老婆说,要尔再添三厘二毫半。
僧白:凭尔算。
杏(行)白:自古道,唐二会挑担,老婆会打算。
虽然我们难以将漳平的道教法事戏与闽南的佛教仪式等同,但漳平历史上隶属于漳州,道教与佛教超度仪式多有相互融合与借鉴,相信漳平“破砂墩”与闽南“打城”应当相去不远。
或许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猴戏”的滑稽功能。在全国多个剧种中都有《目连救母》,但惟有泉州的提线傀儡戏和打城戏中存在“雷有声”这个角色,就连古老的莆仙戏本目连戏也无“雷有声”的踪迹。在提线傀儡本和打城戏本《目连救母》中,雷有声初为强盗,被目连诚孝所感化,跟随目连上西天求法入狱救父,后在观音的试探下色心尽显,被赶回观音处潜心修法。与其相关的重要折子《双挑》《良女试雷有声》在闽南盛演不衰,《双挑》更是闽南超度仪式必备的表演内容。一直以来学界都忽略了对“雷有声”这一角色来历的探究,而笔者认为这很可能与“猴戏”有关。换句话说,目前无论是傀儡本还是打城戏本《目连救母》都不再有猴、猪伴随目连下地狱救母的情节,却多了一个别处没有的“雷有声”,后者极有可能是仪式戏剧残留在成熟戏文中的遗迹。理由有三:
首先,雷有声与孙行者的角色功能十分相似,都是目连入狱释放亡魂的陪同者,所不同的仅是前者中途放弃而后者坚持到了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闽南道教“打天堂城”仪式中,至今仍保存着《双挑》一折的表演内容,由道士分别扮目连和雷有声上场。而根据我们对清代闽南佛教“打城”仪式的推断,孙行者也是以陪同者的身份出现的。
其次,如果比照吴承恩本《西游记》之前的资料,则“猴行者”与“雷有声”的相似处更多。第一,“猴行者”的最初身份是“山怪”,而雷有声是“山贼”,皆有占山为王之意。如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提及欧阳纥之妻被白猿精掠至山洞,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则云“齐天大圣”乃申阳洞中的“猢狲精”,“能降各洞山魈,管领诸山猛兽,兴妖作法。”以上两部皆是学界公认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猴行者”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而在明代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第三本第九出《神佛降孙》中,孙行者也还自诩是“金鼎国女子我为妻,玉皇殿琼浆咱得饮”的盖世魔王形象。而在泉州傀儡本《目连救母》第五十出《守墓招朋》,雷有声出场即表明其山贼身份:“但吾雷有声,招集五百好汉,聚集金刚山,专打劫为活。一半在山,一半在海,依山靠海,出没无常,官兵不敢相侵。”
再次,二者都有贪吃、好色之个性。《补江总白猿传》中化身“白衣秀士”的白猿精专摄美妇数人到洞中供其调戏,《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中更明言“齐天大圣”嗜好“摄偷可意佳人”,且喜“醉饮非凡美酒”。而《目连救母》中的雷有声则更是好色之徒,如第五十一出《却柴》讲述傅罗卜被雷有声一众山贼所掳,观音和弟子势至化身两位美妇前来搭救,雷有声见美妇在旁动了色心,有这样生动的曲文:
(声上,唱)【鱼儿】酒醉肉饱,逍遥山上看景致。(亥,醉,白)看见姿娘。(叫)第三的。(佑上,醉话)(声亥,白)姿娘来。(各亥,唱)忽见山下二个姿娘,打扮乜伶俐。只妇人所见浅,莽撞来只山边,不畏虎狼相侵欺。(亥)硬就合伊硬,软就合伊软,想伊翁内袂走得鳖。(掠,下)……(音叫)我苦,你拙无文雅。(佑亥,问)(音白)你无看见伊来摸阮的胸前?(佑怒亥)(声白)结婚演嘉礼——唠哩嗹。我手指去,她行来给我摸着。
通过以上比对,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初步推断:“雷有声”与吴承恩《西游记》之前在传奇、话本、杂剧中出现的“猴行者”更加接近,似乎说明闽南引入《目连救母》的时间要远远早于《西游记》出现之时,并在西游故事的流传中将《目连救母》中的白猿与“猴行者”进行融合,因而保留了“猴行者”的早期样貌。然则随着小说《西游记》的强势影响,“猴行者”逐渐被抽离出超度功能之外,演化为与《西游记》更相近的《三藏取经》,与《目连救母》共同组成泉州傀儡戏连台本《目连全簿》。至于《目连救母》中目连的同行者,则由另一个更人性化的角色——雷有声来取代。
最后,我们还不难发现,泉州道教“打天堂城”仪式中的雷有声和漳平“破砂墩”仪式中的孙行者,都以滑稽的丑角形象出现。我们可以比较漳平道教“破砂墩”仪式与泉州道教“打天堂城”仪式中的两段台词:
杏(行)者:唉呀,我与唐三藏收去西天取经回来,封他(我)齐天大圣千岁爷爷。今日谁人敢叫我孙杏(行)者?不免咸(赶)下山去,拿来剥皮慢(蒙)战鼓,抽筋作弓弦,把心肝来下食酒,两耳例来作答杯。
雷有声:见前面,杏花村,许处酒旗挂起闹纷纷。见许处有酒兼有肉,煎鱘炒蟹,煨鸡炖鳖,杀鹅□面。牛肉大母块,狗肉大母碟,害得有声空嘴又哺舌,阮今爱吃又爱吞。
同样是目连的随同,却同样是毫无佛性,惦念食色,孙行者与雷有声的功能是基本相同的。他们都以反礼教、反佛性的叛逆形象出现,通过豪放、俚俗、幽默的语言,达到“取笑男女”之效果。
从“猴行者”到“雷有声”,《目连救母》与《西游记》曾在闽南超度仪式中有过如此精彩的汇流,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曾有日本学者发现,明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中称孙悟空为“雷公”,亦即将远古雷神信仰与孙悟空形象相融合,应当是西游故事在明代后半期进一步得到润色的结果。雷有声姓“雷”,而孙悟空亦在明代后期开始称为“雷公”,这究竟只是一种巧合,或者也能进一步说明个中渊源?关于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资料应证,笔者学力所限,只能姑且存疑。
其二,“猴戏”还展示了武术技艺,增强了仪式的观赏性。
“猴戏”的主角是孙行者,而其最大的特点除了个性鲜明,还有敏捷的身手与高超的武技。早在小说《西游记》出现之前,从中国传说中的水怪无支祁,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猴神阿努曼,再到目连救母中的白猿,无一例外都具备高超的武艺乃至神力。可以想象的是,当孙行者融入闽南超度仪式“打城”之中,这一角色也完全可以兼具展示武技的审美功能。这一点,可以在漳平“破砂墩”仪式中得到佐证。根据叶明生先生的调查,孙行者作“逃苔”(即“跳台”)之种种武功、杂耍,来显示其神通无比。如“打席花”(张开草席,以二指撑而施舞之)、“打席筒”(以草席卷之,两头以纸沾油点燃以舞之)、“打筛”(以原筛一个,人坐地上,一手撑于头上施舞之)、“窜桌”(从捆有尖刀的桌子上窜翻而过)、“筋斗”(作种种翻筋斗的动作)等等,这些节目既有娱乐观众的一面,也有显扬道法的一面,但它与宋杂剧中的百戏表演同出一辙。
值得关注的是,在漳州的另一个地区——东山县至今尚存的“和尚戏”,虽未出现猴行者一角,却也存在武技展示的因素。以上文所引“打火城”仪式为例,其中就有一个步骤是“舞杖花”。根据科仪本《火城全章》的提示,“舞杖花”具体表演方式如下:
行走四门,使各路拳杖,任由经师督驶武场。一到城门就举舞杖花,各施展拳术。或举屠虎伏龙步,或使龙戏水步,或表演双凤彩球步,或()鸦独步,以武杖拳打四门到底,长短不拘。锣鼓伴奏助威。
如果将清代地方志中描述的“猪猴搬演”,与“破砂墩”中孙行者的武技、“打火城”中的“舞杖花”相联系,再联想到近代厦、漳一带出现的以武戏见长的“戏盆”,直至当代打城戏“闽南猴王”展现的高超武技,则在仪式戏剧向成熟戏曲演化的过程中,武艺的展示从未间断过。2003年朱恒夫教授曾于美国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发现全本南音曲本《目连救母》,或许可以作为很好的旁证。书脊题为“新刻罗卜挑经救母全本,省城丹桂堂版”。该书分为四卷,64段,约3万字。其中卷三目录如下:
猿精把截 狐精缠卜 神救罗卜 狐精截路 猿精大战 猿精借宝 马康退兵 金星收伏 二精变战 目连脱凡 目连会佛 佛祖赐禅 刘氏起界 一殿发落 二殿治罪 三殿审究 四殿受苦 五殿定罪
从目录可知,南音曲本《目连救母》不仅保留了“猿精”的戏份,而且增加了不少打斗内容。“如《二精变战》,在猿精与众神将大战,因它变化多端而难以捕捉时,齐天大圣主动请缨,他‘驾起云中见得真,看见白猿云里躲,变成孤雁无人闻。齐天大圣忙来变,变成鸦鸟去追寻。飞上云中寻着他,想他难脱老猴人。白猿听到鸦鹰到,就知危险即忙奔。……大圣见他现本相,待吾亦现本原身,火眼金睛百慧生,金丝毛映神光闪,手持铁棍吓惊人。白猿得见他模样,知是齐天大圣身,心内已知无好意,事到头来只得行……’正本只有一个白猿精,被四大神将收伏,做了目连开路的先锋,而南音本又添上一个齐天大圣,并让齐天大圣收伏白猿精,实是一个猴精战胜了另一个猴精。”如果单独将此曲本与郑之珍本的《劝善金科》相比,上述情节的增加似显累赘。但若考虑到南曲之摇篮——闽南一带的“猴戏”渊源,则打斗戏份的增加并不是无中生有的。
四、结 论
综上所述,以孙行者为主角的“猴戏”,绝不仅仅成就了诸剧种以西游故事为内容的传统剧目,更曾在仪式戏剧的演进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对闽南超度仪式“打城”的考察可知,孙悟空、猪八戒曾是目连救母故事中的角色,既和目连一样具备超度功能,又独具丰富的艺术审美功能。一方面,通过孙悟空、猪八戒二人的滑稽调笑,很好地冲淡了丧葬仪式本身的悲伤气氛,也吸引了除丧家之外的大量观众;另一方面,扮演孙悟空者必具备高超的武艺,在护送目连的过程中适时展现武技,更增添了仪式的观赏性,打破仪式本身的沉闷与庄重。
由此可知,以“猴戏”作为切入点,有可能为考察宗教仪式向戏剧艺术的转化过程提供全新的思路。笔者才疏学浅,愿能抛砖引玉,引起方家对仪式戏剧更多更深入的探讨。
注释:
[1]陈多:《新世纪傩戏学发展刍议》,《戏剧艺术》2003年第1期,第104页。
[2]胡天成等:《民间祭礼与仪式戏剧》,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页。
[3]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福建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4][清]薛起凤:《鹭江志》,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 年。
[5][清]周凯:《厦门志》,清道光十年(1830),台北:大通书局,1984 年。
[6][清]林纾:《畏庐文集·诗存·论文》,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
[7][荷]龙彼得:《关于漳泉目连戏》,《民俗曲艺》第 78 辑,1994 年。
[8][17][22][30][33]叶明生:《道教目连戏孙行者形象与宋元<目连救母>杂剧之探讨》,《戏曲研究》第54辑,1998年。
[9]朱恒夫:《目连变文、目连戏与唐僧取经故事关系初探》,《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2期。
[10][11]刘祯:《中国民间目连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第305页,第289页。
[12]J.J.M.De Groot,Buddhist Masses For The Dead At Amoy,Leyde:E.J.Brill,1884.
[13]丁世良等:《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下)》,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206页。
[14]王馗:《香花佛事——广东省梅州市的民间超度仪式》,《民俗曲艺》第134辑,2001年。
[15]2009年3月21~23日,笔者前往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访谈“和尚戏”传承人——禅师释道裕。据释道裕所述,清代初年,东山岛铜陵镇(古称“铜坑”)古来寺住持释道宗创立“香花僧”一派,融武术于佛教法事之中,从事“反清复明”的秘密武装斗争。令人惊喜的是,东山岛“香花僧”与曾主持“打地狱城”的泉州开元寺渊源深厚。清初的泉州南少林,曾是进行反清复明的重要武装力量。而东山岛,是南明政权逃亡的最后一站,许多支持反清复明的武装分子都聚集于此并化身“香花僧”,其中应当有相当数量的泉州南少林武僧。后香花僧逐渐回传至泉州开元寺等地,并延承了香花僧以佛门法事操作为生的传统。几年前泉州承天寺还有一位老和尚是香花僧出身,现在已基本失传。据了解,目前闽南其他地区做超度仪式大部分请道士,只有东山岛仍然保持着请香花僧的习俗。如此看来,东山香花僧至今留存的一整套超度仪轨,应与“打地狱城”原貌相去不远。
[16][34]《火城全章》,东山县“香花僧”传承人之一杨天生先生提供,现藏福建漳州市东山县杨氏家族。
[18]苏警予等:《厦门指南》,厦门:新民书社,1931 年,第 8 页。
[19]《闽闻·石码·居丧演戏》,厦门:《厦门日报》1910年1月18日,第3版。
[20]根据曾学文先生对同安一带的老人们的采访,解放前同安流行的两种戏叫“大开元”“小开元”。“大开元”是从泉州开元寺传来的,由和尚组成的戏班,主要演武戏。遇到民间节日或宗教活动,还经常扮演水浒中的一百零八将踩街游行。而“小开元”是由“大开元”脱化初来,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戏文方面。大开元以演历史戏,小开元主要是演民间故事和《西游记》。老人口中的“大开元”“小开元”戏班,正是打城戏发展初期形成的两个著名班社。如果老人们所述的同安的两个戏班即是演出“猴戏”的戏班,那么曾先生的判断应当是有一定道理的。详见曾学文:《厦门戏曲》,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51页。
[21]郭英德:《世俗的祭礼——中国戏曲的宗教精神》,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37页
[23]笔者曾于2006-2008年多次前往泉州打城戏发源地之一——泉州晋江小坑园村进行田野调查,并对该村吴氏家族道坛“兴源道坛”的超度法事进行全程记录,详见骆婧:《戏曲剧种文化生态研究——以打城戏为个案》,厦门: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6月。
[24][唐]无名氏:《补江总白猿传》,朱玄一等编:《西游记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25][宋]佚名:《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朱玄一等编:《西游记资料汇编》,第38页。
[26][明]杨景贤:《西游记杂剧》,隋树森:《元曲选外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98 页。
[27][28][清]佚名:《目连救母》,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第十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第205~206页。
[29]泉州傀儡戏本《目连全簿》由《李世民游地府》、《三藏取经》和《目连救母》三部组成,打城戏曾完整移植该连台本。
[31]骆婧:《戏曲剧种文化生态研究——以打城戏为个案》,厦门: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6月,第82页。
[32][日]磯部彰:《元本<西游记>中孙行者的形成——从猴行者到孙行者》,《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19-320页。
[35]关于打城戏著名艺人、“闽南猴王”曾火成的高超武艺,可参见詹晓窗:《“闽南猴王”曾火成》,《泉州文史资料》第11辑(1982年6月),第135页。
[36][37]朱恒夫:《论戏曲的历史与艺术》,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170页,第171页。
〔责任编辑 吴文文〕
A Research on Ritual Opera in Southern Fujian:Speaking of Monkey Play and Lei Yousheng
Luo Jing
The Monkey Play used to be very popular in Southern Fujian.Lots of historical evidences see that the Monkey king used to convoy Mulian through the hell to save his mother during Salvation Ritual of Southern Fujian,suggesting that Monkey Play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Mulian Story and owned the function of salvation as well.Taking Puppet Opera and Dacheng Opera in Quanzhou for an example,the Monkey Pla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as entertainment and feat enjoyment in the process from ritual to opera.It shouldn't be ignored that there was a role called Lei Yousheng existing only in Quanzhou’s Puppet Opera and Dacheng Opera.His acting and character were almost the same with Monkey King’s,which suggests that Lei Yousheng may be the vestige of Monkey Play in history.
Monkey Play,Lei Yousheng,Dacheng Opera
骆婧(1982~),女,福建泉州人,文学博士,华侨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016年度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闽南戏文传播研究”(FJ2016C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