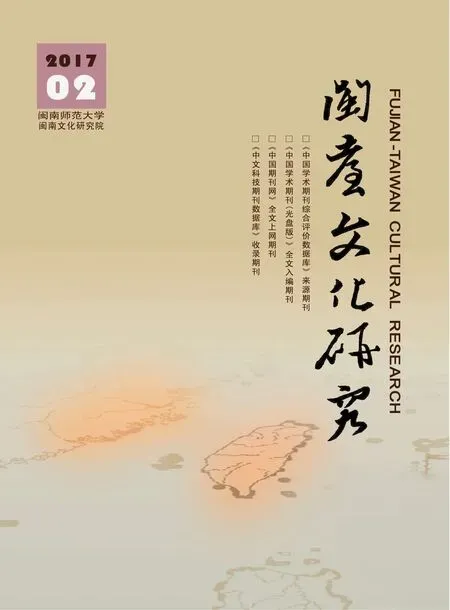论《荔镜记》中黄五娘形象的独特性
何丽娇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论《荔镜记》中黄五娘形象的独特性
何丽娇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荔镜记》是一部明代早期以青年男女的爱情与婚姻问题为题材的戏剧。它是陈三五娘故事戏文的现存最早刊本,也是泉州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戏文。《荔镜记》中的女主人公黄五娘与传统佳人形象的温柔敦厚背道而驰,可谓"七分泼辣,三分温顺",思想上敢于争取婚姻幸福,又有着浓厚的门第之见,是市井女性,同时也受到闽南地区质朴的现实主义精神影响。
《荔镜记》;黄五娘;现实主义
嘉靖丙寅(四十五年,1566)余氏新安刻本《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是关于“陈三五娘”故事现存最早的戏曲刊本,共五十五出,也是现存最早的分出标目的完整剧本。剧本用泉州和潮州方言混合写作而成。由于地方方言的局限以及刊本的粗糙使得以往学术界对《荔镜记》的研究很不够,近年来《荔镜记》的价值被不断挖掘和彰显,关于《荔镜记》的研究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研究者多从方言、音乐、或者涉及《陈三五娘》戏曲表演的角度论及《荔镜记》,而对于《荔镜记》的文学性研究却不多,对于《荔镜记》中的女主人公黄五娘的形象研究已有多篇文章论及,但还未有专文讨论黄五娘形象的独特性以及形成这种独特性的原因。论及黄五娘形象的文章主要聚焦于她对自由爱情的讴歌,对封建礼教的反叛,自身性格上的泼辣,而黄五娘身上有着浓厚的门第之见,这一面却较少有人关注。这种独特性与以往才子佳人题材的戏剧作品中的佳人形象如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白朴《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以及南戏代表作品《拜月亭记》中的王瑞兰相比更为凸显。
一、黄五娘的人物形象
在古典戏曲作品中,以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婚姻问题为主题的有很多。《荔镜记》对于追求自由爱情的赞美,比起许多其他同类作品来,表达得更加大胆和强烈。陈三由于钟情五娘,自愿卖身为奴;五娘为了摆脱包办婚姻,以私奔求自由。元杂剧和南戏以及传奇中也有众多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也塑造了很多成功的才子佳人形象,黄五娘是当中独特的一个,她是富家千金,行为举止与思想却又不像一位大家闺秀。为了说明她的独特性,下文将把她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墙头马上》的李千金以及《拜月亭记》中的王瑞兰作一对比。同样是小姐,同样是佳人,却不尽相同。
(一)七分泼辣,三分温顺
《荔镜记》中的女主人公黄五娘,在作者构织的戏剧冲突和人物行动中,显示了她的独具的性格。这种性格和温柔敦厚的封建标准背道而驰,越过了大家闺秀的规范,用“七分泼辣,三分温顺”形容也不为过。她本是一位富家千金,“挑花刺绣,琴棋书画,诸般都晓”,也十分守礼,当李婆邀她上街赏花灯时,她以“妇人之德,不出闺门”为由拒绝;后来答应与李婆赏花灯时又以“妇人夜行以烛,无烛则止”约束自己,颇有大家闺秀之风范。但当她得知父母收下林家的聘礼,准备将自己嫁与林大,媒婆前来送金钗时,她的泼辣性格暴露无遗。主要体现在第十四出《责煤退聘》中。当李婆请五娘收下林家的金钗时,五娘说:“值人收只金钗发狂病。”并踩踏金钗。作为养在深闺的小姐,她无法阻止别人来求亲、更无法预料父亲是否应允,当她心有所属而父亲将其另外许配的时候,她愤怒、无助、怨恨而无从发泄,便将所有的负面情绪发泄在媒婆身上,于是便有了打骂媒婆这一情节。自古待嫁女子为求取一段好姻缘而不敢轻易得罪媒婆,即使对婚事不满意,以五娘知书达理的富家小姐身份,也不该如泼妇般打骂媒人,其泼辣性情由此可见一般。同样是封建社会里以“情”反“礼”的典型,崔莺莺就表现得十分温文尔雅,她在爱情的表露上虽然大胆,却仍具有相国小姐端庄、含蓄的一面,大胆而不失一定分寸,性格趋于内向。而同样是为了爱情私奔的李千金也表现出了大胆率真、勇敢泼辣的一面。她的泼辣不同于五娘性格中的处事言语的泼辣,更多的是一种敢作敢为的气质。当千金与少俊幽会的事被李嬷嬷撞破,当李嬷嬷斥责梅香帮忙穿针引线,千金却勇于承担责任,说嬷嬷“枉骂她偷寒送暖的小奴才”,误会了梅香。做此事“是这墙头掷果裙钗,马上摇鞭狂客。”自己做事,敢作敢为。这胸怀是多么坦白直率。嬷嬷进一步恶言恫吓,还要送官问罪,千金也毫不畏惧,慷慨陈词,为他们的正当结合辩护,说:“龙虎也招了儒士,神仙也聘与秀才,何况咱是浊骨凡胎。”以龙虎做陪衬,以神仙做对举,从而维护了自身追求爱情的合法权益。进而要解下搂带裙刀,以自杀相威吓。这一招倒真让老于世故的嬷嬷手足无措。这种泼辣,这种胆识,与五娘颇有几分相似。
(二)男婚女嫁,需论高低
黄五娘在《责媒退聘》一出中喊出了一句“姻缘由己”。她不被“父母之命,媒妁之约”所约束,认为个人有追求姻缘的权利。五娘的择夫标准就是“贤”,她认为嫁一个人,并非要看对方是否大富大贵,因为富贵是说不准的。在她看来林大是流薄之子,把她嫁给林大是害她。在这里五娘就如一般的富家或官家小姐,对于另一半的钱财、身份地位是轻视的。可是到后来陈三入黄府为奴,几次与五娘说到自己就是马上官人,并有荔枝为证,五娘起初不信,看到荔枝后又说自己当初是错手投荔枝。按理说,她看陈三的长相与那日登楼看到的马上官人相像,却三番两次不肯认他,经常称呼他为“贼奴”。原因是陈三现在只是黄府的一个奴仆,一个千金怎能与一个奴仆结合?剧本中多次强调陈三是“官荫人家仔”,并把它作为陈三赢得五娘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因为五娘确认了陈三是“官荫人家仔”,她才愿意接受陈三,并毅然与陈三私奔。她嘴上说的是“女嫁男婚,莫论高低”,行动上又处处表现出“女嫁男婚,需论高低。”这就不大同于以往戏曲作品中的小姐形象。一般来说,戏曲作品中的小姐形象对待功名利禄的态度是不屑的。比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身为相国千金,她不爱与自己门当户对的郑桓,却爱上一个穷书生。她追求的只是爱情。她对张生的爱,纯洁透明,没有一丝杂质。当张生被迫上京考试,她悔恨的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两下里”;长亭送别,她给张生把盏时的感触是:“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给张生最郑重的叮咛是:“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担心的是张生不像她那样爱得专一,一再提醒他“若见了异乡异草,再休似此处栖迟。”总之,在她的心中,“情”始终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至于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管。这样的思想,既不同于《西厢记》里的莺莺,也不同于元杂剧中许许多多追求夫荣妻贵的闺秀,她是一个赤诚追求爱情,大胆反抗封建传统的女性形象。李千金,身为总管之女,出身高贵,当她第一次与裴少俊幽会时,裴少俊说:“小生是个寒儒,小姐不弃,小生杀身难报。”李千金则只回他六字:“舍人则休负心!”并毅然与他结合,这也是一个不问出身,心中只有爱情的小姐形象。《拜月亭记》中的王瑞兰也是如此,她出身于高贵门第,是兵部尚书的千金小姐,而蒋世隆不过是一名秀才而已。战火使这对青年偶然相遇,也使他们之间产生了患难与共的爱情。王瑞兰并不在意蒋世隆的社会身份不高,毅然与之结合。王瑞兰不慕富贵,她说:“那玉砌珠帘与画堂,我可也觑得寻常”。她决不肯抛弃陷入困顿的丈夫而嫁作他人妇,“我宁可独身孤孀,怕他待抑勒我别寻个家长,那话儿便休想!”她对蒋世隆的爱情不是建立在富贵功名的基础之上,而是一种患难中建立起来的矢志不渝的真情。在对比之下,黄五娘这个人物形象就多了几分市井女性的气息,少了几分大家闺秀的单纯。
(三)富有主见,敏感多心
黄五娘是一个很有主见,又敏感多心的人。她不喜欢林大,就踏坏林家送的金钗,打骂媒婆,为了反对这桩婚事,甚至还打算跳井自杀。当她登楼排遣烦忧时看见马上官人,毫不犹豫地将荔枝抛向他,以示自己的爱慕之心。她在选择自己的伴侣时是非常有主见的,不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又是一位敏感多心的女性,她的敏感又侧面透露了她内心非常缺乏安全感。戏中用一连串精彩的剧目生动地刻画了五娘的心理活动。当她也觉得陈三与马上官人相像时,她不敢与他相认,怕的是:“是我当初亲看见,我一心恐畏只人不是”,“恐畏世人相亲像,又畏人乘机来假意。”当陈三拿出荔枝时,五娘又予以否认:“是我错手投荔枝。”她不敢轻易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自己的意中人。等她终于认定陈三就是意中人,准备托付终身时又犹豫了,她害怕陈三有家室,怕误了自己一身,之后又经过重重的试探、反复,内心经历了苦苦挣扎才终于认定陈三。戏曲史上,很少有剧作者能把女性的这种敏感性格的过程丝丝入扣地表现出来。张生被迫上京赶考,崔莺莺与他分别时万分不舍,虽也十分怕他得了功名抛弃自己,却也没让张生起誓,只是告诉他若见了异乡花草,也勿将她抛在脑后,在他处栖迟。同样是为爱情私奔,李千金的表现却与黄五娘大相径庭。李千金只凭着一面之缘就断定裴少俊就是日后所托付的对象,为了这一见所钟之情毅然选择与裴少俊私奔。裴少俊并未给她承诺,从后面裴少俊将千金藏在裴府后花园七年可知。这种行为是大胆的,甚至可以说是草率的,她也最终因为自己的冲动得到了一纸休书。相比之下,五娘的敏感多心是比较真实的,更符合一般女性的细腻性格。
二、黄五娘形象呈现出独特性的原因
在上述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黄五娘独具的性格和思想。尤其是第一、二点。她的性格与传统的温柔敦厚背道而驰,行动是大胆的,性格是泼辣的,思想上既是自由的又是重视门第之见的。她更像一位现实生活中的富家小姐而迥异于文人笔下的小姐形象。论及黄五娘形象所呈现出的独特性时,大部分学者都将原因归于地域文化的影响。《荔镜记》作为闽南文学的代表作,的确深深烙印上了闽南文化的印记。如宋妍在《从<陈三五娘>看闽南文化的特性及其形成原因》一文中认为《陈三五娘》的人物形象体现了闽南文化的特性:崇儒与远儒、保守与开放、遵礼与反叛、精英情结与草根意识的辩证统一。她认为五娘对于陈三的反复试探与是否和陈三约定终身的徘徊折射出闽南人质朴的现实主义精神,不过并未对这种质朴的现实主义精神展开说明。刘婷婷的《<荔镜记>考论》也提到五娘对陈三官荫子弟的反复确认体现出闽南市井百姓的性格特征:现实。孙佳佳《明嘉靖本<荔镜记>戏文研究》一文认为《荔镜记》体现了非精英化的市民文化本质,尤其是对于“门第观念”的强调。笔者认为黄五娘身上所表现出的大胆泼辣与浓厚的门第之见不仅仅体现了民间文学视野下的市井女性的独特面貌,还折射出闽南文化中的质朴的现实主义精神。
(一)民间文学视野下的市井女性
戏曲相对于诗、词等文学形式而言,一直被作为是俗文学的代表。这并不代表所有的戏曲作品都是通俗的文学,不同的戏曲形式之间存在着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的对立、融合。比如在元代的发展达到繁盛的杂剧与南戏。从杂剧说起。在元代,杂剧的创作达到了极度繁盛。与宋朝南戏在文人中遭受冷遇的情形不同,元代的杂剧创作引起了饱学士子们的普遍重视,有大量士人一转以往所持“词曲小道”的传统文学观念,将兴趣的精力投到杂剧创作中来,这造成元杂剧作品文化层次的迅速提高,使之升华为称雄一世的时代文体。元杂剧的创作主体是士子文人,他们拥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艺术才华。比如王实甫,他笔下的崔莺莺就“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一位温柔敦厚的大家闺秀。大量士人转向杂剧创作,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和汉族文人失去了仕进之路,又别无谋生之途,便纷纷把精力和才华投入到戏曲创作中去有关,但它客观上促成了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元杂剧虽说也是俗文学,但是它较多地带着文人作家的世界观和审美观的影响。由于元杂剧本身的体制结构的限制以及内容方面的日见贫乏,元杂剧慢慢走向衰落。而这个时候,由于农村经济的发达和传统伎艺的深厚,发源于民间歌舞小戏的南戏慢慢发展壮大。南戏的作者远没有杂剧作家那么幸运,他们很少有名字留下来,因为这些作品大多都是民间作者所写,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钱与权,因此被历史所忽略、所遗忘。南戏的内容大多以反映社会生活、阶级矛盾为主,风格朴素本色、鲜活清新,洋溢着世俗化的审美情趣,而不同于元杂剧的温雅博约。由于时代的不同、社会环境、作者身份等的变化,南戏到了明清时期,也发生了一些分流,分化为民间南戏(传奇)与文人南戏(传奇)两大类。《荔镜记》就属于民间南戏。
民间南戏的特点是重视剧作的故事情节,注重题材的可看性,且大多取材于民间的传说故事,而且会按照民间观众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进行改编与创作。民间南戏的作者大多是民间艺人和下层文人,他们创作的目的大多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审美趣味,使表演的剧目能有市场收益。这样的民间戏剧大多也采用民间叙事的方式。民间叙事是与文人叙事相对立的概念。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最大之差别是俗与雅的分野。民间叙事俚俗粗浅、本色自然,重感观刺激和世俗谐趣;文人叙事则文采典雅,婉曲蕴藉,重精神愉悦和诗意神韵。黄五娘于崔莺莺,同样是反抗封建礼教的典型,一俗一雅,一端庄一泼辣,正是体现了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的不同。黄五娘是商人之女,可以说是当时兴起的市民阶层的代表,她敢于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敢打骂媒人,在对陈三的种种试探中表现出她的富有心机,体现出市民阶层女性的大胆与泼辣,自主与叛逆。她认为“鹦鹉能言争似凤,蜘蛛虽巧不如蚕”,即使鹦鹉再能言善辩也比不上凤凰,蜘蛛虽能拉丝,可比起蚕就差远了。门第比外貌、才情都重要得多,这也体现出市民阶层的固有的封建价值观。市民阶级是一个新兴的阶级,对于社会人生,有着从他们这个阶层出发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他们较多处于社会的中、下层,需要依靠自己努力的拼搏来维持、提升、改善他们的生存处境,即使是出身比较优越的,也多以维持自身的利益与处境为出发点。他们的人生理想比较少有超越性的追求与普世的关怀,他们在一种比较庸常的市井生活中寻求、展开他们的愿望与追求,他们不掩饰自己的功利追求,比较注重现实的利益与现世的安乐。黄五娘对于陈三身份的多番考证,经过重重试探、权衡利弊后才与之定情就体现了市民阶层努力维持自身利益、地位的特点。《荔镜记》这部民间戏剧正是用民间叙事的方式表现了市民阶层的的人物形象、思想和价值观。在上层文人看来,一个女子对男子的感情若是建立在功名富贵上定是庸俗的,对于这样的女子是排斥的,他们对于黄五娘这样的形象大抵是不认同的,但是在下层百姓看来,一个貌美的女子与一个“官荫人家仔”的结合是喜闻乐见的,是符合他们的审美习惯的。他们乐于看到黄五娘跟了气度不凡,仪表堂堂的官家子弟陈三,而不是气度不凡,仪表堂堂的黄家奴陈三。不仅仅是《荔镜记》,明前期民间戏剧中的爱情剧,从故事情节到人物形象,均按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加以创造,完全不同于文人笔下“男以才雄、女以貌胜,花园邂逅,一见钟情”的模式。
(二)闽南文化中质朴的现实主义精神
《荔镜记》作为一部闽南地区的地方戏曲作品,剧中处处彰显着闽南文化。比如戏曲开头的元宵灯会就是闽南地区的特色民俗。元宵被闽南地区的民众视为一个盛大的节日,有赏花灯、踩街等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而剧中的人物形象也深受闽南文化的影响,黄五娘之所以与众不同也正是因为她是一个典型的闽南女子。
陈世雄、曾永义主编的《闽南戏剧》中提到:“闽南文化是一种二元结构的文化结合体。这种二元文化结合体既向往追寻中华的核心主流文化,又在某种程度上顽固地保持边陲文化的变异体态;既依归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文化体制并积极为之作出贡献,又不时地超越传统与现实的规范与约束。”关于闽南文化的类型,论者纷纭,大致有三种意见:1.闽南社会是源之于中原的移民社会,闽南文化在本质上是随同移民携带而南播的中原文化,是一种大陆文化。2.闽南文化是一种海洋文化,这种海洋性在繁荣的海外贸易、海上生活中逐渐成为闽南文化的主要特征。3.闽南文化是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是从大陆文化向海洋文化过度的多元交汇的“海口型”文化。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更为准确、客观。任何一种文化都不会孤立的存在,都难免受到地理环境的变化与外界的影响,这种影响或主动或被动。如刘登翰先生总结的那样,闽南文化呈现出“崇儒”与“远儒”的辩证统一。“崇儒”即对儒家文化思想的崇拜与信仰,而“远儒”则表现出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漠视与背离。《荔镜记》中体现“崇儒”现象的代表人物正是升任为广南运使的陈三的兄长陈伯延,在《送哥嫂》一出中,他苦口婆心地以“世上万般皆下品,算来惟有读书高”来劝勉陈三早日考取功名光耀门楣,后来听说陈三与五娘之事后痛骂陈三“禽兽”,认为其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儒家传统礼法,败坏门楣,这便是“崇儒”的体现。“即便是男女主人公陈三与五娘,亦在言行举止之间流露出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敬畏与矛盾之心”,因此五娘对于陈三若即若离、反复试探,不敢轻易托付终身也是出于对儒家礼法制度的畏惧。同时,“远儒”思想又在这部戏中大放异彩,这种思想又主要集中在五娘身上。闽南地区由于在地理上远离政治中心,也就远离儒家文化的中心,使得该地区较少也较晚受到儒家正统文化的约束、规范与教化,从而表现出更多的非正统、非精英化的文化特征。在地理环境上,闽南地区多丘陵山地,少平原,地瘠民稠,严酷的自然环境,移民的生存意识,共同孕育了闽南文化的务实精神。濒临海洋的地理位置带来的海上贸易的繁荣又弥补了农耕经济的不足,形成了闽南人重商逐利的特点。这种特点体现了闽南人更重物质利益和改善生存条件的价值体系,也形成了闽南人现实功利的性格特征。用朱双一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与中国北方的粗犷豪放、江南的婉转细腻相比,处于中国东南边陲的闽台地方文化或可用粗砾朴实来加以形容。或者说,闽台地方文化具有一种朴拙之美,充满粗野灵动的生命活力,可说是一种质朴的现实主义。”陈三与五娘身上都体现着这种现实主义精神。五娘敢于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说不,在对自己的婚事抗议无效后打算跳井自杀,敢于向自己的意中人抛荔枝以示爱,与陈三定情后又决定与之私奔,都可以看出她的大胆、坦率、冒险的性格。但是,她的性格又不仅仅如此,还有着现实、理性的一面。在她还未完全相信陈三之时对陈三身世反复询问与试探,剧中《打破宝镜》《陈三扫厅》《梳妆意懒》等三出戏细腻地描绘出五娘试探的心理。后来五娘目睹自己抛下的手帕和荔枝在陈三身上,这才确定陈三正是“灯下官人”。然而,这并未给五娘吃了一颗定心丸,在《园内花开》《五娘刺绣》两出戏中,五娘又进一步主动了解了陈三的身世、家庭背景,这些都证明五娘要托付终身的是官荫子弟陈三,而不是黄家奴陈三,在没有确定陈三的身份前,她是不会贸然行动的。她的性格是复杂的,丰满的,既是勇敢自由的,也是现实理性的,体现出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的理想主义情怀不同的性格特征,折射出朴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五娘的性格更符合一个闽南人的性格特征,更贴近生活实际,也体现着闽南文化的多元性。
《荔镜记》这一才子佳人剧是前代同类故事的积淀,黄五娘这一人物形象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对前代同类故事中佳人形象的继承和发展。笔者在文中多次强调黄五娘这个人物形象的独特性,是以元杂剧、文人南戏为代表的文人戏剧中的女主人公为参照的。在民间戏剧中,还有很多个“黄五娘”,她们是下层文人或民间艺人所塑造出的市民形象的典型,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市民阶层的某些特点。
《荔镜记》是民间戏剧文学中的佳作,雅俗交融,生动地体现了民间文学的本质体征,同时也是闽南文学中的经典名剧,在闽南文化圈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剧中深深烙印着闽南文化的印记,女主人公黄五娘大胆泼辣、现实理性的性格特征与传统温柔敦厚的佳人形象背道而驰,折射出闽南文化中质朴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精神与闽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移民历史以及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荔镜记》蕴含了闽南文化的特性,促进了闽南文化的传播,是闽南文学的一朵奇葩。
注释:
[1]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第69页。
[2][3][4][5][20][21][27]泉州市文化局、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合编:《荔镜记荔枝记四种》,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第244页,第247页,第247页,第254页,第277页,第278页,第266页。
[6]孙佳佳:《明嘉靖本<荔镜记>戏文研究》,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7页。
[7][8][9][16][17](明)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38页,第338页,第338页,第337页,第337页。
[10]魏永贵:《一枝独秀占尽春色——读白朴<墙头马上>李千金形象的塑造》,《集宁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第17页。
[11][12][13][14](明)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西厢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3页,第152页,第153页,第154页。
[1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36页。
[18][19]张月中、王钢:《全元曲(下)》,郑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9 页。
[22][32]宋妍:《从<陈三五娘>看闽南文化的特性及其形成原因》,《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23]刘婷婷:《<荔镜记>考论》,泉州: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4]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简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25]俞为民:《南戏流变考述——兼谈南戏与传奇的界限》,《艺术百家》2002年第1期。
[26][29]王夔:《明前期民间戏剧研究》,合肥: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31页,第28页。
[28]黄文娟:《论梨园戏小梨园的市井文人价值取向——以<陈三五娘><董生与李氏>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30]陈世雄、曾永义:《闽南戏剧》,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
[31]刘登翰:《论闽南文化——关于类型、形态、特征的几点辨识》《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33]朱双一:《台湾新文学中的“陈三五娘”》,《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3期。
〔责任编辑 吴文文〕
The Uniqueness of Huang Wuniang in the Drama Lizhi and Mirror
He Lijiao
The drama Lizhi and Mirror is about love and marriage of a young couple in the early Jiajing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It is the earliest edition of the story of Chen San and Huang Wuniang,also the earliest operas known in the Quanzhou region.The heroine Huang Wuniang,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beauty image,is fierce and tough,bold to strive for happiness.On the other hand,she has a strong view of the family status.She is a urban woman in the works of folklore,which is influenced by the realism of Southern Fujian.
the drama Lizhi and Mirror,Huang Wuniang,realism
何丽娇(1992~),女,福建泉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