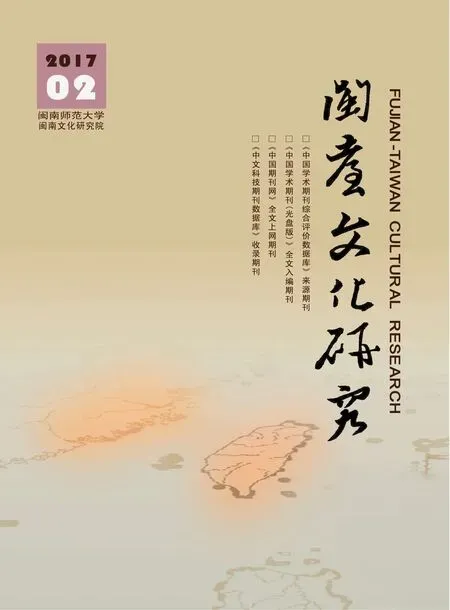陈景肃与漳州理学渊源论略
郑晨寅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闽学与闽南文化研究中心,福建 漳州363000)
陈景肃与漳州理学渊源论略
郑晨寅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闽学与闽南文化研究中心,福建 漳州363000)
陈景肃是漳州理学之承先启后者,与朱子学派关系密切。其师高登以慎独为本,气节凛然,朱熹称之为“一世之伟人”;陈景肃石屏书院弟子杨士训后来亦成为朱门弟子;陈景肃同门林宗臣引导陈淳入朱子门下;陈景肃之孙陈植则求学于陈淳,并在南宋倾覆之际积极进行抗元活动,事不济而退隐漳南,其弟陈格则从容殉难。陈景肃之学术旨趣与程朱之学略近,高登、陈景肃之高行博学为漳州理学的兴起提供了人员上、思想上的准备。
陈景肃;高登;朱熹;漳州理学;渐山七贤
漳州先贤陈景肃生活在南宋建炎至嘉泰间(约1130~1203),其所生活、讲学地区主要位于漳州诏安、云霄一带,宋时隶属漳浦县管辖,故后之《漳州府志》《漳浦县志》《诏安县志》《云霄厅志》乃至《平和县志》《南靖县志》等皆有载。关于陈景肃,最早的省志记载见于弘治《八闽通志》:“陈景肃,漳浦人,绍兴间进士。师事高登,有学行。官至朝请大夫、知南恩州。”最早的府志记载则见于正德《漳州府志》:“陈景肃,漳浦人,师事高东溪,有学行。知仙游县,有陈亨运者,父母没,庐墓三年,时馈粟以旌之。后知南恩州。子宰,孙植,皆以遗泽补官。”光绪《漳州府志》本传较详,兹引如下:
陈景肃,字和仲,漳浦人。唐将军陈元光裔孙也。师事高登,有学行。尝同秦梓出使燕赵,归,表为祈请使,不拜。归,讲学于仙人峰下。登绍兴进士,令仙游,多美政。寻提举湖南,除知南恩州。诏入知制诰,以秦桧故,不拜。出知台、湖等州。题咏多讥刺,桧党恶之。乞归,与门人杨士训、吴大成等讲学渐山。桧死,议均役,复知制诰。致仕时,已八十余矣。适南恩州叛服不常,择使宣慰。朝议非景肃不可,令持节往,岭南遂平。卒赠光禄大夫、资政殿大学士,谥廉献。所著有《撷翠集》若干卷。孙植、格。
由上可知,陈景肃是漳州文化史、理学史上的承先启后者:首先,他是开漳将军陈元光裔孙(开漳陈氏第十九世),其讲学(石屏书院)直承陈珦松洲书院讲学一脉;其次,他师事爱国志士高登,与秦桧党人展开坚决斗争,是闽南地区文人集团(渐山七贤)之首领;再次,他为官多美政,遗泽一方,是能臣廉吏的典范,由“廉献”之谥可见之;最后,他与朱子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漳州理学发展中地位特殊。本文即拟对陈景肃与漳州理学的关系进行讨论,以就正于方家。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旨在梳理闽地理学(儒学)源流,《四库全书》“提要”称其“四五百年之中,寻端竟委,若昭穆谱牒,秩然有序”,本文在叙述脉络上即拟以其为依据。
一、陈景肃与闽中理学之“高东溪学派”
理学产生于北宋,乃源于儒家精英应对时局、重建政治、文化秩序的需求,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漳州建州始于唐垂拱二年(686),自宋以来中国文化重心南移,漳州文教亦逐步发展;朱熹知漳后,在漳州兴教、传道、授业,开启后学,漳州理学自此兴盛。理学亦有“道学”之称,以接续、弘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为己任;又于《五经》之外,更推重《四书》为新经典。据此观之,在朱熹之前,已有漳浦蔡元鼎“著有《中庸大学解》《语孟讲义》”龙溪颜慥“倡明道学”,皆为漳州理学之先声。而“清漳黄氏家世学派”包括黄彦臣、黄硕、黄颖、黄樵仲(朱熹学友)、黄櫄,乃《闽中理学渊源考》所载漳州一地最早之学派;其后则有“高东溪学派”。
(一)“一时倡起之师”:高登
高登(1104~1159)字彦先,号东溪,漳浦人。宣和七年(1125)金兵犯京师,他与太学生陈东等联名上书,请诛蔡京等六贼,名震天下,因极意尽言、讥刺秦桧,屡受摧折,乃至编管容州,至死不忘天下苍生,其事迹见诸《宋史》《漳州府志》等。《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四《承务郎高东溪先生登学派》载:
漳江之学,至北溪得紫阳之传而递衍繁盛,然在靖康间时有东溪高先生者,以忠言志节著声。朱子莅漳,曾新其祠宇,又为之记,言:“先生学博行高,志节卓然,有顽廉懦立之操。其有功于世教,岂可与隐忍回护以济其私、而自托于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语哉!”按:东溪之学,亦一时倡起之师也。
指出在朱熹知漳、陈淳受学之前,高登为清漳一地“一时倡起之师”。《宋史》称“其学则以慎独为本”,《漳州府志》称其处容州时,“执经相从者数百人,登为讲明《大学》、《中庸》之旨”,其学术概可知矣。《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实乃源于对“天道”之体认,在理学视域中,这种内在的体认必须与道德实践相表里。《四库全书》收录有林希元所编《东溪集》二卷,内有《慎独斋铭》,其铭曰:“其出户如见宾,其入虚如有人,其行无愧于景,其寝无惭于衾,请事斯语,无怠厥终。”而其生平气节凛然,令人闻风兴起,四库“提要”称其“忠君爱国之心,每饭不忘如此”。朱熹《乞褒录高登疏》称其“资禀忠义,气节孤高”,《高东溪祠记》则称其“学博行高,议论慷慨”“可谓一世之人豪”,《谒高东溪祠文》乃至称其“所谓一世之伟人,非独一乡之善士也”,给予极高的评价。
(二)“东溪学派”:黄京、林宗臣、杨汝南
《闽中理学渊源考》之“高东溪学派”除高登本人外,仅列门人林宗臣、友人黄京二人,不及于陈景肃(当是因另立有“清漳陈氏家世学派”)。《八闽理学源流》所列高东溪门人则为陈景肃、林宗臣二人。《漳州府志》等又提及杨汝南。以下分别略论之。
据《闽中理学渊源考》“高东溪学派·户曹黄叶叔先生京”载,黄京字叶叔,龙溪人,为官清白,乐善好施,与高登志同道合,“闻登以直言斥,恬无仕进意”。
龙溪杨汝南字彦侯,师事李则,亦以高登为师友,《漳州府志》“高登传”、《东溪集》附录“东溪高先生言行录”皆称:“杨汝南、陈景肃皆师之。”而《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四“县令李康成先生则学派·县令杨彦侯先生汝南”则称其“与庐陵杨万里以节义相勉,与高登尤相友善”。杨汝南摭《诗》《春秋》《中庸》要语著《经说》三十篇以授学者,正德《漳州府志》又曰:“尝扁其所居堂曰‘不欺’,自号快然居士。盖人惟不欺则仰不愧、俯不怍,心自快然,此其学为有本也。”《孟子·尽心上》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为君子“三乐”之一,杨汝南以“快然”自号,又匾其堂曰“不欺”,与高登之“慎独”庶几近之。
《闽中理学渊源考》“高东溪学派·主簿林实夫先生宗臣”则载:
林宗臣,字实夫,龙溪人。乾道二年进士,受业高东溪登之门,官至主簿。一见陈安卿淳,心异之,谓曰:“子所习科举耳,圣贤大业则不在是。”因授以朱文公所编《近思录》。安卿卒为儒宗,实夫启之也。
事实上,直至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由于朱熹等人的大力提倡,程氏之学才开始盛行,从授陈淳以《近思录》可以看出林宗臣与道学精神之相契合,其引导陈淳入道之功不可没。
(三)陈景肃《怀高东溪》诗
以上为“高东溪学派”之大概。东溪学派成员主要来自龙溪、漳浦等地,其学主于《大学》《中庸》,以慎独为本,其行皆重气节、尚忠义,然则陈景肃之师友渊源、学术背景亦可略知矣。《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二有“清漳陈氏家世学派”,称:“廉献陈氏出东溪高公之门,亦以直节著声者。”其受高登忠义直节之影响极为明显。陈景肃有《怀高东溪》二首,兹录如下:
凿泉莫太深,太深井难汲。
登山莫太高,太高顶难立。
山顶仰可观,井渊俯可挹。
那知鸿鹄飞,海杳无消息。
谔谔东溪士,吹箫涧谷春。
一别阻云水,相思劳梦魂。
五湖秋夜月,三岛春空云。
璚标月夜见,玉唾云间闻。
何当一返驾,吟弄终乾坤。
此二诗皆表达了陈景肃对高登的敬慕之意与思念之情。第一首有颜渊“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欲罢不能”之叹(参见《论语·子罕》);第二首“谔谔”一词则出自《史记·商君列传》“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以及《韩诗外传》卷十“有谔谔争臣者,其国昌;有默默谀臣者,其国亡”诸语。一句“谔谔东溪士”,正刻画出高登直言谏诤之风范,亦可见陈景肃之怀抱。
二、陈景肃与“陈氏家世学派”
《闽中理学渊源考》“清漳陈氏家世学派”分“家学”“学派”二者,“家学”列其孙陈植、陈格二人;“学派”列杨耿、吴大成、薛京三人,则应有所补充。
(一)“陈氏学派”:“石屏书院”与“渐山七贤”
“清漳陈氏家世学派·杨国光先生耿”如下:
杨耿,字国光。绍兴中,在太学与吴大成、郑柔、薛京齐名。秦桧柄国,耿等相率乞归,从陈景肃讲学渐山石屏书院。辟精一堂于修竹里,讲明经术,从子士训、士谦皆从之。所著诗多寓言,而忠爱之意宛然如见。
此处所列杨耿、杨士训、吴大成、郑柔、薛京皆为陈景肃弟子,讲学地点在石屏书院,此六人加上翁待举,则为后人所称之“渐山七贤”,石屏书院也成为漳州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中心。
漳州最早的书院乃开漳刺史陈元光之子陈珦所创建之松洲书院,有“八闽第一书院”之称。两宋时,士人多利用书院讲学,书院逐渐成为讲明义理、培养人才之重要场所,但由于北宋的文化中心在河洛一带,“道南”一脉又主要在闽北传播,因此漳州的书院寥寥无几。故作为陈氏后裔,陈景肃之石屏书院可谓直承松州书院一脉。《漳州府志》载:“石屏书院,在四都渐山之麓,宋陈景肃讲学处。”据前引《漳州府志》本传载,陈景肃登进士第前曾“讲学于仙人峰下”,恶秦桧乞归后又“讲学渐山”,故知陈景肃讲学处(石屏书院)实有两处,一在今云霄县仙人峰,一在今诏安县渐山。二者相距不远,陈景肃《石榴洞赋》称:“渐山去仙人峰二十余里……向西为梅港,吴大成之小洲也,东曰竹港。”故移于此地讲学或亦与吴大成有关。
“清漳陈氏家世学派·吴子集先生大成·薛宗汴先生京”又载:
吴大成,字子集,漳浦人。闻陈景肃师事高登,学有渊源,往受业焉。尝游太学,论旧相张浚清忠,与秦桧忤。及廷对,语多侵时宰,桧益恶之,落第。自以终不能为桧屈,归隐渐山石榴洞,讲明正学。乾道中,奉檄湖湘,往还京浙。著有《梅月诗集》,又有《笔义》、《经疑传稿》藏于家。
薛京,字宗汴,与郑柔俱师事陈景肃,肃与秦桧忤,辞知台州,京亦乞归省,桧以其为景肃党衔之。归,与吴、郑、诸杨讲学渐山、九侯间。赋诗自乐,终桧之世,屏迹不仕。
由上可见陈景肃师徒诸人已成为当时朝廷的一股清流,引起秦桧之忌恨。石榴洞、石屏书院皆在渐山,九侯山亦为诏安名胜。《漳州府志》“吴大成传”则称:“景肃卒,为作茔域,心丧三年。”师门风义概可见矣。
《漳州府志》又载:
郑柔,字克刚,诏安人。绍兴中在太学,与时相秦桧、汤思退左。尝建议乞决意北伐,为汤思退所阻。调高要簿,不就,归隐九侯山。所著有《康正题咏》,时甚重之。
翁待举,字至德,先京兆人,徙居漳浦。于时方行舍法,惟待举文字拔出时髦,登政和二年进士。绍兴中知兴化军,不入内寝,夜五鼓辄披衣起,自以瓦釜煮粥啖之。就灯下读《中庸》一遍,乃出莅事。或有干以私者,曰:“某一秉判笔,如见神明罗列其旁。”干者缩舌而退。尝奏蠲本军诸色钱、渔人所输税及浦生之草采者毋出钱,兴化人德之。祀名宦。知琼州,卒。
杨士训,字尹叔,漳浦人。父成大,乡贡士,早世。事母至孝,庐墓三年,哀毁惨切,须发为白。士训性醇静警敏,自刻益励,常从学于陈景肃。及朱文公守漳,置宾贤斋,择士之志学者处之。士训年最少,预焉,称其“学已知方”。郎中王遇见而异之,妻以女。所居号“盘庵”,学者不远百里从之。庆元二年擢进士,调古田尉,再调海阳丞。政尚宽和,讼者以礼义晓譬,多释争而去。后迁永福令。永福俗险健,士训推诚以待之,留意学校,更定祭器,修立坛壝,人士多颂其德。诸台亦以慈祥恺弟、听讼平允荐之。会湖广总领请于朝,愿得廉靖吏以董军饷,遂差鄂州粮料院,荆襄两路军储皆属焉。未逾月,卒于官。平生好赒人急,而自奉甚约,囊槖萧然。卒之日,无以为殓,总帅率所属周旋其丧,以归葬于官陂之南,勉斋黄榦为铭。从弟士谨登嘉定第,任博罗尉,与士训同称贤云。
郑柔与杨耿、吴大成、薛京皆师于景肃、游于太学、格于桧党,不知为何《闽中理学渊源考》未单独有传。《康正题咏》已佚,但康熙《诏安县志》却保留有其《伤春赋》,如其所云“匪春之悲,惟人之怨”,可知虽以伤春为名,实为感伤时事,“六贼累我少阳,三奸贬我胡铨”、“欲破今春痛哭怀,除是销金复我国”,其抨击权奸误国、盼望恢复神州之激昂慷慨,数百年后犹可以想见。
陈景肃为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如果翁待举北宋政和二年(1112)登进士时间无误的话,其时陈景肃尚未出生,故二人实为忘年之交。翁待举以《中庸》为座右铭,“如见神明”一语可见其慎独工夫。
杨士训(1162~1219)亦作“杨仕训”,与其叔父杨耿同师于陈景肃。朱熹知漳后延请八位学官,杨士训为其中一员,后亦成为朱门弟子,朱熹称赞其“学已知方”。《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十一将其列入“朱子漳州门人并交友”,所述生平行状与《漳州府志》几无异,末尾则略有不同:“弟士谨,登嘉定第,任博罗尉,与士训同称‘七贤’云。”此处亦有“七贤”之名,并称杨士谨与士训同为“七贤”,不知与“渐山七贤”有无关系,待考。
明嘉靖年间,陈景肃等七人被列为乡贤奉祀。历史上最有名的“七贤”当属“竹林七贤”,他们优游于竹林之下,纵酒高歌、放浪形骸,却终不免怀抱各异、分崩离析;而以陈景肃为首的“渐山七贤”则讲学论道、抨击时弊,志同道合、始终如一,称渐山、石屏书院为南宋以来漳州文化的重要策源地,并不为过。明代陈若愚《渐山赋》称:“就中陈迹何不有?榴洞白云芜没久。前有薛翁君,后有梅月友。石屏南皋经行处,至今景物如琼玖。绍兴以来多俊英,二杨三陈次第兴。清修白业几尘劫,孰非渐山降神为之精。”赋中标举渐山英才迭出:薛(京)、翁(待举)、梅月(吴大成)、石屏(陈景肃)、二杨(耿、士训),除郑柔之外的七贤皆罗列其中。
(二)“陈氏家学”:陈植、陈格
“清漳陈氏家世学派·进士陈立先生植”载:
陈囗立,名植,以字行,漳浦人。公幼学于世父安卿,十八以祖泽补太学生,调龙溪令,转漳州司理。淳佑四年登进士,提督岭南海路兵马,帝昺浮海,公提岭海舟,见事危,断维出港,自以六舟泊海岭,收亡命,驰檄诸闽,图立宋后。闻张公世杰覆舟,元人索捕急,遂变姓名匿于大芹、白华、九侯间。临终,命葬海滨,南望崖山。弟格,为舟监簿,从容殉节,忠义形于《六咏》。今漳浦人并祀之。
《漳州府志》则载:
格,植之弟也,为宋海监簿。少帝之亡,格从容就死,忠义形于《六咏》。植殓其袍笏,招灵葬于渐山书院。国朝雍正元年,俱祀忠孝祠。
陈植、陈格为陈景肃次子陈宰之子。陈植“幼学于世父安卿”,此“世父安卿”即陈淳(《诏安县志》径称“幼从陈淳学”)。陈植、陈格在宋元易代之际都参与了抗元斗争,陈格捐躯殉节,仅存衣冠冢于渐山书院;陈植至死不忘故国、南望崖山,皆表现出了崇高的气节;其姊陈璧娘亦勉夫抗元赴难、己身绝食而逝。故《闽中理学渊源考》称“一门忠孝儒宗,其渊源卓矣!”《漳州府志》则称:“陈景肃以秦桧之故不拜制诰,子孙化之,视死如归……与东溪后先辉映桑梓,为邦司直不当如是耶!”可谓既有家学之渊源,亦由师门之感召。
三、陈景肃之学术倾向及其对漳州理学之贡献
据《漳州府志》载,陈景肃著有《石屏撷翠集》,当为其文集;《漳浦县志》所载除《石屏撷翠集》外,另有《礼疏》《诗疏》,当为其经学著作,然皆已佚。今所存著作,除前引《石榴洞赋》《怀高东溪》外,尚有《试剑石》《题〈吴子集诗卷〉序》等。其一生忧心国事、勤政爱民、反抗权奸、不屈不挠,实为一代忠义贤良之士。综合上文所述,可作如下概括:以陈景肃为首的“渐山七贤”,其政治上主张抗金恢复、反对和议(如吴大成论张浚清忠、郑柔建议北伐);在地方治理上主张宽严相济、与民休息(如陈景肃议均役、抚南恩州,杨士训政尚宽和,翁待举奏蠲苛税);在人格修养上则修己推诚、独立不屈——凡此,皆与朱子学的基本内容大体相近。而于其学术倾向与在漳州理学史上的地位,亦可作如下界定。
(一)陈景肃之学近于程朱
今云霄仙峰岩七贤祠有据传为蔡世远所题对联:“吾道南来,先朱文公漳南讲学;两宫北去,痛岳武穆塞北班师。”既揭示其忠君忧国之情,又表彰其率先讲学漳南之功。陈景肃石屏书院讲学内容虽不得其详,但约略可知不离忧国忧民、砥砺廉隅之主旨,由上引“讲明经术”(杨耿)、“讲明正学”(吴大成)等可窥其大端。然则此“学”何学?余英时先生认为:“南渡以后,通高宗一朝,王学事实上仍执政治文化之牛耳……在秦桧长期执政下,科举取士一方面仍主王氏‘新学’,另一方面则一再禁所谓程氏‘专门之学’……大概从乾道初年起,由于张栻、吕祖谦、朱熹等人的努力,程学才逐渐进占了科举的阵地。”陈景肃既与秦桧交恶,其所讲之学自然不是荆公新学;而其师高登本身与反对秦桧、力主程学的赵鼎(1085~1147)交好,《漳州府志》载:
是秋差考潮州,登愤权臣专恣,摘经史中要语命题,使诸生论直言不闻之可畏,策闽浙水灾之所自。时丞相赵鼎在潮,谓登曰:‘天下主文多矣,未有如公忠诚爱君者。’留语终日。郡守李广文驰以达桧,桧闻之益怒。
其时赵鼎正受秦桧排挤而安置于潮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更明载高宗之言:“赵鼎主程颐,秦桧尚安石。”上文已言及高登以慎独为本、为诸生讲《学》《庸》,故言高登之学术倾向于程学应无大误,而其弟子林宗臣劝陈淳读《近思录》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就闽南一地而言,其时道学亦传播有年,据《闽中理学渊源考》李清馥按语:“宋南渡后,讲学论道之盛,必曰炎兴乾、淳。余考吾郡士风家法,亦于是时最著。盖诸儒承北宋流风余矩,至靖康时,寖微寖晦矣。龟山杨文靖公载道南来,渡江后,岿然仔肩道脉。于时闽之分派者,多属上游,至是渐遍海澨,盖风气日趋于南,人物亦犹是也。”此处所谓理学风气、人物“日趋于南”,虽主要就泉郡而言,然于漳州亦可类推。因此,虽文献不足征,但亦可略知陈景肃之学术旨趣当与程朱之学较近;也正因文献不足征,故本文于景肃之学亦只能作历史的、而非哲学的叙述。
(二)陈景肃为漳州理学承先而启后
朱熹知漳是漳州历史上一件大事,漳州理学由此开新自不待言。但在朱熹之前,高登、陈景肃之博学高行,已为漳州理学的兴起提供了人员上、思想上的准备,方有其后之漳儒辈出。康熙《诏安县志》在陈景肃七贤传后,引旧志论曰:“吴、郑、薛、杨诸儒具得统于石屏公,其渊源出处亦大相类。奸桧柄国,毒流士大夫,诸公独抗大义,竞崎岖困郁以死,悲矣!诸公诗于流连风景之中错寓忠爱,其最哀激者,尤在《伤春》一赋。杨尹叔氏遭遇考亭,文章行谊为时师表,勤事至死,不负所学,其与诸公并出一门,何多让焉!”既指出遭遇考亭对杨士训之重要意义,又强调诸儒得统于石屏、并出于一门,正是认识到陈景肃之于漳州儒学、理学发展的独特地位。后之漳州太守方来作《碧玉千峰》诗以励学者,其一称颂朱熹(“堂堂紫阳翁,棠阴遍南国”)、其二即揭扬高登(“东溪有人豪,古调谁能续”);又作《石屏陈公庙碑》,称陈景肃为“三代之遗爱、旷世之逸民”,正见出三人于道学之契合。
而今诏安渐山七贤庵所供奉神主牌位共八座,除七贤之外,尚有朱熹,民间亦多有朱熹与陈景肃探讨理学之传说。虽然二人相见、切磋于榴花烂漫之渐山之情景,笔者并未见诸文献,但从朱熹对陈景肃之师高登之褒扬、杨士训先后以陈朱二人为师、陈景肃同门林宗臣引导陈淳入朱熹门下、陈景肃之孙陈植又以陈淳为师等等事实观之,陈景肃传承东溪、启沃后学、接续理学之功,盖不可没矣!
注释:
[1]黄仲昭撰:《弘治八闽通志》卷六十八《人物·漳州府·士行》,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影印弘治四年刊本,第3790页。
[2]陈洪谟修:《大明漳州府志》卷十五《科目志·宋进士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第851页。万历癸丑《漳州府志》则言其令仙游时,除嘉奖孝行之外,更有惩恶之举:“薄赋轻徭,旌善伐恶。县有宿盗蓝飞仙,潜劫邻郡,景肃获其党,诛之,患由是息。”见闵梦得修:《漳州府志》卷十九《宋列传·陈景肃》,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第1428页。
[3]沈定均修,吴联薰增纂,陈正统整理:《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宋列传·陈景肃》,光绪三年芝山书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60页。本文凡未注明之《漳州府志》版本皆同此。
[4]云霄县陈岱大宗理事会编:《陈岱大祠堂·开漳陈氏陈岱世系》未刊稿,2015年,第8页。
[5]李清馥撰,徐公喜等点校:《闽中理学渊源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0页。版本下同。
[6]《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宋列传·蔡元鼎》,第1266页。
[7]《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宋列传·颜慥》,第1247页。
[8]《闽中理学渊源考》,第225页。
[9]脱脱等撰:《宋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八·高登》,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131~12132页。
[10]《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宋列传·高登》,第1259页。
[11]高登:《东溪集》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漳州府志》卷四十二《艺文二》,第1942页。
[13]《漳州府志》卷四十三《艺文三》,第1970页。
[14]《漳州府志》卷四十六《艺文六》,第2065页。
[15]蒋垣:《八闽理学源流》,旧排印本,第51页。
[16]《闽中理学渊源考》,第227页。
[17]《闽中理学渊源考》,第227页。《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宋列传·杨汝南》亦称其“尤善高登”,第1263页。
[18]陈洪谟修:《大明漳州府志》卷二十五《人物传·宋人物·杨汝南》,第1519~1520页。
[19]《闽中理学渊源考》第226~227页。
[20]《闽中理学渊源考》第438页。
[21]《漳州府志》卷四十一《艺文一》,第1932、1868页。笔者按:《怀高东溪》其二可与杜甫《春日忆李白》相参看:“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22]《闽中理学渊源考》,第439页。
[23]可参见拙作:《漳州书院文化探论》,《录根》2016年第3期。
[24]《漳州府志》卷七《学校·义学书院·诏安县义学书院》,第154页。渐山,当地人称为“尖山”,《周易》有《渐》卦,其
《象传》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或为山名所本,待考。
[25]《漳州府志》卷四十《古迹》“仙峰岩”“石榴洞”皆为七贤读书讲学处,第1800、1803页。今云霄县仙峰岩存有“宋七贤讲学处”石碑及七贤祠,诏安县渐山亦有七贤庵。
[26]《漳州府志》卷四十二《艺文二》,第 1936 页。 “洲”本作“湖”,据《诏安县志》所载录之《石榴洞赋》和《漳州府志》“吴大成传”改。
[27]《闽中理学渊源考》,第439页。
[28]《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宋列传·吴大成》,第1269页。而《诏安县志·人物·宋贤达·郑柔》则载“景肃卒,与诸及门具心丧庐墓三年”,则服心丧者又不仅吴大成一人矣。见秦炯纂修:康熙《诏安县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569页。
[29]《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宋列传·郑柔》,第1276页。
[30]《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宋列传·翁待举》,第1263页。
[31]《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宋列传·翁待举》,第1269页。
[32]秦炯纂修:康熙《诏安县志》卷十二《艺文·伤春赋》,第619~620页。
[33]《漳州府志》卷十六《选举一》,第561页。
[34]《漳州府志》卷十六《选举一》亦将翁待举列于“政和二年壬辰莫俦榜”,第558页。然此年份似乎过早,待考。
[35]陈荣捷:《朱子门人》之“朱子门人叙述·杨仕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5~186页。
[36]《闽中理学渊源考》,第320页。
[37]秦炯纂修:康熙《诏安县志》卷十二《艺文·渐山赋》,第620页。
[38]其中“南皋”当指陈景肃七世孙陈汶辉,曾结庐读书于南皋,所著有《南皋集》,见陈汝咸修: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五《人物上·明·陈汶辉》,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052~1057页。“三陈”则不详,待考。
[39]此字上下结构,上宀,下左爿右夢。
[40]《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宋列传·陈格》,第1260页。
[41]秦炯纂修:康熙《诏安县志》卷十一《人物·忠节·陈植》,第574页。
[42]《闽中理学渊源考》,第438页。
[43]《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宋列传》“论”,第 1261 页。
[44]《漳州府志》卷四十一《艺文一》,第1836页。
[45]陈汝咸修: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七《艺文上》,第1251页。
[46]陈汝咸修:康熙《漳浦县志》卷十八《艺文下》,第1464页。
[47]吴大成:《梅月诗卷》,梅洲吴氏家谱编委会编印,排印本。
[48]“均役”乃南宋政府及民间为阻止贫富差距扩大而采取的措施之一,可参见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五章第一节,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49]《南靖县志》则称其“经术精邃”,见姚循义修:乾隆《南靖县志》卷六《人物·宋·儒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83页。
[50]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44~45页。
[51]《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宋列传·高登》,第1258页。
[52]脱脱等撰:《宋史·列传第一百一十九·赵鼎》,第11294页。
[5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二“文靖梁叔子先生克家家世学派”,第204页。
[55]可参见拙作《朱熹知漳与漳州理学之进路》,《闽台文化研究》2013年第3期。
[56]秦炯纂修:康熙《诏安县志》卷十一《人物·宋贤达七人》,第570页。
[57]《漳州府志》卷四十一《艺文一》,第1868~1869页。
[58]秦炯纂修:康熙《诏安县志》卷十二《艺文》,第616页。
〔责任编辑 吴文文〕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en Jingsu and Zhangzhou’s Neo-Confucianism
Zheng Chenyin
Chen Jingsu,a connector of Zhangzhou’s Neo-Confucianism,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Zhu Xi school.Gao Deng,his teacher,was called “the great man” by Zhu Xi;Yang Shixun,his student,later became Zhu Xi’s disciple;His classmate Lin Zongchen led Chen Chun into Zhu Xi’s students;His grandson Chen Zhi learned from Chen Chun,and actively engaged himself in anti-Yuan activitie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Later he lived in the south of Zhangzhou.Chen Ge,brother of Chen Zhi,died for his country.Chen Jingsu’s scholarship is similar to Cheng Zhu,and the behavior and learning of Gao Deng and Chen Jingsu have made a personnel and ideological preparation for the rise of the Neo-Confucianism in Zhangzhou.
Chen Jingsu,Gao Deng,Zhu Xi,Zhangzhou’s Neo-Confucianism,seven sages of Jianshan
郑晨寅(1974~),男,福建云霄人,漳州城市职业学院闽学与闽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