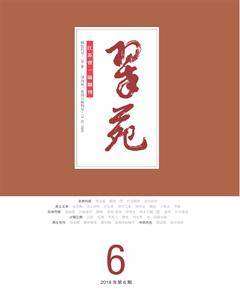苇絮(小说)
于兆文
作者简介:
于兆文,江苏淮安人。江苏省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淮安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大运河文学报》总编辑,淮安区教育局新闻发言人、宣传办主任。已公开出版7部作品集。
一声横玉西风里,芦花不动鸥飞起。
马蹄依旧入青山,柳梢浸月天如水。
一首诗,打开一季的门扉,也打开了我的心扉。
河水在缓缓地流淌,岸边的芦苇,绿了黄,黄了绿。秋天的时候,成片的絮花纷纷扬扬,将大段大段的往事飘洒在堤岸上。迎风吹过,像是白色的波浪起起伏伏,生我的小村便漂浮在这白花花的苇絮里。
坡上还有些无名的花儿如岁月一样,一茬一茬地开着。当初河里的水清澈见底,掬捧即饮,现如今已是混浊不堪,过往船只排泄的垃圾与油污,让一条河日渐憔悴。
世事如涛声,昼夜不息地没过运河两岸人家的心坎。有人在世事中如鱼得水,有滋有味地呼吸,有人在风雨中陷入混沌,近乎苟延残喘,而有人遭遇命运碾压之后则已寻不到一丝活着的气息。
我已三年没有踏上故土,一封父亲病危的电报,将我如罪人般拉回故乡。
下了堤岸,刚进村庄,便有人将乡音重重地扔过来,有几丝久违的感动,更有几分天然的亲切感。
路过废弃的老大队部的公房,我看到了她。如果不是村里人介绍,我是无法将记忆中的名字,与眼前的她画上等号的。
她叫成芳,一个人坐在藤条编成的椅子里,蜷缩着身子,面无表情,目光呆滞。人群从她身边走过,热闹和烦忧似乎都不属于她,外面的一切似乎都与她不相干。她只是坐在一个人的阳光里,时不时地抬起头来,仰望着属于她的一方天空。
50多岁的成芳,旁边坐着一个60多岁的跛子男人,听说是她的护工。那男人时不时地一瘸一拐地起身,帮成芳擦拭着脸,防止她口角的涎水流下来。男人的抚摸,才让她露出一丝笑容,灿灿的,甜甜的,像孩子样的,享受这片刻的欢愉与幸福。
一
一条运河穿过我的故乡,堆堤中央有一个三角洲地带,我们管它叫运南闸。其实,那是一个船闸枢纽,南来北往的船都要从这里经过。
船舶在此停泊,就有人上岸来采购、交换生活用品,渐渐地,运南闸成了货品集散市场,各路游商走贩汇聚于此,做着各式买卖。沸反盈天的叫卖声将小小的三角洲炒热了,这里很快成了远近闻名的闹市区。
公社领导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一家由公社集体投资的运南工农饭店应运而生。第一任经理便是成芳的父亲。有人说,是公社馬书记的儿子相中了成芳,马公子比成芳大七八岁。有人说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马公子在父亲面前美言,才让成芳的父亲从大队支书的“泥腿子”,一下子坐上了社直单位负责人的宝座。饭店的员工,那可都是有大集体工正式编制的,大都是走后门、托关系进来的。成芳初中毕业,也算是个文化人,顺理成章“内招”进来做了会计。
吃了公家饭的成芳,让同龄的孩子艳羡不已。她母亲结婚后一直怀不上孩子,直到30多岁才怀上她,父母非常溺爱她这根独苗。做了会计以后,正值18妙龄的成芳,模样、身段、风姿都赛过画上的美女,像一朵菡萏绿荷,香销四方。有时南来北往的船家上岸来,明里是为了购物,暗里却是为了瞅上美人一眼。
四乡八里,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有门当户对的,有沾亲带故的,有城里的公子,还有上大学的后生,成芳却一概拒绝,声称自己还小,不想嫁人。转眼成芳20出头了,更是出落得风姿绰约,娇媚动人。为女儿的亲事,父母可着急了,下了最后通牒,今年必须选择一个可意的人家。乡里马书记的公子是三番五次地来找成芳,可成芳连正眼都不瞧见人家,每次马公子都怏怏不乐地走了。
不久,成芳的父亲饭店经理的职务被乡里撸了,继续回村里做他的“泥腿子”村支书去了。成芳明白,肯定是马公子将状告到了马书记那里,这是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啊。
父亲不做经理了,不久成芳也被调到了农具厂,成天和一堆废铜烂铁打交道,再没了在饭店里的闲适和风光。
运河边上,无名的花儿依旧一茬一茬地开着,芦苇依旧絮花纷飞,似柳絮,又似杨花,坡上,水里,处处可见浮萍般的诗意,“困酣娇眼,欲开还闭”。
傍晚的时候,成芳常常一个人来到运河边,静静地站在那里很久很久,望着河中南来北往的船儿,她的心绪飞得很远很远。
二
有好事者传来消息,说看到成芳和一个军人模样的人晚上在河边手牵着手。传到了父母耳朵里,一开始,他们不信,后来经过当面核实,成芳还是承认了。
原来女儿的心里早已有了意中人。
那是她的初中同学袁兵,三年前去了部队。他们早就私订终身,山盟海誓之后,一个非她不娶,一个非他不嫁。怪不得那么多人上门提亲,成芳都没有一个答应的。
这门亲事,成芳的父母是断然不能答应的。袁兵家兄弟多不说,他母亲长年累月拖着一个“病秧身子”,家庭条件根本配不上成家,嫁过去肯定要受罪的。
可成芳像是中了魔似的,就是死认一个理,非袁兵不嫁。有人说过,恋爱中的人,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往往智商很低,想象力很丰富,但判断力很差。父母说破了嘴皮也没用,母亲整天泡在眼泪里苦苦劝着女儿回心转意。
袁兵为了成芳,三年服役期满,便退伍回乡来了,谢绝了连队留他在部队发展的好意。那颗驿动的心,早就期待着与另一颗心激越地碰撞。
为了女儿的幸福,父母干脆将成芳锁在家里,轮流看守,不准她再与袁兵见面。袁兵找来各方面的关系,试图打通关节,让成芳父母同意他俩这门亲事。可老两口坚决不允,还放出话来,让袁兵趁早死了心。
后来成芳的父母觍着脸,直接跑到公社马书记家,两家人坐下来,商量起儿女的婚姻大事来。马家自是求之不得,满口答应,主动提出一头办,不要成家花一分钱。事成之后,再将成家父女的工作做一个调整,保准满意。
这门亲事的缔结出奇地快,三天后马家聘礼上门。结婚的事,也顺理成章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月二十六是个良辰吉日,就这一天结婚,双方一拍即合。父母主意已决,成芳再不同意,也由不得她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在农村比什么时候都大得多。
十八的晚上,月亮还圆圆的挂在天上,再有一个星期,她就成为别人的新娘了。这几天,成芳为了麻痹父母,假装答应嫁给马家公子,暗地里却让人送一封信给袁兵,两人约好十八的晚上私奔。
成芳答应了亲事,父母自然放松了警惕。午夜时分,女儿借着上茅房的当儿,悄悄地打开院门溜了出去。袁兵早就安排一条小船在渡口等候,两人连夜从运河上坐船走了。
成芳逃婚的事儿,当时轰动一时。父母哭天喊地,到处托人寻找女儿的下落无济于事。马家更是动员基干民兵在附近乡镇进行拉网式清查,愣是没有找到一丝踪迹。
成家上门,向袁家父母要人,那夫妇更是老实人,没有一点章程,根本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成芳父母也是没了主意,只好悻悻而去。
只是苦了成芳的妈妈,天天要去运河岸边呆上半天。浑浊的目光从苇叶间穿梭过去,看着南来北往的船儿,她真的盼望女儿能从渡口的船上向她走来。
“闺女啊,我和你爸说好了,你和袁兵的亲事我们同意了,只要你回来就行,我们还指望你养老呢……”
有些苇叶经不起顿起的寒凉,成片地落地成泥。茫茫运河的涛声,夜夜入梦,空空的心房里,贮满了亲人的思念和泪水。
三
又是苇絮飘飞的时候,白色的花絮大朵大朵地漂在水面上,像是一条条银色的船儿游弋在河面上。
成芳和袁兵坐在这一船飞絮里回来了。
成芳变得胖了些,从少女成了少妇,有了几分熟女的样子。袁兵昔日青涩的脸上,冒出了凌乱的胡须,像是黑土地上一场风霜凌寒后冒出的一簇青绿。据说,他俩先是去了几百里之外的白马湖上给人看鱼塘,后来投奔千里之外的一个重庆战友,在码头上给人做挑工。成芳实在太想家了,没法放下家里的二位老人,才决意回乡的。
风中纷飞的苇絮,带回来了两个私奔的人,还有一段野合的事实婚姻。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场抱头痛哭,一顿埋怨数落之后,万般无奈的成芳父母最终默认了这桩婚事。村里腾出老大队部闲置的两间公房给他们做了婚房,简单的一场仪式,两家人到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这场婚姻就这么定了下来。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成芳名花有主了,当初打她心思的人,也渐渐地淡忘了。婚后几年,成芳的肚子也没个动静,这让人颇生意外。
成芳的父親也早就不做支书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一天到晚不停地咳嗽,有时候把夜里熟睡的狗儿都咳醒了,叫唤个不停。在一个大冬天,老人吐了一口血,吓得一家人手足无措,只好送到县医院,一查,肺癌晚期。回家不到一个月,老人撒手西去,扔下了成芳母女。
风在呼呼地吹着,苇秆轻轻地摆动,那阳光下大片的苇絮,铺天盖地,上下翻飞,一下子迷蒙了人的眼睛。成芳和母亲像失去了根的浮萍,在水中被波涛冲击得回旋游荡,不知西东。
袁兵成了顶梁柱,他把一个家紧紧地扎在腰间,慢慢地向前走着。
运南闸过去是一个市场集散地,一段时期成了“鬼门关”。来往的船家纷传一句顺口溜:吃饱饭,加满油,路过此地不停留。原来,运河边上的一些人家,找到了一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发家致富的捷径,对过境的拖运煤炭、钢材的货船实行“闪电战”,几十条甚至上百条小船一齐将货船堵住,逼迫船家低价销售煤炭、钢材等紧俏货,如若不同意,上百人直接上船哄抢物资。有些船主稍有反抗,便绳捆索绑,扔入河中呛水淹溺一番,直到你同意为止。
许多人成了“万元户”,袁兵、成芳经不住诱惑,也加入了“水鬼”的队伍,还做起了“匪首”,他们的日子一天天地变得殷实起来。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水鬼”们在强行登船和混战中,有些人落水而亡,有些人被疾驶的货船活活夹死。苇絮随风掠过,轻盈的舞姿醉了西风,醉了人心,让许多热望的眼睛迷失了方向。转眼几年的工夫,运河边上活生生地长出20多座新坟来,其中就有一座坟冢属于袁兵。
一个曾经对未来充满热望,常常在梦里笑醒的人,一瞬间没了家,没了顶梁柱。成芳深陷于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里,守着无边无际的黑暗,她看不到一丝光亮。
四
一场声势浩大的整治开始,所有“水鬼”家的小船,都被公安部门拖去烧毁了。袁兵留下的那些衣物,成芳也顺便拿去扔在船里一起烧了。她天天责备自己,悔不当初,不该让袁兵干这要命的营生。那时候,人们都是穷怕了,看到这么好的发财路子,谁不眼红啊。
望着那腾空的烈焰,成芳真想跳进去,烧掉泪水,烧掉悔恨,烧掉一切原罪。
没了袁兵的成芳,像断线的风筝,飘在天上,孤苦无依。心空荡荡的,脚底软软的,踩在云里,不知方向,不知归处。
乡里的农具厂早就倒闭了,她这个下岗工人,也没了经济来源。又像从前一样,身边追慕的男人渐渐地多了起来。约她看电影的,请她吃饭唱歌的,车来车往,一个比一个殷勤。性情大变的成芳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整天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常常是不醉不归。她一边在缠绵情歌里想起从前,一边在酒精醉意中忘记过去。她用一种放浪形骸,或者说是一种醉生梦死,来麻醉曾经沧海的自己。
年迈的母亲从小骄纵她,现在也无力阻拦她,任凭她去了。只是天天唉声叹气,慨叹她们俩都是“雪花命”,就像淡若轻烟、飞来飞去的苇絮一样,落水无痕,落地无声。
母亲坚决劝她把孩子打掉,成芳执意不肯,她一直盼望像正常女人那样生儿育女。她嫁给袁兵后一直没有小孩,有人嘲笑她是个不会下蛋的公鸡。她盼望这一天许久了,她要留下这个孩子,她要做一回母亲,做一回完整的女人。尽管她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包括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她就是要给自己留下一个血脉,留下一个念想。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她生下一个大胖小子。不知道肚中孩子的父亲是谁。她从一个女人,变成了一个母亲,所有的痛与苦,她独自承受着。母亲已经患上严重的风湿病,行走都已不便。上有老,下有小,为了孤儿寡母的一家子,她豁出去了,不要名誉,不要面子,她只要钱。她像一朵罂粟花,开放在男人的欲望里,疯狂地出卖肉体与灵魂。
有时候,她自己都厌恶自己,以前的她那么洁身自好,现在怎么坠落成这样了?
莎士比亚说过:金钱是罪恶的根源。这话不无道理。
五
她曾是一枝颤立于苇秆的絮花,绒绒的,柔柔的,人见人爱,飘在脸上,抚在手心,都那么惹人喜怜。而如今,在曾经优雅的生命里,她就像一曲无字的挽歌,早已孤独成冰,再也找不回最美丽的音符。
多年以后,成芳送走了母亲,老人去了天堂,与父亲团圆去了。她送走了儿子,儿子进了一所名牌大学。儿子是她的骄傲,从小学到中学,这么多年,成绩一直在班级里名列前茅。但儿子和别人不一样的,就是性格比较内向。小时候,儿子在小伙伴面前一直抬不起头来,常回家问成芳,他爸爸是谁,为什么人家都说他是“野种”? 儿子的痛,更是成芳的罪。她总是安慰孩子,告诉他,他的爸爸是袁兵,一生下来的时候,爸爸就因病去世了。
儿子大了,听到的闲言碎语更多了,有些话他也能听出个明白来,只是默默地存放在心底。这让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他唯有拼命地用功学习,在学习中冲淡这些流言在心灵上留下的印记。
成芳为了儿子,奉献了青春,奉献了人格,奉献了所有的一切。等儿子上完了大学,她也筋疲力尽了。她再也挑不动岁月的重荷了,她没了年轻时的容颜和轻狂,她承受了女人曾经所有的哀伤,迎来的却是让人心碎的凄凉。
儿子大学毕业后,如愿进入省城一家大公司,当上了白领。几年后也如愿晋升、晋级,还娶了媳妇、生了女儿,在省城买了自己的房子。成芳帮着她们带孩子,一家人过上了幸福日子。
一切皆在意料之中,一切皆在意料之外。好日子风生水起之时,却又节外生枝。儿子的丈母娘不知从哪里打听来的,说成芳是个“狐狸精”“风流鬼”,儿子的出生来路不明,是个“野种”。这下可好,儿媳妇听从她妈的话,坚决不允许这样的婆婆和她们在一起生活,怕将来带坏了女儿。
儿子万般无奈,将母亲送回运河边上的老家,每月偷偷地寄一点零用钱给她。重新回到乡下的成芳,神情恍惚了许多,身子骨大不如从前,再也找不到昔日灵动的身姿了。
每到秋天苇絮飘飞的时候,总有人看到运河渡口的堆坡上,她一个人呆坐在那里,手里还攥着大把的苇絮花,放在嘴边一个个吹着,像吹蒲公英一样。她想象着自己变成了一朵朵飞絮,飘到天上,成了云;飘到地上,成了叶;飘到水上,成了船。只有在那时候,她才感到无比的惬意、无比的自在。
有人发现成芳看人的眼神不对劲了,目光明显地呆滞,而且还时常拿着棍子撵人。是不是疯了?有人打电话告知她儿子,她儿子回来将她带去医院,医生告诉他,成芳得了严重的帕金森综合征,这种病发作时常伴有抑郁、暴力倾向。这种病人最好要有人照看,否则容易发生意外。
儿子被吓出一身冷汗,儿子请了三天假陪着母亲。有儿子在身边陪她说话,陪她走路,成芳的病似乎好了许多。可儿子走了以后怎么办啊,他是无法将母亲带回家的,可又不能将她一个人放在乡下。就在这左右为难的时候,一个60出头的老汉一瘸一拐地找上门来,他说愿意照看成芳。
儿子自是高兴,答应给老汉护理费,可老汉一口拒绝,儿子满腹狐疑地走了。事后,他打电话给邻居了解有关情况,邻居告诉他,老汉照顾他母亲很仔细,很周到,让他放心。
儿子的心稍稍宽慰了许多,但他注定无法释然。母亲在他心目中不是一个高大的女人,甚至是一个流言缠身的“丑娘”,但为了拉扯他长大成人,母亲付出了一切。现在,作为儿子的他万分无奈,他没办法改变什么。他从小生活在流言的阴影里,现在生活在家人的阴影里……
六
深秋时节,满目的芦花在瑟瑟凉风中摇摆,苇絮经不起阵阵风吹,纷纷飘落,我那劳苦了一辈子的父亲,也如苇絮一般不堪一击,随风飘逝了。
失去了父亲的母亲,一个人守着老屋,不愿随我进城。她的梦里有过父亲的鼾声,有过运河的涛声,有过一季一季的芦苇花开花谢。
在故乡的日子里,我断断续续地听完了成芳的故事,这个女人像一秆芦苇插在我心里,从葱绿到枯萎,我再也寻不到芬芳的气息,空留一地残存的苇絮。
告别故乡的时候,有人告诉我,现在照顾成芳的老汉,就是当年成芳逃婚的对象,乡里马书记的儿子“马公子”。现在他老伴也去世了,孩子在外地,他退休后一次车祸,腿脚留下了残疾……当地人都夸“马公子”重情重义,听说他还上了当地的“好人榜”。
后来,我再没看到过成芳。
再后来,听人说,成芳死了。
有一天夜里,痴呆症严重的她在护工马老汉睡熟的时候,一个人走了。村里人和趕回来的儿子四下里分头寻找,三天三夜没个人影。后来,警方在百里之外的白马湖里,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经过大伙仔细辨认,还做了DNA鉴定,最终确定了就是成芳。
马老汉说,最近以来,成芳天天都去运河边上。有一天,看到一对白鸟立于苇尖,她回来就说,那鸟是袁兵让来的,带信让她去找他。有人说,这次出走,她八成是去找袁兵了,白马湖是她爱情的驿站,当年她俩私奔待过的地方。有人说,她是水命,就该在水里得到永生。
江头落日照平沙,潮退渔船搁岸斜。
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
我觉得,如果诗意地说,成芳是在这首诗里走的。
那天傍晚,我独自走到故乡的运河边上,一道斜阳远远地挂在天际,当霞光映照在无边无垠的芦苇花上的时候,各种颜色波浪般向我涌来,让我目不暇接,明黄,雪白,奶白,微红,淡青……微风过处,苇花随风飘摇,苇絮又开始纷纷扬扬。
我倒有点相信,成芳如她母亲所说,是个“雪花命”的女人,她其实就是运河边上四处飘散的苇絮。
在那大片大片雪白的苇絮中,她曾像一只蜻蜓,忘情地翩翩起舞,飞啊飞啊,最后她羽化成絮,飘在枝头,飘向大地,飘进河里,最终没入这无边的芦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