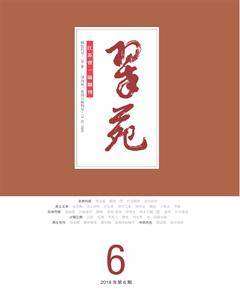附近一带
陶文瑜
一
提起上海来,真的不好意思。我在小学三年级之前,一直以为自己是上海人。说起来,上海人也不能享受什么特别的待遇,因为,当时我们使用的日常用品,比如缝纫机、自行车什么的,都用的上海产品,或者说上海产品在同类产品中比较有品牌吧,所以心里总觉得有点优越感和荣誉感的。
我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上海人呢?因为我父亲在苏州火车站工作。苏州火车站属于上海铁路局,火车站的职工子弟,比如我吧,要生个病什么的,就要到上海的医院里去,其他同学是两节课后家长推着自行车上医院的,我是一大早由家长带着,乘着火车去的。直到四年级之后,我才渐渐明白过来,我其实不是上海人,我父亲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他只是在火车站工作,而这个单位偏巧归上海的一个部门管理,这是丁是丁、卯是卯,我和上海的关系,充其量也就是远房亲戚吧。
这期间我随父亲去看过一回牙齿,检查过一次视力并去过一次西郊公园,去过一次老城隍庙,还有一次是去看父亲的一位朋友。这是我第一次坐电车吧,还走过好几条弄堂,弄堂的口子上总有一家小店,小店里总有一架公用电话。上了点年纪的上海人,一半坐在小店里,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在听半导体;一半在小店外买东西,或者提着买好的东西,回头朝弄堂里面的家走去。
之后的好多年,即使是上中学的时候,我也一直没有去过上海。只是我在铁路中学读书,铁路中学的不少老师是上海人,比如教我物理的戴老师、教我语文的魏老师、教我外语的孙老师,孙老师是我们班主任,每天都要布置外语背诵的作业,谁完不成就留下来,直到背出来才放人。但一般情况下周末要相对宽松一点,周末家在上海的老师都要回去,当时我们自觉性也差,不明白老师这样做是真心地为我们好,星期五的作业相对宽松,因为星期六老师要回去的,他们乘火车回上海,火车不等人,他们对待大家就不那么斤斤计较了。所以,当初我们就已经有了一点双休日的意思了。
后来铁路中学解散了,不少老师调回上海去工作了,有些早就退休了,比如戴老师,戴老师是一个人,退休后还到苏州来看看从前的学生,主要是当时的班干部,我不在其列。这也是从他们那里听来的,对我而言,说起往事来对戴老师还是想念的,毕竟师恩难忘。
现在我和上海的联系比较多,来往的机会也多,不久前一部《茶馆》的书稿,就是受上海大雅文化公司之托做的。我其实不擅长这个题目,但和我谈的是一位美丽温和的女孩,我竟稀里糊涂地答应了。然后,只好自讨苦吃地深入生活,也收集了不少有关上海茶馆的资料。其中有一些是当时苏州的文化人,都是在上海生活、工作的,比如周瘦鹃,他在上海办报刊,搞得红红火火的。
但那时候还没有我,要有我的话,肯定应该和周瘦鹃认识的,因为是同乡,搞不好还是合作伙伴呢。
二
我去南京差不多已经快要长大成人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刚好南京长江大桥造起来了,数百里之外的苏州,也锣鼓喧天地热闹过好一阵子。学校里布置了关于长江大桥的图画作业,因为蜡笔本身就比较笨拙,再加上桥面上开汽车,桥中间开火车,桥下面的水上还要有轮船经过,这样画出来的作业,长和高几乎是差不多的。这说明我当时虽然缺乏想象力和艺术感觉,但毕竟是一个一是一二是二的人。
真正往心里去的风景是秦淮河,这个念想是怎么生出来的,已经记不得了,反正不是读了俞平伯和朱自清的文字,他们的文字只是加强了心里的念想,但主要还是风花雪月的成分多一点。后来,我第一次去南京出差,下了火车就去夫子庙,看到的却是一副集贸市场的样子,真是有点哭笑不得了,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手里提着领带的小贩,一个劲地问我要不要领带。
10元3条,我要那么多领带干什么呢?真是的。
有一阵我一直要去南京出差,是将编好的稿子送给出版社终审。稿子是校园文学的内容,每一回是两到三天,住在出版社的招待所里,靠在招待所边上这儿,是一家点心店。这一家点心店除了对外供应点心,其他的和人家家里几乎一式一样,桌子就是他们吃一日三餐的桌子,炉子也是他们自己烧饭的炉子,进去之后坐下来,几乎就是他们家的亲戚。
点心店的生意很清淡,点心只有面条和馄饨,滋味不能说很好,但看上去很干净。点心店的主人是一个七十开外的老头和一个二十左右的女孩。老头指挥女孩一些事情,对客人十分热情开朗,女孩一直是细声细气的样子。老头应该是祖父吧,女孩就是孙女了,我暗自忖度,老太可能不在了,女孩的父母可能早出晚归上班了,或者就是在外地工作的。这是多好的一家人家啊,我当时也是青春年少,心里想着,在这家人家多待一会儿,或者将来有可能我们单位在南京建立一个办事处,我就可到南京办事处工作,生活真是太美好了。
后来去的次数多了,老头和我的话也多了,有一次老头在我吃馄饨或者面条的时候,问三问四地说,哪儿人呀,做什么工作呀,今年多大了呀,这使我觉得八字几乎有了一撇了。但是老头紧接着说道,他自己已经76岁了,有5个儿子,他和最小的孙子一起过,那个女孩就是孙媳妇。
我在出门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对那个女孩生气起来了,明明是孙媳妇,还要装得像孙女的样子,多不好啊。
再去南京时,我又去了一两次点心店,还是老头和女孩在那里张罗,我只是填饱肚子,那样的感觉一点也没有了。
关于南京还有一件值得记录的事情,就是我的同学季海跃当年毕业分配去了省武警部队。他是学财务的,一开始在监狱里实习,有一天正赶上风雨交加,一个犯人企图越狱逃跑,季海跃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毅然举起了手枪并打中了犯人的屁股。这一枪使他荣立了三等功,并在人生的道路上,完成了一个白面书生到革命战士的转折。
三
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等等,徽州菜简直太一方山水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徽州生得山重水复的样子,赶路实在不方便,赶了早市买菜,回到家已经是黄昏了。所以,因地制宜的吃法就應运而生了,和这样的吃法相适应的,就是又辣又咸。臭鳜鱼和毛豆腐好比一件西服,辣和咸就是挂在这件西服脖子上的领带。这一点我不太适应,我是比较纯正的苏州口味,辣是一点都不碰的。这好比涉外婚姻,有些人习惯,日子过得有板有眼。有的人豁出去之后,坐着飞机千里迢迢地赶到国外,白天、晚上全是一派陌生,真是欲哭无泪啊。
每天夜里,我要等到12点之后,去街上吃一碗小馄饨,觉得踏实了,再回去睡觉。小馄饨的摊子要12点过后才摆出来,那时候城管下班了,估计小馄饨摊主是一个无证摊贩吧。
我是为一家电视台写《徽州》的文字而再去徽州的,记得全是和徽州的春风得意有关。这样的文字,是一个轻灵飘逸的文人和满腹经纶的学者在侃侃而谈。对于徽州,我几乎有点一问三不知,但形成的文字,却是一副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的样子吧。
我就想着从前的徽州在现在的风景里走来走去,好几回觉得很有难度,我要对着老态龙钟的女人,描绘她妙龄少女、如花似月的情态,这是要有耐心和性情的工作啊。
當然也能遇上一些意外的感动,徽州从前有个说法是“程朱阙里,不废诵读”,到后来忙出忙进、七弄八弄的,诵读的风气就淡下去了。我在走过一个不起眼的旧村落时,看到村口的墙面上,依稀可辨的,是用很规范的楷书写的“识字歌”。识字歌是一些朗朗上口的常用词,“之乎者也”的字里行间,落泊成了墙上的一点一划。反过来,程朱学说也应该是从识字歌开始启蒙的,这叫我说什么是好呢?
不久以后,拍摄开始了,有一个深山里的古村落,剧组进不去,村子里连夜推倒了几间路边的房子,然后开出一条路来。
剧组准备拍摄的是傩舞,偏偏会跳这个舞蹈的老头死活不愿意,说是住在他家隔壁的邻居不让他跳,不吉利。他在几十年前跳过一次,邻居曾经把他狠揍了一顿,然后大家都很不开心,他也一直没有跳过这个舞蹈。村领导说,这一回你跳就是了,村里面给你做主。
拍摄的当天正好赶上采茶的日子,村领导说,今天不用去采茶了,学校里也停课,大家都到祠堂里去看戏。
领导还说,总要挤得满满的,拍出来才像个样子嘛。
我从徽州回家的时候,正赶上出门打工的民工离家出门。火车已经超载了,经过绩溪的时候就象征性地停了一下,车门也没有打开,站台上黑压压的民工一片失望。
从前的徽州还有一句俗语是“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往外一丢”就是出门打工的意思吧,因为地少人多,出门打工的习俗保留至今。
绩溪我没有去,那是胡适的家乡。
四
“无锡锡山山无锡”,这是一副对联的上联,下联是有不少的,但都十分牵强。还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油面筋”,下联是“肉骨头”,合在一起是两样食品,拆开来是6个名词,全是人体或者动物身上的零件。油面筋和肉骨头,是无锡的两样特产,你说巧不巧了。因为这个缘故,很长一段时间,无锡在我心目中,好像是一座文字游戏的城市。
第一次去无锡是小学四年级,大背景是这一年国家重新将升学从寒假改到暑假了,我们要多读半年书,按理说我们本来要升五年级了,现在还要再读半年四年级,而四年级的课已经上完了呀,所以,这个半年举办的活动多了起来,去无锡就是其中的一项。
学校的说法是为写作文去的,大家参观了太湖边的鼋头渚、锡惠公园,还有梅园,当时有一个同学说,梅花,其实也不一定有什么傲霜斗雪的品质,她可能比较适合在冬天生长,她要是生在夏天,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老师讲评的时候,说这个同学的思想意识有问题。
我一直有一个念头,就是用小学生作文编印一本导游书,也可以请他们配一些插图,这肯定是很有趣的。
苏州到无锡只是半小时的车程,苏州人眼里的无锡,基本上不能算是外地的,好比阿姨或者小叔子,他们是亲属,感觉上和家属差不多吧。但虽说是比较近,但也不是有事没事老去的那种,还是这个比方,你老往阿姨家跑,不是很无聊吗?
现在苏州的大街小巷里,无锡馄饨、无锡小笼包的点心店开出来不少,其实滋味是不能和无锡当地的相提并论的。这一点和南京盐水鸭仿佛,南京的大餐馆、小饭店也不是都能把菜烧好的,但一道盐水鸭是没话说的,大江南北的地方,也有做盐水鸭的,甚至也有南京人的铺子,味道就是不及南京本地。
我有一次无所事事地去无锡,就是与无锡馄饨、无锡小笼包有关了,说白了,我突然很想吃这两样点心,是一种“别来忽忆君”的感觉吧。专门乘了火车去吃馄饨和小笼包,好像有点大动干戈了,但后来我又一想,人家一男一女两地分居,为了见上一面,不也是火车、汽车地赶过来,赶过去的吗?按说当地异性满街都是,为什么非要赶这么远的路去见这个人呢,道理不是一样的吗?当然我和馄饨、小笼包不是恋人,馄饨、小笼包也不会打着车到我餐桌上来吧?
另外,我还在无锡乡下住过一阵子,我的一个朋友老家是无锡乡下,只是他的父母都已经迁到苏州来了,那儿是他的老家吧,我在他老家住了十来天,具体干了什么已经记不得了。
这个朋友热爱文学,也有很好的文采,但后来歇下来去干别的了,先是当政工干部,后来又搞基建,最后自己打点文化用品生意。不久前他来看我,正好郊外石湖有一家饭店请我吃晚饭,我就邀他一起去了,回来的时候,司机有点迷路了,他就一五一十地指点。
他的生意是跑出来的,先要一家一家联系,再要一家一家送货,所以对各式各样的地形熟门熟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