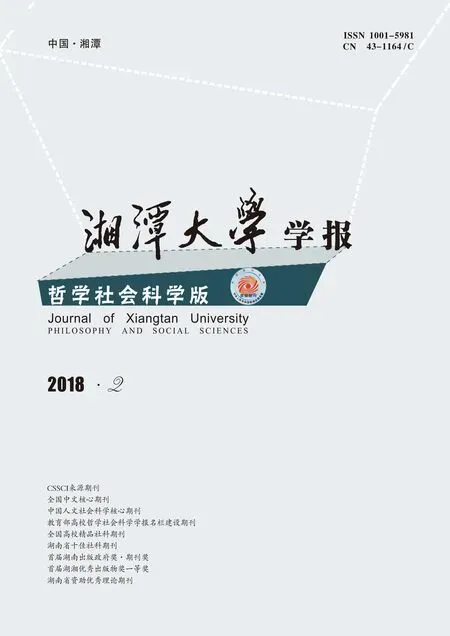街头官僚运动式执法的动员机制
——基于广州市A街道流动摊贩治理问题的探讨*
吴克昌,关飞洲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1 )
一、问题提出
各级政府对社会事务的治理需要采用适当的政策工具,实践表明运动式治理这一政策工具相比常规治理,更容易受到政府权力主体的青睐,比如生活中充斥着“XX专项活动”“XX严打”“XX整治活动”等各式各样的运动式治理活动。基于运动式治理活动的频繁出现,有学者提出了“中国制度化悖论”[1]和“运动式治理悖论”[2]47-72,认为改革要求实现常规化的治理,但是却以非常规化即运动的方式进行,而同时悖论的存在也在一定意义上佐证了运动式治理相比常规治理具有独特的治理优势。
常规治理的失败触发了运动式治理的产生[3]22-46,因此运动式治理的治理成效和治理优势是相对常规治理而存在的。与常规治理表现出来的低效、失灵不同,运动式治理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达成治理目标[4]111-115,实现治理绩效。而常规治理为何会失灵?运动式治理又通过何种方式弥补常规治理的不足?学者们从不同的侧重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常规治理建立在部门化、规则化运作[5]5-21,[6]105-125的官僚制基础之上,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繁杂的事务处理程序带来了常规治理的低效率,而运动式治理能够打破官僚制的弊端和治理过程的制约,整合部门力量,完成特定的治理任务。[6]105-125而在运行体制的基础上,则包括两种比较具体的研究路径,一方面是从治理资源的角度,认为运动式治理是政府在国家治理资源匮乏之下的理性选择[7]115-129,能够弥补常规治理中治理资源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由于国家“基础性权力”[8]185-213尚未建立起来,常规治理的失灵,不仅造成社会问题的久拖不决,更会在社会问题的日益积累下,对社会稳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运动式通过动员社会力量的方式,建立国家与社会良好的相互关系,既能集中和利用社会治理资源,又能够在社会通力合作解决社会事务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再生产和再扩充[7]115-129,进而提高国家政权的合法性[9]63-77,[10]70-96。
学者们对运动式治理的优越性,主要是围绕上述官僚体制的基础,以及治理资源的匮乏和国家基础性权力的缺失,从比较宏观的角度而展开的,而对治理主体的关注则比较少。治理方式和治理决策是否奏效,关键在于处于基层政策执行端的执法主体能否通过现实的执法活动,实现治理目标和治理绩效。所以在以往学者对运动式治理相关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着眼于治理主体的执法能动性,探讨运动式治理通过何种方式作用于执法主体,从而产生优于常规治理的治理结果。为了能够凸显执法主体对治理过程的影响和作用,本文把执法主体限定为处于基层一线执法层面的街头官僚*李普斯基(Lipsky)在1977年《建立一个街头官僚理论》一文中首次使用“街头官僚”的概念,1980年出版《街头官僚:公共服务中个人的困惑》一书,标志着街头官僚理论的正式建立。群体。街头官僚作为最基层的执法人员,承担着自上而下的重要的执法任务,其执法行为的选择能够对执法目标的实现产生直接和有效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佐证。对选取的案例进行详细的呈现,深入地说明街头官僚常规执法和运动式执法的具体过程,并从中探析运动式治理的优越性。
本文所使用的案例材料为笔者在2016年3月至2017年4月实地调研所得。为了便于深入地分析广州市流动摊贩治理过程,笔者在对广州市流动摊贩治理整体性把握的基础上,选取了广州市天河区A街道城管流动摊贩的治理过程进行相关调研,主要采用了参与式调研、深入访谈和历史文献分析法等资料收集方法。(1)参与式调研法。在与广州市天河区A街道城管部门取得联系之后,获得部门主管领导的准许,有机会参与A街道城管执法队的执法过程,实际感受城管执法人员的常规执法和运动式执法过程。(2)深入访谈法。在调研过程中,深入访谈的对象主要有A街道城管部门的领导、数名基层执法人员、流动摊贩代表以及社会群众代表,受访人员共20余人。(3)历史文献分析法。笔者收集到的相关历史资料主要包括:广州市出台的法规及政策文件、城管部门出台的规定和办法、城管部门通过自媒体平台对外公布的信息以及第三方媒体对流动摊贩治理的相关报道等网络信息。
(二)分析框架:运动式治理的动员机制
街头官僚处于政策执行的末端环节[11]41-48,其核心职能在于对政策和法律的执行。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自由裁量权和责任控制[12]30-34,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为街头官僚执法提供了充足的弹性空间,影响到执法目标和治理绩效的实现。赋予街头官僚充足的自由裁量权,提高其执法能力,同时又对其加强责任控制,则是保障街头官僚实现良好执法绩效的重要途径。街头官僚的执法能力和执法弹性空间,在治理过程中受到注意力分配、治理资源和绩效考核等因素的影响,并在运动式治理的动员机制下分别得到提高和控制。学者们普遍认为,运动式执法的动员机制,能够把一般的行政治理任务上升为政治治理任务[13]83-106,在有限的时间内突破常规治理体制的约束,调动政府系统内外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14]73-97,[15]38-46,实现既定的治理目标。因此,本文试图构建起街头官僚运动式执法的动员机制框架,探索和分析街头官僚在动员机制下执法目标、执法资源和执法绩效责任的优化过程,进而解释运动式执法及其动员机制的优越性。
1.注意力的分配与执法目标
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内,应该把哪一项社会事务放在优先治理的位置,常常是政府治理面临的困境。常规治理要求政府在官僚体制的基础上,全方位地履行职能,所以在常规治理体制中,政府部门、领导干部以及街头官僚需要处理繁杂的社会事务,其注意力无法有效地集中到某一项社会事务的治理中去,因此街头官僚的执法目标是相对分散的。
运动式治理动员机制的优越性之一,在于能够通过“首长站台”[3]22-46的形式明确和聚焦治理的目标。运动式治理的开端往往在于某一项社会事务引起了政府部门、领导以及社会公众的注意,并促使其进入政府的决策议程。政府部门和领导的注意力的分配,把街头官僚的执法行为聚焦到具体的目标上,为街头官僚指明了执法的方向。同时执法目标的聚焦,缩小了街头官僚的执法空间,降低了执法随意性。所以,运动式治理中街头官僚更倾向于实现具体的执法目标,产出执法绩效。
2.治理资源与执法条件
常规治理失灵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治理资源的匮乏,治理资源主要包括政府系统内部资源和社会非政府资源。[16]31-35在常规治理中,政府系统内部资源的不足,一方面表现为治理资源数量上的短缺,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各职能部门相互之间的壁垒的存在,政府系统内部资源无法得到有效整合和利用。
运动式治理动员机制的另一个优势则体现在能够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充分发挥矩阵式组织结构的作用[17]161-170,推进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和资源共享。社会非政府资源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社会公民等主体的资源和力量,在社会事务的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优势,社会组织和公民能够在动员机制下直接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过程,建立与政府之间的良好互动合作,为社会事务的治理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
街头官僚在政府系统内部资源匮乏以及社会资源不足的条件下,面对复杂的执法环境和不可预期的执法风险和结果,表现出执法能力不足、执法积极性不高的倾向,容易产生执法不严、一线弃权[11]41-48等现象。运动式治理对治理资源的动员和整合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街头官僚的执法条件,能够提高街头官僚的街头执法能力,降低来自执法对象和执法现场的执法风险,提高街头官僚的执法积极性,减少执法弃权等行为的产生。
3.绩效考核与责任控制
绩效考核能够对社会治理实践起到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的作用。运动式治理的动员机制,对治理活动的绩效考核提出了可量化、操作化的要求,强化绩效考核控制效力。而在常规治理中,由于缺乏具体可操作的量化考核指标,绩效考核机制对街头官僚的执法约束强度相对有限。运动式治理的绩效考核指标往往表现为具体化和可量化的指标。[13]83-106。聚焦的执法目标和可量化的考核指标,压缩了街头官僚的执法空间,降低了执法弹性,并激励街头官僚为实现良好的执法考核结果而规范执法行为。
与绩效考核相配套的奖惩制度,是通过奖优罚劣的方式对街头官僚的执法行为进行结果控制。在运动式治理的考核总结和评估阶段,会对相关职能部门和街头官僚的执法绩效进行考评和排名,从而进行奖励或惩罚。在运动式治理中,有学者认为负向的惩戒措施更容易对街头官僚的执法行为产生刚性的约束力。[18]113-133因此运动式治理能够通过具体的可操作化的绩效考核机制,控制街头官僚的执法责任,引导执法目标和执法绩效的实现。
通过分析上述影响因素,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运动式治理动员机制解释框架。在常规治理中,治理资源的匮乏、治理目标的分散以及绩效考核软约束的存在,一方面制约了街头官僚的执法能力,另一方面无法对街头官僚的执法弹性空间形成有效的控制,从而在治理过程中带来了街头官僚偏离执法目标的可能性,导致常规治理的失灵。运动式治理,在动员机制的作用下表现出强大的治理优越性。运动式治理的动员机制首先是弥补了常规治理中治理目标分散、治理资源匮乏、绩效考核软约束的缺陷,保证了街头官僚执法目标的明确性和聚焦性,充分调动了政府系统内外部的治理资源,提高了绩效考核的可操作性和强控制力。其次通过对治理目标、治理资源和绩效考核三个维度的作用机制,在提高街头官僚执法能力的同时,又压缩了街头官僚的执法弹性空间,从而推动了运动式治理目标的实现。

三、案例选取:广州市A街道流动摊贩问题治理
研究新时期运动式治理相对常规治理的特点和优势,需要把握专项治理这一代表性治理类型,因此本文选取了广州市A街道流动摊贩问题治理为案例。案例的选取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典型的街头官僚代表的选取。城管作为城市综合管理执法人员,其工作的场域大多情况下是在街头,处于一线执法的位置,直接参与具体的执法活动,与执法对象直接产生执法关系,能够体现出城管主体明显的街头性质,是街头官僚典型的代表之一。不仅如此,城管作为一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拥有自由裁量权,对执法目标的实现具有正面的促进和负面的偏离的双重影响。
二是社会治理问题的选取。流动摊贩问题存在于国内外的各个城市,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并在城市化极速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城市管理的顽疾。对于流动摊贩问题的治理,城管部门经常面临着常规治理失灵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城管部门往往会不定期地开展一些专项整治活动,通过运动式治理的方式解决常规治理无法解决的顽疾。
三是对案例发生地点的选择。广州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又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为流动摊贩问题的存在提供了条件,而广州市A街道因良好的区位条件成为流动摊贩问题治理的重点区域。广州市政府近些年来,加大了对城市“六乱”的治理,流动摊贩问题为重要的“一乱”。在对流动摊贩问题的治理过程中,A街道也探索了一些治理路径和手段,但是该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本文旨在通过观察A街对该问题的治理,探析运动式治理的动员机制的实现过程。
四、案例呈现:A街道的日常巡查和专项整治
A街道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建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2005年广州市行政区划调整,形成了现如今的所辖区域。调整后的A街下辖十二个社区委员会,总人口超过八万人,其中外来人口近三万,这为该区域内的流动摊贩的存在提供了稳定和广泛的客流基础。另一方面,A街位于广州市现代化的大都市中心区域,交通便利,全街有主干道十一条,街巷十五条。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A街内迅速崛起了数量众多、极具规模的百货商场、酒楼大厦、医院和文化基础设施,以及中高档写字楼,形成了多个人流众多、消费需求旺盛的繁荣商圈。A街道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广阔的消费需求市场,为流动摊贩的持续生存提供了极大的诱惑力。近些年针对该区域流动摊贩问题的治理,A街道形成了以日常巡查为基础,专项整治行动为辅的治理模式。
(一)日常巡查的时空划分[19]31-47
在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对A街道流动摊贩的日常治理,城管执法队采用的是巡查的方式。受于执法人员数量的限制,A街道城管日常的街头巡查,并不是全覆盖A街道辖区的所有区域。
日常巡查执法有区域重点的进行,主要的原因在于流动摊贩治理中投入资源的不足。从城管队伍的构成上看,A街城管执法队只有八名带有编制的城管员,以及数十名协管员。在日常的巡查中,A街城管执法被分为几个组,分别负责巡查辖区内的几个重点区域,每个组由一到两名的在编城管,和三到四名的协管员组成。在巡查的方式上面,A街城管多数情况下采用驱车的方式进行,基于驱车方式的选择,A街城管执法队员刘某解释道:“其实我们选择驱车的方式是有原因的,首先是我们负责的区域这么大,巡查一圈下来是很费时间的,步行的方式太慢了,不利于及时发现和制止摊贩,另一方面呢,摊贩可以远远地看到我们的巡逻车,而收摊撤退,也能够减少我们(城管和摊贩)之间的直接冲突,这也算是一种灵活的方式,更或者说是执法条件受限下的无奈之举吧。”(访谈记录:20161020GFX)A街道城管对流动摊贩日常巡查在空间上的选择差异,给A街道辖区内的流动摊贩留下了较大的生存空间,基于此,流动摊贩有针对性地采取了规避城管执法人员的策略,更多地活跃在容易被城管执法人员忽视的非重点区域,“这样一来一方面是不至于往城管的执法枪口上撞,另一方面就算是被城管逮到了,求求情,城管也会通融一下”。(访谈记录:20161020GFX)在非重点区域,A街道城管采用比较柔性的执法方式在于,其面对的向上的执法压力相对比较小。实际情况表明,A街道城管空间选择性的日常巡查的结果,只是改变了流动摊贩问题在A街道内部的空间分布情况,把流动摊贩从重点执法区域,驱赶到非重点执法区域,并没有实质性地解决掉流动摊贩问题。
A街城管的日常巡查不仅存在空间上的选择性,亦存着时间上的选择性。一般而言,城管对流动摊贩的执法时间是根据流动摊贩的活动时间而定的。A街辖区内的流动摊贩会随着早高峰的到来和消费需求的增多而活跃起来。流动摊贩的存在,增加了道路的拥挤程度,加重了街区的无序程度。所以在早高峰时段,A街道城管执法队是高度重视流动摊贩的治理问题的当值的城管执法队几乎是全员出动,加大街道区域内尤其是重点区域的执法力度。除了早高峰时段,晚高峰时段亦是如此。其余的大部分时间,受执法条件的限制,A街道城管人员无法保持长时间、高强度的巡查执法力度,会相应地缩减执法人员数量和降低执法力度。“平时我们巡查就是三四个人一起,或者开着电瓶执法车,或者步行,一方面我们的精力和体力都是有限的,无法一直保持高强度的执法,而高峰时期,我们不仅要赶走流动摊贩,更重要的是要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而另一方面,社会上都说我们为了城市的门面,不管弱势群体的死活,事实上我们也明白,如果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不停地街头巡查,他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必然会激发相应的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访谈记录:20161020GFX)由此可见,高强度解决流动摊贩问题容易激发社会阶层矛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看,处于矛盾中的城管执法无法有效地解决流动摊贩问题,而只能是有保留地采取执法行为。
A街城管日常巡查执法的时空选择性,在长期的流动摊贩治理活动中逐渐成为相对比较稳定的模式,为流动摊贩提供了规避城管执法的空间和时间上的策略选择。在与A街城管执法队打交道的过程中,众多流动摊贩逐渐摸清楚了城管执法在巡查空间和执法时间上的规律,并据此作出应对措施,凭借长期的“斗争经验”逃避城管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
所以在流动摊贩的日常巡查执法中,A街城管队伍在与流动摊贩的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时空上的默契,对于城管而言,只要在巡查时能够把流动摊贩赶走即可,对于流动摊贩而言,看见城管的到来,还是要“配合”一下巡查执法过程,而主动选择让步离开执法区域,这样就形成了A街城管与流动摊贩“猫鼠游戏”的局面。
(二)专项整治行动
A街城管队在日常巡查执法的基础上,不定期地对流动摊贩进行专项整治行动。专项整治行动能够通过聚焦细微之处,充分体现运动式治理的独特优势。A街的城管执法队每一次专项整治行动的开展都是随机的,但不是随意的,是A街城管执法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在笔者对A街城管执法队跟踪式调研的一年多时间里,共参与了九次A街城管执法队针对流动摊贩问题开展的专项整治行动,每一次的专项整治行动都有其在特定时间节点上的特定原因。首先,2016年3月和2017年2月的两次专项整治行动,是基于春节过后流动摊贩大批返城,以及学校开学的时间段,流动摊贩开始了新的一年的生意,是A街道城管治理该问题的重要阶段。其次,2016年6月至9月之间的三次专项整治行动,主要是为了广州市能够顺利通过国家文明城市的复检工作。再次,2016年10月至12月之间的两次专项整治行动则是在市民的投诉之后,A街道城管队迅速展开的专项整治行动。其余还有两次则是根据A街道城管队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乱象而开展的专项行动。针对特定阶段的专项整治行动,A街城管队的林副队长有这样的感受和体会:“专项整治行动,要求我们的城管队员加大执法力度,可是加大执法力度,就容易引起与摊贩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我们不愿意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没办法,对于流动摊贩的治理,在有些时候是面临着很大压力的,比如说之前的亚运年,以及近段时间的国家创卫迎检,都是重要的阶段,在日常的‘苦口婆心’的劝说式执法无法有效解决流动摊贩问题、社会矛盾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采用短时间内奏效的专项整治执法行动。不仅如此,流动摊贩问题的长期存在,给市民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矛盾,我们需要在矛盾的能量爆发之前采用合适的方式对其进行解决,才能更好地维持社会的稳定。”(访谈记录:20160613GFX)
与日常巡查执法不同的是,专项整治行动中的参与执法主体不只是A街城管一个部门,也包括其他政府相关部门,比如公安、工商、食药监等主体,多部门的联合参与为城管部门予以执法权限和执法力量上的支援。在专项整治行动中,工商部门有权限按照无照经营的事由查处流动摊贩,食药监部门能够对一些兜售食品尤其是熟食的流动摊贩采取监督和执法的行为,而公安部门则能够通过暴力机关的职能定位,全程陪同和保障A街道城管和其他部门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相比日常巡查执法中的人少、权少的执法条件,A街道在专项整治行动中能够借助其他执法部门的执法力量,弥补单一部门执法时的缺陷和不足,改善A街城管在流动摊贩治理过程中与流动摊贩群体的街头力量对比。同时在城管执法力量增强的形势下,A街道辖区内的流动摊贩也往往会审时度势,减少与众多执法人员的直接对抗,打消能够逃避执法的侥幸心理。
此外,A街城管专项整治行动相比日常巡查执法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在于,日常巡查执法中城管执法人员只是暂时地把流动摊贩驱离执法的重点区域,很少情况下会扣押流动摊贩的物品,而持续多日的专项整治行动则不同,城管普遍地倾向于扣押流动摊贩的物品,包括车辆等工具和售卖的物品,而流动摊贩对扣押的物品交完罚款之后才可以赎回。而对于该环节的差异之处,A街城管林副队长解释道:“日常中,我们(城管)来了,摊贩磨磨蹭蹭地离开了,我们走了,他们(流动摊贩)就又回来了,起不到治理的效果。而专项整治行动中,通过扣押的方式,能够提高他们摆卖的风险和成本,可以对他们起到一定程度上的震慑作用。另一方面,对扣押的物品记录在案,是对我们严格执法和高强度执法的证明,说明我们的执法绩效,面对上级机关也好有所交代,毕竟投入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是要做出点成效来的。”(访谈记录:20160613GFX)因此,A街道城管执法人员在专项整治行动中,会加大执法的力度和强度,改变日常巡查中的柔性执法状态。
五、案例分析:流动摊贩专项治理的动员机制
(一)执法目标的聚焦
常规治理是广州市A街道城管治理流动摊贩问题的主要方式,而其效果却是比较有限的,以至于A街道的流动摊贩问题至今依然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从城管执法目标实现的角度分析,一方面,城管日常执法目标处于分散状态,城管领导和执法人员的注意力难以聚焦到流动摊贩问题的治理上。A街道城管执法队在流动摊贩治理的过程中,需要承接城管执法市局和区分局的业务指导,流动摊贩治理只是其众多工作职责内容的一个方面,由于日常工作内容的种类多、范围广,A街道城管的执法目标很容易被分散到各种工作内容中去,难以聚焦到流动摊贩问题的治理上。而以运动的方式采取的专项整治行动,在动员机制下,能够聚焦A街道城管更多的执法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在治理目标和内容设置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广州市A街道城管在日常治理过程中多采用柔性的执法方式,执法力度有所保留,一是受制于执法人员数量和执法权限,二是在于保证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后者是各级政府极为重要的目标。因此,A街道城管执法人员在常规治理中,会对治理目标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从而采取恰当的执法方式。流动摊贩等社会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会在日积月累中成为难以解决的社会顽疾,问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会在久拖不决中得到增强,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当城管部门或者政府其他相关部门意识到社会秩序稳定的前提在于对某些社会顽疾的解决时,则会把问题的解决放在突出的首要位置。在开展运动式的专项整治行动中,A街道城管在得到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授意下,会重新对执法目标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把问题的解决视为首要目标,在控制社会风险的情况下,投入较多的执法力量,加强执法力度,力求在短时间内解决流动摊贩问题,缓解因该问题长时期积累所产生的矛盾。
因此,从广州市A街道城管日常执法和专项整治行动的执法目标来看,运动式治理相对于常规治理比较大的优势之一在于,运动式治理能够在动员机制的作用下,聚焦街头官僚的执法目标,把问题的解决上升为街头官僚的首要目标。
(二)执法资源的整合
常规治理资源的不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绝对资源不足,二是相对资源不足。绝对资源不足体现在面对众多的社会治理事务,政府所掌握的资源是极为有限的,不能满足社会治理现实的需要。相对不足则体现为资源分散在不同的部门之间,由于条块的分割,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20]34-37
广州市A街道的流动摊贩问题治理亦是如此,城管对流动摊贩常规治理的失灵,既体现在治理资源有限的数量配置上,又体现在治理资源处于分散状态方面。
广州市A街道城管治理资源的有限性主要表现在物质性资源和执法权限两个方面。物质资源的短缺体现在城管执法人员的数量配备不足,A街道下辖十二个居委会,人口众多,商圈繁荣,而街道城管执法队伍只有八名在编城管员和数十名不在编的协管员,相比繁重的城管工作,人员配备的短缺问题则显得尤为突出。在A街道区域内的某商场周边乱摆卖的流动摊贩分分表示:“我们在这摆摊的人也不少,不惧怕那几位巡查的城管,只要我们护着摊位不被收走,他们也没更多的办法。”(访谈记录:20161023GFX)而在执法权限上面,执法权限的主体可能涉及工商、食药监、环卫部门、交通部门等等,这些部门的执法权限是城管部门所不具备的。同时各个部门由于其本部门职能工作的需要以及部门利益的存在,治理资源在常规治理中处在一种过于分散的状态,无法得到有效的整合利用。
广州市A街道城管针对流动摊贩的专项整治行动,通过高效的动员机制,一方面增加了物质性资源和执法权限,另一方面整合了多部门之间分散的执法资源。专项整治活动主要是通过执法人员的增加、执法设备的投入以及增强执法部门的协调合作等方面(如表1所示)实现了政府内部治理资源条件的改善,以此来保障城管执法人员执法能力的发挥。针对流动摊贩问题的专项治理行动,往往会突破日常巡查执法中的时空默契,改变城管与流动摊贩之间的稳定关系,增加执法主体和对象双方的冲突可能性。而执法资源的增加和执法条件的改善,在提高城管执法人员执法能力的同时,降低了街头执法地的风险和不确性,保障了执法行动的顺利进行,促进城管执法队在短时间内产生执法绩效,实现执法目标。

表1 广州市A街道流动摊贩治理专项整治行动执法资源配备

续表
除了政府治理资源,非隶属于政府内部的社会主体在强大的社会责任的推动下,会选择投入充足的社会资源进入运动式治理。[21]66-67在专项整治行动中,广州市A街道城管执法队借助于社会执法资源,比如社会志愿组织、社会媒体以及部分市民的直接参与,改善执法条件。对社会非政府资源的动员和整合,能够集中民智,提高城管执法队与流动摊贩的力量对比,降低街头执法风险。同时社会主体的参与,能够以第三方的身份对城管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因此,运动式治理的动员机制,能够有效地调动政府治理资源和社会非政府资源,改善街头官僚的执法条件。而其他执法主体和社会组织等其他群体的参与,在保证执法过程顺利进行的同时,加强了对街头官僚执法行为和过程的监督,制约了执法弹性空间,促使街头官僚朝着既定的执法目标采取规范的执法行为。
(三)绩效考核的强控制和强激励
绩效考核的方式能够从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对街头官僚的执法责任进行控制。针对城管在流动摊贩治理过程中执法自由裁量权和执法结果的考核,广州市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和办法:《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2016年第二次修订)》《广州市流动商贩管理暂行办法》。一方面流动摊贩治理的责任由街道城管执法部门向上逐级承接,另一方面流动摊贩治理的监督则通过“条”的关系逐级推进。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对城管的绩效考核方式会根据执法方式的差异有所不同。
在绩效考核的指导意见下,不同执法方式下的绩效考核内容和方法会有比较大的差异。广州市A街道城管的日常巡查执法方式呈现出区域性和时间性的选择性执法,A街道城管的首要目标在于维持辖区内的良好秩序。与此目标相匹配的日常绩效考核的重点不在于问题的解决,而在于城管执法行为的规范,避免不利于社会秩序稳定的其他问题的产生。“在日常巡查执法中,我们选择柔性执法的重要原因在于,不愿意在自己当班时间出现与流动摊贩的冲突事件,一旦发生冲突,靠我们几个城管很难控制混乱的局面,很多时候无论是谁的错,我们一般都会受到一定的处分和惩罚。”(访谈记录:20160613GFX)日常执法考核方式,无法对A街道城管执法人员产生正面的执法动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执法的不作为。因此常规治理中的绩效考核,虽然有利于控制街头官僚的执法弹性空间,但无法为街头官僚提供足够的执法动力。
运动式治理绩效考核在动员机制的带动下,弥补了街头官僚执法动力不足的问题。运动式治理的目标在于解决社会问题,因此激励街头官僚解决该问题,实现良好的绩效,则是绩效考核设置的落脚点。A街道城管在专项整治行动中,在执法条件的改善、绩效考核的激励和制约下,加大了执法的强度和力度,短时间内迅速解决流动摊贩问题。“我们区专项整治行动的考核方式相对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就是全面检查各个街道辖区内出现了几例乱摆卖的现象,不仅包括重点区域,也包括非重点区域,然后给各个街道排名,名次靠后的则会有相应的惩罚。”(20160613GFX)由此可见,专项整治行动中的绩效考核也倾向于通过量化的方式来衡量城管执法人员的执法效果。因此,广州市A街道城管执法队在明确的执法目标下开展可行的专项整治行动,相应的绩效考核不仅能够有效地激励其解决问题,也能够在社会秩序稳定的次要目标下规范其执法行为,控制其执法责任。
六、结论
本文在前人对运动式治理和常规治理体制层面的比较研究基础上,引入街头官僚理论,从治理主体的角度对运动式治理的动员机制进行了探讨。分析发现:运动式治理能够发挥动员机制的强大作用,把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带入政策议程,凝聚政府部门、领导干部以及基层执法人员的注意力,聚焦社会问题的治理目标,整合和利用政府和社会治理资源,以及提供量化有效的绩效考核,在提高街头官僚执法能力的同时,控制其执法弹性空间,达到治理目标,实现治理绩效。
执法能力代表了街头官僚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实现执法目标,执法弹性空间代表了街头官僚是否有意愿实现执法的目标,而对于执法能力和执法弹性空间在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孰重孰轻,本文并没有作出相应的探讨和分析,而在运动式治理日渐受人诟病的情况下,对此问题的讨论又显得很有必要。街头官僚在执法过程中本身具有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选择性执法,既是执法能力不足的变通,又是执法弹性的体现。因此,在治理实践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好执法能力和执法弹性空间的程度问题,则是十分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1][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M].顾速,董方,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2]杨志军. 运动式治理悖论:常态治理的非常规化——基于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分析[J]. 公共行政评论, 2015(02).
[3]徐岩, 范娜娜, 陈那波. 合法性承载:对运动式治理及其转变的新解释——以A市18年创卫历程为例[J]. 公共行政评论, 2015(02).
[4]程熙. “运动式治理”日常化的困境——以L县基层纠纷化解活动为例[J]. 社会主义研究, 2013(04).
[5]陈家建. 督查机制:科层运动化的实践渠道[J]. 公共行政评论, 2015(02).
[6]周雪光. 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J]. 开放时代, 2012(09).
[7]唐皇凤. 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J]. 开放时代, 2007(03).
[8]Mann M.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J]. Archives Europeennes De Sociologie, 1984,25(02).
[9]陈恩. 常规治理何以替代运动式治理——基于一个县计划生育史的考察[J]. 社会学评论, 2015(05).
[10]倪星, 原超. 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规化”的?——基于S市市监局“清无”专项行动的分析[J]. 公共行政评论, 2014(02).
[11]韩志明. 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与责任控制[J]. 公共管理学报, 2008(01).
[12]周定财. 街头官僚理论视野下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研究——基于政策执行主体的考察[J]. 湖北社会科学, 2010(05).
[13]狄金华. 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 对中国中部地区麦乡“植树造林”中心工作的个案研究[J]. 社会, 2010(03).
[14]冯仕政, 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J]. 开放时代, 2011(01).
[15]文宏,郝郁青. 运动式治理中资源调配的要素组合与实现逻辑——以武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为例[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6).
[16]唐贤兴. 中国治理困境下政策工具的选择——对“运动式执法”的一种解释[J]. 探索与争鸣, 2009(02).
[17]臧雷振, 徐湘林. 理解“专项治理”:中国特色公共政策实践工具[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6).
[18]文宏, 崔铁. 运动式治理中的层级协同:实现机制与内在逻辑——一项基于内容分析的研究[J]. 公共行政评论, 2015(06).
[19]刘磊. 街头政治的形成:城管执法困境之分析[J]. 法学家, 2015(04).
[20]容志, 胡象明. 治理资源的重构:安全生产事故的制度反思[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4).
[21]文宏,郝郁青. 运动式治理视阈中地方政府调配非隶属关系主体资源的逻辑分析——以兰州大学“双联”工作为例[J]. 思想战线,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