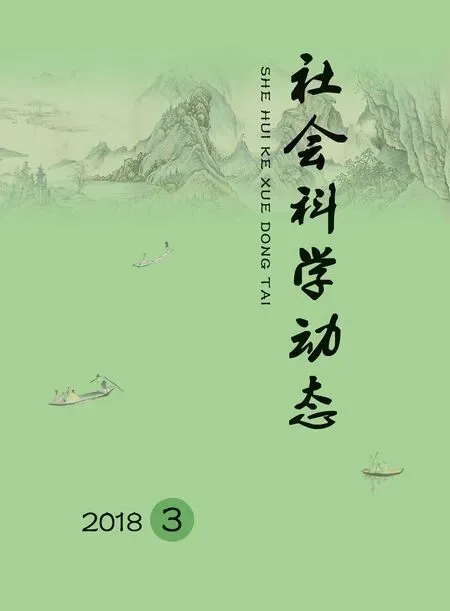中国古典外交研究的扛鼎之作
——黎虎先生《汉代外交体制研究》述评
杨永俊
对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的研究,黎虎先生应该是其中的拓荒者与集大成者。他于1979年发表《解忧公主出塞的历史贡献》,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外交历史事件的探讨①。之后一发而不止,相继于1986年发表《北魏的四夷馆》②,1988年发表《殷代外交制度初探》③,1993年发表《郑羲使宋述略》④,或论述外交设施,或阐述外交制度,或论及外交使节,从不同角度与侧面开展了对中国古代外交的研究。先生于1998年出版的《汉唐外交制度史》专著,既是对自己研究中国古代外交成果的总结,更是全面系统探讨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山之作⑤。在此之后,研究中国古代外交的论著与论文逐渐增多,俨然形成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一个不可小觑的热点。黎虎先生于2014年推出的煌煌巨著《汉代外交体制研究》⑥,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研究的内涵,精彩呈献了在精深考证基础上的新颖观点,切实提升了中国古典外交研究的理论高度。
一、系统研究,拓展中国古典外交内涵
《汉代外交体制研究》是黎虎先生积15年之功的研究成果。论著分上下册,共1200页,近100万字,7大章,分别论述了汉代外交前驱——周代交聘、外交媒介——使节、外交方式、外交通意工具、外交接待设施、外交礼仪与法纪6大内容,其中外交方式分为上下两章,一共用了8节内容进行介绍。黎先生的《汉唐外交制度史》和《汉代外交体制研究》构成了我国古典外交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内容,由此,我国古代外交的全貌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都得到了十分全面系统的呈现。不宁唯是,上述诸构成要素之间的匹配关系、主从关系、内在逻辑关系,首次清晰合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中国古典外交体制的复杂、有序、严密、完善几近一览无余。黎先生的著作在对外交体制全面、精详考证的同时,还有对我国古代外交原则的理论阐述,对外交发生学的学理思考。内容系统而全面,论述充分而透辟,观点新颖且关切时代外交主题。
相对于最近十多年出版的几部论述我国古代外交方面的论著,黎先生的论著在内容的系统性、全面性与创新性方面无疑是最为突出的。
李云泉先生最近10年先后出版了《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外交关系体制研究》⑦与《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⑧两部著作。两著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分六章论述我国古代朝贡制度历史发展演变脉络,明清两代朝贡制度则为其重心所在。李著合“朝”与“贡”为一,把“朝贡”当作我国古代外交的主要形式,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朝”与“贡”尽管经常是相伴随发生的外交行为,但两者性质有别,两者或结合进行,或独自开展。蔡宗宪的《中古前期的交聘与南北互动》⑨论述中古前期南北朝廷之间以交聘为形式的外交活动,然交聘仅仅是我国古代外交形式的一种,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形式,其内容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吴晓萍的《宋代外交制度研究》⑩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从其强调外交决策制度与外交机构的内容可以看出,吴著的写作深受黎先生《汉唐外交制度史》的影响;同时,吴著也试着从使节、外交礼仪、外交文书等制度层面进行系统化的完善,但是,其内容的系统性、全面性、深刻性与黎先生的《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差距较大,不在一个层级。韩雪松的博士论文《北魏外交制度研究》⑪也大体遵循黎先生的《汉唐外交制度史》的写作范式,抓住外交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并侧重于对遣使、接待、文书三大外交制度的论述。其内容未超出黎先生关于我国古代外交制度与体制的论述范畴。
上述论著都从各自关注的时代与领域,丰富了中国古代外交研究,都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学术价值;但是,从内容之全、观点之新、理论之高、论述之精等方面进行对比,黎先生的《汉代外交体制研究》无疑是其中最为厚重的学术巨著。
二、观点新颖,建立在充分论证基础上
一篇论文抑或一部专著,判断其学术价值之有无或大小的主要依据:是否为学术界呈献了新观点,或提供了怎样的新观点。《汉唐外交制度史》填补了我国外交制度系统研究之专著空白。它首先提出了“外交圈”、“区域性外交与世界性外交”以及“中国古典外交”等新概念,认为世界外交历史是从“区域性”到“世界性”的发展过程,中国古代外交一直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而不像“西方外交圈”是多中心的⑫;同时,论著还提出了中国古代外交的三种类型与层次:中原皇朝与当时的外国、而且现在其地还在中国境外的国家的外交;中原皇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外交;中国境内各独立政权之间的外交⑬。在此基础上,《汉代外交体制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对东亚外交圈的论述,阐述我国古典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新观点。这些新观点或源于推陈出新,或匠心独运所得,都是建立在大量史料引述与谨慎求证基础之上。略举数例以享读者。
1.汉代外交使节多用勇士而先秦多用辩士
《汉代外交体制研究》第二章第一节论述了汉代外交使节人选特点,“先秦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的外交使节是以‘辩士’为主,‘勇士’(‘壮士’) 次之,而汉代则以‘勇士’(‘壮士’)为主,‘辩士’次之。这是中国古代外交使节人选所发生的第一次大变化。”⑭
为了说明汉代外交使节多用勇士,黎先生利用表格十分详细地列举了汉代出使人员的身份与职衔状况,对比统计出汉代外交使者中“勇士”数量多于“辩士”,以数据说话,雄辩有力。
黎先生进而探讨其变化的三大原因:一是“外交圈由先秦的华夏文化圈向异文化圈的扩展”⑮;“二是外交对象中社会发展阶段后进于中原王朝者大为增加”⑯;“三是随着外交空间的扩大导致外交旅途的空前遥远和艰险”⑰。
黎先生认为其变化的深层原因是:以秦汉统一国家形成为标志的中原国家走向成熟,而其周边的匈奴、西域诸国、西南民族政权开始形成雏形国家或族群联盟,于是有了开展相互交往的基本前提条件。随之我国古代外交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以内部交聘为主改变为与外部交往为重。而不同国家与族群间因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语言上的隔阂,一定程度上导致华夏辩士施展其巧舌如簧长技的重要性降低。
先秦时期的交聘,主要行于华夏诸侯之间,因同种同文,交聘人员多用辩士;两汉凿空,外交活动开辟新天地,种族不同文化相异,地域遥远交通险恶,外交使节自然以勇士为主。得出这一结论似乎不难,但如果研究者没有贯通中国古代先秦交聘与秦汉之后外交的功力,势必不能形成对两大时代不同外交体制的对比分析,则恐怕很难得出这一结论。黎先生论著先有第一部分对先秦交聘精深研究的基础,接承的第二部分又对汉代外交人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故这一结论的得出实属顺理成章。
这一新见不仅从一个新颖的视角揭示了先秦到两汉外交使节人选的变化,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期间的外交巨变,在史学研究方法论上具有宏观审视与微观考察相结合从而结出学术硕果的启示意义。
2.婚礼催生后代的交聘礼仪
婚礼是交聘礼仪的重要渊源,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共性”与“相关性”,这是黎先生的重要发现之一。一般情况下,很少有学者会把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婚礼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外交礼仪联系起来。而《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在论述先秦交聘时,把交聘礼仪与婚姻礼仪联系起来,认为婚礼早于交聘礼仪,它对交聘礼仪有影响并发生催生作用;“联姻虽然不能说是远古时代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交往的唯一方式,但其为当时最为频繁、活跃的交往方式则是无疑的,它所积累的交往方法与惯例影响了其后的交聘礼仪应当是很自然的事情”⑱。考虑到我国古代家国同构的国家建制特色,黎先生上述论述既得之自然,又十分在理。
黎先生深入探讨了婚礼与交聘礼之间存在着诸多“共性”或“相似性”,归纳为4个方面:“均属对外行为”⑲,“均需要通过使者而进行”⑳,“均具有对等性特征”㉑,“具体仪节的相似性”㉒。黎先生认为,婚礼与交聘礼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相似性并非偶然,恰恰是前者对后者产生重大影响的反映。国家形成前就已形成的婚礼不仅影响并催生国家形成后才出现的交聘礼,而且在家国制度形成后,婚礼与交聘礼之间依然存在着长时段的关联性,具体表现在先秦时期分封诸侯国之间频繁的政治联姻活动,这时的政治联姻往往与分封国家之间的交聘政治活动互为表里,遵循着大致相同的仪式传统。先秦时期婚礼与交聘礼的渊源关系甚至在我国汉唐及其后的古典外交关系中烙下深深的印记,表现为我国历史上对外关系往往采取独具东方特色的“和亲”(广义)外交。
这一重要发现,不仅于古典外交生成学具有别开生面的学术价值,而且是我国近年来礼学史研究上一个真正的进展,开辟了一条中国古代礼学研究的独特路径,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3.古代外交礼仪法纪中的外交惯例
本书第七章以较大篇幅论述国际惯例与国际法问题。黎先生认为:“汉代外交礼仪中的对等、平衡与非对等、平衡;报答与报复;外交特权与特权之侵犯等方面的原则、规章无不蕴涵着丰富的古典国际法的原则和规章,一定意义上中国古代的‘礼’就是东亚外交圈中的国际法的胚胎,‘礼’与‘法’有着相生相成的内在关系。”㉓在外交准则惟西洋法马首是瞻的今天,黎先生的发论可谓振聋发聩,令读者耳目一新。
黎先生并未就此打住,而是进一步申论说:“以外交圈中强势和处于中心地位一方之国内法或惯例延伸于外而逐渐成为国际惯例或国际法,这是古代国际惯例或国际法形成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㉔接着列举了汉朝与匈奴之间在“国家的承认、领土与疆界”、“条约”、“涉外犯罪”三个方面的大量历史事例,详尽论述了汉代的“礼”“法”往往成为东亚外交关系法的国际法规。
汉朝的外交礼仪法纪为什么能成为当时东亚外交圈中的国际惯例与国际法?黎先生从综合国力上求解:“因为汉王朝是当时东亚外交圈的核心,其综合国力无可匹敌者,其法律体系之完备亦无出其右者。在与四方国、族外交关系的互动中,基本上是汉王朝处于强势地位,故各种外交谈判和协议、条约中汉王朝处于优势和主动地位,令其基本外交意愿和政策得以遂行。”㉕综合国力中最为关键的是政治文化软实力,表现为周秦与两汉时期的中原王朝政权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与超越周边的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文化优势。
黎先生的上述论述,是对《汉唐外交制度史》中所提出的与“西方外交圈”相对应的 “东亚外交圈”新理念的进一步阐述与深化,并且上升到了一般外交惯例及国际法的这一规律性的高度。
三、学理探讨,提升中国古典外交研究理论高度
对中国古典外交的研究,近年才形成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从对现有成果的梳理分析,大多数成果还处于对外交史料的爬梳整理、对外交历史事件内在联系着手探究的起步阶段。尽管有学者进行过贯通古今的研究,如李云泉的论著六个章节中用专章内容论述朝贡的理论基础与礼仪原则,从华夏中心意识与大一统观念、华夷之辨两个方面展开这一话题的论述,然而不论是“华夏中心意识”,还是“大一统观念”,抑或“华夷之辨”这些观点,基本上都是传统史学聒叙的老话题,其理论建树实则不多。大多数成果属于断代史,如上述吴晓萍、蔡宗宪与韩雪松的专著或博士论文,侧重于朝代外交事务的外貌式研究,基本上还未上升到中国古代外交理论探讨的高度。这些学者之所以在学理阐释上存在共同的缺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作者从事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时间还不长,仓促上阵,史学积累与理论思维火候的欠缺,或多或少都有关系,学理探讨要在长期历史研究与思考中积淀。
黎先生从事中国古代外交史的研究,如果从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开始,则已经有30余年,如果从其《汉唐外交制度史》论著写作开始,也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黎先生学术视野广阔,涉及历史领域较广,跨越时代较长,对中国古代外交的研究几乎没有间断,即使其笔触曾经伸向饮食、民俗、职官、民族关系,也可以看作是作者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自然延伸,故而,中国古代外交课题可以说是他整个学术研究的中心与主要建树。也正因为这样,黎先生在中国古代外交研究方面的知识积淀与学理思考时间最长,其中国古代外交理论架构已经初步成型并呈现出鲜明的学术特色。黎先生在《汉唐外交制度史》中已经提出并开始探讨“外交圈”新概念,也试着对“中国古典外交”进行理论探讨;这种学理探讨在其《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中展示了向广度与深度延展的理论发展趋势,成为其内容中起着画龙点睛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1.周代交聘的基本原则——对等性
《汉代外交体制研究》提出了“对等性原则”㉖、“礼尚往来原则”㉗,它是对我国古典外交关系形成之前先秦外交关系研究的高度的理论提升。对等性原则体现为交聘主体的对等性、接待人员的对等性与接待仪节的对等性。
“对等性原则”产生的渊源有三:一是政治原因,即封建体制中敌体关系的形成发展。这种敌体关系恰恰是在封建等级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在周天子作为等级塔尖,其下的公侯伯子男等诸侯之间,各自形成不同的对等政治实体。随着周天子最高王权衰落,对等政治实体逐渐向敌体关系转化。以往学术界恰恰被这种封建等级关系所蔽,以为周代交聘是一种非对等性,而未能透视其对于对等性关系的催生意义。二是思想渊源,即源自我国传统的礼学思维。礼的本质特征是“报”,一来一往谓之报。“礼尚往来”是对等原则在礼仪关系中的体现和运用。三是哲学渊源。我们的先人对礼所具有的往来原则的认识源于中国传统的易学两仪思想,源于国人关于万事万物无不由对立双方构成的朴素辩证思想。论著把“对等性原则”产生的哲学渊源与周代的“中”、“和”、“德”哲学理论联系起来,认为交聘所遵循的“对等性原则”恰恰是这种哲学思想在外交事务中的一种体现。
黎先生进而从普世性外交准则高度进行剖析,“周代交聘礼中的对等性原则不仅在日后汉唐时期的交聘——外交制度中有所继承、借鉴,而且与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对等性原则亦有相似、相通之处”㉘,先秦交聘所遵循的对等性原则其实是一种具有突破时空局限的普世性外交准则,它既适用于我国的先秦外交,也作用于汉唐宋元明清整个中国时代的外交,并为近代与当今国内外的外交活动所共同遵守。
这一理论建树,不仅揭示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灵魂和本质特征,还颠覆了发端于“欧洲中心”论的传统外交学中的定势思维,对于争得中国学术界在古典外交学理研究中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2.汉代外交方式的“普世性原则”
《汉代外交体制研究》说:“上述朝、贡、赐、封、质侍、和亲、互市等为汉代主要的外交方式,是为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外交之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们并非仅仅为中国古代外交所行用,同时也为古代世界各国外交所行用,是为普世性的外交方式,也就是说它们不仅通行于东亚外交圈,同时亦通行于西方(西域)外交圈,可谓举世皆然。”㉙论著选择了朝贡、质侍、和亲三种外交方式,从东西方的外交史事进行论述,论证其普世性的体现。
对于汉代外交方式的普世性的形成,黎先生认为是由古代世界外交的普世性所决定的,“中国古代外交是古代世界中独具中国特色、东方特征的一种古典外交,同时我们也要指出,中国古代外交也是具有普世性特征的外交,它的基本内涵和特征与古代世界各国的外交也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国古代外交既非独一无二,更不是另类的”,“古代外交的普世性除了体现于上述外交方式之一致性之外,还体现于外交的形成以及外交体制其他构成方面的一致性”㉚。
就中外文化在“礼”与“法”上的差异可能导致读者对中外古代外交的误解,黎先生特别强调指出:“论者往往强调古代中国为‘礼仪之邦’,似乎‘礼尚往来’为中国古代所独有,事实上讲求礼仪、礼尚往来举世皆然。虽然东西方文化存在地区性差异,例如西方世界强调‘法’,东方世界强调‘礼’,但是彼‘法’中有‘礼’,同样在此‘礼’中有‘法’,不过其角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也就是说西方世界的‘法’中不仅包含着国际法,同时也包含着外交礼仪,东方世界的‘礼’中不仅包含着外交礼仪,同时也包含着国际法的内容。”㉛这一新见不仅对于认识东西方外交的共性,对于中外文化和历史比较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黎先生进一步从学理层面探讨古代世界外交方式普世性的原因,“古代东西方的外交基本上是不约而同在各自的国际环境中独自孕育形成起来的,究其原因,除了相互影响、借鉴之外,最主要和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类本性的相同与相通”,“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在人际关系中,希望得到对方的善待、尊重,因而逐渐产生、积累了人际关系的种种惯例、规则,‘礼’、‘法’即从中萌芽发展起来。因此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和国家的外交中,礼尚往来和对等性精神就不约而同成为人际关系的‘礼’与‘法’乃至国家之间外交中的普遍惯例和规则,是为外交之‘礼’与‘法’”,“外交的普世性归根结底是由人性的相同相通所决定的”㉜。
从外交普世性角度来恰如其分地分析我国古代外交方式,并从人性的共性角度来探讨外交普世性的根本原因,这样的论述无疑是极其深刻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人们习惯性地把外交定位为西方近代国家政治的产物,探讨外交的普世性都习惯性地以西方历史与西方价值观为依据,黎先生能够在西风劲吹下坚守中国历史文化本位,从我国古代自身的外交方式出发,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国际普遍性原则,这种以我为主的研究范式与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坚守态度值得肯定与称赞。
3.外交与“人性”及“国性”的关系
最能体现黎先生《汉代外交体制研究》理论高度的是关于外交与“人性”及“国性”关系的论述。在论著“跋语”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探讨汉代外交之所以能取得丰硕成果的原因,认为汉代外交的发展除了其综合国力的空前提升这一根本原因之外,“与‘人性’和‘国性’也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黎先生给“人性”与“国性”进行了界定,“我们所说的‘人性’是指人的本能及其内在精神因素,所谓‘国性’是指‘人性’之体现于国家的本能及其内在精神因素”,“‘人性’与‘国性’是相通相关并相互影响的”㉝。
黎先生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一般意义上的外交起源问题:“‘外交’既是‘人性’也是‘国性’的重要属性之一。人的本质是其社会性,人不能脱离社会而自闭独处,故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是人的‘本性’之一;推而广之,邻里之间、家庭之间、氏族部落之间,乃至国家产生之后的国与国之间,无不需要相互交往而不能自闭独处。相互交往即‘外交’的原始,相互访问亦为外交之原始。”这种由近及远的探讨看似浅显易懂,却往往为外交史研究者所忽略。忽略之原因,或许认为这种类比推理过于简单,不成理由;或许认为过去的研究者从传统思维定式出发,过于关注外在宏观层面上的国家政治经济需求因素,而相对忽视了内在的微观层面作为国家构成因子的人及其心理因素。
从人的基本属性探讨汉代的外交特征,黎先生认为,“汉代突出的时代精神,也是这个时代的‘人性’与‘国性’中的亮点”。论著从“利欲‘本性’的发挥”㉞、“好奇心‘本性’的发挥”、“想象力‘本性’的发挥”三大方面展开论述,并以汉代凿空西域、打通西南为例子,论证了汉朝的外交与汉天子的欲望追求以及西域诸国统治者对汉代财富的巨大吸引力的密切关系,“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进程向人们提供了准确无误的信息,对于利益追求的‘本性’是外交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汉代外交关系中所展现的探索、开拓精神是极其鲜明突出的,那是一个充满探索、开拓精神的伟大时代,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的好奇心就是十分突出的”;“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外交谋略——翻开了汉代外交的另一新篇章”㉟。
言外交,多从政治之延伸、军事之手段、经济之需要、文明差异之相倾等角度或原因来探讨一般意义上的外交动力与渊源,较少从人性的自然需求角度与统治者作为自然人的心理或意志角度展开剖析。黎先生能从心理层面的崭新角度,探讨我国古代外交与一般外交的动因与规律,极大地开辟了外交学研究的新路径、新天地。
四、考证精细,或补经史之失或还历史之真
《汉代外交体制研究》是一部叙议结合的长篇学术巨著,其立论的新颖、学理的精深,往往建立在对外交史料的详细爬梳与外交史事的精详考证钩沉还原的基础上。
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钩沉史事,寻找内在联系,还历史事件以真实面貌。历史越是久远,史料记载越是简略,历史真实的还原越加困难。尽管如此,历史研究者依然秉着谨慎求真的态度,尽量探讨出历史事件之间内在联系,还历史事件以真实。在叙述汉代外交历史事件时,黎先生对历史上叙述不清或考证失误方面的问题,做了不少补正的工作。
1.关于两汉朝会中之“三独坐”问题
朝会是外交活动的重要形式。然而,关于两汉朝会中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尚书令独享专座原因的探讨,不论是《汉官仪》的解释,还是杜佑的注释,乃至迁延至今的许多论著,都没有很好说明其受尊重的特殊性是什么。黎先生认为,“‘三独坐’问题必须与朝会问题联系起来,必须与他们在朝会中的职责——监察联系起来,必须将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才能说明何以此三者得以在朝会中受到独坐之殊遇?以及他们在朝会中独坐的作用和意义。”㊱
黎先生正是本着对“三独坐”在朝会中所发挥的监察作用,从整体角度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御史中丞是朝会法令的监察者,司隶校尉是朝会纪律的保证者,而尚书令是方针政策与制度的这一更高层面的监督者。三者之间分工不同,各有侧重,但相互制衡,共同形成三位一体的监察机制。“三独坐”之所以独尊,正因为他们的共同作用,确保朝会的胜利进行。
黎先生还进一步考证了“三独坐”逐渐形成的过程,认为传统的关于“三独坐”形成于东汉值得重新考证,因为早在西汉成帝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三独坐”,著中列举了大量的相关史料予以论证。
黎先生的考证,不仅使两汉时期朝会中独尊“三独坐”的原因解释得更合情理,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还通过史料的列举,让“三独坐”逐步形成的时代脉络清晰起来。
2.关于典客、大行令、大鸿胪职官设置问题
典客、大行令与大鸿胪是两汉时期最重要的外事职官。然而对这些职官设置时代,相关历史的记载不相统一;后世史学家的校注歧见纷纷。黎先生并没有回避这一问题,他通过罗列西汉典客、大行、大鸿胪任职表,把这3个职官出现的史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得出以下认识:
(1)任职典客者,见于高帝、惠帝、吕后、文帝时期,不见于景帝及其后;任职大行者唯见于武帝前期;任职大鸿胪者始见于武帝太初元年及其后,而不见于此前之任何时期。
(2) 臣瓒、颜师古等关于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已改典客为大鸿胪之说可以否定。
(3) 从汉初直至武帝太初元年(前104) 之前的元封六年先后以典客、大行为官称,均不见以大鸿胪为官称,恰恰在太初元年(前104)始见以大鸿胪为官者。表明《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太初元年改大行为大鸿胪之记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4) 与此相关,《史记·叔孙通列传》 《索隐》所引以及《汉书·叔孙通传》注引韦昭谓“大行人掌宾客之礼,今谓之鸿胪也”,这个注解并不正确,因为汉七年朝会中出现于《史记》 《汉书》中司仪官员“大行”并非日后之大鸿胪前身,而是典客之属官。
(5) 结论:《汉书·景帝纪》中元二年所载令中之大鸿胪、大行,并非当时之官称,而是西汉后期之官称;《史记·景帝本纪》以及《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景帝中元六年改典客为大行,武帝太初元年改大行为大鸿胪的记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黎先生的考证基本上可以将这个两千多年的学术纷争划上了一个句号。
3.关于“谒者治礼”中的“治礼”的解释问题
论著第七章第一节论述两汉的外交礼仪,涉及到西汉七年(前200)朝礼中有“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的记载,学者对其中的“治礼”有不同的理解:或认为是官名,是“治礼郎”的简称,乃大鸿胪之属官;或以为是动作,作“赞助礼仪”之意。如果脱离其他史料单独解释,则两说皆能自立,但如果结合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史料,就会发现两说都有问题。黎先生在引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里的‘治礼’当为官名,他们与谒者一起负责朝会傧赞。何以然?”“首先,西汉有‘治礼’一职。治礼为鸿胪属官大行之属官。”㊲“其次,从其他礼仪场合中两者合作傧赞事宜中可以推知。”㊳“ 第三,从后世朝礼中谒者与治礼合作傧赞事宜中亦可推知。”㊴
黎先生尽管依然认为“治礼”是官名,但认为它不是大鸿胪属官“治礼郎”,而是大鸿胪属官大行之属官。鉴于先生对先秦两汉经史资料十分精熟,在职官训诂方面有着深厚造诣,加之所罗列的历史证据丰赡确凿,故而黎先生的这一新见更符合历史真实。
上述精彩考证例子在论著中不胜枚举,如第四章第六节对两汉时期“和亲”历史现象的考证,第七章对周秦两汉朝礼仪式中的“九仪”与“九宾”历史沿革的考证与梳理,等等,莫不如此。
五、关切现实,对当前与今后外交活动以深刻启迪
本论著的研究对象虽然是我国汉代外交体制,但其总结的中国古代外交理论与剖析的中国古代外交经验,蕴含着著者对于现实的关怀与思考,对我国当前与今后开展外交活动提供了深厚的学术支持。
1.外交的基本原则古今相通,中外趋同
外交的基本原则如对等性原则、礼尚往来原则、趋利原则、维护核心利益原则等,是不分古今中外,放之四海而皆准。黎先生在论述先秦交聘的“对等性原则”与“礼尚往来原则”,就已经论及到它对后世外交的通用性;论述两汉外交方式的普世性原则,认为这种普世性原则建立在人类所共有的心智结构与大体趋同的心理基础上,同样具有普世的特征。尤其是在本书“跋语”部分,黎先生从人的社会性与心理普遍存在的利欲心、好奇心、想象力等角度,阐释古今中外外交活动的共同心理基础。汉代所开展成功的外交活动,恰恰是基于这些基本原则而取得的,它的成功为我国当前与今后开展外交活动积累了可供借鉴的宝贵财富。
2.以“和亲”为特色的汉代外交,值得殷鉴
殷鉴的可能,建立于所处国际环境的大体相近或相似。随着我国经济总量逼近世界超级大国美国,随着我国政治与军事实力在稳步提升,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现在所处国际环境与汉代中前期的国际环境有很大的相似性,如当前的中、美、俄关系与西汉前中期的汉、匈奴、乌孙关系,西汉统治者在协调三者关系中通过自身成功的以“和亲”为主要特色的外交手段削弱匈奴,为汉朝的发展强大扫平道路。汉代的广义“和亲”政策与我国建国初的和平外交五原则及改革开放时代的“韬光养晦”政策,与我国对外关系中的“搁置争端”政策以及近年提出的“和平崛起”政策,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相似性。针对我国当前所面对的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政府似乎应该从汉代的“和亲”与先秦的“和戎”外交策略中汲取经验,从而成功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开展的政治外交围困。
3.对外交软实力的强调与论述,意味深长
黎先生不仅在本论著的相关章节中,而且特别在跋语部分专门就外交方面的软实力问题加以论述,所费笔墨甚多,认为我国两汉时期外交上很善于利用软实力文化牌,达到以柔克刚的奇效。黎先生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大量的史实论述我国汉代重视外交软实力,应该是有其对现实外交问题的思考甚至焦虑在其中。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高度发展、而文化软实力相对薄弱的尴尬处境,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强势,我国在外交场合上经常处于左支右绌的不利境况。西方的文化,西方的世界观,被视为普世的观念,成为西方干预其他国家的有力武器。我国当前外交的劣势,恰恰是因为政治与文化软实力的不够强大造成的。如何夯实我国的政治文化软实力,并以之转化为外交魅力,这是值得当前我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思考的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提倡技术创新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正是看到了我国当前国家竞争力的短板在于文化软实力。
六、瑕不掩瑜,完善拓展空间依然存在
《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在中国古典外交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实际上还可以胪列更多,以上仅为笔者感受最为深刻的几点。瑕不掩瑜,再伟大的著作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因此,本书存在一些白璧微瑕的问题亦属难免,主要表现在篇幅结构、内容剪裁与理论阐述三个方面。
1.篇章结构,不够匀称合理
本书从外交媒介、外交方式、外交通意工具、外交设施、外交礼仪法纪五个方面,对汉代外交体制进行论述。但篇幅有所侧重,其中“外交方式”内容最多,篇幅接近全书三分之一;对“外交礼仪法纪”,也不惜笔墨,篇幅仅比“外交方式”少30余页;论“外交媒介”的篇幅,比“外交礼仪法纪”少了近60页,不到“外交方式”的一半;篇幅较小者为“外交通意工具”,内容仅为“外交媒介”的一半、“外交礼仪法纪”的四分之一;篇幅最小者则为“外交设施”,仅有38页,大约相当于“外交方式”的十分之一或“外交礼仪法纪”的九分之一。由“外交方式”的360页,降至“外交设施”的38页,这种内容篇幅落差呈断层式跌落,篇章结构安排似不尽合理。当然,作者对此显然也有所意识,如对“外交方式”的论述,分为上、下两章,目的大概就是有意令章节间的落差幅度变小。对于本书篇章结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盼望作者将来修订时,能够有针对性地加以调整完善。
2.内容剪裁,还需精雕细刻
本书可谓鸿篇巨制,史料翔实,驰论纵横捭阖,析理鞭辟入里。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该书的篇幅结构还可继续优化,这就要求作者对论述的内容作进一步的精雕细琢。窃意可以考虑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其一,在论述汉代外交体制之前,应首先叙述汉代外交体制形成的背景与体制形成发展的基本情况。然而,作者却以“周代交聘——汉代外交之先驱”作为开篇,离“汉代外交体制”的主题似乎有些遥远,容易让读者产生远离主题的感觉。
其二,阐述汉代外交体制,仅涉及外交媒介、方式、工具、设施、礼仪、法纪六个方面,内容的完整性仍嫌不够。上述六个方面确属汉代外交体制的主要内容,但汉代外交机构、汉代外交决策机制等方面,似仍可略加交待。一种可能是,黎先生在撰写本书时,实际上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只是因为《汉唐外交制度史》对此已有精致阐发,故此处未再重复。《汉代外交体制研究》毕竟属于一朝的外交体制专论,与《汉唐外交制度史》这种纵跨数代、历时千载的外交制度史研究,无论在写作目的性还是论著的完整性上,都有不同要求,聚焦一朝一代的外交制度史偏重于内容的全面系统,即使在其他论著中已有阐述,也有必要进一步复述或重写。当然,这个看法纯属笔者的一孔之见,未必恰当。
其三,论著缺少一个总括性的章节。作为一部全面深入阐发汉代外交体制的巨著,该书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提炼,不能将论述止步于对外交体制基本内容的论述,还应该在此基础上,总括、归纳出汉代外交体制的特色,及其对后世外交制度发展的深刻影响。不仅可以从横向的角度,与同时代的古罗马帝国外交体制进行对比研究;还可以从纵向角度,与先秦交聘作比较,还可以与隋唐乃至其后的外交体制作比较,如此则会极大拓展本论著的研究视野。
3.理论架构,有待系统全面
本书属于历史学与外交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著者需要对这两大学科有比较系统全面深刻的了解。黎先生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著名专家,对中国古代史的了解十分全面系统,理解精深独到;同样,因为从事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研究历时较长,他对外交学的基本原理及中西外交历史发展脉络也有较全面系统的掌握,从其对汉代外交方式的普世性与汉代外交“礼”“法”的国际法特点等的论述可以略见端倪。不过,就本书所提供的信息来看,黎先生对于现代外交学的某些理论,重视程度稍嫌不足,对于所涉及的现代外交理论内容的阐述,系统性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如果本书在这个方面对于现代外交理论能够再多一些关注的话,则其在理论方面的建树,将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提升。
最后,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上对《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一书所存在问题的“指正”,纯系笔者一管之见,未必准确。事实上,笔者所指出的这些问题,皆属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丝毫不会影响本书在中国外交史研究领域、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不仅如此,黎先生在本书所确立的中国古代外交体制的写作范式,完全可以用之于从事其他朝代外交体制的研究。如《魏晋南北朝外交体制研究》、《隋唐外交体制研究》均可依本书范式而面世,从而形成从周秦到隋唐的中国古典外交体制研究系列,这既是黎先生的心愿,亦为学术界所殷切期盼。
注释:
① 黎虎:《解忧公主出塞的历史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② 黎虎:《北魏的四夷馆》,《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
③ 黎虎:《殷代外交制度初探》,《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④ 黎虎:《郑羲使宋述略》,《文史哲》1993年第3期。
⑤⑫⑬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6、7、9页。
⑥ 黎虎:《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⑦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⑧ 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
⑨ 蔡宗宪:《中古前期的交聘与南北互动》,台湾稻香出版社2008年版。
⑩ 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版。
⑪ 韩雪松:《北魏外交制度研究》,吉林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 黎虎:《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 198、198、199、201、177、118、122、124、126、1041—1042、1042、1081、66、89、89、660—661、677、 680、683、1130、1131、1136、 899、838、 840、8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