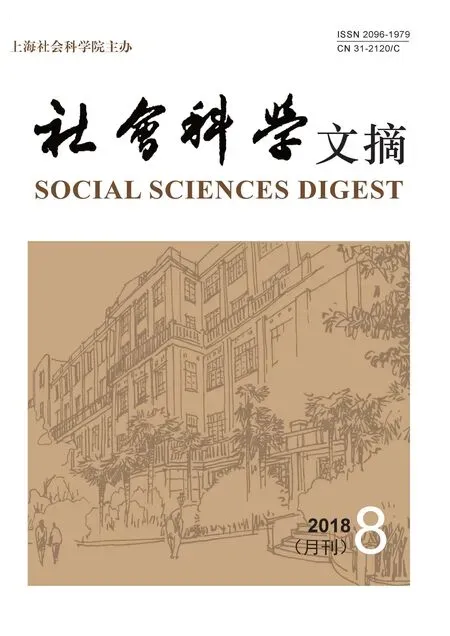关于中国乐文化传统视域下的《牡丹亭》评价问题
——兼与朱恒夫等商榷
《牡丹亭》历来被视为明清文人戏曲的代表作。它在以“妙处种种,奇丽动人”而不断为人称颂的同时,其主题思想的矛盾与剧情关目之不足甚至戏词中之淫词亵语也常常为人所诟病。朱恒夫教授等数年前发表了《作品的缺陷与评论的缺陷——读汤显祖的<牡丹亭>及其评论》一文(以下简称《缺陷》),该文认为《牡丹亭》“具有很大的思想及艺术价值”的同时,“它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一一列举了《牡丹亭》剧情构造的“芜杂”、关目编织的“松散”以及人物形象及主题思想的矛盾;指出了当代评论界对于《牡丹亭》思想价值的误解。
追根究底,《牡丹亭》乃是根植于一个深厚的中华乐文化的传统当中,它不仅属于一般文人自我述说与倾诉的传统,即抒情诗的传统,更是属于在不断被演述、被生发、被重组改造的话语系统,即乐文化的传统。故而,本文意在将《牡丹亭》置于其所赖以生存的中国古代乐文化的传统当中来加以释读和评价,以期获得关于《牡丹亭》的更为准确和全面的理解,消除一些不应该有的误读。
《牡丹亭》的传统基因
很显然,人们已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不能以一种理想的甚至西式的戏剧样态来衡量和剪裁《牡丹亭》,更不能以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原则来“硬评”《牡丹亭》。因为,对于《牡丹亭》因梦成戏、慕色而亡、人鬼幽媾、还魂复生的剧情构造来说,“如果仅仅将‘还魂’情节解释为浪漫主义手法或超现实主义方法,实际上很难让今天的欣赏者进入汤显祖所设置的语境中并获得真正的审美认同”,甚至很可能造成对于《牡丹亭》思想与艺术的恣意曲解。于是,我们也就有必要去追问:汤显祖所设置的语境具体是什么?《牡丹亭》究竟属于什么样的传统?它有着怎样的文化传统的基因?
在剧情构造上,《牡丹亭》全剧共有52出,以主人公杜丽娘游园之际的春闺一梦为关节点,一线绵延,多有穿插,且起伏不定,以至于给人以“结构松散”“篇幅过长”的感觉;且自《牡丹亭》诞生以来,就很少有全本演出,甚至每有演出,必加删减。《缺陷》一文对于《牡丹亭》“作品的缺陷与评论的缺陷”的分析虽由此出发,却没有追根究底,至少并未曾顾及到《牡丹亭》的传统基因。该文只是拿着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尺度来要求《牡丹亭》的“真实性”而排斥其“虚幻性”。殊不知,《牡丹亭》虽有其取材渊源,却绝非因袭成篇。它其实更属于一个文人的奇思妙想。
中国传统乐文化大致有着三个层面的建构:其一是巫乐文化,其二是礼乐文化,其三是俗乐文化。三种类型文化的层垒叠合构成了中国古代乐文化的基本形貌。它们相互关联,又各自有别,不断重组,衍生出包括歌舞表演以及戏曲等在内的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乐文化的样式。中国传统乐文化成为戏曲艺术的真正母体。戏曲蕴含并传承着中国乐文化的传统基因,同样,乐文化也影响并制约着戏曲的形态样式及其演变。无论是曲还是乐,无非都是对于戏曲乐文化传统的一种体认和追溯。某种意义上,《牡丹亭》也许更近乎“古之乐”的。当然,戏本于乐,却不等于乐。显然,《牡丹亭》并非只是古代版的“人鬼情未了”,而主要还是古代文人基于民间传说基础上的奇思妙想或传奇构制而已。
《缺陷》一文认为“《牡丹亭》中许多摹写生活的情节是经不住推敲的”,指出:“用浪漫的的手法所构造的情节,我们应该用浪漫主义创作原则来审视;而依据实际生活创作的内容,则必须用‘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标准去衡量”。这难免显得与《牡丹亭》的“语境”及传统有些格格不入。
确实,《牡丹亭》难以扯得上所谓“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原则的,但如果不去顾忌所谓“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在欧洲文学中的具体所指,《牡丹亭》确实不失为一部具有浪漫情怀的精心的文人之作。但是,应该更确切地说,它虽然代表着这样一种显在的“文人叙事”,而同时又与勾栏瓦肆的“民间叙事”有着割不断的情缘。既有民间故事的素材取舍,更有着剧作家个人化的大胆想象。它就是一个梦,一个关于情爱的生死之梦。它不仅是主人公杜丽娘的,更是剧作家汤显祖的。
从戏班搬演的角度来看,《牡丹亭》固然不是当行本色,却也并非完全没有舞台意识,《牡丹亭》关目之“芜杂”与戏词之戏谑,并非不堪,而是不甘。汤显祖不屑于追求文人的雅洁,《牡丹亭》中就有意穿插了“戏”(戏耍、戏弄)的成分,当然亦不能混同于民间俚俗杂耍。汤显祖的创作完成了一次真正的回归,回归到乐文化的根基处。作者不是不熟悉舞台,只是不肯屈就于舞台而已;不是他不配合演唱,而是不能“为文造情”“以辞害义”,故而才“不妨拗折天下人的嗓子”。
如果说,《牡丹亭》犹如一棵自然生长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乐文化便构成了适合它生长的土壤,并且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养料。汤显祖遵从一种“真情”“至情”的自然美学观,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中国乐文化的基因,批判地吸收并融合了礼乐、俗乐、巫乐等诸多文化因子,才成就了这部作品的伟大。故而,也只有回归到中国传统乐文化的语境当中,才能够做到对于《牡丹亭》全面的理解与独到的阐释。
《牡丹亭》的巫乐精神
《牡丹亭》有着深厚的巫文化根源,这不仅与汤显祖出生、为官的地域有关,与剧作的取材有关,更是与汤显祖所接受的思想渊源及巫乐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关。汤显祖的祖籍在江西临川,其一生的行迹,也多在吴楚之间。吴楚之地原本就有着深厚的神巫文化的基础,并且经过长时期的流传而形成独特的巫乐传统。先秦商周时代的巫风炽盛,深刻地影响到自屈原以来的中国艺术精神,形成所谓南方文化的“浪漫”传统。而这一传统的延续,追根究底,无非都是与巫乐文化的传承有关。延至明清,中国艺术的神巫色彩已然褪去不少,但是,巫乐文化的底色依旧,传统也并未终结,甚至内化为艺术家的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循乎此,明代汤显祖《牡丹亭》能构造一个“因梦生情、慕色而亡、超越生死”的情色世界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从汤显祖的思想倾向来看,道家的“任自然”与其“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正好契合。而道家思想的根源恰在于巫风炽盛的南方。于是,汤显祖与吴楚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巫乐传统也就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显示出汤显祖之于老庄乃至佛道思想的汲取,而且其创作中具有鲜明的神话思维的色彩。
唯其如此,神巫,在《牡丹亭》的形象谱系中,也就有了某种特殊的地位及表现。一方面,人鬼神仙杂处,甚至相亲相恋;另一方面,《白蛇传》之类亦复如是。
细加分别,《牡丹亭》之神巫谱系大致可以归为三类。其一是花神,花神在民间信仰中是司花的神祗。以花神舞的方式表现一种性的隐喻,一种生命活力与激情的宣泄。其二是阎罗殿里的判官、丑鬼。这些判官、丑鬼形象多与民间信仰有关,但又何尝不是现实官场的直接映射,甚至比现实官场还稍多些人情味。从而,在中国民间信仰的神鬼谱系中,他们也就具有明显的二重性。其三是主人公杜丽娘的神魂。有别于《李慧娘》乃至《活捉》中的“鬼魂”,杜丽娘之神魂是穿越阴阳,超越生死。
因此,有关神鬼世界的描绘,在《牡丹亭》中绝非可有可无,而是显示出《牡丹亭》之于巫乐文化的汲取,或者说,巫乐文化成为《牡丹亭》的一种精神源头。正是受巫乐文化的影响,汤显祖的创作总是穿越于神鬼与人间,纠缠于现实与梦幻的二元世界。梦,既是《牡丹亭》的主题意旨之所寄托,也是其剧情构造的核心。或者说,正是巫和梦,不仅在《牡丹亭》的心理原型的构成的意义上实现了人神的沟通,体现出《牡丹亭》创作的神话思维的特性,而且也使得《牡丹亭》更具批判性色彩与超越性品格,体现出一种自然天成的浪漫气质。
《牡丹亭》与礼乐传统
《牡丹亭》之于礼乐文化传统关联,不仅属于意义层面上的,与全剧的主题思想的表现有关,而且是结构层面上的,甚至进而影响到舞台形制。
迄今为止,一般人认为,汤显祖《牡丹亭》的思想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而事实上确是如此吗?
其一是反封建。汤显祖及其《牡丹亭》都明显不构成对于“封建”政治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何来所谓“反封建”?如果说,杜丽娘出生成长的环境属于封建官僚家庭,她所接受的教育也基本上属于“封建式”的,那么,其官僚家族文化以及封建观念对于人性的禁锢是明显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牡丹亭》具有某种“反封建”的色彩。故而,与其笼统地说《牡丹亭》“反封建”,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对于杜丽娘所置身于其中的封建家庭与社会伦理关系的一种批判。因此,“反封建”一说也就不免显得有些大而无当。
其二是破礼教。所谓礼教,原本就是传统礼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主张温柔敦厚、乐而不淫的礼乐来说,《牡丹亭》的作者无疑采取了一种反思和批判的立场和姿态。然而,《牡丹亭》对于礼乐教化也不是全盘否定。在《牡丹亭》所构建的生与死、神鬼人的二元世界当中,如果说,人的现实世界充满着礼教的束缚,礼教成为人的精神桎梏,那么神鬼或者人死后的世界则完全可以摆脱这一切。汤显祖对于礼教的这种二元化的处理,既是他对于礼教意识的大胆质疑,同时也确实是《牡丹亭》主题表达的矛盾之处。
其三是反理学。随着王学左派的兴起,人们才开始了对于理学的系统反思和批判。王阳明提出的“良知”观念无疑成为对“天理”的有效的校正和补充。汤显祖就是站在王学左派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强调人间“至情”,而反对“灭人欲”,主张扬“情”抑“理”,张扬“至情”。在汤显祖看来,天理只有顺应了人情,才是真正的“天理”。
确实,如《缺陷》一文所揭示的,究竟是颂扬爱情,还是表现情欲,确乎造成《牡丹亭》主题思想表现的一些矛盾性,也为人们认识和评价《牡丹亭》的思想和意义平添了一道迷障。但是,过分强调《牡丹亭》之宣扬“情欲”而无关“爱情”显然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其内在逻辑仍是“天理”与“人欲”的对立。
可以说,《牡丹亭》不是简单的对于礼乐传统的反叛,而只是对于礼教中的非人性的反思和挑战。比如,性爱,无疑是《牡丹亭》着力表现的主题之一。情与欲,从而表现人的七情六欲也就成为诗歌乃至全体艺术的根本,成为传统中国诗艺的基础。
诚然,《牡丹亭》的主题表现是有矛盾性的。因为,恰恰是礼乐文化的传统赋予了《牡丹亭》一个特殊的精神立场和价值标准。这种独特的立场和标准也使得《牡丹亭》有了基本的“奇”与“正”的定位:《牡丹亭》所传之“奇”无非是相对于礼法之“正”而言的,“奇”和“正”,实则相反而相成,没有“正”,也就无所谓“奇”。在这个意义上,汤显祖的艺术贡献并不完全在于所谓“反礼教”,而是在礼乐文化的传统规训下一种新的价值伦理维度的探求与突破,即以情为据,以生死为期许,它自是对于理学教条的一种反拨,更是对于礼乐文化的价值诉求的一种积极的拓展。从而,《牡丹亭》中对于个体情欲的抒写,其实并没有彻底摆脱礼教的羁绊,而是在古老的礼乐文化的根基上长出鲜活的嫩芽来。
《牡丹亭》与俗乐文化
作为一部文人创作的《牡丹亭》,究竟与俗乐文化传统有着怎样的关联?
《牡丹亭》之所以在表现“幽怨”“冷静”的同时又很“热闹”,就是因为它的根深扎在传统俗乐文化的土壤之中,从而在其舞台表现上俚俗不拘。可以说,俗乐文化的喜乐精神与文人的悲悯情怀,造就了《牡丹亭》的特殊的品格和品味。
俗乐,乃是相对于礼乐而言,是基于民间民俗娱乐之上的一种乐文化形态。从历史的发生来看,俗乐的兴起与巫风的退隐有着一定的关联。俗乐与巫乐,原本是相表里的,而与礼乐文化相并立。如果说,巫乐的主要功能是娱神,则俗乐主要是娱人与自娱。
唯其如此,俗乐文化之于《牡丹亭》,不仅构成了它生长的土壤和动因,而且直接构成其剧情发展及意象呈现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牡丹亭》当中就不仅有着诸多喜闹的场面排场,同时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世俗化的格调。
就《牡丹亭》的排场而言,自《牡丹亭》诞生以来的各种演出文本,尤以喜剧性的铺陈排场为甚,虽然这种铺陈并不为多数文人所认同,但却吸引了更多的观众。
就《牡丹亭》的格调而言,俗乐文化多以嬉闹见长,至于《牡丹亭》的所谓“低俗”、粗俗,其实更多属于舞台上常有的科浑,目的主要还是适应观众的俗趣,以及有着更多的民间典仪的直接展示。
唯其如此,《牡丹亭》中,大雅和大俗、文人雅趣与民俗娱乐才得以相互交融。杂而不越,也就成为《牡丹亭》的魅力所在。
结论
究竟如何全面地理解与评价作为中国戏曲文化的经典文本之《牡丹亭》?无疑,《牡丹亭》的成就与瑕疵并存。只是《缺陷》一文对于《牡丹亭》思想及艺术上的不足的揭示稍显浮表化,而未能深及根源,且其“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评价视野显然与《牡丹亭》的产生土壤、生存环境是不适宜的。
就主题表达而言,如果说《牡丹亭》一剧的传奇故事在世俗的眼光中似乎显得荒诞不经,但在戏剧舞台上却又在情理之中,它惊世骇俗,却又入情入理。
就剧情构造而言,既然《牡丹亭》所言无非一个“情”,一个女子上天入地、寻觅真情的故事,那么,其情境设置与意象营构也就无不围绕此“情”而展开。这种“情”也就成为《牡丹亭》“还魂再生”的剧情模式的主要动力源。
故而,唯其以“情”为纲,以“礼乐”“俗乐”“巫乐”为纬,融传统乐文化于一体,《牡丹亭》的主题表达与剧情构造才显得既一以贯之又包容性极强。而并非像朱恒夫教授等人文章中所揭示的那样“在现实主义故事情节的板块上随意编构内容,淡化了作品的艺术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