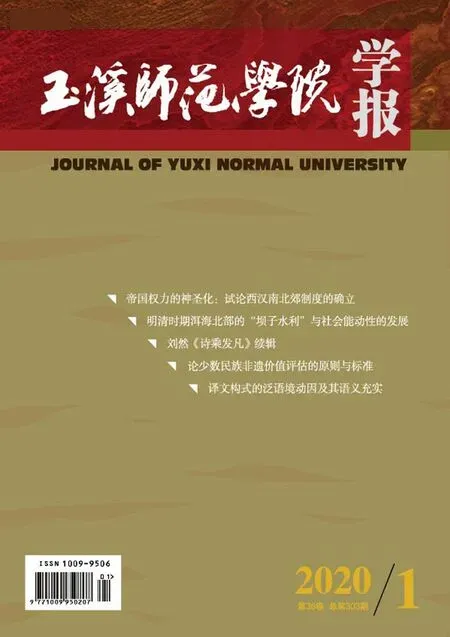神圣与世俗的对立与冲突
——《红楼梦》主题的重新探讨
杨 朴,杨 旸
(1.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 文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2.国家开放大学 实验学院,北京 100039)
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人生悲剧说,阶级斗争说,反封建说,爱情悲剧说,四大家族兴衰说等等(1)王蒙.王蒙的红楼梦[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274.。应该说,每种主题说都接触到了《红楼梦》的一些重要内容。书名从《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到《红楼梦》的多种变化,已经表现了作者和编者对作品不同内容把握的变化。《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它具备了可以从多种角度理解与阐释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可能性。
但是,一部作品的主题应该是从作品最主要的结构形式生发出来的,一部作品最主要结构形式是固定不移的,因而,它的主题也就应该不是变动不居、多种多样、其说不一、莫衷一是的。《红楼梦》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红楼梦》一开篇(第一回)就为人们讲述了一个玉石神话:女娲补天遗留一块大石头,变成了可大可小、来去自由、晶莹鲜美的玉石。这块玉石随着贾宝玉的转世投胎而来到现实世界。有的版本还表现了转世投胎的贾宝玉是那块女娲补天遗下的石头变成的神瑛侍者所变的。也是在第一回,在玉石神话之后,紧接着讲述了疯狂落拓的跛足道人给甄士隐唱《好了歌》和甄士隐为《好了歌》做注解的故事。
《红楼梦》一开篇就以女娲在大荒山炼石成玉——“通灵宝玉”来历的神话象征了一个神圣的世界,又以《好了歌》及其注解象征了一个世俗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结构在一起,构成了神圣与世俗的对立与冲突。神圣与世俗对立与冲突的结构便构成了《红楼梦》的一个重要原型。贾宝玉衔玉而生就是带着神圣性进入世俗社会的隐喻,《红楼梦》神圣与世俗冲突的主题正是由此而展开的。《红楼梦》第一回就展现了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并且使这种神圣与世俗的对立与冲突成为整部《红楼梦》的主线,贯穿于《红楼梦》的始终。神圣与世俗的对立与冲突构成了整部《红楼梦》的主题。
一、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
《红楼梦》是由神话世界和现实世界两个系统构成的,神话世界最重要的就是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但它不是对女娲炼石补天神话原封不动的运用,而是改写。它把传统的女娲炼石补天神话改写成了一个新的玉石神话。在这个玉石神话中,曹雪芹既创造了一个“大荒山”的神圣世界,又创造了一个炼玉的神圣行为,还创造了一个“通灵宝玉”这样神圣的“显圣物”。
我们先来看看曹雪芹是怎样对女娲补天故事进行改写的。《红楼梦》开篇第一段是作者创作意图的自述,第二段则是故事的正式开始。在故事的开始时作者这样写道:“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说来虽近荒唐,细玩颇有趣味。”然后,引出这样一个神话:
却说那女娲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练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一块未用,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自来自去。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这是一个讲述“通灵宝玉”来历的神话,它是来源于女娲补天神话原型的,是对女娲补天神话原型的改造: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3)刘安.淮南子:卷6[M]//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6:95.。
从曹雪芹女娲炼石补天神话和《淮南子·览冥训》女娲补天神话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两者的重要区别:《淮南子·览冥训》女娲补天神话非常明确表现的是天塌地陷,人民陷于毁灭的灾难,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然后是天塌地陷得到圆满的弥补,人民得到重生。但在曹雪芹改写的女娲补天神话中,不再表现天塌地陷和人民陷于灾难,也不再表现天塌地陷得到弥补,人们得到重生。在这一改写中不再表现女娲的补天行为,而只是讲述了女娲“补天之时”的炼玉行为,讲述了炼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补天之玉,然而补天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而那块被弃之石在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来自去,可大可小,其实是已经变成了“通灵宝玉”。经过这样的改写,曹雪芹就把一个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改写成了一个女娲炼石而使其成为“通灵宝玉”的神话。
曹雪芹重新创造女娲炼石而使其成为“通灵宝玉”的神话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炼石成玉,是一种神圣性的表现。玉来源于石,但是玉的形态和品性又高于石,因而就具有了一种神圣性。伊利亚德说:任何一种东西本身并不具有任何价值,“其价值在于它和原型的关系,在于一系列使之同周围世俗的东西区别开来的行为或话语”(4)[罗马尼亚]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学的范型[M].晏可佳,姚蓓琴,译.贵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81.。
据叶舒宪研究,在中国崇玉是一种文化大传统——以玉为神圣精神之原型,有万年的历史(5)叶舒宪.中国圣人神话原型新考——兼论作为国教的玉宗教[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3):277-286.。崇玉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大传统,是因为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型。玉是象征天,象征神,象征高尚人格的。人们崇拜玉,就是因为玉虽然来源于石但又有超越于石的本质属性,因而它就具有了超越平常的神圣性象征意义。宗教史学家伊利亚德曾经深刻地论述这种象征意义,他说:“万石之中,只有一颗石头可以变为神圣——同时刹那间,它弥漫着存有——因为此石布满神力,或拥有魔力,要不然,就是它用以纪念神话事件,诸如此类等等。物体一旦成为外在力量的容器,这力量即会使它与周遭的环境有所分别,并赋予它意义与价值。这外力可能寓于此物的本质中,也可能寓于其形表。一块岩石所以显得神圣,因为其存在即神力所现,无从压缩,没有弱点,远超人力所及;它自然不受时间左右;它永远真实。就是最平凡的一颗石子亦然;它可因其象征的形状或来源而变成宝贝,因为它充满巫术或宗教的力量。”(6)[罗马尼亚]伊利亚德.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M].杨儒宾,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2.
曹雪芹表现“通灵宝玉”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其实就是在表现玉与神相通的神圣性。曹雪芹在崇玉文化大传统基础上即在原型意义上表现玉的象征意义,“通灵宝玉”的象征意义来源于崇玉文化大传统原型,因而,神圣性就成为“通灵宝玉”的象征意义,“通灵宝玉”其实是曹雪芹表现神圣性的一个原型符号。
玉为女娲所炼,因而具有了神圣性。“通灵宝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玉,而是经由女娲所炼,是女娲炼石成玉的。女娲是要补天而炼玉的,女娲补天其实是女娲重新创世的行为,玉的补天功能即参与女娲的重新创世,使玉具有了非同寻常的神圣性。女娲炼石之时就把女娲女神的神圣性注入到了宝玉之中,使宝玉具有了女娲女神文化基因。
更为重要的是,曹雪芹要创造一种新的神话原型。玉石虽然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虽然已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型,但是,曹雪芹仍然觉得不够,仍然觉得没能把玉石的神圣性表现得更典型,因而他要创造一个新的神话,为玉找到一种神话的源头。新神话的玉石并非一般的玉石,而是经过女娲所炼,而且是女娲为补天所炼的玉石。这就给玉石的神圣找到了一种起源,就成了一种神话的范例、神话的原型。而所有事物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来源于神话原型,或者就是神话原型的体现。曹雪芹的这个新创的玉石神话包含了曹雪芹对神话的深刻理解。“通灵宝玉”之所以是神圣的,因为它来源于女娲的炼石补天神话原型,是经过女娲女神所炼而成。正如著名宗教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只要某物与周遭同类事物有一明显的差异,如:名山、大川、神木、巨石;或此物曾与神圣人物或神圣世界沾上边,如:圣者之遗物、来自天上之陨石等等,神圣即汇聚于某物,它与周遭即有一本体论的断层。”(7)[罗马尼亚]伊利亚德.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M].杨儒宾,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3.
大荒山是神圣性的又一种体现。曹雪芹是以大荒山与现实社会的“荒远”来表示它的神圣性的。因为在曹雪芹看来,现实世界是一个世俗的世界,因而与它相距荒远的大荒山世界就是一个神圣的世界。显然,曹雪芹以时空的荒远来表现文化精神的初始性和神圣性。关于这个问题,叶舒宪曾有过深刻的论述:“《山海经·荒经》为中国文学中‘荒远怪异’意象和‘荒诞无稽’观念提供了‘政治地理’的原型。时间的‘古’和空间的‘远’是对‘荒’的想象之条件。在儒家正统意识控制下,文化代码系统专用‘荒’‘怪’‘异’之类象征边缘性和异端性的语汇来为‘王化之外’的空间和事物命名。而与‘中心’和秩序相对立的‘荒’的理念也为一切反叛和挑战正统价值的言论找到立足点。贾宝玉来自‘大荒山’,庄子、曹雪芹等标举‘荒唐言’,皆为其例。”(8)叶舒宪.“大荒”意象的文化分析:《山海经·荒经》的观念背景[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94-101.在曹雪芹的艺术表现中,那个大荒山相当于宗教体验中的世界的初始形成。它产生的精神是原始的、纯净的、神圣的,后来都要回到那里去以便重新获取那源头的精神。
伊利亚德关于宇宙空间的非均质性为我们理解曹雪芹宗教性的大荒山的意义提供了帮助。他说:“对宇宙空间非均质性的宗教体验是一种原发的体验,这种宗教体验能够被比作世界的形成。这并不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测,而是在对这个世界形成一切反映之前的一种最初的宗教体验。正是这种在空间中形成的中断才使世界的创造成为可能,因为它为未来的所有发展向度揭示了一个基本点,确立了一个中轴线。当神圣以任何显圣物表征自己的神圣的时候,这不仅是空间的均质性的一种中断,更是一种绝对实在的展示,也展示了它与其所属的这个光影苍穹非实在性的对立。正是神圣的这种自我表征,才从本体论的层面上建构了这个世界。在一个均质而又无限浩瀚的空间中,不可能有任何的参照点,因而也无任何方向得以确立其中。只有显圣物才揭示了一个绝对的基点,表明了一个中心。”(9)[罗马尼亚]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M].王建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2.大荒山的神圣意义正是以这种宗教文化为背景而建立起来的。
女娲炼石成玉的神圣性最最重要的体现,还通过那个由跛足道人唱的《好了歌》和甄士隐的注解象征的社会状态的比照中体现出来。
《好了歌》的内容是这样的: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甄士隐对《好了歌》的注解更多的是表现人生无常,命运多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是核心思想。《好了歌》及其注解所表现的是人的贪欲,堕落和毁灭。它实际是一种世俗世界人生状态的象征。著名学者刘再复对《好了歌》有过精彩的总结:“《好了歌》描述了功名、娇妻、金银裹挟着人的生命向前滚动。功名伴随着喧嚣,娇妻伴随着背叛,金银伴随着血腥,但世人照样让他们裹挟着自己的生命往前滚动。裹挟着打着事业之旗,立功立德之旗,衣锦还乡之旗,五颜六色,浩浩荡荡,滚动不止,追逐不已,‘好’总是难‘了’。世人要钱不要命,要名不要命,要色不要命,所以才会被裹胁。这个命,是个体生命的自由与尊严。《好了歌》揭示的是俗气大潮流。这种潮流使人类世界变成猪的城邦和心的荒原。”(10)刘再复.红楼哲学笔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05.“俗气的潮流”是对《好了歌》内容最好的概括。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曹雪芹把《好了歌》及其注解与女娲炼石成玉的神话排列组合在一起来表现。这样,女娲炼石成玉的神话与《好了歌》及其注解就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艺术结构。由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女娲炼石成玉的神话是象征神圣的,而《好了歌》及其注解是象征世俗的,那么女娲炼石成玉的神话与《好了歌》及其注解的二元对立实际就成了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
神圣与世俗的对立与冲突是《红楼梦》一个相当隐蔽的原型结构。说它是一种相当隐蔽的原型结构,那是因为,世俗世界是在甄士隐的故事中出现的,这就使人们很容易从理解甄士隐的故事入手,理解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及其甄士隐的注解。但是甄士隐的故事其实是出现在贾宝玉的故事之中的,甄士隐的故事是为贾宝玉的故事做铺垫的。甄士隐梦见了石头神话,接着又听到了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加上他丢了女儿,家里又失了火,然后他就出家了。甄士隐的出家实际上构成了贾宝玉出家的先例。甄士隐在短时间内悟道,贾宝玉则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悟道的。但甄士隐听到的跛足道人《好了歌》和他自己对《好了歌》的注解,又不止是对贾宝玉故事做铺垫的,而是为整部《红楼梦》建构了一种最基本的结构,是曹雪芹创造《红楼梦》大创意的体现。
艺术理论家告诉我们,一般情节虽然是重要的,但是惟有结构才是思想的体现,因为结构在一起的东西产生新的形式,而新的形式才产生新的意义。艺术理论家贝尔说:“不断地指出艺术品中那些组合在一起的产生有意味形式的部分和整体(换言之,它们的组合),正是艺术批评家的作用之所在。”(11)[英]克莱夫·贝尔.艺术[M].周金环,马钟元,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5.
从结构形式的角度看,女娲炼石成玉的神话与《好了歌》及其注解组合在一起,就生发出神圣与世俗的对立、矛盾与冲突,这是由女娲炼石成玉和《好了歌》形成结构形式的结果。如果将女娲炼石成玉和《好了歌》及其注解单独看,特别是将《好了歌》及其注解单独看,并不能看出神圣与世俗对立的意义,但由于将两者结构在一起,就生发出了新的意义。这种组合结构绝非我们的过度解读,而是曹雪芹的有意为之。曹雪芹在一百二十回小说的第一回就建构了这样一种神圣与世俗二元对立的结构,足见这种结构对整部小说的极其重要。而整部《红楼梦》的主线正是沿着第一回展现的神圣与世俗二元对立结构展开的。
但是,曹雪芹建构这样一个神圣与世俗对立、矛盾与冲突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神话与世俗的对立、矛盾与冲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对立、矛盾与冲突呢?
我们只能在女娲炼石成玉的神圣和《好了歌》及其注解的世俗的二元对立去寻求解答。那个神圣和世俗二元对立的冲突是关于人的。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还有女娲抟土造人神话是虽然是讲述造人的,但那是属于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而曹雪芹根据女娲炼石补天神话改写的女娲炼石成玉神话,则是表现人性的。它是用玉的纯净和美丽象征人的至真至纯和美丽。因而,玉的神圣性其实就是至真至纯人性的象征。而《好了歌》及其注解的世俗性则是贪欲堕落人性的象征。
正是在这里,我们终于理解了曹雪芹《红楼梦》大创意的根本之所在:他运用女娲炼石补天神话改写的炼石成玉神话,进行了神话的“基因重组”,由女娲开天辟地创世的造人,改写成了创造至真至纯的人。女娲炼石成玉的象征意义在于,它通过女娲所“炼”,把真正的人的灵魂注入到了顽石之中,而使之成为人的神圣性的原型符号。宗教史家告诉我们,宇宙生成的神话是作为人类行为的典型范式神话被讲述的。但是,曹雪芹把那个女娲炼石补天的典型范式神话由宇宙生成改写成了玉的生成即象征人的生成的神话,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的生成的范式神话。曹雪芹是在人的贪欲、堕落和人性毁灭的现实基础上重新创造至真至纯的人。他要用至真至纯得像“宝玉”那样的人去对比现实中虚伪、贪婪、丑陋、肮脏与龌龊的人,从而唤醒贪欲堕落之梦中的人们。“通灵宝玉”的象征意义在于,由于它是来源于女娲炼石成玉神话的,因而它是神圣的;贾宝玉衔玉而生,象征贾宝玉的灵魂中具有了这种神圣性,“通灵宝玉”成了贾宝玉的“护身符”,说明贾宝玉思想性格中具有至真至纯的人性。
二、神圣在世俗世界中的毁灭
贾宝玉带着“通灵宝玉”来到现实人间,是从神圣世界来到世俗世界的象征。在曹雪芹的艺术表现中,神话与现实相互联系,神圣与世俗相互依存而生发艺术意义。我们对《红楼梦》的解读,特别是对贾宝玉形象的分析,就应该紧紧与神话联系在一起,而不应该将其割裂。
神话对贾宝玉的意义,就是指贾宝玉的出身与来历是神话性的,贾宝玉是石头——神瑛侍者变的。这就给贾宝玉带来了神性的特质。他是经过女娲炼石补天的石头所变,因而就带来了神圣性。这个神圣性还是以“通灵宝玉”来象征的。经过了女娲所炼之石变成的玉,本身就具有了神圣性,但曹雪芹还嫌不足以表现贾宝玉的神圣性,还让他带来“通灵宝玉”。“通灵宝玉”是对贾宝玉形象神圣性的进一步强化。“通灵宝玉”是玉石神话原型的象征。曹雪芹在表现贾宝玉思想行为的时候,是与神话紧密相连的,甚至表现了他思想行为的源头就在女娲炼石成玉的神话那里。贾宝玉虽然出身于贾府,但是,贾宝玉是带着“通灵宝玉”的,贾宝玉还是经过女娲所炼之石所变的,贾宝玉还有神话学的出身。贾宝玉自然就带有来自神话“基因”的神圣性。
贾宝玉所进入的现实世界是《好了歌》及其注解所象征的世俗世界。贾宝玉进入这个世俗世界,是有几种力量驱使、诱惑与规定的:第一种是他的出身规定的,女娲所炼之石使他先天地具有了神圣性。第二种是一生一道对他的规定,一生一道要他“下凡”去经历经历,那意思是要他在经历世俗之后能够幡然醒悟而出世。第三种是贾宝玉的先祖,他们托付警幻仙姑,要贾宝玉先经历繁华世界,然后痛改前非,走入所谓仕途经济的正途。第一种贾宝玉出身所带来的是神圣性,而第二种和第三种都是指向世俗性的。这再一次表明,贾宝玉人生所经历的就是神圣与世俗的冲突。
“通灵宝玉”随着贾宝玉出生而成了贾宝玉的灵魂,它象征着神圣性的与生俱来。贾宝玉对青春女性的崇拜与呵护是贾宝玉神圣性品质最强烈的体现。贾宝玉对青春少女的热爱、呵护与崇拜是其对当时男尊女卑和男性统治思想及其价值观的绝对叛逆。这是来自女娲女神的神圣品质。女娲补天神话是与女娲造人神话构成互文的。女娲造人也就创造了宇宙。女神创世神话是女性主义神话学的表现形式,只有在女性主导的社会被男性所统治的文化大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女娲炼石补天的真正意义。女娲之所以要补天,那是因为女性创造的宇宙世界被男性所破坏,因而女娲要补天。补天当然是一种象征,即要用女性价值观重新弥补被男性价值观破坏的“天”——女性主义为主体的社会。贾宝玉是被这样的女神所炼的石头而成为的玉,也成为转世的人,因而,他的精神品质中就有着“补天”的文化精神基因。贾宝玉一周岁的时候,他的家庭给他举行了一个“抓周”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对于代表人世间金钱、权利等所有物件,他都一概漠不关心、毫无兴趣,而专门抓取象征女性的胭脂钗环。这就是他的女娲补天精神基因对他的潜意识的支配作用。他的父亲据此说他将来是酒色之徒无疑,那是贾政不能看到贾宝玉精神世界的神圣性基因所致。“补天”基因反映在贾宝玉的人生中,表现为他对青春女性的热恋崇拜和尽情呵护。
与青春女性“厮混”是贾宝玉最突出的特性。比如黛玉、宝钗、袭人、鸳鸯、妙玉、金钏等等,凡是美丽的少女他都愿意亲近,一起游戏玩乐等。贾府上上下下的人都以为他的这种行为是他风流成性的习性;很多读者也以为是他纨绔子弟的恶习。但这却是对贾宝玉对女性热爱、呵护和崇拜的最大误解。贾宝玉对青春少女的关怀、呵护和同情,也是贾府中任何男性所不具备的情感态度。当看见一个女孩被雨淋湿了,他高呼着“下雨了,快避雨去罢”,而他自己却“大雨淋的水鸡似的”;刘姥姥瞎编一个女孩死去的故事,他却要一定找到那个庙去祭奠(第三十九回);晴雯从卧室出去,他怕冻着她,让她到自己的被窝里来取暖。而这个丫鬟身份的少女死去之后,他做了感天动地的“芙蓉诔”。在大观园的“怡红院”(怡红院就是根据贾宝玉愿意与“红”即女孩儿在一起的赋名——这与曹雪芹的“悼红轩”是相互呼应的)里,贾宝玉更是体验到了与青春少女在一起的无忧无虑和至真至情。
贾宝玉愿意与女孩“厮混”与关怀女孩儿,这与贾宝玉的“抓周”是一种呼应,也好像印证了贾政所谓“酒色之徒”的预先判断。一般读者也不大容易理解贾宝玉亲近青春女性的思想行为。但这与贾宝玉由出身带来的神圣性有关。贾宝玉身上带着“通灵宝玉”,他就带着由女娲所炼之石而成为玉的精神品性,他是以人的至真至纯的本性接近所有人的。贾宝玉愿意与青春女性“厮混”是他崇拜青春女性的体现。大观园是女儿国,在那里没有别的男性,只有贾宝玉独自一个男性与众多青春女儿生活在一起。那是一个独立于贾府、独立于男性统治世界的自由王国。余英时把大观园作为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一个独立世界来论述(12)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但大观园是与玉石神话相连的,是玉石神话的神圣性在现实世界中的投影。因而大观园与现实世界构成的对立仍然是(玉石)神话世界与现实世界根本对立的体现。
在贾宝玉的思想感受里,青春女性的美与青春女性的鲜艳、明丽、清纯等精神品质连为一体。她们容貌的美丽是与她们精神品性的美丽体现与象征。贾宝玉崇拜青春女性以他对男性的厌恶为前提。贾宝玉对女性的情感态度以“女清男浊”的观念为思想基础。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
贾宝玉为什么非常厌恶男性呢?那绝非是贾宝玉的同性相斥的嫉妒,而是来自于他关于人的思想观念,是由他的“三观”即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决定的。贾宝玉对女人“三变”的认识——少女时代是一颗珍珠,晶莹剔透、天真无邪,闪闪发光,一旦嫁给男人这颗珍珠就会发污,而到了老年就会变成死鱼的眼珠子。这是因为贾宝玉对男性和女性的文化精神认识不同所致。在他看来,青春女性是清纯、美丽、自然、无私的,一旦嫁给男人就进入了男人控制的世俗世界,被男人的自私和贪欲价值观所污染了。而男人是肮脏、龌龊、贪欲、狡诈的。其实贾宝玉女人三变的认识也是他对所有人三变的认识。贾宝玉说:“(女子)嫁了人,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第五十九回)人是带着至真至纯的神圣性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但是却被这个世俗世界的金钱和权力诱惑与腐蚀,而改变了自己至真至纯的本性。贾宝玉对女性的崇拜的实质是对真正的人的崇拜。贾宝玉的前世是“神瑛侍者”,所谓“侍者”就是奴仆;而“神瑛”就是女性。贾宝玉给女性当侍者就是给女性当奴仆。可以说,贾宝玉在世俗世界中对女性的崇拜来自神界的神圣原型。
但是,在那个男性统治的世俗世界里,贾宝玉对女性崇拜与呵护并没有挽救一个女儿,反而更加速了世俗邪恶势力对青春女性的摧残。“子落枝空”的审美感受,正是贾宝玉对失去女儿世界的悲剧感受。在第五十八回,大病初愈的贾宝玉来到大观园,看见一株杏树花期已过,产生一种“子落枝空”的悲凉感。那是因为在此之前,他听说岫烟要出嫁了。岫烟的出嫁使他感到有一个女儿要走向卑劣的男人,走向龌龊的社会,走向脏脏的生活。在贾宝玉看来,那就是少女的毁灭,青春的毁灭,真善美的毁灭,人性的毁灭。贾宝玉把这种感受投射到了杏树花期已过的意象之中,他的女儿毁灭的悲剧感受决定了他对杏树的“子落枝空”审美感受。
“木石前盟”爱情是贾宝玉由玉石神话带来神圣性的又一体现。曹雪芹在两个大的方面描写了贾宝玉与林黛玉爱情的神圣性。一方面是贾宝玉与林黛玉一见面就感到了电闪雷鸣般的震撼,两个人都觉得对方是在哪里见过的似曾相识,这就是所谓的一见如故、一见倾心、一见钟情;另一方面是他们都觉得对方看着“面善”,都觉得是在哪里见过的感受,实际是他们真的看见了“梦中情人”。而这个“梦中情人”就是他们的恋人原型。曹雪芹通过“木石前盟”的神话形式,呈现了这一恋人原型。贾宝玉与林黛玉之所以一见如故,那是因为他们“前世”曾经有过的木石前盟之恋。作为贾宝玉前世的神瑛侍者,曾经在三生石畔灌溉过林黛玉前世之身——绛珠仙草。绛珠仙草因而又草木幻化为女儿身,但她没有什么可以还给神瑛侍者,发誓来世要以一生的眼泪还他的浇灌之恩。贾宝玉和林黛玉一见钟情的现实与二人木石前盟的神话之间,具有一种决定性的联系:木石前盟神话对一见钟情的原型作用。正是这种木石前盟神话对现世爱情的先天规定,才使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具有了神圣性。王蒙用“天情”来说明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正是对这种神圣性的表达。
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是痴迷、沉醉并与生命一体化了的。在贾府,林黛玉是贾宝玉唯一的精神相通者。在与林黛玉的爱情中,贾宝玉没有表现出与另外青春少女比如袭人等的肉体欲望,而更多的是表现他们之间在精神世界的紧密联系,他们在一起或者是讨论老庄哲学,或者是探讨“西厢记”与“牡丹亭”,或者是抨击虚伪的假道学,或者是共同体验青春生命的流逝。当然,还有很多时候讨论的是林黛玉对贾宝玉的误会、隔膜和猜忌等等。他们的爱情具有强烈的超越性特点,超越肉体之恋,超越世俗之恋,是他们恋爱的最大特点。他们都把对方视为自己灵魂的知音、知己,他们都把爱情视为生命的唯一价值。因为他们的爱情是超越于世俗的,因而,他们的爱情便具有了显而易见的神圣性。他们的爱情痴迷、沉醉,与人生意义一体化,这种显而易见的神圣性仍然是被木石前盟神话决定的。木石前盟作为一种神话原型,是人的爱情至真至纯神圣性的象征。木石前盟的“石”已经不是作为原始状态的“石”,而是经过了女娲所炼的“石”,实际上已经是玉了,玉就是神圣性的体现,而被石转化的神瑛侍者所浇灌的绛珠仙草成为女体,也就具有了神圣性。由此可见,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仍然是与玉石神话相关的,他们爱情的神圣性是玉石神话神圣性派生出的。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中表现着这样一种逻辑线索:玉石神话原型——木石前盟——爱情。贾宝玉是把玉石来历(神话)的神圣性带进了他与林黛玉的爱情。但是,他们来自神界的神圣爱情并没有战胜世俗世界的婚姻。“金玉良缘”是世俗婚姻制度的象征,在“金玉良缘”的世俗婚姻规定中,“木石前盟”的爱情终于被彻底毁灭了。
贾宝玉人生道路的选择是玉石神话神圣性的最重要体现。鲁迅曾经对中国人的人生道路有一个深刻的比喻,他说中国早就为年轻人预备好了人生之路,那就是两面是高墙,只有中间一条路可走。人没生下来路就已经预备好了。贾府为贾宝玉预备的人生之路就是这样的。在贾宝玉还刚刚十几岁的时候,他的已经故去的先祖就托付警幻仙姑给贾宝玉以人生道路的指引,其方式是让他先领略荣华富贵和性爱生活,然后使他能够醒悟,以便走上所谓的人生正路。而贾宝玉的父亲更是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想要使他走上仕途经济、读书做官的人生之路。贾宝玉的先辈不管是已经死去的还是在世的,都要把贾宝玉按在一条早已为他准备好的人生之路上。那条道路就是读书做官,读的书尽是虚伪的假道学,做的官是贾雨村那样的贪官。走上这样一条人生之路,失去的是人的至真至纯的赤子之心,失去的是人的自由,失去的是人的所有美好的一切。而在这条道路上越往前走就越走向人的反面,最后成为一个龌龊无限,贪欲无限,虚伪无限的人。在这条人生之路上,“惟有功名忘不了”“唯有金银忘不了”,其结果是“反认他乡是故乡”。那是世俗世界为所有人当然也是为贾宝玉提供的一条固定不移的人生之路。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必须要走的人生之路。
贾宝玉有自己的神圣出身,那出身使他就像戴上了“通灵宝玉”那样具有了神圣性。贾宝玉的人生之路就是他用神圣性对世俗性的抗拒。贾宝玉的神圣性是与生俱来的,这种神圣性集中表现在他的自由自在的灵性上。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经过女娲所炼,而又没能去“补天”,但“自经锻炼,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娲皇未用,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这说明,自由自在已经成为贾宝玉现在的灵魂。贾宝玉是带着自由的神圣性来到世俗世界的,他对读书做官的人生道路的抗拒,对贪欲、肮脏、龌龊人生道路的鄙视,对自由自在人生的坚守,对至真至纯人性的坚守,就成为他独一无二的人生之路选择。贾宝玉当然没有改变贾府的世俗性,更没有改变世俗社会——贾宝玉没有那样宏大的力量,那样要求贾宝玉也不是现实的,但是,在那样一个物欲横流、贪欲无限、几乎无官不贪的社会里,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人的本性,几乎所有人都“反认他乡是故乡”的现状里,贾宝玉毕竟做到了“守身如玉”,他并没有丧失自己人之为人的神圣性。
太虚幻境的“女儿国”是现实世界“大观园”的原型,那也是一个神圣的世界。而大观园之外的贾府则是世俗世界。这两者同样是神圣与世俗的对立与冲突。曹雪芹是别出心裁地表现了大观园后来被元妃命名为“怡红院”的那个所在与太虚幻境“女儿国”与神圣世界“女儿国”的隐秘联系。作品第十七回是这样描写的:
贾政与众人进了门,两边尽是游廊相接,院中点衬几块山石,一边种几本芭蕉,那一边是一树西府海棠,其势若伞,丝垂金缕,葩吐丹砂。众人都道:“好花,好花!海棠也有,从没见过这样好的。”贾政道:“这叫做‘女儿棠’,乃是外国之种,俗传出‘女儿国’,故花最繁盛,——亦荒唐不经之说耳。”众人道:“毕竟此花不同,‘女国’之说,想亦有之。”宝玉云:“大约骚人咏士以此花红若施脂,弱如扶病,近乎闺阁风度,故以‘女儿’命名,世人以讹传讹,都未免认真了。”众人都说:“领教!妙解!”
现实世界以海棠花象征“女儿国”——这名字由贾政说出颇富深意——与太虚幻境的“女儿国”同名。曹雪芹以这种同名来表现太虚幻境女儿国的神圣性在现实世界的发生。贾宝玉最初将其赋名为“红香绿玉”,恰好与他在大荒山所带来的“通灵宝玉”一样,具有神圣性的象征意义。大观园里的青春少女是一种生命的诗意状态。那是一个与贾府隔绝的世界,那里除了贾宝玉一个男人之外——而这个男人是崇拜青春女性的——再也没有另外恶浊逼人的男人,因而也就与《好了歌》及其注解所象征的那个世俗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的世界。而这种鲜明的对比也就是神圣与世俗的鲜明对比。由怡红院扩而大之的大观园,是青春少女的世界,是诗意栖居的世界,是纯净的世界,是真善美的世界,是爱的世界,是情的世界,是纯粹人性的世界。一群青春少女学诗、吟唱、游艺、饮酒,开诗社,你赠我答,尽情欢乐。她们有时也苦闷,有时也流泪,有时也有些小矛盾,但是那是青春少女的苦闷和忧伤,而绝非那个《好了歌》及其注解所象征世俗世界勾心斗角、你争我斗、尔虞我诈、贪得无厌、为获得功名利禄的苦闷和忧伤。
曹雪芹以怡红院和大观园的所在极尽诗意之可能地描写了贾宝玉和一群青春少女的欢乐生活,意在突出人的真善美的神圣性。但是,这种来自神界的“女儿国”并不能获得长久的存在。一件小事的发生,大观园就遭到了无情的“抄检”。神圣的“女儿国”经过一个晚上就彻底毁灭了。还有黛玉、妙玉——这带“玉”名字的女性,也都或死去或被强人掠去而不知所终。黛玉之所以要“葬花”,是因为怕花儿顺水流出之后,被大观园之外世界的污泥浊水所污染。在“葬花吟”中她唱道“质本洁来还洁去”,说明黛玉对世俗世界肮脏龌龊的恐惧与抗拒。妙玉是何等的洁净,连刘姥姥使用过的碗她都要丢掉,因为她怕世俗世界的肮脏玷污了她的圣洁之境。但是,“欲洁何曾洁”,妙玉被一伙强盗掠走,遭到了最不堪的凌辱与蹂躏。妙玉的命运最典型地体现了世俗对神圣的毁灭。还有那些不带“玉”名字然而同样具有玉精神的女性,在世俗力量的无情打击中,也都一个个走向了毁灭的结局。
贾府之中的那个贾雨村,当官之后就“未免贪酷”,为了当官可以徇私枉法;贾琏和王熙凤等等也都是贪欲无限的人。当然还有贾府之外的甄宝玉,他是贾宝玉的另一种人生道路。甄宝玉起先比贾宝玉还激进,说道女儿两个字的时候,要焚香漱口,同样厌烦仕途经济,但是到后来他还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从神圣走向世俗。在贾宝玉的生活环境即那个世俗世界之中,人们或是为了权力,或是为了金钱,或是为了性欲,而改变了自己即改变了人的初心与本质,在《好了歌》所象征的世俗世界中,“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其实是在表现世俗世界人性的畸形、堕落与毁灭。
三、结 语
《红楼梦》第一回就呈现了一个神圣与世俗对立与冲突的结构,这个结构成为《红楼梦》一个重要原型。《红楼梦》所有故事都是这个神圣与世俗对立冲突结构原型的具体化展开。因而,神圣与世俗的对立与冲突便成为《红楼梦》最基本最重要的主题,神圣与世俗的对立与冲突就是人性与反人性的对立与冲突。《红楼梦》是以人的彻底毁灭的大悲剧在进行着大震撼、大警醒与大呼唤:在一个贪欲堕落肮脏的世俗世界中,人应该保持人的赤子之心的神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