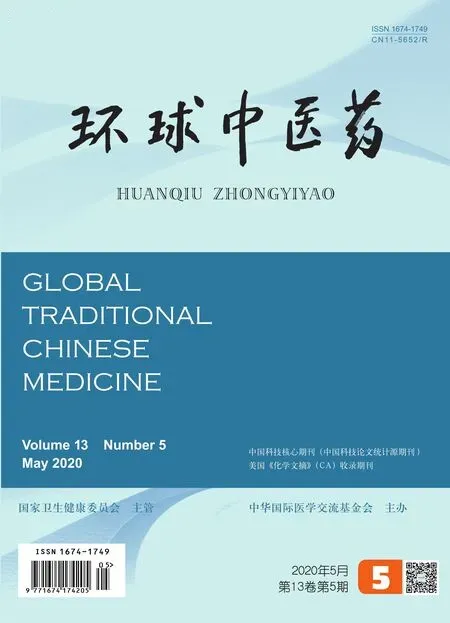“肝应春”理论本质内涵探讨及临床意义
李婷 刘雷蕾 韩琦 李文娜 李佩佩 谈博 马淑然
中医学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活动要和自然界的变化相适应,而“肝应春”是天人相应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肝应春”的本质,可以为多种疾病提供预防及治疗的理论依据。目前关于“肝应春”的理论研究偏重于宏观探讨,并未深入研究肝脏具体哪个功能增强或减弱。因此,课题组系统阐释了在春季肝疏泄、藏血功能如何调节其自身以应升发之气,其他季节如何调节他脏应于四时之变。肝脏疏泄藏血功能随季节变化的自稳机制,对精神情志类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
1 关于“肝应春”理论内涵的不同认识
对于“肝应春”理论本质,学术界认识尚不统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侧重从肝生理特性和功能及五行归属角度讨论“肝应春”的内涵;第二,从肝疏泄失常致病角度讨论“肝应春”的本质。
1.1 从肝生理特性和功能及五行归属角度探讨“肝应春”本质
有学者将肝的生理特性类比春季植物的升发之性,如刘燕池[1]认为肝疏泄调畅气机的功能,与春季树木生长伸展和生机勃发之性类似。袁卫玲等[2]认为肝升发之气随春季阳气升发而升发,肝木之性亦随之舒畅条达。李素敏等[3]认为春季阳气萌动,万物复苏,肝内应藏有生升之气。
有学者从五行角度论述“肝应春”。杨芳艳等[4]强调五季之气五脏应之,肝五行属木,在时应春。陈玉萍等[5]基于五行理论认为肝是在春季起主要调节作用的自稳时间调节系统。
有学者认为肝气升发疏泄的生理功能与春季气候变化相关,如吴菁等[6]认为“肝应春”主要体现在其升发疏泄之力增强,并处于主导地位。覃骊兰等[7]认为“肝应春”核心思想是肝的生理功能与春季气候变化具有同步相应与协同变化的关系。侯雅静等[8]认为肝的生理功能与春季的气候变化协调一致,其生理功能自稳调节在不同季节会相应改变。
1.2 从肝疏泄失常致病探讨“肝应春”本质
第一种观点认为肝疏泄太过致精神类疾病高发,如精神分裂症春季新发、复发率较高。高丽波等[9]认为肝疏泄太过,肝阳上亢,容易出现狂乱之证。第二种观点认为肝疏泄不及致情志疾病高发,如抑郁症。陈颖之等[10]认为肝喜条达而恶抑郁,若不顺应春季升发肝气,肝气郁滞于内,气机不畅则百病丛生。临床表现为情志抑郁,多疑善虑,胸闷,喜叹息。刘仕琦等[11]认为抑郁症春季高发,其发病机制在于肝疏泄功能不及,气血郁滞。第三种观点认为肝之病变得春升之气资助,可以好转。杨云霜[12]认为肝气通于春,肝的生理功能春季旺盛,肝病在春季得自然界之气滋助可以好转。
综上所述,生理层面上,刘燕池、袁卫玲、李素敏等从肝气在春季升发的角度认识“肝应春”本质;杨芳艳、陈玉萍则从五行角度认识“肝应春”本质;吴菁、覃骊兰、侯雅静则从肝生理功能层面讨论“肝应春”的本质。这些学者对“肝应春”的认识仍停留在肝气发挥主升、主动、主疏泄功能与春季升发之性类似,以上这些观点虽然从肝的生理特性和生理功能论述了“肝应春”的理论内涵,但只是具体阐述春季肝主疏泄,主升主动,并未提及春季肝主藏血如何变化以及肝主疏泄和藏血的关系。
病理层次上,高丽波、陈颖之、刘仕琦等认为肝疏泄太过或不及易引发精神情志类疾病,并具体到相关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杨云霜认为肝脏疾病亦可在春季好转,但未具体阐明春季肝的生理功能哪些加强,哪些减弱。高丽波虽然指出肝疏泄功能春季最旺,但对春季多发疾病的具体机制未能深入阐述。而且上述观点涉及一个矛盾点,既然肝气在春季最为旺盛,为什么春季又多见肝系疾病,很难自圆其说。再者,杨云霜认为肝病在春季得自然之气的滋助可好转,但临床上并非所有的肝系疾病均会在春天好转。因此,此观点与临床实际不完全吻合。
基于理论与临床实践,课题组提出肝存在自我调节机制,具体表现为疏泄和藏血两个方面,“肝应春”是肝应春季升发之气,疏泄功能增强,特别是肝阳之气的升发功能增强,并处于主导地位,而肝藏血功能则相对减弱,两者发挥着对自身及其他四脏的调节作用,而其他季节肝则处于从属地位,协助或抑制其他四脏以维持机体应时而变,如果肝疏泄和藏血功能与季节变化不相适应,则会导致一系列疾病的发生。因此,“肝应春”实质是肝调节机制在自然界自我调控的反应。
2 肝对自身及其他应时之脏调控机制探讨
2.1 肝通过疏泄藏血调节自身以应春升之气
肝主疏泄和藏血是肝生理功能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一者属阳,向外向上,一者为阴,收敛内藏。肝主疏泄更多表现在促进血液与津液的运行输布。肝主疏泄,调畅气机,促进血液、津液运行,使之畅达而无瘀滞。而肝贮藏的血液,通过肝主疏泄,可以根据机体活动量的增减、情绪的变化、外界气候变化等因素调节人体各部分血量的分配,当机体剧烈活动或情绪激动时,通过肝气的疏泄作用将贮藏的血液向外周输布以供机体需要;当机体安静或情绪稳定时,部分血液归藏于肝,如王冰注释《素问·五藏生成篇》所说:“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脏。”
肝应于春,并非肝所有功能在春季全都增强,而是肝疏泄功能增强,藏血功能相对减弱。肝气正常升发启迪诸脏,脏腑之气升降有序,气机调畅,促进血液随之运行,环流周身,内养脏腑,外溉四周,藏泄有度[13],如唐容川所言:“肝属木,木气冲和条达,不致遏郁,则血脉得畅。”[14]
2.2 肝通过疏泄藏血调节他脏以应四时之变
2.2.1 夏季肝对心调节以应夏 心之阳气最旺的夏季,肝疏泄功能增强,升发之气较春季加强,调畅全身气机,进而促进全身气血津液的畅通。夏季,肝疏泄功能达到顶峰,为“心应夏”提供内在驱动力,若无肝木的疏泄条达,就无法达到精、气、血、津液向外布散,精神焕发,出汗增多,心跳和脉搏加快的“心应夏”的状态[15]。同时,肝藏血功能进一步减弱,随着神的物质基础血的减弱,所以心藏神功能在夏季减弱。《类经·藏象类》云:“神藏于心,故心静则神清;魂随乎神,故神昏则魂荡。”若两者协调不当,易发生“暑气扰神”的季节性病变。因此,在夏季,肝疏泄增强,藏血减弱很好地调节了夏季心主血脉和藏神的变化。
2.2.2 长夏肝对脾调节以应长夏 长夏是夏季向秋季的过渡季节,多雨多湿令肝主疏泄功能减弱,藏血功能则进一步增强。长夏时节,脾主升清的功能处于相对抑制的状态,运化功能相对下降,人体气血津液从趋于体表向趋于体内转变。长夏肝疏泄和藏血功能的转变促使脾与长夏之气相通应,成为应长夏之时的主脏之气。此时脾的功能由升清为主逐渐转化为统血为主,为秋冬之际气血津液趋于体内奠定基础。于肝而言,长夏肝的疏泄和藏血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从而调节脾气机升降平衡及脾统血与运化升清的平衡。
若肝气过旺影响脾运化与升清的功能,可见肝脾不和之证,表现为头目眩晕、两胁胀闷、纳呆、腹泻等。若影响胃受纳与腐熟功能,可见肝气犯胃之证,出现呕逆、嗳气、脘腹胀满疼痛等症状。
2.2.3 秋季肝对肺调节以应秋 秋季肝疏泄功能进一步减弱,肺宣发布散的津液变少,因此燥秋之时,人体气血津液处于内敛状态,此时肝藏血功能相对加强,促使肺肃降收敛功能加强,使肺肃降功能正常发挥,一身气血津液更多地内养脏腑,下输膀胱。因此,在肝藏血与疏泄的调控下,肺宣发功能减弱,肃降功能加强,气血津液更多地趋向体内,向上向外布散减少。
病理情况下,肝气升发太过,致肺气肃降不及。《王氏医案释注》言:“左升太过,右降无权。”临床上,肝木之气太过,反侮肺金,可出现咳嗽、咯血等症状。
2.2.4 冬季肝对肾调节以应冬 寒冬时节,肝藏血功能达到一年之际的峰值,而疏泄功能则处于谷值。肾主藏精、纳气的功能也达到峰值,肝较低的疏泄功能可促使肾气封藏有度,而肾的闭藏功能可防肝疏泄太过。同时,冬季肝疏泄功能处于低谷,使肾主生殖、生长发育的功能降低。另外,肝疏泄功能的降低使肾阳蒸腾气化水液功能降低,多余的水液则从膀胱排出,导致小便量多,此为肝应时而变对冬季肾脏的调节作用。
3 “肝应春”理论具有临床意义
3.1 “肝应春”有助于解释肝系疾病的病理变化
肝疏泄太过或不及均可发生病理变化。某些肝系疾病春季加重,某些缓解,临床中这些疾病的病理变化机理不明确,而肝疏泄藏血的调节机制有助于解释临床完全相反的症状。
3.1.1 肝疏泄太过易致肝风内动 素体肝阳偏亢或肝阴不足,当春季肝升发太过,可引发肝病[16]。《史载之方》云:“夫春气本和,而反伤于热,此阳气所胜,肝家受热。”若顺应春升之气,肝气升之太过,则肝风内动,肝阳上亢,易致中风病变出现。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曰:“入春地气升,肝木风动,遂令右肢偏痿,舌本络强,言謇。”具体而言,可见阳亢劲急之病,出现头晕欲仆、四肢麻木、活动失灵、言语不利、半身不遂、口眼斜等症。

3.1.3 肝疏泄不及可缓解情志疾病 春季有所缓解的疾病大多是情志疾病。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多种情志病变的缓解在一定程度上受季节变化的影响[18]。情志病春季缓解是因为轻微的疏泄不及得春升之气所助,疏泄不及的状态得到改善。这也从侧面证实机体顺应了春季的升发之气,机体即使处于疾病状态,亦可得到缓解。
综上,从病理角度分析,春季肝系疾病主要表现为疏泄太过引发肝风内动和疏泄不及而致肝气郁滞。前者导致筋脉挛急失养,引起肢体震颤,手足麻木;后者因为肝气虚弱,无力升发,疏泄不及引起一系列郁滞之状。相反,机体顺应了春升之气,因肝轻微疏泄不及导致的情志病变也会得到进一步缓解。
3.2 “肝应春”理论有助于解释疾病季节性发作的病机
3.2.1 “肝应春”理论可解释部分过敏性疾病季节性发作的病机 过敏性疾病可应用“肝应春”理论进行阐释,并可据此解释与季节相关的某些疾病的产生,如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均在春季多发。
从天人相应角度分析,“肝应春”理论与过敏性鼻炎发作或加重的时间规律具有相关性。肝为风木之脏,风气通于肝,风易入之。肝经“布胸胁,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与鼻相通。无论是外风流窜还是内风上扰亦或内风招致外风,外风引动内风皆可借助肝经影响到鼻而致鼻窍失司,导致以鼻塞、鼻痒、喷嚏、流涕等为主要表现的呈季节性发作或加重的一类疾病的发生[19]。
荨麻疹一年四季均可发病,但春季多见。展照双等[20]基于“冬不藏精,春必病温 ”理论,认为若先天肾精不足,又因冬季摄生失养使肾水失于封藏,至春季阳气萌动之时,则致厥阴肝木疏泄过激,木气拔根,相火妄动,此时感受春季风热时令邪气,内外相引而发为荨麻疹,这从侧面印证了肝应于春理论的正确性。
3.2.2 “肝应春”理论可解释精神情志类疾病春季多发的原理 春季易导致诸如躁狂症、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等精神情志类疾病的发生。若肝疏泄功能太过,肝阳上亢,化为肝火,心肝火旺,表现为面红、目赤、急躁易怒,甚则哭笑无常发为癫狂之证。所以躁狂症的发病多与心、肝相关。春季气候不稳定,气压较低,人体为适应气候变化,其体温调节中枢-下丘脑会对体内环境和内分泌系统进行调节,使人情绪波动,所以精神分裂症在春季新发和复发率较高。春季是抑郁症的高发季节[21],因肝与春之气相通应,喜条达而恶抑郁,如果肝失疏泄导致气机郁滞不畅,则易导致抑郁症发作。抑郁症的季节性发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季节变化对人情志的影响。
3.3 “肝应春”有益于指导临床治疗
春季高发疾病如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躁狂症、精神分裂症等均可在“肝应春”理论指导下遣方用药。
3.3.1 “肝应春”理论可指导过敏性疾病的辨证和治疗 治疗方面,过敏性鼻炎的治疗需循序渐进,分阶段进行辨证论治。发作期以疏风祛邪为主,兼顾兼夹的其他病邪的治疗和通利鼻窍,宜用苍耳子散;缓解期着重调整脏腑功能,益气实卫、养阴柔肝、疏肝通窍、补脾益肺、壮肾助阳等,酌情使用玉屏风散、左归饮、右归饮等。
荨麻疹为血热受风者,治宜疏风凉肝,清热解毒,以荆防消风散、小柴胡汤或荆防败毒散加减;风盛者,治宜疏风解表,以消风散或秦艽牛蒡汤加减[22];血热者,治宜清热凉肝,以凉血解毒汤治疗;气滞血瘀者,治以活血化瘀、通络利窍,方以通窍活血汤合苍耳子散。其中消风散最为常用,疏风除湿。清热活血凉血亦可治疗急性期荨麻疹,酌加地肤子、防风、蝉蜕、赤小豆清热祛湿止痒,也可以活血养血祛风,酌用活血祛风汤和当归饮子[23]。
3.3.2 “肝应春”理论可指导精神情志类疾病的辨证和治疗 针对春季高发的精神情志类疾病,躁狂症阳证分型多不离肝,如肝火内扰型、肝胆郁热型、肝郁脾虚型等,针对肝失疏泄证,拟用当归龙荟丸、丹栀逍遥散、逍遥散、六郁汤[24],亦可重用生铁落,平肝重镇降逆泄火[25]。
精神分裂症不同证型宜使用不同的方剂进行治疗。肝气郁结型予逍遥丸合礞石滚痰丸加减;肝郁化火型用丹栀逍遥散合左金丸加减;肝郁脾虚型多用逍遥散;痰火扰神型多用黄连、黄柏、当归、龙胆草、芦荟、生大黄、牡蛎、知母、芒硝、石膏、甘草等;气滞血瘀型,此处气滞单指肝气郁滞,拟用龟板、枸杞、生地、香附、青皮、大腹皮等[26],亦有用黄连解毒汤和癫狂梦醒汤联合泻火解毒治疗此类疾病的报道[27]。
抑郁症分型总有肝气郁滞型[28]。肝郁可能是抑郁症发病的重要环节,柴胡疏肝散、逍遥散加减化裁使用较多[29],出现频次较多的药物多为疏肝解郁之品,如当归、人参、柴胡、甘草、浮小麦、茯苓之品[30]。
综上,过敏性疾病在急性期均以疏风凉肝为主,兼以随症加减。而精神情志类疾病则更多选用疏肝之品,因为只有肝疏泄功能正常,这类疾病才有好转的迹象。肝气机升降功能正常,五脏就能发挥正常的气化功能,而气化的产生又受到肝疏泄功能的影响,与“肝应春”相关,所以这些疾病的治疗均是在“肝应春”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4 结语
中医“肝应春”理论具有十分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据此分析、诊断、治疗疾病不但对许多过敏性疾病和精神情志类疾病的病因病机的产生有所启迪,还有助于提高临床治疗效果。目前对于“肝应春”的实验研究以及与现代神经内分泌的关系研究尚未深入,因此有必要加强“肝应春”理论的实验研究以揭示这一理论的科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