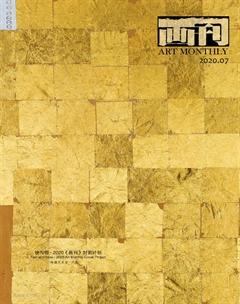“新美术馆学”与自我批判体制
王璜生

“体制批判”的理论话题及相关论述,近10年来国内似乎讨论得比较多。一方面,这样的理论思考与研究为艺术生产机制、艺术制度等带入新的视角与探讨的深度,开阔了艺术理论、批评及相关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另一方面,我们也意识到,从“体制批判”到“体制化”的过程具有一种互相转化、无法摆脱的内循环特征。无论是处于艺术生产体制中的艺术家、艺术生产者等,还是本身就是体制一部分的博物馆、美术馆、艺术机构、艺术市场等,都逃脱不了“体制化”的结果,或根本就乐于安享“体制化”。这也就使得我们会怀疑“体制批判”是否是一个假命题?“体制批判”是否只是一种艺术策略,而最终还是认同并乐于“被体制化”?或者,中国这样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体制机制,其运转功能强大,其相关的利益后盾盘根错节。而作为意识形态体制中的博物馆、美术馆系统,能否从这样的体制内部来进行“批判”与“反思”,推进中国的美术馆学科理论及实践与国际前沿文化对话的可能性,也参与到当代艺术生产机制及理论研究的社会实践中?这正是本文写作与研究的出发点。
作为美术馆学的研究者,希望从美术馆体制的主体内部来探讨“体制批判”的相关问题,同时也有必要简单梳理“体制批判”理论出现针对性及反思性的理论过程。
一、美术馆是“体制批判”首当其冲的对象
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界较多地讨论“体制批判”问题。“Institution”一词具有多重含义,在这里译为“体制”,但它兼有无形的“制度”和有形的“组织”多重含义,所以“体制批判”实际是指代对于艺术制度和体制的批评。
在“体制批判”的针对性论述中,往往作为艺术生产体制的主要交叉节点——博物馆、美术馆,成了批判、反思与挑战的重要对象。博物馆和美术馆在整个艺术生成机制、结构与流程,包括艺术家、环境、时代、思潮、批评家、理论、市场、画廊等环节中,是关键的聚合点。美术馆和博物馆的策展、理论表述与批评、艺术史话语、空间展示及展览方式、收藏机制,以及美术馆的解读及与公众的关系等,成了艺术生成机制中一系列重要的因素、焦点,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关系。因此,在“体制批判”的理论框架中,无论是对策展机制、展览制度的批判,还是艺术价格体系、市场规则、社会机制等的生成,还是艺术史法则、艺术语言系统、公众策略等,往往交叉点与生发处都与美术馆、博物馆密切相关,美术馆、博物馆本身也在这样的艺术体系与社会规则中生成自身的制度性话语及操作性法则,极大地影响着整个艺术生成体系的建构与演进。
因此,博物館、美术馆体制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也就一直是“体制批判”及新博物馆学反思首当其冲的对象。在“体制批判”中,从理论家、哲学家、文化学家层面,对艺术的生产机制,包括对历史中的艺术生成与转型作出了很多精辟的分析、论述;从艺术家的层面,针对艺术体制的空间问题、权力问题、收藏体制问题等,进行了批判性、介入性的创作;而作为体制中主要一环的机构,特别是博物馆、美术馆,也对自身的运作机制作出了层层的反思,在“自我批判”中体现出对体制及体制化的抗争。
首先是来自哲学家、理论家的“体制批判”。从哲学家、社会学家的角度来看,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强调的是艺术品价值生产的体制,而不是具体的艺术品生产。价值是不能单靠具体的物品本身来实现的,作品能否有价值得需要别人来相信和认同。人们接受艺术品是因为相信和认同艺术品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而要实现艺术品的接受,就需要有美术馆、批评家、策展人,也包括学院、艺术教育等各个机构和环节来发挥作用,构成一个场域、一个权力空间,艺术在其中获得“圣名化”。艺术的价值是由这样的权力空间与体制场域所赋予的。
在体制论的视角下,艺术处在一个由理论、观念、机构、空间、人员等各种要素所构成的庞大的权力空间当中。这一系列的权力空间,可以在作品所处的物理空间中获得一个表面印证。当年,杜尚的小便器《泉》之所以成为划时代的“艺术品”,它的生产机制就是围绕着展览会、美术馆这样的文化权力空间而综合生成的;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也具有相似的意义。杜尚的小便池是摆在展览会上,而非普通人的家中;沃霍尔的汤罐被挂在画廊里,而不是摆在超市中。展览会、美术馆、画廊,不只是一个特殊的地点,更是一个可以给放置于其中的物品以艺术之名的地方。这样的权力空间产生并召唤着一种对艺术的信仰和认同,那么,在这里,艺术、艺术家、意义生成、社会认知、艺术史认可,从而进入收藏、市场、价值认知等,都围绕着美术馆、展览机构这样的权力空间及权力体制来展开。“体制批判”主要针对的是“权力”“空间”“话语权”等体制机制,而恰恰,博物馆、美术馆就是这种权力体制的代表。
同样,从“体制批判”一开始,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就表现出对博物馆、美术馆体制与收藏模式的挑战与反思。同时,也受欧洲社会左派思潮的影响,其作品的表现形式较多地是批判美术馆空间及制度所代表的权力。
艺术家一方面针对性地挑战博物馆、美术馆的收藏权力及系统机制,这种能够带动艺术生产、社会联动、市场价值等的体制系统,往往通过艺术博物馆的“权威性”与“收藏”“进入艺术史”“永久保存”等价值认知与运行机制,使得艺术生产及社会价值成为约定的可能。而如大地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克里斯托(Christo Javacheff)等,他们在荒野大地上进行的艺术创作,初衷是针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工业化文明及体制的反叛,这其中,从具体的艺术形式形态看,更具有反博物馆、美术馆特定展出场域与收藏体制的批判性。
对特定地点的场域特别是美术馆这个具有标志性的空间、陈列法则及隐含的权力机制作出针对性的批判,麦克·亚瑟的“芝加哥计划”是很具典型性的。麦克·亚瑟将一尊从让-安托万·乌东(Jean-Antoine Houdon)的大理石原作翻铸的乔治·华盛顿铜像,从台阶顶层移到了原本用来展示18世纪法国作品的画廊展厅的中心。当作品被移动到了展示18世纪法国作品的展厅时,它就失去了原来的语境,原本的政治属性被一种美学和艺术史语境所替代。
艺术家马克·迪翁(Mark Dion)的装置作品常常模仿美术馆、自然博物馆、艺术学院的展陈与内部装饰。自1993年以来,他利用考古学、生态学以及美术馆学中收集、排序和展示物体的科学方法创作出了一系列鸟舍作品——《自然世界剧场》(Theatre of the Natural World),来质疑这些由机构与体制塑造出的所谓“客观”与“理性”的观看方式。
而汉斯·哈克(Hans Haacke)的《凝结体》(Condensation Cube,1963-1965)和《MoMA调查》(MoMA Poll,1970),所批判的不仅仅是博物馆、美术馆的空间与体制,也不仅仅是那包含各种空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的泛体制,而是引向存在于上述体制元素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网络,那些存在于特定社会空间中的抽象不可见的力学和关系。
从20世纪60、70年代到90年代,西方一直不断涌现着做体制批判的艺术家,其批判的对象也并不仅局限在美术馆,同时还有画廊、艺术家工作室、双年展和其他艺术话语形成的场所。后来的体制批判艺术家从单纯对博物馆、画廊等体制的批判扩展到其背后的艺术家身份问题、种族问题与大众观看方式的思考。
二、“体制化”的美术馆“自我批判”何以可能
随着一些体制批判的作品被机构收藏与接纳,这些作品的创作目的也就很难再有批判效应。人们对批判性展览的接受度更广了,但作品却很难再次如浪潮般涌现,当今的体制批判艺术实践趋于个体化、特别化。
美国学者安德莉亚·费瑟(Andrea Fraser)在《从体制批判到批判的体制化》(From the Critique of Institutions to an Institution of Critique,2005)中发问:在当下,“体制性批判”是否已经被体制化了呢?可以说没有任何批判能够脱离艺术机制,脱离艺术机制的批判显然也是边缘化的、没有影响力的。因此,我们必须明白的是艺术体制不只是体制化为美术馆这类的机构,它同时也被人们所内化。它内化在促使我们得以生产、书写与理解艺术,或仅仅是将艺术辨识为艺术的种种能力与感知模式之中,并形成一个庞大而繁复的共谋结构。
安德莉亚·费瑟说:“今天,人们认为不存在‘外在于体制的空间。因此,当博物馆和市场已经成为无所不包的文化工具时,我们怎能想象对艺术体制的批判,遑论将其实现?今天当我们最需要体制批判的时候,它却已经死去,成为其自身成功或失败的牺牲品,被它曾反对过的体制所吞没。”
几乎与艺术的“体制批判”理论及实践前后脚,20世纪60-70年代开始,西方的博物馆、美术馆出现了后来被称之为“新博物馆学”的理论及实践,它们针对的正是博物馆、美术馆的体制,从博物馆自身内部对藏品体制、陈列体制、空间权力问题、公众政策、社区生态等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及相应的实践,最主要的是对博物馆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及这种体系背后的文化权力、种族性别、文化平权等理论进行介入。其实,这其中的根本点也即“体制批判”,即博物馆、美术馆体制机制的自我反思。
在欧美,随着现当代艺术在艺术博物馆的高度活跃,针对引发的问题越发具有社会学意义与前沿性,新博物馆学也不断引发与当代艺术的对话,于是更直接催生出“新美术馆学”的理论论述与艺术实践。
“新美术馆学”的核心问题包括:一是关于“人”。这个“人”,作为主体的问题,指向艺术家、公众等,其实也包括美术馆管理者、策展人等。“新美术馆学”除了关注作为社会、历史、个人性的艺术家,关注作为艺术家的“人”的身份,包括文化身份、集体身份、社会身份、时代与区域身份等。它注重“人”的身份的主动建构与被建构的过程,艺术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的。此外,它也特别关注体制化的美术馆框架中的公共服务、公众政策、文化策略等问题。当然,在美术馆体制中的人,如何管理、运营、组织,包括反思、批判这样的体制机制,也是一个应该高度受重视的研究对象。
二是关于“空间”,多向度的“公共空间”问题。“新美术馆学”视野中的空间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公共空间”,包括精神空间与物理空间。“公共空间”虽然不是新的概念,但对于当前中国的美术馆而言,却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核心职能,其重要性等同于展览、典藏、教育、研究等传统功能。“空间”本身是多层次的,包含它的物理形态、精神形态、社会心理形态等,都与“公共空间”的实現密切相关。“空间”维度的打开,势必也是一种对于空间权力、空间制度化、空间认知等的新态度。
三是“新美术馆学”中的重点,即关于“体制”“制度”的建构、质疑、反思与批判问题,这当然指向于体制制度中所提出表现的“权力”问题。
对于中国的美术馆体制来讲,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及历史进程,目前重点依然在建构与完善的过程中。然而,在这样建构与完善的基础上,我们如何来认识美术馆体制的独特性及时代性;同时,在时代的思想、文化及潮流中,批判、重思、建构美术馆与时代、区域文化,及人与艺术生产相呼应的体制、制度、机制。
美术馆的公共性意味着它将被视为独立文化议题、文化政策与理念、意识形态与全球重大问题表达、讨论甚至争论的场所空间。对“治理”和制度的认识扩大了美术馆在文化历史活动中的参与性,也加强了人们对美术馆文化功能的认识。同时对内而言,美术馆需要规范化与体制化的运作。制度的建构过程本身隐含着一些合理性,但同时生成很多自身的问题。美术馆的制度化权力包括行政、策展、展览、资金分配、藏品管理等诸多面向,这使美术馆在政治现实与文化激荡中面临着改革、反思与质疑。
这样的反思与质疑,也即美术馆作为一个权力空间和文化标志的空间,以及作为知识生产和文化生产的体制化阵地,我们应该如何对体制问题反思与批判、对策展方式的质疑、对权力体系的消解等,这也集中反映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在美术馆体制批判中找到了一个新的发泄对象和思考对象。
在制度、体制的层面上,美术馆显然受制于国家政策和制度,它必然会受到意识形态与相关诉求的影响。美术馆有必要履行一些重要的公共职能,同时努力保持自主的尺度。于是从一个权力框架内看美术馆成为一种必然,同时也引发了对于“制度”与“权力”的具体思考,例如:
1.藏品的入藏制度、管理制度在发生重大变化,数字化、社会化、知识产权与使用权等。
2.策展权力的质疑及策展体制的新思考、新实践。
3.展览体制、话语权及话语方式的重新思考。
4.美术馆的权力让渡与自我批判意识、美术馆的文化平权。
5.国际新关系中的美术馆体制变革。
……
这样,“新美术馆学”需要向内展开,批判性地关注美术馆的实际操作问题,也关注美术馆运用过程中的制度问题及相关当代文化理论问题。“新美术馆学”在国家文化政策的法律下运营,在这一过程中,艺术机构、艺术生产和艺术世界都带有制度研究的属性。而“新美术馆学”不再是稳固的,而是反观性的,它置身于批评现场,需要批判思维;它考量权力场域、政治场域、艺术平台共生制约关系,也特别关注当代意义的多元文化概念。
从美术馆的内部,对体制化的美术馆进行挑战、反思甚至批判,这样的实践,也许更能引发体制化内部的自我批判精神与具体工作实践。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空间协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第三届CAFAM双年展”,正是以这样的自我反思与质疑批判为出发点,对美术馆的展览运行机制、双年展的体制、策展人及策展的权力机制、美术馆的空间权力、美术馆与社群关系、文化平权与民主等问题进行反思、讨论与批判性实践。
安德莉亚·费瑟曾尖锐指出:“问题不在于反对体制:我们就是体制。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代表何种体制?我们将何种价值作为体制化的标准?我们奖励何种形式的实践以及我们渴望什么形式的回报?体制批判要求我们问自己这些问题,因为艺术体制内在于人的心中,由人来体现和执行。”因此,体制中的“自我批判”而产生出“批判的體制”,“由此体制批判才得以对艺术体制进行评判,评判其代表性文本提出的批判立场,评判其‘抵抗和反对场所的自我定位,评判其激进的神话和象征的革命。”
这样,从“新美术馆学”的理论与实践的角度,使“体制化”的美术馆“自我批判”应该成为可能,也使以人为主体及执行者的“新美术馆”可能构建为“批判的体制”,成为具有“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的美术馆。
注:本文原为“2019·全国批评家年会:批评视野的艺术机构”大会演讲稿,2020年6月15日重新修订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