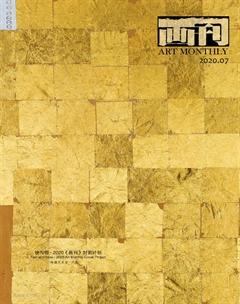从同质走向多样的空间:文化多样性语境下作为公共空间的美术馆
徐梦可

道格拉斯·科瑞普(Douglas Crimp) 在《后现代博物馆》(The Postmodern Museum)[1]一书中,以柏林旧博物馆(Altes Museum)为例,对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诞生作出了分析。科瑞普认为:柏林旧博物馆[在建立初期名为“皇家博物馆”(Koenigliches Museum)]是一次现代艺术理念的制度表达。由于该馆的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是黑格尔的密友,科瑞普在书中称:这一博物馆的设计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黑格尔艺术哲学的支配性影响。他认为艺术博物馆是一个去政治化的空间,把艺术作品从现实的生活语境中抽出来置于其中。于是,艺术博物馆成了一个“排斥与限制的空间”[2],一个脱离社会语境的“异位”[3]的存在。
公共性:博弈与支撑
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美术馆与政治、社会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在经历了空间上的拓展转化(奇珍橱柜、大师工作室、博物馆、艺术厅等)和功能上的推陈出新(王室权力象征、贵族特权彰显、知识生产的工具等)后,美术馆本身已经从一个封闭的场所逐渐成长为一个面向全体公众开放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经过了几个世纪的重组和发展,美术馆的语境越来越广阔,而这逐渐开放、发展的过程离不开一条红线——有趣的是,这一点也是科瑞普提出的——那就是美术馆依赖于一种考古的认识论:展示在其中的物(object,也就是美术作品)遵循着一种“虚构的逻辑”[4]。
这种“虚构的逻辑”绝非诞生于偶然之中。如何对美术馆空间内部进行分类和排列,反射出的是某种对世界的理解。这样一来,当我们用考古学的思维去回顾博物馆的发展史,即可以看到这种逻辑——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知识”不断系统化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术馆不仅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人在美术层面的认识论和知识结构,其本身也是应时代文化知识的要求而诞生和发展的。因此, 如果没有这种“虚构的逻辑”,美术馆就会从一个表征的空间变为一个缺乏意义的仓库。
知识与机构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博弈又相互支撑的关系,这种关系和“权力”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权力和知识的态度变化会导致机构的转型。在美术馆和构建美术馆的知识互为共构的过程中,由于“知识”本身的调整,美术馆实际的所指也在调整。从公共空间的角度看,它决定了“公共”这一概念所指的变化。美术馆空间不再是一个“限制”出入的场所,相反它成了一个“公共文化空间”,面向全体公民敞开大门。
由于美术馆与知识和权力相关,某种程度上来说,美术馆既是主流文化的表征空间,也一直是文化政策扶持的重点。以美术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设施的运营就占据了国家大部分的文化预算。美术馆属于公共文化领域,它需要去反映公众的利益。然而,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多样性”和“全球化”已经逐渐重新定义了民族国家及其运作的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管理和定义文化机构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当我们把美术馆称为“公共文化空间”的时候,我们说的“公共”究竟指的是什么?它真的是属于“公共”的吗?“公民”的概念又有什么新的变化?这一变化又会对美术馆本身产生什么影响?
认同感:同质与转化
提出这些问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市中的“公共空间”——不仅指美术馆,还有博物馆、文化中心、剧院甚至是广场等——都受到了传统意义上同质化的“公共”文化概念的支配,其反映的是那种公共文化的规范和标准。这就导致在公共领域/空间中,多样性文化群体的代表和身份没有得到完全的彰显。自2000年以来,传统意义的文化概念已经逐渐被一种差异性、多样化的文化概念所取代了。以欧洲政府来说,二战以后,少数群体一直被欧洲社会看作是一种不得不面对的“不幸问题”,问题的本质是欧洲战后新建立的文化秩序,要求欧洲政府必须要处理主流文化和少数群体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当时面对“少数群体文化”的焦点是其给整个文化秩序带来的问题和困难,以及多数群体及其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或者控制这些问题。而到了20世纪末,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用简单的“少数/多数”这种二元对抗方式无法真正理解文化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要超越这种简单的理解框架,就需要一个新的概念。于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多样性”取代了“少数群体”,成为理解欧洲文化差异性新的概念框架,且立刻促发了很多积极的进展。
首先,人们不再把“文化多样性”视为一种由少数群体提出的一种“他者”的术语,而是将其视为公共空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次,“多样性”概念的提出不是让人们努力实现差异的去种族化,而是不自觉地扩大了差异性的范围,将性别、年龄、性取向、是否残疾等条目纳入讨论范围之中。最后,“多样性”的概念让人们可以看到差异的复杂性,抛开问题表象,“差异”不再成为需要被同化、被解决的“问题”,而是成为公共文化空间的积极资源。换句话说,“它差异性”变得有效了。2000年12月7日,在欧洲委员会第733次部长代表大会上,部长委员会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可以看作是“多样性”取代“少数群体”的重要标志之一。
從传统的角度看,与少数群体相关的议题和政治事务往往是在严格的国家背景下解决的,解决方法几乎是根据该国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举个例子,如果少数群体表示自己的文化需要被国家承认,那么该国通常会施行一种让多数群体包容少数群体的社会和文化政策。但这么做的结果通常是让少数群体的社会和文化观念融入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社会文化秩序当中。从这一视角来看,少数群体的问题就基本被“解决”了。比如在美术馆里设立“黑人艺术”展厅等,看上去是对少数文化的包容,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同质化的、流于表面的解决方法。不仅如此,在20世纪初,这种整合主义方式的困难和局限性已经开始愈发凸显。随着不断增长的移民数量和移民人口生活方式的转变,“少数群体”的问题已经跳脱到国家参考框架之外,开始被当作“多样性”现象纳入国际和跨国家参考框架之内了。2001年7月,欧洲委员会修订了《文化多样性宣言》,增设了一条“(成员国已意识到不再)只能在国家一级有效处理文化多样性问题”。有趣的是:不只在欧洲,整个世界都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01年底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第31届会议上也审议通过了《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及《行动计划要点》,《宣言》的第10条专门强调了国际合作和国际团结。
文化从同质走向多样,另一个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就是公民身份的改变,这也决定了在作为公共空间的美术馆中,“公共”这一概念的承纳范围。公民身份代表了一个自然人在现代国家中的成员身份,把形形色色的人带入到了一个政治共同体当中。德里克·希特(Derek Heater)曾说:“公民身份有助于驯化其他认同相互撕裂、分化与离散的冲动。”[5]这就是公民身份中的一个基本价值:归属感。它象征着一个公民对这个国家的认同。在现代国家当中,公民身份和共同的国族认同息息相关,而国家认同本身就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国家认同不仅包括了国家要满足领土内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还要制定统一的、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体系,最重要的是要包含共同的社会文化。按照这种逻辑,共同的社会文化本身就是制造公民身份的重要一环。那更进一步来思考,在新的文化需求语境下,公民权就有了新的要求:让人民生活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之中,且有权保持区别性和差异性,也就是一种新的“文化公民”概念,从而适应从同质性文化原则向异质性文化原则的转变。
思维转化:何为空间的多样性
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如果没有进行思维转化,还是用一种“少数/多数”二元分割的观点去建构一个多样性空间,就可能会有事倍功半的效果。在多样性文化空间的要求下,以美术馆、博物馆、剧院为代表的公共空间作出了许多尝试。很多美术馆都在现实运转模式中,去尽力符合文化公共空间的公众权利和充分表征的原则。詹妮·威尔逊(Jenny Wilson)在“新观众项目”(New Audiences projects)的一个报告中,概述了艺术行业在拓宽自己观众渠道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报告专门指出:在2008年到2013年的英国,能走进剧院、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大多是中产阶级白人。而当时的艺术界依然存在一种观念,就是简单、错误地认为黑人、亚裔艺术会吸引来黑人或者亚裔观众。2003年由英国文化委员会出版的《文化多样性与受众发展》报告,就特别强调了这种简单的、用基本术语来进行定义分类的方法会破坏公共空间的同质结构。比如,为了吸引亚洲的观众而专门建立一个“亚洲剧院”,“不仅贬低了作品,也会减少观众”。艺术家不会喜欢被简单的种族、出身的方式区分,观众也一样不会。美术馆如果要让自己的公共空间属性在文化多样性语境下成立,就一定要去做一些特殊的尝试,在拓宽自己展示范围的同时,吸引那些本不大愿意进入美术馆的群体。
然而威尔逊指出:那种妨碍人们参观的习惯(也就是所谓的“知觉障碍”)是非常难以被突破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美术馆就需要发出一种欢迎和包容的信息,而非通过定义“多样”而让这种“多样”显得更加突兀。遵循着博物馆本身的工作惯例,在试图建立一个“多样”空间的时候,美术馆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不同的社群聚集在一起,然后通过种族把大家区分开来,进行更细致的工作。然而问题是:少数族裔社群本身或许不是一个同质群体,其本身非常的多元化,这样定义的方式抹平了内部差异,没有考虑到年龄、经济、宗教、婚嫁等方面的问题。如果要在现实的运转模式中尽量遵循公众权利原则和充分表征原则,就需要通过多个层面来了解一个社群,從人口、地理、语言、宗教、消费行为等角度入手。这不仅要求美术馆要呈现出一个包容的形象,而且也要在作出大量调研的基础上积极促进美术馆的多样性。
我们必须认识到,多样性文化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它是动态的、有机的、不断地建构和消解着的。这也就要求美术馆不断地调研、分析,在重新解读文化定义的基础上对机构进行调整,多使用机动性较强的临时项目的手段,去实验、去探索。在新的语境下,作为公共空间的美术馆有责任、也有义务去“滋养”多样性资源;在“知识”已经调整的情况下,去积极转变自己的空间形态,建立起有效的与多样性文化持续互动的方法。这是转变文化认同形成基础的最佳方法,从而有利于给多样性文化建立一种持续有效的动态发展机制。
注释:
[1] Crimp, Douglas. The Postmodern Museum. na. 1987.
[2]福柯在其《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中,使用了“排他性”这一概念。在该文中,福柯指出:博物馆与图书馆是“无限积累时间的差异地点(Heterotopias)”。更多论述请参考 [法]米歇尔·福柯著,严峰译《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P18-28。
[3]《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法]米歇尔·福柯著《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包亚明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P11。
[4]《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美]珍妮特·马斯特编著,钱春霞、陈颖隽、化建辉、 苗杨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5]《公民身份——世界史, 政治学与教育学中的公民理想》,德里克·希特,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