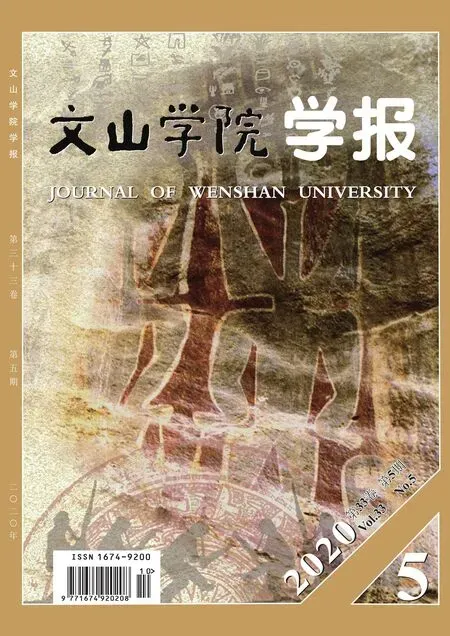“听”“聆”的同源关系及历史演变
刘越昕,武 璠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聪”“听”“闻”“聆”等动词均是上古及中古听觉动词语义场成员。学界对“听”“闻”“聆”三者作为常用听觉动词的历史演变及交替关系研究众多,如张楠,白云(2009)分析表“用耳朵接受声音”的词语“听”“闻”“聆”发展脉络及其现代方言分布[1];曾石飞(2011)将中古听觉语义场“听”“闻”“聆”作简要分析,认为三者在具体时期有不同用法。听觉动词语义场研究不胜枚举,但从语音和字形两方面分析“听”“聆”二词词源关系文章甚少[2]。王力在《同源字典》中明确“听(thyeng)”“聆(lyeng)”二者同源,认为透母与来母为旁纽关系且二字叠韵[3]。黄易青认为,“声音形象与视觉形象在感觉上可以相通:‘聆是耳通。圣、听均从耳,也是耳通……’”[4]王力先生在构拟上古语音系统时未将i元音认定为主元音及同源词判断标准①,黄易青用视觉与听觉相近特点解释二字相通的说法也稍有欠缺,所以亟需理清二者形体意义与语音关系来验证二者的同源关系。
文章从字形和语音角度验证“听”“聆”同源关系、两者作为听觉常用动词的演变过程、两者在使用过程中的差异原因分析展开探究。
一、“听”“聆”二字同源关系考证
蒋绍愚在同源词判断依据上说:“判断同源词必须严格按照三个条件来判断:1.读音相同或相近;2.意义相同或相近;3.有同一来源。”②金理新《上古汉语形态研究》中明确指出:“同源词,顾名思义就是指共同来源的语词……我们应该研究的是同源词构成的语音规则。”[5]根据蒋先生和金先生的判断,同源词需有共同来源,即形体反映的词义要相同或相近或相通、上古拟音的声母与韵母要相同或相近。从汉字形体意义及语音联系来分析“听”“聆”的同源关系就异常必要。
(一)形体意义分析
所现最早文献中“声”“听”“圣”三字最早字形如下:
声:

(《甲骨文合集》后1.7.10
金石之又(有)声也。

合27632无名组)
(上博性情论3号简)
听:

(喜)司败李听受期。

(《甲骨文合集》3682)
(包山文书20号简)
圣:

(乙5161(甲))

大音祗(希)圣(声)
(郭店老子丙5号简)

圣(听)之不足(聞)
(郭店老子乙12号简)
从所现先秦文献可发现三字存在,值得注意的是:1.三者字形相近,都由构字部件“耳”与“口”(突出人形中头的部分,像人跪坐着听对面人说话之形)组成,都有“出于口入于耳”义;2.三者意义相通,在使用中可互换,如“圣”字后两例分别与“声”“听”相通。这种用法在楚简中不胜枚举,如:
(1)其圣(声)变则(其心变),其心变则其圣(声)亦然。(性自命出32, 33)
(2)誉毁在旁,圣(听)之弋母之白。(穷达以时14)③
小篆字体将文字象形意味削弱、符号性加强。许慎《说文解字》作为当时第一部考究文字字形、分析文字语源的字典,记载“听”“声”“圣”三者字形及意义关系:

《说文·耳部》云:“声,音也。从耳,殸声。殸,籀文磐。”徐锴《说文系传》:“八音之中,唯石之声为精诣,入于耳也深……故于文耳殸为声。”《说文·耳部》云:“听,聆也。从耳、惪,壬声。”段玉裁注:“耳惪者,耳有所得也。”《说文·耳部》云:“圣,通也。从耳,呈声。”[6]小篆虽相较古字结构更加复杂,但其中“耳”与“人跪坐”部分依旧是三者核心成分。三者皆从耳,可见意义相近。
历史所现较早文献资料“令”“命”字形如下:
令:

(《甲骨文合集》32870历组)

(小臣宅簋西周早期集成420)

令壴圍命之於王大子而以阩
(包山文书2号简)
命:

(《甲骨文合集》14127正)

(命簋西周早期集成4112)

安命而弗宎(夭)
(郭店唐虞之道11号简)

或命(令)之或唬(乎)豆(属)
(郭店老子甲2号简)
所现先秦文献可见,字形上看,甲骨文中两者同形④,像人跪跽听候发令。即使金文“命”加义符“口”与“令”产生区别,但两者都有“令”主要结构,字形相差较小;词义上看,两者意义相近亦可相通,如“命”字最后一例中两字可相通表“发号施令”义。
汉代前的文献资料并未发现“聆”的存在,但“聆”来源于“令”。“令”“聆”是古今字关系,后者继承前者“听从命令”义分化新字。早期文献中已有“令”有“听”义的用法如:
(3)故国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商君书·算地》⑤
(4)古之圣王,审顺其天而以行欲,则民无不令矣,功无不立矣。(《吕氏春秋·为欲》)⑥
可知,“听”与“聆”创立之初字形都有部件“耳”“口”,都有“(人跪坐着)用耳朵接受声音”义,为其同源提供字形及意义条件。两者形体意义关系如下:

(二)语音关系分析
据金理新构拟上古语音系统可知,“听”上古与中古时语音形式分别为*s-liŋ、*theŋ,汉代出现的“聆”中古时语音形式为*liŋ。由此可知:
从声母看,中古边音-l-来源于上古边音-l-或颤音-r-。上古用作动词的“令”语音形式为*riŋ,其引申义后造字“聆”继承“令”特点中古语音为*liŋ。而“听”上古时语音形式为*s-liŋ,加词头s-表动作行为持续性,与不加词头的变体“聆”意义并无多大差别。中古“听”语音形式为*theŋ,辅音th-是上古s-词头附加在流音l-/r-词根前演变的中古时期的形式。⑦而边音l-可与辅音th-谐声,所以中古“听”与“聆”为谐声关系。⑧从韵母看,上古到中古鼻音一般会保留下来。由于“听”字上古语音有鼻音韵尾ŋ,过渡到中古依旧为鼻音韵尾ŋ,而“聆”字中古时也是鼻音韵尾ŋ,两者同属耕部。
古代专书中也有语言学家对“听”“聆”二者同源描述:
听,《说文·耳部》:“听,聆也。从耳、惪,壬声。”《广雅·释诂》:“听,聆也。”⑤《广韵》:“听,他丁切,又他定切,耕部。”
聆,《说文·耳部》:“聆,听也。从耳,令声。”《广雅·释诂》:“聆,听也。”《广韵》:“聆,郎丁切,耕部。”
综上,“听”与“聆”上古就形成声母谐声、韵母同部的关系,辞书采用互训为二者释义,更加验证二者之间语音与意义的同源关系。二者语音关系如下:

二、“听”“聆”的历史演变
汪维辉认为“常用词是词汇系统的核心部分,起着保证语言的连续性和为创造新词提供基础的重要作用……将常用词的产生时间及更替过程调查清楚对于考订疑伪古籍的相对年代无疑会有大的帮助。”[7]作为表听觉感官动作的动词,“听”“聆”被人们作常用词使用。但由于产生时代不同,两者使用频率、使用场合、组合条件等均有差异。章节将从义项分布与组合能力两部分讨论“听”“聆”两词共时分布与历史演变。
(一)上古时期(西汉之前)
在先秦文献资料中并未发现“聆”的存在⑨,当时“听”已是表听觉感官的核心词汇。
“听”在上古时期义项分布为:
1.用耳朵接受声音、听到
(5)明者听而视之,乃小人也。(周 庚桑楚《洞灵真经》卷三)
2.听从、听取、接受
(6)公不听,兴师伐鲁,造于长勺。鲁庄公兴师逆之,大败之。(战国 管仲《管子》卷六)
3.治理、考察、审理
(7)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战国 孟轲《孟子》卷八)
4.允许
(8)静郭君辞,不得已而受,十日谢病,疆辞,三日而听。(秦 吕不韦《吕氏春秋》卷八)
“听”在上古时期组合情况主要分以下几种:
1.听+n.
据文献记载,“听”可与名词性词语组合表“以耳受声”“听从”“考察、治理”的对象,主要有“听事”“听讼”“听命”“听政”“听狱”“听朝”等,例如:
(9)言听事行,则如师徒之势(战国 韩非《韩非子》卷十七)
(10)夫明达之才,将欲听讼,或诱之以诈。(周 庚桑楚《亢仓子》)
(11)我代韩而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战国策》卷八)
(12)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战国 荀况《荀子》卷五)
(13)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战国 墨翟《墨子》卷九)
(14)……良玉之絇,其长尺,冰月服之以听朝。(春秋战国 晏婴《晏子春秋》谏下第二)
2.听+v/v+听
“听”与意义相近相关动词连用形成“闻听”“听治”“听断”等同义连文结构或表“听”后所做动作;也可和“兼”构成“弗听”结构表示“听”状态、性质。
(15)闻听而明誉之,定其当而当,然后士其刑赏而还与之。(战国 荀况《荀子》卷九)
(16)……四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战国 韩非《韩非子》卷三)
(17)政令法,举措时,听断公。(战国 荀况《荀子》卷二)
(18)明主者兼听独断。(战国 管仲《管子》卷二十一)
3.a.+听
上古时期已现“不听”“弗听”等表施事者不愿完成动作,例如:
(19)韩君弗听,公仲怒而归,十日不朝。(战国 韩非《韩非子》卷三)
(20)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战国 孟轲《孟子》卷十)
(二)中古时期(汉代至魏晋南北朝)
汉代动词“聆”作为独立汉字并继承“令”的“听从”义,“听”仍是听觉感官动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动词。
“听”除了继承上古时期几个义项外,还出现“听凭”“允许”等义项。
(21)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汉 班固《汉书》卷五)
(22)昭王大怒,欲听其自杀也。(汉 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八)
中古时期“听”组合能力较强,沿用上古时期三种用法同时,还产生“听许”“听采”“反听”“过听”“洞听”等用法,前三种属“听+ v./v.+听”表“听”后所做动作结果或与“听”相关的动作,后两者属“a.+听”形容“听”的性质或状态。
(23)皆止于公,公欲自损以成国化,宜可听许。(汉 班固《汉书》卷九十九)
(24)今正欲听采风谣,虚实难悉。(南北朝 魏收《魏书》卷二十一)
(25)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汉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
(26)朕过听贺良等言,冀为海内获福,卒亡嘉应。(汉 班固《汉书》卷十一)
(27)无达视洞听之聪明,皆案兆察迹,推原事类。(汉 王充《论衡》卷二十六)
“聆”最早现于汉代,且在中古用例不多,仅“仔细聆听、认真听”一个义项。
(28)镜纯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声。(漢 揚雄《揚子雲集》卷四)
(29)观跃鱼于南沼,聆鸣鹤于北林。(三国 曹植《曹子建集》卷一)
“聆”产生初期组合能力较弱,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v.+聆/聆+v.(尤“聆听”“听聆”)
“聆”产生时与“听”义相近,二者常连文表“听、仔细地听”义。除此还有“悟聆”表“仔细地听、体悟”义、“耳聆”表“用耳朵仔细听”义、“聆玩”表“聆听玩味”义。
(30)聆听前世,清视在下,鉴莫近于斯矣。(汉 扬雄《扬子法言》卷九)
(31)执粹精之道,镜照四海,听聆风俗,博览广包……(汉 扬雄《扬子云集》卷四)
(32)耳聆雅颂之声,目覩威仪之序……(南北朝 沈约《宋书》卷十九)
(33)商舟淹留,聆玩不已。(南北朝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
2.a.+聆
中古时“聆”与“听”都可前加形容词表动作状态、性质,与“听”类似,“聆”也有“不聆”“过聆”“详聆”等组合。
(34)魂神迁移,精爽翱翔。號之不應,听之不聆。(三國 曹植《曹子建集》卷九)
(35)何为过聆晋语,简在心事乎!(汉 应劭《风俗通义》愆礼第三)
(36)诺,子详聆吾言,而深思念之。(漢 佚名《太平經》卷四十三)
3.聆+n.
“聆”最初由“令”的“听从命令”义演变而来,所以“聆”对象都非普通事物或声音,是需要仔细、认真听的声音,如:
(37)瞻仪情感,聆音心悲。(晋 陆云《陆士龙集》卷三)
(38)故聆曲引者,观法于节奏,察变于句投,以知礼制之不可逾越焉。(南北朝 蕭統《文選》卷十八)
(三)近代汉语(隋唐至明清时期)
近代时“听”“聆”代替并排除“察”“聪”等有“听”义但不常用的动词成为听觉感官动词语义场的常用动词。在较长的发展中,两者有了较大的差别:首先,使用环境与义项数量上,“听”逐渐用于口语中并拥有较多的义项,“聆”较多用于高雅书面语中且未增多义项,两者意义差别决定各自服务不同宾语。其次,组合能力上两者也有较大差异:“听”既可作为词单用,又可作词根,但“聆”逐渐降格为语素,逐渐不再单用,而与“听”等词根结合成动词。同时,使用频率上,“听”远超“聆”居听觉感官动词语义场首位。
“听”在近代义项除继承上古及中古义项外,还出现“等候”等义项。
1.v.+听/听+v.
这一时期产生“听凭”“听允”“听任”等组合,例如:
(39)只得听凭分析,同孩儿谢了众亲长……(明 抱瓮老人《今古奇观》卷三)
(40)时政得失, 预以谋谟, 动辄匡谏, 事多听允。(唐 李延寿《北史》卷三十六)
(41)买卖听任冨吏,价数不可知。(宋 刘攽《汉官仪》卷下)
2.听+n.
随使用频率不断增多,“听”与受事对象的组合能力不断增强,出现“听歌”“听教”“听话”等结构:
(42)昔申喜听歌,怆然知是其母,理实精妙然也。(唐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二)
(43)近日有心来听教,奈何方面事怱忽。(宋 赵汝腾《庸斋集》卷二)
(44)有学者终日听话……(宋 陆九渊《象山集》卷三十四)
3.a.+听
(45)倐然气肃烈,一夕俱沉冥。试语尘中士,细听秋虫声。(宋 陈思《两宋名贤小集》卷二百九十四《杂兴》)
“聆”在近代中得到发展,虽只有“听(尤指仔细地听)”义项,但组合方式更多样化。
1.聆+v.(仅“聆受”)
2.聆+n.(仅“聆教”)
(47)倘荷不弃,京寓甚近,学生当得供奉,得以朝夕聆教。(清 曹雪芹《红楼梦》第一百四回)
通过对上古至近代“听”“聆”的义项分布及组合能力的分析可知,“听”较“聆”早出现并表“以耳受声”等与“听”相关的动作意义。在历史发展中,虽两者都保留“以耳受声”义项,但侧重点不同:首先,“听”用法更广泛,“聆”更多表“仔细认真地听”,多用于高雅书面语中。其次,“听”义项数量及组合能力优于“聆”,在口语与书面语中更多被使用。同时,“听”一直可用作独立词做句子谓语或作词根,但“聆”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降格为不成词语素,须与其他成词语素组合才能构成新词。
三、“听”“聆”使用差异分析
(一)理性意义与词义色彩的差异
“听”“聆”在理性意义及词义色彩上都有细微差别,前者主要指词义反映动作方向不同。
1.词义反映动作方向不同
《经典释文》对“听”注音反映出陆德明对“听”动作方向的理解分为“(上对下说)下听上”的平声“吐定反”与“(下对上说)上听下”的去声“吐丁反”两种,如:
(48)又怨襄王之与卫、滑也,故不听王命而执二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经典释文》卷十六:“听,吐定反。”
(49)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诗·郑·将仲子》)《经典释文》卷五:“听,吐丁反。”
从《经典释文》注音可知当时对“听”注音已有二分,读若“吐定反”的方向为“下听上”,而读若“吐丁反”的方向为“上听下”。其他注疏作品中也可找到相关解释:
(50)释(56)例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僖中第六:“聴音吐定切。”
(51)释(58)例宋李樗《毛诗集解》卷九:“听,吐丁反。”
对“聆”注音只找到“郎丁反”一种。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唐顔师古《匡谬正俗》、元戴侗《六书故》等专书中都释“聆”为“郎丁反”(或“力丁反”“历丁反”等)。且“聆”表“认真、仔细地听”,在动作方向上为“下听上”。
综上,两者在动作方向上有细微差别,“听”有“上听下”与“下听上”两种,而“聆”只有“下听上”。
2.词义色彩不同
“聆”产生于“令”的“听从命令”义可知,“聆”一般指“听取高雅、严肃的声音”义,而“听”在产生时可与各种声音搭配。二者词语组合情况也反映出词义色彩的不同,“听”可与“声、音、命、事、郑、令、刑、教、朝、话、曲、戏”等词搭配,而“聆”仅可和“音、曲、教”等搭配。这也反应前者情感色彩丰富,可用于口语或书面语中,后者情感色彩更严肃,多用于书面语中。
(二)语法功能的差异
语法功能不同决定二者搭配能力不同,上文“听”“聆”二词在上古至近代中义项分布与组合能力反映出二者都可与相关意义动词搭配构成新动词,如“听察”“听许”“听取”“聆听”“聆玩”等;二者都可后加名词构成新动词,如“听曲”“听话”“聆教”“聆音”“聆曲”等;二者都可前加形容词构成新动词,如“细听”“过听”“细聆”“详聆”等。但二者在语法功能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是否独立成词、其后宾语性质及能否省略两方面。
1.是否可以独立成词
“听”不仅可与其他语素构成新动词,还可单作动词表示“以耳受声”义。“聆”随时间推移逐渐不能独立成词,必须与其他语素结合做句子谓语,如:
(52)谏曰:“江南,国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将何以卫社稷乎?”不听。(清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
(53)宝玉听毕,忙转身回明贾母。(清 曹雪芹《红楼梦》第十六回)
(54)宝玉接过来,一面目视其文,耳聆其歌曰……(清 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回)
2.所带宾语性质及能否省略
所现文献可见两者都可后加双宾语,如“听/ 聆+人+事/言”组合:
(55)季兴乃握震手曰:“不听君言,几葬虎口。”(宋 周羽翀《三楚新録》卷三)
(56)今聆君言娓娓,使我终日倦。(清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百三十七)
但两者不同的是,“听”后宾语可不出现,“聆”后宾语基本不可不现。这由于“听”可独立作单音动词造成。比如在表示“不愿听取”这一义项时,“听”后往往可省其后宾语,但根据上下文语境可补出,而“聆”却较少省略,如:
(57)虞公弗听,遂假之道。(战国 韩非《韩非子》卷三)
(58)二府不听,公乃上疏论其事。(宋 毕仲游《西台集》卷十三)
(59)雷霆骇地,聋夫弗聆其响者,盖机感之绝也。(唐 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三)
(60)然当世之士未尝不聆言,而心尝睹形,而目成也。(明 高叔嗣《苏门集》卷五)
四、结语
文章从“听”“聆”二字来源出发,先分析二者字形、语音、意义上的同源关系,又从义项分布和组合能力角度梳理二者从上古至近代使用情况的共时分布与历时演变,最后简要分析两者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差异的原因,希望能为汉字同源关系的验证及同源词使用的历史演变提供分析与补正。
注释:
① 文章采用金理新构拟的上古汉语语音系统,认为前高元音i在中古汉语中占据主元音地位。
② 引自蒋绍愚(2005)《古汉语词汇纲要》一书,书中还提到:“读音相同而意义相差甚远,就只是同音词。意义相同或相近,而读音相差深远,就只是同义词。读音相同或相近,意义相同或相近,那也只是音义的偶然相 同,而不是同源词。”
③ 两例引自晏昌贵(2000)《郭店儒家简中的“圣”与“圣人”的观念》一文,文章列举多处“听”“声”“圣”相通用例。
④ 林义光《文源》云:“按:诸彝器令、命通用,盖本同字。”
⑤ 王念孙《广雅疏证·释诂》云:“聆,从也。注:‘古通作令’。”详见《广雅疏证》第8页。
⑥ 王念孙《广雅疏证·补证》云:“聆,古通作令……令谓听从也。”详见《广雅疏证》第416页。
⑦ 引自金理新(2013)《上古音略》270页第七章“边音、颤音和半元音”第四节(上古汉语*sl-复辅音中古演变为透母th-是演变的其中一个分支,实际要复杂得多)。
⑧ 清代段玉裁有根据谐声系统的特点总结出“同谐声者必同部”原则,认为声母谐声的字必属同一韵部,这一观点在“听”“聆”二字的同源关系上得到了极好的验证,二字透母来母谐声,二字同属耕部。
⑨ 在秦代文献《吕氏春秋》中有“聆”的古字“令”表示“听从”义的用法,读若“郎丁切”,前文讲述“令”“聆”关系时已举例,又如《吕氏春秋·为欲》:“故古之圣王,审顺其天而以行欲,则民无不令也。”许维遹集释:“令谓听从也。令、聆古今字。“但此处我们不讲此种用法作“聆”在先秦的用法,只以其独立出现在文献中的最早用例作为其产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