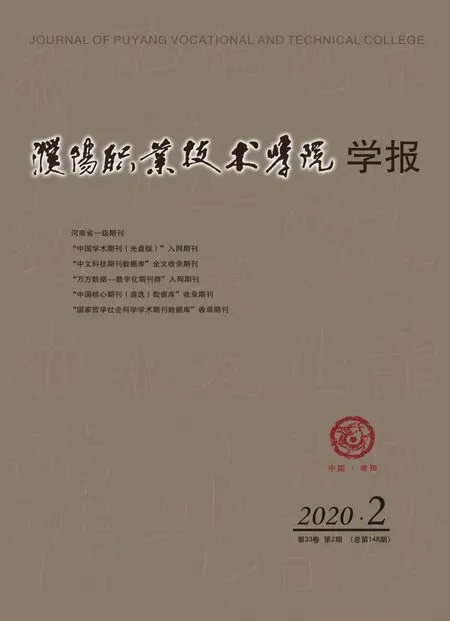论李贽“童心说”
隋晓聪
(新疆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一、“童心说”产生的思想渊源
(一)阳明心学的影响
李贽“童心说”的产生与阳明心学有密切联系。程朱理学提出“天理”是万事万物的起源,万物皆有一“理”,可以通过“格物”,认识真理。王阳明在早期是推崇和效仿朱熹的,朱熹提倡的“格物致知”的求理方法,他曾经借“亭前格竹”的方式亲自实践过,但是却无法悟得其中的道理,反而忧劳成疾,这使得王阳明对朱熹求理的方式产生了怀疑,自己便另辟道路去思索求理的方式。他认为天下事物无穷无尽,通过“格物”来求得真理是不现实的,应将精力放在人自身,他认为理学家所说的“天理”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中的,而非存在于外在的客观世界中,“格”之对象在“心”,而非外物,于是王阳明提出了自己的理学观点“致良知”,“良知”指的是个人的道德意识,强调通过完善个人的道德修持,提升自身的道德境界,回归本然之心以求得真理。王阳明的“致良知”的理学观点要求人们由心外求理转向心内求理,强调“心”的重要作用,重视人的内心世界,带有朦胧的个体意识和自主精神,这对李贽“童心说”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李贽“童心说”是其反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武器,他提出重视人欲、维护人欲,主张顺应人的自然本性,重视独立人格,使其“童心说”具有了鲜明的叛逆性和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想色彩。这不仅是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也发展革新了阳明心学。
王阳明对外界见闻与主体“良知”之间关系的论述,也对李贽“童心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在《传习录》中云:“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 ”[1](104)他认为“良知”是个体内心所有,并不是由外界见闻生发出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外界见闻的触发和影响,李贽受其影响,将一般人失去童心的原因归结为“闻见道理”,他在《童心说》中说:“盖其方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2](276)李贽所说的“闻见道理”指的是道学家所推崇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是“假道学”。他亦在《童心说》中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2](276)其认为“童心”就是初生儿童的“赤子之心”,是至纯至真,不受世俗观念影响的,而“闻见道理”即是破坏“童心”的社会世俗观念,因此,他将“闻见道理”视作“童心”得以保持的障碍。由此可见,李贽的“童心说”的理论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受王阳明观点的影响。
(二)禅学、道学思想的影响
李贽“童心说”深受禅学思想的影响,他在《童心说》中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2](276)他提到的“本心”一词是禅宗术语,禅宗的佛性论以“心”为本体,人想要获得解脱,就必须保持“本心”的澄澈清净,摒除尘世的影响,这样才能明心见性,成圣成佛。李贽将“童心”界定为“本心”“真心”,从术语表达上就可看出他对禅宗佛理的借鉴。高僧慧能认为,任何人都有佛性,佛性的保持在于人之“本心”的清净无染,要始终保持着“净”“空”的状态,但因为世人常常会受世俗的纷扰、诱惑,以致失却本心,迷失本性,无法明心见性、成圣成佛。因此,世俗的纷扰成为保持“本心”澄明清净的障碍,佛家认为只有抛却尘世烦扰,返回原初,方能恢复 “本心”,明心见性,成圣成佛。对于这种佛学心性思想,李贽在《答明因》一文中曾这样阐述过:“心性本来空也。本来空,又安得有心更有性可说乎?故二祖直至会得本来空,乃得心如墙壁去耳。既如墙壁,则种种说心说性诸缘,不求息而自息矣。诸缘既自息,则外缘自不入,内心自不喘,此真空实际之境界也,大涅槃之极乐也。”[3](18)李贽借鉴禅宗思想,将之运用在了其“童心说”中,他认为“童心”就应保持本源清净,“童心”缺失是因为受外界“闻见道理”的影响,逐渐将其遮蔽、掩盖掉了。由此可见,李贽对外界“闻见道理”的否定与禅宗“佛性本清净”的观点,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李贽在借鉴禅学思想的同时,也吸收了道家思想。老子的“无为”思想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倡导“无为而无不为”,其精神实质是“道法自然”,《老子·三章》是老子“无为”思想的最重要体现,他在此篇中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4](40)李贽肯定了老子“无为”的思想,他说:“今一不敢为于悖乱、争盗之事,则志弱而骨自强矣。所以然者,无欲故也。”[5](14)他认为这可以“常使民混混沌沌,无有知也,无有欲也,纵有聪明知识者出,而欲有作为而自不敢,则天下皆归于无为矣”[5](14)。由此,我们可以明识老子和李贽皆认为“争盗”的源头在于“欲”,“欲”的出现是因为“知”,故若“无知、无欲”则“无为”,“无为”则可“无不为”。《老子·十章》曰:“……专气至柔,能婴儿?涤除玄览,能无疵?爱民治国,能无为?”[4](58)老子将对“道”的理解与婴儿联系在一起,他的人生理想是涤除玄览,归于浑沌虚无的状态,回归到婴儿的状态,而婴儿状态才是始终保持本心,纯真质朴、无欲无知无为的最佳状态。李贽对此阐释道:“夫婴儿百无一知也,而其气自专百无一能也,而其气自柔。专气致柔能入婴儿,则可为抱一矣。”[5](22)婴儿之心不受世俗道理的影响,处于未经社会化的浑沌无知状态,由于“无知”而“无欲无为而无不为”。由此可见,李贽认为的“婴儿之心”与道家的“无为”思想在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李贽的“童心”旨在强调人的最初之心,本然浑沌状态,正是指婴儿无知无欲无为的赤子之心。
二、“童心说”的美学内涵
(一)真实美
禅学讲“本心”,只有保持“本心”才能澄明,进而达到真实的最高境界。道家崇尚自然,以“真”为美,倡导返朴归真,“真”在道家被视作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李贽深受禅宗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其“童心说”必然具有真实美的美学内涵,但李贽是一位充分肯定世俗生活的人,他所说的“真”并不像禅道那样排斥人的各种欲望,其强调的重点在于要求创作者保持真性情,抒发真感情。他说:“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2](276)他认为“童心”即是“真心”,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创作者应是始终保持“真心”的“真人”,要以“真”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标准,表达至真至纯的情感,这样才能创作出天下之至文。李贽认为“闻见道理”是障碍“童心”的原因,他说:“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 ”[2](276)由此可见,“童心”失,则全都是“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2](276)了。李贽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腐朽,文坛尽是假人言假言,文假文的局面。政治的黑暗、腐朽,注定整个社会是没有光明和希望的,缺乏作家真情实感的文学,是没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假文学”,李贽提出的“童心说”,贵真实,反虚假,以提倡抒发真情实感,反对假理为核心,在当时实属一股清流,不管是针对文学创作,亦或社会,都具有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
(二)自然美
李贽从体现“童心”的“至文”出发,要求文学应达到“化工”之美,即自然之美。他在《杂说》中说:“《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 ……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第二义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 ”[2](274)李贽在这段论述中所说的“画工”,指的是人工,而“化工”,指的是天工,他崇尚的是“化工”,即自然造化之工,认为“画工”有人为斧凿之迹,故落第二流。“化工”在李贽看来是无法可依,无迹可觅的,似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自然无为的玄妙美学观,但却不同于老子的这一美学观。李贽以“童心”为理论基础,以抒发自然情感为落脚点,将“化工”与自然情感的表达密切相联,其强调文学作品虽出自作家之手,但创作不应刻意雕琢,应不露斧凿之痕迹,保持羚羊挂角,“清水出芙蓉”的自然造化之本色。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点即文学创作必须表现人的自然本性,表达作者的自然情感,这样的文学作品才符合“化工”之美的美学标准。
李贽在《读律肤说》中说:“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于礼仪,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仪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非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2](364)在这段论述中,李贽批判了文学创作要遵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传统观念,他认为情性的抒发应自然,而自然抒发的情性,礼仪即在其中,不必再有另外的人为的礼仪加以牵合矫强,否则会阻碍自然情感的真实流露,失掉自然之美。
综上,李贽崇尚“化工”传神之美、自然之美,要求文学创作应自然天成,不着人为雕琢之痕迹,以“自然之美”为美学标准,这样创作出的文学作品才能表现人的真性情,才是体现作家“童心”的“至文”。
三、“童心说”对明清文坛的影响
李贽的“童心说”,以及他评点《水浒传》中的许多思想和观点,是对当时复古文坛的巨大颠覆和反拨,同时也对后世的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公安三袁的“性灵说”就是在李贽“童心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代焦竑、汤显祖、金圣叹、胭脂斋等人又分别在诗文、戏曲、小说等不同方面继承并发展了李贽的思想,使此后的文坛产生了新的文艺思潮。下文将选取三例加以论述。
李贽的“童心说”以“真”为核心,公安派受其影响。袁宏道以“性灵说”为中心,提出文学创作应表现“真”,他在《叙小修诗》中赞扬其弟小修的诗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6](212)他主张文学创作要抒写作家的性灵,强调作家内心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袁宏道的这种思想显然是对李贽“童心说”的继承。公安派批评复古模拟之风,强调“变”,他在《叙小修诗》中说:“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惟夫待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 ”[6](214)袁宏道指出时代是不断发展的,文学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所说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随时变是袁宏道强调“变”的内涵之一,而另一内涵是其从“变”的角度提出了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他认为文学创作应在继承的基础上有独出心裁的新创造,而继承是取传统之精华,并不是一味地复古模拟。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说:“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唯有推陈出新才能使文章保持鲜活生机,永久流传,才能推动文学向新的方向发展。公安派“变”的思想既是对李贽“童心说”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其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此外,袁宏道提倡文学作品应追求自然之趣,表现作家自身独特的个性,这也是在李贽“童心说”思想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公安派的思想学说深受李贽“童心说”思想的影响,两者都具有反理学、反传统的时代精神,都带有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启蒙主义色彩。
汤显祖在文学思想上也深受李贽的影响,他是“唯情论”的倡导者。抒发情感是文学的本质特征,《礼记·乐记》中有“情动于中,故发于声”,《毛诗序》中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文赋》中提出“诗缘情”,都是在强调情感是文学创作的动力,而文学创作的重点就在于情感的表达。汤显祖认为任何体裁的文学作品都重一个“情”字,只要是抒发作家至情至感的作品皆是天下之至文。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说道:“天下女子有情宁有杜丽娘者乎!……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7](9)由此可以看出,汤显祖将情感放在文学创作的首要位置,或者说将至情至感的抒发作为评判文学作品优劣的首要标准,认为只有倾注了“情之至也”的文学作品,才是上乘之作,“情之至也”即指人内心自然产生的至真至纯至诚的情感,与李贽“童心说”中强调要表达真性情有异曲同工之妙。故而,汤显祖推崇的“唯情论”直接受李贽“童心说”影响的同时,又将文学创作中的情感因素推到了一个至高点。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也受李贽“童心说”思想的影响。他在《水浒传序一》中提出文章“三境”说,他说:“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 ”[6](251)金圣叹的“三境”说的直接思想来源,是李贽《杂说》中“化工”“画工”说。他的“圣境”即李贽的“画工”,“化境”即李贽的“化工”,“神境”则介于“画工”与“化工”之间。显然金圣叹的“圣境”“神境”说是对李贽“画工”“化工”理论思想的直接继承,而他提到的“神境”则是在继承基础上的生发拓展。金圣叹与李贽一样推崇自然天成、不着人工痕迹的“化境”,将其视为文学创作应该达到的最高境界。由此可知,金圣叹的思想主张深受李贽思想的影响。
四、结语
李贽的“童心说”是其提出的具有创见性的理论学说,在晚明文坛上掀起了一阵“狂风”,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力,成为他反理学、反传统,倡导“真人”“真情”的重要思想理论武器,在当时具有强烈的反叛性,带有鲜明的个性自由、思想解放的启蒙主义色彩,其理论渊源是对禅学思想、道学思想的良好继承与发展,其美学内涵也体现出了李贽的真知灼见。“童心说”认识并触及到了文学的本质,无疑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着针砭时弊的作用,对后世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这一理论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刻性。笔者从思想渊源、美学内涵以及对明清文坛产生的影响三个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研究论述,其中仍有很多有待完善、挖掘的问题和方面,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