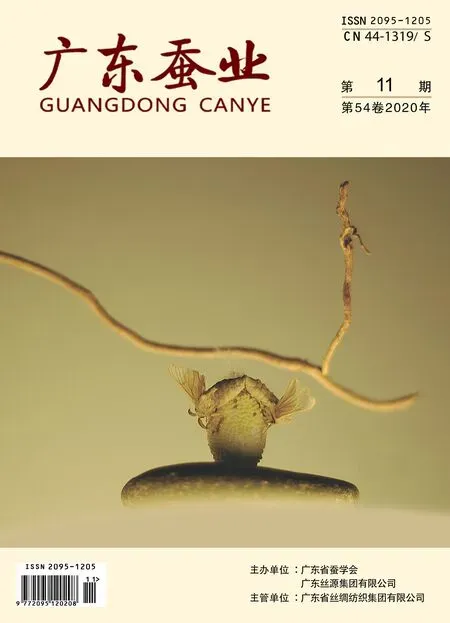粤港澳大湾区乡村发展研究
梁益铭
粤港澳大湾区乡村发展研究
梁益铭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000)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立足于国家竞争和社会需求的重要战略规划,对内地九市和港澳两地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大力提倡发挥城市集群作用下,粤港澳大湾区乡村地域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重视。文章基于城乡互动视角,侧重考察城市作用下乡村的自我发展,发掘粤港澳大湾区乡村发展新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乡村发展;城乡互动
1 现实背景
长期以来,市场经济下城市对乡村不断强化的地域剥削严重拖滞了乡村的崛起发展,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2017年我国正式提出国家级战略目标——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珠三角的9个城市聚合起来,充分利用优势互补和发挥协同效应,集中财税政策、基础建设和技术创新等支持,目标是建设国际一流的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给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粤港澳大湾区以不足全国1%的土地,不足全国5%的人口,创造出全国12 %以上的经济总量。[1]同时,大量已有和新建的跨海桥梁、铁路通道、码头机场等交通设施打造了全球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不同区域间的通行效率高,尤其是近几年以轻轨建设为特点,城乡交通网络不断完善,大大助力了乡村工业化和城际人口流动。在以广、深、港、澳等一线城市为核心的珠江口一百多公里的范围内,有20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内地九市就有36 500 家工业企业,并且东莞、中山等市的乡镇企业发展趋势迅猛,如中山市的小榄、古镇等乡镇,吸纳了大量本地和外地的劳动力就业。
推进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一直是粤港澳大湾区乡村发展的主要途径。2000—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乡村地区的非农产业产值的占比不断增加,平均增长了11.7%,区域内各城市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总体下降幅度大,总体下降了30%,显示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平衡度较高,城乡经济发展的关联度不断增加,城乡发展协调水平好[2](见表1)。

表1 2000 /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城乡经济与人民生活指标
注:资料来源于各城市2000年和2015年统计年鉴。由于国家统计局调整,200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统计数据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纯收入,2015年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 理论背景
2.1 城乡互动内涵
在“城乡互动”内涵的表述上,普林斯顿(1975)最早对城乡相互作用进行了定义和归类,认为其包括5个方面,即人的运动、商品的运动、资本的运动、社会交易、行政和服务的供应。[3]国内外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城乡互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过程,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难以十分准确地去定义。
2.2 城乡互动的相关研究
Unwin认为乡村区域内的农场私有化、农民增收渠道丰富、土地制度变革等要素合力促进了城乡互动的发展[4]。Gelan用城乡CGE模型指出,城乡之间的开放性贸易往来是推动城乡互动结构下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国内研究中,曲亮把城市和农村二者引入拥有巨大联系的生态群种,利用生态学所研究的共生学科介入城市与乡村关系影响要素研究中,然后通过分析它们之间的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外环境等,为研究城市与乡村互动的影响要素提供新的视角。罗雅丽、李同升(2005)强调政策制度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机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认为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影响城乡互动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5]
2.3 乡村区域发展的相关研究
国外为乡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要点。城市地理学家芒福德十分认同赖特的“广亩城市”理论,他分析指出,在权力中心分散化的城市建设上形成更大的区域统一体,可以把这种区域统一体带来的经济增长引向不同的社区,以区域整体发展促进城乡的平衡,消灭乡村与城市的发展差距。[6]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中指出,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带来各种要素自由流动,会使得劳动力、技术等重要发展资源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所以必须通过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去刺激和指导落后地区的发展,他从政府角度分析城乡交流,充分肯定了政府在城乡统筹中的重要作用。[7]
3 存在问题
3.1 乡村特征淡化,乡村价值流失
改革开放后长达四十多年的高速工业化下,粤港澳大湾区乡村依靠珠三角地区城市的发展辐射效应,迅速推进乡村工业化进程。由于大面积的土地资源、丰富的工业原料、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国内外投资的工厂进入乡村地域。受到市场配置作用的驱使,耕地的产出效益低于工厂生产的产出,大片农田被出租转让,成了非农建筑用地,被大面积的厂房和烟囱管道替代。
乡村特征的淡化不是其自我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城市资本冲击下发生的地域功能同化,农业的发展地域被城市工业扩张挤占,乡村劳动力性质变化,因农业生产而呈现的景观逐渐消失,其特有的地域价值也慢慢流失。
3.2 土地管理混乱,土地资源紧缺
根据 2018年广东省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数据统计得出:粤港澳大湾区全区土地总面积约为55 903.5万亩。除香港澳门外,其中耕地903.8万亩,园地583.28 万亩,林地 3 979.54 万亩,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 046.49 万亩,村庄用地496.69 万亩,城镇及采矿用地840.05 万亩,交通运输用地 208.92 万亩。相比于2014年时的923.9万亩的耕地面积,606 万亩的园地,4 010.7万亩的林地面积,1 056.9万亩的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449.3万亩的村庄用地,664.8万亩的城镇及采矿用地,154.95 万亩的交通运输用地,[8]主要涉及乡村产业发展的耕地、园地、林地和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的面积都呈现出下降的态势,而城镇化和工业化类型的用地都明显上升,考察城市化重要的指标——交通运输用地面积也上升了接近一倍,表明当前乡村地域发展所需要的土地绝大部分被用于发展城镇建设的房地产业和轻、重工业等,土地资源的减少进一步限制了乡村的发展选择和持续发展水平。同时,土地功能布局也存在缺陷。粤港澳大湾区内有大量乡村发展起来的小城镇,村镇管理的不足、不科学的土地规划和土地改造的低限制等,导致了盲目地兴建住宅和建设工农业生产,造成了许多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和破坏。
3.3 环境污染严重,忽视环保建设
2013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提出,“珠三角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相关信息显示,在珠三角土壤中,三级和劣三级土壤占到总面积的 22.8%,28%重金属超标(第一财经日报,2013),主要超标元素为镉、汞等,广州、佛山及周边经济较发达地区较为严重。[9]大湾区建设之前的发展时期,乡村地区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和城镇化,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进行“粗放式”工业化和农业生产,忽视自然保护的重要性,导致了河流、土地和空气的深度污染,尤其是乡村的耕地破坏最为严重。长期以来,政府为了取得税收和GDP的增长,对这种生态消耗型的乡村发展模式没有进行有力的行政规范,环境管理的缺位纵容了农民的自主开发。粤港澳大湾区乡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尤为突出,较高的土地市场价值导致了乡村的公地私用和垃圾处理空间有限的问题。乡村垃圾的传统处理方式主要是掩埋,甚至有些地区还存在着焚烧垃圾的恶习,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了土地的开发利用,还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
4 对策建议
4.1 再现乡村主体价值,发展有乡村特色的产业
乡村不是城市发展的经济负担,更不是所谓时代进步的历史遗留。其包含着生态、文化、历史等多方位的乡村主体价值,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应被重新呈现出来。乡村景观相对于城市景观有着独特的休闲旅游价值,乡土文化在工业文明中具有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或缺性,乡村田园生活对于快节奏的城市日常生活来说也有着无法比拟的吸引力。粤港澳大湾区乡村本身也有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是接近高人口密度的湾区城市群,具备深度开发的市场潜力和收益转化的可能性。首先,政府应该摈弃注重工业化的乡村经济增长的理念,树立城乡优势互补的乡村开发思想。以城市化为发展标准的思维只能单纯地把乡村变成城市,并不能够长远满足人民生活发展的需要,找到乡村地域的特色更能够实现城乡互动的价值。其次,支持湾区农业的持续发展。乡村产业根植于农业的发展,而农业也是城市生活的重要食品来源;保护基于自然土地开发运作造就的淳朴民风、绿色食品等乡村主体特色。再次,积极拓展乡村产业模式。乡村旅游、有机农业、养生保健等多种产业都可以利用好乡村特有的自然生态优势,拓宽经济收入渠道,增强“自我造血”的能力,为农民增收,让乡村发展不再依赖于环境资源的过度消耗。
4.2 推进田园城市建设,推进城乡环境一体化
推进城乡环境效益共享,推进城乡环境治理体系一体化,着力打造“城乡互融,城乡互通”的田园城市,是粤港澳大湾区城乡互动的重要方式。由于二元化的城乡结构,早期内地九市和港澳地区的城市及乡村环境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区域状态,普遍认为城市与乡村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分属不同的管理系统,加上珠江口地区工业化,城市发展早期污染严重,各方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整治高污染高排放的环境问题,城市得益于统一治理机制和市民较高的环保意识实现了环保状态的革新。但随着工厂迁移和乡村的工业化起步,之前普遍较为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遭到了重大破坏,乡村环境问题恶化将不断反作用于城市。因此,首先政府应该单独设立城乡环境管理部门,整合城乡环境治理的资源力量,统筹城乡环保发展规划,加强环境治理的专业素质培养,保证环境管理队伍的执行能力。其次建设好统一的公共环保基础设施,结合城乡环境管理机制,延伸城市的公共环境治理技术和设施至乡村地域,设立城乡间自然生态片区隔离带,完善城乡共有垃圾处理系统,联结地区的污水排放管道,建设区域环境质量监测站等,为未来更好地进行有规模效应的城乡环保治理、城乡环保体系建设打好物质基础。再次培育城乡居民的环保意识。加强环保教育是发展环保事业的根基,要让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具备“生态环境共享、环保人人有责”的城乡环保理念,否认“环境保护单边主义”,认识到城乡环境共生共存的现实状况。
4.3 完善城乡土地资源管理制度
提高城乡土地应用监管水平,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建设土地收益共享机制,是完善城乡土地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举措。粤港澳大湾区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使得当地土地价格处于较高水平,其土地收益率一直位于全国前列,但城市扩张导致了严重的乡村耕地占用问题。首先,应当看到大部分乡村居民对土地收益的依赖性,要在乡村普遍实行的集体土地股份制上健全收益共享机制。对于乡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出租条款,可以增设对未来该土地建设收益的比例享有权利;对于乡村个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可以融入土地入股的机制,让村民参与到地区发展的红利分配中。其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城乡土地流转中的作用。政府应当严格划定土地资源的流转范围,严禁乡村集体土地的随意转让开发;实现土地拍卖、招标、出让等土地流转工作的透明化、公开化,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动态的土地市场价格公示机制,同时建立起专注于土地市场买卖主体的电子征信中心,建设独立的土地状况实时监管机制。再次,要强化土地应用的审批和监管,提高城乡土地资源的配置应用水平。城市的发展必然带来土地需求和地域扩张,但对乡村土地的吞并不是必然的前进方向。城市土地可以通过向内地更新扩张满足升级发展的需求,拆除危楼老房、清理废旧工厂、重建公园绿化等措施都是城市持续发展的体现。而留有丰富自然资源和生态景观的乡村土地,应该明确“去城市化”的目标,令乡村土地的原有价值回归,恢复乡村土地的使用性质,划定土地应用范围,同时要严防土地建设申请挂羊头卖狗肉,建立土地监管巡视小组,落实检查工作,对城乡土地管理工作及时查漏补缺。
5 结语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的国家发展战略,在珠三角原有的深厚经济文化政治基础上不断寻求着新的发展突破口。过去很多的城乡发展规划主要集中于城乡间的单向联系,没能注意到城乡双向联动的效益,导致很多城乡问题恶化,比如乡村环境被破坏、土地矛盾突出、城镇化质量低下等,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转型发展的阻碍。城乡协调不仅是地区经济上的单纯联动互补,更重要的是,还有利于从根本上消解长期户籍制造成的区域发展收益分配不平等现象。积极推动城乡两大区域的协调发展,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两大群体走向更高水平的平等互融,是根除农民工的自我卑微感和城市身份的所谓优越性的必要方法,是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这对持续的社会和谐和国家稳定有着深远影响。
[1]张国尧.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20(10):121-125.
[2]周春山,邓鸿鹄,史晨怡.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特征及机制[J].规划师,2018,34(4):5-12.
[3]PrestonD. Rural-urbanandinter-settlementinteraction:theoryandanalyticalstructure[J]. Area,1975(7):171-174.
[4]TimUnwin. AgriculturalRestructuringandIntegratedRuralDevelopmentinEstonia[J]. JournalofRuralStudies,1997,13(1):93-112.
[5]曲亮,郝云宏.基于共生理论的城乡统筹机理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4(5):371-374.
[6]崔西伟.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以成都市为例[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7.
[7]鄢洪斌,袁媛.城乡经济联系与互动理论及其启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25(7):179-183.
[8]广东省土地利用现状汇总表(2016年)[Z/OL].(2018-09-30).http://nr.gd.gov.cn/gkmlpt/content/0/607/post_607796.html#684.
[9]胡小飞.珠江三角洲土地整治效益综合评价[D].广州:华南农业大学,2016.
梁益铭(1999- ),男,汉族,广东广州人,本科,研究方向:经济学。
10.3969/j.issn.2095-1205.2020.11.64
F127
A
2095-1205(2020)11-13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