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理论视域下张爱玲自译散文研究
——以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自译本为例
李 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和散文大家。人生的孤独凄凉和人类情感的残缺是其文学作品常见的主题基调。短篇小说《倾城之恋》、长篇小说《十八春》,以及散文集《流言》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张爱玲还是一位译界名人,她的自译作品受到广大中外文学爱好者的喜爱,她在将自己的英文作品翻译成中文时,充分考虑到读者对象的变化,对译文作出恰当的处理,使之符合目标读者的期待,这与接受理论学派的观点与做法不谋而合。本文以接受理论为研究视角,将着墨重点放在张爱玲撰写的英语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及其自译本《更衣记》文本研读上,旨在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中英散文译者广泛而深入的思考。
一 自译与接受理论
“自译是作者翻译自己作品的行为或者是这种行为的结果”[1]。译者通常为双语或多语作家,并精通两国甚至多国语言,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自译者将原语作品翻译为目标语时,会因读者需求的不同而对译作作出相应调整。
接受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接受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德国的姚斯和伊瑟尔,他们强调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研究各类文学艺术。“文学创作中的‘接受理论’是以读者的解读活动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理论。接受理论学派认为作为解读对象的文本,不是由作者独创的,而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2]。接受理论学派提出应改变文学理论中的“作者中心论”,确立“读者中心论”。他们认为,文本会因读者阅读体验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意义。作为接受理论学派的代表,姚斯通过分析读者对文本的接受程度,探究读者对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启示以及文本意义生成的作用,而伊瑟尔主要是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研究读者对文本的反应。接受理论学派宣扬: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并不处于被动地位,而是根据已有的期待视野,积极主动地运用自己的认知去接受并理解文本意义。接受理论学派认为,“在文学阅读中,文本提供的只是图式,而非‘事实’,文本具有刺激读者自己去建立这些‘事实’的功能”[3]。在阅读时,读者构想出来的形象会从文本中涌现出来,文本和读者可以相互连接,相互渗透。姚斯提出,“衡量一部作品的审美尺度取决于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得到满足、超越,还是对作品失望或者对作者见解予以反驳”[4]。他认为,在接受理论还未提出时,文学批评只重视作品本身以及作家的主观臆想,并不关心读者的立场,这是文学批评的一大失误。伊瑟尔指出,“读者的接受过程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在阅读文本时,读者会把作品与自身的经验以及自己对世界的想象联系起来,产生意义反思”[5]。
二 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与《更衣记》
何为散文?广义地讲,凡是不属于韵文的文章都可称之为散文。散文不受分场分幕、情节、韵律等的限制,是一种灵活自如、轻松恣意的文体,作者可以直抒胸臆,畅谈天地,因而散文会给读者带来亲切自然、笃诚真实之感。
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是张爱玲旅居美国时创作的英语散文作品,文章于1943年刊载于上海The Twentieth Century月刊。1943年12月,张爱玲将这篇英语散文自译为《更衣记》,并发表在上海《古今》杂志上。1945年,张爱玲将《更衣记》收录至散文集《流言》中。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散文百年精华》一书收录了张爱玲的《更衣记》。这一散文名作详细地描述了自清朝至民国三百年来不同时期中国民众的服饰特点,反映了特定时期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心理,通过一系列社会风尚的变迁折射出中国民众社会心态的变化。张爱玲的《更衣记》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观察视角,彰显出中国丰富的人文知识,这一作品“不是光凭 才 气 就 能 写 得 出 来 的”[6]。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这一散文名作语言流畅,言简意赅,色彩鲜明,张爱玲在撰写原文时既泼得出又收得住。中文自译本《更衣记》延续了张爱玲诙谐睿智、独特华丽的创作风格,她在将自己的英文作品翻译成中文时,充分考虑到读者对象的变化,对文章作出适当的调整,使之符合不同读者的需求与期待。
三 张爱玲的自译策略
张爱玲在自译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时,考虑到中文和英文读者在思想、文化以及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并对文化因素予以重点考量,文化差异是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不容忽视的问题。“文化翻译不仅仅是文化传真,更不是简单地传递文化信息或重建文化形式。关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变迁和对相关文化现象进行比较,构成了文化翻译的主要特征”[7]。笔者将从文化背景知识的省略、文化类比的使用,以及情感语气的变化三个方面来探究张爱玲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自译本《更衣记》的翻译。
(一)文化背景知识的省略
在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中,张爱玲在提到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时,采用了文中注解的方式,她在英文原作中对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做了大量补充,意在让英文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而在英译汉时,张爱玲删去了原文中注解的内容。
且看下面的例子:
例1

译文:“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11]。
由于大部分英文读者对王昭君这一中国历史人物不甚了解,张爱玲在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原文中用文内加注的方式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王昭君”这一人物的形象特点,为读者补充必要的文化背景信息,让读者对王昭君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在中国,王昭君是人尽皆知的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昭君出塞”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因而在中文译作中,张爱玲删除了原文中的加注部分,这种处理方式使文章更为凝练传神。
在文学审美活动中涉及三大要素:作者、作品和读者,而接受理论学派将读者的作用与地位凸显出来。张爱玲在自译文本的过程当中,对文化背景信息做了适当的删减处理,正是最大限度地从读者视角出发。在自译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时,张爱玲省略或删除介绍中国文化背景信息的例子不胜枚举。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主要描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时装流变,原文中的文化背景知识对中文读者来说早已了如指掌,张爱玲在自译时言简意赅地进行了文化整合处理,符合接受理论学派的文学创作主张。
(二)文化类比的使用
“文本是一个未定与确定、开放与封闭的辩证统一体”[12]。为了让英文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服饰和社会习尚,张爱玲在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中曾多次引用英文读者熟悉的意象。而她在自译文本《更衣记》中,将这些用来对中国文化进行类比或比喻的内容进行了归化翻译或者直接删除。譬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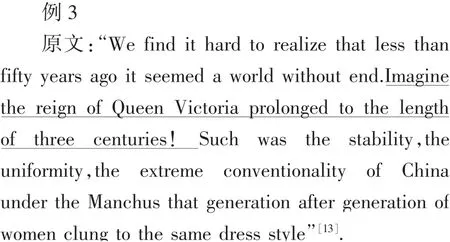
译文:“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宁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14]。
对于不太了解中国历史的英文读者而言,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到底是何面貌,他们可能无法想象。基于接受理论,张爱玲在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中将清朝时期的中国与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的英国进行类比,让英文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自己挖掘文本潜在信息。英文读者熟知,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历史上的在位时间仅次于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通过联想类比,读者便能很快地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在清政府长期统治期间,中国民众的服饰烦琐有余而变化不足,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的服饰特点与穿衣风格颇为相似,张爱玲所用类比恰到好处。然而在英译汉时,其根据读者群体的差异,将原文类比文字直接删去,并对译文进行归一化处理。
例4


译文:“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16]。
张爱玲将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中的“Gothic cathedral(哥特式教堂)”与中国的“大观园”进行类比,哥特式教堂与大观园均是装饰烦琐的建筑类型,通过这一形象类比,巧妙地表达出“女人”并不是由细枝末节“堆砌”而成的复杂“景观”这一含义。
张爱玲从读者接受视角出发,运用形象贴切、便于读者接受的类比手法,生动形象地传达出原文与译文应有的文化底蕴。
(三)情感语气的变化
“翻译的目的根据接受者不同,而会有所不同。译者可以根据特定的读者对象,用最适当的翻译策略来达到目的与文本意欲达到的目的”[17]。张爱玲根据中英读者价值观念的差异,在自译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时,对部分字句作了情感和语气上的调整,以便使其中英文本能够被不同的读者所接受。
比如:
例5

译文:“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19]。
汉英(中英)两种语言分属于不同的语系,汉语属汉藏语系,“模糊见长,朦胧见美”[20]。英语属印欧语系,以“精确之美”为其主要特色。“汉语这一语言偏重于意向性,强调顿悟与意会;而英语则更注重逻辑性与对象性,此外,英语强调的是客观科学的表述,因而西方人多偏重于理性思维,而中国人 则 感 性 认 知 较 多”[21]。在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原文中,张爱玲用“the maiden of low degree”直截了当地表明走起路来“引起轩然大波”的是“地位卑贱的姑娘”;而在其自译本《更衣记》中张爱玲根据中国人的认知习惯,将“the maidenof low degree”委婉而含蓄地译为“小家碧玉”,对于中文读者来说这一表达显得更为妥帖与得体,也更易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
例6

译文:“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23]。
张爱玲在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中,用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英文单词“erotic”(《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第674页写道:erotic一词的意思为“showing or involving sexual desire and pleasure;intended to make sb feel sexual desire)性欲的,性爱的,色情的”[24]。在中国人眼中,英美文化相对开放,西方人说话做事比较直接,他们表情达意讲求目的的直达性;而中国文化相对保守。基于接受理论,张爱玲在自译“It was declared to be of frankly erotic interest”这一部分时,正是考虑到当时中文读者对与“性”相关的“色情”类话题颇为忌讳,于是她选择“删繁就简”,用“挑拨性”一词含蓄地表达原句话语意旨。这种处理方式,可使译文在读者中间获得更高的认可。
基于读者接受视角,张爱玲在自译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时适当变换情感和语气,让译文表情达意变得更为妥帖自然,使之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四 结语
“翻译是有目的和意图的交际行为,翻译目的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方法和策略”[25]。张爱玲的英语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和自译本《更衣记》均是文学佳作,张爱玲的英文写作水平丝毫不逊色于那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作家。基于接受理论,其在英译汉时充分考虑到读者对象的变化,通过省略文化背景知识、运用文化类比,以及变换情感语气等诸多翻译策略,对文章进行极富生命力的再创造,译文完全延续了原文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魅力。张爱玲的文学作品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研读其自译作品对当代翻译教学实践及英汉散文翻译创作将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