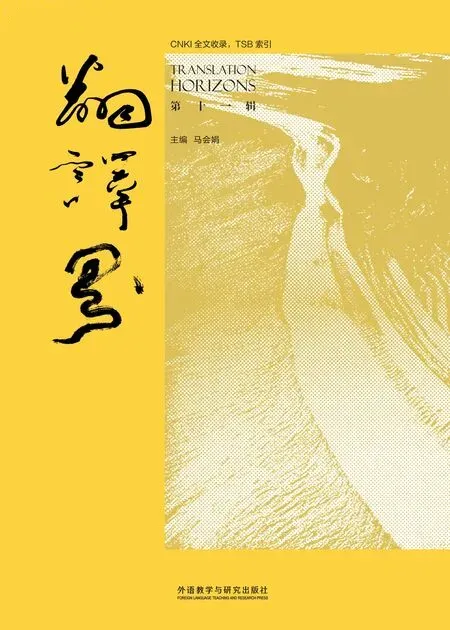中国古典戏剧外译中的“小说化”改编——以莫朗的《西厢记》法译本为例①
张 蔷 山东大学
1 引言
元杂剧《西厢记》在我国戏剧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其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被视为“天下夺魁”之作。1833年,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在《文学欧洲报》(L’Europe littéraire)上发表了《西厢记》第一折的法译文。1871年,他完成了这部作品前16 折的翻译,随后译文发表于瑞士东方学期刊《集之草》(Atsume Gusa)。自此,这部作品进入了西方读者的视野,成为继《赵氏孤儿》之后最受关注的中国古典戏剧作品。
《西厢记》目前共有7 个法译本①据笔者统计,除去本文中提到的儒莲、莫朗和沈宝基的3 个译本,《西厢记》还有其他4 个法语译本:曾仲鸣在《中国诗歌史论》(Essai historique sur la poésie chinoise,1922)、徐仲年在《中国文学选》(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1932)收录的经典片段节译;2007年孙家裕的漫画改编本《西翼的楼阁》(Le Pavillon de l’aile ouest);2015年法国美文出版社(Les Belles Lettres)“汉文法译书库”(Collection Bibliothèque chinoise)系列丛书出版的、由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教授蓝碁(Rainier Lanselle)翻译的法汉双语对照版《西侧楼阁》(Le Pavillon de l’ouest)。。其中,乔治·苏利耶·德·莫朗(George Soulié de Morant,1878—1955)于1928年出版的《热恋中的少女莺莺:中国十三世纪爱情小说》(L’Amoureuse Oriole:jeune fille.Roman d’amour chinois du XIIIè siècle)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译者通过对《西厢记》进行“小说化”的改编,确立了新的戏剧典籍翻译范式,使这部中国古典戏剧开始以通俗文学读物的形式在西方普通读者中流布。然而遗憾的是,莫朗译本的独特价值尚未被学界关注。译者为弥合中国古典戏剧与西方现代读者之间的差距付出了哪些努力?跨文类改编的深层动因何在?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回答,期待以译史为鉴,为中国古典戏剧走进世界文学版图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2 莫朗与《西厢记》的译介
莫朗于1878年出生在法国巴黎,幼年跟随东方主义女作家朱迪特·戈蒂埃(Judith Gautier,1845—1917)学习中文以及中国礼仪和文化。他于1901年来到中国,先后为汉口铁路公司和法国驻上海总领馆担任翻译,1906年被任命为法国驻云南府总领事。1918年返回法国后①关于莫朗的归国年份,学界尚无定论。有资料显示,1911年莫朗因病返回法国,而后于1917年再次来到中国,1918年返回法国。但是1917年至1918年莫朗在中国的活动留下的史料相对较少,仅有其本人的口述为证,因此部分学者对他的这段经历存有争议(参见Nguyen,2012:58-59)。本文依然采用学界普遍接受的说法,将1918年视作莫朗彻底告别中国、返回法国的年份。,他潜心中国古典文学译介,并致力于中医针灸术的研究和推广。《西厢记》是莫朗最早关注的中国文学作品。在191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专著《中国文学论集》(Essai sur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一书中,莫朗节译了该剧“墙角联吟”的片段,删减了其中抒情性的唱词,仅保留对白(Soulié de Morant,1912:247-252)。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戏剧与音乐》(Théâtre et musique modernes en Chine)一书中,莫朗将《西厢记》视作中国最优秀的古典戏剧,并对其情节进行了概述(Soulié de Morant,1926:25-26)。1928年,在原有节译片段的基础上,莫朗将《西厢记》改编为小说《热恋中的少女莺莺:中国十三世纪爱情小说》,由法国著名的弗拉马利翁(Flammarion)出版社出版。
该改编本共246 页,穿插有10 幅展现人物形象和主要场景的插图,并附有莫朗所作的序言和跋文。在序言中,莫朗高度评价了《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称“任何一部[中国文学]作品所取得的成就都无法与之相比”(Soulié de Morant,1928:6),认为该剧的成功除了得益于作者的创作才华之外,还在于人物、故事以及情感的真诚与真实性,《西厢记》因此具有跨越时代的文学价值。如他所言:“故事发生在过去,而人物却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同上)。另外,莫朗在序言中还梳理了西厢故事在唐传奇、诸宫调、杂剧、南戏等不同体裁中的流变,并在跋文中概述了元杂剧《西厢记》的前身、唐代元稹所著《莺莺传》的悲剧结局,首次为法国读者呈现了较为完整的西厢故事样貌。
3 “小说化”:戏剧文本流变和传播的重要途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区分了“纯叙事”和“模仿”两种叙述模式:诗人以自己的言语完成整个诗篇,即为纯叙事;诗人隐藏在人物对白之后,展示人物话语,则为模仿(柏拉图,2003:358)。受柏拉图模仿/叙事二元论的影响,当代文学理论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和哈钦(Linda Hutcheon)分别提出了“叙事化”(narrativization)和“小说化”(novelization)两个相近的概念(Genette,1982:402-404;Hutcheon,2013:38-45):以对话为主体的戏剧文本在改编时遭遇叙事元素的篡改(包括篇幅调整、对话概述、叙事者聚焦等),完成从模仿模式到叙事模式的转变。
文本的跨语际旅行产生了原文(original text)、源文(source text)和译文三个概念:“相对于译本而言,原文一词隐含翻译所依据的文本是‘原’先、先在、根本的;源文强调的则是译本的来‘源’”(庄柔玉,2015:127)。一个译本的原文和源文可能指向不同的文本。根据源文本的不同,戏剧翻译中的小说化改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译者直接以出发语中存在的小说改编本为源文本,作品经历了“原文—语内改编—源文—语际翻译—译文”的流变过程,其中语内改编与语际翻译可以异时异地、由不同主体完成。19 世纪初,英国兰姆姐弟(Mary &Charles Lamb)将20 部莎士比亚戏剧改编为适合本国青少年读者阅读的短篇小说,以《莎士比亚故事集》(Tales from Shakespeare)的形式出版。林纾以此为底本翻译出版了《吟边燕语》,便是这类改编的典型例证;另一类是原文与源文为同一文本,译者直接以戏剧作为参考底本,跳出字句窠臼,以语篇作为操控对象,通过自上而下地、有目的地选择语言资源,对整个语篇进行重写(张美芳、黄国文,2002:4),完成语言和体裁转换。作品流变经历了“原文/源文—语际改编—译文”三个阶段。莫朗对《西厢记》的小说化改编属于此类。
4 从戏剧走向小说:莫朗法译《西厢记》的体裁重构
如上文所言,莫朗对《西厢记》的小说化改编是对原文语篇的直接操控。一般来说,元杂剧的语篇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物话语之外的副文本,包括作品的标题与科介。所谓科介,即用来描述人物的表情、动作、武功或歌舞的舞台指示(徐扶明,2014:197-198);二是人物话语,其中以曲词为主,对话性宾白为辅。下文将从作品的标题、科介和曲词三个层面探讨莫朗对古典戏剧进行小说化处理的具体策略。
4.1 标题改写
标题与作品主体之间应该是一种默契的“合作”和“对话”关系:标题为文本主体做出概括表述,而文本主体为标题的内涵提供阐释框架(虞建华,2008:68)。原文标题中“西厢”二字点明故事发生的地点,而“记”是文类指称词,元、明两代作家常用此词命名以才子佳人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如《琵琶记》《金钱记》《花笺记》等。在《西厢记》的首个法文译本中,儒莲采用“转音+直译”的方式,将标题译为《西厢记或者西侧楼阁的故事》(Si-Siang-Ki ou l’Histoire du Pavillon d’Occident)。这种翻译方法虽兼顾原标题的音与意,但是否适当却有待商榷。其一在于“西侧楼阁”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只是一个陌生的地点符号,其二在于法文中“故事”(histoire)一词指称范围更为广泛,可对应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演义”“传”“记”等多个文类。莫朗则将原标题改写为《热恋中的少女莺莺:中国十三世纪爱情小说》,以女主人公的名字作为标题,在副标题中直接更改作品的文类归属,由杂剧变为“爱情小说”(roman d’amour)。改写后的标题引发了西方读者对遥远的东方叙事文学的想象,为其理解文本准备了条件。
另一方面,莫朗对标题的改写与译本重构的叙事结构形成参照。《西厢记》原文以张生、崔莺莺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为五本元杂剧,即由五个情节相对独立又前后关联的戏剧单元组成,每一本细分为一个楔子和四折正文,因此该剧共二十折①也有学者将《西厢记》第二本中出现在第一折后的楔子视作独立的一折,因此《西厢记》也有“五本二十一折”之说。。然而在《西厢记》西传的过程中,早期西方译者参考的底本多为清朝初年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批本。后者最大的特色是删除了原作的最后一本《张君瑞庆团圆杂剧》,以张生赴京赶考、与崔莺莺离别收尾。虽然莫朗并没有点明参考的底本,但是从译本的情节来看,他采用的底本同样应为金圣叹批本。他打破了原作的叙事结构,不再以“本”和“折”作为切分文本的单位,而是将作品分为16 个小说章节,标以罗马数字,并按照小说体制添加事件性章节标题,如“爱情的苏醒”“移居寺院”“危机中的寺院”“请宴”“悔婚”等,串联起了整个故事的架构。可以说,译者对作品体制的重构与译文标题形成了良好的呼应。
4.2 科介增补:叙事元素的僭越
每当一种叙事版本被重述或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总是会被注入新语境中传播更广泛的其他叙事元素或者注入个体叙事者或重述者的叙事元素(贝克,2011:33)。一部作品由戏剧改写为小说,意味着大量非对话元素进入文本,在篇幅和功能上超越人物对话,成为串联情节的核心元素。《西厢记》原文中的科介文体形式精炼,用以点明上、下场和说话的人物。莫朗通过大幅度增添叙事元素,将程式化的科介改写为丰富细致的人物动作和场景描写,明晰了叙事空间。
以该剧戏剧冲突最为强烈的“寺警”片段为例。该段描写的是:强盗首领孙飞虎欲夺崔莺莺(旦)为妻,率兵包围了崔家所在的普救寺。在崔夫人与长老法本、众僧手足无措之时,张生(末)提议写信请求援兵支援。如果我们把原文和译文中的人物话语去掉,仅保留叙事元素,可得到以下文字:
原文:孙飞虎上……法本慌上……夫人上慌……旦引红娘上……飞虎领兵上围寺……夫人、洁同上,敲门了……夫人云……夫人哭……末鼓掌上云……见夫人了……夫人云……末云……(王实甫,2011:14-16)
译文:Devant la porte ouverte du pavillon occidental,Originede-la-loi parle avec agitation à la Mère... Cependant, dans sa chambre bien close, Oriole songe, étendue sur son lit... La-rouge entre sans bruit... La Mère et Origine-de-la-loi appellent sous la fenêtre. Oriole se lève. Larouge l’aide à se vêtir et demande, inquiète... La jeune fille, sans répondre, se penche au panneau de la fenêtre que La-rouge vient de relever, et salue sa Mère et le Religieux... Oriole a pâli mais son visage est ferme... La Mère sanglote... Oriole, impatiente, l’interrompt...Origine-de-la-loi intervient... La Mère ayant retenu ses sanglots, dit enfin... Oriole, grave et sérieuse, a hoché la tête... Elle achève sa toilette et, suivie de La-rouge, elle rejoint sa mère et le vénérable. Ils se dirigent vers le temple. Les religieux atterrés et silencieux sont assemblés déjà. Tchang est parmi eux, le visage calme.Origine-de-la-loi gravit les marches de l’autel,se tourne vers les auditeurs et dit.(Wang,1928:56-64)
译文回译:西厢房的门开着。门外,法本和尚焦急地同夫人谈论着……然而,与此同时,在门扉紧闭的卧房里,莺莺正躺在床上,沉浸在幻想中……红娘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夫人和法本和尚走到窗下叫道。莺莺坐了起来。红娘帮她更衣,面露担忧之色……年轻的女孩莺莺没有回答,而是倚靠在红娘刚刚卷起窗帘的窗户旁,向夫人和法本和尚问好……莺莺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了,但是她神情坚定……夫人啜泣起来……莺莺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法本和尚插话道……母亲停止了啜泣,说道……莺莺面色凝重,摇了摇头……梳妆打扮之后,莺莺前去与夫人和长老会和,红娘紧随其后。他们一同朝佛堂走去……受到惊吓的众僧已经安静地聚集在佛堂里。张生也在其中,神色淡定。法本一步步走上祭坛,转身对众人说道。
原文中,科介是唱词的插入语,语篇衔接功能大于表意功能。剥离了曲词的科介(如“夫人慌上”“旦引红娘上”“孙飞虎领兵上围寺”)凝练地点明了空间的转变以及在场的人物,呈现了虚拟的叙事空间。至于场景、人物动作及心理状态的呈现,则需要读者借助于上下文曲词以及与程式化表达之间的默契程度进行想象。程式化、写意化的科介无法满足现代小说的叙事要求,也无法帮助目的语读者重构完整的叙事空间。莫朗在译本中增加了地点指示词(如“西厢房门外”“门扉紧闭的卧室”“窗边”“佛堂”“祭坛”),完整地串联起了情节演进的地点。除此之外,通过对人物动作和神态的扩写(如“坐起”“更衣”“担忧之色”“面色苍白”“神情坚定”等),清晰地再现了寺院围困前后戏剧冲突的张力,虚拟的空间和人物动作得以具体化、形象化。
4.3 曲词省略与概要:叙事时距的缩短
热奈特认为,文本体现的是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之间的关系。故事时间是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而叙事时间是文本讲述故事所占用的时间。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长度很难实现绝对等值,由此产生了“时距”(Genette,1972:122-123)。在莫朗看来,元杂剧唱词的抒情性大于叙事性,曲词打断了情节线的发展,故事时间暂时停止,叙事时间延长:“中国戏剧更注重形式而非内容。一些片段充满诗意、热闹喧嚣,至于它们是否与结局有合理的联系并不重要”(Soulié de Morant,1912:246)。为了缩短叙事时距,增强作品作为小说读本的连贯性和情节冲突的紧张性,莫朗采用了省略和概述两种策略来缩减作品中曲词的比重。
省略的部分包括文本中程式化的结构,如原文中用于铺垫情节、介绍登场人物的楔子,以及每一本结束后用于概括前文情节的定场诗。作品开篇崔母介绍家世背景、主要人物、来普救寺原因的曲词在译文中完全不见踪影。崔家的身世背景通过后文对话逐一向读者揭开。
除此之外,唱词中与情节发展无关的抒情成分也被部分删减。以下试举一例:
原文:这的是兜率宫,休猜做了离恨天。呀,谁想著寺里遇神仙!我见他宜嗔宜喜春风面,偏、宜贴翠花钿。(王实甫,2011:3)
译文:Son visage animé par la brise printanière me trouble et m’enivre.Des fleurs d’or incrustées de plumes de martin-pêcheur tremblent dans sa chevelure.(Wang,1928:21)
译文回译:她的面庞被春风拂过,让我惊慌、沉醉。镶着翠鸟羽毛的金花在她的头发中微微颤抖。
原文是张生在普救寺初遇崔莺莺时的一段兼具抒情和描写功能的唱词。前一部分用来表达男主人公情不自禁的激动心情,后一部分用来描绘张生视角中莺莺的外貌。“兜率宫”与“离恨天”为佛家用语,分别指称佛教净地和男女相思烦恼的状态。为了不给没有佛教背景知识的西方读者造成困扰,莫朗没有进行繁琐的解释,直接省去“这的是兜率宫,休猜做了离恨天。呀,谁想著寺里遇神仙!”两句,增加“troubler”(使惊慌)、“enivrer”(使陶醉)两个动词来加速叙事。
此外,莫朗使用概要的策略,省去言行细节,用极短的话语概括人物唱词。在《西厢记》“白马解围”片段中,莺莺一家被盗匪孙飞虎围困在普救寺,鲁莽滑稽的惠明和尚主动请缨突出重围,给援兵报信。这一部分由惠明的9 段唱词构成,与情节发展并无直接关联,仅用于刻画人物的情绪。莫朗直接将惠明的唱词删掉,甚至省略了惠明这一人物,用一句话概括了情节发展:Un messager habile s’est chargé de faire parvenir la lettre au Maréchal Tou.(“一个身手敏捷的信使成功地将信送到了杜将军手上”)(同上:70)。由此可见,译者通过改写或删减曲词,缩短了叙事的时距,使故事情节更为凝练。
5 重返历史现场:莫朗《西厢记》法译本体裁选择的动因
我们在研究翻译文本时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厘清这种解释得以发生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即这种解释何以发生(宋莉华,2015:157)。任何译本都是社会文化语境与译者主体选择共同作用的产物。我们将莫朗的《西厢记》小说改编本置于历史维度中考量,借助“概念史”研究范式,并结合译者身份及译介目的,厘清莫朗的跨文体改编背后的动因。
5.1 概念史视阈下的法译《西厢记》体裁指称变迁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概念史”(history of concepts)于20 世纪60、70年代在德国史学界兴起,随后开始应用于人文社科领域。概念史家关注的是“语词”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语词的含义一般较为明确,可以被精确地界定,而概念的内涵则往往模糊、多义,只能被阐释(黄兴涛,2012:12)。概念史研究的是历史进程中同一概念的不同语词表述,或概念在文本中的不同呈现(孙江,2008)。概念因此具有历史性、变异性和模糊性,反映着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知识形态以及概念使用者的意图。
相比于小说和诗歌,以《西厢记》为代表的“元杂剧”这一体裁概念在融入西方文学体系时遭遇了更多的壁垒。沿袭古希腊传统,西方各文学体裁之间界限分明。而元杂剧曲白相生、抒情与叙事并重,在西方体裁分类中找不到对等物。因此,当中国古典戏剧进入西方时,译介者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元杂剧概念的指称问题。
在早期中西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元杂剧的代言体叙事就曾令西方译介者感到困惑。与西方戏剧不同的是,元杂剧中很少出现人物之间的对话,而是由演员直面观众,陈述情节或表达情感。18 世纪,马若瑟神父(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在初读《赵氏孤儿》时,就感到无法区分中国戏剧与小说:
中国戏剧与小说相仿,二者唯一的区别在于戏剧中插入一些人物,让他们在舞台上讲话,而在小说中,则是作者讲述人物的话语和经历……剧本对话之中夹杂着大量唱词,演员在念白中突然开口演唱来表达喜悦、痛苦和生气、绝望的表演方式令我们感到震惊。(转引自Du Halde,1735:341-342)
马若瑟对元杂剧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西方汉学界对《西厢记》体裁的认识。1719年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院士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1863—1745)在为法国皇家图书馆编纂目录时,将《西厢记》误归为“历史传说”(historiola)(宋莉华,2018:164)。由于《西厢记》中夹杂着大量的叙事性元素,19 世纪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及其弟子在论述这部作品时,倾向于将其视作“长篇小说”(roman)或者“对话体小说”(roman dialogué)(李声凤,2015:118-128)。在文学断代史巨著《元朝世纪》(Le Siècle des Youên)中,安托万·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2)称“《西厢记》是抒情诗(poésie lyrique)的杰作”(Bazin,1850:211),认为它的成功不在于情节,而是得益于“语言的高雅、对话的生动以及和谐的诗歌魅力”(同上)。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Giles,1845—1935)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虽然将《西厢记》归入戏剧(drama),但是在评论时称:“元代戏剧中最值得一读再读的是《西厢记》……这部广受上流社会欢迎的作品,与其说是一部戏剧,不如说是一部小说”(Giles,1923:273)。
诠释学认为,理解不会凭空产生。理解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前结构与理解对象的内容的一种相互对话和交融的结果(洪汉鼎,2008:55)。人们总是带着既有期待或筹划,即“前理解”,去阅读一个陌生的文本。西方汉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可能影响了莫朗对《西厢记》体裁的判断。在将作品改写为小说的同时,莫朗在译本前言中承认《西厢记》是一部体裁界限不清的作品:
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这部作品都是新颖独特的。这既不是一本小说,也不是一部戏剧。它没有小说中的隐形作者,也没有再现日常生活的戏剧对话。在这里,人物在观众面前演唱他们最私密的情感。这是一个链条,串联起了内心情感和诗意描写,喜悦、爱情与绝望交替出现。这种方式出乎我们的意料。(Soulié de Morant,1928:5)
从“历史传说”“对话体小说”到“抒情诗”,西方汉学界对《西厢记》体裁指称的变迁反映的是中西文学系统之间体裁的不对等性。元杂剧概念在西方文学系统中定义不清,指称的模糊性一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另一方面被译者主动内化在他的翻译决策中,为他的跨文体改编提供了理据。
5.2 从经院汉学走向大众文学:中国古典戏剧翻译范式的转变
除了历史文化因素,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在体裁选择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莫朗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型译者(scholar translator)。从他的个人经历看,他长期从事商务、外交翻译,在上海、云南等地生活数十年之久,远离欧洲汉学中心,与前辈经院汉学家亦无师承关系。这种职业经历使他在翻译范式上与法国汉学传统有着明显的差异。
如上文所言,莫朗的译本并非《西厢记》的首个西文译本,儒莲已于1871年完成了对《西厢记》前16 折的翻译。然而儒莲的《西厢记》首译在后世译者看来却多有纰漏。正如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Antoine Berman,1942—1991)在《作为翻译空间的重译》(La Retraduction comme espace de la traduction)一文中所指出的,任何作品的早期译文都不可避免地充满瑕疵和误译,重译是对译本“原初缺陷”(défaillance originelle)的修复(Berman,1990:5)。莫朗时隔半个世纪对《西厢记》进行重译,不仅仅是对儒莲译本缺陷的修正,更是对既有汉学翻译范式权威性的挑战。
以儒莲为代表的19 世纪法国汉学家译介中国古典戏剧时,重视的并不是作品本身具有的文学价值和美学意义,而是更多地赋予了这些作品“民族志”的功能(夏颂,2016:290)。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以及观察实验的方法被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戏剧文本成了语言教学的工具和风俗文化研究的切入点。语文学范式(philological paradigm)在19 世纪法国汉学家的翻译活动中成为主流。在翻译《西厢记》时,儒莲多采用异化策略,以逐字逐句翻译或音译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剧本的文体结构和表达方式,并辅以大篇幅的注释,对文化负载词和诗歌意象进行翔实的解释,并在每一页上提供了唱词的中文原文和法文译文(参见Wang,1872)。
在莫朗看来,儒莲的语文学范式翻译并不适合普通读者的阅读:严苛的直译策略虽然能够帮助读者获取更多与中国有关的信息,“看起来也更加科学”(Soulié de Morant,1919:10),但是只适用于“翻译铭文或者史书中晦涩的段落”(同上)。对于纯文学作品来说,直译策略“抹去了作者想要传递的印象和幻想。读者每遇到一个单词,便会到脚注中寻找意义,剥夺了读者应该从书中获得的乐趣”(同上)。因此,在翻译《西厢记》时,为了提高读者的兴趣和阅读的流畅性,莫朗将作品的“本真性”让位于“故事性”,把不易于西方人理解的元杂剧改写成小说,弱化文本类型的异质性。莫朗的翻译活动标志着中国古典戏剧在法国的翻译从“源语中心主义”向“译语中心主义”的转变,使《西厢记》走出了经院汉学研究的范畴,其目标读者开始从汉学家和汉语学习者走向对东方文学好奇却知之甚少的普通法国读者,并直接影响了后续译者的翻译方法①莫朗之后,旅居里昂的中国学者沈宝基于1934年出版了法文博士论文《西厢记》(Si Syang Ki),其中附有《西厢记》全文翻译。尽管在论文中沈宝基认为莫朗的改写使作品丧失了诗意的原貌,认为莫朗的译本只是改编,算不上翻译,但是他在翻译时同样借鉴了后者“小说化”的策略,摒弃了原有的戏剧体制。。
另外,从莫朗本人的体裁倾向性来看,他对小说体裁更加熟悉。1920年代是他翻译的高峰期。除了《西厢记》之外,他翻译了多部中国古典通俗文学作品,如节选自《三言二拍》的《中国爱情故事》(Les Contesgalants de la Chine,1921)、《西游记》的改编本《猴与猪,中国十三世纪的奇妙探险》(Le Singe et le pourceau, aventures magiques chinoises du XIIIe siècle,1924)、改编自《长生殿》的小说《杨贵妃恋爱记》(La Passion de Yang Kwé-Feï,1924)、《好逑传》(La Brise au clair de lune,1925)等。在短时间内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成法文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大部分作品为长篇巨制,含有丰富的文学、文化典故。小说化改编无疑是一种快捷便利的翻译方法,提高了翻译的速度和文学作品传播的效率,为中国古典文学更快地融入现代世界文学体系提供了可能。
6 结语
“戏剧作为一种文学和艺术体裁,就其作为印刷出版的戏剧文学文本而言,它所受到的阅读范围从来就无法与小说相比”(王宁,2018:123)。兰姆姐弟的小说化改编使莎翁戏剧从精英走向大众。同样地,通过对科介的扩充和对唱词的删减,莫朗以短小紧凑的篇幅、通俗易懂的方式向20世纪初的法国读者传递了古老的西厢故事。
作为非经院汉学家,莫朗的译介目的已经不再是为法国汉学界的中国语言和风俗研究提供依据,而是面向普通法国读者讲述中国故事。诚然,译本有其时代和体裁的局限性:作品在遭遇译者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丧失了原有的体裁特色和诗学特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部经典作品只有不断适应目的语文学系统和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才能够吐故纳新,获得后世生命。莫朗对《西厢记》的“小说化”改编虽然是中国古典文学外译史上的个例,但是时至今日,这种大众化的译本对于激发异国读者的兴趣、扩大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力依然具有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