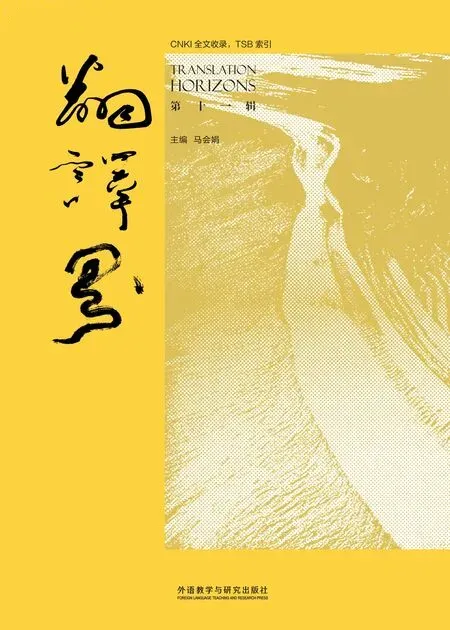《金瓶梅》的魅力——日本汉学家、《金瓶梅》译者田中智行先生访谈录
田中智行 任清梅
大阪大学 青岛大学
田中智行先生是大阪大学语言文化研究生院副教授,教授中国文学,主要从事《金瓶梅》研究,论文包括《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译注稿(上)》《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译注稿(下)》《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态度:对金圣叹的继承与演绎》等。近年来他一直从事《金瓶梅》的翻译工作,并于2018年出版了《新译〈金瓶梅〉(上)》,反响热烈,受到学界瞩目。据田中老师说,《新译〈金瓶梅〉》还会继续出版中卷和下卷。2019年10 月25—27 日,第四届《翻译界》高端论坛暨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青岛召开。田中先生受邀参加并做了主旨报告。会议期间,采访者有幸就《金瓶梅》在日本的传播状况及《金瓶梅》的翻译情况等问题向田中先生请教。希望本次访谈的内容对中国古典文学翻译“走出去”起到借鉴作用。
任清梅(后简称任):田中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
田中智行(后简称田中):任老师,您好。非常高兴认识您。
任:日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吸收在明治维新之前都有很深的印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转向学习西方。在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影响之下,中国不少古代典籍被翻译成各个国家的语言进行传播。在现当代日本,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文化的接受和吸收是怎样的情况?
田中:日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超越了时代,从古至今一直存在。说实在的,我个人认为,这跟中国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几乎没有太大关系。2018年3 月我在早稻田大学的研讨会上有幸跟几位最近出版了新的中国翻译作品的译者进行了交流。这些新的译著包括元曲的几个曲目、《杨家将》等,这都是先前不曾翻译过的。《杨家将》的翻译是由早稻田大学的冈崎由美老师以及神奈川大学的松浦智子老师共同翻译的。另外,2017年《水浒传》的新翻译也出版了。还有我的《新译〈金瓶梅〉》,也是刚出版的。近几年,有各种各样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被汉学家们翻译并陆续出版。但是,这与中国当前的文化外推策略没有太大关系。就像孙悟空这个人物,日本孩子从小就知道。大家也都关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否还存在一些未被发现的有趣故事。《三国演义》的爱好者们,不仅会在网络上交流,还会在现实中见面交流。仅仅是《三国演义》这一本书,它的爱好者就数量庞大。所以,日本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接受与吸收是一直存在的。
任:也就是说,自古至今,日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与吸收就没有停止过。那您觉得,日本当代的一般民众,在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接受上,与对欧美文学的接受相比,哪一个范围更广一些呢?
田中:这是由个人喜好所决定的。具体如何不好说。比如说喜爱法国文学的人,可能对《三国演义》不是那么感兴趣。我去年出版了《金瓶梅》,但是不少人对《金瓶梅》抱有一种错误的认识。我记得在中国买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上面标注的是“世界文学经典名著文库”,而不是大学生必读丛书系列(笑)。它是作为世界文学作品来推广的,我亦觉得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日本要求在高中时学习“汉文”,就是文言文,大家对中国文学的印象就是要拿来学习的,因为全是汉字,看上去很难。像《三国演义》可能算是个例外。真的把中国文学像法国文学那样作为世界文学来看待的人,还是比较少的。但是,《金瓶梅》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文学作品相比,都是毫不逊色、非常有意思的。我当时读英译本《金瓶梅》时,便觉得《金瓶梅》特别有意思。当然我也读过70年代出版的日译本,是用比较古老的日语翻译的,年轻人读起来比较吃力,所以我就想用一种更新鲜的语言,年轻人能读懂的语言,将我自己体会到的《金瓶梅》的有趣之处展示给读者。如果读者里有世界文学的爱好者就更好了。
任:所以,这也是日本虽然已经有日译本《金瓶梅》,但是您还是重新来翻译的原因吧。
田中:我高中的时候,在学校的图书室借阅过《金瓶梅》。在这之前我一直很喜欢《西游记》。上中学的时候,日本的暑假有自由研究这一作业。我当时所在的中学,是一所相当重视暑假自由研究的学校,所以我初中三年,一直在研究《西游记》。记得偶尔有一次将自己的感想寄给某个大学的老师,老师表扬了我,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在这方面有一点天赋,所以当时就决定读一下其他的作品试试。因为是高中生,处于青春期,所以就拿《金瓶梅》来看,当时觉得特别无趣,跟我所期待的完全不一样。直到大学毕业,对它也没有太大兴趣。在这之后,我觉得白话小说的几大名著,其他几本在日本的研究都很盛行,唯独《金瓶梅》的研究还没有那么深入,想它或许也是有些趣味的。后来听说出了英译本,我想既可以练习英语,又可以练习白话文,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就将英译本与原文一边对照一边学习,来备考研究生的入学考试。读了英译本之后,我觉得很有意思。高中时读过的同样的章节,在英译本里翻译得那么准确到位。我当时就感叹如此有趣,真的是杰作啊,应该更加好好学习研究。
任:所以,您喜欢上《金瓶梅》也可以说多亏了英文本的翻译。
田中:对的。当时读的英译本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芮效卫教授(David Tod Roy)翻译的。当时这位老师只是出版了一卷,一共是五卷。那一卷的反响特别好,对它的评价也很高。我还记得美国的亚马逊网上有很多评论,几乎所有的人都给了五星评价,其中只有一个人给的评价是一星。那个人是这样评价的:“我就像在吃高级西餐,端上来的第一道冷盘非常美味,这之后的菜品就一直就让我苦苦等待着”。芮效卫的第一卷翻译是在1993年出版的,之后一直隔了七八年才出版了第二卷。所以这位读者便觉得出版了如此美味的第一卷,却迟迟不出第二卷,就给了一星的差评。我对这个评价印象深刻,想想或许他说的是对的。(笑)
任:现在应该全卷都已经出版了吧。
田中:是的,出版完了。芮效卫教授几年前去世了。齐林涛博士正在研究芮效卫的翻译。齐老师说过,芮效卫教授论文并不多,他几乎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了《金瓶梅》的翻译上。他做了大量的调查,对原文的理解与把握都很精准,翻译时的表达都坚持一贯性,而且彻底地追求这种一贯性,特别让人敬佩。到现在我还把芮效卫教授的翻译放在身边,几乎是一行行地学习,看到某些句子的时候,我便想,原来这里是这样来解释的,真的让人佩服。
任:《金瓶梅》被芮效卫教授翻译成英语,在日本也有好几个版本的翻译,田中先生现在也在做《金瓶梅》的翻译。作为《金瓶梅》的翻译家,您觉得《金瓶梅》能在世界上传播、被翻译成各国语言的原因是什么呢?
田中:《金瓶梅》表面上描写的是以中国为舞台背景的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其实是很巧妙地刻画了人类的普遍心理,读完以后,会觉得自己就是被刻画的那个人。而且并非只是刻画某一个人以期感动读者,作者是用一种很客观的视角来刻画人物的。读者阅读的时候会跟书中人物共有某种不符合道理的错误感情,此时,作者会给读者提供一种客观批评这种感情的视角。这种写作方式与小说的展开方式,会让读者对书中人物沉迷于欲望之中这样的事情有一种真实体验感,能够给予理解。读者在读的过程中,也会自我注意到其实自己跟书中人物一样也可能会沉溺于迷惑之中,要有所警醒。这正是作者独具匠心、巧意安排下达到的效果,他希望读者能从作品中读到自己的影子。也可以说《金瓶梅》是一部体验小说,有很强的吸引读者的力量。
比如西门庆这个角色,大家普遍认为他不是一个好人,但是在李瓶儿死的时候,他却展现了很有人性的一面。正妻吴月娘不让西门庆靠近李瓶儿,但是西门庆却甩开吴月娘,坚守在李瓶儿身边。这一场面是比较感人的。只不过因为这两个人最初的相遇是私通的方式,是一种不被原谅的相遇方式。这样看来作者既没有将他俩作为好人来描写,也没有将他俩完全作为恶人来描写,其实就是写了普通人,不可能全都做正确的事情,也不可能全都做坏事。它倾诉了人类归根到底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在某种条件的束缚之下,拼命挣扎着活下去的,这是人类很普遍的现象。这也可能是作者要诉说的主题吧。我翻译的过程中,也被西门庆对李瓶儿的深情所感染,如果是我自己深爱的妻子去世的话,我大概也会以这种口吻跟她讲话吧。围绕李瓶儿临死之前说的话,我曾写过随笔发表。第62 回李瓶儿向西门庆表示自己已经时日不多,除非再重生一次,否则不能再与西门庆见面了。这其实是提起了一种不可能的条件,虽然很想再见到你,但是不能做到了。为了强调不可能做到,列举一些不可能的条件。比如重生一次,或者在阎王府见面等。原文中是用了“除非”这个词语。“除非”之后加一些不可能发生的条件,这样的句子,在《金瓶梅》当中仅此一例,他处看不到这样的例子。即李瓶儿在临死之前,用跟平时不一样的语调,变得有些感性、情绪也比较激动,给西门庆留了临终遗言。这部分也是比较感动的。因为这跟平时的李瓶儿的说话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将临死之人的遗言以痛切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李瓶儿死后虽有重生入梦的情节,其基调是悲剧性的。她最初跟西门庆相识,背叛自己的丈夫花子虚并致其死亡,归根到底是没有将她作为一个好人来写的。出发点并没有将李瓶儿作为一个正面角色来写,但是即使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在小说的手法上也下如此的工夫,让她说出那些使得读者情不自禁被感染的话,这无处不显示出作者的写作手腕之高明,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做到的。
这也是《金瓶梅》的魅力所在,并不是单纯的普通的写作手法。作者笔下的好多东西都是矛盾的,好人做的事情不一定全都是好事,坏人也不一定全做坏事。我虽然不是太想用“写实”这个词语,但是的确就是将人的本性写了出来。所以即使是坏人,也有让人恨不起来的一面。比如收取贿赂、欺负弱者、裁断不公正等,这些都是人性的一面。以前日本有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家曾经说过中国文学里没有绝对的恶魔与上帝,即不存在绝对的正义与非正义,这是中国文学的特点,是一种成熟的成人文学。我亦觉得如此。《金瓶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是一部成熟的文学作品。写成人的成熟文学,其中有性描写也无可厚非,更何况性描写不是主要部分,所以大家对《金瓶梅》的认识还是有些差池的,这一点我觉得比较遗憾。我出版《新译〈金瓶梅〉》的时候,就跟出版社要求,封皮上一定不要出现男女的画像;也跟出版社要求,在书的腰封上也不要用性描写做文章,只按照一部纯文学作品来宣传即可。
任:我们上高中的时候,《金瓶梅》是被禁读的。现在大家能读到的大多也是性描写被删节的版本。事实上,因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而禁读《金瓶梅》这一想法是错误的。毕竟性描写不是《金瓶梅》所要表达的主题。
田中:是的。说起性描写的翻译,这很困难。其一是因为它沿袭了一些前人文献的表达,如果不仔细查阅文献,便不能正确把握意思,翻译起来比较困难。比如,其中大量引用了《如意君传》①《如意君传》是明代第一部艳情小说。的性描写,所以有的学者也由此而认为作者也并非是自己一心一意闷头进行性描写的写作,性描写并不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关于性描写的翻译确实是很难的,比如西门庆跟郑爱月在妓楼的那一段,先是对妓楼室内的描写,比如墙上挂着什么样的画、妓楼的样子如何,其中引用着其他的前人文献,描写得非常繁琐,这部分的翻译真的很费精力。在这大量的描写之后便是性描写,翻译起来很累。
对青楼精致详细的描写,表现出了与郑爱月第一次性爱的西门庆渐渐高涨的心理过程。今天亦是如此,性爱这种人类原始的身体活动,通常被文化装置(例如在博物馆约会、吃法国料理、举行婚礼等)层层包裹。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参见第五十九回),青楼的建筑与装潢,以及食物和游戏本身即是对性心理的间接描述。读者通过阅读冗长的让人着急的描述,可以共享西门庆的心理过程。因此,为了准确地翻译这里的“性描写”,甚至有必要对详细的文化背景进行注释,以便现代日本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所以当主人公终于上床睡觉时,译者也已经精疲力尽,有美女也不管了,恨不得马上入睡。(笑)
任:听您这样说,翻译《金瓶梅》真的是太辛苦了。您在翻译过程中,还遇到了什么其他的问题了吗?
田中:嗯,跟性描写的翻译不同,也有翻译起来比较难,但是很享受的部分,比如双关语的翻译以及绕口令的翻译。将中国的双关语用日语的双关语翻译出来,是比较难的,但也是一种挑战。这里面有种游戏的成分。我举个实例来说明。比如有这样一个双关语,来自唐代诗人刘禹锡《竹枝词二首其一》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里面有两个qing,一个是指天晴的晴,一个是指情谊的情。翻译成日语的时候,这两个qing 字在日语中的发音却不一样了,一个变成了“sei”的音,一个变成“jo”的音,那就构不成双关了。所以我就把后一句翻译成“ふられそうだがふられない”。“降る”和“振る”,二者都读作“ふる(furu)”,前者是下雨的意思,后者是被人甩的意思。意思就是看上去要下雨又不下雨,看上去被人甩又不被人甩,这样也构成了双关。“下雨”跟“晴”相关,“被甩”跟“情”相关。这个用法,我也是想了很长时间,吃饭的时候也在想,突然才有了灵感的。
任:对于《金瓶梅》里面出现的诗词,您是怎么翻译的呢?您觉得诗词的翻译是个难点吗?
田中:大体说来,诗是受限制的,有各种要求的,比如要借用典故,或者具备七言、五言以及押韵等,所以我认为翻译的时候翻译为日语的内容也有某种限制会比较好。有限制的语言和无限制的语言,两者分别有自己的优劣。日本也有“五、七、五”的俳句,如果将俳句的字数扩大,是不是会表达出更多的意思呢?那也不尽然。正是因为有这些限制,译者才会努力寻找符合这种限制的准确词汇,从而产生出一些优秀的美好词语。与此相同,我在翻译诗词的时候,尽量使前后句子的字数保持一致。而且,在翻译对仗的句子的时候,也会尽量将前后句的汉字词汇与汉字词汇对齐,假名词汇与假名词汇对齐。
我举个实例,出现在第十五回中描写元宵节的情景。这部分一直用对仗排比句。比如里面的“王孙争看,小栏下蹴鞠齐云;仕女相携,高楼上妖娆炫色”(兰陵笑笑生,2000:182)。我是这样翻译的:“王孫たちは争い見て、小欄の下には蹴鞠が雲まで上がり、仕女たちは連ね立ち、高楼の上にて嫣然と色をば誇る”(田中智行,2018:304)。“王孫”对应“仕女”,“争い見て”对应“連ね立ち”。再比如,“卖元宵的高堆果馅,粘梅花的齐插枯枝”(兰陵笑笑生,2000:182)。我翻译成“元宵のだんご売りは、菓餡を積み重ね、梅花のかざり貼りは、枯枝を揃え挿す”(田中智行,2018:304)。“売り”对应“貼り”,“積み重ね”对应“揃え挿す”,同时汉字对应汉字。在翻译对仗句的时候,我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处理的。使得汉字与汉字对齐,假名与假名对齐。当然并非所有的对仗都可以按照这个原则来处理。通过这样的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也让自己在某个限制范围内来摸索最合适的词汇来完成翻译。
另外,再举一个歇后语的例子。在第二十三回中,蕙莲对西门庆说过这样一句话:“后边惜薪司挡住路儿——柴众。咱不如还在五娘那里,色丝子女”(兰陵笑笑生,2000:289)。“惜薪司挡住路儿——柴众”这一歇后语本来的意思是指惜薪司堆满了柴,把去司府衙的路都挡住了,比喻人多闲话多。这里不能采用直译,因日语里是没有这样一个词语。于是我翻译成“惜薪司が通せん坊—火遊びした日にゃ炎上します”(田中智行,2018:478)。为什么这样翻译呢?因为日语里面的“火遊び”一方面可以指真的玩火,另一方面也比喻“做危险的事情”“男女偷情”。“炎上”这个词,既可以指真的火烧起来,也可以指流言满天飞。所以这样来翻译,跟原文要表达的“闲话多”的意思就吻合了,而且也有双关的意思。一方面指要玩火的话,房子就会烧着了;另一方面也指如果在这里偷情的话,后院的女人多,流言蜚语很快就会传遍的意思。如何将这两个意思融到一句话里,我思考了很久,费了一番精力。
任:您这样翻译通俗易懂,日本的读者也一下子就明白了。
田中:希望他们能够明白。到目前为止,日本大多数的翻译都是直译的,如果直接翻译成“惜薪司前面有很多柴火,挡住了去路”的话,这样翻译是无法理解其中意思的。或者,以前的翻译在后面做一下注解,注明在汉语当中,这句话是双关的意思。这样一来,读者也只是明白了汉语里面是双关的,而日本的翻译并没有变成双关。读这样的日译本,也是索然无趣的。我读了原著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认为在翻译的时候必须要把这种趣味翻译出来才可以。当然并非所有的表达都能翻译得特别有意思,但是我还是尽力要按照这个原则,让译本同原著一样有趣。
任:您的翻译态度令人感动,翻译《金瓶梅》真的是很耗费精力的一项工作。您应该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吧?
田中:是啊。最主要的问题是我的孩子都太小了,我也需要照顾他们。最大的烦恼就是没有时间翻译。所以近五年,我几乎都是每天早晨四点起床来翻译的。虽然大家都说《金瓶梅》是晚上的文学,但是对于我来说,是吃早饭之前的文学(笑)。开个玩笑,等全部翻译完之后,写后记的时候,我要把题目改成《吃早饭之前的工作》。日语中,“朝飯前”这个词语还有“简单”的意思,所以早饭前的工作,也是简单的工作的意思。说是简单的工作,其实是在吃早饭之前的一段时间做的工作。
任:您翻译《金瓶梅》真的辛苦了,这根本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是一项很艰辛的工作。
田中:没办法,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太有意思了。
任:听您讲了这些,我大体也了解了您关于翻译的一些理念。想跟您确认一下,您在翻译当中,最注重的是什么?是考虑读者,让翻译更通俗易懂,还是尽量忠实于原文,或者二者兼之呢?
田中:我翻译《金瓶梅》的出发点,是因为我读了以后,觉得特别有趣,我想将我自己认为有意思的作品翻译出来让更多的人读到它。有一半的因素是自我表达吧。将自己读到的、体会到的内容忠实地反映到翻译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要将我感受到的反映到翻译当中。这或许是我个人的一种理解,但是说得极端一点儿,也无妨。我花费了好几年来翻译,即使最后被别人说我的翻译有误,那也没有办法。对文学作品的解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终究翻译不是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对自己而言的正确答案,能捕捉到就可以了。通过对译文的打磨,应该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的意思。至于正确与否,再过一百年二百年,我认为的正确的事情或许也变得不正确了。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有一个努力翻译《金瓶梅》的我,这样的我是如此解读《金瓶梅》的,我想把我的这个样子写到文字里。
任:真的很佩服您的这种翻译态度。谢谢您!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关于《金瓶梅》在日本传播的方式这一问题。您觉得像小人书(类似日本的漫画,字数比漫画稍多一些)这种方式可行吗?我知道《三国演义》之所以在日本那么受欢迎,得益于日本漫画家横山光辉的漫画《三国志演义》。
田中:在日本,像古典文学作品《源氏物语》也有类似漫画。《金瓶梅》最近也有漫画出版,但是跟原文内容相差太大。在推特上检索《金瓶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有关《金瓶梅》的漫画。所以,漫画形式的传播是存在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文学作品还是需要通过文字来表现的。《金瓶梅》不仅故事很有意思,它的语言也非常有趣,表达也熠熠生辉。如果只通过读简要的故事情节就说“好的,我明白《金瓶梅》了”的话,就太可惜了,因为他们没有真正领会到《金瓶梅》的魅力。如果是入门级别,看看漫画倒也可以;若是真想了解《金瓶梅》,还是要看书的,特别是希望读者能读我的《新译〈金瓶梅〉》。我希望大家读过之后,能发出这样的感叹:“《金瓶梅》真的是一部杰作啊!”
任:田中先生,谢谢您!听您一番讲述,收获很多。我也感受到您对《金瓶梅》的深切喜爱。再次衷心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采访。期待您的《新译〈金瓶梅〉》中卷和下卷早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