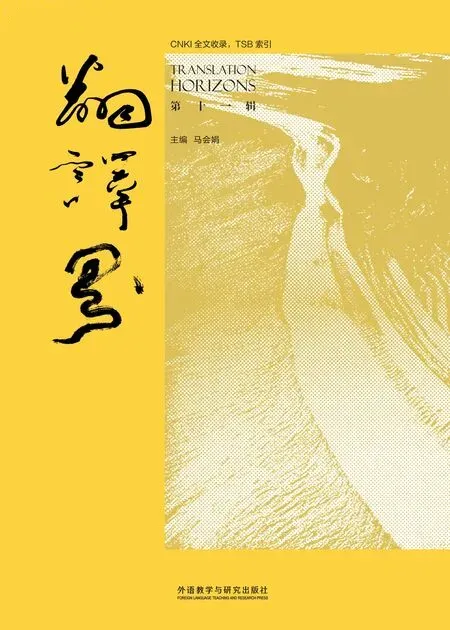“人史”抑或“文史”——论中国翻译史研究的社会学视角①
欧阳凤
湖南女子学院
构建中的翻译学科需要翻译理论、翻译史和翻译批评三大支撑,其中翻译史更被看作权力转向后翻译研究最关注的内容之一(张旭,2010:30)。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翻译研究学者却忽视了翻译史的研究与撰写,比如霍姆斯与图里的翻译研究结构图就未提及翻译史这一分支。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翻译史研究有必要建构起自身的理论框架和行动指南。本文将就此进行探究,首先分析中国翻译史研究与撰写的现状和问题,而后借用社会学的史学观以及部分可行理论进行自上而下的范式探索,继而在总体指导思想下举例细化,希望能为翻译史的撰写提供有益思考。
1 中国翻译史研究与撰写的现状和问题
19 世纪下半期,中国开始出现零星的译本札记与译书目录,并于1880年刊印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文,介绍了19 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江南制造总局的西书翻译情况,这是现当代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发轫(邹振环,2017:19-20)。从史料编撰来看,1927年蒋翼振编著的《翻译学通论》集结了梁任公佛典之翻译、清吴挚父与严几道论译西书、梁任公论译书、傅斯年译书感言等12 章,是笔者发现的较早的翻译理论史著作,而后是1933年吴曙天编的《翻译论》。1940年黄嘉德编辑出版的《翻译论集》中的第四辑题为“翻译的历史”,则是笔者发现的较早的翻译实践史论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翻译史研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在1984年迎来了中国的“翻译史年”(同上:208-209)。这一年罗新璋编写的《翻译论集》出版,汇集了各种翻译理论资料,同年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推出了两卷本的《翻译研究论文集》,开始重视翻译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此后,我国翻译史研究进入持续发展期,笔者以“翻译史”为关键词在读秀等平台上进行中文搜索,相关论著有90 余种,专门的“中国翻译史”40 余种;在中国知网上以“翻译史”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到期刊论文600 余种,而以“中国翻译史”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期刊论文有200 篇左右。特别是近十年来,翻译史研究得到了较快增长。①搜索日期为2019-12-26。
虽然翻译史研究成果众多,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学术问题,“众多翻译史学作品普遍性地存在:(1)时间点不明确、不准确;(2)人物志与专题史料交错;(3)软史料与硬史料不分,且硬史料不用或用得不当”。其次,意识与规范问题。再次,管理问题:当前翻译史建设存在术语不统一、翻译史研究活动散乱、翻译史作品的出版和发表缺少专业的审查机构、翻译史的专业研究队伍建设不足四个方面的缺陷(贾洪伟,2019:122-124)。最后,还有学者指出国内翻译史的撰写缺乏理论指导,在方法论层面不够深入(蓝红军,2016:5;屈文生,2018a:831;包雨苗,2019:93 等)。以往的国内翻译史研究深受基于系统的翻译研究的影响,大部分采取结构主义原则,忽略了行动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即便涉及译者等微观层面,客观史料与主观阐释依然常处于分裂状态,仍需“令客观主观化”(subjectivize the objective),正如要“令主观客观化”(objectivize the subjective)一样(Pym,2009:24)。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加强方法论层面的探讨。
当前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方面影响最广并沿用至今的著作是皮姆(Pym)1998年撰写的《翻译史研究方法》(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皮姆认为翻译史是翻译学界忽视已久的话题,比如霍姆斯(Holmes)和图里(Toury)等人建构的译学结构图中就没有翻译史这一分支(Pym,1998:1-2)。为了引起翻译学界对翻译史的重视,皮姆在该书中给出了翻译史研究的基本框架、翻译史编撰的四大原则以及翻译史创作的三大部分(同上:ix-x、5-6),这对于国内的翻译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国内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方面的论文不多(参见岳峰,2005;王建开,2007;许钧、朱玉彬,2007;熊宣东,2011;夏天,2012a、2012b;穆雷、欧阳东峰,2013、2015;黄焰结,2014;屈文生,2018a;贾洪伟,2018、2019),著作则更为稀少,其中又以邹振环的《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最为全面。作者以“起承转合”为线索,以翻译史研究论著为主要资料,结合其他文献,首次勾勒出20 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发展演变的脉络与系谱(邹振环,2017)。这些论著主要着眼于史料文献是否扎实、论述品评是否客观深入,在具体研究方法层面着墨不多。随着时代、技术的进步,翻译史研究方法也应与时俱进。当前,翻译史研究“正经历着从旧文重编到开拓创新、从宏大历史到微观叙事、从文学翻译史向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转向”(屈文生,2018b:22),这与社会学以及社会史学中的部分观点不谋而合。因此,笔者拟从方法论层面剖析翻译史研究与撰写过程中的社会学视角,并就“治文”与“治人”的次序问题展开论述,进而在示范举隅中进行模拟实操。
2 中国翻译史新方法论——社会学综合视角
近年来,社会翻译学发展迅速,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同时也面临不少问题,比如术语不统一、研究对象过于宏观、研究模型难以有效指导翻译实践等(Zheng,2017:30-31)。笔者认为,社会学针对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理论,在借鉴时应该有所扬弃。因此,本文摆脱了通常意义上的社会翻译学理论框架,即布尔迪厄(Bourdieu)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拉图尔(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卢曼(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而是先从社会学的历史观入手。因为本文的研究主题为中国翻译史,而史学方法又对翻译史研究意义重大(穆雷、欧阳东峰,2015:115)。社会学的历史观通常可从社会史和历史社会学两个跨学科分支着眼。社会史和历史社会学都要求超越史料(李里峰,2018:27)。社会史主张回到历史场景,注重描述和阐释,历史社会学往往超然于历史,注重分析和解释,这与翻译史研究中常说的“史论结合”不谋而合。
那么如何进行解释与阐释呢?“新一波历史社会学研究更加侧重历史情境的模糊性(ambiguity)与偶变性(contingency)对于行动者的选择与行为的影响……在什么样的历史场域中,在什么样的历史转捩点上,行动主体会做出回应性选择(无论是理性的抑或是非理性的),改变行动,从而深度影响历史的进程。一般而言,当行为者处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必然会面临选择”(严飞,2019:177)。这种模糊性和偶变性淡化了结构主义机制与模型之预设。借鉴社会史或者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翻译史研究学者既可以寻找共性,发现普遍规律或者模式,也可以寻找不同之处,以便更为深入地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者不应预设机制、模型,而应在史料的分析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在以往的翻译史研究中,图里提出的翻译“规范”是一个重要概念。但是,“翻译理论中的传统可能只是例外,而非规范”(Pym,2009:42)。因此,翻译史研究与撰写过程中不宜用预设的翻译规范去生搬硬套,介绍译者对规范的学习与遵循,而应该展示译者对前辈们所积累的“总惯习”的继承与偏离,介绍译者的成长之路及其对“总惯习”的贡献。也就是说,研究者要抛却结构决定论,但可以总结部分结构性规律。
同时,翻译史研究应该抛却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观点,不再将人与物、有名与无名、中文与外文、时间与空间等概念分割开来。首先,社会学史观在将“人”拉回研究的中心(孟庆延,2018:178),而翻译史也在从只关注文本或者语言转为关注译者自身以及译者所处的复杂环境(Pym,2020:5)。译者进入翻译史的研究中心,这与社会学的研究进展十分契合。拉图尔在其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提出的“行动者”概念既包括人,也包括物,译者、编辑、译本等,都可以纳入行动者的范畴。至于具体的路径是从译文到译者还是从译者到译文,传统的结构模型是二分的(原作与译作、源语与目标语),都是译文为先的。但是,现实情况往往并不这样,比如在民国时期的翻译活动中,此方是中文或者白话文,而彼方则可能是英语、日语、世界语、法语或者俄语;语种异常繁杂,往往极难追溯译本源语,因而这种情况下二分法的意义并不大。因此,翻译史的写作要避免模式化、结构化,而应该允许差异的存在。有鉴于此,皮姆建议采用“先译者再译文”的研究路径,认为:如果通过考察人物生平和社会背景或者阅读序言、书信以及研究对象的作品,就能直接实现翻译史的诸多目标,那么就无须进行错综复杂的文本批评(Pym,2009:37)。有名与无名这一对概念也是相对的,无名的译者更值得我们去挖掘,发现其被历史淡忘的价值,甚或发现其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至于语言文化,译者身上的文化间性有时并不局限于两种文化之间,常常涉及三种或以上。以往的翻译研究(比如翻译规范研究或者多元系统翻译理论)往往将译者预设为目标语言的成员,限定在某个系统内,这是不合理的。此外,很多译者不仅做翻译,还可能身兼数职,如梁遇春(1906—1932)①福建福州人,散文作家,擅长翻译,曾任上海暨南大学助教,后又任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著有《春醪集》《泪与笑》(遗作),译有《近代论坛》《荡妇自传》《英国诗歌选》等。既是翻译家,又是作家。因此,译者往往是跨职业、跨语言、跨文化的。为何能跨、怎么跨、跨得如何,这些问题其实就构成了其背后的网络。再者,这种跨职业、跨文化中心常常在哪里?这些网络的汇聚点在哪里?比如民国时期,跨职业、跨文化中心通常是上海、北京等大都市,译者要么自己身处这些大城市,要么其所处网络的中心位于这些地方,因而时间与空间在翻译史中也应是并存的。我们可以将“形成”(making)作为关键词,来研究翻译文本和译者的创作,这通常会涉及人、物、时间、地点、进程等多种因素。
最后,研究与撰写的技术层面也应体现出社会学网络的联合与会通,社会学这种连接与融合在分析手段上的体现之一,是用信息技术来分析、研究人文领域的知识,即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数字技术的发展在翻译史的研究与撰写中占有重要位置,我们可以通过构建翻译史料数据库,更广泛、全面地收集史料,从而避免史料选择的随机性或者“代表性”,实现“去中心化”。当然,这样也有利于史料的储存、检索与获取。我们还可以使用语料库的方法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以及搭配进行分析、解读,从而提出新问题,解决旧问题(Wakabayashi,2019:132)。借助新技术以及社会学视角,中国翻译史研究与撰写有望实现宏观、中观、微观分析的融合统一。
3 中国翻译史研究撰写个案——基于社会学范式构思一部《民国翻译史》
基于上述行动者优先的原则以及综合会通的分析方法,我们现在来构思一部《民国翻译史》,其步骤如下。
第一,搜集译者们的原始数据(生平故事、译作创作、诗学观念、他人述评、通信日记等),再进行整理分类,将译者(尤其是那些无名译者)从长期的压制状态下解放出来。搜集的内容不应囿于译者的翻译活动,而应该扩大到他们的生平经历、通信交友、创作评论等,甚至时人或者后人对他们的研究评述。研究者应该突破传统的结构主义范式,因为这种范式对译者身份的理解过于简单,而在现实生活中,译者通常具有多重身份。他们可能具有多学科或者职业背景,这些学科或者职业背景也会对其翻译活动产生影响,所以研究者要扩大原始数据的搜集范围。
第二,选择合适的数据库建设或者分析工具,对原始材料进行梳理,而后进行语料库或者大数据分析。近二十年来,翻译平行语料库以及不同版本的语料库层出不穷。但是,数字人文下的分析路径远不止于此,研究者可以进行如下拓展:(1)建立多级分层语料库或者数据库,比如第一层为文本(原文、译文、其他作品、书信等),第二层为学术研究,第三层为外部评论,分析哪些译作备受关注,得出译作的社会“影响因子”。(2)建立译文手稿数据库,分析翻译过程。(3)进行主题建模,分析重复出现的主题,并在设定的时间区间内进行历时比对,观察翻译偏好随着时间的变化如何流变。(4)进行大数据分析。比如研究者可以梳理哪些译者在相同的期刊或者出版机构发表或者出版过译作;分析这些译者的通信或者散文、杂文等,探究译者之间是否存在交集,从而建立起相对精确的行动者网络;分析出连线最为密集、复杂的节点人物,网络连线越密集,说明其权力越大或者位置越关键;对这些重要节点进行强调,使得以往隐性的网络凸显出来,发掘以往被历史尘埃掩盖的重要或者关键人物。同时,这些行动者网络是流动的,没有具体形状和边界,也就是说,研究者可以不断对其进行补充。以女性译者陈敬容(1917—1989)①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女诗人、翻译家,曾任《文史》杂志和文通书局编辑,《中国新诗》《森林诗丛》编委,著有《星雨集》《盈盈集》《交响集》《陈敬容选集》,译有《安徒生童话选》《巴黎圣母院》《绞刑架下的报告》等。为例,我们可以从其伴侣出发勾勒其翻译活动的网络。通过其恋人曹葆华(1906—1978)②四川乐山人,诗人、翻译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译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马恩列斯论文艺》《论艺术》《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著有《现代诗论》等。,她与一些文学文化团体和编辑界人士有了交集,与何其芳等人建立了联系。此外,其他行动者对其诗歌创作与翻译的批评,激发了其进一步的行动(比如自我辩护、翻译俄语作品等)。通过分析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与对抗,以及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比如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可以追踪、构建出民国时期新诗界、翻译界、出版界生动复杂的图景。
第三,进行阐释。因为数据不会告诉我们为何某个译者、某部译作或者某个主题颇受欢迎,而社会学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又有重描述而轻解释的不足,所以,有必要再结合社会学中布尔迪厄的场域、惯习、资本等概念对译者行为进行分析、解释。研究者可以从翻译活动的发起层面分析,探究译者进入翻译场域的多重目的(增加象征资本、获得经济资本等);从翻译活动的进程进行分析,考察翻译网络中其他行动者对译者翻译活动的影响,比如可以考量女性译者的配偶对其翻译抉择的推动或者阻碍作用;从其翻译活动决策过程分析并探讨译者如何在多个选项之间进行选择、为什么选择这个而非其他的、译者的用词偏好是什么、译者的偏好发生了什么变化等。这些都可以借用数据分析工具,由此可以得出译者翻译决策背后的原因以及翻译惯习的形成和演变,而不是简单地评价译者遵循了什么样的翻译规范;从翻译的接受、影响层面分析,可以借助情感分析等系统地识别或者分析舆论对某部作品的态度,或者译者、读者对某些主题的偏好等。这些分析促进了翻译史研究与撰写中宏观与微观角度的拉伸转换。
第四,利用(未来可能的)互文、超文:翻译史的研究或者撰写告一段落后,未来还可能将其融入相应的数据库中,并向局部或者全部公众开放评论、编辑权限,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学术探讨与翻译史的编辑中来。将相互关联的多个文本置于一个庞大的文本网络中,利用超文本将禁锢于纸张的互文性解放出来,超越传统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共享,使得翻译史研究不再因为出版而停止生长,从而获得无穷的生命力。
当然,基于上述步骤的《民国翻译史》的实现存在很大难度。首先,这项工作要求跨学科、多技能人才之间的全力合作,借助全新的信息技术和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进行可能性极为丰富的阐释,并且留下开放的、可不断拓展的版本,而非以往凭借某位历史学家一己之力,穷尽数年甚至数十年之功,方得的一部固定的巨著。其次,费用方面耗资不小,主要是原始语料的收集、整理和数字化等。如果采用数字化方法编撰史料,还要注意文本的版权问题,一些文本可能无法进行数字化。最后,就是有可能陷入史料的“唯数据化”,一些研究者甚至不再看文本,也不再强调“描述”。
4 结语
近现代中国,尤其是明末清初、民国时期,有大量的翻译史料有待发掘、阐释,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前景广阔。同时,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尚未形成,还需要史学界与翻译界的研究人员通力合作,继续完善翻译史研究的内容、方法和路径。本文结合了社会学中不同的理论学说,涵盖社会史和历史社会学的史学观念以及布尔迪厄和拉图尔等人的社会学理论,将之融合到中国翻译史研究撰写中,首先给出了宏观的方法论指导,继而展开具体的实践步骤,设想了一种国内翻译史撰写或者研究的可行路径,对于消减中国翻译史研究中结构主义范式的影响具有一定作用。文章提倡以人为本,以行动者为先,但并未忽视文本的意义,主张对文与人进行综合阐释。笔者希望未来的中国翻译史研究中,微观的文本分析不再牵强附会,宏观的历史描述不再千人一面,从而实现人史、文史的融会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