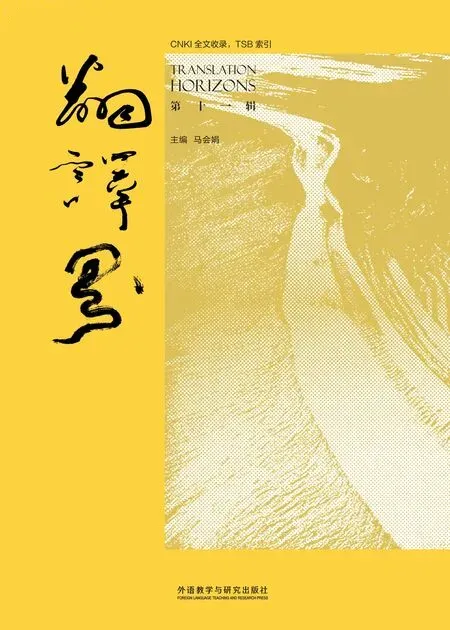中外文儿童文学翻译描述性研究述评①
卢 宁
北京语言大学
1 引言
20世纪50—60年代,翻译研究以语言学范式为主导,而80年代以后,描述性研究和文化研究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进而推动了翻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语言学派翻译研究主要以原文为中心,关注从语言对等角度“怎么译”的问题,属于规约性研究;而描述性翻译研究将翻译研究从“对转换的静态语言分析和一对一等值的执迷中摆脱出来”(Munday,2001:122),转而关注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系统和社会文化历史中的位置和功能。
翻译研究与儿童文学研究均为20 世纪中叶确立的新兴学科。而作为二者交集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一方面似乎自然而然地获得了“边缘的边缘”的研究地位,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没有囿于对单纯语言对比和静态对等概念的执迷,而是关注包括语言和文化因素在内的整个翻译活动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动态呈现。可以说,描述性研究对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尤为适合。
2 描述性翻译研究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霍姆斯(James Holmes)在翻译学架构图里将翻译研究分为纯翻译研究与应用翻译研究,纯翻译研究又分为理论研究与描述性研究(转引自Toury,2001:10)。描述性翻译研究事实上于20 世纪70年代因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多元系统理论”的提出而开始受到关注。随后,埃文-佐哈尔的同事图里(Gideon Toury)拓展了霍姆斯架构图里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分支,提出应该从译入语及其文化出发来研究翻译活动,因为译作是译入语中的“文化事实”。图里在其《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中主张:“实证研究的目的在于以系统、控制的方式解释‘真实世界’的某些部分;因此,任何实证科学如果不包含描述性分支,都不能称为完整、自主的”(Toury,2001:1)。而翻译的描述性研究和理论研究是相互促进和相互推动的,描述性研究必然会对理论分支有所影响,助其完善(Toury,2001:15)。
不同的翻译研究路径建立在对翻译本质的不同认知基础上。在语言学理论框架内展开的规约性研究中,翻译被认为主要是语言现象和语言活动,而在描述性研究中,翻译活动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得到了更多重视。“规范”研究是描述性翻译研究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因为规范决定着一种社会活动(如翻译活动)是否适当,并需要对制约这种社会活动的各种因素做出反应。换句话说,很多描述性翻译研究是围绕翻译规范展开的。
描述性翻译研究也是一种方法体系,与规约性研究关注“应该/不应该”不同,描述性研究不涉及价值判断,只是客观表述由实证数据所反映出的“翻译是什么”及其所涉及的“何人、何事、何时、何地、如何”(who、what、when、where、how)。正如朱志瑜所言:“描写翻译研究的任务是发现翻译的规律,包括翻译过程、产品、影响、效果等等,相关的问题有译文读者的接受,不同文化、不同历史时期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文本、读者、译者、赞助人等与翻译策略和结果的关系等等”(朱志瑜,2009:6)。
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核心是对译作性质的认定:译作是译语文化中的事实。翻译的发生源于译语文化中的空白或“匮乏”,需要翻译作品来填补,这种填补可以是一个文本也可以是一种“模式”(model),即多个同类型文本(Toury,2001)。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包括童话、儿童小说等,正是中国文学系统中所匮乏的一个模式空白,因而它的翻译引进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整个20 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事实上是由大量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改编、译写作品同受外来启发而逐渐萌生的原创儿童文学共同组成的(张建青,2008;李丽,2010;王泉根,2015;朱自强,2015)。
儿童文学翻译与成人文学翻译相比,在纯语言和文学层面研究意义都有限。有学者认为,儿童文学研究在学术界地位低人一等,究其不受尊重的原因,则是学者们没有找到适合儿童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仍然在传统的“文学批评”框架内研究儿童文学。由于发展环境原因,儿童文学所遵循的规范有异于当下成人文学的规范,因此,在文学批评的框架中开展儿童文学研究不过是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强行寻找成人文学的文学价值,其结果显而易见,并使儿童文学遭到否认(Shavit,1992a:3-4)。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情况也十分类似:如果不考虑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而只是把它当作传统语言学对等分析或文学翻译价值判断提供的新的语料库,那么其价值将会被大大削弱。沙维特(Zohar Shavit)指出,儿童文学是文化中多个系统之间关系聚合体的产物,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系统、教育系统和文学系统。正因如此,儿童文学为研究文化中复杂的结构和动态关系提供了绝佳的研究对象(Shavit,1992b:2)。儿童文学翻译涉及源语和目标语两个文学-文化系统及其关系,为翻译研究增加了新的维度。如果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考察儿童文学翻译的过程和作品,考察其符号功能,必定会丰富其研究内涵,实现其独有的研究价值。莱西(Gilian Lathey)强调说:这种在社会历史语境中研究翻译文本的描述性研究“被证明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特别有意义”(Lathey,2006:13)。
3 外语学术界中儿童文学翻译的描述性研究
从20 世纪80年代到21 世纪,外语学术界中儿童文学翻译的描述性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研究角度:以色列学者沙维特的研究在文化符号学理论框架内进行,基础是埃文-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同时借鉴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芬兰学者普尔蒂宁(Tiina Puurtinen)则在图里的翻译规范和文本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研究的理论框架内,从语言对比出发,结合语言学与翻译规范理论,用实证和语料库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意大利学者伊波利托(Margherita Ippolito)基于语料库研究方法进行翻译共性研究;还有德国学者奥沙利文(Emer O’Sullivan)的比较儿童文学研究,英国学者莱西的儿童文学翻译史研究,以及从社会学视角展开的研究等。
特拉维夫大学文化研究学院教授沙维特是较早从描述性角度进行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是外语学术界从事儿童文学翻译描述性研究最重要的学者之一。虽然图里也就童话翻译进行过个案研究,但他只是将儿童文学翻译作为一个案例,来证明其关于文学体系中翻译规范的观点(Toury,2001)。图里的学术兴趣并未真正放在有别于成人文学体系的儿童文学次级系统上,去探讨其独有的特点,真正将研究重点放在儿童文学系统上的是沙维特。她的重要论文“儿童文学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与功能”(Shavit,1981)以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为出发点,将儿童文学看作文学多元系统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提出了关于儿童文学翻译行为模式的若干观点,并主张这些行为模式对其他国家的儿童文学系统也普遍适用。沙维特认为:作为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边缘地位的一个系统,儿童文学的翻译受到多重摆布和约束;进入儿童文学系统的文本受到一系列制约。她提出,儿童文学翻译有两条原则:(1)为了让文本对儿童有用,为符合社会认为“对儿童有益”的东西而做调整;(2)调整情节、角色塑造以及语言,让其适合儿童的理解水平和阅读能力。这两条原则在不同的时代、因对儿童文学本质看法的不同而分别占支配地位,它们可能是互补的、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两条原则决定了选择什么文本来翻译,也决定了译者在多重规范制约之下,对文本的系统性操控。这些操控包括:(1)从属于现有的文学模式;(2)译者操控文本的完整性;(3)简化文本的复杂程度是儿童文学翻译中的主流规范;(4)基于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原因而改写;(5)受书面语、文学化语言等文体规范制约。论文通过译入希伯来语儿童文学的实例展示了这些操控行为是如何发生的及其背后可能的原因。
沙维特的专著《儿童文学的诗学》(Shavit,1986)在诗学和符号学理论框架中集中而深入地研究了儿童文学的内在本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普遍行为模式、儿童文学发展的特殊文化语境等重要问题。该著作第五章“儿童文学的翻译”以目标语为中心对译入希伯来语的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包括节译和改编)进行研究,从翻译的角度进一步讨论了因儿童文学在系统中所处位置所致的诗学约束的问题。沙维特认为,儿童文学翻译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儿童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边缘地位决定的,“对儿童有益”和“让儿童能懂”两条原则构成了儿童文学翻译的规范;在这两条原则基础上,目标语儿童文学系统中的现有文学模式、意识形态、伦理和价值观以及文体规范等都操控着译者,让他们对翻译文本进行自由度极大的删节、增添、改写。沙维特在差不多三十年后的论文(Shavit,2014)中进一步重申和阐发了这些主要观点,基本没有大的改变和增加。
虽然《儿童文学的诗学》(Shavit,1986)仅有一章专门讨论儿童文学翻译,但全书关注的儿童文学议题与儿童文学翻译息息相关,因为制约儿童文学创作的种种社会文化因素对儿童文学翻译同样也起着制约作用。沙维特指出,在所有制约因素中,最本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儿童文学的双重属性——即它既是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文学系统的一部分;这种双重属性可以解释儿童文学在一般文化中和特殊的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从属地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显然也是如此)不仅要忍受文化上的从属地位,而且在诗学方面还受制于比成人文学作家更多的强制性约束,只有服从这些约束,才能确保作品被儿童文学界接受。沙维特发现,为了克服从属地位和诗学制约问题,儿童文学作家找到了各种解决方法;本书第三、四章讨论了其中两个相互对立的极端解决办法,一种是“矛盾文本”(ambivalent text):作者以儿童读者为伪装,实则以成人为预设的目标读者,以此获得摆布现有儿童文学模式并提出新模式的自由;另一种则是有意识地放弃取得成人读者的承认,从而得以无视制约因素,沙维特称之为“非经典化儿童文学”(non-canonized children’s literature)。沙维特关于这两种解决方法(尤其是“矛盾文本”)的文学模式、文本结构、作者及读者等方面的分析,对于分析儿童文学翻译中的一些现象并提出解释性假设有一定启发。
沙维特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虽然她主张所有国家的儿童文学发展都共有普遍适用的结构特征和模式,并试图描述这种普适的发展模式,但这一观点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O’Sullivan,2005:45-46);而且,即使儿童文学发展模式相似,由于文化传统不同、加上时代发展变迁导致观念的变迁,她以特定时期希伯来语儿童文学为主要对象进行的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目的语系统中的儿童文学翻译,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此外,沙维特的研究中没有对儿童读者的年龄和儿童文学的子类别进行区分,从“简单和简化模式仍是绝大多数儿童文学的主流规范”(Shavit,1986:125)及其他关于规范的讨论可以看出,她所默认的“儿童”似乎指低龄儿童,而事实上,儿童文学下属的不同子类别文学模式(如图画书和儿童幻想小说)的差异是很大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阅读特点也不一样,有必要分开讨论其翻译规范。
芬兰约恩苏大学的普尔蒂宁是另一位致力于儿童文学翻译描述性研究的学者。她完全接受沙维特关于儿童文学翻译规范的“对儿童有益”和“让儿童能懂”两条原则,研究出发点和沙维特非常相似,但她大量使用了实证和语料库研究方法,对沙维特从理论推演出发、用个案分析说明理论问题的研究方式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也是她对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主要贡献。普尔蒂宁针对美国幻想小说《绿野仙踪》两个芬兰语译本的可读性进行的对比研究被图里称为描述性研究初始阶段比较研究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Toury,2001:72)。她其后的论文“翻译儿童文学: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Puurtinen,2006①该论文首次发表于1994年。)讨论了不同的翻译理论方法对一个儿童文学译本比较研究项目的适用性;研究对象仍然是《绿野仙踪》的两个芬兰语译本,整体上仍采取了图里的翻译规范文本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研究的理论框架,从图里、沙维特、克林伯格(Göte Klingberg)、赖斯(Katharina Reiss)、豪斯(Juliane House)、奥伊蒂宁(Riitta Oittinen)六位学者提出的翻译研究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角度考察了这两个译本,讨论了这些理论方法对个案的适用性,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得出了一些关于这两个译本的可接受性的初步结论。两个译本的出版时代、目标读者、功能都一样,但在文体风格,尤其是句法结构上却有显著不同。一位译者多用简单限定结构,从而造成流畅自然的动态风格;另一位译者则多用复杂的非限定结构,造成正式而静态的风格,增加了读者的短期记忆负担,减弱了文本的可读性。但该研究仅关注文体因素,未注意道德、意识形态等其他社会文化参数。
普尔蒂宁在其博士论文《翻译儿童文学中的语言可接受性》(Puurtinen,1995)、“芬兰儿童文学的句法规范”(Puurtinen,1997)和“儿童文学的句法、可读性和意识形态”(Puurtinen,1998)等论文中扩展了研究对象的范围,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增加了实证研究,并加入了意识形态维度,大大拓展了研究的深度。研究基于由英语原文文本、对应的芬兰语译文文本和芬兰语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构成的一个平行语料库和一个可比语料库,比较了一种句法现象——非限定性句法结构(以下简称NC),在翻译文本和原创文本中的出现频率,发现英芬翻译作品中NC 的出现频率显著高于芬兰语原创作品。普尔蒂宁对于研究结果做出如下解释:高频率的NC 可能被视作芬兰儿童文学一种翻译腔特色;也就是说,对于翻译作品和原创作品存在着不尽相同的句法规范,翻译规范可能允许更大程度的非限定性。翻译规范和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学系统中的地位有相关性,多元系统论(Even-Zohar,1990)认为,翻译文学通常占据外围位置,因而服从既有的规范和传统化的模式。儿童文学整体都占据着边缘位置,儿童文学译作理应占据最边缘的位置,遵循目的语主流规范。然而,考虑到芬兰语儿童文学中翻译作品比例巨大,其可能获取了一个更中心的地位,甚至可能是一种创新力量,也有可能儿童文学译者创造了(也许是无意地)新的规范,并可能逐渐影响原创作品。此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探讨英语和芬兰语儿童文学中反映意识形态的特定的微观和宏观语言策略,比较意识形态在英语和芬兰语文本中不同的语言实现方式,揭示意识形态因素可能对翻译进行的操控。这项实证研究从语言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了翔实的描述,并对芬兰语中翻译文本和原创文本的差异及翻译中的一些处理办法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
《简化、显化及范化: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儿童文学经典的意大利语翻译研究》(Ippolito,2013)是意大利学者伊波利托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基于语料库完成的儿童文学翻译的描述性研究。这项研究目标读者为8—10 岁儿童,包括20 本译入意大利语的童书和20 本非翻译的意大利语童书建成的可比语料库,旨在验证贝克(Mona Baker)提出的简化、显化、范化等“翻译共性”(translation universals,又译“翻译普遍性”)是否适用于译入意大利语的儿童文学翻译,并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分析了意大利“多元系统”中的儿童文学翻译。
21 世纪描述性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贡献来自德国学者奥沙利文的《比较儿童文学》①本书最初由德文写作,出版于2000年;英文译本出版于2005年。(O’Sullivan,2005)和英国学者莱西(Lathey,2010)的儿童文学翻译史研究。奥沙利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考察儿童文学的翻译,并以丰富的历史个案研究为儿童文学的国际交流史提供了新的视角。这是一部比较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作品,既有对比较儿童文学学科的全面探讨,也有深度研究,由于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密不可分,本书也集中深入地讨论了儿童文学的翻译和接受,分析了译入语文化中的规范和价值观、翻译过程中译者出于对儿童读者接受能力的揣测而进行的改写和调适等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并用众多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案例展示了译著为何能特别清楚地反映出特定时期、特定文化中的儿童文学观和儿童观,以及为何儿童文学领域和一般文学领域中的翻译实践差异如此之大。
奥沙利文的另一大贡献是结合叙事学和翻译研究,用叙事学理论支撑的文本分析充实了关于社会、文化、文学、教育规范影响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层面:通过译者在翻译话语中的现身来展现儿童文学翻译受到的各种摆布。奥沙利文重点讨论了“隐含译者”和“隐含读者”的概念,她用多个案例分析了译者声音体现在译本的副文本和文本中并淹没了源语文本叙事者声音,指出译者的声音反映出译者对目标读者的预期和主导儿童文学翻译的规范。译者所处的文化和时代的儿童观(notion of childhood)决定了译者所持的儿童形象(child image),从而影响译者对隐含读者的建构,使得目标语文本和源语文本的隐含读者不一样,这种差别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又由于儿童文学翻译中涉及成人(作者、译者)和儿童(读者)的不平等交际而特别明显。
英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专家莱西的著作《译者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角色:隐身的讲故事人》(Lathey,2010)是一部开创性的儿童文学翻译国别通史,历时性描述了英国9 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以译者为主线,将译者置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译者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作用,勾勒复杂翻译活动的整体图景。这部著作考据翔实精深,在按历史年代对儿童文学翻译活动进行全景式描绘的同时,也对女性译者、作为中介者的译者、重译等重要问题以专门章节聚焦讨论,还通过与几位知名译者的直接沟通来描述她们的翻译活动、翻译行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看法、翻译策略等。该研究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和翻译史学的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社会学视角是近年来翻译研究中新兴的理论视角,近年来也开始有研究者将其应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中国台湾学者钟玉玲(Yu-Ling Chung)的《台湾的翻译与幻想文学》(2013)虽然严格说来不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但其研究对象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有所重叠。该书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惯习/资本/场域框架,将中国台湾20 世纪末开始的幻想文学翻译的兴起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开展研究,以独特视角探讨了翻译“场域”中不同因素之间动态的复杂关系,重点讨论了作为“文化经纪人(cultural brokers)”和“社会网络中介者(social networkers)”(Chung,2013:12)的幻想文学译者,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值得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借鉴。从社会学视角进行研究的还有郭罕圆(Kwok,2016),她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四种汉语译文为个案研究对象,从社会学角度讨论了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忠实问题,对比了克林伯格提出的忠实于源语文本和奥伊蒂宁提出的忠实于读者的原则,主张后者的对话性观点对儿童读者更为有益。
还有一些从描述性角度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个案研究:本-艾瑞(Nitsa Ben-Ari)的“儿童文学翻译规范中的说教与教育倾向(1992)认为儿童文学翻译中,教条与服从的规范比一般文学中更为突出,且在该德语-希伯来语儿童文学翻译个案中被意识形态上的教育倾向放大。拜斯马特·埃文-佐哈尔(Basmat Even-Zohar)的“希伯来儿童文学中的翻译政策:林格伦个案研究”(Even-Zohar,1992),主要讨论了希伯来语书面语和口语分离的情况下,处于多元系统边缘的希伯来语儿童文学的翻译规范问题。梁文骏(Liang,2007)关于儿童幻想小说翻译的描述性研究讨论了“哈利·波特”系列丛书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研究异化和归化策略在儿童读者中的接受情况,并在中国台湾的翻译儿童幻想小说这个多元系统中考察这些翻译策略是符合现有规范还是创新之举。研究发现:由于儿童幻想小说在中国台湾的翻译儿童文学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翻译策略也是以充分翻译为主,但儿童读者对此并不十分欢迎。
芬兰学者奥伊蒂宁的《为儿童而译》(Oittinen,2000)并非鲜明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但较有代表性。奥伊蒂宁本人同时是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和插画家,她的研究关注儿童受众对于翻译文本的可能的反应,并主张以儿童为中心的翻译途径。《为儿童而译》在翻译功能理论、接受美学、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基础上,关注儿童文学的译者、读者和翻译情境,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为儿童而译”的观点,将翻译视作不光包含文本,而且涉及读者、作者、插画作者、译者、出版商等多种因素在内的对话情境。奥伊蒂宁将研究的重点投向译者,关注译者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他们的儿童观——如何参与到翻译过程中;同时她对儿童读者和儿童阅读的重视是此前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所缺乏而急需的。从她对插图和出声朗读两方面因素的强调,可以看出她研究中的儿童受众主要是学龄前儿童,但她似乎认为儿童文学是同质的,由此忽略了儿童文学这个复杂广泛的研究领域里年龄、文体、功能、文本类型等各方面的差异,将复杂的问题简化了。此外,奥伊蒂宁给出了许多译者“应当”如何与目标语文化中的儿童沟通的建议,选择了偏向规约性的研究途径。
外文中关于描述性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除了莱西的国别翻译史研究外,其他研究的语言方向均为英语译入非英语,这与各国儿童文学翻译的现状有关,如芬兰和意大利儿童文学中,翻译作品占比都非常高,前者“翻译作品占每年出版的儿童文学的65-70%,且翻译作品中半数来源于英语”(Puurtinen,1998:526),后者在1997—2009年期间翻译作品也约占整体儿童文学出版的半数(Ippolito,2013:6)。因此,这些特定国家和语言的儿童文学翻译成为尤其值得研究的对象。中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繁荣的现状与其十分类似,也因此使得普尔蒂宁等非英语国家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者的相关研究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有较大借鉴作用。
4 中文学术界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描述性研究①本文中所说的“中文”研究主要指中国学者在国内用中文发表的研究,他们用英语发表的研究则归入上一节。
中文学术界关于儿童文学的翻译研究始于20 世纪80、90年代。早期研究以探讨语言层面上“应该怎么译”为主,如徐家荣的论文“儿童文学翻译对译文语言的特殊要求”(1988)。现有资料显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专著仅有寥寥几部,其中明显属于描述性研究的仅有一部:李丽的《生成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1898—1949)》(2010);进入21 世纪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论文数量激增。在CNKI 上的检索显示,1984—2013年间发表的457 篇儿童文学翻译论文中(张静,2014:107),描述性翻译研究占73 篇,涵盖了翻译规范、多元系统论、操控理论、意识形态和儿童观等主题。有几项描述性翻译研究分别聚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几个重要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
从晚清到五四是中文学术界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最为关注的历史时期。
秦弓(2004a,2004b,2004c,2004d)对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从选材、来源国家、文学种类、翻译方法、语言特点乃至装帧印刷各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述,探讨了这些特点背后当时译者、文学家与评论家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看法,并对重要的儿童文学原作者(如安徒生、王尔德),译者(如鲁迅、周作人),作品(如《爱的教育》《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在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领域是开创性的,考据翔实,较为全面;但它以描述翻译活动全景为主,对于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挖掘较少。
宋莉华(2009)对晚清到五四时期的西方来华传教士从事的儿童读物的编译与出版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据、梳理和介绍,认为传教士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带来新的文学内容和艺术手法,并进而带来了西方现代的儿童观和教育理念,催生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和现代儿童观的萌发,形成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以上研究都侧重于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的描述,属于翻译史研究。
关于译介学研究方面,应该提及张建青(2008)的博士论文《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译介学视野下的晚清儿童文学研究》。作者以晚清新的“儿童文学观”萌生发展为主线,串联起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创作,从而确定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具体时间为1908年,标志为孙毓修编纂的《童话》第一编《无猫国》。
文军、王晨爽(2008)对抗战时期(1931—1945)的外国儿童文学译介情况按照国别、文体等类别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分析了这段时期儿童文学的译介特点及外国儿童文学译介对抗战儿童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其他译介研究则聚焦于儿童文学翻译史上较为重要的译者及重要译作,如朱嘉春(2019)考察了清末民初出版家孙毓修与其编译的《童话》丛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重构了这位“开了中国儿童文学之先河”(朱嘉春,2019:120)的译者的翻译活动。作者认为《童话》中文本的编译策略体现出译者“为儿童而译”的宗旨,但同时译者加入其中的大量训诫话语又反映出当时儿童文学翻译的“成人本位”。
此外,李青(2016)对于包天笑译介教育小说《儿童修身之感情》的研究、张建青(2019)对于周桂笙儿童文学翻译活动的研究也都是对我国儿童文学翻译萌芽时期重要译者和作品的描述性研究。
李丽(2010)的《生成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1898—1949)》以多元系统论和勒菲弗尔三因素理论为出发点,使用描述性翻译研究、接受美学和比较文学接受学的研究方法,对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的生成、接受与影响进行考察,是一项较为成熟的描述性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作者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数据整理,梳理出“清末民初/ 民国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编目”,采用多重视角考察了“生成—接受—影响”的连续整体。但在接受研究部分,对于儿童文学最重要的读者——儿童的论述不足,被成人读者所淹没。可以推想由于年代久远(或许还有儿童观的原因),直接史料难以获得,甚为遗憾。
如上所述,中文儿童文学翻译描述性研究聚焦晚清至五四、抗战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前这几段历史时期,对1949年之后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较为薄弱。“从多元系统论视角对儿童文学翻译的重新审视”(谭敏、赵宁,2011)一文对埃文-佐哈尔和沙维特的研究和理论观点进行了较为详尽深入的介绍和阐发,但该文主要讨论文学模式在儿童文学系统和成人文学系统中的转移,基本没有涉及儿童文学翻译实践,更没有涉及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实际情况。近年来儿童文学翻译规范研究中颇受关注的是徐德荣、江建利(2011)对《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翻译的个案研究,该研究通过比较、分析不同时代的译者在翻译同一部作品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发现在词汇、句法、某些修辞等语言层面上,不同时代的译者多采取相似的翻译策略,这是因为他们遵循相同的可读性期待规范和忠于目标读者的责任规范,而在文化负载词、一些特定的修辞及语篇层面上则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这是遵从了不同的翻译规范,受到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因素及目的语文化的主流翻译期待规范的影响。该研究还认为,译者会受到不同的翻译规范的制约,这些翻译规范可能互相抵触,而译者有着自己选择翻译规范的能动性。该研究将文本中不同因素分开考虑,分别考察具体翻译策略和翻译规范的历时性变化的方法操作性较强,对儿童文学翻译规范研究方法有参考价值。
5 儿童文学描述性翻译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国际上英语学术界的儿童文学描述性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规范、多元系统论和翻译操控论的理论框架中,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早期以个案研究、文本研究为主,到了后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更新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思路,语料库方法被越来越多地使用,新的研究视角也被引入。但应注意的是,翻译研究的人文属性决定了不应过度依赖量化研究与语料库方法,量化研究始终应当与质性研究结合,与个案及文本分析相结合,相互补充。前述沙维特在80年代提出的儿童文学翻译规范的两条原则及儿童文学译者在多重规范制约之下,对文本的系统性操控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而其后普尔蒂宁等学者采用的基于语料库的儿童文学规范研究方法和钟玉玲等学者采用的社会学研究视角也值得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者借鉴。
与国际上英语学术界相比,中文儿童文学描述性翻译以翻译史研究、译介学研究和小规模的个案研究为主,主要聚焦中国晚清至五四、抗战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前这几段历史时期,对中国1949年之后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较为薄弱。翻译规范研究,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儿童文学翻译规范研究,则更加稀少。1978年以来,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朱自强,2014:5),儿童文学翻译也随之经历了一个飞速发展时期,这段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规范具有研究价值。
现有的中外文儿童文学翻译描述性研究几乎都默认儿童文学是一个同质的笼统整体,但笔者认为,对儿童文学的翻译进行描述性研究应包括对儿童文学细分后的子类别研究,因为儿童是人一生中身心发生急速、巨大变化的时期,儿童文学读者年龄的差异特征跨度较大,其阅读能力、阅读习惯、阅读心理等随时发生变化,因此针对不同年龄阶段读者的儿童文学文体类型、特征及翻译中所关注的重点也会存在较大差异,如儿童幻想小说和图画书在儿童文学中是两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子类别。以图画书为例,国外近年已有学者从符号学与多模态的研究视角对图画书翻译展开研究(Oittinen et al.,2018)。而在国内,2000年前后儿童幻想小说作为独立文类的确立和图画书(即“绘本”)的兴起也是原创儿童文学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最为突出的两个新趋势(朱自强,2014:212),但这两个子类别都强烈依赖外国同类型作品的翻译才得以萌芽、发展和兴盛。20 世纪末以来儿童幻想小说和图画书的翻译热潮填补了中国儿童文学子系统中这两种模式的空白,并影响、催生了同类型的原创作品。这些独特现象很值得我们展开描述性翻译研究。
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内容丰富,视角多样,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主要梳理了中外文主要的描述性研究,其他类型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代表性成果只能留待另文述评。即便如此,描述性研究也难免挂一漏万,难以尽述。如本文梳理的研究主要是产品导向(product-oriented),少数为环境导向(context-oriented),而过程导向(process-oriented)和功能导向(function-oriented)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较为欠缺,或可在今后进行梳理。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