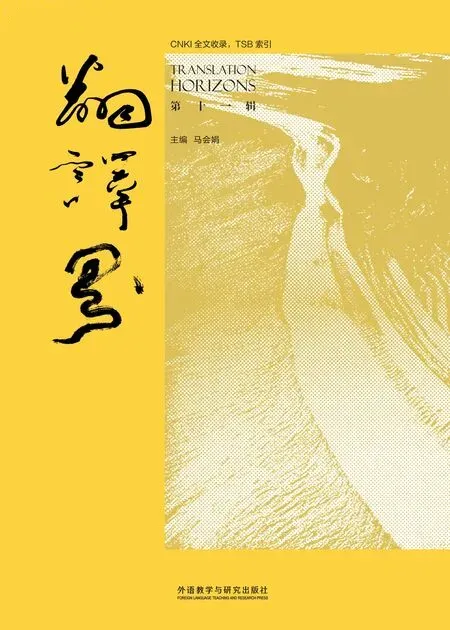“摆印善书,散播天下”:作为翻译出版赞助者的广学会
杨华波
厦门大学
1 引言
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是清末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组成的出版机构,由1884年设立的“同文书会”改组,1887年成立于上海,1894年改名为广学会。因战时需要,广学会曾于1941年搬迁至成都,并于1942年9 月与其他教会出版机构一起组建为基督教联合出版社。抗战胜利后,广学会搬回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于1956年与中华浸会书局、中国主日学合会、青年协会书局等出版机构合并组成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广学会的历史始于1887年,止于1956年,前后共计70年。作为较早转变传教观念的传教士之一,同文书会创始人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深知通过翻译可以将更多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输入中国,启发民智,从而间接推进在华传教事业。他曾在《同文书会实录》中宣称,创立此会是因为目睹了中国人的不足之处,决心译介西学以补其不足,因而“摆印善书,散播天下”(韦廉臣,1890)。基于这一共识,广学会历年译印了大量西学书籍,特别是1891年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接任督办(后改称总干事)后,他和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传教士在华人笔述者的帮助下翻译出版了众多关于西方历史、政治和宣传社会变革的书籍,以期影响中国士大夫阶层和读书人,推动中国变法维新。戊戌变法时期,广学会的社会影响力达到顶峰。清朝灭亡后,广学会的出版重心逐渐转向宗教读物,影响力也日渐式微。1919年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接任总干事之职后,广学会差不多完全转向翻译出版基督教义和灵修类书籍。由于广学会不仅是传教组织,同时也是出版机构,翻译和出版对其而言是一体两面的,因此本文将其翻译活动和出版活动放在一起讨论。
基于广学会在近代政治、文化、宗教等领域的影响力,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从整体上关注其出版活动,如熊月之(2011)重点考察了广学会1900年前的西学出版活动,李志刚(1997)探讨了广学会出版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转变,而何凯立(2004)则梳理了广学会1912—1949年的出版活动;第二类是以某一译作为核心的研究,如赵建民(2001)、卢明玉(2012)对《文学兴国策》的研究,刘雅军(2004)对《泰西新史揽要》的研究;第三类则是以译者为中心的研究,如高黎平(2006)对林乐知的研究,陈建明(2018)对华人编辑谢颂羔的研究。总体而言,现有对广学会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集中于其清末的翻译出版活动,对1911年后的文字事工着墨不多;已有成果多为历史领域的研究,专门研究其翻译出版活动的论著相对较少,缺少翻译研究视角下的专论。因此,本文尝试从翻译研究的视角,利用安德烈·勒菲弗尔关于翻译赞助者的理论,不仅考察广学会在清末的翻译出版事业,同时也关照其在进入民国后的翻译出版活动,以期从整体上系统梳理广学会对翻译出版活动的赞助作用。
勒菲弗尔(Lefevere,1992:15-17)在其《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书中将赞助者定义为拥有可以促进或阻碍阅读、写作或改写权力的个人或机构,认为赞助者主要通过其代表的意识形态和经济上、地位上的赞助达到操控翻译活动的目的。赞助者对翻译的操控作用主要体现在:从意识形态上决定选题和译著的形式,即哪些书籍会被翻译出来,采取何种形式;从经济上确保译者得到一定的酬劳,保障其生活;此外,赞助者还可以帮助译者在机构内部或社会上获得一定的地位。当以上三个要素集中于同一个赞助者时,我们说赞助者是不可分的,反之,赞助者是可分的。赞助者主要从外部系统影响翻译活动,内部系统的诗学规范(poetics)也可以通过译入语的文体特征、概念体系、读者的阅读习惯等方式对翻译活动施加影响。外部系统和内部系统彼此不是隔绝的,二者密切相关。在外部系统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赞助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往往可以通过支付版税或雇佣专业人员,从而影响甚至决定译入语的诗学规范。
2 广学会翻译出版活动的分期
晚清是域外知识大规模输入的年代,广学会积极融入这一潮流,其在清末译介的内容侧重于历史、政治、地理等人文社会科学,也有少量内容涉及数学、化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宗教类书籍则不占多数。民国后,广学会调整了翻译出版方向,译印了大量布道或宣传教义的宗教书籍,教会出版机构的特色更加明显。广学会在七十年的历史中充分发挥了翻译出版赞助者的作用,其出版物总量远远超过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同时期的出版机构,达两千多种①王树槐(1973)统计出广学会1887—1911年的出版物为461 种(其中,纯宗教性书籍约138种,占总数29.93%;非宗教性书籍约238 种,占总数51.63%;含宗教意味同时含有其他内容的书籍约85 种,占总数18.44%)。何凯立(2004:93)统计出广学会1912—1949年出版的新书数为1,610 种,但缺失1941—1944年的数据,而陈喆(2004:46-47)则统计出广学会1941—1944年在成都共出版新书71 种。因此,综合三者的统计数据可知,广学会在1949年前总计出版新书2,142 种。但是,这个统计数量并不准确,因为在1956年合并前广学会仍然有零星出版物问世。此外,可能存在一书多名、再版或将图册算作新书的情况。由于目前尚无完整的广学会出版目录,本文暂采用以上数据。,其中译著占有极大的比重。李志刚(1997:175)就曾指出,广学会“历来出版的书刊,以翻译居多”。虽然目前尚无完整的广学会出版目录,无法准确统计广学会出版物中译著的数量和比例,但总体来看,译著是广学会出版物中的主流。之所以要对广学会的出版物进行分期,是因为广学会的翻译出版活动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翻译主题的选择、译者聘用、语言风格和翻译策略等方面均随中国局势的演变而不断调整(同上:163-178),而广学会在不同时期对翻译出版活动的赞助方式及力度也不尽相同。本文对翻译采取较为宽泛的定义,将《中东战纪本末》和《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等编译性质的书籍也归为译著。此外,考虑到广学会所属报刊上广受好评的译文往往会结集再版,因此本文只讨论其以书籍形式出版的单行本译著。
广学会的翻译出版活动可划分为三个时期②关于翻译活动的分期,本文认同邹振环(2017:7-8)的观点,不以政治事件为唯一标准,而是充分考量广学会翻译出版活动自身的特点。因此,第二时期的结束时间被划分为1940年而不是1937年上海沦陷之时,因为广学会在1937—1940年内的出版活动与此前相比并没有下滑,甚至呈现增长态势,直到1941年迁至成都后才陷入低潮(何凯立,2004:93)。此外,不同于以往研究将广学会1911年后的翻译出版活动看作一个整体(如李志刚,1997),我们认为广学会1940年前后的活动存在明显的分界线,1940年前不管是出版新书还是重印旧书都维持较大的规模,1940年后全面下滑,因此有必要对其1911年后的翻译出版活动进行二次切分。,即1887年至1911年的第一时期,1912年至1940年的第二时期和1941年至1956年的第三时期。第一时期从1887年同文书会创办开始至1911年。同文书会自其创立后即确立了翻译传播基督教和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宗旨,李提摩太就任督办后走上层路线,推动广学会译印了大量历史、政治以及鼓励变法的著作,如《泰西新史揽要》《文学兴国策》《列国变通兴盛记》,宗教书籍相对较少。据王树槐(1973)统计,清末广学会所印行的四百多种著作中,非宗教性书籍占比超过一半,而纯宗教性书籍仅占30%左右。第二时期从1912年民国建立至1940年广学会迁往华西前为止。此一阶段,宗教类著作的翻译出版逐渐增多并成为主导,虽然中间经历五四运动、非基督教运动和本色化运动,但以宗教读物为重点的方针没有改变,出版了“旧约释义丛书”“灵修生活丛书”等系列著作。第三阶段从1941年开始至1956年广学会退出历史舞台。由于国内战火纷飞,再加上经济困难,广学会的翻译出版活动几乎陷于停滞,1945年抗战胜利后虽然重新搬回上海,但直至1956年,广学会的翻译出版事业仍然没有太大起色。在后两个阶段,广学会出版物中宗教性书籍占据绝对主导,非宗教书籍所占比例不到10%(何凯立,2004:91)。从整体上看,广学会的译著在第一时期以西学知识为主,虽然数量不多,但影响力巨大;第二时期内专注于宗教读物,数量虽然大为增加,但影响力明显下滑;第三时期则属于勉力维持的阶段,鲜有译著问世。由于第三时期内广学会的翻译出版活动乏善可陈,因此后文将重点讨论广学会在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内的赞助者角色。
3 广学会对翻译出版活动的赞助
翻译出版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相关个人或机构的赞助,广学会对翻译活动的赞助作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在意识形态方面体现为对翻译主题和内容的选择、审查;(2)在经济方面体现为对译者或译著出版经济上的资助;(3)赋予相关翻译出版推动者和译者一定的地位。由于广学会不同时期内的翻译出版活动具有不同的特点,广学会的赞助作用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下文将基于已划分的三个时期来探讨广学会的赞助作用。
3.1 意识形态下的内容选择和审查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而是受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在众多的因素中,意识形态作为“看不见的手”可以干预主题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特别是对某些新概念的阐释(王东风,2003)。为了更易于让中国人接受,广学会在译著中借用了较多中国旧有的概念,以迎合主流的文体习惯,但具体的翻译策略和表现形式更多体现在诗学范式方面。虽然广学会为了适应政治环境的变化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做了一些改变,但它最核心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基督教文明——却从未改变。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主题或原文本的选择。晚清译印西书影响较大的三家出版机构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和广学会中,尽管传教士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学会内都堪称中坚,但由于其背后的支持力量不一样,意识形态和目的不同,造成二者在选题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前者是中国政界和学界中有识之士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自强而设立的,在清政府的自强意识下以求增强国力,主要出版实用型的科技书籍,而后者则是由新教传教士、外国商人和外交官员建立的传播基督教的出版机构,因此其出版物以通俗科学知识和宣传基督教义的书籍为主。
关于广学会翻译出版活动的意识形态,毫无疑问是基于其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政治立场的(何兆武,1961)。林乐知等人曾尝试将清政府变成大英帝国的保护国,于是出版《印度隶英十二益说》造势。为鼓励清政府变法维新,广学会又曾译印《英兴记》《条陈改政之急务》《富国养民策》等书籍。然而,广学会的政治立场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时期会随政治局势的变化有所转变。民国建立后广学会式微,但其明显转向当政的国民政府,出版过《共产主义之研究》《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等书,反对共产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学会的意识形态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转而出版《无产者耶稣传》。但是,以上明确表明政治立场的书籍数量极少,是迫于政治形势的权宜之计,主要是为了迎合主流的意识形态以便于传教。纵观广学会七十年的翻译出版轨迹,其核心意识形态仍然是资本主义基督教文明。
广学会之所以在第一时期注重通俗性知识的译介,是因为这迎合了广大中国人在国门大开和民族危机加剧之时,迫切需要学习西方知识以自强自救的心理,通过提升华人知识水平,进而推进传教事业。其实,在中国传播西学并不新鲜。明末利玛窦(Matthieu Ricci)等传教士即通过这种方式来争取明朝士大夫的支持,清末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也通过创办报刊宣传西方史地知识。因此,广学会翻译出版西学书籍的手段至多是传教士“科学传教”传统的延续。尽管广学会也会引介国外最新思想,如在《大同学》一书中介绍马克思学说,但并不系统,因为这些思想并不利于其传播资本主义基督教文明。可见,即使是引入西学,也是有所侧重的,不同于严复译介西方民主启蒙思想。广学会已出版的西学书籍也多用宗教学的观点进行阐发或解释,以求彰显“上帝的全知全能”,如韦廉臣在《格物探原》中将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归因于“上帝”的存在,《文学兴国策》则认为中国革兴教化的道德基础是基督教等。
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的失败标志着广学会上层路线的破产,其读者对象也由士大夫、知识分子转向下层信教群众和普通民众。此后,随着海外留学生逐渐肩负起传播西学的责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民营出版机构开始崛起,再加上教会内部对于宗教读物需求的增长,广学会转而在第二时期和第三时期专注于出版宣教和灵修类书籍。宗教书籍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圣经教义或圣徒事迹,直接体现了广学会的意识形态和翻译出版目的。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广学会翻译出版中的变与不变,即变的是随时势适当调整其翻译出版活动,不变的是其最终目的,即传教。诚如李提摩太所言,广学会的“最大目标就是推广基督教文明”(转引自顾长声,2004:154)。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还表现在对翻译出版内容的审查。在出版物的译印方面,广学会拥有一套日渐完善的流程和机制,以对翻译出版内容进行评议审核,从而确保符合其意识形态的作品面世。在李提摩太担任总干事期间,一切出版事宜均须由他决定。等到他于1916年卸任后,广学会内部成立了一个由总干事、编辑人员和教会领袖组成的出版委员会,该委员会直属于董事会,其职责是“挑选出准备出版的作品,审核所有送来的手稿与书籍,推荐可以印刷的手稿与书籍,决定发行的数量与售价,从整体上监督出版部的日常工作”(转引自何凯立,2004:91)。20 世纪30年代,广学会还制定了审核稿件的详细流程,其中包括:“所有来稿都须送交两个独立的阅稿人,通常其中有一人是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待他俩送来审阅报告后,部门委员会再在此基础上制定明确的建议书,决定采用或是退还来稿,提交给最高委员会最后决定”(同上:92)。可见,广学会对于翻译出版工作是非常审慎的,从其设置专门的出版委员会并对来稿进行高层评议可知,意识形态的把控极其严格,而广学会出版的全部译著,无不是基于其意识形态并经过严格评审后的产物。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广学会在三个时期的内部编辑人员构成上一窥其意识形态的稳固性。作为教会出版机构,广学会在第一时期的主要撰稿人是西方传教士和华人笔述者,传教士的意识形态自不必说,即使是早期发挥巨大作用的华人笔述者任廷旭、范祎等人最终也受洗成为基督徒。第二时期,随着本色化运动的开展,华人独立译述开始增加,但他们也是谢颂羔这样的教内人士。进入第三个时期,广学会的本色化进一步加深,华人董事和干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们的身份也基本是基督徒,鲜有教外人士的参与。
3.2 对译者和出版物的经济支持
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一直存在强调意识形态和诗学、忽视经济要素的问题。事实上,经济要素对于翻译活动的整个流程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耿强,2017)。由于广学会本身既是一个翻译机构,也是一个出版机构,因此它对翻译活动的经济支持除了支付译者薪酬以保证他们的生活外,还表现在提供资金以保障译著的顺利出版发行。在广学会的资金来源中,尽管书籍和报刊的销售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其最主要的收入却来自捐款。1891年至1911年间,广学会的售书所得约33 万元,占总收入的43%,捐款及其他收入共约41 万元,广学会之所以得以维持,主要依赖捐款(王树槐,1973)。捐款中虽然有私人捐助,但主要来源却是西方各差会的捐款,其中尤以英国为多,超过全部经费的一半,早期主要来自英国格拉斯哥基督文化社(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和妇女会(Ladies Branch)等机构。20 世纪20年代以后,来自美国的资助逐渐增多(何凯立,2004:83)①事实上,作为翻译出版赞助者的广学会背后还存在着其他赞助者,如基督教在华各差会。各差会不仅提供经费,其意识形态和传教方式也会影响广学会的翻译出版活动。但是,这一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如李提摩太虽属英国浸信会,该会却并不支持李提摩太通过传播西学知识的方式传教,广学会之所以会打上李提摩太的烙印,是与李提摩太个人富有前瞻性的眼界分不开的(郭至汶,2019)。由于广学会背后的赞助者较为复杂,非本文所能详述,因此只集中谈论广学会自身的赞助者角色。。
在译者的聘用和薪酬方面,由于传教士在译书过程中往往不具备扎实的汉语写作能力,而中国译者大多不谙西语,因此明末西学传入时的“西译中述”模式在清末仍相当普遍(于醒民,1985)。为了翻译书籍,广学会内的西方传教士不得不依靠华人笔述者的襄助。广学会作为一个传教士出版机构,其对西人和华人译者的经济支持各不相同,初期广学会的薪水“多为付诸中国助手之用,传教士不支薪水,其生活由原教会维持。少数雇用之西人,虽然领取薪水,但为数不多”(王树槐,1973:207)。李提摩太、林乐知、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花之安(Ernst Faber)等传教士口述者均由基督教各差会派遣,其薪水由各自所属的差会提供,因此不领广学会的工资。而华人笔述者则不同,他们多为绝意仕途的旧式文人,之所以甘愿辅助传教士翻译书籍,经济上的原因是很重要的。广学会提供的薪水对他们来说有足够的吸引力,可以保障他们的生活。
李提摩太担任广学会总干事之时,其手下有专门的编辑团队为他服务,这些编辑专职从事翻译或行政工作(何凯立,2004:91)。从李提摩太翻译出版的众多著作中可知,他们基本上是熟稔汉语的华士,包括蔡尔康、任廷旭、范祎等人。李提摩太因为自身汉语水平的限制,往往需要借助这些华士对译文进行修改润色。发表于1895年的《广学会第七年综纪》记载,当年“报馆费用并华友脩金三百四十二元三角八分”。其中,两位“华友”的“束脩”在1895年前都是由李提摩太负担,但此后其中一人的酬金归广学会支付(铸铁庵主人,1895)。此外,1898年的《广学会第十年管收除在四项清帐》显示,上一年“付蔡先生十一个月束脩(为)三百十五元”,而“会报馆两位先生十一个月束脩一百七十六元四角”(广学会,1898)。蔡先生即为蔡尔康。作为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得力助手,他协助二人翻译了《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大同学》等一系列颇有影响的著作,而他的收入也远多于报馆中的其他华人编辑。由此可见,广学会对于华人译者,尤其是出力颇多的译者的经济待遇还是较为优厚的,而正是这样优厚的待遇,才保证了华人能投身于广学会的翻译工作,也才造就了广学会在清末的强大影响力。笔者发现,广学会在清末的华人笔述者多达三十余人,除了蔡尔康、任廷旭、范祎外,还有魏彭寿、邱起霖、曹曾涵、徐惟岱等人,甚至还有清末著名文士王韬。他自陈之所以协助传教士译书,乃是“迫于衣食”(王韬,1987:83)。后期,特别是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之后,尽管华人译者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更多地开始独立译书,但广学会对译者经济上的赞助作用却呈减弱的趋势,因为受教会差派的华人译者和编辑逐渐增多,作为专职的传教人员,他们的薪水均由所属的差会负担,如谢颂羔在广学会内的活动就由加拿大长老会提供经费(陈建明,2018)。
由于广学会是一个非营利性质的教会出版机构,因而其对翻译的赞助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译著的出版和发售方面。第一时期因为经费较为充足,又走上层路线,为了促进新知识的传播,广学会在各省乡试考场上免费赠送了大量出版物,既有西学读物,也有宗教小册子(王树槐,1998:41-42)。第二时期,由于上层路线的失败和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开展,其出版开始集中于宗教读物,但教会书籍仍多是免费赠阅或亏本销售。抗战时期,由于各地战乱,广学会书报销售不畅,同时又失去教会的资助,对翻译出版活动的赞助处于低潮,只能在西南地区和其他教会出版机构联合成立基督教联合出版社,借助该机构的资金援助出版了少量著作,而其中译著的数量更是少之又少。受战事影响,1938年上半年的广学会书籍销路不畅,收入锐减,工作人员只有从前的1/3,勉力支撑。1941年广学会出版新书62 种,画册2 种,重印122 种;1942年还能出版新书8 种,重印2 种。其后则是每况愈下,1943年仅出版新书1 种,画册2 种;1944年没有新书出版,仅重印1 种,出年历1 种。到了1945年,仍旧没有新书出版,且只剩年历1 种(陈喆,2004:46-47)。由此可见,受时局和经费的影响,广学会赞助翻译出版的力度在不同时期是有差异的。
广学会还通过出版其他机构的译著间接促进了翻译活动的开展。近代来华传教士之间因为千丝万缕的关系和共同的传教目标,不同出版机构因此存在着版权共享的情况。广学会在清末的翻译重心在历史、地理和政治等社会科学领域,相关译著多为独立译出,而数学、化学、天文等自然科学译著,如《代微积拾级》《化学须知》《天文揭要》,则大多来源于墨海书馆、益智书会等其他教会出版机构(杨华波,2019)。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和销售渠道,广学会刊印或销售其他出版机构的译著并使之流通实际上也是赞助了翻译活动的开展。
3.3 给予翻译推动者和译者相应地位
由于广学会是一个兼具翻译与出版的机构,因此它既可以对译者,也可以对一切有利于其翻译出版活动的人进行地位上的赞助。作为一个由在华传教士、商人和外交人员成立的出版机构,尽管广学会的具体事务由传教士操持,但商人和外交人员也十分重要。早期广学会的组织由会员和董事会组成,会员可以通过订阅《万国公报》或捐款获得这一身份,而决定会务的董事则一般由传教士、大商人或外交人员构成。商人为广学会提供必需的经费,在会内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因而人数也较多。在1890年的39 名董事中,商人多达16 名,而传教士仅占9 名(王树槐,1973)。此外,外交人员在广学会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并推动会务的顺利开展,广学会选择给予他们一定的荣誉,从而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扩大出版物的影响。广学会成立初期经常出现董事会成员人数多于会员的情况。因此,“所谓该会之董事,似有不少人系因其声望而被罗致者,并非自动加入该会为会员”(同上:195)。广学会通过名誉或地位赞助其翻译出版事业最典型的案例,是于1888年由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司长的赫德(Robert Hart)出任会长多年,直至其1911年逝世为止。之后,“继任广学会会长的不是英国或美国驻华公使,就是英美驻沪总领事,或上海工部局总董”(江文汉,1964:17)。可见,广学会的董事或会长可以作为一项荣誉赠予那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外交人员,而他们的影响力则有利于广学会的译著直达官绅等社会上层人士。
作为广学会中主持实际工作的督办或总干事,这一身份和地位同样会对翻译出版活动产生一定的赞助作用。王树槐(1973:224)统计发现,广学会1897—1911年间发行一万册以上的书籍共计24 种,其中督办李提摩太之书有12 种之多,“李提摩太身为督办,不免多印自己的书,此乃由于主观价值之判断所致”。客观上说,广学会赋予李提摩太督办之职也是他得以大量印刷出版译作或著作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广学会第一位华人总干事朱立德的翻译出版活动中也有所体现。朱立德于1937年8 月开始担任广学会总干事之后,仅1939 和1940年两年内他在广学会就至少编译了《列王纪释义》等8 种书籍①据我国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https://library.hkbu.edu.hk/)和国家图书馆(http://www.nlc.cn/)在线检索(检索时间:2017年12 月18 日)。,这不能说没有总干事这一职位带来的某些赞助作用。虽然广学会历来是传教士主导的教会机构,但华人通过其努力和工作上的贡献往往也会得到他们的认可,从而在会内或是其相关机构内担任一定的职务。作为传教士译书或撰文中须臾不可离的助手,清末华人笔述者可以通过协助华人译书得到某些尊崇的地位,如蔡尔康就因其辅助林乐知译书办报而升任广学会会刊《万国公报》的主笔。可见,为了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广学会积极吸纳华人进入管理层,通过给予译者一定的地位以推进广学会事业的发展。
据此我们可知,对于广学会内部早期的华人编辑而言,广学会同时主导了意识形态和对他们经济上、地位上的赞助,因此是不可分的。但对于大多数的传教士译者或编辑来说,广学会的工作不能为他们提供经济上或地位上的好处,因此其赞助是可分的。
4 广学会译著对于诗学因素的适应
诗学因素存在于文学系统之内,主要由包括学者、批评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控制。虽然诗学因素对文学和翻译的操控作用主要在系统内部,而赞助者对翻译的操控作用主要在外部,但是赞助者往往会通过权势或经济手段收买或利用专业人士,让他们参与到翻译活动中来,润色修改译文,以使译文符合译入语文化的诗学规范。尽管勒菲弗尔强调影响翻译的主要因素是意识形态,但这并不代表诗学因素在翻译中的地位不重要,恰恰相反,有时候会存在着迎合译入语文化的诗学特征来传播意识形态的现象(王宏志,2007:50)。广学会为了扩大其译著的销量和接受度,采取多种方式迎合中国主流的诗学规范,包括扩大华人主笔的数量和自主度,根据目标受众调整译入语,以及在翻译策略上更多采用归化译法。
广学会继续沿用明末以来的“西译中述”这一合作译书模式,第一时期内的传教士口授者主要有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笔述者则有蔡尔康、范祎、任廷旭等传统文人,他们大多在襄助传教士翻译前已在报界有所历练,如蔡尔康就曾任职于《申报》《字林沪报》等报纸,是资深的报人,对读者的阅读偏好和主流的文体范式十分熟悉。后期,随着教会学校的建立和中国译者外语能力的提高,由华人直接执笔翻译的人数大量增加,中国译者独立译述渐渐成为主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谢颂羔,他在1926年至1950年间翻译、编著了160 多部图书和小册子,成为广学会后期文字工作的中坚(陈建明,2018)。然而,传统的译述方式仍然存在,如英国传教士莫安仁(Evan Morgan)就在他的中国助手周云路的帮助下翻译了《新约述要》《历史上之基督》等书籍。
文字事工一直是传教士在华传教的重要工作之一。随着五四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的展开(杨剑龙,2010),为进一步采用中国人自己耳熟能详的话语传教,广学会开始将翻译重任进一步交给中国基督徒,尤其是1922年5 月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全国大会上,教会文字出版工作的本色化被提上日程,因为“外国人说中国话,说出来多是外国的中国话,不是本色的中国话”,并最终决定“今后更多出能应时需的中国本色文字,著作人须得要中国人充当”(李志刚,1997:169)。此后,广学会中华人编辑和译者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文字工作,至1937年,广学会会内总共七位专职编辑中已经有刘美丽、洪超群、夏明如、梁得所和谢颂羔等五位华人。此外,广学会还积极和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刘廷芳等人合作译书,以便“能合新中国的需要”(济泽,1934)。
选取何种文体,文言还是白话文,与译著的受众密切相关。清末,社会知识分子都使用文言文,而教育程度不高的广大下层人民都使用白话文。虽然白话文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用白话文书写的小说更是广泛流传,但在晚清,文言文仍是社会上的主流诗学规范。同为翻译大量西方著作的译者,严复和林纾都不约而同采用文言文作为译入语即是明证。由于广学会初期的读物主要是为了在中国普及历史、地理、社会科学等西学知识,受众主要是中国上层士大夫、新式官僚和读书人,因此其代表性译著,如《泰西新史揽要》《百年一梦》均用文言文翻译。然而,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尤其是清朝的灭亡,广学会上层路线彻底失败,其翻译出版重心开始转向中下层人民,这个群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受众的转变再加上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为了更好地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从而宣扬基督教,从前的文体文言文也开始转为白话文,并逐渐成为广学会报刊书籍中广泛采用的语言(何凯立,2004:87)。
在翻译策略上,广学会主张采取相对归化的译法,将西方的概念用中国已有的概念来阐发或解释,这种译法最初出现在基督教文献的翻译上。晚明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早已认识到中西调和的重要性,在其1595年出版的《天主实义》中就表达出了儒家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天主”,两种学说中有很多共同点(陈戎女,2001)。“孔子加耶稣”是利玛窦等早期来华传教士采取的翻译策略,到了清末,广学会最初仍以这种思维翻译西方宗教读物,如出版于1903年的广学会新译《缺一不可》首章首句就译为:“按《大学》所记:欲平治天下之举,始必修身……”(高葆真,1903:1),这很明显借用了中国儒家经典《大学》中的段落作为全文的引子,反映出清末传教士翻译西学书籍中仍然尊崇汉语在概念和表达习惯方面的某些诗学规范,采用归化或自然化的做法以减小对译入语文化的冲击。在李提摩太翻译《泰西新史揽要》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清政府的意识形态,李提摩太将“法国大革命”译为“法国大乱”或“法国大患”,将“自由的进步”译为“绥靖百姓”(顾长声,2004:160);为了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李提摩太在公元纪年上配以中国的纪年方式,还补上各国世系,以符合中国的史书传统(关志远,2012)。
5 广学会赞助行为的影响
赞助行为并不是单向的表现为位于优势地位的赞助者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和地位手段促进翻译活动,翻译活动的成功开展也会使赞助者获益,这种益处主要体现为使赞助者“获得文学声誉、社会地位以及对于文化的宰制权”(卢志宏,2015:19)。具体到作为翻译赞助者的广学会,它不仅依靠历年来出版的译作普及西学、推动社会变革、传播基督教义,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获得巨大的社会声誉,同时还成为近代来华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教会出版机构,在行业内占有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
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产生重要影响力的书籍中,广学会的译著无疑占有一席之地。作为近代普及西学的先驱,广学会赞助翻译出版活动的行为有力促进了历史、政治等社会科学知识和地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在清末维新变法时期,广学会出版了一系列旨在推动清政府改革的译作,影响力空前提升,以致其很多出版物为光绪皇帝所购,而梁启超所编《西学书目表》中也将《泰西新史揽要》《文学兴国策》《百年一觉》等广学会译作视为西学入门的必读书,其中《泰西新史揽要》更被梁氏誉为“西史中最佳之书”(梁启超,2018:101)。在中国近代的西学东渐大潮中,广学会的地位十分重要,不可低估。总体而言,广学会在清末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其翻译,尤其是结合评论、按语的编撰作品开始了紧贴中国实际并鼓励变法而宣传西学的历史;二是广学会著作多有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开启了之后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的滥觞;三是广学会的翻译出版活动因为其灵活的推广方式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推动了西学传播的新局面(熊月之,2011:443-444)。
传教士设立出版机构历史悠久,在广学会之前较为知名的有墨海书馆、美华书馆、青年协会书局、圣经公会和圣教书会等出版机构。与广学会相比,以上出版机构要么存在时间较短,要么出版题材较为受限,远远无法在影响力上与广学会相提并论。在广学会存在的七十年中,在李提摩太、林乐知等在华各差会精英的主持下,其出版物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宗教知识,还包括大量教材和学术著作,涉及的题材之广,数量之多,足以成为近代传教士出版界的翘楚。进入民国后,广学会还翻译出版了大量与基督教相关的著作和丛书,对于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引介和普及也有其贡献。总之,广学会翻译出版的众多著作为其奠定了近代来华传教士设立的规模最大、出版数量最多的出版机构的地位。
6 结论
综上所述,广学会作为近代中国一家重要的出版机构,其翻译出版活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社会形势的演变而逐渐调整,并紧密贴合其意识形态和传教目的。在不同时期,广学会在翻译主题、译者来源、诗学特征、翻译策略等方面都是不同的,广学会对不同时期翻译出版活动的赞助力度和侧重点也有差异。广学会的赞助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不同时期译著的选择上,并通过经济上和地位上的赞助推动其翻译出版活动。本研究通过发掘文献,从赞助者的视角考察广学会的翻译活动,包括其中后期的翻译活动,以期呈现广学会翻译出版活动的全貌。赞助者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超越单纯的文本分析,从社会文化的维度挖掘广学会翻译出版活动更深层的原因及其与社会的动态关系,从而更好地评估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