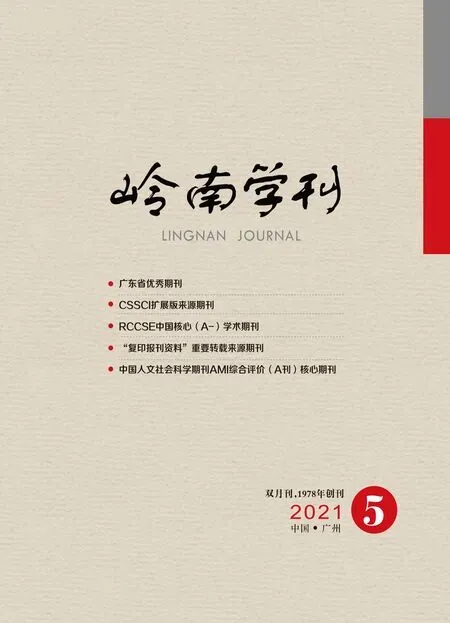从天德观到人德观:先秦道德观的深化探析
吴灿新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 广州 510050)
自古以来,中国都极为重视伦理道德。从而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形成了伦理中心主义的主流文化,也造就了“德主刑辅”的德治型治国模式。伦理道德在中国如此重要,那么,它究竟来自何方?这正是中国历代思想家孜孜以求的重大理论谜底。而中国早期著名思想家周公、老子、孔子和孟子等都为此作出了自己的巨大努力,为中国传统思想界认知道德本源问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周公的天德观
周公(大约商末周初—公元前1100年前后),姓姬名旦,他是周文王的第四子,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对建立、巩固和发展周朝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成为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后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其思想言论见于《尚书》诸篇。
古代中国其独特的地理生态环境,造就了炎黄子孙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由于农事耕作受到天气条件的严重制约,使人的命运与天的运行紧密相连。在相当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时代,人在天的面前往往无能为力,无法正确认识天的威力,于是往往将天拟人化,以为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天神的安排和命定的,从而导致人必须顺应天命的思想观念之形成。[1]
天命观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夏朝。在中国远古原始部落时期,最高权力的传承实行禅让制,历来传贤不传子。从最古老的历史典籍《尚书》中可知,无论是尧传位于舜,还是舜禅位于禹,都不是因为血统,而是由于其贤德。而禹则传位于子启,从此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为了使世袭制度名正言顺,夏王朝提出了天命观,宣扬王权乃来自天命,以论证其合法性。如启伐有扈氏于甘时,他在战前誓师中宣告道:“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恭行天之罚”[2]87,意为上天因此要断绝他们的国运,现在我只有奉行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商人灭夏后,继承了夏朝的天命观,并把天命思想与宗教迷信结合起来。“殷人迷信鬼神、上帝,认为通过甲骨卜兆显现出来的鬼神、上帝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3]35同时,商朝也开始把天与德联系起来。“惟天监下民,典厥义……天既孚命正厥德”[2]118,意为上天考察下民,主要看他是否循义理行事……上天已发出命令,以端正人们的德行。
周人灭商后,周公在总结夏商灭亡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2]216,意即我们不可不鉴戒夏代,也不可不鉴戒殷代。我不敢知晓说,夏接受天命有长久时间;我也不敢知晓说,夏的国运不会延长。我只知道他们不重视行德,才过早失去了他们的福命。我不敢知晓说,殷接受天命有长久时间;我也不敢知晓说,殷的国运不会延长。我只知道他们不重视行德,才过早失去了他们的福命。现今大王继承了治理天下的大命,我们也该思考这两个国家的命运,继承他们的功业。由此可见,周公一方面还十分重视天命,因为周朝依然需要利用天命的至高权威性来论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周公常常强调,周代商,是天命之故:“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故乱,弼我”[4]161,不是我们小小的周国敢于取代殷命,是上天不把大命给予那信诬怙恶的人,而辅助我们。一个王朝是否得天之命,靠的是什么?周公已经明确意识到,天命能否眷顾,从根本上来说,就看一个王朝的统治者是否有德。因而另一方面,周公更多地看到了道德人事在朝代更替中的关键作用。虽说天赋王命,然而“天命靡常”,因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4]194。皇天为何“唯德是辅”,是因天命以德为本,是因德乃天立。也可以说,德总是和天的意志联系在一起的。周公的天命观对夏商天命观的变革,最重要的是将德与天紧密联系起来,不仅王权来自天命,而且王权来自道德;有道德才有天命,道德本乃天赋天立。《尚书》中就十分强调天德,《尚书·吕刑》说:“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2]320。就是说,能心存无私,与天合德,人之生死,上天所托,生杀予夺,代天讨罚,符合天意,配享天命。天德是上天为下界立下的道德准则。上天监察世间统治的好坏,就是以此标准去衡量。周公由此赋予了天以至善和赏罚明辨的特性,使天成为人世间王权的监督者,也使天成为了道德的来源者。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周公是探索了道德根源的第一人,他将德与天紧密联系起来,将天德明确为天赋天立;并由此突显了道德的至上权威。这是周公在道德根源问题上的重大思想理论贡献。
二、老子的道德观
老子(约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姓李名耳,是继周公之后最著名的思想家,是道家的创始人,存世有《道德经》(又称《老子》)。老子曾任周朝的史官,因此,周公的天德观他是熟悉的。然而,老子并没有照葫芦画瓢,却超越了周公的价值论天德观,从本体论意义上提出了其道德观。
在周公那里,天、天命固然是道德的最终与最高根据,但它主要是价值论意义上的,而并非本体论意义上的。老子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探讨本体论问题的哲学家,也是第一个从本体论视角上探讨道德之源的思想家。在老子之前,古代中国有过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如清朝马骕在其著作《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记载,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在夏商周时代,也有过天是生成万物的根源之认识,但至于天的根源问题却没有触及到。到了老子,则开始推求天的来源,由此他提出了道。当然,在老子之前,道的概念已经出现。最早,道的含意是指道路、路途,如《易经·履卦》中说“履道坦坦,幽人贞吉”[5]30。尔后,在《尚书》里,道有了比较抽象的意义,开始作为规律、规则等理解,如《尚书·洪范》中说:“无有作好,遵王之道”[2]144-145。而到了老子,他“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道’作为世界的本根,天地万物都是由道产生的”[6]58。他在《道德经》第一章中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4]958在老子看来,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是宇宙万物的始基。那么,这个道是个什么呢?他在第二十五章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4]963这个“大道”,不仅在本体论上是宇宙的万物的始基,而且在价值论上也是天地人最高最终的根据。
既然天地因道而生,万物因道以成,那么德无疑也是生成于道。在老子那里,道是德之源,是德之本;德是道之用,是道的载体,是道的体现。“在道家眼里,正是这种神秘的‘道’孕育并产生了一切万物,包括道德;道德不过是‘道’在社会和人世间的反映和表现。”[6]59而德在《道德经》中又是一个等差概念,它分为上德和下德。上德以道为体,以无为用;上德之人德合天地却不自以为有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4]966大意是:有上等德的人,不自以为有德,所以是有德。下等德的人是有心施德,所以他无德。有着上等德的人无为出于无意,所以无所不为。下等德的人,无为出于有意,所以无所作为。下德是大道“废”后才出现的,是人们因欲而兴、因求而得的产物,它的具体内容包括世俗所谓仁义礼智。《道德经·十八章》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4]961即是说,清静自然,纯和平淡的上乘社会秩序被破坏后,才会用仁义来作为民众行为的补充指导;智巧、技能发展进步了,虚伪和权谋也从中滋生了;父子、兄弟、夫妇等人伦大多逆伦叛上,不敬不爱,才会认识到孝顺、慈爱等人伦的可贵;整个国家陷于混乱,面临崩溃,才会衬托出忠臣的力挽狂澜、一柱擎天。
在伦理道德的根源问题上,老子把周公带有神化意义上的天德观变革为哲学意义上的道德观,把其伦理道德智慧奠定在其哲学最高范畴道的根基之上,走了一条“形而上”的认知路线。由此可见,老子的重大思想理论贡献突出表现为,他用道的概念否定了从远古以来直至西周时代上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否定了道德决定于天命的看法。老子将周公的道德来源认知从上天拉到“大道”之上,他迈开了走出宗教或神化之网的第一步,闯入了理论思维的新天地。
三、孔子的情德观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是比老子晚些时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
孔子曾访学于老子,对老子的思想也比较熟悉。但是,孔子最推崇的则是周公,在《论语》中孔子感叹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7]68。因此,孔子既谈天命,也谈道。然而,孔子谈天命和道,已与周公和老子不同:“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7]176。因为在孔子那里,无论是天命还是道,都褪除了其原来浓厚的神秘色彩,进一步迈出宗教或神化之网,向“人道”发展,张扬人的主体性积极因素,具有更加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1]
周公在构建天德观的过程中,产生了“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思想,使人与天在天德的基石上统一起来。他的天德观无疑带有神化的色彩,但其天德的提出,不仅使天的神性渐趋淡化,使天命的消极性减退,进而激活了天德观中的积极要素;而且使人的主体性逐渐显现,相对于神的地位逐步上升,由此对孔子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刻的伦理影响。孔子沿着周公的积极思路大步往前走,进一步超越了周公的天德观。在周公那里,有两个理论难题没有解决:一是德由天赋,但这种德的根据与来源无法进行理论证明。二是天命依德而转移,但什么是最高的德,周公也并没有指明。
在孔子看来,要解决这些问题,既不能走周公天德观的神性之路,也不能走老子道德观的道性之途,而应当从人道之中去探寻。在人道之中,仁德应是最高的德,是最高的伦理道德准则。《论语·里仁》中孔子说:“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7]33要知道是否过错,可以仁来判断。那么,什么是仁?《论语·颜渊》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也可以说是‘爱人’。”[3]106孔子从仁出发,提出忠恕之道。《论语·里仁》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7]35忠恕之道最根本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7]190。“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7]65那么“仁”这种根本的最高的德又从何来?在孔子那里,作为爱人的仁,既是一种最重要的道德感情,也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准则。这种最高的道德准则源于道德情感,也就是说,这种爱是建立在亲亲之爱的基础之上的。《中庸》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4]430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生活基本单位的农耕经济,因此重视家庭、重视家庭人际关系成为其必然性道德要求。而维系家庭关系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血缘亲情;在传统社会中,血缘亲情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父母子女亲情,而反映这种父母子女亲情的道德要求则是孝。故在传统社会里,孝为百德之本,孝为百德之先。孔子在《孝经》中写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4]865故孔子认为,正是这种血缘亲情,成为了“仁”德的根本与源泉。《论语·学而》中孔子就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7]2无疑,从古代中国家庭人伦关系的视角,可见亲情是人之生存的基本要素,也是家庭生存之根本要素,从而亲情成为孔子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本源。
孔子的情德观,是人德观的第一个形式,他扬弃了周公的天德观和老子的道德观,既摆脱了周公天德观的神秘性,也脱离了老子道德观的过度抽象性,张扬了他俩人的主体性积极因素。如果说,老子的道德观走了一条“形而上”的哲学认知路线,那么,孔子的情德观则从天命、大道到仁德再到孝德亲情,把伦理道德奠定在其伦理学的亲情人道基础之上,走了一条“形而下”的伦理学认知路线。孔子沿着这条人道的道路前进,将天上的道德拉回到人间,为中国古代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人文基础。
四、孟子的性德观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被称为亚圣,与孔子合称孔孟之道。孟子属孔子第四代弟子,是曾子的再传弟子。他对孔子备极尊崇,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8]49。因此,他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学说。孟子扬弃了孔子的天命和天道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8]119孟子把天命天道移向人道,张扬孔子的人文主义精神;并顺着这种精神指引的方向,去探寻道德的起源。
孔子在探寻道德本源上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将周公的天德和老子的道德发展为情德,将道德的本源引到人间亲情之上。而孟子则进一步将人间亲情探底到人性之上。关于人性问题,最早以性的概念出现,在《尚书》中就有过“不虞天性”“节性”等字句,指的都是天之性情和人的性情。但此时,它虽有了些许道德含义,然还没有上升为道德的本根。孔子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接近这一认识的人,他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7]206。人的天生本性原是相近的,但却由于后天的习染不同才相互有了差别。但孔子却没有继续深入这一认识,而在道德本源上由性转向了情。孟子则将孔子关于性之说进行到底,他天才地看到了人性与动物性的根本区别,认为人与动物之根本不同,就在于人有道德而动物没有道德,“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8]87。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以其有道德也。如果一个人想吃就吃、想穿就穿、想玩就玩,而不接受教育的感化和拘范,那么这个人和禽兽又有什么区别?人之所以能够接受教化有道德,从根本上来说,就在于人性本善,因为人性之中,先天就有善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8]185。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的要求并非源于人性之外,而是源于人的本性本心之中;人通过内省可以去保持和扩充人性中的这些本有先在的善端,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向恶转化。
由此,孟子在弘扬孔子仁德的同时,进一步为孔子的“仁爱”思想提供了其终极意义上的支撑。在孟子看来,仁爱固然直接发源于家庭血缘亲情,但是,从本根上来看,它则发源于人性之中,是人性之中的“恻隐之心”这一善端发扬光大的结果。基于仁爱所施行的仁政,就是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之上的。孟子就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8]53-54“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就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无疑,孟子认为这种同情仁爱之心虽在本根上是源于人性,但在直接现实性上则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因此,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孟子在弘扬孔子的情德观时,既超越了周公的天德观和老子的道德观,也超越了孔子的情德观,发展出了道德本源论上的性德观。孟子从被后来的西方著名伦理学家康德所说的“实用理性”出发,将道德本源定格在人性之上,这既是古代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重大成就,也是后来中国传统道德本源论的强大引导者。一方面,孟子之后,谈道德本源论,基本离不开人性论;另一方面,无论后来者如何看待人性,但孟子的性善论,始终是中国传统伦理学的主流。孟子之后,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针锋相对地提出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他明确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4]1346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所以一定要有了师长和法度的教化、礼义的引导,然后人们才会从推辞谦让出发,遵守礼法,而最终趋向于安定太平。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主张性有善有恶:“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9]202朱熹(1130年—1200年)则是性两元论的集大成者,他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9]219。理是纯善的,气则清浊不齐,故气质之性有善有恶。王守仁(1472年—1529年)不赞同性两元论,提出了性一元论:“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9]222。凡此种种人性论,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有所发展,但终究离不开孟子的性德观之道。
孟子的性德观,是人德观的第二种形态,其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沿着孔子的人德观的人的主体性方向,将道德的本源最终从天上落实到人间,从人之外在引向人之内在,从天德到人德,基本完成了古代早期中国思想家对道德本源的探寻;并在很大程度上抹去了以往道德本源论上的神秘与宗教色彩,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当然,孟子的性德观虽有许多合理之处,但他把道德的本源放置在抽象的人性之上,毕竟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道德本源论,缺乏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则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上去揭示道德本源论,指出人的本质属性在于人的社会性,人类社会是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波浪式向前发展的;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殊产物,既是人的质的规定性,也是人性的根本要素,但其本源归根到底与人性一样,都是由社会存在特别是经济基础所决定,从而科学地揭示了道德的真实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