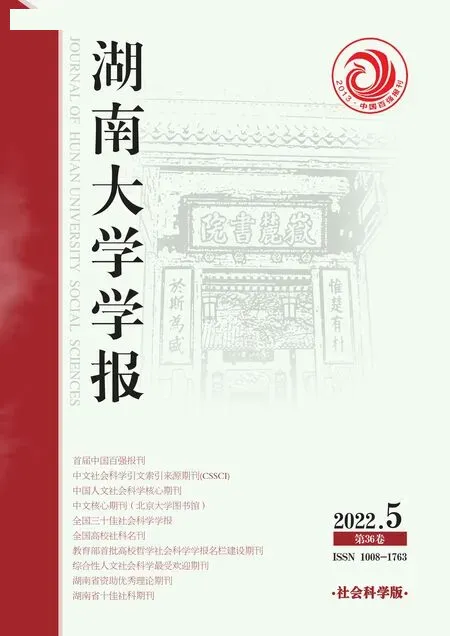民国时期熊十力与船山学研究*
郭 钦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文化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3)
熊十力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其《心书》(1918)、《新唯识论》(语体文本,1944)、《读经示要》(1945)等著作既反映了熊十力对王船山学术思想的认识历程,也大体能反映民国时期熊十力对王船山学术思想的研究情况。
一 “得悟道器一元,幽明一物”:《心书》对船山“道器”论的悟与不悟
《心书》是熊十力在1916年至1918年间的笔札,共二十五则。蔡元培在《熊子真心书序》中言及了熊十力作此书的缘由:
余开缄读之,愈以知熊子之所得者至深且远,而非时流之逐于物欲者比也。自改革以还,纲维既决,而神奸之窃弄政柄者,又复挟其利禄威刑之具,投人类之劣根性以煽诱之,于是乎廉耻道丧,而人禽遂几于杂糅。昔者顾亭林先生推原五胡之乱,归狱于魏操之提奖污行,而今乃什伯千万其魏操焉,其流毒宁有穷期耶?呜呼!履霜坚冰至,是真人心世道之殷忧矣。今观熊子之学,贯通百家,融会儒佛。其究也,乃欲以老氏清净寡欲之旨,养其至大至刚之气。富哉言乎!遵斯道也以行,本淡泊明志之操,收宁静致远之效,庶几横流可挽,而大道亦无事乎他求矣。是则吾与熊子所为交资互勉,相期以为进德之阶梯者。其即以是编为息壤之誓言焉可也。[1]3
依蔡元培言,早年的熊十力鉴于民国初年社会道德败坏,而欲寻一法子救之。其法则仍脱不开儒佛老氏之道,其文化复兴之思想由此可见。故而,尊儒的王船山的学术思想必是其追求的治世之道之一。
熊十力的《心书》中有作于1916年夏的《船山学自记》,言及习“船山学”缘由及其所初步认知的王船山学术。
余少失怙,贫不能问学。年十三岁,登高而伤秋毫,时喟然叹曰:此秋毫始为茂草,春夏时,吸收水土空气诸成分,而油然滋荣者也。未几,零落为秋毫,刹那刹那,将秋毫且不可得,求其原质,亦复无有。三界诸有为相,皆可作如是观。(1)所引小字内容为熊十力自注,本文所引熊十力自注均如此标示。顿悟万有皆幻。由是放荡形骸,妄骋淫佚,久之觉其烦恼,更进求安心立命之道。因悟幻不自有,必依于真。如无真者,觉幻是谁?泯此觉相,幻复何有?以有能觉,幻相斯起。此能觉者,是名真我。时则以情器为泡影,索真宰于寂灭,一念不生,虚空粉碎,以此为至道之归矣。既而猛然有省曰,果幻相为多事者,云何依真起幻?既依真起幻,云何断幻求真?幻如可断者,即不应起,起已可断者,断必复起。又舍幻有真者,是真幻不相干,云何求真?种种疑虑,莫获正解,以是身心无主,不得安稳。乃忽读《王船山遗书》,得悟道器一元,幽明一物。全道全器,原一诚而无幻;即幽即明,本一贯而何断?天在人,不遗人以同天;道在我,赖有我以凝道。斯乃衡阳之宝筏、洙泗之薪传也。《船山书》凡三百二十卷,学者或苦其浩瀚,未达旨归。余以暗昧,幸值斯文,嘉其启予,爰为纂辑,岁星一周,始告录成,遂名《船山学》。故记其因缘如此。
余曩治船山学,颇好之,近读余杭章先生《建立宗教论》,闻三性三无性义,益进讨竺坟,始知船山甚浅。然考《船山遗书》目录,有《相宗络索》《八识规矩颂赞》二书。自邓显鹤、曾国藩之伦,皆莫为刊行。诸为船山作传者,亦置弗道。吾臆船山晚年或于佛学有所窥,陋儒或讳其书不传,未可知耳。[2]5-6
长录此文,一是展现熊十力的儒、佛思想较早即有。二是也想明示熊十力起初与王船山结缘,主要还是因其佛学研究这一块“种种疑虑,莫获正解”而转读王船山之书,进而体悟到王船山“道器一元,幽明一物”之论,并称此论仍“衡阳之宝筏、洙泗之薪传”。三是通过比较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论》,又认为在佛学方面“始知船山甚浅”。由上可知,此时期的熊十力思考人生,总体上是信服佛家思想的,但也初步悟到了王船山的“道器一元,幽明一物”的思想并受其影响。
在《心书》中,熊十力还提及王船山其他方面的思想。如在《与张素武》篇中论船山的太虚气化论宇宙观:
大论以肉体不死立宗,极善。然所据以为断者,乃谓肉体变化于宇宙间,有聚散,无消灭,论者所徽,神气离合聚散,我、物无常等。故无死,此犹张载、王夫之之旧说耳。船山宗张子,以物之生死,由太虚理气浑然之实体变动而有聚散,聚而生物,散则物死,大化周流不已,然能化与所化只是一体。故船山曰:“不是阴阳五行之外别有个天。”其说为主动,与近世柏格森之旨略近,非善读者不能得之,以其言皆散见也。如若所云,肉体既聚散无常,岂无常之物,而可谓不死?请更论之。[2]26-27
处在对各种学说的认识时期的熊十力,虽认同王船山的气化论,然而他在此后的“更论之”中却是以佛法来论肉体生死问题的,此文末说:“一切法无起灭,色法恶有灭,是故说言肉体不死。”[2]27可见,佛教的无起亦无灭,才是熊十力借船山气化论要表达的对人生的哲学认识。也可看出,此时的熊十力,对船山学、佛学等都有兴趣,思想比较杂乱。熊十力并没有体悟到王船山对佛教的真知。
熊十力在《心书》中还推崇王船山的法治、虚君思想,他在《心书》的《钩王》篇中言:
儒者尚法治,独推王船山。案其言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外,以虚静统天下。《读通鉴论·晋论》。远西虚君共和之治,此先发之矣。值世网密,微辞以见意,思深哉。船山处异族专制之下,不敢倡言民主,而思想实及之。船山固东方之孟德斯鸠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非其伦已。[2]27-28
熊十力大赞王船山的法治、民主思想,以为于西可比孟德斯鸠,于东则超世所盛赞的《明夷待访录》。至于学行,熊十力不止一次对黄宗羲、王夫之进行对比,在《心书》的《至言》篇中,熊十力甚至认为“宗羲学行,固不逮衡阳远甚”,为何有此论断?先看原文:
迩者余杭章先生尝曰:“鄙人自处,唯欲振起姚江学派,以挽今世颓靡巽懦之习。”丁巳夏与民友会书。迹先生行谊,固佛之侠者,何取托于姚江哉?近人颂明季节义,归功姚江者,盖祖黄宗羲。宗羲学行,固不逮衡阳远甚。衡阳尝痛心于明季士大夫,以气矜亡国。力诋姚江,其说实非过激。王守仁有术智,未能忘功名,而以圣自居。此即我执为无穷祸根。故其党多气矜。观挽世予圣之士,其偏执妄逞,何尝不诵法姚江也。要之挽(晚)(2)笔者疑原文“挽”应为“晚”,故拟改正以括号分别,下同。明士风近季汉,今不可取则。[2]40
熊十力之所以认为黄宗羲学行不如王船山,仍是因为黄宗羲在总结明亡教训之时,碍于乡谊,对王阳明姚江学派尤其是其后学的历史作用有不切实际的评价,比如黄宗羲将“明季节义,归功姚江”。而王船山则以“明季士大夫,以气矜亡国”而“力诋姚江”。熊十力非常认同王阳明“有术智”,但更认同王船山所论王学末流以“气矜亡国”之说,故熊十力认为王阳明“未能忘功名,而以圣自居”,“故其党多气矜”。这么观察下来,熊十力甚至怀疑章太炎“何取托于姚江哉”?
可以这样说,此一时期的熊十力确如丁去病为《心书》之作《跋》所言,其因“讽世情深”[3]42,一会儿佛,一会儿儒,然其徘徊之际,渐重儒家,所以熊十力曾题壁曰:“数荆湖过客,廉溪而后我重来。”[3]42襟怀如此,也就可以解释熊十力用包括王船山在内的资源去复兴儒学的内心追求了。
二 “翕辟成变”:《新唯识论》对船山宇宙观的理解和不解
熊十力的“翕辟成变”说是其哲学思想上的一大创建,而船山解《易》 “乾知大始”之论则是其重要借鉴。王船山在《周易稗疏》中解“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时说:
若云乾主大始,则亦作也,能也,何以别于坤之简能而成物也?天以气化,以神用。神气之灵为聪明。今观万物之生,其肢体、筋脉、府藏、官骸,与夫根茎、枝叶、华实,虽极于无痕,而曲尽其妙,皆天之聪明,从未有之先,分疏停匀,以用地之形质而成之。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4]782
熊十力在《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成物”篇中对此有长篇批说:
王船山解《易》,说“乾知大始”云:“今观万物之生,其肢体、筋脉、府藏、官骸,与夫根茎、枝叶、华实,虽极于无痕,而曲尽其妙,皆天之聪明,从未有之先,分疏停匀,以用地之形质而成之。故曰‘乾知大始’”云云。余按《易传》曰“乾知大始”,乾者,阳也,相当吾所谓辟。辟者,本体自性之显也。故于用而显体,则辟可名为体矣。体非迷暗,本自圆明。圆明者,谓其至明,无倒妄也。故以知言。大始者,自本体言之,则此体显现而为万物。自万物言之,则万物皆资此真实之本体而始萌也。大始之大,赞词也。此中意云,本体具有灵明之知,而肇始万物。故云“乾知大始”。船山云用地之形质,实则地即形质,特以地为主词耳。此形质非别有本。盖即本体流行,不能无翕。翕便成形质。而本体或生命之显现,必用此形质以成物也,否则无所凭以显也。船山所说,吾大体赞同。唯其云“天之聪明,从未有之先,分疏停匀,以用地之形质而成之”,此则有计划预定之意,吾所不能印可。夫《易》言“乾知大始”者,乾,注见上。谓乾以灵知而肇始万物,知读智。不可妄计宇宙由迷暗的势力或盲目的意志而开发故。此处吃紧。《易》之义止于此,并不谓乾之始万物也有其预定的计划。而船山乃谓“从未有之先,分疏停匀”云云,是与《易》义既不合。而其义之不可持,则吾前已有言之矣。然本体之显现而为万物也,虽无预定计划,而不妨谓其有计划,只非预定耳。但此计划二字,须善会,非如人之有意计度也,其相深微而不可测。[5]351-352
关于“乾知大始”,熊十力基本继承了王船山“乾主大始”说及其基本解释。从上述引文可知,王船山说“若云乾主大始,则亦作也,能也,何以别于坤之简能而成物也”亦即“乾”为造作天地万物之初始,坤承乾道则形成具体的万物。熊十力说“大始者,自本体言之,则此体显现而为万物。自万物言之,则万物皆资此真实之本体而始萌也”。相对王船山所言,熊十力是用“本体”概念来说“乾”的。但两人所说,以现代词语来说,大意是“乾”(本体)是抽象性的“物”的统括,而“坤”则是具体性的物质形态,故而,熊十力说“船山所说,吾大体赞同”。
但是,熊十力所认“乾”(本体)与王船山所认“乾”(本体)的实质是不同的。正因为有此别,故而双方在宇宙观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焦点就在于对“乾坤并建”论的分歧。
王船山之“乾主大始”说与“乾坤并建”说实际是一致的。关于这一点,王船山在《周易外传》卷五中说:“大哉《周易》乎!乾坤并建,以为大始,以为永成,以统六子,以函五十六卦之变,道大而功高,德盛而与众,故未有盛于《周易》者也。”[6]989类似的还有“乾坤并建于上,时无先后,权无主辅”[6]989“无有乾而无坤之一日,无有坤而无乾之一日”[6]1070等说。由以上可看出,王船山所说“乾坤并建”,无先后,无主辅,不可分离,是万事万物之源,这就是王船山的宇宙观。
本处所引熊十力一段话,倒是没有对“乾坤并建”发表议论,然而在《读经示要》中,熊十力则是批评“乾坤并建”的,他说:
但船山于本原处,不能无误。其言乾坤并建,盖未达体用不二之旨,遂有此失。坤元亦是乾元,非并立也。乾之不能无坤者,特故反之,以成其变耳。本体固绝待,而其现起为大用,则不能不有一反动,以成变化。老云反者道之动是也。学者细玩《新唯识论》翕辟之义,便知船山有未透在。船山未见本体,盖由反对阳明与佛老之成见误之也。[7]839-840
熊十力说王船山“乾坤并建”说未达“体用不二”,理由是“坤元亦是乾元,非并立也”,因此不存在“并建”。咋一看,熊十力此说似正确,其实不然。熊十力才是将“乾坤并建”当作二元论的。这就要追查其对于“乾坤”相互关系的理解。前引《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成物”篇中,熊十力说“乾者,阳也,相当吾所谓辟。辟者,本体自性之显也。故于用而显体,则辟可名为体矣。”由此可知,熊十力以“乾”(“辟”)为“体”。那么,“坤”是什么?熊十力所言的“辟”又是什么呢?前引在《读经示要》中,熊十力甚至断言:“学者细玩《新唯识论》翕辟之义,便知船山有未透在。”熊十力认为王船山“未透”的又是什么呢?看来,真要“细玩翕辟之义”,看看这两位通过“翕辟”(王船山称“阖辟”)对乾坤关系究竟是如何理解的。
何为翕辟?先看这两个词的来源。《易》是“翕辟”“阖辟”的来源。《易》言“翕”“辟”:“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8]162-163此处讲“坤”的“翕”“辟”指静与动,与“乾”之静与动是一致的,是天地“成物”的变化。《易》又言“阖”“辟”:“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8]169此处,以“户”的“阖”(合)与“辟”(开)之形象动作,来讲“乾”“坤”的“大化”,即万物生生不息的变化,实际与“翕辟”一样,都是讲世界万物的生成、变化和发展。
王船山据此段《易》“阖辟”之说,论阖辟关系:
阖有辟,辟有阖,故往不穷来,来不穷往。往不穷来,往乃不穷,川流之所以可屡迁而不停也;来不穷往,来乃不穷,百昌之所以可日荣而不匮也。故 阖辟者疑相敌也,往来者疑相反也。然而以阖故辟,无阖则何辟?以辟故阖, 无辟则何阖?则谓阖辟以异情而相敌,往来以异势而相反,其不足以与大化之神,久矣。[6]1082
王船山此处所论《易》之乾(辟)坤(阖)关系,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正是乾坤并建而大化流行,这是一种辩证宇宙观。熊十力也讲“翕辟观”,他“拿乾卦来表示辟,拿坤卦来表示翕”[5]330。 在熊十力这里,“翕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熊十力言:“依恒转故,而有所谓翕,才有翕,便有辟。唯其有对,所以成变,否则无变化可说了。”[5]99这是一种相反相成的“成变”的关系。由此可见,熊十力所讲“翕辟观”,与王船山所讲“阖辟观”基础含义是一样的,都是讲“乾”(“辟”)“坤”(“翕”或者“阖”)之宇宙动静变化和万物生成。
注意,熊十力认为依“恒转”才有“翕辟”,那么“恒转”又是什么呢?“恒转”是熊十力借助佛教《成唯识论》中的“恒转”创造的一个哲学本体概念,依熊十力所说:“我们从能变这方面看,他是非常非断的。因此,遂为本体安立一个名字,叫做恒转。恒字是非断的意思,转字是非常的意思。非常非断,故名恒转。”[5]95恒转与翕辟是什么关系呢?熊十力说:“恒转现为动的势用,是一翕一辟的,并不是单纯的。翕的势用是凝聚的,是有成为形质的趋势的,即依翕故,假说为物,亦云物行。……辟的势用是刚健的,是运行于翕之中,而能转翕从己的,……即依辟故,假说为心,亦云心行。”[5]101由此可见,熊十力借助“恒转”论,在“翕辟”论中灌入“心物”内容,此“辟”之“心”究竟是何心?又来自哪里?熊十力言:
泰初有翕,泰初即已有辟。我们把这个辟,说名宇宙的心。伟大的自然、或物质宇宙的发展,虽不是别有个造物主来创作,可是,自然或一切物并非真个是拘碍的东西,他们一切物。内部确有一种向上而不物化的势用即所谓辟潜存着。[5]109
这就是熊十力所言的“辟”(宇宙之心)。以“翕辟成物”为例而言,熊十力一再强调“宇宙之心”的作用,其言:
所谓辟者,亦名为宇宙的心。我们又不妨把辟名为宇宙精神。这个宇宙精神的发现,是不能无所凭藉的。必须于一方面极端收凝,而成为物即所谓翕,以为显发精神即所谓辟之资具,而精神则是运行乎翕之中,而为其主宰的。因此,应说翕以显辟,辟以运翕。盖翕的方面,唯主受,辟的方面,唯主施。受是顺承的意思,谓其顺承乎辟也。施是主动的意思,谓其行于翕而为之主也。……翕和辟,本是相反的,而卒归于融和者,就在其一受一施上见得。受之为义,表示翕随辟转。施之为义,表示辟反乎翕而终转翕从己。己者,设为辟之自谓。所以,翕辟两方面,在一受一施上成其融和。总之,辟毕竟是包涵着翕,而翕究是从属于辟的。[5]112-113
从此段看,熊十力在翕辟观上是主张相反相成达到“融和”成物的,这与王船山所言阖辟观是一致的。然而,在熊十力这里,翕辟又有“受施”(从和主)的关系,这一关系之所以出现,是宇宙之心(辟)在主宰。所以,熊十力说这是唯物者、唯心者都认识不到的。他说:
我们何以把辟叫做心,把翕叫做物呢?旧唯识论师,以为心是能分别境物的……是把他当作静止的物事去看,而不了解他的本身元(原)来只是很微妙的一种势用。……唯物论者把物质看做为本原的,旧师也以为物质有他的因素,名相分种子。这都是把物看成实在的,都是极大的错误。实则物并不实在,亦决没有旧师所妄想的物质的因素。物者,只是我所谓收凝的势用所诈现之迹象而已。[5]110-112
综合上面两段引文,足可以回答熊十力之所以说“船山有未透在”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熊十力认为王船山虽然认识到了“翕辟”互动,但认为王船山并未悟透“辟”这个不仅是“宇宙大心”,还是宇宙万物变化的主宰。这样一看,乾(辟)在熊十力那里似有“造物主”的功用。然而,熊十力却只承认翕辟成变在受施上融合,从而又否认有人格化的“造物主”说。这就是熊十力很矛盾的地方。这个矛盾还体现在对王船山“成物”的“未有之先,分疏停匀”说的不当批评上。
让我们回到前面《新唯识论》(语体文本,1944)“成物”篇中所引王船山云“天之聪明,从未有之先,分疏停匀,以用地之形质而成之”之说。熊十力认为王船山此说有“计划预定之意”,这是他不认可的。熊十力所说王船山有“计划预定之意”本身是个误解。其实,王船山云“天之聪明”“地之形质”实际是指“乾”(天)为万物生发的根本依据,“坤”(地)成具体形质而有万物。“聪明”与“形质”不过是作为乾坤的阳阴二气发用之功能的显现,是乾坤并建之体现,并无先后。而熊十力并未能理解王船山的乾坤并建一元论,而是将船山的乾坤并建论理解成二元论,则自然按照自己的逻辑主观地认为王船山所言“聪明”与“形质”有先后之分,即“乾”有预定“坤”之意。这当然不符合他的“心物一体”的本体论。矛盾在于,熊十力又承认翕辟“受施”,即宇宙这个大心“乾(辟)”是有“灵知”的“造物”行为,这其实又是“乾元”“坤元”分离的二元论。二元论者自然有“受施”,而这需要有“宇宙之心”“有计划”地来预定“物”,但他又不承认“心物”分离,也就不承认“预定”。这是矛盾的。
熊十力的这种矛盾的理论,一方面承认翕辟互动以成变,表面上没有而实际上认可“乾坤并建”的宇宙论,这是熊十力能理解王船山的方面;另一方面,熊十力在本体论的立场上否认了心物的实在性,即不想离开他以“宇宙之心”为体的观点,然而在解释翕辟成变(大用流行之显现)为万物的现象时则又表明心物万象其实是实在的,这就陷入了难以自圆的境地。所以,熊十力最终也就不能理解乾坤并建、翕辟成变,在王船山处是实在的阴阳二气变化,也就不能理解重“气”的王船山关于物质及其运动的解释了。[9]
三 “生、动、有与情一于性”:《读经示要》对船山哲学和精神的认同与不认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1945)中论晚明清初学术时,对于船山哲学有一个总体评价。他说:
此期哲学,仍继续程、朱以来之反佛教精神。而依据《大易》,重新建立中国人之宇宙观与人生观。奏此肤功者,阙惟王船山。余昔与人书,有云:船山《易内外传》宗主横渠,而和会于廉溪、伊川、朱子之间。独不满于邵氏。其学,尊生,以箴寂灭。《易》为五经之源,汉人已言之。而《易》学,不妨名之为生命哲学。特其义旨广远深微,包罗万有,非西洋谈生命者所可比拟。明有,以反空无。横渠云:“《大易》言幽明,不言有无,显而可见者谓之明,隐而不可自见者谓之幽。”船山以为宇宙皆实也,皆有也。不可说空说无。其于佛老空无二词之本义,虽不免误会,然以救末流耽空之弊,则为功不浅。船山曾研佛家有宗,盖亦融有义以言《易》。主动,以起颓废。此则救宋、明儒家末流之弊,与习斋同一用意,但习斋理解远不逮船山。率性,以一情欲。船山不主张绝欲或遏欲,而主张以性帅情,使情纵性,则欲无邪妄。而情欲与性为一矣。此与程、朱本旨并不背,可惜戴震不识性,而妄奖欲。论益恢宏。浸与西洋思想接近矣。此所举四义,实已概括船山哲学思想。学者欲研船山学,不可不知此纲要。自清末梁任公以来,时有谈船山者。大抵就涉猎所及,而摘其若干辞义,有合于稗贩得来之新名词或新观念者,以赞扬之。至于船山之根本精神,与其思想之体系及根据,则莫有过问者。今人谈旧学,无一不出此方式。而欲学无绝道无丧得乎?呜呼!吾老矣。眼见此局,不知所底。……中国人经三百年汉学风气,斫丧性灵,生命力空虚,已至极度。倚赖外人之劣性,与贪淫、忍酷、骗诈、委靡等恶习,及思想界之浮浅混乱现象,皆由生活力太贫乏故也。船山哲学,实为振起沉疴之良药,遗书具在,学者凝心读之,而得其深广之思,感其浓厚之悲,有不愤发为人者乎![7]838-839
熊十力言,作为张载的继承者,王船山“依据《大易》,重新建立中国人之宇宙观与人生观”,其“纲要”有四:“尊生,以箴寂灭”,这是船山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学观,非西方生命哲学所能比拟。这是批佛教的寂灭。“明有,以反空无”,这是船山的宇宙观,主张世界是实在的,不是空无的。这是批佛老的空无。“主动,以起颓废”,这是船山的静动观,主张世界是运动的,不是静止的,可救宋、明儒家末流空疏之弊。“率性,以一情欲”,这是船山的伦理观,主张性、情、欲统一,实际是批宋儒“天理人欲观”,但熊十力未看到这一点。熊十力认为这四个方面是船山学术的“根本精神”,可以正“斫丧性灵”的学风,是“振起沉疴之良药”,可救现世。熊十力说:
船山《易内外传》确甚重要。吾所举四义,即生、动、有与情一于性,四大基本观念。此吾综其全书而言之世。学者深玩之,可见其大无不包。足为现代人生指一正当路向。[7]839
可见,王船山易学对熊十力影响确实甚大。他还说:“吾平生之学,穷探大乘,而通之于《易》。尊生而不可溺寂,彰有而不可耽空,健动而不可颓废,率性而无事绝欲,此《新唯识论》所以有作。而实根抵《大易》以出也。”[7]916熊十力能“通之于《易》”,有“尊生”“彰有”“健动”“率性”之悟,自然来源于船山“尊生”“明有”“主动”“率性”之论,而这正是王船山哲学高明之处。熊十力批评前人道:
魏、晋人祖尚虚无,承柱下之流风,变而益厉。老庄不言刚健,而言虚静。魏晋人不善学之,竟成颓废。故是变本加厉。遂以导入佛法。后汉、魏、晋间,凡努力吸收印度佛教思想者,皆深于老、庄者也。宋儒受佛氏禅宗影响,守静之意深。而键动之力,似疏于培养。寡欲之功密,而致用之道,终有所未宏。《易》戒非几之萌,即不主纵欲。然言智周万物,言备物之用,言开物成务,则后儒所不省。二千年来,《易》之大义,湮绝已久,晚明王船山作《易外传》,欲振其绪,然于体用之义未融,此中却有千言万语道不得,学者若如《新论》,肯下一番功,方识吾意。情性之分莫究,天人之故,犹未昭晰。羽翼《大易》,疑于弗备。《新论》之作,庶几船山之志耳。[7]916
熊十力批评汉魏至宋明习《易》者,不仅未得其大义而致用,反而陷入颓废虚静。王船山虽高明,但熊十力认为其“欲振其绪,然于体用之义未融”,故熊十力欲补船山之不达,“《新论》之作,庶几船山之志耳”。
正因为王船山亦有缺失,熊十力对王船山的本体论颇有不认同之处,前已引用,熊十力说“船山于本原处,不能无误。其言乾坤并建,盖未达体用不二之旨,遂有此失”[7]839,又说“船山未见本体,盖由反对阳明与佛老之成见误之也”[7]840。按此说,熊十力认为这是王船山在对宇宙万物认识的根本上出现了问题,是有意反佛老之学和阳明心学。
至于对王船山“尊生”“明有”“主动”“率性”之论,熊十力主要对“率性”之论有不同的意见。熊十力说:
船山主张率性以一情欲,自甚谛。然反对阳明,而不悟心即是性,即功夫似无入处。由阳明之说,本心即是非,性心之外别有性也。故自识本心,存养勿失,凡生心动念处,皆是顺吾本心之明,一直扩充去。即一切情欲,皆受裁于心,而莫不当理。易言之,即情欲莫非性之发,以无妄情邪欲相干故也。是则情欲一于性,而非有善恶之二元明矣。然若不承认心即性,即率性功夫从何入手?夫性既不即是心,则性便超脱于心之上,何得裁制情欲,而使之当理乎?譬如主人不能裁制奴仆,则奴仆叛主而逞其妄。即不得以奴仆之动作,为主人之动作也。性不知节其情,而谓情与性为一可乎?阳明彻悟本体,故将心与性、理、天、命、道等名词,均说成一片。……船山将性与天、命、道等,皆妄分层级,而心不即是性,则心性又分层级。又以理为气之理,不即是心,几成唯物论。[7]840-841
熊十力以心学解读王船山“率性以一情欲”论,认为王船山“不悟心即是性”,因而不识“心”为“本体”,也就不识“即一切情欲,皆受裁于心”及“情欲一于性”。熊十力认为王船山之所以有“率性以一情欲”论,仍是以“理为气之理,不即是心,几成唯物论”。两人所论因本体不同,其识见自然千差万别。
言及此,大体上可以对熊十力在1949年前关于王船山的认识作一总结,还是用熊十力在20世纪40年代末自己的话来说,恐怕更恰当:
船山在哲学方面之发明,余尝综以明有、尊生、主动、率性四义,见《读经示要》第二讲,此所以救宋明溺于二氏之弊,功绪甚伟。其为学之方面甚多,如哲学、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政治、社会等学,多有独辟之处,为汉以来群儒所不逮。然其于各方面虽有许多精思妙语,但未能分别门类详细发挥。如虚君共和之论,船山明明说到,而只寥寥数字,不曾盛阐明之,诸如此类,不可胜举。是不足为船山病,中国学术界,自汉以后,诸子百家之业久废,分类研究尚无其风,思辨之术更非素讲,船山虽天纵,其能绝不为时地所限乎?余平生于古今人,多有少之所歆、移时而鄙,独至船山,则高山仰止,垂老弗变,其书感人至深如此。[10]193
熊十力虽盛赞王船山,但始终认为:“船山不幸而宗横渠,故于本原处始终不透。余尝欲取其《全书》中凡谈及道体者,条列而辨正之,卒以心所欲为而未得为者极多,竟鲜此暇。”[10]193
总体而言,熊十力从哲学上对船山学有继承、有批判。但终究因为其宗主、宗旨不同,为学之道也就与王船山同趣异旨。不过,这不妨碍熊十力对王船山的敬仰,故有“独至船山,则高山仰止,垂老弗变”之慨。可见,王船山的学术尤其是人格精神对熊十力的影响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