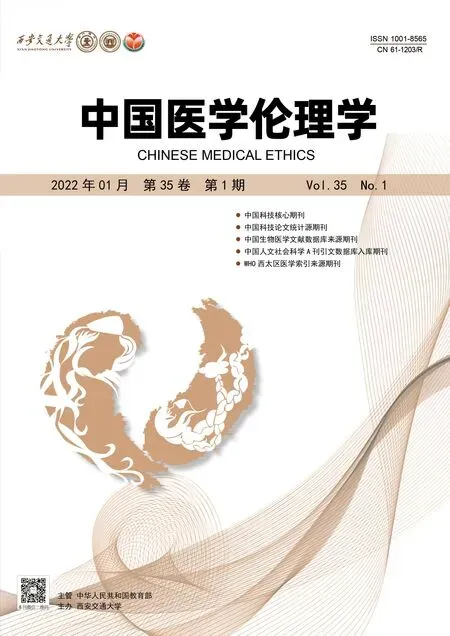《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缺陷和修改建议
蔡 昱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221,yucaicn@vip.sina.com)
器官移植已经成为目前许多器官衰竭患者挽救生命的终极手段,器官移植术在近几十年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未来也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作为具有开拓性的“高、精、尖”技术,器官移植是现代医学的“奇迹”,但如果对其伦理内涵、合法性依据和社会代价缺乏充分的考量,则对技术的过分追求可能成为现代医学的一种错误承诺。由此可见,器官移植技术特殊的重要性恰恰在于伦理和法律方面,而不仅在于技术与效益。它显示出了技术进步与法律和伦理之间所形成的持久张力。我国于2007年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器官捐献与移植的规范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和关键性的作用,但十几年的应用实践也暴露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一些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中提出如下修改建议。
1 完善立法宗旨——明确“供体权益保护优先”
一般来说,一部法律要在总则中规定此部法律最为核心的法条,包括调整范围和立法宗旨等,而立法宗旨的重要性在于它所表达的是此部法律的法律精神。我们可以发现,《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立法宗旨规定在第一条,即“为了规范人体器官移植,保证医疗质量,保障人体健康,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条例。”显然,这里的“保障人体健康,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表达得太过模糊和宽泛,没能体现器官捐献与移植技术的本质与特征所要求的法律所需保护的各方权益的位阶,即优先顺序,即在这样一个利益冲突明显的领域,没有突出哪些是更为重要的法益,哪种是更为珍重的价值。
1.1 器官捐献的本质——供体承受为受体利益设计的医疗介入
显然,器官捐献是为了受体的利益而发展的医疗技术,其本质可以看作是可选择的(即完全可以不选择)、为了延长受体的自然的生命过程而对供体施加的非治疗性的、具有损害性的医疗介入,因此,一般来说,供体承受了损失而没有受益。也就是说,在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主要的三方参与者中,受体和医方都是受益者,只有供体没有受益且承担了损失。
1.2 器官捐献与移植技术的特征——潜在的激烈的利益冲突
器官捐献与移植技术的特征在于潜在的激烈的利益冲突。具体地说:一方面,受体和医方需要更多的可供移植的器官;另一方面,不仅供体的自主决策权和对自己身体与器官的所有权需要得到尊重和保护,而且,供体作为患者(而非捐献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也需要得到保护。此种利益冲突的激烈性在于它所关涉的是生命可否延续。
1.3 基于技术的本质和特征的权益保护位阶
正是由于器官捐献的本质可以看作是为了延长受体的自然的生命过程而对供体施加的医疗介入,同时,器官捐献和移植中存在着激烈的利益冲突,因此,为了避免利益冲突的伤害,各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的法律中都会制订相关的程序性规则以坚持供体的“患者”身份与“供体”身份分开(即“供体与患者分开原则”),与之相对应的是对于医生来说的“照护患者供体的医务人员”和“与捐献和移植相关的医务人员”要分开(即应该是不同的人),如照护供体的医务人员与摘取和使用器官的医务人员(移植专业的医务人员)和照护受体的医务人员要不同、判断与宣布供体死亡的医护人员要与照护受体的医务人员和参与器官摘取与使用器官的医务人员要不同[1],捐献的尸体器官只有在确定死亡后才能被摘取等,其目的是确保医生忠诚于患者,即器官移植的目的不能使医生放松对可能的捐献者的合法合理的医疗标准的执行。这在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体现为第二十条,即“摘取尸体器官,应当在依法判定尸体器官捐献人死亡后进行。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不得参与捐献人的死亡判定。”显然,这些避免利益冲突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保护器官供体的权益,因此,表达了一个潜在的权益保护的位阶,即供体(而非笼统的器官捐献者)的权益保护具有优先性。
1.4 立法宗旨不完善可能造成的实践困境
显然,供体(而非笼统的器官捐献者)权益保护的优先性对器官捐献与移植技术具有基础的价值指向作用,需要体现在器官捐献与移植的每一个环节中,因此,它应是《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宗旨之一。当前,此宗旨仅仅隐含于《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十条的文字中而没有在第一条的立法宗旨中明确规定,由此,便不能在错综复杂的捐献与移植实践中,尤其是伦理审查实践中起到应有的方向性的价值指导作用。
这里仅举一例:假设有一位从未结婚的先天性痴呆的脑死亡患者,其父母欲捐献其器官。显然,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查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其一为鉴于此脑死亡者生前没有能力表达同意,因此,应同意此捐献;而与之相反的声音则会认为此脑死亡者生前没有能力表达不同意捐献,因此,不应同意此捐献。表面上看,两者意见都有道理,但其实,它们所表达的是基本的价值取向的不同。此时,如果有对供体(而非笼统的器官捐献者)的权益保护具有优先性的价值指导,就很容易发现哪一种才是合理的选择。
1.5 修改建议
由此我们发现,供体(而非笼统的器官捐献者)权益保护的优先性需要以明文规定的形式体现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第一条中。因此,建议将第一条修改为:
“为了规范人体器官移植,保证医疗质量,保障人体健康,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尤其为了保证器官供体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条例。”
2 附条件地增加捐献尸体器官的亲属范围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八条规定,“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也就是说,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时,是否捐献器官由其最近亲属共同决策。此规定具有合理性,但不能规范实践中最近亲属不存在的情形,同时,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遗产继承的规则,即当没有最近亲属(即第一顺位遗产继承人)时,由第二顺位遗产继承人继承遗产不一致,因此有剥夺第二顺位遗产继承人的继承权之嫌。因此,建议附条件地增加可捐献尸体器官的亲属范围。
2.1 离体器官的法律性质
我们可以借鉴普通法通过一系列案例演化而来的在尸体及其器官上的类财产规则,即将尸体和离体器官认定为一种特殊的物,我们可以称之为“类物”,即一方面,离体器官是物,故可以引用与物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保护,如当器官被损毁时,其所有人可以就此损害要求赔偿。同时,将它认定为物,才可能允许器官捐献;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与一般物不同的特性,即它曾是与“人格”合而为一的“身体”的一部分,因此,残留了人格属性。如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离体的人体器官残留了人的特征,而对于亲属来说,此器官更是残留了某个具体的人的特征,因此,对此种“类物”必须给予特殊保护。此种特殊保护在器官的处置上表现为必须合乎公序良俗原则,如器官摘取过程中不能有侮辱动作,摘取后需要重建外形,器官不能随意毁损等;在器官的所有权上表现为对权能的限制(即“有限的所有权”),如禁止在活人间转让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器官[2],对家属来说,其对尸体器官的“使用”以捐献为限,且此捐献只能得到法律规定的适当补偿,不可进行器官买卖等。
2.2 亲属捐献尸体器官的条件
既然尸体和尸体器官是“类物”,便可作为遗产而被法定继承人继承。实际上,亲属可以对尸体器官进行捐献的必要条件首先就在于其因继承而获得的对作为遗产的尸体器官的所有权。然而,所有权只是亲属可以捐献尸体器官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因为器官上残存了供体的人格属性,因此,需要特殊保护。在这里,此种特殊保护体现在对供体的意愿的尊重(即尸体器官是否可以捐献的根本依据在于供体的捐献与不捐献的倾向),也就是说,亲属可以捐献器官的另一个条件在于他们对死者的生命态度、文化信仰和志趣等的了解,即他们了解死者是否愿意捐献器官的倾向。由此,便需要亲属和死者曾长期生活在一起。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亲属捐献尸体器官的条件在于:①亲属对尸体器官具有所有权,即从死者那里继承了尸体器官;②亲属曾和死者长期生活在一起,即了解死者捐献或不捐献器官的倾向。
进而,我们可以发现《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赋予最近亲属对尸体器官的捐献权的合理性。一方面,《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由此,最近亲属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通常可以继承作为遗产的尸体器官,即获得了对尸体器官的所有权;另一方面,一般情形下,最近亲属,即配偶、子女、父母是长期与死者生活在一起的人,即是最了解其生命态度、文化信仰和志趣的人,也即是了解死者是否有捐献器官的倾向的人。因此,由具行为能力的最近亲属捐献尸体器官是合适的。
2.3 扩大捐献尸体器官的亲属范围并附条件
由以上可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规定的由最近亲属捐献尸体器官是合适的。然而,此规定没能涵盖实践中的没有最近亲属的情形,同时,还与上述《民法典》中遗产继承的规则不一致,即有剥夺第二顺位遗产继承人的继承权之嫌。因此,根据上述亲属捐献器官的两个条件,建议附条件地增加可捐献尸体器官的亲属范围。即首先建议扩大作为遗产的尸体和尸体器官的继承范围,也即如果没有最近亲属,第二顺位继承人可以继承死者的尸体和其器官,从而获得尸体和尸体器官的所有权。这样也利于对尸体和其器官的保护。但具有所有权并不意味着是适格的捐献人,即还需要第二顺位继承人中有人和死者长期生活在一起从而了解死者的生命态度、文化信仰、志趣等,也即了解其捐献器官或不捐献器官的倾向,这是器官作为一种特殊的物所残存的供体的人格属性所要求的,即对供体意愿的尊重。
综上,建议将亲属捐献尸体器官的规定修改为: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如果没有前述最近亲属,可以由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且其中必须有人和该公民长期生活在一起。
3 明确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作为尸体器官供体并进行严格规制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八条规定,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同时还规定,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由于需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表述模糊,即没有明确其所指是“供体”,还是捐献自己或亲属器官的人,这就使得“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中的“公民”处于一种灰色地带,即不知尸体器官供体是否包括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此种模糊的立法态度不利于对作为弱势群体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原因在于,这种模糊的态度的本质在于法律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尸体器官供体既没有禁止,也没有进行规范和限制。
从法律的总体精神上看,需要保护弱势群体,即需要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此种保护在器官捐献与移植方面应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需要保护这些弱势群体的与其残存能力相适应的自主决策权,和其有民事行为能力时的意愿,这符合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具体地说,现代民法越来越重视对人之意思自治的维护和对人之自我决策权的保障。比如在成年人的监护制度中,各国纷纷废止了剥夺行为能力的禁治产宣告制度,而新的监护制度均体现了充分调动能力不足者的残余能力、尊重其自我决定和给予其恰当的自治范围的原则[3];另一方面,要充分保护弱势群体的各方面的权益,包括尊重他们的人格权及这些人格权在其尸体器官上的残留。因此,亲属捐献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尸体器官的依据应该是: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生命态度、文化信仰、志趣和捐献与不捐献的倾向;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其有行为能力时的所有观点和意愿,而不是亲属自己的意愿。由此,需要对可以捐献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尸体器官的亲属进行限制,即他们必须与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同时,当无民事行为人不可能表现出基本的志趣和是否捐献器官的倾向,如先天性痴呆者,则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将他/她作为尸体器官的供体,除非指定捐献给其近亲属(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推定其同意)。显然,这是器官捐献与移植中的“供体权益保护优先”所决定的。
4 严格限制下允许“成熟的未成年人”捐献活体器官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九条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也就是说,我国不允许未成年人捐献活体器官。完全拒绝未成年人活体器官捐献的优点是能保护他们不承担风险,且提供了法律的确定性。然而,当今医事法的趋势是赋予未成年人更多的自主性,且完全禁止未成年人捐献活体器官存在一些弊端:一方面,人们普遍接受未成年人对关涉自己的医疗作出力所能及的决策,因此,此种立法方式不能保护有决策能力的未成年人,即所谓的“成熟的未成年人”的自主决策权;另一方面,捐献活体器官有可能是未成年人保障自己在受体(经常是其最近亲属,如父母、兄弟姐妹,尤其双胞胎兄弟姐妹)的生命与健康上的利益的最佳方式,即客观上存在着此种捐献的需求。显然,在存在需求的事务的管理上,法律的疏导与规制应胜于严格禁止。因此,建议在严格限制下允许未成年人捐献活体器官。
4.1 “成熟的未成年人”规则
完全禁止未成年人的活体器官捐献实际上是假定只有当人们到了成年的年龄(我国一般为18岁)才拥有医疗决策能力。显然,对于医疗决策能力来说,未成年人的成熟度和认知能力这些实质性的素质比年龄本身更为重要。实际上,智力和心理发展研究显示11~15岁的未成年人对(包括器官捐献在内的)假设情境的分析能力已经得到了发展。14岁的未成年人的医疗决策能力已经和成年人相似[4]。由此,“成熟的未成年人”规则,即将具有医疗决策能力的未成年人视为成年人,也即允许有决策能力的未成年人自主作出医疗决策在医事法中已有坚实的根基[5]。
根据前述认知和心理学研究,“成熟的未成年人”规则应该也适用于器官捐献领域。但需注意的是,虽然成熟的未成年人有资格作出捐献器官的知情同意,但其同意并非捐献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这是保护弱势群体的要求。
4.2 “成熟的未成年人”的认定:门槛年龄(14岁)与决策能力评估
为了尊重和保障“成熟的未成年人”的自主决策权,建议采用“门槛年龄+决策能力评估”的方式认定未成年人是否是“成熟的未成年人”,即是否有能力作出捐献器官的自主决策。具体地说,根据上述认知和心理学研究,建议设定14岁为门槛年龄,如果未成年人超过此门槛年龄而低于18岁,则对他/她进行灵活的决策能力评估来确认其是否具有作出捐献决策的实质能力(一般包括理解信息能力、保有信息能力、交流信息能力、权衡信息并作出选择的能力)。
4.3 对“成熟的未成年人”捐献活体器官的条件限制
在允许成熟的未成年人捐献器官的基础上,需要对此捐献设置严格的限制,这些限制体现为如下四个原则。
一是(客观上的)“最大利益原则”及“既存的特殊亲密关系原则”。在这里,之所以强调“客观上的”最大利益原则,原因在于此处的最大利益必须为客观利益,并不参考未成年人的主观同意和单纯的心理收益(如自尊心的提升等)。同时,此种(客观上的)“最大利益原则”的判断标准在于未成年人和受体间存在“既存的特殊亲密关系”,也就是说,未成年人在受体的生命与健康上具有足以超过捐献的损害与风险的重要利益,受体的死亡将给未成年人带来足以超过捐献的损害与风险的重大损失。
由此可见,只有当未成年人与受体存在既存的特殊亲密关系时,才能保证捐献符合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为此,立法要对此种捐献的受体有严格的限制。因此,建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14岁以上的具有决策能力的未成年人只能捐献活体器官给父母或兄弟姐妹。
二是未成年人“有意义的同意原则”及“拒绝有效原则”。这里所谓的“有意义的同意”是指确保未成年人的同意是基于完全的理解(即有意义的理解)之上,而非仅仅是同意。同时,若未成年人拒绝捐献,则无论其是否具有医疗决策能力,都不允许摘取器官,即使其与受体间存在特殊密切关系。显然,拒绝有效原则可以通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纯获利行为不受行为能力的限制给予辩护。
三是父母(或监护人)同意原则。由于未成年人比成年人更易受剥削等伤害,而捐献也并非直接为未成年人的利益所设置,因此,此种捐献需要在未成年人的同意之上再设置父母(或监护人)同意,也就是说,即使未成年人有能力作出捐献的决定,任何器官捐献也都要得到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
四是特殊的正当理由原则。多数情况下,器官移植相关法律都要求对使用未成年人的活体器官给出特殊的正当理由,也就是说,除了要求未成年人必须在受体的生命与健康上有重要的利益外,还要有其他有力的原因来支撑为什么选择他/她来捐献。这些特殊的正当理由包括:对于受体来说其他治疗手段不切实可行;没有切实可行的其他捐献者或未成年人捐献器官的成活率非常显著地优于其他捐献者(如未成年人与受体为双胞胎)等。
综上,未成年人为弱势群体,因此,未成年人的同意不能单独授权器官摘除手术,还需证明此捐献在客观上符合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且需有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和特殊的正当理由,这些条件缺一不可。由此,建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
成熟的未成年人进行活体捐献必须满足:
①仅可捐献组织和一侧肾脏给父母与兄弟姐妹;
②除需本人书面形式的同意外,还需其父母或监护人的书面形式的共同同意;
③对于受体来说其他治疗手段不切实可行,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其他供体,或未成年人捐献器官的成活率非常显著地优于其他捐献人。
成熟的未成年人是指14岁以上,经两名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心理医生评估证明具有决策能力的未成年人。
5 法律表述中区分“供体”和“捐献者”
器官捐献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与捐献相关的主体,第一种是器官供体,即承受器官摘取手术的人;第二种是捐献自己器官的人;第三种是捐献亲属器官的人(即作为器官这一特殊之物的财产继承人的亲属)。在实践中,第一种人和第二种人可能重合,但第一种人的范围显然要大于第二种人,如尸体器官捐献中会出现父母捐献孩子器官的情形,其中,孩子本人是供体,但不是捐献自己器官的人。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并没有区分上述三种情形,而将他们统称为“捐献人” “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或“公民”,这种模糊在法律理解上造成了分歧,不利于对器官捐献和移植技术的规范。因此,建议立法中严格区分上述三种主体,或至少区分“供体”和“捐献者”,以免造成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