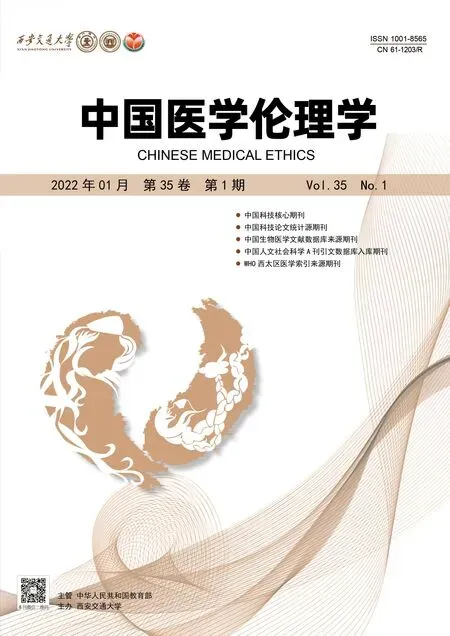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新时代器官捐献*
杜 萍
(海军军医大学人文社科部,上海 200433,371496488@qq.com)
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起步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回顾其发展历程,着实不易。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a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CDCD)成为唯一合法器官来源,中国器官移植的系统性工作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2020年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其中第四编《人格权》第二章《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第一千零六条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利诱其捐献。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1],至此,公民器官捐献有了最可靠的法律依据。当前我国建立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五大体系,即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术后登记体系、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监管体系,逐渐受到世界认可和赞誉。截至2021年7月6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有效志愿登记人数为3 557 022人;截至 2021年6月30日,实现捐献35 030例,共捐献器官103 923个[2]。
对于我国器官移植的系统性工作而言,核心问题在于器官捐献环节,也就是器官捐献的数量与质量。虽然我国在器官捐献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因等待移植患者群体基数庞大,器官的大量需求与不充分供给之间还存在较大矛盾。中国的人均器官捐献率和捐献者的人均器官捐献数量均低于其他国家和世界水平[3]。这并非是单纯的医学问题或管理学问题,而是渗透着社会文化的综合性问题。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使得我国在推进器官捐献工作方面决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模式,而要立足国内,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找寻新时代器官捐献工作的价值引领和情感依托,促进中国器官捐献工作的健康发展。
1 “孝道”与“仁爱”的碰撞
在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中,器官捐献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对身体完整性的破坏,破坏身体被视为“不孝”,会对捐献者造成巨大的道德冲击和心理压力。《孝经》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成为传统社会中奉行孝道的圭臬。这句话从字面意思看,行孝的起点是保护好父母给予的躯体,这是行孝的前提。但从二十四孝记述的故事来看,卧冰求鲤、恣蚊饱血、扼虎救父等为了尽孝而毁伤自己躯体的行为并不罕见,可见对于身体的“不敢毁伤”并非绝对的,要看“毁伤”的目的。从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来看,维护身体的完整性被上升为一种尊严,所以古人将对身体的破坏作为对犯罪者的惩戒列入刑罚之中。《古文孝经孔氏传》有云“盖三代之刑有劓(割掉鼻子)、刵(割去耳朵)及宫(破坏生殖器官),非伤身乎?剕(把脚砍掉)非伤体乎?髠(剃去头发)非伤发乎?墨(在额头上刻字涂墨)非伤肤乎?”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也印证了在当时的社会,毁伤身体发肤对个人的惩戒意义。因此“不敢毁伤”是用于提醒人们行孝的核心应该是遵守社会法纪,不要因违法而受到刑罚毁伤身体发肤。另外,从《孝经》的上下文表述来看,“孝之始也”之后阐述了与之相对应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即爱惜身体,侍奉亲人是孝的开始,是小孝;而立身行道,有所建树,使父母显赫荣耀,是孝的归宿,是大孝。从这个意义上看,身后器官捐献无疑是“立身行道”的表现,是“大孝”之举。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础,对当代社会中从个人到家庭,从国家到世界的诸多问题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孔子认为“仁者爱人”“仁”是做人的根本,既然是根本,就具有普遍的意义,“爱人”是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孟子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仁民爱物”“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他倡导的“仁爱”突破了血缘亲情的界限,将爱的外延进一步扩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人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也要爱其他人,要将别人的父母子女看作自己的父母子女一样[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恻隐”“奉献”等道德精髓,都为今天的器官捐献提供了充分的伦理辩护。器官捐献并不是“不孝”的行为,而是深怀仁爱之心,奉献自我,造福他人的伟大善举。
2 “乐生恶死”与“正视生死”的选择
对于生死的态度及认知也影响着器官捐献的决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乐生恶死”是一种集体文化无意识。我们忌讳谈死亡,甚至用很多词汇代替“死亡”的表述,对死亡充满恐惧。也恰恰是因为恐惧和避讳,“死亡”显得愈加神秘,以此形成负向循环。因此,跟死亡相关的一切都不愿意被讨论和提起,包括器官捐献,因为捐献的决策就意味着死亡的来临。但“正视生死”却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死亡在很多时候猝不及防,现代医学还不具备控制生命长度的绝对技术。儒家的生死观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其生命观的重心是“生”,注重生命的社会价值,强调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孔子注重生,很少谈死,强调“未知生,焉知死?”孟子讲“舍生取义”,阐述了儒家对待死亡的终极标准,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但要死得其所,要赋予死亡某种价值和意义。道家文化崇尚自然,从人和自然的关系中探讨生死问题,主张顺应自然,反对违背自然规律而行事。庄子把生与死融入天地之中,他认为既然生死不可避免,那么人们对生死的态度就应该坦然顺从。儒家和道家文化都重视人的生,倡导尊生惜命,而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有所区别,儒家注重道德和价值,道家追求自然和恬淡。但无论是“乐生恶死”的谨慎还是“正视生死”的豁达,都可以为身后器官捐献找到道德支持。既然生命可贵,死亡又无法避免,那么捐献有用的器官挽救他人生命应该是符合儒、道两家文化的价值判断的。
除去对生死的好恶,传统文化中对死亡的判断标准依然影响着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器官获取的关键节点上,还面临死亡判断标准与器官摘取时机的重要问题,这会影响器官的质量和有效性,国际脑死亡判断标准对保证供体器官的质量最为有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庄子认为人的生与死是气的聚与散的形式转化,“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运用到中医学上,由自然之气到生理之气,也就成为了古人判断生死的一个重要标准----死亡是人体之气的终止。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古代的死亡判断方法中,不但有着心肺死亡(气散)的操作实践,同样也有脑死亡的文化基础。《黄帝内经》谓“失神者死,得神者生”,而神在于何处呢?张仲景在《金匮玉函经·证治总例》中指出:“头者,身之元首,人神之所注”,也就是神在于头脑之中,脑死、神失,人就会死亡。李时珍首次提出“脑为元神之府”“元神”就是人的精神意识活动。清代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写道:“脑髓中一时无气,不但无灵机,必死一时;一刻无气,必死一刻”,他将脑功能活动提高到人的生命活动的主宰地位,无疑是因为注意到了脑与死亡的关联。以上这些观点都为脑死亡标准的确立提供了传统文化的理论支撑。
我国现阶段临床执行器官捐献的死亡判定标准分为三大类:中国一类(C -Ⅰ)为国际标准化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中国二类(C -Ⅱ)为国际标准化心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中国三类(C -Ⅲ)为中国过渡时期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plus cardiac death,DBCD)[5]。其中DBD类判定标准获取的器官质量最高,移植成功率最高;DCD类判定标准获取的器官质量较低,移植成功概率较小,特别是面临的关于“抢救与放弃”之间的伦理争议较大;DBCD类判定标准则考虑了器官摘取需求、中国文化背景和当前脑死亡立法缺位的现状,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创新。近些年来,我国C -Ⅰ和C -Ⅲ类器官捐献占全部身后捐献的75%,脑死亡的观念在中国公民心中逐渐成为主流,这对器官捐献数量和质量的提升非常有益。
3 个人意愿与家庭决策的博弈
中国社会中的家庭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伦理单位。千百年来的医疗实践中,中国的家庭(不仅指核心小家庭,也包括宗族大家庭)作为伦理决策的角色出现很常见,甚至很多时候其决策权力和地位凌驾于个体之上。在我国进行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达个人意愿只是进入捐献流程的第一步,而真正完成器官捐献,不仅需要符合特定的医学、伦理学条件,还必须经过家属的书面同意才能完成[6]。在实际操作中,因家属阻挠而未能成功捐赠的案例非常多。因此,要解决家庭决策对器官捐献工作的障碍,关键在于明确家属为何反对捐献,并设法解决这些问题。儒家认为“家”是社会的基础,是最小的生产单位,也是最实际的社会形式,个人是家庭的组成部分。《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居于社会实践的核心地位,家庭意见对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比其他国家,器官捐献率最高的两个代表性国家西班牙和美国在捐献意愿上实施的是推定同意(presumed consent)和个人决策(individual authorization)制度。这些制度和模式都有不可避免的伦理问题,是否适应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观仍值得商榷。西班牙的推定同意建立的假设是:除非明确表示不愿意捐赠,否则所有符合标准的人都是默认捐献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推定同意并不是真正的个人同意,如果推定同意与家庭决策发生冲突,捐献不会实现[7]。但是以推定同意作为前提,以“决定退出”作为补充在客观上确实能提高捐献的数量。美国使用个人授权制度进行器官捐献。个人进行授权的方式包括在考取驾驶执照时选择意愿或者在捐献者登记处登记授权,个人有确定捐献意愿时不需要咨询家属或与他们分享感受,只有在个人未授权而死亡的情况下才会邀请家庭参与决策。这一制度使得第一授权人的意愿受到了法律保护,而完全忽视了家属的意见,美国家庭在参与捐献决策中被边缘化了。
在中国的文化中,家庭是人与国家之间的基础社会建制,是我们体验生活的核心,也是承担抚育儿童和赡养老人责任的中心,完全忽视家庭的身份和意义,仅由个人决定自己身体的去向和结局,无疑会增加社会的冲突。特别是在面对生死这样的重大问题时,忽视家庭意味着伦理和情感的缺位。因此,在器官捐献的政策机制方面不断完善和细化,提供规范、长效的捐献救助体系以保障器官捐献者的权益,特别要重视家属的意愿表达,明确他们在保护逝者权利和承担社会道德方面的双重责任,让捐献者家庭感受到公平公正和充分尊重,让他们有更好的思念承载方式,才是促进家庭决策向着有利于捐献方向发展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