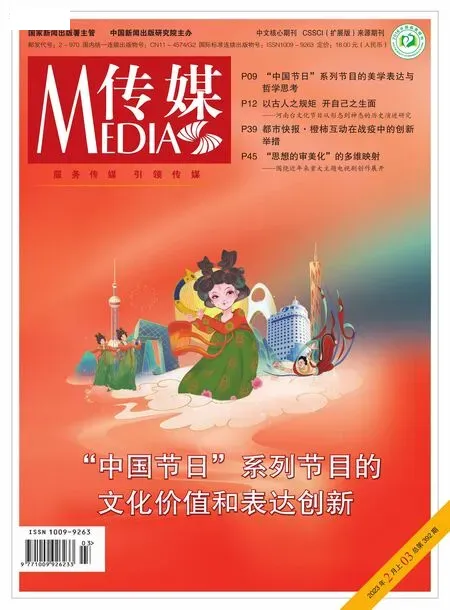网红经济与MCN管理机制研究
文/刘嫱 吕欣
2022年1月至3月,本研究课题组对国内某主要MCN机构进行了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括该机构首席财务官(CFO)、MCN业务负责人及数名网络红人,内容涉及“你觉得网络红人作为职业其特殊性在哪?”“作为MCN机构管理者,如何看待点击量转化?”“怎么看待人设?”以及“聊聊签约MCN机构后每天的工作节奏”等非固定结构的开放性问题,时长在30至60分钟不等,以此深入探究并尝试理解网红经济与MCN管理逻辑、网络红人的生存现状和社会意涵。
一、网红经济与MCN机构
时至今日,互联网俨然成为构建公众生活方式的核心场域,我们的劳动、消费、娱乐、社交等社会行为业已全面嵌入网络空间。当公众注意力、信息消费内容以及社会资本不断汇聚于网络媒介平台时,互联网经济乘势崛起。技术的裹挟促使数字内容生产与传播的权力下移,一时间,来自社会多阶层的公众不断涌入UGC平台,营造出了“人人皆网红”的时代错觉,而那些“从草根到精英”的数字劳动者并不愿承认他们曾经历过“劳不对酬”的状态。
1.从“网络红人”到“网红经济”。自2016“网红元年”以来,“网络红人”作为社会热词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然而“网络红人”的概念却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兴起之时,即在互联网场域内引发民众关注的人或物,其生成与传播机制均受互联网媒介自身的特殊性影响。“网红经济”则是在2015年淘宝召开的“网红现象研讨会”上被提出的一种新的“互联网经济形态”,指由网络红人所带来的经济活动及经济收益。由于网络红人在特定垂直领域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力,网红经济将网络红人在各大平台上聚集的人气和注意力转化为对产品的购买力,在迎合粉丝受众需求的同时实现定向精准营销。网红经济一经出现便成为数字从业者的“新蓝海”。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网络红人、博主、UP主等内容创作者的劳动方式、劳动场景和劳动产品的形态,重塑了他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却没有改变机器大工业时代所形塑的资本市场与传媒产业间的内在逻辑。
2.MCN机构的多重属性。网红经济的迅猛发展离不开MCN机构的加持。MCN(Multi-Channel Network),即多频道网络,最早出现于YouTube,指签约多个PGC账号,并为其提供资源扶持、合作管理等服务,以实现内容持续输出的组织或公司。在国内,适逢网红经济兴起,内容提供者需要实现商业变现,广告商需要精准寻找适配的营销载体,各大互联网平台需要优质内容留住用户,MCN的概念便本土化为一种基于多频道网络的新型网红经济运作模式,负责连接内容制作方、广告商和平台方。自此,传统的“资本—劳动者—消费者”的三元劳动关系链条,在网红经济背景下呈现出了“资本—中介组织—劳动者—消费者”的新形态。
作为内容产业的重要链路,MCN机构“游说”于内容制作方、广告商和平台方之间。一方面,MCN将内容创作者聚合起来,利用自身资源为其提供内容生产管理、平台对接、广告代理、流量引流、粉丝运营、社群维护等服务,使其既能深耕于内容创作本身,又能实现持续可靠的商业变现;另一方面,MCN机构分别为广告商、平台方提供优质的广告代理与稳定的内容输出,构建了“内容—渠道—运营—受众”有机互动的闭环运作模式。在本研究的访谈过程中,有受访者提到“MCN并不是内容和流量的所有者,而是分配者”,侧面印证了MCN的中介属性。作为“网红孵化器”,MCN机构在网红经济运营中的作用更为突出。通过筛选、培育、签约,融合多种内容创作形态,将内容创作者孵化为网络红人。MCN机构以一定比例与网络红人分成,这种分成大多在签约时就已经就写入协议中。值得一提的是,MCN机构普遍有一整套针对数据分析和后期维护的逻辑和方法论,具有系统和完善的账号维护体系,强调数据赋能的运营逻辑。

3.新近变化。据艾媒咨询《2021—2022中国MCN行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的MCN机构数量超30000家,市场规模已超过330亿元。预计2022年MCN机构数量超40000家,2023市场规模或将达到500亿元。网红经济的持续盛行让劳资双方看到了依旧可瓜分的明显红利,入局者井喷式爆发。许多UGC平台的头部用户滋生了成为网络红人的想法,各大平台也越来越关注到MCN机构的重要性,先后推出了自己的MCN机构及招募合作计划,如B站的超电文化、萌派等。在B站、抖音、快手、小红书等文化社区和视频平台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后,大量处于分散状态的博主不得不顺从平台的数字化指标,以点击率、流量为核心,将自己的喜好让步于受众的关注,去进行内容生产劳动。UGC平台从展示自我的分享场域,变成了逐利的盗猎场。
与此同时,MCN机构的头部优势逐渐显现,从早期广告主和品牌方的“非必选项”变成了“必选项”,全素人晋升网络红人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变得越发困难。随着网络红人群体的不断壮大,人们对“网络红人”的表述逐渐精简为“网红”,其词性内涵也几经辗转、褒贬不一。在与受访者A的沟通中,笔者得知,MCN机构更愿意把他们所孵化的“网络红人”称之为“红人”或“达人”,而不是“网红”,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网红现象背后的大众心理变化,以及网络红人在业界身份的浮动。
二、网络红人的身份构建
通过了解网络红人的劳动实践、心理状态和身份认同,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下网红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劳动问题,进一步揭示当前网红经济与劳动关系的本质和规律。
1.数字劳工+情感劳工的双重身份。关于对“数字劳动”的概念探讨由来已久。斯蒂安·福克斯认为“数字劳动是生产性劳动,包括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链条上涵盖各种劳动”,并在其研究中分析了不同类型的“数字劳工”,如生产计算机硬件设备的工人、开发软件的程序员和工程师、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内容产销合一”的用户等。蒂兹纳·特拉诺瓦借用拉扎拉托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将用户在网络平台上进行的信息浏览、内容发布和社群互动等行为都视为数字劳动。质言之,数字劳动作为数字时代的一种新型劳动形式,涉及数字媒体生产、流通与使用所需的各种体力和脑力劳动。“情感劳动”的概念也与非物质劳动理论联系紧密,属于非物质劳动的类型之一。Hardt和Negri指出,非物质劳动涉及情感的生产与控制,并要求(虚拟或实际的)人类接触,即身体模式上的劳动。情感劳动主要与非物质服务、无形情绪和沟通行为的生产有关。情感劳动并非传统马克思批判理论所述的强制性劳动,而是一种主体性的生产,情感劳工在实践中自我肯定、自我驱动,以获得自洽的认同与满足。
MCN签约红人的工作内容与工作方式,决定了其数字劳工和情感劳工双重职业属性。他们既要完成包括脚本撰写、素材拍摄、后期剪辑在内的数字内容生产,又需要在其中投入大量的情感劳动,如自我陈述、情绪表演、与粉丝沟通交流等,符合上述关于数字劳工与情感劳工的诸多外延。
2.他者认同与自我认同。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野来看网红经济,很难摆脱对资本权力的审视,从而忽略对个体微观层面变化的关注——网络红人的自我建构与价值认同。互联网经济中的劳动参与也可以是积极主动的、富有创造性的、充满交互的,蓬勃发展的UGC文化就是最好的佐证。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具客观性与真实性,对于网络红人的身份构建这一议题,笔者从他者(MCN机构管理者)和自我(MCN网络红人)角度分别进行了深度访谈。
受访者B为MCN业务负责人,阐述了网络红人的身份属性——跻身素人与明星之间,比素人更易受到大众关注,但没有所谓的“明星光环”,收入与普通职业相比较高,但生命周期未知,喜忧参半。受访者B还提到网络红人需要直面自己的所有数据,每一条数据带来的结果(涨粉、掉粉等)都会被频繁地看到。而且网络红人的工作环境单一,通常只跟固定团队合作,线上社交广泛,线下社交匮乏,因此他们也比普通人更容易焦虑。MCN签约红人则普遍将自己看作有一定话语权的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简称“KOL”),希望能做出正向的文化、价值输出而不仅仅是“恰饭”赚钱(受访者E),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受访者F)。他们对自己的职业选择是满意且自豪的,能够从内容生产中收获认同感和满足感。
有趣的是,笔者在访谈中发现,对于网络红人的身份认同,MCN机构的管理者和红人给出了几乎相悖的思考态度,前者侧重“焦虑”“生命周期短”“工作环境单一”等消极层面,后者则强调了“KOL”“内容生产输出”“实现自我价值”等的积极层面。双重性的回答恰恰建构了MCN网络红人身份认同的完整逻辑:一方面,网络红人劳动背后的确存在着隐形剥削;另一方面,网络红人在劳动过程中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和情感获得。
三、平台询唤:作为网红经济的驱动逻辑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首次提出了“询唤”(Interpellation)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人作为自由的个体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行走,当听到背后有人呼唤时会不自觉地转身,以一种新的身份去体验所处的环境,从而结束了自由个体的状态,这一过程即为“询唤”。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功能,把具体的个人询唤为具体的主体,以确保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阿尔都塞认为,个人一旦被“询唤”为主体,一般情况下是“自己起作用”,因为主体的本质是无意识地臣服。此时,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就不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强制性的、被迫的,而是自动的、服从主体意愿的。
把上述概念放在网红经济的背景下:资本平台构筑了一套“走红”的逻辑,对用户的思维进行建构,使其相信“人人皆网红”的合理性与真实性,并臣服于平台制定的劳动规则——这便是“询唤”作用的达成途径,它支配着网络红人的实践立场和态度。平台采取非暴力的形式对用户进行涵化劝服,让他们对现有的劳动结构和关系从不怀疑越矩,自由安分地做好网络红人的角色,忠实地维系着网红经济中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系统。其中,非强制性的思维控制在平台与用户之间建构了一种特别的召唤关系,网络红人受到召唤进入到内容生产中,在内容生产中获得了主体性。在这个过程中,网络红人看似有着包括弹性的工作时间、无拘束的创作空间、人性化的管理体制在内的绝对自由和话语权,殊不知,这种赋权只是资本平台与MCN机构联合制造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现实是一整套对劳工进行控制的隐形机制。
四、询唤之下MCN机构的管理机制
在资本平台循序渐进的询唤和MCN机构的管理驱动下,网络红人认同“数据为王”“兴趣化劳动”“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等概念并将它们贯穿工作始终,不断适应同行之间的激烈竞争,花更多的自由时间提升自身素质和创作能力,强调规训与自我负责,主动地为“资本增值”服务。
1.数据规训。当前互联网经济生态中的劳动者并不独立,平台限制使他们成为“平台依赖型创业者”(Platform Dependent Entrepreneur),在享受平台给予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平台的诸多约束。比如许多网络红人在创作或发布内容时,都困扰、受限于不明确的账号权重、无从得知的最佳分发时间,以及谜一样的流量池算法等等。米歇尔·福柯将既与学科、知识技能体系相关又与训练、纪律惩罚体系相关的特殊权力形式定义为“规训”,使其成功的手段是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平台以琢磨不透的算法黑箱作为规训的手段,完成对网络红人劳动行为的隐形限制与裁决。MCN机构也深谙此道,有一套完整的规则去管理网络红人,“定时更新”“周更日更”“点击率”“粉丝转化率”等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简称“KPI”)被事先拟定在合约之中,在算法和数据库的支持下,以一种精确隐蔽的方式对网络红人的劳动行为进行操纵和控制,使签约的网络红人不得不随时随地拍摄、加班加点剪辑,以完成内容更新、粉丝转化等KPI。
除了来自平台和MCN机构的监视,观众也在“规训”的火堆里添了把柴,一条视频的好坏全看观众买账与否。福柯曾将目光比喻成“权力的眼睛”,认为观看是一种权力的实施。观众在观看视频时以一种群体围观的方式对网络红人形成监视,监视着他们的更新频率和内容的好看程度,网络红人的生产权利逐渐让渡给了观众的消费权力。
MCN机构、平台及广告商透过数据,将网络红人的个人价值与其生产的内容进行捆绑,并将点击率、粉丝转化率等直接量化为经济收益的指标,对网络红人的劳动行为进行规范化裁决,决定其收入的多寡。正如边沁“全景敞视监狱”隐喻一般,MCN机构、平台方、广告商及用户群作为现实时空的补充和延伸,使得网络红人难逃资本和技术的监视与规训。在被迫接受规训之后,网络红人们对数据极为敏感和信任,他们偏执地相信如果一条视频的点赞过低,那一定是因为内容不够好,并会不停地反思到底哪里不够好(受访者D)。这种对数据的过分依赖,以及高时长、高情感投入的数字劳动极易引发焦虑情绪,成为异己的力量影响网络红人的心理状态。他们逐渐按照平台规则来认知世界,在面对技术逻辑时不得不做出调整和改变,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其作为价值主体的创新力和引导力。同时,数据对网络红人的规训也导致了其行为的趋利性,如果一些内容的反馈数据好,他们会下意识地去做同质化的内容。
2.保护与“冷启动”。签约MCN机构的网络红人与处于分散状态的头部用户相比,其劳动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受保障,可以对创作内容及合作的广告商进行筛选。通常情况下MCN机构的商务会先过滤掉三无或口碑不太好的产品,制作人会根据品牌调性将内容推荐给相应的红人,但最终的决定权仍保留在网络红人手上(受访者B)。虽然可以选择最优的广告主,但MCN网络红人却难逃“冷启动”的隐形控制。MCN机构不会轻易解聘已经孵化成熟的网络红人,但对素人或者粉丝基数小的红人,会设置两到三个月的“冷启动”周期,在周期内对他们进行正常孵化,观察其成长模型和潜力,以淘汰不达标的红人(受访者A)。由此可见,虽然MCN机构会在一定层面上对签约红人的生产内容进行保护,但一些新签约的红人承受着被数据规训甚至惩罚的压力,被点击率与转化率量化,承担可能被解聘的风险。
3.生活世界劳动化。乔纳森·柯拉瑞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中指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无休止的需求导致一系列界限的消失:白天与黑夜、公共与私人、活动与休息、工作与休闲。网络红人的工作模式印证了其观点的真实性。他们通常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这就意味着休息的时间也同样不明确。受访者C在聊到自己一天的工作安排时,说道:“从睁眼到睡前,我都在工作。自产内容就是这样,需要不停地构思一系列跟内容有关的东西。”受访者G也表现出了对“难以切割的工作与生活”的疲惫:“做博主有一点很不好的地方就是,不管去哪里、做什么,都想拍下来,因为这些可能成为视频素材,不管未来能不能用上。久而久之,整个生活都变成了工作。”不限时间地点的网上工作本应是一种自由,但从受访者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种趋于隐蔽化的剥削方式,只是乐意为之,或者无力改变。
此外,网络红人发布的内容蕴含着社交属性,其劳动产品不仅包括数字化的图文、视频,还包括与粉丝之间带有情感因素的社交关系。因此,网络红人不仅要迎合粉丝喜好创作视频,还要花时间和精力维系与粉丝之间的良性关系,如回复粉丝评论和私信,开直播间与粉丝互动等。这些互动并不总是积极正向的,许多网络红人都会被恶评困扰。
也许,网络红人承受的最大压榨是工作对生活和情感的裹挟。对他们来说,生活是工作的素材,情感是工作的必需品。网络红人会为了涨粉停滞或者掉粉而感到焦虑,为了留住现有的粉丝且获得更多的粉丝,他们只能不断“内卷”,尽可能把内容做到优质精良。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付出更长的工作时间,压缩自己的生活,把生活彻底劳动化。
五、总结与思考
MCN网络红人的劳动权益和实际生存状态,能够映射互联网经济体系中的其他劳动个体,用宏观的视角来看甚至能够衡量整个网络社会的文明程度。当绵密的数据监视取代内容自生产的真正福祉,一步步消耗网络红人的身份属性,让他们丧失了合理的生产报酬、基本的休息时间和自由的创作权利,迫使他们将自己的生活、情感和社会关系异化为纯粹的劳动产品之时,就有必要对网红经济的本质保持清醒认识。应长期关注“网红经济”生态发展样态,抑制平台、广告方、MCN机构三方异军突起的垄断行为,维持资本与媒介的平衡;充分发挥网络红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探索构筑良性“询唤”的方法,实现个体的全面解放,保证数字从业者包括收入权、休息权、自由权在内的基本劳动权益,促进网红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而提高社会幸福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