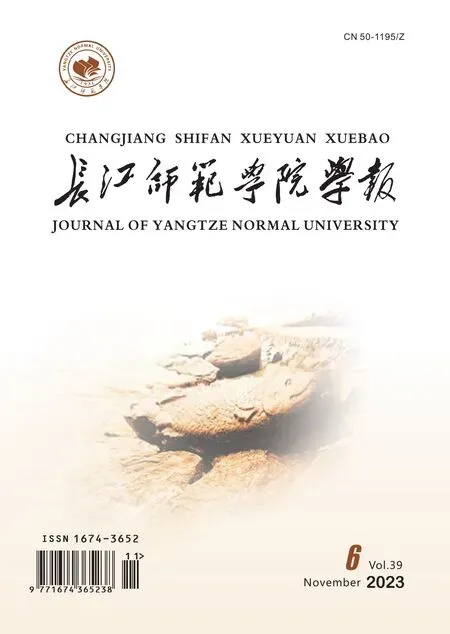中国文化记忆研究的主题聚焦与现实实践
李嘉鑫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000)
文化记忆理论由阿斯曼夫妇完善,于20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文化记忆理论传入之初便引起国内学界的热烈讨论,涉及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与民俗学等多个学科。经过数年沉淀,学者们开始将文化记忆理论与我国历史现实相结合,将其应用到具体问题的分析上。现如今,我国文化记忆研究已经涌现出众多成果,且已有学者围绕文化记忆理论发展进行研究回顾。但是,前人在进行研究回顾时主要聚焦于文化记忆的理论探索与跨学科应用,而忽视了学者们将文化记忆理论应用到国家认同、文化自信、文化传承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努力。因此,本文在叙述文化记忆理论的发展脉络与中国图景的基础上,着重论述文化记忆理论在国家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理论实践。
一、文化记忆研究的缘起与完善
20世纪以前,西方社会对于记忆的认知尚停留在生理主义和个体主义范畴,以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为代表的心理学家致力于从心理学角度进行记忆研究。转折来自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bwakh),他为记忆研究提供了社会框架与集体概念。
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的研究围绕两个维度展开,即集体记忆的界定及其与个体记忆之间的关系。记忆在社会性动物中是一种社会化活动,因此,不同于单纯的历史记事,包括集体记忆在内的各种记忆都是基于现实实践进行的“回忆”,即重构。而回忆的进行则需要一个集体性框架下的唤醒机制,这种机制依赖于具体时空的媒介刺激。当个体受到刺激进行回忆时不是对过去的如数家珍,个体的回忆内容依附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框架与群体内其他成员的刺激。在此基础上,哈布瓦赫开始回答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关系。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集体记忆为个体记忆提供框架,个体记忆通过集体记忆实现自己。社会个体只有将自身代入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中才能进行回忆,而集体记忆则是众多个体记忆的有机整合。所谓的有机整合并不是众多个体记忆的简单相加,而是集体记忆在一定现实条件下将个体记忆视为结构要素以特定的方式进行建构。在哈布瓦赫看来,这里的特定方式是有能力有条件对过去事件进行再叙事与新解释的机制,而这套机制在某些语境中则被视为“国家在场”。
哈布瓦赫将社会学视角引入记忆研究领域,但是他仅强调集体记忆的客观现实性,相对忽视记忆的传承机制。在此之后,以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与阿斯曼夫妇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记忆的传承机制进行研究。
“记忆之场”是诺拉在重新审视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概念,并在1978年为《新史学》撰写“集体记忆”词条时给出定义。诺拉指出,记忆之场是社会、国家、民族和政党自愿放置记忆内容的场所,是他们的记忆可以被找到并作为其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场所。在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一书中,他从三个层次对记忆之场进行了界定。“从‘场所’一词的三种意义上来说,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的和功能性的场所,不过这三层含义同时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1]记忆之场具有四个特点。首先是残存性。记忆存在损失的可能,承载记忆的空间也会随着历史发展出现残缺,并最终成为某种记忆唯一的物质承载。其次是互动性。记忆之场的完整性要求“记忆—承载物—记忆主体”相互作用,其中作为记忆主体的人只有不断地进行仪式重复才能使记忆之场得以维持。再次是多变性。同一个记忆之场对不同记忆群体而言承载的记忆是不同的,其用途也是不同的。最后是广涉性。记忆之场并不要求以客观的地理空间而存在,虚拟空间、建筑空间等都可以作为记忆之场存在。
与诺拉同时代的阿斯曼夫妇则是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扬·阿斯曼(Jan Asman)的文化记忆理论是在继承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扬·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是一种机制。它被抽取出来、对象化,然后存储在一些象征形态当中,后者不同于听到的言语或者看到的姿势,它是稳定的、超然于具体情景的,它们也许会从一种情景转移到另一种情景之中,从上一代传承给下一代。”[2]扬·阿斯曼强调记忆、团体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认为文化记忆兼具认同、重构、形式稳定、组织依附、价值评价与自反性等特点。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一书中,扬·阿斯曼基于时间角度对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进行发展,提出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并从记忆内容、记忆形式、记忆媒介、时间结构以及记忆承载者五个方面进行区分界定。在对文化记忆进行时间性梳理之后,扬·阿斯曼从空间维度考察文化记忆的传承媒介、知识结构与交际形式,提出口头文化的“仪式关联”与文字文化的“文本关联”,并指出在仪式一致性向文本一致性过渡中“卡农”起到的关键作用①扬·阿斯曼指出卡农的书写文本与“传统之流”的差异在于文本的固定性与神圣性,这使得卡农的书写文本是不可以被改造,更不允许被亵渎。扬·阿斯曼从四个方面总结卡农的潜在含义:(1)强化恒定性:从精确到神圣。(2)消除差异:基于理性的关联与约束力。(3)界限的强化:两极分化。(4)价值成分的强化:促进身份认同。所以,当一种文化群体内部出现分裂、传统失去效力的时候,群体成员便有必要做出决定,选择遵循何种秩序,这便是卡农形成的时机,也彰显出卡农所具有的促进强化身份认同的功能。参见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此外,扬·阿斯曼还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出发提出民族身份认同及其持久性受制于文化记忆及其组织形式。与扬·阿斯曼关注于早期文明中的远古记忆不同,阿莱达·阿斯曼(Aleda Asman)从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进一步探究文化记忆理论,并以记忆的功能价值作为参考标准,将文化记忆划分为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
在此之后,文化记忆研究呈现全方位发展态势。首先,西方学界就重大历史事件探讨现实中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双向互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罪行、苏联时期的国家创伤以及东欧剧变都深刻影响了欧洲的集体记忆与记忆研究。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学界持续关注“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及因技术革新和人口流动带来的集体记忆弱化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出“旅行记忆”“跨文化记忆”及“世界性记忆”等新概念和新问题。最后,在文化记忆的多学科参与方面,文化记忆理论不仅影响了社会学、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研究范式,还拓宽了文学、心理学、传媒及景观学的问题视角。
二、中国文化记忆研究的主题聚焦
中国学界对文化记忆经典理论具有全方位认知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开始为文化记忆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在文化记忆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文化研究,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理解过去二十年中国学者所做出的努力。
(一)记忆的强化:象征与阐释
根据文化记忆理论对文化的解释:“庆典和仪式是无文字社会用来把文化内涵的扩张情景制度化的最典型的形式”[3],即文化记忆形成关键在于仪式的经典化。所谓经典化,便是将特定仪式加以典范、神圣的制作过程[4]。伴随着仪式经典化的完成,一套象征体系与权力话语便得以构建,承担记忆专家角色的统治阶层正是通过对仪式解读权力的掌握达到对社会的控制。之后,仪式对文化记忆的垄断逐渐让位于文字书写,但是仪式所承载的祖先记忆、情感根基在维系族群团结、传承文化等方面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5],故而仪式的记忆垄断逐渐过渡为记忆强化、记忆传承与记忆认同。今日之仪式,便是借助特定的文化形式与符号象征来表达、强化群体共享的文化记忆。这种文化记忆是高度凝结的,仪式中的特定行为、象征符号、时间地点等因素会以压缩凝练的形式存储大量文化信息与价值标准[6]。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区域、各民族以及各群体都拥有历史悠久、受众广泛且内涵独特的群体性仪式。伴随着文化记忆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我国学界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化记忆理论应用到仪式研究中,在提炼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象征仪式进行记忆阐释。李菲通过对嘉绒藏族锅庄舞中身体表述的研究发现,仪式中象征符号具有能指与所指双重含义。对于嘉绒藏族而言,“右旋”作为固定化的身体表述,其背后所承载的是远古先民的本教信仰以及本族群共享的祖先记忆[7]。高海珑基于在河南地区火神会期间的田野考察提出“神话记忆模式”,该记忆模式是指在一个文化体系中神话记忆以特定的格式得以保存。以火神祭祀为例,作为族群祭祀仪式的“火神会”需要借助特殊的祭祀机构和流程,以特定的符号仪式来表现火神神话的象征,并通过各种仪式行为对火神记忆进行传承[8]。除此之外,声乐祭祀、黎族打柴舞、梅山教“跄太公”仪式和苗族还傩愿等都是当地族群进行祖先追忆,表达民族信仰与价值观念的重要方式。
伴随着全球化对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冲击,学者们开始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出发对传统节日的传承与保护、节日仪式的变迁与发展和仪式主体变迁等命题进行研究。袁理脉借助对苗族四面鼓舞的田野调查,展示了在经济社会环境变迁以及族群主观价值认同变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四面鼓舞作为传统仪式逐渐被附加强身、观赏、娱乐以及文化传承等功能[9]。黄彩文将壮族皇姑节视为承载地方记忆与民间信仰的节庆活动,伴随着“非遗化”与仪式展演的实现,其文化功能扩展出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的作用[10]。
(二)记忆的展演:文本与场域
仪式之后,文本与场域成为文化记忆焕发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媒介。文化记忆视角下的文本是指代替先前口耳相传与祖先神话并使历史记载与传统解释多样化的传播模式,而这种传播模式最初表现为被上层社会垄断的文字作品,后来伴随着社会变迁以及技术发展,记忆文本呈现多元化趋势,印刷品、现代传媒以及信息技术都是记忆传播的重要媒介。至于场域,“任何显著的实体,不论其实质是物质还是非物质的——只要它成为某一社会记忆遗产的象征性元素,就可以称之为记忆场域”[11]。因此,记忆场域并未局限于人为创造的物理空间,还包括自然空间与虚拟空间等。文本与场域作为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两者在表现形式、记忆传递以及发展变迁中具有各自的特性。具体而言,记忆文本的主要载体以文字作品、影像制品为主,记忆场域以地方空间、展演空间为主。
文化记忆理论传入中国后,在文学创作与传媒影视等领域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讨论与反思。文化记忆对中国学者而言不仅是理论学说,还是研究视角、阐释策略与实践路径[12]。学者们不仅关注中国语境下的记忆书写与生产,还从文化记忆的视角审视文学作品、影视创作与文化活动的功能、价值与变迁。刘顺总结了文化记忆视角下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的三个路径,包括记忆的内容、记忆的展示以及记忆的认同[13]。洪治纲基于对不同年代文学创作风格的总结,指出不同代际作家群写作叙事与审美选择的差异源自“不同历史文化语境和成长记忆对人类精神的潜在规约”[14]。张爱凤通过对新兴的文化综艺节目进行观察,指出由国家主导的原创类文化综艺节目在对抗娱乐资本、凝聚社会共识与塑造国家自信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5]。毕旭玲围绕“康王建城”故事的版本变迁,指出基于现实所进行的文化记忆重构在“康王建城”的叙事变迁中得以体现,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城市自身社会经济状况变化引发的自我调适[16]。
记忆场域不等同于简单的物理空间,既充当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媒介,也经历着记忆的重组与建构。不同于阿莱达·阿斯曼强调记忆场域内部的权力话语、记忆选择与表征过程,我国学者对记忆场域的研究更具现实性[17]。我国学者充分认识到历史文化悠久的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类型的记忆场域,并围绕记忆场域的空间叙事、知识生产与功能发挥等主题展开研究。其中,樊友猛、吕龙和刘玉堂等重点关注乡村文化记忆对乡村旅游、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张静、孟阳和王润等关注城市建筑中存在的空间叙事。基于市场同质化对记忆场域的侵夺,我国学者主要关注城市记忆场域的文脉延续和乡村记忆场域的复兴与再利用。郭凌指出城市的历史传承与人文精神塑造离不开城市记忆的凝聚作用,因此在快速城市化的当下进行城市记忆重塑是有必要的,同时指出在维护城市记忆空间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社会变迁的必然性与记忆空间的再生产[18]。记忆场域内部的结构关联与话语体系也是我国学者关注的重点。王华对乡村社会“高音喇叭”的角色转变进行研究,指出“高音喇叭”权力话语转变的根源在于国家权威与市场力量的“拉锯”[19]。除此之外,我国学者在近几年开始注意档案馆、博物馆在传承文化记忆中扮演的角色。哈丹丹以民乐县乡村文化展览馆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乡村博物馆在记忆传承中的作用以及集体记忆的建构路径[20]。
(三)记忆的关照:历史与建构
基于记忆对群体的现实价值,文化记忆被划分为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那些被当下人民持续进行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记忆被称为功能记忆,其突出特点表现在群体关联、现实建构与价值选择。当某种记忆在群体中得到巩固时,这种记忆背后的符号象征与价值意涵便存在被取舍的可能,并被赋予新的符号系统与寓意象征[21]。因此,功能记忆并不是持续尘封于文本中的文字,而是带有鲜明的群体痕迹与时代烙印。对于功能记忆的承载主体而言,他们倾向于将记忆借助文化书籍、建筑空间与信息传媒等外在媒介和仪式活动、集体回忆与纪念庆祝等实践活动加以强化、重构与传承。因此,对功能记忆的研究便是将当事人认为的历史当作一种有利于当下存在的记忆[22]。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者的研究重点不仅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还有过去对特定人群的影响,无论过去的实践主体与特定人群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历史、现实、记忆与建构的关系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便被以王汎森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关注。进入21世纪,我国学者从文化记忆的理论视角出发,基于中国文化记忆的延续性、整合性与多元一体性以及中国历史的“悠久、详密和不间断”进行历史与现实研究,其中既包括以族群认同、文化变迁、文化传承和神话传说等为对象进行的历史记忆研究,还包括以近代以来标志性事件和公众性历史人物的记忆形象为研究对象所展开的探讨。毛睿在对马来西亚华人群体进行研究时指出,在20世纪后半叶马来西亚持续恶化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汉丽宝公主和亲故事作为马来西亚的地方民间故事,被马来西亚华人群体通过文学创作、话剧展演与时空追溯等手段积极主动塑造为承载历史价值、凝聚族群认同的文化记忆[23]。黄浩将黄飞鸿的公众形象代入具体的创作时空中,指出黄飞鸿形象的转变离不开文学创作与影像建构,而在创作过程中现实社会的时代变迁不断在黄飞鸿系列作品中加以展现,同时在黄飞鸿的作品中岭南被塑造为具有特殊想象意义的文化记忆空间[24]。除此之外,当下社会的文化记忆重塑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其中尤为关注在非遗、文化传承等语境下群体所进行的记忆再现与重塑。张崇借助青田朱氏宗族文化记忆重建的案例说明,族谱、纪念场所、特定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等都是将特定文化记忆进行传承的重要因素[25]。王焯以“祖家坊”为个案,展现了人们在充分认识到“老字号”的现实价值后将其积极转变为一种实践互动,并以此进行记忆重塑[26]。
三、中国文化记忆研究的理论实践
(一)记忆理论与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国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的国家的心灵性活动”[27]。对于历史悠久延续的中国而言,国家认同在中华文明个体身上不仅表现为政治性国家认同,即对社会主义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认同,还表现在文化性国家认同,即对“文化中国”的认同①从不同维度去理解“中国”的国家概念,可以有“王朝中国”“制度中国”“地理中国”“文化中国”等不同解释。其中文化中国是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根基,它存在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又借助各种象征符号加以表达,如汉字、图画、礼乐等。参见刘刚、李冬君《文化的江山》,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其中,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而文化中国及其文化记忆则是文化认同的根本。因此,文化记忆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文化记忆为国家认同的形成提供了有效资源,包括合法性支持、情感纽带和行为认同,等等;另一方面,国家认同是当今各个国家、民族构建文化记忆的目标和归宿②关于文化记忆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部分学者从国家认同的四个维度出发进行论述。殷冬水认为国家认同的时间维度关注的便是文化记忆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探讨的是国家如何借助历史书写和记忆选择来创造合法性。参见殷冬水《论国家认同的四个维度》,载《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我国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研究文化记忆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一,学者们探讨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杂交时代如何借助文化记忆强化国家认同。张德明强调民族文化记忆问题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坚持文化身份认同的核心问题,但是不能回归到保持本土文化“纯洁性”的原教旨主义中,应该坚持在整体自我意识基础上与他者进行开放交流[28]。冯绍坤强调在当下国际话语体系中历史叙述话语权的重要性,指出个体身份认同是由共享的历史与文化记忆界定的,历史叙述的话语权利是否掌握在自己手中决定了一个民族是否把握“围绕话语所确立的自我身份”[29]。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我国学者也注意到信息传媒在文化记忆与国家认同互动关系中充当的新变量。黄卫星指出在开放联动的互联网中文化记忆凸显多元、矛盾与立体的特性,使国家认同变得具有选择性、对立性与多重性。这便要求我们在全球化冲击主权边界和文化身份的“危机”下积极规避互联网对个体身份认同的弱化和对文化记忆的消解[30]。其二,学者们立足于国家认同的视角充分发掘有助于增进国家认同、增强国家意识的文化记忆。吴娜重视红色文化记忆在塑造国家认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红色文化记忆建构的宗旨在于强化国家认同[31]。傅成婕、罗峰与杨婕等重视现代传媒中文化记忆再现对身份认同塑造的重要作用。
(二)中华民族文化记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二十大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3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3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我们必须科学准确地把握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与现实格局。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历史发展中中国各民族形成了在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格局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共享一套塑造“自我”和区分“他者”的文化记忆,即中华民族文化记忆。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传承、发掘与唤醒,在增进中华民族团结、激发中华民族共有情感、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根基和共渡中华民族难关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科学理论与指导方针提出之后,我国学界也注意到中华民族文化记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互动关系。
现如今,我国学者对中华民族文化记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互动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四个维度展开。首先,从学理上论述文化记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冯月季认为文化记忆所塑造的民族认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情感维系的作用,而中华民族认同是基于文化符号所进行的中华民族文化记忆重塑[34]。麻国庆注意到中华民族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民族交往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的关系[35]。其次,从文化记忆理论出发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特别是文本、场域和象征符号在其中所发挥的功能。王楠将文本书写和空间场域作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集体记忆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通过记忆形塑和情感触发唤起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36]。再者,关注文化记忆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文化逻辑,学者们都注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蕴含着被各民族共享的大一统思想和历史传说。王丹等通过对民间神话传说的研究发现蕴藏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文化根基。武沐等叙述了中国大一统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各民族不断塑造丰富的历史,突出中国少数民族在大一统历史中的重要地位[37]。最后,侧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文化记忆个案研究。一方面学者们强调不同类型文化记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如龙柏林等关注到红色记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强化、信仰凝聚的作用[38]。另一方面,重在发掘凸显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文化事项中的集体记忆,例如学者们对三线建设、文学作品与公共记忆等进行的研究。
(三)中华民族文化记忆与文化传承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39]这段论述不仅讲明了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容与目的,还指明了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方法路径。根据文化记忆理论对文化传承的解释,文化传承兼具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两个维度:一方面,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框架与现实需要中被不断重塑与阐释,以此实现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另一方面,历史流传下来的“组织化、经典化”的文本、场域和仪式等充当着记忆“冷藏”的媒介[40]。文化传承便是在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的交互中进行,且两者缺一不可。尘封文本的文化记忆需要人们的活态传承加以唤醒,而实践中的交往记忆则需借助定型、稳定的传承媒介来克服时间局限性,以期实现“回忆—认同—延续”的传承路径[41]。对于中华民族文化记忆而言,因其连续性与阶段性可以划分为三种记忆类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记忆、中华民族革命文化记忆和社会主义先进时期中华民族文化记忆。这三种文化记忆在当下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因此社会对这三种记忆的传承、唤起存在不同的路径。
我国学者基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进行文化传承的研究试图避免陷入二元对立的困境,并且认识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和多层叠加、融合变化的复杂情况”[42]。他们强调文化传承并不是对传统的简单效仿,而是基于当下社会的现实需要与实践主体的多元性而进行的“活态化”记忆重塑。具体而言,我国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围绕四个维度展开。其一,对中华民族文化记忆在当下社会的传承与变迁进行研究。其二,围绕“怀旧”与“乡愁”两大主题,关注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记忆断裂。其三,对文化传承“仪式动力”的关注,尤为关注舞台展演对文化传承的价值。张爱凤、张晶、文卫华、赵谦等强调现代文创纪实类节目对文化记忆的传承作用。其四,对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的研究。
四、结语
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梳理和总结,笔者发现中国文化记忆研究存在“引入学习—学科应用—现实实践”的线性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学者的研究凸显了三个特点。首先,中国文化记忆研究的跨学科性与现实性。文化记忆理论在中国发展的二十余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现代与过去、发展与传承、书写与解构之间的冲突不断凸显。文化记忆理论在此时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开创性的学术视角,它被学者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加以广泛应用。这种研究不仅推动了文化记忆理论的深化与实践应用,还促使我国学者从记忆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和中华文化的传承路径。其次,对中华民族文化记忆延续性、阶段性和多元一体性的充分认识①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延续性、阶段性和多元一体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华民族文化记忆存在“根文化”,这种“根文化”在时间维度上赋予了中华民族文化记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在空间上则促进中国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情感认同。其次中华民族文化记忆是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孕育不同性质的文化记忆,对这些性质差异且一脉相承的文化记忆的传承、发掘则需要借助不同的手段。最后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多元一体性是基于中华民族发展格局提出的,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各民族所存在的独特民族记忆,但也不能忽视“根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记忆情感认同中所发挥的维系作用。,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记忆与西方民族文化记忆的根本差异。一方面,中华民族文化记忆所具备的这三个特性,使中国文化记忆研究避免陷入西方学者强调通过文化记忆建构“想象共同体”的困境,而是强调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线性发展,它在今天所发挥的价值作用并不是被单纯建构出来的,而是在历史传承基础上的现实重塑。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导致学者们对中华民族各时期所留存下来的文化记忆持有不同的审视态度,这种态度有利于当下合理推动各种类型文化记忆的发掘、唤醒和传承。最后,国家在场。西方学界的文化记忆研究虽然也会涉及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但是在中国,个体、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表现得更加深入,这也使得中国社会被持续包裹在国家权力话语体系中。因此,相比于西方社会提供的无序解决方案,中国社会在面临诸如非遗、文化传承、文化振兴和民族团结等重大课题时“国家在场”可以提供有序组织的上层解决方案。这也使得中国文化记忆研究与中国重大社会话题保持着紧密联系。
但是,中国文化记忆研究也存在几个突出问题。一是相对缺少对他者文化记忆的关注与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便不断被我国政府在国际上进行倡导与提议,也被多数国家领导人赞同与肯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依赖于各国人民民心相通,而各国文化记忆的沟通交流、各国人民对他者文化记忆的情感共情是实现民心相通的有效途径。因此,中华民族文化记忆有必要走出国门并被其他民族感知认识,同时中国文化记忆研究也应重视对其他国家、民族文化记忆的研究,以期更深层地认识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民心所想。二是相对缺少国际对话。自西方文化记忆理论传入我国之后,我国学者将主要目光集中在经典文化记忆理论和中华民族文化记忆,忽视了近些年西方学界基于文化记忆所展开的理论探讨与学术争论。这种画地为牢的方式非常不利于中国文化记忆研究的持续发展,我国学者应当积极关注国外学术的发展趋势,并将国际上的新提法、新视角、新命题等积极介绍给国内学术界,以期实现中国文化记忆研究与国际文化记忆研究的接轨。三是相对缺少对博物馆、档案馆等记忆展演空间的重视。博物馆、展览馆作为城市空间中历史文化展演的重要媒介,在文化记忆唤醒、传播和记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且馆内空间设置、展品布局、灯光色彩等因素会影响展演效果。因此,对该领域进行现实性研究有利于借助展演活动增进个体的国家认同,增强个体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感知度。针对此问题,我们应当在借鉴西方做法的同时,根据自身的文化特色开展行动。四是现实实践研究有待继续深入开展。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新提法和新论断,这些论断和理念需要文化记忆理论从自身的问题视角出发围绕新命题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