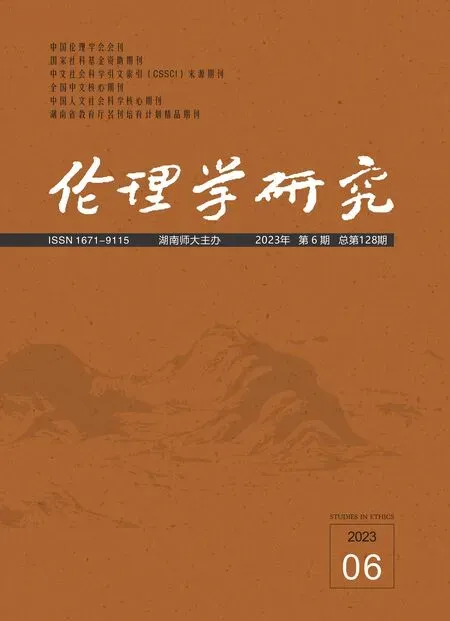传统社会乡贤文化及其当代实践转换
许源源,涂颖洁
崇贤尚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之一,也在传统政治活动中得到了践行。《尚书·尧典》提到“明明,扬侧陋”,表明帝尧因虞舜为贤能之人而予以重用。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认为“大同”之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传统崇贤尚能的理念不但体现在国家层面,在基层社会中亦是如此,“乡贤”即为这种政治理念在传统基层社会中的极佳例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100)随着现代化洪流滚滚前行,在农耕文化下孕育出的传统乡贤文化,经过增删补益和实践转换,可以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提供一种重要的备选方案。
一、古代乡贤文化的伦理意蕴和功能
“乡贤”这一概念诞生于东汉年间,《辞源》记载:“东汉孔融为北海相,以甄士然祀于社。此称乡贤之始。”[2](3117)乡贤指代的是群体,是植根于乡村沃土的民间力量,他们热心地方公务,推行社会教化,能够用自己的德行对乡民产生正向影响和引导作用[3](70-71)。乡贤的本质前提是“乡”。从地域上看,乡贤是在当地有一定威望的社会贤达,具有本土本乡的地缘属性,是民间治理的代表,也是凝聚各种乡村发展力量的重要“粘合剂”[4](96)。乡贤的根基是宗族。乡村社会对乡贤具有极强的识别力,作为精英群体的乡贤,无论是离土离乡还是留守乡土,都嵌套在乡村社会结构当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特性,决定了乡贤回归乡土社会的情感动力来源[5](133-134)。乡贤的依附是村庄。村庄是乡贤的家园,是他们的活动生存空间,也为孕育乡贤文化提供了土壤。费孝通指出:乡村的熟人社会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人与人之间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表现为“差序格局”,人的行为约束不是靠“契约”,而是靠默认的行为规范和信任[6](34-36)。传统乡贤通过率先垂范、劝诫教化等来形成并维系村庄内生秩序,不仅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国家治理的服务半径,减少了国家的治理成本,成为行政嵌入式民间治理的重要辅助手段和民间治理的重要方式[3](72)。正因为乡贤的产生和发展有其不同的特点,所以古代乡贤文化具有独特的伦理意蕴与功能。
1.乡贤文化的伦理意蕴
乡贤在传统乡村治理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是基层社会管理的中坚力量,在基层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乡贤文化正是以传统乡贤为基础而产生的具有独特精神气质和浓郁乡土气息的伦理文化。
乡贤文化是一种崇贤尚能的伦理文化。传统社会是以伦理纲常为本位的社会,强调“以德为先”,社会治理强调血缘宗法与社会伦常的有机融合。尧舜禹“禅让”的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原因之一是它充分契合了尚贤的理念。西周时期,人们在政治上追求“敬德保民”“德主刑辅”,儒家强调个人层面的立德修身和国家层面的“为政以德”。春秋时期,礼乐崩坏,战乱纷纷,诸子百家积极地思考社会治理的出路。孔子认为,政治应该尚德政、举贤才。在乡贤的文化实践中,伦理是评判其社会行为的价值准绳,其价值观念、人格操守、行为模式无不为伦理纲常所覆盖。“乡贤文化是中国历朝历代乡贤德行凝结的意识形态的集合”[7](63-67),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乡贤文化体现了中华传统伦理精神。乡贤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规定的有关社会生活和个人行为的伦理精神。乡贤在传统乡土经济社会活动中,所遵循的天人合一、仁礼统一、性善为本、重义轻利等伦理模式,都体现着儒家伦理的价值意蕴,是儒家道德观念系统、道德行为系统、道德心理系统的集中呈现。乡贤是乡土社会良知的杰出代表,从“志于学”到“不逾矩”,从“学思结合”到“反身内省”,体现了乡贤对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的追求。乡贤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民众,既有君权化的官方色彩,又有民间化的个体痕迹。乡贤既可以立庙堂享忠君之禄,又可以归乡里被孝亲之泽;既体现逃逸隐世的出世精神,又体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精神。乡贤文化是古代乡土文化与社会宗法制度对冲的结果,也是乡贤对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的感悟和体认。
乡贤文化是一种践行美善德行的文化。乡贤之“贤”,所表现的是“德贤”。从字面上言,“贤”特指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所谓贤明、贤达、贤良,皆包含贤行,所以“贤”很大意义上是一种伦理概念。乡贤是乡村的精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深受他人的信任和爱戴,乡贤文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8](30)。也就是说,“贤”既是一种道德意识,也是衡量乡贤的内在道德尺度,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乡贤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贤”也会变成文化自觉,成为一个人是否成为乡贤的重要前提。“贤”能激励乡贤拓宽自己的道德视野,进而促使他们在道德比较中对自己的德性进行精进与提升。因此,“德贤”的引领力量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以“忠”与“孝”等行为范式带领乡土社会形成习惯力量,构筑乡民的自觉意识,在乡村道德教化和民众安抚中具有显著作用。
2.乡贤文化的政治功能
作为乡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乡贤以自身的嘉言善行垂范乡里,为激励乡土后生奋发有为发挥着重要的榜样作用。
乡贤文化是乡村“德治”的伦理基础。乡贤的文化特质,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尚贤与德治有着紧密的关联。乡贤在维系伦理关系与乡土认同,促进淳德教化、定纷止争,加强宗族治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儒家所倡导的从个人到国家层面的德治成为主导后,中国传统社会认同的政治清明的关键就在于识别并提拔德才兼备的人,如此,“德”与“贤”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样的政治理想,为基层社会中孕育出乡贤文化提供了良好的伦理基础。乡贤及其文化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费正清更是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称为“乡绅社会”[9](32-39)。在传统社会中,乡贤是基层社会管理的中坚力量,在基层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皇权不下县”这一说法的由来[10](64)。乡贤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性精神文化的标识,其本身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而家国同构的传统亦为乡村德治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可见,乡贤及其文化构建了乡村德治的伦理基础。
乡贤是乡村“德治”的政治力量。《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三不朽”为后人评判乡贤提供了价值尺度。春秋战国时期,乡贤被称为“父老”,即年高德劭的闾里老人,他们在乡村社会具有较高威望。西汉制定并实施的“三老”制度,把乡间“能率众者”纳入社会治理体系中,明确指出“三老”应以身作则,引导乡民崇德向善。汉代以降,统治者为了教化老百姓,广泛开展祭祀活动,地方官员和士大夫积极参与。这些说明乡贤能够“被当作是独特的基层治理模式,贤能政治基于选贤举能机制,将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分配到各个政治管理岗位上,为政治实践活动奠定担保的基础”[11](25)。因此,在浓厚的乡贤文化背景下,兼具德才和威望的乡贤,可以分担乡村治理的责任,在基层社会中扮演管理者、协调者的角色,承担了以宗族教化为底色的政治教化任务,为乡村社会的安定提供保障。这是传统中国乡村治理的常态。
乡贤文化是维系乡村“德治”的精神基石。强调家国同构是乡贤的文化职责,也是乡贤的政治任务。传统乡贤之所以能够在乡村甚至国家层面立德、立功、立言,是因为它代表的是国家主流文化秩序,是官民之间上通下达的桥梁,因此乡贤能够深受百姓拥戴,进家谱入祠堂,入方志登国史。需要指出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因为中国传统的社会行政系统并不直接参与最基层的乡村治理,而乡村能够长治久安往往需要乡贤发挥积极作用。实际上,在封建社会中,皇权需要通过乡贤以非组织化形式延伸至乡村社会。作为乡贤这一群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士绅,拥有大量基层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资源,从而将国家与基层社会衔接起来,起到沟通上下的作用,使皇权力量能够在基层社会中得到充分体现。换言之,皇权并不是没有触及乡村民间,它只是通过一种更加隐蔽或伪装后的方式,对乡村民间实施治理,而乡贤就是终端治理的执行者。
整体而言,乡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贤这一群体的伦理特性,使其成为传统社会和谐安定的“稳定器”,为促进乡村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近代乡贤文化的式微与解体
自鸦片战争始,中国国门洞开,皇权加速没落,乡贤的作用也在不断减弱。及至新中国诞生之前,帝国主义持续对我国进行经济、文化掠夺,战争也蔓延到了乡村地区。他们觊觎中国乡村所积攒的有形文化财富,采取抢、偷、烧、毁等方式,能带走就带走,不能带走就毁坏,乡村的文化体系遭受重创[12](49-50)。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代乡贤文化持续式微与离散解体,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清朝末年统治阶级废止科举制度对乡贤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众所周知,从隋朝到清朝,科举制是广大读书人尤其是下层子弟实现阶级跃升最主要的途径。元代之后,四书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因此读书人只需要学习四书五经,即可抓住阶级跃迁的机会。《牧令书》有记:“士为齐民之首,朝廷法纪尽喻民,唯士与民亲,易于取信。如有读书敦品之士,正赖其转相劝诫,俾官之教化得行,自当爱之重之。”[13](32)可见,无论是上层社会还是基层社会,士绅乡贤通过科举进阶之后,有着很高的社会威望和丰富的社会资源,是国家政权需要笼络的特权对象。然而,当晚清政府宣布“自丙午(1906 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延续了1300 多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废科举从源头上掐断了乡贤赖以产生的政治通道。而彼时诸多乡间读书人,他们空有四书五经的知识,不但无法进入仕途,甚至难以养活自身。人们信奉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念,在时代不断前行的进程中被侵蚀,读书人亦沦为又穷又看不到希望的群体。此外,高昂的税负、频繁的战争,导致乡村社会出现权力真空,彼时,各种所谓的江湖豪杰、不法商人、三教九流都涌现出来,企图掌握真空下的治理权力,导致乡村社会结构变得更加杂乱无序。
在社会历史迅速变迁的进程中,传统的德才兼备居于乡村的乡贤群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之人才流失,使乡村传统文化道德的空间不断被侵蚀,乡贤亦变得鱼龙混杂进而其权威性大打折扣,导致乡贤存在的主客观条件被瓦解,传统的乡贤文化亦摆脱不了凋敝的命运。
2.近代乡贤的优劣分流导致乡贤文化逐渐走向衰落
传统中国是以“伦理”为主导的,乡贤士绅通常兼具“一家之长”和“一乡之望”的双重身份。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乡贤能够在乡村甚至国家层面引导乡民崇德向善,在诉讼调解、开办学堂、教化民风等方面也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为乡村社会的安定提供了有效保障。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政府、乡贤和农民之间的固有关系被打破,乡贤群体自身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外国工业的侵入,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几乎被全面摧毁,“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来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14](715)。这不仅导致大量农民破产而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也造成了农民与政府、乡贤间的矛盾激化。乡贤群体亦随之发生转变,有的最终演变成了欺压百姓的劣绅、土豪,并逐渐占据了权力核心位置,走向了农民的对立面。1908 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设立城镇乡地方自治机构,规定“城镇设议事会议员,以二十名为定额……城镇乡议事会议员由本城镇乡选民互选任之”[15](731-732),企图把地方自治的权力交给地方士绅,既想改善地方社会秩序,稳固其统治基础,又妄想可以减少其基层社会的管理成本,重建其皇权的权威性[16](323-324),但土豪劣绅早已把握了地方权力的核心,清政府的这种转变并不能改变其统治的本质。
虽然部分传统乡贤依旧存在,但是他们已经不能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表,也不能正常发挥上通下达的桥梁作用。在这种大变局的历史进程的推动下,乡贤群体已然转型,传统的乡贤文化亦随之迅速式微,乡贤文化在基层的影响力迅速下降,以往以崇德向善为精髓的乡贤文化也被这个特殊的时代逐渐遗忘。
3.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人才涌入城市促进乡贤文化解体
近代以来,清政府被迫开埠通商,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贸易往来,刺激了清朝经济。据《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记载,1901 年清政府财政收入总额为8820 万两,海关税占2470 万两,所占比重已达28%,成为仅次于田赋(占34%)的第二大税种[17](253),而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比如上海等地更是迅速地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工商业的发达使城市经营实业赚取的经济效益远超务农所得,城市成为国民经济生活的轴心。再加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幅提高,大量的乡村人才为了改善生活,前往城市谋生。与此同时,居民的消费重心逐渐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大量的洋货商品也让城市的吸引力逐渐增强,而乡村的传统手工业则走向没落,人才外流严重。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这一五千年来都同泥土打交道的民族,因泥土而辉煌,亦因泥土而没落。”[6](1-7)在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城市化的强烈影响下,加之西方经济文化的侵蚀,部分乡贤群体对本土本乡的情感愈发淡薄,即使他们始终眷顾家乡,但现实的压力使他们逐渐脱离了乡村社会,乡贤的基础人群被击溃,这对传统的乡贤治村与乡贤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在东西方文化不断冲突融合的大背景下,以往自给自足的封闭环境、彼此互助的熟人社会、纲常伦理的绝对权威逐渐成为过去式。不管是拥有一定学识和能力的读书人,抑或经济实力比较充裕的有钱人,都会离开乡村,去拥抱新型的生活方式。传统乡贤群体亦变得更加地分散,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乡村以及乡贤在内忧外患的现实冲击下,逐渐陷入更大的困境中,乡贤文化迅速解体。
三、现代乡贤文化的转型和超越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民公社模式”,到改革开放后的“两委治村”模式,在乡村治理问题上党和政府一直在探索。传统乡贤群体的消失和乡贤治村模式的终结,让与之相辅相成、互相塑造的乡贤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载体和政治基础。
1.现代乡贤文化的转型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深入到基层社会,一方面,制定并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方面,逐渐赋予村民更多的自治权。与此同时,政府不断推进城镇化建设,乡村的变化日新月异。近年来,在新型乡村治理体系下,乡贤文化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各级政府也持续推动乡贤文化在中国式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继续绽放异彩。与此同时,乡贤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变化,乡贤亦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即所谓的“新乡贤”。“新乡贤”是本地精英与在外典范的结合体,不管是本土的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专家,还是在外打拼事业的学者、商人甚至官员,若是愿意利用自身的资源反哺家乡,塑造良好的道德风尚,为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都可以称之为乡贤。新时代的乡贤重新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的民间力量,用“新”字来冠名这一群体,不只是确认了这一群体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文化价值,也是确认了这一群体在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和正向作用,确认了其在健全乡村公共治理体系中承担的重要职责。如今,乡贤参与村治演变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即中国现代的“新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是乡村文化体系中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为深远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构成元素。它承载着中华传统美德,体现德治善治的历史经验,在维持乡村社会和谐发展上助力颇大。进入新时代,新乡贤作为社会治理参与者,在乡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重要力量。立足于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这一历史时期,置身于新时代社会文化发展背景,研究新乡贤文化独特的属性,特别是它所蕴含的崇德向善的人文道德、德治善治的伦理效应,从而推动新乡贤文化主体、角色、功能进行新的超越,意义重大。
2.现代乡贤文化的超越
(1)主体超越:推动新乡贤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催生了新乡贤群体,新乡贤亦成为乡村社会的新生道德力量。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需要从文化的角度进一步厘清新乡贤的判断标准,推动新乡贤主体不断超越。
其一,推动新乡贤构成从单一向多元转换。在过去几年间,为实现新乡贤文化的创新发展,实现新乡贤主体的多元化,国家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不断为新乡贤队伍的壮大和新乡贤返乡建功立业营造良好的环境。地方政府也行动起来,结合当地的实际,拟定并实施“回巢计划”,推动新乡贤通过新的方式承担乡村治理的职责,不断建立健全乡村治理结构。2023 年7 月20日,农业农村部等九部门联合下文,开展“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提出要引导品行好、有能力、有影响、有声望、热衷家乡建设事业的专业人才、经济能手、文化名人、社会名流等能人回乡参与建设,鼓励引导退休干部、退休教师、退休医生、退休技术人员、退役军人等回乡定居等。这些人群,都是未来新乡贤多元化发展的依托,只要他们够“贤”够“能”,就能够成为新乡贤的一员。
其二,推动新乡贤的价值取向转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发展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使命。新乡贤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者,其价值取向、精神状态和综合素质,将直接影响新乡贤文化的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进程。因此,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要引领新乡贤增强爱国情怀,心怀家国,坚定地跟国家站在一起,把个人理想和国家的命运、乡村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要营造尊重、鼓励新乡贤的社会舆论氛围,激发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培育他们的使命感和自豪感。要推动新乡贤坚守传统乡贤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等道德立场,发扬重视家庭、家教、家风的优良传统,引领乡村道德发展。要引导新乡贤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正确处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勇于创新,诚信守法,立足乡情,寻求乡村发展的正确方法,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2)角色超越:推动新乡贤成为公共伦理的弘扬者
推动新乡贤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骨干精英,必须倡导新乡贤传承传统乡贤文化蕴含的崇德向善的优秀文化基因,推动他们成为公共伦理的弘扬者,成为乡村德治善治的能者,为构建现代新乡贤文化、塑造良好的社风民俗提供新的道德范本。
其一,推动新乡贤成为公共精神的倡导者。公共伦理,是乡贤文化最重要的文化意蕴。弘扬公共伦理而产生的公共精神,是新乡贤文化精神的核心内涵。公共精神是社会主义公民道德最基本的要求,培育公共精神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乡贤文化建设中文化精神的具体化呈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乡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特别是乡村振兴给乡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的社会风尚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新乡贤是乡村伦理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载体,也是乡风文明“软环境”建设的先锋,他们的所作所为,有着润物无声的渗透作用。因此,要使新乡贤公共精神的弘扬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同频共振,就要大力挖掘乡贤文化中的伦理资源,合理设定公共伦理标准,重塑乡贤伦理文化在公共生活中的表达方式。要通过新乡贤的道德行为,彰显民主观念、公正理念、责任意识等公共精神,带动农村公共精神的培育。
其二,推动新乡贤成为公共道德的践行者。加强乡村道德建设,除了通过教育传递道德知识外,还可以通过新乡贤的道德实践,引领乡民道德意识的培养和道德行为的践履。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新乡贤道德示范工程建设结合起来,与新乡贤文化建设推进工程结合起来,全面提升新乡贤的道德水平。要着力在新乡贤道德建设的长效机制上下功夫,进一步完善乡村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规范,使新乡贤成为乡村公共道德的践行者。要联系乡村生活实际,大力开展乡村公民道德建设主题实践活动,鼓励新乡贤参与公共道德建设,依托文明村镇创建、传统节日和农村文化活动等载体,为新乡贤的道德实践提供平台,让新乡贤以实际行动回应乡民对改善公民道德建设状况的期待,并形成良好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要对新乡贤在乡村公共生活中的表现,诸如遵纪守法、移风易俗、家庭和谐、邻里和睦、公益事业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充分发挥新乡贤对乡村公共生活的引领和渗透作用。
(3)功能超越:推动新乡贤成为时代精神培育者
新时代催生了新乡贤,亦催生了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加强新乡贤时代精神的培育,进而推动新型乡贤成为时代精神的培育者,是乡贤伦理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
其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全过程。新乡贤不仅是乡村社会德行的标杆,也是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上的实践者[7](6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但延续了古代优秀传统价值观,同时也承载着当代价值观念,是国家主流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构传统乡贤文化,推动乡贤文化的共融再造,是新时代必须解决的新课题。因此,要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新乡贤的自觉追求,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同时,要进一步丰富乡贤文化时代内涵,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实际活动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行动指南,将国家主流价值观融入乡村治理中,既尊重乡村熟人社会历千百年而形成的道德规范,又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在乡村道德文化建设中以身作则,引导村民积极向上向善,追求美好生活。
其二,以乡村公共治理体系统领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在乡村治理中,新乡贤不仅是公共精神榜样、道德教化的力量,同时也是乡土文明的继承与发扬者,是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桥梁与纽带。因此,在乡村振兴中,要把乡村公共治理与新乡贤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以乡村公共治理体系统领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全过程。要鼓励新乡贤积极投身于乡村治理的创新实践,努力营造有利于他们干事创业的氛围,使他们在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大潮中站在时代的前沿,与其他乡村治理主体互嵌共融、形成合力,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的成效。要动员他们担当好产业发展指导员、村级事务监督员、村庄建设智囊员、邻里矛盾调解员等的角色,在乡村教育、尊老敬老、关爱儿童、帮扶济困、招商引资等方面,深挖资源价值,带动壮大村集体经济。要对新乡贤参与村级治理的内涵和外延给予具体的界定,在坚持村党组织和村委会是治理主体的基础上,将新乡贤这一文化力量嵌入到乡村治理结构中,形成治理合力,使乡村振兴能够利用的文化力量更为强大。
总之,传统乡贤文化深深镌刻着地域精神文化印记,成为离乡游子维系乡情的重要精神纽带,更是激发乡贤反哺乡梓的精神原动力。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关键是要在党的领导之下,激发社会各界特别是新乡贤的潜能。将新乡贤更多地融入现有治理体系中,进一步彰显新乡贤文化的伦理蕴意和道德功能,使其为乡村治理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