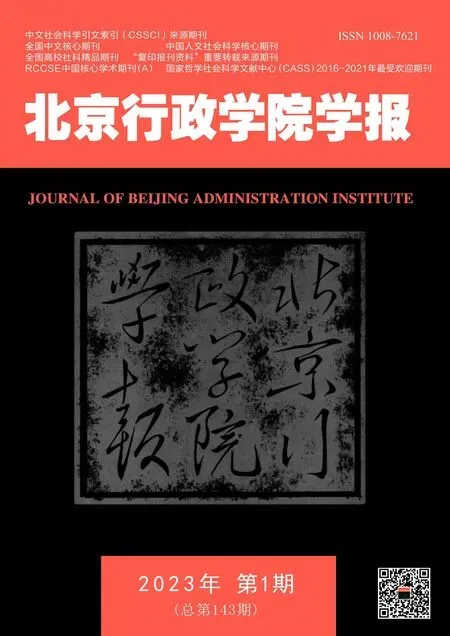如何识别相对贫困:海外研究的学术谱系与前沿动态
□吕普生 陈子旋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大痼疾。21世纪伊始,联合国将“发展与消除贫穷”列入了《联合国千年宣言》。2015年,联合国又制定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把“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作为首要目标。随着近百年来全球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越来越多发达国家摆脱了绝对贫困而步入治理相对贫困的阶段。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陷入绝对贫困境地的同时也面临着愈发严重的相对贫困问题,甚至在特定的衡量标准下,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贫困发生率高于发达国家[1]。
作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2]。在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后,我国的反贫困事业将面临方向性调整,即把反贫困的重心转移到治理相对贫困、统筹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与消除绝对贫困不同,相对贫困的治理任务将更为艰巨,原因首先在于相对贫困在贫困认知上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在衡量标准上具有复杂的多维性,在贫困特征上具有明显的相对性。故而,相较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往往更加难以被发现和测量。
正因为上述特点,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和研究方法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由于暂未发现一种科学完备的相对贫困理论可以囊括所有问题要点,目前学界几乎难以对全球范围内的相对贫困现象作出全景式描绘和整体性归因,也难以对全球的相对贫困治理提出普适性的方案。正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那样,贫困问题只能是一个描述性陈述,而不是一个规范性陈述,人们通常所使用的贫困的“政策定义”也存在着根本缺陷,难以准确把握政策制定中的政治问题[3]29-34。
尽管相对贫困的这些特性加大了研究难度,但并不意味着无法对其开展相关研究。目前国内学界对于相对贫困的内涵、测量方法、贫困线划定等问题存在着一些争议,而海外学界由于对相对贫困的研究开展得较早,对上述争议性问题的探讨已取得一定进展。在我国反贫困事业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海外学界围绕相对贫困问题特别是如何测量和识别相对贫困群体展开的学术研究进行系统性跟踪,提炼其学术脉络和发展谱系。测量和识别相对贫困群体,是相对贫困治理的前提工作。就目前中国的相对贫困治理而言,只有找到“测量和识别相对贫困的科学准则”,才能精准地绘制中国相对贫困人口的地理空间和群体空间分布图,从而为精准而有效地开展相对贫困治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系统地梳理海外学界关于测量和识别相对贫困的学术传统和前沿动态,能够为我们发展一套契合我国实际的相对贫困识别理论和科学准则,提供思想和理论资源。
基于上述考量,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重点关注海外学界关于相对贫困内涵、致贫原因、测量方法、贫困线划定依据等问题的研究,因为这四个问题是理解和把握相对贫困的核心问题,只有以这些关键问题为导向,才能较为完整地呈现既有研究谱系。二是以研究视角为区分标准,将海外代表性研究分为相对收入贫困、多维贫困、增长性贫困与主观贫困四类,在阐述各自观点基础上评述其得失。之所以以研究视角为标准展开分类,是因为研究视角是区分不同研究路径的主要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项研究的学理逻辑与研究进路,进而最终影响其研究结论。另外,之所以选取上述四种研究视角来刻画研究谱系,原因主要有三:其一,不可否认,海外既有研究存在其他分析相对贫困的视角,但这四个研究视角所涉及的代表性文献数量占据该领域研究的较高比重;其二,这四种研究视角界限分明,基于每种视角所展开的研究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其三,四种研究视角下的相对贫困问题都是贫困研究领域的经典议题,总体上能够呈现出海外学界就相对贫困研究提出的基本理论观点。此外,四类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既存在并列关系,又存在一定的层次递进关系。在系统评述各类代表性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最后还将展开相关学术讨论,并对中国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的研究空间和趋势作出展望。
二、收入贫困视角:相对贫困研究的单维进路
相对收入贫困视角源自本杰明·西伯姆·朗特里(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的收入贫困研究,他认为贫困线需按照“获得维持体力的最低需要”的货币预算进行划定[4]。据此,朗特里提出人口统计比率(Head Count ratio,H)的测量方法,该方法以“获得维持体力的最低需要”的货币量化收入作为贫困线,然后从收入分配角度测量收入低于该贫困线的人口数[5]。这一测量方法得到了汤森(Townsend)、韦斯布罗德(Weisbrod)等学者的广泛应用。之后,巴彻尔德(Batchelder)采用了另一种将贫困线与收入分配相结合的方法——收入差距比率(income-gap ratio),该方法的目的是测算所有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缺口占贫困线本身的比例[6]。这些经典的收入贫困测量方法为其他学者定义和测量相对贫困提供了有益启发。
(一)从相对收入对比中识别相对贫困
参照朗特里关于收入贫困的思考进路,德塞尔夫(Decerf)认为相对贫困应该如此定义:由于社会参与的成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变化,因此相对贫困阈值取决于所处社会的收入标准。而如果一个人的收入远远低于所处社会的收入标准,使自身面临被社会排斥的风险,他就被认为是相对贫困[7]。可见,在德塞尔夫的定义下,一个人是否处于相对贫困的境地,取决于其个人收入与社会标准收入之间的对比,并且判断标准的关键并不是低收入本身,而是低收入带来的社会排斥。2002年,挪威政府推出《反贫困行动计划》(Action Plan for Combating Poverty),其对于相对贫困的定义也体现出衡量贫困人口个人收入与社会一般收入二者之间差别的重要性。该计划指出,相对贫困是如此一种状态:“个人收入低,可能加上与疾病和损害等相关的高必要支出,从长远来看,他们无法满足基本的福利需求……发现自己的个人收入与人口中的一般收入水平有显著差异。”[8]
“相对贫困体现在相对收入对比之中”,这种结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相对贫困的定义问题,但对于“相对贫困线应以何种方法进行划定”这一问题,国外学界又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从现实来看,目前国际上存在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两种贫困线,在众多的相对贫困线里,影响范围较广的是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采用的平均收入比例线或收入中位数比例线。国际上的相对贫困线虽然已经被正式应用于贫困衡量工作,但部分学者认为它们仍存在较大的缺陷。这部分学者从不同理念出发,利用各自所掌握的数据,提出了不同的相对贫困测算方法,力图提出新的相对贫困线。
(二)相对收入贫困的测量与划定
阿特金森(Atkinson)和布吉尼翁(Bourguignon)在研究中希望能够寻求一个同时衡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贫困的框架,这种框架的形成需要克服不同地区关于绝对贫困的定义差异难题。其研究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利用一条关系生存的绝对线和一条关注社会排斥的相对线来产生综合指数,以此评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所利用的两种贫困线是由达到特定能力水平所需资源的价值所决定的[9]。这一思路启发了德塞尔夫,他改进了阿特金森等人的框架,设计了一个新的相对贫困衡量框架。简单来说,德塞尔夫的框架采用了一个绝对线和一个“混合”相对线,同时设定后者的所有阈值都高于前者。这指的是,在绝对线的阈值以下,收入贫困的相对方面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当一个人不是绝对贫穷时,其贫穷的相对方面才会变得重要起来[10],这体现了生存性的绝对贫困在贫困衡量与评价中的优先地位。之后,德塞尔夫又在其另一项研究中利用等贫困曲线(iso-poverty curves①一个集合,在同一条等贫困曲线上的人群绝对贫困程度相同。)形成等贫困地图(iso-poverty map②多条等贫困曲线形成的区间。),强调基于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而形成的综合指数应以等贫困地图为基础,因为等贫困地图描述的是被测人群绝对贫困的状况,这将使得综合指数更能凸显出对收入贫困的绝对方面的考量。
当然,将绝对贫困线与相对贫困线结合从而发展出分析框架与评估指数这一方法并不是测量相对收入贫困的唯一进路,另辟蹊径并取得良好成效的是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团队的研究。拉瓦雷等人采用了与以上学者不同的方法来构建相对收入比较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应用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人们在评估自己相对于他人的收入表现时是否倾向于“上下看”,即将自己的收入进行更高水平和更低水平的相对比较。在具体计算上,拉瓦雷等人首先将相对比较(u)定义为“个人经济福利(至少部分)取决于个人相对于社会中一组比较者的情况”[11]。在相对比较中,在社会经济平稳增长的前提条件下,如果个人消费小于个人相对收入,则可以将该测量对象的境况理解为“相对剥夺”;如果个人消费大于个人相对收入,则可以将该测量对象的境况理解为“相对满足”。在此基础上,拉瓦雷等人进一步将全球贫困线定义为一条基于恒定福利水平的贫困线。作为补充,他提出了一个测定全球贫困线的要求——“福利一致性”(welfare consistency),即衡量全球相对贫困时,福利的国际比较必须锚定于一个合理的和共同的个人福利概念,以此来判断每个人的贫困状况[12]。这一观点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同。
(三)强相对贫困线的应用与创新
经合组织成员国大多采用收入平均数或中位数比例来划定相对贫困线,这一方法起源于福克斯(Fuchs)的研究。福克斯最早在研究中提出收入中位数比例的划分方法,他认为相对贫困线一般而言是平均收入或中等收入的“恒定分数”,因此美国将人均收入中位数的50%定为相对贫困线[13]。欧盟社会指标小组(Sub-Group on Social Indicators)建议将收入贫困作为欧盟成员国共同的主要贫困指标,原因在于“它提供了一条便于跨国比较的贫困线”。据此,欧盟将地区收入中位数的60%作为相对贫困线[14],并且确保贫困线与实际收入增长同步上升。
这种依照收入中位数比例制定的相对贫困线被拉瓦雷等人界定为“强相对贫困线”(strongly relative lines)[15]。强相对贫困线通常以一个数值自定义的常数来表达相对贫困群体收入的比较对象(比较对象包括人均收入中位数、地区收入中位数等),用固定百分数来划定比较对象在相对收入对比中的水平。例如,在福克斯采用的“强相对贫困线”中,数值自定义的常数(或称相对收入的“比较对象”)是人均收入中位数,固定百分数为50%。
以“强相对贫困线”为基础,迪恩·乔利夫(Dean Jolliffe)和埃斯彭·比尔·普里德兹(Espen Beer Prydz)进一步创新了相对贫困线的划定思路。他们在研究中使用了覆盖107个国家的699个“国家贫困线”的样本,提出了一条“社会贫困线”(societal poverty line,SPL)用以衡量相对贫困。在他们看来,国家贫困线通常反映了社会对满足基本需求和以最低限度参与社会之成本的看法,因此,他们在研究中假设许多国家的贫困线都具有此种意涵。部分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参数化了社会贫困线和国家贫困线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社会贫困线是根据最低需求成本和社会参与成本的平均水平评估而来的。具体而言,“社会贫困线”是一个区间,区间下限为国际绝对贫困线(从2005年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25美元到2015年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9美元[16]),区间上限为国民人均消费中位数的50%,公式表达为:SPL=max($1.90,$1.00+国民人均消费中位数的50%)[17]。按照乔利夫和普里德兹的解释,50%这一比例为社会贫困线赋予一个相对要素,即随着人均消费水平的增加,社会贫困线的上限也在不断上升,这反映了社会参与的成本随经济发展而增长。可见,社会贫困线在衡量相对贫困时具备以下优势:其区间上限更符合国家贫困线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其区间下限能使得社会贫困线更好地与定义极端贫困的国际贫困线相协调。
“强相对贫困线”丰富了相对贫困研究的理论成果,并且成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但其测算流程的科学性以及测算结果的准确性却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拉瓦雷等人认为这种“强相对贫困线”违反了贫困的直观单调性定理(intuitive monotonicity axiom):如果所有人的收入都增加(减少)相同的比例,那么总体贫困衡量标准必须下降(上升)。但是,在“强相对贫困线”的测量方法下,所有人收入的等比例增加会使贫困率保持不变[18]。甚至还有学者对以相对收入来识别与划定相对贫困的方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例如,德菲纳(DeFina)和塔纳瓦拉(Thanawala)指出,收入贫困无法与相对贫困中的其他现象相关联,因为“无论如何衡量,都不一定与反对剥夺或社会排斥的进展有关”[19]。
尽管学界对相对收入测算方法还存在上述质疑,但总体而言,该方法因其贫困线的直观性和数据获取的简易性,为相对贫困的识别和测量工作带来了诸多便利。此外,以“强相对贫困线”方法作为划线依据的国家都对本国居民收入情况进行了考量,无论对收入中位数采用50%还是60%的比重,都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在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工作中,该方法也能够为政府识别相对贫困群体提供明确的理论标准,政府能够针对“强相对贫困线”之下的人群进行更为精准的施策。在理论特点方面,相对收入测算方法也将“相对性”体现得较为明显,将整个国民收入纳入考量的特点使之具备一定的理论说服力和现实操作性。也正是由于以上优势,以相对收入作为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几乎已经成为西欧国家的主流,西欧各国只是在数据设定的细节上存在着差异。
三、多维贫困视角:相对贫困的综合性讨论
将各种维度聚合为一个总体变量(例如相对收入)来衡量相对贫困的方法被视为一维方法。在这种方法下,穷人群体的范围是根据一个单一的临界值来确定的,总体贫困状况也是根据一个一维指标来进行评估。一维方法在一些学者看来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因为在使用该方法时,一维指标“识别通常通过设置一条对应于该指标的最低水平的贫困线来进行”[20],这样只能反映有多少人口处于贫困线之下,而不能反映这些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如何。一维方法有其局限,而现实中相对贫困的识别与衡量却又十分复杂,这引起了学者们的反思:在单维聚合变量不能被合理地构造、反而存在几个不同但又同等重要的贫困衡量维度时,我们应该如何确定穷人群体进而衡量他们的贫困程度?随着理论的更新和技术水平的提升,新的衡量方法不断被提出,其中的多维方法成为众多学者确定贫困人口和衡量贫困程度的首选。
(一)多维贫困视角下的贫困定义
多维贫困视角主要源自汤森(Townsend)和森对贫困的理解和对传统衡量方法的反思与改进。在汤森看来,贫困是一种相对剥夺——在社会中常见或习惯的饮食、便利设施、标准、服务和活动的缺乏或不足,并且生活必需品的范畴也并不是固定的,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改变[21]。
森在其研究中形成了可行能力剥夺理论,他认为,贫困不应该用收入或主要商品来定义,而应根据各人选择自己生活的能力来定义[22]。由于贫困是因人们缺乏可行能力而造成的,这些可行能力包括获得食品、衣着、居住等各种功能性活动的能力,因此他认为需要构建多维指标来测量贫困,这些指标需要包括可行能力提到的食物、饮用水、卫生设施、健康保健、住房等[3]。传统的贫困衡量方式只是通过计算人口统计比率(Head Count ratio)和收入差距比(income-gap ratio)这两种变量来完成贫困衡量工作。对此,森认为,这两种变量加起来并不能充分捕捉贫困现象,因为合理的贫困衡量方法必须对穷人群体的收入分配十分敏感[23]。于是,森提出了一个贫困度量公式:P=H{I+( 1 -I)G}。该公式反映了人口统计比率(H)、收入差距比(I)与穷人之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G)之间的函数关系[3]。
(二)双阈值法及其变式与创新
继森的研究之后,其他学者对于如何选择和确定多维贫困衡量体系中的维度、通过何种方法加以计算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研究。总体而言,多维贫困衡量方法的核心理念就是在已搭建好的多维指标评价体系中测量特定群体是否存在多个指标的阈值不足,来判断该群体是否处于多维贫困境况,以及判断该群体多维贫困程度的深浅。
萨比娜·阿尔凯尔(Sabina Alkire)和詹姆斯·福斯特(James Foster)基于森的可行能力剥夺理论而提出的双阈值法(又称AF法),是被应用得最广泛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双阈值法的第一个阈值用来确定谁在哪些维度上被剥夺,第二个阈值从多维角度综合评价一个人是否贫穷或被剥夺。换言之,该方法对每个维度内的贫困指标都设定了贫困阈值,通过测试被测对象的指标贫困情况来确定各个维度分别有哪些人被剥夺。同时,该方法还设定了贫困的多维度阈值来判断跨维度之下一个人是否贫穷或是否被剥夺。运用双阈值法测试相对贫困时,首先,需要根据个人或家庭的数据构造剥夺矩阵;其次,对各相对贫困指标进行赋权;再次,根据贫困临界值识别个人或家庭是否处于贫困状态,得出剥夺矩阵;最后,得出个体是否处于贫困状态,求取剥夺计数函数以及相对贫困指数[24]。双阈值法的优势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该方法能够同时将离散型的定性数据和连续型的定量数据纳入计算模型进行测量;其二是该方法具有很强的应用弹性,能够将维度、指标、临界值等关键要件留给使用者,使其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和设定。从功能上来看,双阈值法既可以显示不同区域、种族、人群内部的贫困构成,也可以显示哪些类型的贫困助长了群体内的贫困现象,同时还可以监测特定地区或特定群体的贫困变化。
卡梅洛·加西亚·佩雷斯(Carmelo Garcıia-Perez)等西班牙经济学家对双阈值法进行了测量方法上的创新。他们提出了一种通过结合贫困的相对方面来建立阈值标准的方法,这一方法有三个主要步骤:贫困维度的选择;在每个维度上确定穷人、确定多维贫困群体和非穷人的区分标准;通过贫穷指数来汇总信息[25]。在双阈值法的第一个阈值界限中,如果测量对象在某个维度内达到标准的指标数量少于该维度设立的指标剥夺阈值,那测量对象在这个维度上就可以被认定为“被剥夺”。双阈值法的第二个阈值界限基于一个人被剥夺维度的加权(PM),这是一个新的变量,该变量可以根据每个人的被剥夺维度加权将其划分为多维贫困或不贫困:如果PM值大于等于贫困阈值,则测量对象是多维贫困的;如果PM值小于等于贫困阈值,则测量对象不处于多维贫困境况中。
除了双阈值法及其变式,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其他衡量相对贫困的方法。例如,阿尔凯尔等人提出了一种用以衡量长期性多维贫困(chronic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的方法,既可以测量每个时间段的多维贫困,也可以测量跨时间段的持续性多维贫困。该方法主要分为三个步骤:首先,确定被剥夺的指标和阈值界限;其次,将各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计算每个人的评分,并确定多维贫困或非贫困的时期;最后,计算每个人经历的多维贫困时期[26]。依据这三个步骤,阿尔凯尔等人使用了教育、住房和就业/收入这三个权重相等的维度,每个维度下都设立了不同的指标以搭建指标体系。
(三)多维贫困方法的现实应用
综合上述各个学者的研究来看,采用多维贫困视角来审视相对贫困人口的广度以及相对贫困程度的深度是较为全面且科学的,因为每个多维贫困评价体系的指标都可以根据各国或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和调整,也可以通过对各个指标分别赋予大小不同的权重来体现它们在重要性方面的不同地位,这为不同国家基于自身国情调整相对贫困测量手段提供了较大的自主空间。多维贫困视角下的双阈值法及其变式,也直观地以公式形式呈现出了相对贫困群体的各方面状况。
正是因为多维贫困方法具有贫困衡量维度的全面性和实际操作的可行性,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的相对贫困治理实践之中,在衡量全球和地区多维意义上的相对贫困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OPHI)联合开发的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就设立了健康、教育、生活水平三个维度,在各维度下分别设立了不同的指标,每个指标都有着相对应的阈值以及权重,这样的指标共有10个[27]。
四、增长性贫困视角: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分析
如果说收入贫困、多维贫困两个研究视角关注的问题是“什么造成了贫困”,那么增长性贫困视角则将关注点转向了另一个宏观问题上,即“经济增长是否有助于减少相对贫困”。前两个视角的思维逻辑是原因导向,增长性贫困视角的思维逻辑是结果导向。在相对贫困层面,增长性贫困存在于一个吊诡的现象之中:许多发达国家和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是其社会相对贫困率却并没有像本国绝对贫困率那样显著下降,反而不断攀升。于是,这种现象引发了学者们的思考:经济增长是否一定会带来相对贫困程度的加重?如果是,又有哪些措施能够缓解相对贫困?
(一)增长性相对贫困与“亲穷人增长”
在增长性相对贫困的研究中,学者们都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两个重要概念进行了分析,这两个概念分别是“亲穷人”(pro-poor)和“亲穷人增长”(pro-poor growth)。“亲穷人”是经济发展的一种特征;“亲穷人增长”反映了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不平等三者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将“亲穷人增长”分为“绝对的亲穷人增长”(absolute pro-poor growth)和“相对的亲穷人增长”(relative pro-poor growth)[28],前者指的是经济增长为穷人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后者指的是经济增长为穷人带来的益处多于为非穷人带来的益处,这是一种相对比较下的穷人受益情况。因此,“相对的亲穷人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不但要减少绝对贫困现象,还要避免社会分配不平等的加剧。
万广华(Guanghua Wan)等人对经济增长和不平等的关系作了深刻分析,以此来探讨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他们在研究中指出,与绝对贫困的情况相反,经济增长实际上引发了中国相对贫困的上升趋势。对减缓相对贫困而言,中国在改变扶贫战略的同时,不能再依赖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来减少相对贫困。相反,需要关注收入不平等问题,制定由政府主导的“亲穷人”政策体系。并且,除了常见的社会援助手段之外,还应向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教育、培训和其他机会[29]。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森的观点形成了呼应。森对贫困问题持“可行能力剥夺理论”,因此他的贫困研究更多地关注穷人的参与,他将“亲穷人增长”定义为“穷人可以通过积极参与经济活动而且能够显著受益的增长”[30]。
克拉森(Klasen)认为,“亲穷人增长”意味着穷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增长[31]。吉恩伊夫斯·杜克洛斯(Jean-Yves Duclos)在此基础上对“亲穷人增长”概念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只有使穷人的收入按比例增长以超过相对标准,并且在经济衰退时不会导致穷人收入在绝对意义上的下降,这样的经济增长才能被视为是“亲穷人增长”[32]。从杜克洛斯的定义来看,单纯以“经济增长是否带来了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或者比例的下降”作为“亲穷人增长”的评判标准是不科学的。按照他对“亲穷人增长”的定义,我们可以推断,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缓解相对贫困问题,除了要保障相对贫困群体收入的稳定性增长之外,还需要建立健全经济疲软甚至经济危机时期的相应保障机制,以减少返贫现象的发生。
(二)增长性相对贫困的衡量
奥古斯汀·夸西·福苏(Augustin Kwasi Fosu)指出,各国由于不平等程度和收入状况不同,将经济增长转化为减贫的能力因此存在重大差异[33]。为了了解经济增长对促进减贫的作用程度,国外学界对如何测量经济增长形成的减贫效果开展了相关研究。
Pen.J.提出了一个较为直接的方法——“Pen’s parade”,该方法通过关注穷人的收入增长率以评估经济增长是否有利于穷人,重要步骤是计算总人口中最贫穷的那一部分人的经济增长率[34]。这一方法成为衡量相对贫困程度的经典方法,被许多学者应用于研究之中。例如,大卫·杜拉尔(David Dollar)和阿尔特·克拉(Aart Kraay)采用了Pen的方法,通过计算最贫穷的1/5人口的平均收入增长率来检验总体经济增长是否“对穷人有利”[35]。
在这之后,一些学者提出了其他的代表性方法用以衡量增长性相对贫困。本文着重介绍以下三种方法:卡卡瓦尼(Kakwani)团队提出的“亲穷人增长指数”(pro-poor growth index)、阿尔特·克拉对穷人“平均收入增长率”和“相对收入增长率”的衡量,以及索恩(Son)提出的“贫困增长曲线”(Poverty Growth Curve)。
卡卡瓦尼等学者使用“贫困等效增长率”(poverty equivalent growth rate,PEGR)来衡量“亲穷人增长”。他们设计的这个测量指数不仅将经济增长率纳入了考量范畴,还关注了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受益程度。在具体测量增长性相对贫困时,“等效贫困增长率”指数通过计算“贫困的增长弹性”(the growth elasticity of poverty)而得。“贫困的增长弹性”指的是,当社会平均收入增加1%、收入分布保持不变时,社会贫困发生率的变化情况[28]。如果“等效贫困增长率”的数值高于经济增长率,那么增长将被假定为有利于减贫的。并且,“等效贫困增长率”的数值越高,则说明经济增长带来的减贫程度就越大。可见,“等效贫困增长率”指数体现了贫困现象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其一是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越高,就越能够为大规模减贫提供有利条件;其二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变化,因为不公平的收入分配会增加社会的贫富差距,使贫困群体在规模逐渐扩大的同时,贫困程度还在持续地加深。这两个关联因素也为人们开展增长性相对贫困的治理提供了实践方向。
阿尔特·克拉应用标准的贫困分解技术确定了“亲穷人增长”的三个动力:平均收入的高增长率、贫困对平均收入增长的高敏感性、相对收入增长的减贫模式。其中,平均收入的高增长率和相对收入增长的减贫模式在克拉的研究中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两个动力来源,因而她主要讨论了二者的衡量方法。平均收入增长率用家庭平均收入或消费的平均年增长率来衡量;相对收入增长率用“基尼系数(Gini index)的年均比例变化”和“贫困人口数量变化的离散时间分布”来衡量。经过分析后,克拉得出结论:从中长期来看,重视相对收入增长以及平均收入增长的减贫模式,二者对于缓解相对贫困非常重要[36]。克拉的研究提醒我们,平均收入与相对收入二者随经济的同步增长,能够有效地治理由经济增长带来的相对贫困问题。
借鉴Pen的理念,索恩利用“穷人平均收入增长率”与“穷人占比”这两个变量构建坐标轴,提出了“贫困增长曲线”。在坐标轴中,横轴标识0到100%,用以表示“穷人占总人口的比重(p,p<100%)”;纵轴表示“穷人平均收入增长率[g(p)]”。然后,按数据刻画曲线,就可以得出一个社会的“贫困增长曲线”。如果g(p)大于p的平均增长率,就说明此时的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是“亲穷人增长”;如果g(p)为正数,但小于p的平均增长率,那么此时的经济增长减少了贫困,但不平等程度加深;如果g(p)是负数,那么此时的经济增长会引起严重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问题[37]。
结合上述既有研究不难发现,经济增长是否会带来相对贫困程度的加深,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测量与验证的问题。换言之,不能因为大部分情况下经济增长都有利于贫困人口生活条件的相对改善,而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增长也必然会缓解相对贫困。正如萨米·毕比(Sami Bibi)等人所指出的,“虽然收入的正增长通常会增加穷人的绝对收入,但对他们在总收入中的相对份额并没有系统性的影响”[38]。相对贫困往往与不平等相挂钩,在不平等的分配格局下,经济增长并不能给贫困群体带来普遍性的福利,反而会拉大社会不同阶层的收入鸿沟。通过对上述研究进行归纳,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增长影响相对贫困的程度受到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例如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制度、经济增长的类型、经济发展的质量、市场机制以及穷人参与经济过程的能力等。缓解增长性相对贫困并不仅仅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更多的是要求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重视质量、在收入分配中重视公平、在社会保障中重视相对贫困群体再生产能力的培养。
五、主观贫困视角:相对贫困的心理学观照
相对贫困不仅可以通过财富和收入来衡量,还可以通过贫困群体的主观感受来衡量。前文提到的三个研究视角,关注点皆为相对贫困群体所面临的客观境况,而忽视了这类人群的主观心理动态。主观贫困视角下的研究则有效地填补了这一空隙,为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一)主观贫困研究的形成与发展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对18世纪欧洲工人由贫困所产生的羞耻感作了经典描述:“一件亚麻布衬衫严格来说并不是生活必需品……但在当前的欧洲大部分地区,一位声誉较好的工人如果没有一件亚麻布衬衫,那么就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因为没有这样的衬衫表明他穷到了可耻的地步。”[39]可见,摆脱贫困不仅需要摆脱物质上的匮乏状态,还需要摆脱这种主观上的贫困耻辱感。学者们对贫困与主观心理的研究便形成了贫困心理学这一交叉研究领域,贫困心理学研究的重点通常是穷人的心理结果、因果归因和人格特征。相对贫困除了物质上的劣势和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外,还包括社会和心理代价,如自尊减少、漠视和尴尬[40]。美国人类学教授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是最早展开贫困心理研究的学者之一。刘易斯认为,贫困的持续存在是穷人特定行为模式的产物,这些行为模式通过社会化过程一代一代相传递,反过来,这些价值观和行为又成为穷人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决定因素[41]。随着贫困问题逐渐成为一个愈发重要的议题,学者们更多地将贫困放在概念的主位,而心理层面的感知则被归纳进主观贫困的相关研究。斯图尔特·C.卡尔(Stuart C.Carr)对主观贫困的既有研究进行了总体性分析,他总结出了三条关于主观贫困的研究路径:探索穷人的人格特征、寻找贫困的因果属性、关注心理结果[42],这些研究路径目前仍对主观贫困研究发挥着重要影响。
此外,部分学者对已有客观贫困线的质疑也推动了主观贫困研究的发展。在部分持主观贫困视角学者的研究中,无论是按照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计算而得的绝对贫困线,还是按照国内居民收入中位数的一定比例(50%或60%)计算而得到的“强相对贫困线”,这些衡量标准的科学性都值得商榷。例如,乔达(Jodha)指出,数据可用性不足、没有定期的年度调查数据以及调查随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些都是传统的贫困衡量标准所面临的问题。同样,家庭调查准确获取收入和消费数据的能力也存在漏洞[43]。迪顿·安格斯(Deaton Angus)也认为,由于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的情况存在差异,因此采用一条客观贫困线是不妥的[44]。塔希尔·马哈茂德(Tahir Mahmood)等人则指出,贫困线是由使用标准的技术规则制定的,如收入、支出或消费,但这些贫困线都没有进行过充分的民主讨论[45]。这些独到的见解,促使研究相对贫困问题的学者们将注意力转向主观贫困,寄希望于从人们的主观贫困感知中得出主观贫困线的划定依据。
(二)主观贫困的测量方法与分类
主观贫困的测量方法主要考察被测对象的自我定位,这种自我定位是被测对象主观上对自己的收入情况、生活状况等在社区、城市乃至整个社会中所处阶层的认知或估量,以评估社会个人的福利状况和最低需求。考察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来进行,根据不同的识别方法,我们可以概括出国外主观贫困研究中的两类问卷设置方式:“收入评估问题”(Income Evaluation Question,IEQ)、“最低收入问题”(Minimum Income Question,MIQ)。
“收入评估问题”问卷关注的是主观贫困人群对于自我收入的评价。这种问卷设置方法源自伯纳德·范·普拉格(Bernard Van Praag)的研究,他提出了一个主观贫困衡量标准——将收入充足性的自我报告转化成贫困线[46]。在家庭调查中,被调查对象会被问及什么收入水平在自我看来是“非常坏的,坏的,不好,不坏,好,非常好”,通过收集这类收入水平评估,普拉格可以计算出被试群体的大致主观贫困线。塔希尔·马哈茂德团队采用这种问卷设置方式来研究巴基斯坦的主观贫困问题,他们对被调查对象所提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些人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富人),有些人有较低的经济地位(穷人)。下面是从1到10的比例。数字1到10代表了经济地位的不同水平,从最低到最高。在1—10上,请注明你所处的位置。”[45]同样,坎特里尔(Cantril)在调研中设置了一个“坎特里尔梯”(Cantril Ladder),被试群体需要根据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在所划定的梯度上找到自我评估后的定位[47]。
“最低收入问题”问卷则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人们对贫困的看法之上。以这类问卷来调查主观贫困,能够得出在人们认知中最低收入水平的标准。这种问卷设置方法源自戈德哈特(Goedhart)团队的研究。戈德哈特等学者在家庭调查中设计的问题是:“维持生计最低需要什么样的收入水平”[48]。另外,谢尔登·丹齐格尔(Sheldon Danziger)等人也成功利用“最低收入问题”问卷研究了美国的主观贫困问题。丹齐格尔团队对3160个美国家庭发放了问卷,受访者需要对“维持生活最低需要多少收入”这类问题进行选择与填写。结果显示,人们关于最低收入水平的标准,随着他们实际的平均收入的增长而增加,也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并且当时美国家庭的主观贫困线高于政府设定的客观贫困线[49]。
纵而观之,主观贫困线既可以体现为一种最低生活标准,也可以体现为一种“收支平衡”的基本生活水平,还可以体现为一种对应于社会某个阶层的经济水准。学者们对于造成主观贫困的原因也有着多种解释,这些原因客观上体现为收入/消费的相对不足、社会排斥等;主观上体现为自我阶层定位、幸福感评估、相对剥夺感知等。以主观贫困视角研究相对贫困,优势在于研究者可以从测试对象基于自身所有属性值的全方位评价中,获得其对于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政策实施效果的态度与总体评价。这也使得主观贫困研究打开了相对贫困研究的另一扇方法之门,成为客观相对贫困研究的有益补充。
不过,虽然对于主观贫困的研究确实能够为识别和缓解相对贫困提供方向性启发,但是过于强调主观因素在相对贫困中的重要性也会令这类研究陷入窘况。例如,以主观贫困视角来分析相对贫困,很容易得出一个较为矛盾的结论:客观上不贫穷的人可能会感到贫穷,而客观上贫穷的人则可能不会感到贫穷。而在这种可能存在的现实情境里,依据主观贫困视角来认定相对贫困群体就可能与人们对于贫困的普遍认知相悖,这容易导致贫困治理工作收效甚微。此外,由于主观贫困方法带有极强的主观性色彩,主观贫困研究也面临着一些方法论层面的问题,如被试群体的错误回答、问题解释的随机差异、受访者情绪和偏好(品味和个性)的特殊差异等,这些不确定性因素都可能给研究结论带来颠覆性的偏差。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以研究视角为依据将海外代表性研究分为四类:相对收入贫困视角、多维贫困视角、增长性贫困视角与主观贫困视角。相对收入贫困视角下采用的收入中位数百分比(或称为“强相对贫困线”)方法是一种衡量相对贫困的一维方法,其优点在于简单直观,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实用性,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承袭了此前学界以“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收入水平”来衡量绝对贫困的基本方法。然而,相对收入贫困视角也受到了广泛质疑,原因在于它只能反映收入层面上的相对不足,而现实的问题是,相对贫困的致贫原因并不局限于收入层面,其他经济和社会要素的匮乏对于贫困群体的处境也有显著的消极作用。
多维贫困视角克服了相对收入视角的单一性弊端,其核心理念是将致贫原因指标化,并搭建一个多维贫困的评价体系,将测量对象的生活、经济、教育、健康、能力、社会参与等状况嵌入评价体系中。多维贫困视角的代表性方法是阿尔凯尔和福斯特提出的双阈值法(AF法),具体存在两种不同的阈值界限,分别测量各维度内的贫困指标和跨维度下的相对贫困。以双阈值法为基础,学界还进行了测量方法的改进与创新,增强了多维贫困测量的科学性与全面性。由此,多维贫困视角凭借指标选择、权重赋予、体系搭建、样本嵌入等程序成为测量相对贫困的主流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全球的贫困测量与治理实践中。
增长性贫困视角关注经济增长能否缓解相对贫困。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是减贫的有利条件,但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增长会自动带来相对贫困的缓解。受分配制度、经济增长类型、经济发展质量、市场机制健全程度以及穷人参与经济过程的能力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对“经济增长能否缓解相对贫困”这一问题而言,需要视不同情况具体分析。对这些影响因素的考察也为海外学界探讨如何缓解相对贫困提供了新的方向,也就是更多地关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
主观贫困视角展现了贫困心理学对贫困人口心理动态变化的关注。这类研究主要考察相对贫困群体关于自我与他人在收入、消费、福利待遇等方面差异的主观感知,或是该群体在不同范围内的自我阶层定位。通过收集以上数据资料,学者们能够划定特定群体范围内大致的主观贫困线,并且对被测群体的致贫原因作出归纳。
上述四种研究视角都从不同侧面回答了相对贫困研究的一系列核心子问题——相对贫困的内涵、致贫原因、测量方法、贫困线划定依据,极大丰富了相对贫困研究领域的学术观点、增加了该领域的知识积累。然而目前海外学界对相对贫困的研究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相对收入贫困、多维贫困、增长性贫困与主观贫困视角中的每一个视角都提供了一种相较于其他三者而言不同的相对贫困研究进路,但这些视角并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相互替代的关系。原因在于,每一种研究视角都有其合理成分,其不同的侧重点展现了其独到的研究切入点,学者们依据各种视角特有的分析逻辑能够对相对贫困问题展开相应论述,得出的结论也有助于推动相对贫困的治理进程。但是,囿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单个视角下进行的研究或多或少存在着论证“空隙”,甚至其结论的科学性也会遭到其他学者的质疑。这提醒我们,面对复杂的相对贫困问题,不应将这些分析视角割裂开来,而是应该综合各类研究视角之所长,提供在同一情境下对于相对贫困的完整理论解释,从而搭建一套更具包容性和有效性的解释框架,以填补单视角下论证的局限。
其次,国别差异是相对贫困治理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但目前部分研究追求的更多是一种统一性、普适性,即寄希望于找出一条可以衡量全球或大范围地区(例如欧盟、东亚等)的相对贫困线。可是,即便在欧盟这类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各成员国的相对贫困状况也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各成员国采用的主要是“强相对贫困线”,但在收入中位数的比例设定上仍有着明显区别。因此,在理论研究和方法创新上可以尝试着归类总结,但在实际的衡量与治理上则需要视各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而定。实际上,海外学界已经有学者针对单个国家或小范围地区开展相对贫困研究。例如埃林·博格拉亚斯(Elling Borgeraas)等人对挪威三种不同的“贫困”衡量标准进行了比较研究[50]。这种立足于具体国情的国别研究取向或将是今后相对贫困治理研究的重要方向。
最后,对于一些特定贫困概念和新近出现的学术议题,既有研究还缺乏充分讨论。相对贫困的致贫原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不限于上述四种主要研究视角所归纳的主客观因素,至于其他原因,我们可以通过界定相对贫困的其他类别加以分析。例如,流动性相对贫困是由政策性移民搬迁、城乡人口流动、跨地区人口流动等原因导致的移民群体的相对贫困,表现为移民群体在文化融入、权利享有、福利保障等方面的相对困难。此外,还有更为宏观的政策性相对贫困、结构性相对贫困等,这些类型的相对贫困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当前我国的贫困治理事业正处于过渡阶段。在推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我国需要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在稳中求进、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不断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制度建设,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相对贫困治理模式。国内学界研究我国相对贫困问题时需要批判性地学习和反思海外研究成果,既关注国际组织与发达国家在相对贫困治理上的共性经验,也要立足于我国实际,提出契合我国相对贫困实际情况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建议。有鉴于此,结合上述四种相对贫困研究视角,国内学界的后续研究或许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我国相对贫困内涵的区域差异性问题、相对贫困线的划定与调整依据、相对贫困人口的动态监测,以及我国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等问题,并且研究这些问题的关键路径在于对地域、城乡之间不同人群生活水平进行整体性研判。
根据有关统计,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2.56[51],这说明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存在显著差距,农村地区依然是相对贫困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如果按收入五等份分组,20%高收入户与20%低收入户的倍差,在我国全体居民当中为10.2,在全国城镇居民中为6.2,在全国农村居民中为8.2[51]。由此可见,我国至少在城乡之间、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对贫困问题。
科学测量和精准识别相对贫困人口,是中国开展相对贫困治理的根本前提。只有解决了测量和识别问题,才能精准绘制我国相对贫困人口的地理空间和群体空间分布图,并对相对贫困人口进行动态监测,从而为科学制定相对贫困治理政策和创新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科学理论依据。就如何测量和识别相对贫困群体而言,通过系统梳理海外学界的研究传统与前沿动态,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首先,收入水平依然是我国测量相对贫困的核心指标,以地区收入中位数的特定百分比(比如40%—60%)科学划定我国的相对收入贫困线,有助于对我国相对贫困人口的总体规模和空间、群体分布进行动态监测,从而为制定宏观性、区域性相对贫困治理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其次,家庭主要劳动力的教育年限与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家庭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具有根本性影响,因而也是测量和识别相对贫困人口的关键标准,治理相对贫困的一条重要路径就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最后,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社会排斥,也会加深相对贫困状况,科学测量我国相对贫困人群的社会参与度,有助于从社会融合的角度来识别相对贫困。
以上这三点启示,对于我国开展相对贫困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在制定相对贫困治理方案时,一方面可以借鉴多维度测量方法,从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社会参与等多个角度设置相对贫困阈值,并赋予不同阈值差异化的权重;另一方面也需要将相对贫困治理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相结合。具体而言,需要加强脱贫人口、返贫人口的动态监测工作,精准测量和识别相对贫困人口,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以打破城乡壁垒,消除我国城乡之间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社会排斥,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准治理相对贫困和推动乡村振兴同向前进。以上分析表明,系统梳理海外相对贫困研究的学术谱系与前沿动态,中肯评述不同视角下所采用的相对贫困测量方法与治理方案,对推动我国相对贫困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